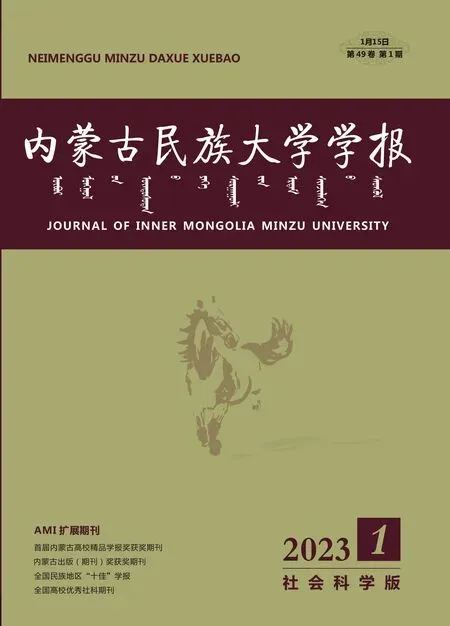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高度统一
——谈司马迁《史记》的写作艺术
2023-08-06于景祥
于景祥,韩 伟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司马迁的《史记》,无论是在史学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都达到了巅峰状态。如果以文史结合的方式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它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就历史的真实而言,它求实考信,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录;就艺术的真实而言,它善于在典型的历史环境中,塑造出高度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既源于历史,又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再现。
一、追求历史的真实
从史学角度看,司马迁的确是良史之才,这一点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也是他成为史学一代宗师的内在因素。所谓“良史”,自先秦以来主要是指在记述史实和修史之时坚持实录直书的原则,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正像刘知几《史通·外篇·惑经第四》所说的那样:“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409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虽然说司马迁在作《史记》之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可是他又不能不承认“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2737—2738。班固不仅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材”,而且还说明其“良史”的具体表现,即“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这种“实录”精神,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本点在于追求历史的真实。在《史记》一书中,这种“实录”精神和求真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求实考信和“不虚美,不隐恶”。
其一,求实考信是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因为对他所生活的汉朝,好多事情耳闻目睹,即使没有耳闻目睹,也可以间接了解,容易把握其真实性,而汉以前以至于上古之事,年代久远,要做到真实客观,必须通过求实考信,方能达到或接近客观真实。为此,司马迁深入实地,认真进行调查和考核。《太史公自序》说他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3]3293《魏公子列传》说:“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3]2385《樊郦滕灌列传》中又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3]2673《孟尝君列传》中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3]2363《屈原贾生列传》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3]2503《魏世家》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3]1864司马迁当郎中之时,“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3]3293,又有了机会,对我国的大西南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为太史令后,经常跟随汉武帝去各地“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3]1404。各地的社会风俗、山川地理、河流水利都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如《五帝本纪》就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3]1415这样深入实地考察核实,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客观、真实的依据,所以顾炎武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4]同时,也正是靠这种实地考察,重视向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访问请教,更弥补或者纠正了旧有史料的许多缺失,修正了旧时记载、传闻的不少问题,其中有关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被杀一事的重要材料,就是考察访问所得:“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3]1833。此外,他还通过与西汉名将卫青直接共过事的人,深入了解这位威震天下大将军的为人处世之道:“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无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3]2946,所以正是这种求实考信的精神使《史记》一书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性。
其二,“不虚美,不隐恶”的直书实录是司马迁修史特别是修本朝历史的重要原则。例如对刘邦的功过是非,司马迁就采取“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一方面客观地指出他的功绩:“子羽暴虐,汉行动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唯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3]3301书中正是根据这个精神写了刘邦由起事反秦、楚汉相争、统一国家、建号称帝的全过程,确实符合历史实际,不是“虚美”。另一方面,对刘邦的缺点,司马迁也如实反映,不为尊者讳。在《项羽本纪》中,作者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刘邦的怯懦、卑琐和无能,而其中有两个片段非常真实地描绘出刘邦丑陋的一面: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3]322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3]328
通过这两则刻画描写,真实地再现出刘邦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除此之外,在《留侯世家》中,作者又写刘邦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中,还写到刘邦猜忌功臣;而在《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之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恶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3]2627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严酷事实。可见,作者确实做到了“不隐恶”。再如项羽,作者一方面肯定、赞扬他的功绩:“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3]338—339另一方面又客观地批评了他的过失:“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3]339,由此便揭示出他必然失败的内在原因。其他如李广,这本来是司马迁非常喜欢、赞赏并为之鸣不平的人物,但是在书中,他还是坚持实录直书的原则,优点缺点一并写出。首先,《李将军列传》中客观真实地写出他的优良品格:“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3]2872又以“太史公曰”的形式直接评论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3]2878在这由衷的颂歌与赞美的同时,也没有掩饰李广的缺点,所以在列传的正文中描述李广“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3]2874,客观写出他有时也很好杀。此外又写李广家居之时,尝因犯夜被霸陵尉拘留,等到他又被召为右北平太守时,“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3]2871,反映出这位“飞将军”有时小肚鸡肠、官报私仇的缺点。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求真的态度还表现在客观真实地记录和反映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对此进行了生动的反映:“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虽然这些造反行为被统治者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3]3151。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官逼民反”的社会现象。同时,司马迁正是基于实录直书的原则,对秦末农民起义,也进行了真实的反映,并且用历史家的眼光给予客观的评价。他在《陈涉世家》里,不仅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而且还对其失败的基本原因也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这次起义的正义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了陈涉等人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3]3310—3311,并且破天荒地把这一出身如此低微的农民领袖安排在“世家”之中,这是其他封建正统史家难以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中客观地记载和描述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游侠、刺客等下层人物,也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表现。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称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焉。”[3]3181又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闲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3]3182—3183显然,作者认为游侠有其存在的价值,不但没有“退处士”之义,而且肯定游侠“不轨于正义”有其可贵之处,与当时统治者对游侠的贬抑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司马迁对统治者的所谓仁义,明显是很有微词:“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向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峤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与此相反,他认为游侠的行为是真正仁义之举:“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3]3318很明显,他对当时统治者提倡的虚假的儒家仁义道德之类表现出蔑视的态度。
由于《史记》采取这种直书实录的原则,这就使得它的思想观念远远超出当时“独尊儒术”的藩篱,“其是非颇谬于圣人”[2]2737—2738,然而其科学性、进步性恰恰就在这里。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在《藏书》卷四〇《司马迁传》中说得比较透彻:“班氏父子讥司马迁之言也。班氏以此为真足以讥迁也,当也,不知适足以彰迁之不朽而已。使迁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以为迁乎?则此史固不待作也。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5]
其实,司马迁的良史之才还不仅表现在求实考信的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这两方面,对正史体例、范式的创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作者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2]2735,即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讨古今历史变化的原因。为此,他集先秦史学之大成,以超凡的能力,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历史时空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事件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创建了以纪传为主,书、表形式兼备的史学体例,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主要是两种体例:一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体例,这包括按帝王的世代顺序记叙的政治、军事等天下大事的“本纪”,叙述先秦各诸侯国和汉朝享有封土的功臣贵戚们的国别史与家族史的“世家”;记叙立功名于天下的英雄人物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以及与华夏民族相互依存的兄弟民族的特殊人物的“列传”。二是以事为纲的叙事体例,其中包括排比、并列历代帝王和诸侯国政治、军事大事的“表”,关于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专门论述的“书”。正是这五种不同的体例,互相配合补充,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整体结构,确立了中国古代正史的基本范式,代表了我国历史上史学的最高成就。
二、通过典型的历史环境塑造出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史传散文的巨著,它以人物为中心,开创了纪传体散文体制,因而其成就最突出之处也自然体现在人物的描写上面。换句话说,《史记》作为纪传体史书,它本身这种特殊体例为成功地描写和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首先,《史记》的主体“本纪”“世家”“列传”以人物为中心,从纵横两个方面,真实地再现了典型历史环境下的人物形象。从总体上看,宏大的历史背景,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从个体上看,具体人物的历史活动和个人命运;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对人物思想、个性、品格的影响;个人的经历、身份、气质、教养、行为方式对历史事件乃至个人命运的影响等等都得到近乎全景式的展现。同时,因为各类人物的历史作用各有不同,这些传记的历史容量和叙述重点也大不一样。
其一,就“本纪”而言,《史记》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是特别成功的,可以这样说:本书通过描写项羽、刘邦的一生,反映秦汉之际的历史演变甚至可以说是由个人写出了一个时代,特别项羽的形象描写与塑造更为精彩。书中在表现这个人物时,确实是通过典型的历史环境,集中于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这三件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事件,来展现他传奇式人物的特殊风采与特殊品格。钜鹿之战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陈胜、吴广兵败,项梁失利身死,轰轰烈烈的起义军处于劣势,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是在这种危急情况之下,项羽率领楚军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以一当十,连胜九阵,把兵骄气盛的秦军主力打得落花流水,一举造成暴秦灭亡的定局。作者正是通过这样典型的历史环境的描写和刻画,展现出项羽过人的胆略、超常的斗志,一个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鸿门之宴揭开楚汉之争的序幕,是项羽一生事业和整个生命的转折点。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刘邦与项羽的行为与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刘邦本处劣势,如同板上鱼肉,听凭项羽宰割;但是他在张良等人的协助下,收买了项伯,麻痹住了项羽,挫败了范增,最终化险为夷,表现出随机应变、老谋深算的特点;而项羽则被动消极、盲目自大,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隐患,最后放虎归山,显示出粗疏无谋、优柔寡断、严重缺乏政治斗争头脑的一面,从而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垓下之围着重描写陷于四面楚歌绝境之中的项羽,进一步展示这位末路英雄的性格与心理特征,一方面写他在穷途末路之时不失英雄本色,宁死不过江东,他对乌江亭长说:“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3]336同时又写出他经不起失败,还自负为英雄,说什么“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3]339,拒绝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至死仍然执迷不悟。通过这三个环节,不仅生动描述出秦朝末年历史发展演变的主要过程,而且更从各个方面展现出项羽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与性格,使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完整。
其二,就世家而言,也是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着重按历史发展的顺序,通过典型的历史环境描写,特别是历史事件和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的思想与性格,并且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如《陈涉世家》《留侯世家》等等,在人物描写上都十分精彩。《陈涉世家》开头便描写陈涉“佣耕”之时便有大志,抱负非凡,生动鲜活:“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3]1949然后又通过“举大计”的实际行动展示其谋略与智慧:“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3]1950此外,作者还通过语言、行动相互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刻画人物:“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3]1952,从而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便生动鲜活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其三,作为帝王大事记的本纪和诸侯史的世家,在人物描写、形象塑造之时,有时自然要顾及历史的发展顺序,不少历史事件的原委不能不有所交代。这样,在有些情况下,人物描写容易被冲淡,但是列传相比之下则自由得多,更方便于在典型的历史环境之下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具体说来就是:其材料取舍、详略处理以及时空转换都可以灵活安排,所以便于集中笔墨,突出中心,加深主题,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这方面,《李将军列传》就是典型。李广是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匈奴人称之为“汉之飞将军”[3]2871;他从军五十年,“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3]2876,英勇善战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为了表现这一点,《史记》精心选材、科学提炼,集中描写了三件事,虽然这三件事在历史上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在表现李广英勇善战这一点上则十分有力:第一件事情发生在汉景帝之时,有一天李广率百骑追逐匈奴射雕者,但是突然与匈奴数千骑遭遇,敌众我寡,形势严峻,他的部下都非常害怕,掉转马头想要逃跑,李广却从容镇定,他抓住敌人把他们当作“诱骑”的心理,反而向前靠近敌阵,下马解鞍,让手下纵马而卧,进一步加深敌人的疑惧。同时,他还亲率十余骑,射杀匈奴出阵的白马将,从容往返,毫无惧色。这样,匈奴骑士更生疑惧,怕遇伏兵,连夜撤退,于是李广等人脱险。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遭遇战,显示出李广智勇双全的名将本色。第二件事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在“出雁门,击匈奴”的战斗中,李广不幸负伤被俘,躺在匈奴骑士用绳索做成的网兜上,开始之时,“广佯死”,麻痹敌人,但是后来他看准一次机会,趁其不备,一跃而起,跳上旁边胡儿的坐骑,夺过弓箭,且走且射,最后摆脱数百胡骑的追击,南驰数十里,死里逃生,回到汉营。这一次虎口脱险,突出表现了李广的机智。第三件事发生在汉武帝元狩二年,这次李广率领的四千人遭到匈奴左贤王四万骑的包围。从实力上说,他们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李广无所畏惧,从容对敌。他先派儿子李敢率领数十骑先行冲击,突入敌阵,一进一出而还,以此表明敌人可以对付,并不可怕,这样便安定了军心,接着他“圜阵外向”,用弓箭挡住敌人的四面围攻。当时敌人箭如雨下,他手下的士兵也死伤过半,吏士皆无人色,汉军的箭也将用尽,但是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之下,李广却始终镇定自若,挽强弓专射匈奴的副将,杀数人,坚持到第二天援军到来,力战解围。此次战斗,转危为安,突出展现了李广的勇敢。在大小七十余战中,作者专门选出这三次众寡悬殊、敌强我弱、形势极为不利的战斗,从而表现出李广非凡的机智勇敢和超人的胆略,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而这种效果的取得主要依赖于作者善于选材与精心构思。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又不仅仅重视单个人,又创立了人物合传与类传。集中展现了某一阶级、某一阶层、某一行业的人物群像,因此历史人物的共性和个性都得到重视,都得到充分展现。如《刺客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等等,都是如此。还有,《史记》有近百篇人物传记,有一人专传,有两三个人合传。有的如《酷吏列传》是十人的类传,这样便出现一个问题:平行的人物各传在记叙同一事件时,非常容易交叉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不得不在叙及某人某事时,常以“事在某传”加以避免,这便是《史记》创造的“互见法”,即把历史事件或人物生平分散在各个篇章当中,有详有略,参差互见,既相互规避,又彼此补充。这样既保持主题集中,中心突出,首尾完整,又相互照应,避免重复与累赘。如高祖、张良、樊哙诸纪传中,都涉及“鸿门宴”一事,但都是一带而过,略略提及,而在《项羽本纪》之中则集中笔墨,不但情节完整,而且叙述详尽,既对其他各传有所补充,又不重复累赘。其他如《吕后本纪》完完整整地叙述事情本末,而在孝文帝本纪、陈平、周勃世家略有说明,相互补充,所以主次分明,重点突出。
三、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高度统一
《史记》从史的角度为“史家之绝唱”,但是从文学的角度又是“无韵之《离骚》”,是文情并茂的大作。那么,司马迁是怎样处理良史的实录原则和文学的艺术想象、史学家的理性精神和个人的情感爱憎倾向性等问题的呢?
关于史学的实录原则和文学的艺术想象,《史记》真正做到了二者相互统一,其实,也就是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其做法主要是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基础之上对某些情节、细节等等做无损于历史真实的补充,因而使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更突出、更完整、更有典型性。如《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都写了这样的情节:刘邦、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时,目睹这位“始皇帝”的赫赫威仪,都生羡慕之情,刘邦的反应是“大丈夫当如是也”[3]344,项羽的反应则是“彼可取而代也”[3]296。从刘、项两个历史人物的总体活动来说,这样的情节和细节很可能得自传闻或虚构,但是又不违反历史的真实性,而且恰恰通过这样的情节与细节更深刻地表现出二者性格气质上的巨大差别,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史学的科学性与文学的艺术性得到完美的统一,关于史学的理性精神和个人的情感爱憎倾向性问题《史记》一书处理得也很适当。从实而论,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有明显的爱憎倾向的,如《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倾注了司马迁出自肺腑的同情与爱戴,尤其是《李将军列传》更是如此。书中他满腔热情、满怀敬意地赞扬了李广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干,《太史公自序》中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作《李将军列传》。”[3]3316传中又写他“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在战场上,每遇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3]2872。又写李广被迫自杀后,“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3]2876。此外,更着力描写李广的射宽狭、射猎雕者、射白马将、醉后射石等,突出地表现了李广这位名将的英武风姿,还写他在匈奴境内以四千对四万的浴血大战,表现其超凡的将才。与卫青、霍去病之传相比,显然能够看出司马迁的同情甚至偏爱,但是同情归同情、偏爱归偏爱,这些并不影响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理性精神,因为他所描述的李广在历史上也确实具备这样可贵的品格和特殊的才能,作者是在实事求是的理性原则基础上进行提炼和集中,从而真实展示其英雄品格。同时,司马迁在描写、赞美李广英雄本色的时候,又客观地描写了他的不足,如诈杀降者、官报私仇杀霸陵尉,所以总体上他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还是坚持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理性精神,从《史记》中可以看出,李广的优点和缺点都清晰可见。清代黄淳耀曾说:“李广非大将才也,行无部伍,人人自便,此以逐利乘便可也,遇大敌则覆矣。太史公叙广得意处,在为上郡以百骑御匈奴数千骑,射杀其将,解鞍纵卧,此固裨将之器也。若夫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进如风雨,退如山岳,广岂足以与乎此哉?淮南王谋反,只惮卫青与汲黯,而不闻及广。太史公以孤愤之故,叙广不啻出口,而传卫青若不值一钱,然随文读之,广与青之优劣终不掩”①,应该说这是有得之言。
《史记》非常注意通过重大历史事件来表现人物,但是并不忽视有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细琐小事,特别是那些能够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微末小事。通过这些小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既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又鲜明地揭示出人物的本性。如《李斯列传》写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3]2539这个故事不仅揭示了李斯贪恋禄位的本质,而且为他日后做到秦国丞相,因贪恋禄位,不敢坚持正义,最后被赵高所杀埋下伏笔。再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3]3137通过描写其儿时游戏,生动地展示出张汤残酷的性格。还有《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3]2766—2767
虽然是些细节小事,但是却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态。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司马迁善于从生活细节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语言、行动等等细节小事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一方面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写出了人物前后一贯的性格史。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说,作为史传散文的《史记》,之所以取得上面所说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上的创造。从散文角度考察,其语言上突出的特色:一是叙述语言生动传神。如《汲郑列传》说“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3]3114。再如《淮阴侯列传》写萧何走失,刘邦“如失左右手”[3]2611。《史通·叙事》篇评价说:“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1]174二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刘邦骂郦食其:“竖儒!几败而公事。”[3]2040刘彻骂郑当时:“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3]2851全用当时口吻,不避俚俗,显示出人物的本色。再如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然而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清楚地显示出他们不同的性格和心态: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大胆,天不怕,地不怕,强悍爽直的性格充分显露出来;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语虽委婉,但是贪婪多欲的本性也暴露出来了。三是在汉代通用的书面语中经常插入一些口语,生动、鲜活,提高了语言的真实性和表现力。如《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过去的老伙伴见他所居宫殿是那么富丽壮观,于是感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3]1960“夥颐”本来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一“夥颐”显示出陈涉宫殿陈设之丰富;一“沉沉”则表现出宫殿的广大深邃,惊异的语气中生动地显示出身居下层的普通农民的质朴性格。四是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如《李将军列传》中的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3]2878;《货殖列传》中的谚语“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3256;《郑世家》中的“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3]1777,《平原君列传》中的“利令智昏”[3]2376等等都是生动的例子。民谣如《淮南衡山列传》中的“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3]3080。《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引颍川儿歌:“颖水清,灌氏宁;颖水浊,灌氏族。”[3]2847总之,《史记》的语言,虽然多是文言而不是白话,不过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并且经常把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中的词句改成一般通俗易懂的语言。所以,《史记》的语言既丰富多彩,表现力强,又大多通俗易懂,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因此直到今天仍有活力。
总之,司马迁作为良史之才和文学大家,正是发挥了他自己文史兼备的特殊修养,所以便在其《史记》一书的人物形象塑造中采取文史结合的方法,既追求历史的真实,又在此基础之上讲究艺术的真实,最终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完美统一的境界,成为后世的楷模。
[注 释]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陶菴全集》卷四《李将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