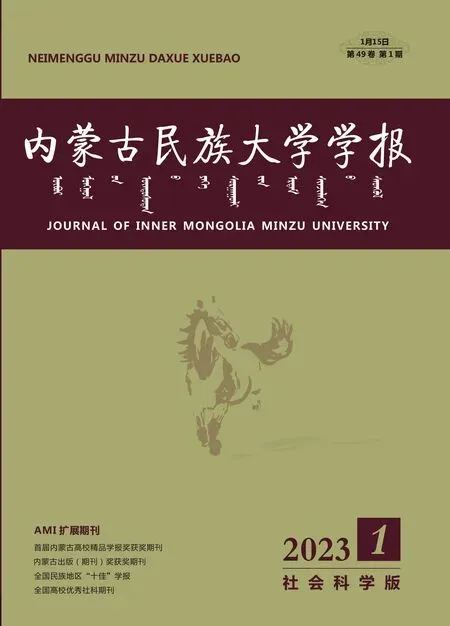《北虏风俗》中的道德观探析
2023-08-06王若明赵佳慧
王若明,赵佳慧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北虏风俗》,又名《夷俗记》,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作者萧大亨(1532—1612)。萧大亨,字夏卿,号岳峰,山东泰安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1年)进士,是嘉靖、万历、隆庆三朝的重臣。他历任边道二十余年,在山陕等地任职,身处边界前线,任职期间亲历隆庆和议始末,又经历顺义王继嗣、洮河之变,后期还节钺宣化、大同、山西三镇。萧大亨一直致力于促进并维护明蒙和平贡市,秉承与蒙古各部和平相处的理念,为边界安定、人民安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明蒙关系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虏风俗》是萧大亨在对这一时期蒙古社会和蒙古族熟悉的基础上,记录下来的认识和体验。在体例上,“平列分目体”的使用让主题明确,记录集中,条理更加清晰,其中句读的使用,区别于同时期文献,有利于文献阐释。内容上,《北虏风俗》从生产、生活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展现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多从微观角度进行描写,细节的勾勒得益于萧大亨多年的戍边经历,体现了萧大亨的军事策略和开明的民族观,同时也勾勒出蒙古族对道德认知的基本态度和道德规则的基本立场。
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共识,是不成文的规则。道德观是在道德认识基础上对道德的一般观点,它的形成与生活的时代、环境和人们的认知有关,可以表现在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等各个方面。透过《北虏风俗》对蒙古族民俗的记载,可以窥见这一时期蒙古族人原始的道德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蒙古族禁忌很多,《禁忌》以及其他篇目都有所描写,这些禁忌与生活息息相关。王学辉的《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运动》谈道:“禁忌成为原始社会唯一的社会约束力,是人类以后社会中家族、道德、文字、宗教、政治、法律等所有带有规范性质的禁制的总源头。”[1]蒙古族在忌惮禁忌的基础上,自觉遵守一切习惯,逐渐形成了原始的道德规范。关于蒙古族社会生活的民俗,在《匹配》《待宾》《战阵》等篇目中,对蒙古族人性格、婚俗、人际交往的描绘,可以更直观了解蒙古族习俗和风尚。可见,蒙古族的道德观从对自然的敬畏开始形成,依靠习惯法“约孙”(yousun)来维护社会秩序、调整人际关系,直到第一部成文法《大扎撒》颁布,原始的道德规范已经内化成一种不可撼动的社会共识,引导他们的行为,和成文法一起维护社会秩序。《北虏风俗》中展现蒙古族道德观的内容有很多,大致分为两类,归纳为生态道德观和伦理道德观,以下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生态道德观
在人和自然界交往的过程中,人类做事情合乎自然规律,保持生态平衡,这是道德的,反之为不道德。生态道德是道德观中一个特殊的部分,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要尊敬、爱护自然。生态道德观早已有迹可循,“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我们做的一切都要合乎天道,不可以僭越。孔子主张“知天命”[2]9“畏天命”[2]160,只有对天地足够尊重、敬畏,人类才能在自然中繁衍生息,万事万物才会各司其职,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蒙古族早期信仰萨满教,主张泛神论,认为“万物有灵”,天、地、神掌管一切,崇拜天地、山川、动植物,这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展现。后来藏传佛教传入,讲因果善恶、业报轮回,更强调内心的约束,道德约束力更强。禁忌和宗教相互影响,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逐渐形成了朴素的生态观,他们自觉约束,相互监督,尊重自然中的一切。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己融入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一)对水草的爱护
蒙古族逐水草而居,水源和草场是发展畜牧业的前提。他们生活的地区水资源匮乏,以使用地表水为主,严禁浪费和污染,《北虏风俗·帽衣》:“非惟衣垢不浣,即其夫终日垢其面,经年垢其体”[3]631。蒙古族从不在河里洗衣服,害怕惹怒神灵,同时保护了水资源。蒙古族禁止在草原上挖坑、乱掘草根,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挖掘草场,要尽快填平,以防地表层遭破坏,造成沙化,放牧也是实行轮休制度。《北虏风俗·耕猎》:“且也艘田沃壤,千里郁苍,厥草为天,厥木惟乔……则互市之开,其于材木,不可胜用矣。”[3]629在记载中,蒙古族生活的地区草木葱郁,松柏很多,土地肥沃,从侧面看出他们大规模放牧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对草场造成严重的破坏,对草场和森林的保护十分有效。这些习惯在《大扎撒》颁布前就已经存在,依照《大扎撒》的第五十八条规定,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中。[4]10第五十六条规定: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4]9习惯法转化为成文法,也就是社会共识凝结成具体法律,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范,原始的习惯同时作为道德规范和法律,仍然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扩大了影响力。
(二)对野畜的保护
蒙古族善于把握自己在自然环境中的位置,有很强烈的共生意识,能和其他种群和谐共生。《北虏风俗·耕猎》:“若夫射猎,虽夷人之常业哉,然亦颇知爱惜生长之道,故春不合围,夏不群搜,惟三五为朋,十数为党,小小袭取,以充饥虚而已……较猎阴山,十旬不返。”[3]629他们生活环境恶劣,资源稀少,牛羊是其主要的生活来源,通过打猎来补充日常需要,以射猎为需,也以射猎为乐。从《北虏风俗》中可以看到蒙古族在春天让万物生长、繁衍生息,夏天群兽成长的时候从不围猎。只在物资不充足、难以维持生计的时候,小规模捕猎,直至秋天,鸟兽成群,他们才进行大规模的捕猎行动。《北虏风俗·牧养》:“野产之物,若黄羊盘羊野猪野牛野马野驼野鹿之类,皆不可驯致,惟大猎时则能获之。”[3]634在日常生活中也禁猎珍贵、稀少的野兽,即使在合围时,也要在野兽聚集的地方捕获。同时期颁布的《阿勒坦汗法典》[5]中也提到对偷猎野畜的处罚,禁猎期、禁猎种类和禁猎区的存在,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稳定了生态平衡,还实现了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下来,有着无法磨灭的历史功绩,对当今社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对家畜的保护
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对他们来说,马不仅是出行工具,驯为战马,可以上阵杀敌,也是主要食物来源,马是他们衣食住行的重要保障。《北虏风俗·牧养》:“夷人畜产,惟牛羊犬马骆驼而已,其爱惜之勤,视南人之爱惜田禾尤甚……彼且曰我分其乳,则驹食乳少,故冬月耐寒,不分其乳,则驹食乳多,至冬月不耐寒。”[3]633他们认为马是天神的恩赐,马是有灵性,有神性的,对马匹的爱护体现在各个方面,视马匹为亲友。蒙古马和主人的感情也很浓厚,十分忠诚,所以蒙古族一般情况下不杀马吃肉,即使是祭祀杀马也要进行祷告。他们对其他赖以生存的牲畜的感情也很深,擅长饲养牛、羊、驼。《北虏风俗·牧养》:“大抵马之驹,牛之犊,羊之羔,每一年一产,产于春月者为佳,羊有一年再产者,然秋羔多有倒损之患,故牧羊者每于春夏时,以毡片裹羝羊之腹……彼此交作,不数日而毡毕成,骆驼则二年一产,力能任重,每藉以负载行装,故虏贵驼也。”[3]633他们对牲畜极为看重,有一套科学的合理的方法去牧养牲畜,从不对牲畜无限制地索取,求取马乳也分时限,秋羔倒损便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取牛羊乳也并非随时随地索取,可见蒙古族对大自然取之有度、取之有道,而不是一味索取、贪心不足。
以上从蒙古族对待水草、野畜、家畜三个方面,展现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与大自然的相处方式。当时的蒙古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对世间万物充满了未知和恐惧,在蒙昧的状态下,他们自发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禁忌,比如对水的崇敬、害怕打雷、对马匹的崇拜等。他们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摸索出一条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达到了人和自然的平衡。这种质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法则,约束自我、眼光长远、泽被后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恶化的当下,原始生态道德观中的智慧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
二、伦理道德观
伦理学源自西方,是关于道德的科学。约翰·杜威在《伦理学》中说道:“伦理学是一门研究行为(conduct)的科学,它考察行为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有一个单独的术语用来指被这样考察的行为,那就是‘道德行为’或‘道德生活’”[6],这是西方对伦理学的解释。中国古代也存在关于伦理学的思考,但并未称之为伦理学。我国没有纯粹的伦理学,多与其他学科交叉,以儒家为主,先秦已经存在。中国传统的伦理学更侧重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贴近人伦概念,比如君臣父子、天人合一等。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有时会被混为一谈,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二者的相同点在于,都追求善,并给出行为规范以作指导;区别在于,道德是个体的,是主观的,更侧重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而伦理是社会的、客观的,把人置身于社会中考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北虏风俗》对生活场景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蒙古族在婚姻家庭、人际交往中的习惯和方式及其体现的伦理道德观。
(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
古代社会有收继婚的风俗,包括父死儿子娶庶母、叔死侄子娶婶娘、兄死叔伯娶嫂子等。当时蒙古社会收继婚依然存在,《北虏风俗·匹配》:“至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不如此反相讪笑”[3]624,体现了收继婚仍然被认可,符合当时蒙古社会的价值观。《北虏风俗·埋葬》:“其所嬖幸之人虽不尽杀,但自生母以外,仍为子所收,子死,父则擐甲持刃,向门三砍,仍收其媳,惟此淫俗固佛教所不能变者。”[3]627萧大亨谈到,佛教的理念也未影响收继婚的风俗,称之为“淫俗”,可见当时汉人对收继婚的态度。早在秦汉以后,中原的收继婚就已经开始受到限制,明代更是被法律禁止。如今看来,收继婚有违人伦,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蒙古族生活环境恶劣,资源稀缺,已婚女性被认为是家庭共有财产,为了避免财产流失,保护家族利益,保证子嗣繁衍和婚后和谐等,收继婚是很实用的婚嫁方式,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加以指责和否定。当然其中也有比较野蛮的做法,《北虏风俗·治盗》:“即奸其舅母,亦无呵责之者”[3]626,如果是外甥侵犯了舅母,是可以被宽恕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家庭内部关系的混乱,这是传统道德中有违礼法的部分。
关于婚姻的伦理道德,《北虏风俗·匹配》:“其有夫妻反目别娶有妾者,妇家廉知之,即窃入其幕,杀其所娶之妾,尽驱其马驼以归,若妇不悦夫,则随其所欲嫁,夫亦认不敢言也”[3]624。夫妻不合,男子纳妾,正妻因此受辱,有权利杀死妾室、带走财产。如果女子对丈夫有意见,也可以再嫁他人,男子无权发表意见。可见在蒙古社会,已婚女子对自己婚姻有一定的发言权,在一定条件下,女子有选择的权利。蒙古女性在婚姻上的地位较高,游牧生活需要女性承担繁重的劳动,男子征战对家庭疏于关照,男尊女卑观念淡化,而且由于征战需要,蒙古人重视子嗣繁衍,一夫多妻制很普遍,女性的地位也随之升高。当时出台的《阿勒坦汗法典》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已经全面完善,这是特殊环境下民风民俗的反映。蒙古女子在政治和家庭生活中都有参与的权利,《北虏风俗·帽衣》:“人言虏多受制于妇……凡衣服冠履,一切巨细之事,皆出其手,夫自持弓射猎外,无所事事也,平则司牝鸡之晨,怒则肆狮子之吼”[3]631。男女分工固然不同,女子做家务、抚育子女,男子负责打猎,蒙古女性是家庭的核心,在蒙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总体看来,当时蒙古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明显,反而是女性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二)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观
蒙古族在人际交往中也体现了与中原相异的伦理道德观,《北虏风俗·听讼》:“夷人杂居沙漠,喜则如马之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曲直已分,则令曲者为直者奉酒,次日直者亦不敬,逐相欢如故也”[3]626。由此可知,蒙古族直率坦荡、心胸开阔、明辨是非、不计前嫌。《北虏风俗·教战》:“且射骑于此益精也,及至勇力出众,众甚重之,虽虏王台吉恒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即勇力者或珍其臂而夺之食,虏王台吉亦欢然不以为怪也。”[3]635蒙古族尚武,欣赏勇士和英雄,“珍其臂而夺之食”在汉人看来是对权力僭越和挑战,蒙古族统治者却不以为意,包含了对勇士的赞赏和鼓励,蒙古族骁勇善战与这种观念密不可分。
《北虏风俗·待宾》:“夷人应酬礼节,无所谓揖逊谦让之仪,其在幕中,宾坐于西北隅,主坐于东北隅……皆趺迦箕踞,不倚不席也,主人待之,仍饮以乳以茶以酥油,次则酒肉之类,宾主食毕,则以其余者犒从群,然聚食于一幕,而主仆不分也。”[3]628待客讲礼仪,但不繁缛,他们座次合理,坐姿得体,体现了主客之间相互尊重,其中谈到“主仆不分”,可见尊卑界限被淡化了。再如《北虏风俗·教战》:“出行无导从,服饰无等级,行如雁行,人亦莫知谁为王,谁为台吉也,夫自幼至长,惟力是恃自上至下,惟力是爱。”[3]636《北虏风俗·习尚》:“其俗不竞富贵不戚贫贱,虽家无升斗,处之晏如,最敬者笃实不欺,最喜者胆力出众,其最重者然诺,其最惮者盟誓。”[3]634他们的服饰没有等级之分,不以贫富为待人接物的标准,一旦许诺,绝不轻易悔改。尊卑观念的淡化,人与人之间平等地交流,使他们更团结、更亲密,有助于化解内部矛盾,体现为人格的平等,颇有大同社会的风范,但他们自上至下并非毫无章法,对虏王、台吉、酋首都十分敬重。《北虏风俗·敬上》:“至若毁骂酋长,凡听闻者,人人皆得杀之。”[3]631形成了一个祷告祈福的体制,“近奉佛教,或有疾病,辄召僧讽经祈祷,台吉为虏王祷,诸夷为台吉祷,其敬上勤恳如此。”[3]632蒙古族还很尊重知识,《北虏风俗·尊师》:“夷人能书,则随酋首往来,列于诸夷上一等”[3]629,对有学问的人敬重如此。在如今看来,这种人际关系不无理想化色彩,但是在当时真实客观存在。蒙古族讲礼法,由于草原的特殊环境,远不如中原地区复杂,呈现出简单且有序的特点。时代的变迁使我们无法重现当时的情境,但可以无限趋近这种美德,将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明才会延续,道德水平才能提高。
蒙古族相互扶助,有很强的集体意识。《北虏风俗·待宾》:“又有生平不相知识,或贫或馁,不必卑辞哀请,直入其幕而坐之,主人食即以其食剖而分之,以故行人过客,往往望屋而食,虽适千里者,奚必三月聚粮哉,亦有贫夷食寡,恐人之分其食也,辄幕夜付餐,晨起蓐食,若候至日中,则食虽甚寡,亦必均分而无吝矣。”[3]628蒙古族热情好客的传统延续至今,行人过客,无论贫富,都可以成为座上宾。贫者也毫不吝啬地分享仅有的粮食。蒙古族这种热情好客、相互帮助的性格是草原游牧文明中一朵绚烂的道德之花,这与生活环境恶劣、资源匮乏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必须组成一个集体,取长补短,去完成个体难以完成的任务。这种高尚的品德在作战中也有表现,《北虏风俗·战阵》:“偿有一人折马,众必以余马载之,不然酋首必重其罚也,有被创者,危在呼吸间,众必捐躯以援之……援一散夷,散夷亦敬如父母,归则尽分其资材,且世世德其人而不忍忘矣”[3]637。如果在战争中有人负伤,其他人会全力营救,营救伤者的人并非为了得到丰厚的回报,这种奉献精神和强烈的集体意识是很珍贵的。在这些道德观的指导下,蒙古族在战争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萧大亨也对此进行了高度赞赏:“论者咸曰,虏猛甚,不可当也,不知虏岂虎而翼,飞而食人哉,盖酋长之于群夷也,获则同其利,群夷之于党伍也,危则同其害,利害相同,千人一志,奚俟三令五申,然后蹈白刃,赴汤火哉。”[3]637萧大亨还反思中原士兵的行为:“合我中国法令,敢私卤获一介乎,被危者肯越伍相援乎,即勇而直前,首级不及格,肯论功乎。”[3]637两种作战风格相比,萧大亨不仅赞赏蒙古族无私奉献、团结一致的精神,还充分肯定他们在战略、战术上的策略和方法,也可见萧大亨客观的军事思想和先进的民族观。
三、对当代的启示
《北虏风俗》是一部全面记载蒙古族风俗的文献,突出的特点是分章节记述,内容丰富翔实,为研究蒙古社会、蒙古族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萧大亨在边关任职数年,与蒙古族近距离接触,十分熟悉并且能融入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他真实客观地记录了蒙古族对待自然以及在人际交往中个体的态度和集体的原则。在萧大亨笔下,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如画卷般展开,通过对真实情况不加渲染的刻画,逐渐勾勒出当时蒙古族的道德观念系统。作者以客观详尽的笔触,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蒙古族文化的发展、进步,体现了对边疆地区民风民情的适应和尊重,充分赞扬了蒙古族可贵的品质,表现出相对开明进步的民族观,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的思想也刻有时代的烙印。
随着社会发展,人类无限制的索取,最大限度地占有自然资源,如今蒙古族生活的地区出现荒漠化、水资源缺乏、森林覆盖率低等问题,这与《北虏风俗》描绘的情形截然相反。蒙古族的生态道德观在千百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生产力和现代化的冲击下逐渐崩塌,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重拾与万物相互依存的生活方式。蒙古族生态道德朴素、宽容,社会建设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在民族融合的今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蒙古族在婚姻家庭上和人际交往中体现出的互相尊重、相互扶助的道德品质也值得当代人学习。随着时代发展,物质资料越来越丰富,个人和集体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我们倡导个人的价值和权利,主张个性独立、自由,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维护家庭。集体主义主张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需要个人绝对忠诚,在集体中相互帮助。在当今社会,个人主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利己者多于利他者,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这些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相悖的。真正做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协调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个人需要以一种更好的方式融入集体,达到和谐。蒙古人相互扶助、利害相同、千人一志的美德便是个人与集体相协调的最佳佐证,给当代以启发和精神力量,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北虏风俗》的记录下,蒙古族在特殊环境下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传统道德观,独具民族特色,在生态保护方面和伦理道德方面,都有效地维护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协调了人际关系,这些道德观在今天仍然闪耀着人性和理性的光辉。与此同时,在继承传统道德观的同时,要注入现代理念。当今世界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传统道德观无法作为一种约束,如果强行将其作为约束力量,往往适得其反。蒙古族传统道德观要结合社会存在,充分保证个人自由,才能更容易被接受,推动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