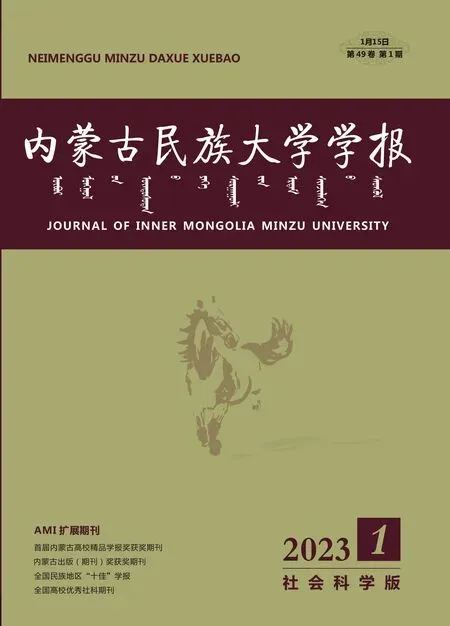云南边境民族母语创作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多维审美研究
2023-08-06李瑛
李 瑛
(云南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云南边境民族,指分布于云南边境线上的16个少数民族,其母语创作是关联同源民族跨国界文学的现象,中华认同是其重要议题。中华民族认同是包含各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一体”认同,层次丰富,内容宏大,由于边境民族的发展历史具有自己的特性,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背景,故而中华民族认同书写呈现多声音叙述、差异性表达多元结构与审美意识,境内外同源民族作家以形象、抒情、叙事等独特母语话语表达云南边境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践行多向度美学旨趣:境内母语作家显示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国家—社会主义中国”一体化认同特征,境外母语作家则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家园”认同审美特质,但两者均为中华民族认同之统一整体性表达,证明当代云南边境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是深层次而根本的认同,不仅彰显边疆文学独特的人文精神,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1]重要理论的形象阐释与文学实践,复杂而丰富、客观而真实、独特而完整地构建了云南边境民族母语创作中华民族认同的别样表述:相关万里,归属同心。
第一,族源认同深层审美独树一帜。
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了中华整体历史的形成,族源认同实际上与民族迁徙相辅相成,民族迁徙促发族源追寻情结,丰富民族认同本质内涵。在中华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认同历程中,西南地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云南成为赋有特殊意义的代表:对内,融入中华,与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直保持着古老的文化联系;对外,与地缘最近的东南亚各国同源民族交流互动,民心相通,血脉相连,奠定多极关系辩证统一与共生融合基础。边境少数民族作家们执着坚守中华民族认同书写,尤其是境外同源民族作家们,在疏离流动的艰难岁月里,在异国他乡的奋斗生活中,通过文学想象,用母语讲述族群融入中华的生动故事与艰难过程,不断注入同根同源中华民族认同新鲜血液,获得超越地域、时空和现实利益的审美表达与精神升华。
景颇族女作家霜童静斑虽然出生和成长于缅甸,但她的小说常常插入景颇族从中国迁徙至缅甸的族源记忆,中华民族认同情感隐晦而深沉。在其短篇小说《NU U E SHA E》(《母亲,孩子》)中,就穿插了景颇族母亲教育孩子时讲述景颇族民间故事“母子江水”的情节。故事说,从前有一个景颇族妇女,背着她的孩子从缅甸目拽省然崩下来。走得太累了,她就把孩子放下,然后去打水喝,可是等她打水回来后,孩子不见了,她拿着打水的水桶,喊着孩子的名字,汉译:
“孩子啊……孩子啊”,她去森林里叫着寻找孩子。走散了的孩子也因为找不到妈妈,所以嘴里喊着“妈妈……妈妈”寻找母亲。母子俩就这样一直相互寻找,但是却没有相遇。最后,妈妈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心脏破裂而死,她的孩子也因为太累太饿悲惨地死去。母子中间隔着一座大山,没过多久从他们母子去世的地方流出了两条河流,这两条河就是迈立开江和恩梅开江,传说两条江水就是那对母子。他们母子因为特别爱对方,所以即使离散后变成了河流,妈妈也没有放弃寻找儿子,同样地,儿子也一直在寻找妈妈。可能是急迫的心情所致,两条江水流速都很快。如果人们不信的话,听一听,那江水发出的声音每时每刻都是“妈妈-孩子,妈妈-孩子”的声音。从不同的地方流出来,最后到了当佩城相遇,合拢成了一条河流,就是伊洛瓦底江。
故事里的母子,最后化成两条江,一条是迈立开江,一条是恩梅开江,相互寻找,江水并流后,叫伊洛瓦底江,一起奔流在缅甸大地上。恩梅开江上游为中国怒江州境内的独龙江,源头在西藏察隅县境伯舒拉山南麓,与迈立开江为源头—支流关系。两条江水极具母亲—孩子之象征意味,令人感慨不已。
实际上,缅甸景颇族作家普遍拥有热烈而感人的中华民族认同创作思想。缅甸景颇族诗人诺腊崩2016年3月在中国德宏景颇文刊物《文蚌》上发表诗歌《MANAU》(《目瑙》),描写景颇族跳目瑙的盛大情景,各个支系的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吹着各式各样的乐器,跳着各式各样的舞姿,热切表达“Chyurum sha ni a manau nan rai/Shawa mun sen shang mai ka”即“同根同源民族的目瑙/千万人在跳”的激动心情:
景颇人民团结一心
聚在目瑙场
一起拥护领头人
瑙双后面是瑙然
瑙然后面是百姓
与之相比,德宏景颇族载瓦文诗人石木苗也有一首相似的诗歌作品《MUNAU ZUM》(《目瑙纵歌》):
春暖花开时
跟在老者的后面
从天上跳下来
雾都鸟做瑙双,在前面(领舞)
五颜六色的花香四溢
在目瑙中展示自己民族的历史
把天上的种子邀请下来
一路播撒下来
这里的景颇山变成了茂密的森林
这是经由族源认同而通向中华民族认同的诗歌之路,两首诗歌异曲同工,着力描写“聚在目瑙场”的集体主义与团结精神。“目瑙”是景颇族最盛大、最隆重、参加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传统节日,“目瑙”意指大家一起来跳舞,“瑙双”为领头者,负责方向,“瑙然”为领舞者,负责舞姿,“瑙双”和“瑙然”后面,各自跟着百姓队伍,无论人数多少,两支队伍队形多变,规模宏大,秩序井然,“目瑙”及“目瑙场”象征坚定的信仰,历久弥新,代代相传,成为中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着中华民族认同的强劲力量。
境外苗族作家的苗文小说创作,以持续追索民族传统的精神表达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深厚情感。由于苗族迁徙的地域广阔,居住国家广泛,作家们的小说避免不了异国情调的描写,如老挝的亚热带山区、篱笆环境、美国的现代化公路与电话等,但无论怎样,“国外苗族母语书面文学作品均以苗族生活为题材,而且传统性较为突出,特别是一些不良习惯,往往成为促使作品故事情节发展的焦点,有的作品,虽然描写的是现今的生活,但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主人翁的挫折遭遇等,均是传统所致。对此,作者当然不是讴歌颂扬,而是希望通过反映,让现在的人了解过去,对比现在,找出阻碍民族发展的症结,改变落后,向前发展。应当说,这是非常积极的……作为年轻一代,唤起本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和觉醒,不能不是一大重任,作者的意图如此,读者看了作品一般也会有这种认识,这可以说是国外苗族母语书面文学作品反映苗族传统生活的重要价值。”[2]境外苗文作家对苗族传统生活的反复描写,表面看,只是关乎文学题材选择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具有更深层的含义,一方面,境外苗族作家们在讲述苗族远离故土、分散各国的个人经历时,总是尽力描写苗族人在各种境遇里突破他国文化包围的文化态度及文化选择;另一方面,主人公设置多为苗族,所讲述的都是苗族人的故事,体现境外苗族对延续民族精神的责任感,保存离散苗族群体的民族记忆,决不陷入民族认同的危机之中。由此可见,境外苗族作家母语创作充分表达了苗族人民中华民族认同的整体美学认知,意义深远。
与境外苗族创作形成唱和,境内文山苗族诗人和歌词作者张元奇有一首诗歌《我们的名字叫苗族》,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表达苗族致敬故乡、致敬中华的博大情怀,汉译:
为什么我们要说自己的语言
为什么我们要穿自己的服装
不为别的什么
只为我们的名字叫苗族
……
这首诗歌在1987年文山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被朗诵,受到了广大苗族人的称赞,“后来由文山苗族陶永华谱成歌曲,流传到越南、老挝、泰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苗族聚居区,对促进文山苗族和国外苗族的友好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诗歌激起离散千年、遍布世界多地的苗族同胞共同的民族认同感和中华民族认同感。
傈僳族年轻的诗歌作者余七斤在自己未发表的傈僳文诗歌《ATRRIT LISU TITHEINT SO》(《天下傈僳一家人》)中写道:
我们是分布各地的傈僳族,
腰带是我们傈僳族的象征。
穿珠戴贝是我们傈僳族的标志,
我们是心地善良的民族。
鱼氏、乔氏、蜂氏一家亲,
虎氏、熊氏、李氏和鼠氏心连心。
我们有兄弟勒墨、鸟氏、麻氏族,
我们有姐妹怒氏、侗家、猴氏族。
米钱、木氏、欧氏、茶家族,
孔氏、杨家、白姓人。
天下傈僳一家人。
……
无论你是怒江傈僳人,
还是维西傈僳族,
我们都是一家人。
无论你是在云南,
还是在四川,
我们都是一家人。
无论你在越南,
还是你身在美国,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之间没有抱怨。
我们之间没有仇恨。
诗歌里的傈僳人,多区域分布但族源一致,散居各地却多元汇聚,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不断向前推进民族认同,国家大一统与多极性并存,最终形成中华民族认同多维审美特质。
第二,文化认同美学精神海纳百川。
中华文明是世界至今唯一存续不断的古老文明,是“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②,是具有独特历史特征的共同体。当代中国56个民族亲如一家,尽管边境地区有不少民族跨国界而居,但同源民族之间往来频繁,因为有传统深厚的共同文化、语言和习俗,而且长期保持相互通婚、边民互市的习惯,云南即为其中典范,为边境少数民族母语创作中华民族认同书写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和不可替代的叙述话语权。
1995年,缅甸作家恩胖诺布创作景颇文小说《GU ONG A SENG》(《翁哥和恋人波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缅甸景颇族男孩爱上了中国的景颇族女孩,怎么办?小说男主人公早翁,是到中国芒市学习汉语的缅甸青年,在芒市期间,参加目瑙活动时爱上了一个名叫波相的中国景颇族女孩,他明白,要建立和这个女孩之间的情感交流,先要打消两人因国籍不同而带来的距离。于是,早翁找波相聊天,主要话题就是围绕两国景颇族亲如一家的关系而展开,特别是家族名号问题,这是能否通过景颇族婚俗的关键环节,因为景颇族遵循传统的单向姑舅表婚的原则,即姑家男子能娶舅家女子,但舅家的男子不可娶姑家女子,形成“姑爷种”和“丈人种”的婚姻关系。早翁自报家族名号为“卡树卡沙族”,并特意询问波相的家族名号,波相说自己属于“木然”家族,并表示很少听到过早翁家族“卡树卡沙族”的名号,早翁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长篇大论秀了一把所掌握的民族文化知识,讲述景颇人家族名号的代际划分,告诉波相,我们都是从一个老祖宗分支而下,“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兄弟姐妹”,早翁妈妈所属的家族与波相所属的家族是同一个——木然家族,早翁妈妈等同于是波相的姑姑,按照景颇族婚俗文化,这样的情况符合“姑爷种”,他俩可以婚恋,言下之意,你我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但我们不仅是亲戚,而且还符合景颇婚俗规范。这个男孩成功了,最终他带着女孩回到缅甸拜见父母。作者也成功了,他把一个跨国爱情故事提升为不同国家同源民族认同的隐喻,怀着尊重历史的态度,看待和解决边境地区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现实问题,构思精巧,意义不凡,趣味横生中触发思考。
怒江傈僳族作家熊泰河有一首傈僳文小诗《KORSHITZIL QILA WA》(《阔时节到来了》):
相思鸟儿啼叫着,
黄鹂鸟儿鸣叫着。
白族新年杜鹃开,
傈僳新年樱花开。
阔时节到来了,
新日子来临了。
……
孩童需要细聆听,
子孙记得常领悟。
勿忘共产党。
勿忘祖国。
阔时节欢乐起来,
新年佳节欢快起来。[4]
浓郁的起兴手法,强调春天的到来,反复强调“新日子来临了”,这“新日子”,不仅指季节轮换,更指傈僳族“阔时节”文化内涵,与中华民族新年佳节同欢乐同幸福,展现傈僳族中华文化认同的深厚情感。
哈尼族年轻的作者李初三在诗歌《HAQNIQ MILHAOQ》(《哈尼人家》,未发表)中则以和缓的笔调,通过对自然资源的人文解读,展示对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认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叫“本那”
本那,生我养我的故乡
三月桃花开满山
八月梯田似黄金
山涧流水入人家
还有,还有
门前流过的那条大河——本那河
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哈尼
哈尼,生来便是我的名字
阿爸午时耕梯田
阿妈家里织布儿
老人和小孩讲(听)着哈尼故事
哈尼的姑娘如彩虹般美丽
哈尼,哈尼
心似星光般明亮的人儿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名字叫哈尼
这是浓郁的乡土山水诗与深情中华颂的合奏曲,音韵节奏和谐,循环使用叠句,增强咏叹力量,咏叹中的本那河,被塑造成一个沉厚的形象,流淌着哈尼族的希望和故事,流淌着心底挥之不去的乡愁,流淌着哈尼族中华民族认同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独特地标景物:桃花、梯田、河水。
第三,“中华民族—国家—社会主义中国”一体化认同的爱国美学新维度。
自古以来,中国与中华不可分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中华—社会主义中国”与各民族历史上坚守的“中华—国家”传统认同意识叠加重构,形成云南境内少数民族母语创作“中华民族—国家—社会主义中国”一体化认同书写一大特色,同时也是境内外同源民族母语作家中华民族认同书写审美差异之一。境内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关联叙事性、抒情性、政治性和制度性,审美创建边疆文学社会主义中国新词意境,形象阐释边疆云南新的风貌与形象,凸显“中华民族—国家—社会主义中国”一体化认同的爱国美学新维度。
首先,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对边疆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实际效应。西双版纳傣族第一代母语诗人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等堪称首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们从封建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一改旧社会傣族“召片领”附庸歌手身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诗人。康朗甩创作傣文诗歌《土地的主人》:“来吧!醒来的傣家,让社会主义的种子,也在西双版纳的大地上萌芽。”[5]康朗英创作傣文诗歌《人民大会堂》:“作为中华儿女的骄傲,我若能投生一千次,也要选择投生在你的怀抱。”[6]波玉温创作傣文诗歌《亲爱的祖国》:“亲爱的祖国啊!我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在党的领导下,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们拿着箭弩守卫在云南边境,猫头鹰不再敢飞进祖国的森林,傣家人享受着人间的好光景。”[6]三位民间歌手创新傣族民歌章哈形式,结合全新思想与古老艺术,第一次塑造出社会主义建立初期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抒发对社会主义中国崭新气象的深厚热爱,充满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认同的人民性力量。
其次,集中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维系中华认同的向心力,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国家—社会主义中国”一体化认同爱国美学精神。哈尼族诗人哥布的母语长诗《YOQMIL YOQGAQ》《神圣的村庄》把民族迁徙与中华认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等多域话语紧密结合,设置从传统到现代不同身份的叙事者,他们是咪谷、莫匹、女巫等宗教叙事者,乡长、村长等乡村领导叙事者,当家男人、当家女人等普通百姓叙事者,打工仔、打工妹等新一代哈尼叙事者,这些角色已然成为哈尼—中华双重意义象征符号,把哈尼族历史文化美丽图景绘入多民族国家巨幅画卷,意味着一个逝去的传统形态与一个进行中的新型社会碰撞后的相融统一,经由审美路径探索民族前行方向。长诗最终通过村长之口,确定哈尼历史文化与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中国不可分割的血脉深情:
在祖国的一隅 我们
安居乐业身体健康
红河流域七十万人
垦殖梯田繁衍自强
在这个世界上二百多万人
血管里有哈尼的血液在流淌
大家庭面貌焕然一新
像三月的鲜花在大地上开放
今天是属猪的好年头
今天是属鸡的好属相
我们是亲爱的兄弟
我们有世代的交往
国家政策是富裕的通道
干部和百姓一家人一样
杂交水稻是我们的粮食增产[7]
长诗打破时空,体现哈尼族融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共同体的诗学表达:“在祖国的一隅,我们,安居乐业,身体健康”,简朴的句子抛出一条拥抱中华、拥抱祖国的精神纽带,“强烈的对(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又包含着对自己的国家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8]。
此外,德宏州傣族诗人岳小保2011年8月出版了傣文诗集《金田玉地》。诗集有一个重要系列,就是叙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位国家领导人到访德宏的历史事件,抒发傣族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深厚情感。从1952年毛主席接见德宏首任州长刀京版写起,接下去是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参加中缅边民大会的国际大事、1955年刘少奇接见德宏州副州长雷春国等等国家领导人看望边疆人民的国家大事,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掘反映国家领导人关心边疆、团结奋进的创作视角,流露出边境地区人民自觉的国家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及其在地缘关系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如傣文诗歌《毛泽东》:
1952年
祖国解放三年
今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刀京版
刀京版是德宏州的首位州长
毛泽东指引并叮咛嘱咐
让各个边疆民族领导者建设好边疆
德宏从此走向繁荣
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共产党功劳胜于大海
带领男女老少共建边疆
各民族团结一致共护边疆
祝愿农工商及其他领域不断发展
祝愿从今往后祖国上下都繁荣富强
祝愿祖国永远屹立世界[9]
质朴明朗真诚的诗句道出边疆人民爱国心理的最深层意识,与“秦时明月汉时关”等古诗中描写边疆的征战、矛盾、冲突状态形成对照,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边疆表现稳定、和谐、繁荣形势,这与我国领导人对边疆的关心、牵挂与建设分不开,如同诗歌所记述的,开国领袖毛主席就曾在北京接见了德宏首任傣族州长刀京版,此后一代又一代领导人都到过祖国的西南大门,看望边疆百姓、关心边疆发展,纵观历朝历代,几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其巨大的影响力正如诗歌所总结:“各民族团结一致共护边疆”“共建边疆”,把边疆百姓对领袖的爱戴与爱国情怀、国家命运、中华认同紧密关联,这一文学精神已然成为新的美学经验贯穿历史。
云南是中国边境民族母语创作文字种类最多的省份,第一个母语作家为刀安仁,他是盈江干崖(今盈江县新城、旧城等区域)第24代傣族宣抚土司,使用自己的母语——德宏傣文,于1890年创作了《抗英记》等一批作品,至此,云南边境民族母语创作已走过百年历程,目前拥有傣、苗、景颇、哈尼、傈僳等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母语文学创作,持续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21世纪以来呈繁荣趋势,汇成边地之母语创作“云南现象”,不仅在云南文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同时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是推动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动力之一,是中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格局中的重要成员,各民族骨肉相连、文脉相通,其中华民族认同书写的多维审美,展示出作家个人与民族文学绚丽美学风貌中一个重要的特色与亮点,除丰富的美学价值外,还具有文学史、民族史、制度史等多重社会价值与功能,其母语文学独特话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信仰等多方面内容,既为云南边境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同时生动展现了饱含离愁、情怀、回归等多重意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独特而重要的当代审美路径,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边境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和情感支持。
[注 释]
①[缅甸]霜童静斑:《母亲,孩子》,引自《霜童静斑小说集》(上、下,景颇文),仰光孙班印刷厂,2006年12月版。
②转引自陈金龙:《新中国70年国家形象的建构》,《贵州民族报》,2019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