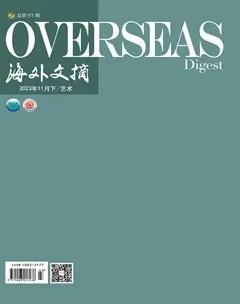“外江戏”的演变与粤东客家文化的交织
2023-06-23王子熙李恩卉
王子熙 李恩卉
外江戏,最初指清朝同光年间以皮黄为主声腔的潮梅外江戏,后由广东大埔人钱热储于1933年正式命名为汉剧。本文详细回顾了汉剧的起源、发展,以及它如何深受皮黄汉调的影响,并最终北上成就京剧,南下影响粤剧等地方戏曲。同时,本文着重分析了汉剧与客家文化间的互动:从经济不发达的客家山区到繁荣的潮汕地带,汉剧不仅获得客家人的深厚喜爱,而且在客家文化的支持下得以保存和发展。此外,本文还讨论了客家人对汉剧的情感寄托和文化认同,以及汉剧如何成为客家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深化了两者之间的相互成就与促进关系。
0 概念释义
外江戏,广义是指清初以来广东地区对外来戏曲样式的统称,狭义则指从外地来到本地演出的戏班。清朝同光年间(1861年-1908年),外江戏特指一支分布在“赣之南,岭之东,闽之西部”、以皮黄为声腔主体的潮梅外江戏。1933年,广东大埔人钱热储提出外江戏改名汉剧。他在1933年出版的《汉剧提纲》“作书缘起”中开宗明义:“何谓汉剧?即吾潮梅人所称外江戏也。外江戏何以称汉剧,因此种戏剧创于汉口故也。”随后他还讲,“汉剧作于汉口,流行于鄂皖之间,经安徽石门桐城、休宁间,人变通而仿为之,又称徽调。自是而后,乃复分支,流而北上者经北京人将唱白弦乐鼓乐悉易高亢之音,称为京剧。今亦称平剧。流而南下者,至广州一带,又经粤人易以喧闹之音,称为粤剧。惟在赣之南,岭之东,及闽之西部者,皆本其原音,不加增易,故特标其名曰外江。试观今之平剧粤剧,与夫外江剧,其皮黄曲调,皆大同小异,其旧传剧本,皆十九相同,可以证明其同源异派。又吾南方人俗语,称长江一带人皆曰外江人,今以戏剧特称外江剧,则其中音节关目,皆属汉剧真传不加易变,更可了然。[1]”
1 外江戏的历史和发展
清代中叶,汉剧在湖北形成,原以秦腔经襄阳南下演变出来的西皮为主要腔调,后来又吸收了安徽传来的二黄。早期同徽剧经常相互影响,形成了“徽汉河流,皮黄交融”的皮黄腔风格。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襄河、荆河、府河、汉河四支流派。分别以襄阳、沙市、德安(今安陆市)、汉口为中心。襄河派以襄樊为中心,沿汉水向外传播,上至郧阳,下至钟祥,流播到陕西,河南南阳、许昌等地。府河派主要流播于随州、枣阳、孝感、黄陂以及河南信阳、驻马店和山西晋阳等地。汉河派主要传播于鄂东南的成宁及鄂东的黄冈地区,并向外流播安徽、江西等省。最值得注意的是,荆河派,以沙市为中心,不断向周边辐射,不仅在湖北境内向西形成了南戏,还沿荆河流播至湖南,并进一步传播到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等地。在这一过程中,荆河派的皮黄调被荆河戏、常德汉剧(后改名武陵戏)、湘剧、祁剧和桂剧等地方戏种吸收,形成了各自的主要声腔。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不同剧种对皮黄腔的称谓均为“南北路”[2],展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清嘉庆、道光年间,汉调流传到北京,加入徽调班社演唱,逐渐融合演变而成京剧。而粤剧的形成相对较为复杂。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在广东流行过的戏曲品种,有切实资料可查的有弋腔、昆腔、梆子、徽调 (石牌 )、汉调( 楚腔 ) 等。除昆腔外有时把其他品种称为 “乱弹 ”“梆子乱弹 ”“乱弹诸腔 ”这些戏班统称为 “外江班 ”[3]。“乾隆末年,外江班达到高峰,上会戏班达50余个,从业人数保守估计两千(以每班40人计)开外,彻底改变此前昆班主宰广州剧坛的局面,而形成了以徽班、湘班为主的乱弹时代。”清代兴建的广州梨园会馆的碑记中,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粤44个外江班中,徽7班,湘18班。这说明,在乾隆年间来粤的“外江班”中,徽和湘所占比例很重[4]。而欧阳予倩、周贻白、黄镜明等学者认为皮黄腔早在乾隆年间就已随徽剧陆续传入了广东。此外,这些湘班又都以汉调自名,虽有长沙班、祁阳班、常德班、岳阳班之分,其腔调都称 “南北路 ”,只祁阳班杂有昆腔,长沙班兼唱高腔,因此粤剧又笼而统之地将“南北路”称为汉调。综上所述,粤剧在演变过程中,以徽班和湘班为媒介,深受皮黄汉调的影响。
咸丰八年(1858年),潮汕汕头被正式开辟为英法与粤东的通商港口,由此迅速崛起,成为粤东、赣南、闽西地区的重要港口与商贸集散地,一跃成为粤东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遵循“商路、官路即戏路”的理念,这里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文化需求吸引了众多外江戏班来此演出,以满足不断壮大的观众群体的文化需求。随着外江戏班的大量涌入,潮汕地区逐渐成为了一个戏剧文化的交汇点。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为了适应这一文化交流的需要,外江戏班在潮州上水门区域捐资兴建了“外江梨园公所”。这里不仅是他们的集会场所,也是各类文化活动的举办地。
康保成、陈志勇认为,外江戏进入粤东潮汕地区,其中一条重要的路线是从赣南,经闽西,再至大埔、梅县,最终抵达潮、汕。另外两条路线,一条由广州至海陆丰,至梅州,再顺梅江、韩江到潮汕;另一条是直接从陆路,即从赣南的赣县,再经寻乌,陆路80里进入梅属诸县。三条不同的路线图都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息:即外江戏进入粤东,首先到达的就是以大埔、梅州为代表的客属聚居地,并在此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驻点[5]。此观点与民国时期潮戏研究专家萧遥天的论述相契合。他曾明确指出:“外江戏之入广东……其流入之路线必由闽西赣南经客家繁布之梅属诸县。[6]”“外江则自安徽播赣南、闽西,经客族嘉应州而至。[7]”
鉴于当时梅属客家地区经济基础尚处于发展阶段,大多数具备实力的外江戏班并未选择在此长期发展,而是转向了粤东经济中心——潮汕。但不可忽视的是,从此时起,客家人便深信外江戏正是他们的祖先南迁之前,在中原地区所演唱的戏曲。穿越客属各县市,这些外江戏班无疑也感受到了客家民众对外江戏艺术的浓厚热爱和期盼。
2 汉剧与客家文化的融合
在清代同治至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时期,外江戏在潮汕地区达到了繁荣的高峰。这背后的成功源于多方面的推动。首先,潮汕当时经济繁荣且社会稳定,为外江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加之潮州的本地戏剧相对较为落后,外江戏因此得以迅速崛起,填补了文化空白。再者,由于清代的“回避制度”[8],导致大量在潮汕的官员都来自外省。这些官员自然偏爱他们熟悉的、使用中州官话的外江戏。他们对外江戏的娱乐需求和喜爱,无疑提高了其在潮州的影响力。此外,外江戏以其儒雅细腻的风格与潮汕文人尚雅的文化审美完美契合,因此深受他们的青睐。许多文人因此纷纷组织各类社团,如外江音乐社、汉乐儒乐社等,进一步推动了外江戏在潮汕的普及和流行。可见,光绪年间,外江戏在潮汕地区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展现,更是体现了当地士绅崇尚古典雅致品位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这种戏剧形态汇聚了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之精髓,深得坐轿、有闲的社会精英们的钟爱,外江戏也被赋予了高雅精英文化的属性。
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清朝统治政权在潮汕地区的逐步崩溃,原来热捧外江戏的外籍清廷官员相继离开粤东。与此同时,使用当地方言的潮剧开始崛起并逐渐成形。潮剧不仅吸纳了外江戏等各种艺术的精髓,更在对其艺术形式的创新中,敏锐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满足了潮汕观众的审美需求,迅速受到潮州观众的喜爱。另一方面,曾经盛行的外江戏,因其守旧的艺术态度和远离革新,逐步在潮汕文化中失去影响力。为了开辟新的生存之路和艺术路径,外江戏开始从潮汕城市向客家山区转移。此后,外江戏班只是在每年重要的赛神活动时节,才由墟镇赶回潮州,候场待聘[9]。这不仅是地域的转移,更是一场深度的文化融合与转型。外江戏与当地的民俗活动及习俗的交融,使其不再仅仅是士绅精英的艺术品位,而是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与他们的传统和文化习惯紧密相连。换言之,如果“娱乐”仅仅是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以提高生活质量的话,那么,习俗的需求就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而是生存的必需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在1939年潮汕沦陷后,粤东的外江戏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导致多数戏班解散。在这关键时刻,客籍艺术家罗梅波与萧道斋站出来,分别成立了“同艺国乐社”和“新老福顺班”。这两大社团不仅传承了广东汉剧的演出传统,更关键的是,在逆境中保全了外江戏的核心成员,为该剧种的延续提供了条件。到了1950年,基于客属之地的这两大戏团的底蕴,大埔与梅县相继成立了“大埔民声汉剧社”与“梅县业余汉剧研究会”,两者逐步演变成今天的广东汉剧院。
3 结论
综上所述,从民国到建国期间,客家人钱热储将外江戏正式命名为汉剧。这一改变不仅涉及到名称,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地理和受众的广泛转型。汉剧的舞台中心从潮汕向客家山区转移,其主要受众也由潮汕城市的上层精英转为客家地区的广大民众。这标志着汉剧从精英文化走向了民间大众文化,并与客家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紧密结合。此外,当汉剧遭遇历史低潮,客家人以其深厚的包容性接纳了这一艺术,为其提供了避风港;而当汉剧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客家人再次挺身而出,确保了其传统得以延续。
究其背后,粤东客家族群与汉剧之间存在深刻的历史和文化缘由。客家族群,经历了从东晋五胡乱华到南宋末年元蒙南侵的五次大规模南迁,前后累积了近千年的漂泊与迁徙历程。这种历史沉淀为客家人打下了一种对故土、对历史的深沉情感基础。汉剧,源于中原,其使用中州官话作为戏曲语言,对于南迁的客家人来说如同乡音般亲切。这不仅唤起了他们对祖地的怀旧情怀,更与他们的审美追求——崇尚古朴与典雅的风格相呼应。汉剧的舞台语言和审美取向与客家人的文化和审美心态产生了共鸣,为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情感与文化的双重连接。更进一步,汉剧为客家人提供了一种对于族群来源的追溯与情感寄托,成为了他们自我身份的重要标识。在这样的互动中,客家人与汉剧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与成全的关系:客家人为汉剧提供了新的生命力,而汉剧则在文化上滋养了客家族群,加深了他们的自我认同。■
引用
[1] 钱热储.汉剧提纲[M].汕头印务铸字局,1933.
[2] 陈志勇.广东汉剧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3] 余勇.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D].广州:暨南大学,2006.
[4] 冼玉清.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3):105-120.
[5] 康保成,陈志勇.广东汉剧与客家文化[J].学术研究,2008(2): 146-152+160.
[6] 萧遥天.潮州戏剧音乐志[M].马来西亚:槟城天风出版公司,1985.
[7] 萧遥天.潮州志·戏剧音乐志[M].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
[8] 刘嘉林,何宪出.回避制度讲析[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0.
[9] 谢雪影.潮梅现象[M].汕头: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资料科.民国廿四年铅印本,1935.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之子课题“口头语言类民俗艺术研究”(22DZ0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子熙(1988—),男,甘肃庆阳人,博士,就职于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通讯作者:李恩卉(1993—),女,安徽亳州人,博士,就职于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