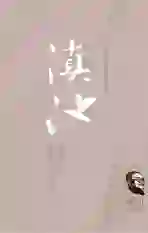眉毛记(短篇小说)
2023-05-30王祥夫

王祥夫 著名作家,画家。文学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美术作品曾获“第二届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奖”、“2015年亚洲美术双年奖”。
怎么说呢,飞机离起飞还有两个多钟头。魏马就一直坐在那里看书,他把头垂得很低,他戴了顶帽子,他一般很少会戴帽子,朋友们都也知道魏马不怎么爱戴帽子,他最近去发廊做的锡纸烫头发尤其好看,他喜欢那种蓬松的感觉,但他这次出门不戴帽子不行,他没办法不戴帽子,这是件没有办法的事。
魏马吸了吸腮帮子,用手摸了一下左边脸。
魏马想把手里的这篇小说看完,小说里写一个人在夜里总是感到害怕,总觉得会有坏人从外边撬开门闯进来,为了这事他总是睡不好觉,所以他给自己做了一个金属的脖套,睡觉的时候就把这个脖套套在脖子上,这么一来他就认为即使有人从外面闯进来也不会把自己掐死或者是用一根很细的钢丝把自己勒死。读小说的时候魏马觉得这种事一般不会在生活中发生,除非你得罪了什么人,或者是你干了什么坏事,魏马一边看这篇小说一边想,人身上最薄弱的地方确实还是脖子,晚上在外边散步或平时在什么地方走路有人从后边袭击你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只须悄悄跟在你后边用手里的细纲丝往你脖子上一勒你就死定了。
魏马觉得自己以后也得做这么个脖套,金属的,外面包一层很棉的那种厚布,但这种脖套好像在冬天戴最合适,外面一穿衣服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但夏天戴好像就比较麻烦,当然不是不能戴。
魏马抬起头朝外边看了看,又有一架飞机起飞了,发出很大的轰隆声。飞机场候机厅的四面从上到下全是大玻璃,可以从里边看到外面。这是现在几乎所有飞机场的建筑模式。天现在好像是又晴开了,原来报告说是有雪,但现在的阳光很淡薄,不过冬天的阳光向来都是这德性。魏马知道内蒙那边现在正在下很大的雪,已经冻死了不少羊,他已经看到那张照片了,死羊堆积得像座小山。
魏马的朋友小铁现在还被困在雪里,只不过小铁不像那些羊,他给自己找了一家小旅店,房间因为没有窗户而很便宜的那种,虽然没有窗户但在靠南的那面墙上很装逼地拉了一道窗帘,你要是拉开窗帘就会发现后面只不过是一堵墙。
小铁发短信说他本来很快就要到家了。
“想不到会下这么大的雪,高速公路完了。”
“所以说下雪真是个麻烦事。”魏马说今年的雪怎么下得这么早。
问题是,小铁身上的衣服很单薄。魏马想了想,他想把小铁穿的是什么衣服想起来,他们分手还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天气还不这么冷,但魏马记不起来了,他让小铁给自己发张照片过来看看。
“就是想看看你现在什么样?穿什么衣服?”
跟几乎和所有在机场候机的人一样,魏马是一边看书一边看手机。魏马把帽子压得很低,低到帽檐儿一直遮住了眉毛。也就是在这时候魏马听到了飞机晚点的广播。
“他妈的!”魏马站了起来,在心里骂了一句,他看看左右,觉得自己应该去吃点什么东西,薯片?汉堡包?这些他都吃腻了,候机大厅的一层那边可以吃到很好的面条,魏马比较喜欢面食。
魏马拉着拉杆儿箱下了楼,往右拐,那边没几个人。面条上来的时候小铁发来了照片。他发现照片上的小铁嘴角处长了一个疙瘩。
“你可真是憋坏了。”魏马马上发了一条短信。
“好长时间没做手工了。”小铁那边的短信也嘻嘻哈哈地发了过来。
“好吧,这种事几乎人人都在做。”魏马在短信里说。
这时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很胖的女人在他旁边的那张桌边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香气一下子就朝魏马这边飘了过来,魏马不知道这是什么香水,怎么会这么香?魏马从侧面看着这个很胖的女人,双下巴,或者应该是三个下巴。她也点了一碗面。魏马忽然希望她最好应该还有点别的什么举动,比如和那个一直在看手机的服务员说点儿什么?或者是挑挑她的毛病,但什么也没有,这个胖女人好像除了吃面别的什么也不想,所以注定不会有什么新鲜的事。魏马又朝她看了一眼,这个胖女人长得挺一般,就是皮肤很白很好,但这样的女人根本就不可能带给自己任何想象。
魏马这时候很想想想女人,毕竟离登机还有很长时间,自己总得打发一下时间。魏马就又给自己要了一杯热牛奶。
服务员把牛奶端过来的时候魏马又忍不住朝那边看了一眼,这个红衣胖女人靠鼻子那地方长了一些雀斑,因为吃面条,她已经把红色的外衣脱了,就搭在她对面那把椅子的椅背上,这样一来她就显得更胖,魏马只能看到她的侧面,就觉得她胸脯那地方很好看,她穿的那件白毛衣真是很性感,把线条都一一勾勒了出来,胖人穿衣服很容易达到这种效果。
这时又有一个人走了过来,这个人胡子可真重,现在留胡子的人很少,除非他是个阿拉伯人。这个人可能很长时间沒刮他的胡子,所以他的胡子显得很重,这人手里还拎着一个包,很一般的那种帆布大包,里边鼓鼓囊囊塞了不少东西。魏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外出打工的,打工的现在坐飞机的也很多。
柜台里边的女服务员朝大胡子走过来,她想问问他要点什么。大胡子把头一下子抬了起来,他上面是那种很大的图,图上是一碗面,紧挨着还是一碗面,再看,还是面,分别是牛肉面、鸡蛋西红柿面和猪肉臊子面,每一种面的上面还标着价钱,但都不便宜。魏马忽然又希望这个大胡子会闹出点什么动静来,比如大声说话,质问那个女服务员这地方的面为什么这么贵?但这个大胡子什么也没说,他一转身去了旁边,旁边是机场的小超市柜台。魏马看着他去那边买了一桶方便面,紧接着魏马就看见他去了机场紧靠洗手间的热水器那里去泡他的泡面。魏马觉得自己好像想起了什么,对了,魏马明白自己是又想起了为什么几乎是所有的机场的饮水机都靠近卫生间?为什么?这种问题也许会在百度上查到,但魏马不想查。
魏马看看手边的牛奶,他想让牛奶再凉凉,牛奶不错,结皮了。
那个大胡子把面泡了一会儿,然后就靠着饮水机“唏哩呼噜”吃了起来,魏马看着那边,很想向他招招手让他坐过来,这边吃面的人也没几个,椅子都空着,魏马还朝服务员那边看了看,那个女服务员从魏马一开始坐下来吃面就一直在不停地看手机,她的手机上滴哩嘟噜不知挂着一串什么零碎。
魏马又朝大胡子看了看,希望他过来,魏马都想好了,只要他一朝自己这边看自己就会朝他招手让他过来。但大胡子一直不朝这边看。大胡子吃面的声音很响,“呼噜呼噜、唿噜唿噜”,这种声音能让人产生一种饥饿感,或者是让人想再吃点什么,他妈的。大胡子很快就吃完了,饮水机旁边一般都会有个垃圾桶,大胡子已经把泡面的纸筒扔在垃圾桶里了,接着是擦嘴的餐巾纸,接着是,他提着他的大帆布包去了洗手间。
魏马吸了吸腮帮子,左边那颗牙已经疼了好长时间了,他已经吃了好长时间的“替硝唑”,还时不时会加一颗“芬必得”,魏马弄不清楚自己这是要掉牙还是要长牙,为了这他还去路边牙医那里问了一下,那个精瘦的牙医坚持要让他去挂号,他对牙医说我只想问问这边的牙是要掉还是会再长出一颗新牙。瘦牙医的态度很明显不想和他多说什么,只对魏马说了一句:
“一切皆有可能。”
因为吃面魏马觉得自己已经热了起来,他不经意随手就把帽子摘了下来,旁边穿红衣服的胖女人马上就吃惊地张大了嘴,还忍不住“啊”了一声。魏马马上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魏马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么粗心大意,怎么会把帽子摘下来?便马上又把帽子重新戴在了头上,并且把帽沿往下拉了又拉。
魏马用眼睛的余光看着旁边的红衣胖女人,她还在朝这边看,这女人可真胖。
这时候广播响了,通知坐FD2这趟航班的人们开始安检。
魏马站起身来,把手机拿好了,从左一把右一把的椅子间走过,吸着腮帮子往安检那边快步走,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前边居然就是那个大胡子,这时又有一架飞机轰然降落了,声音很大。
魏马可以从大玻璃墙看见这架飞机的灰色尾翼。
“咱们可能就是这架飞机。”魏马听见自己对走在前边的大胡子说了一声。
“这架飞机不小。”大胡子说,明白魏马是跟他说话。
“大飞机安全。”魏马说。
“我也喜欢大飞机。”大胡子一说话魏马才明白这其实是个年轻人。
“对,安全。”魏马说小飞机总是在空中颤抖。
“如果碰到气流的话。”魏马说。
大胡子没说话,显然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强气流。”魏马又说。
“什么是强气流?”大胡子说。
“就是很强的那种。”
魏马觉得这个大胡子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怎么连强气流都不知道?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安检口了,年轻安检员坐在玻璃柜台朝他们看了一眼,那只能说是玻璃柜台,就好像商店收款的那种。不同的是里边有一个摄像头,还有一个可以给手消毒的那种一按就往出呲水的塑料瓶子,机场要求人们过安检的时候必须要往手上挤一点那种粘乎乎的液体,好像这已经成了安检的一部分,登机口那边也还有一个这样的瓶子,登机的人在登机之前还要再次往手上擠一点那种粘乎乎的东西,好像那也成为了登机的一部分。
大胡子进去了,但很快他被拦了下来,好像他的包里出了点什么问题。因为安检口的磨砂玻璃门遮挡着,魏马只能看到大胡子的一部分,他的后背、屁股、还有后脑勺。里边的安检在盘问他什么,声音并不严厉。但魏马听不太清。他只听见大胡子在里边不停地解释“这是瓦刀,这是瓦刀,这是瓦刀嘛。”这时坐在玻璃柜里的那个年轻安检用手指敲敲桌子对魏马说请他把帽子和口罩都摘一下。
“你朝这边看。”年轻安检指了指摄像头。
魏马的问题就出在摘帽子上,他把帽子摘下来,过安检当然必须摘帽子。
“你不能过。”年轻安检员看了一下魏马的身份证,忍不住笑了一下。
其实魏马早就知道安检会来这么一手,但魏马还是问了一句,“为什么?”
“你的脸和身份证不附。”安检说。
“你能不能听我说。”魏马说,魏马想把眉毛的事讲一下。
“你对我说没有用,这个不让你过。”年轻安检又指了一下摄像头。
立在那里的黑色摄像头很像是外星人的小脑袋,瞪着一只眼。
“你听我说。”魏马又说。
“下一个。”年轻的安检让下一个过来。
魏马回头看了一下,后面居然是那个很胖的红衣女人。
“我怎么办?”魏马小声问那个年轻安检 。
“下一个。”年轻安检说,没看魏马。
“这全怨我那个室友。”魏马嘟囔了一句。
魏马的室友,当然现在不是了,他们一从学校出来就根本不可能再住在一起了,魏马和这个室友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们的关系突然好起来是大三那年,因为有一次魏马在篮球场上出了点小事故,两只手上缠满了绷带,这样一来,他就只能让室友帮他的忙,比如洗脸和洗脚,室友还帮忙给他洗臭袜子,那是夏天,天很热,魏马既然去不了浴室,室友还会给魏马擦身子,这么一来呢,他们的关系忽然就不一般了,起码在别人看来是这样。
前几天,室友请魏马过他那里去吃烧烤,顺便想让魏马见见他的新女友。魏马现在没有女朋友,他的前女友一个人去了西藏,但前女友的母亲还经常和魏马时不时通个话,魏马前女友的母亲没有丈夫,她们早就离异了。魏马前女友的母亲甚至说你那会儿让她怀上孩子就好了,女人只要一有孩子就不会到处游荡了,更不会去西藏。魏马的前女友的母亲好几次都要请魏马出来吃饭,魏马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就连一次也没去。
“你们是不是每次都采取措施?”
有一次,魏马前女友的母亲居然在电话里这么问魏马。
当时魏马一边接电话一边正在穿鞋,但一下子了怎么也穿不进去了。
“丈母娘这么问可不是什么好事。”魏马的室友对魏马说。
其实那时候魏马还没下定决心和女友分手,魏马和女友分手多半是因为她的母亲,她怎么可以那么问话?魏马不想给自己找一个这样的丈母娘。
一般人以为吃烧烤会去郊外,但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魏马的室友住在最高的那一层,这你就明白了吧,站在他上边的露台上只能看见下边那些大树的树梢。他们要在露台上烧烤,其实这事也没有什么好讲的,肉是晚上魏马的室友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已经腌入了味,是事先剁碎的那种肉,用调料拌了一下,然后用手团成一个一个的大丸子再穿在竹签上就行,这种烤肉的好处是既容易入味又容易烤熟。问题是出在烤肉的时候魏马想把火弄旺一点,因为魏马喜欢吃烤的很有嚼头的那种,他弯腰吹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火一下子就回到了他这边,露台上也没有风,但“呼 ”的一下子一个火苗子就冲着他来了,就这么回事,他当时一根眉毛就没了,是右边这根,其实不是全被燎没了,还多少有点毛碴,但朋友们说还不如把它们全剃了,眉毛这东西会马上又长出来。所以说,魏马现在的脸上只有一根眉毛,魏马的皮肤很白眉毛很黑,这么一来呢,魏马的那张脸可真是太特别了,一张脸上只有一根眉毛,而且特别黑,这可真不是一般的特殊。
“我呢?怎么办?”魏马还站在那里,他又小声问了一下。
“你不能过去,你和身份证不附。”安检对他又说了一句。
“你听我说好不好。”魏马想把事情讲一下。
“你自己去想想办法,你一根眉毛绝对不行。”安检指了一下那个摄像头。
“要开证明吗?”魏马听见自己这么问了一句。
“什么证明?”年轻安检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时魏马后边的那几个人也已经看到魏马的那张脸了,有人在后边笑出了声。这让魏马很恼火,这时里边的说话声也大了起来,是那个大胡子还在和里边的安检争论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魏马很想知道里边出了什么事。“你必须托寄。”里边的安检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瓦刀,但我们知道这是刀具。”
很快,魏马就看见那个大胡子很生气地从安检另一边的一个通道冲了出来,他真是冲了出来,手里拎着一把瓦刀。大胡子经过魏马身边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笑了一下,这就让魏马可以来得及问他一声。
“你怎么又出来了?”魏马紧跟着大胡子,问。
大胡子边往那边走边让魏马看他手里的瓦刀。
“他们不懂这是瓦刀。”大胡子说。
“那你要干什么。”魏马觉得这回可能有乐子看了。
“我能做什么,我只能去托運。”大胡子说现在很难买到这么好的瓦刀了。
“一把瓦刀怎么托运?”魏马还紧跟着大胡子。
“总会有办法的。”大胡子说。
“这也太麻烦了,你就不会到了地方再买一把?”魏马说。
“这把瓦刀使出来了,太顺手了。”大胡子又说,大步往那边走。
魏马停了下来,不再紧跟着大胡子了,魏马眼看着大胡子去了托运打包的那个地方。那地方没多少人,堆了几个打好的箱子,还有一辆机场推东西的那种小车,正被一个小屁孩子推的转来转去。
“先想想你自己吧。”魏马听见自己对自己说,大胡子的瓦刀和你又没什么关系,先想想你自己怎么过安检吧。魏马现在已经明白那个大胡子可能是某个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了,这又有什么意思?没意思。魏马想出去先抽支烟,他看看左右,这时候他太想抽烟了,一边抽烟一边想想自己应该怎么办,好在离飞机起飞还有好一阵,飞机晚点这时候倒像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烦死了!”魏马对自己说。
魏马已经透过玻璃看到外边正有几个人在抽烟。从机场候机厅里一拥而出的人一般都会马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急不可待地去抽烟,一部分急着去打电话。魏马到了外边,他给自己点了一支烟,这口烟可吸得真够长的,也很舒服,吸烟有时候就是很舒服。这时候一个女孩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她把鞋子一下子脱了,魏马不知道这个女孩要做什么,但他马上明白女孩儿的鞋子里可能进了砂子,这会儿她已经弄好了,这女孩忽然看着魏马笑了起来。
“你别笑。”魏马知道女孩笑什么。
“你怎么一根眉毛?”女孩说。
“以后不吃烧烤了。”魏马说。
女孩又看了看魏马,“你这边的眼睫毛也没了。”
魏马不想多说什么,他想出来吸支烟好好儿想想自己应该怎么过安检。他在心里轮番把几个朋友都想了想,但觉得他们都不靠谱。
“是不是安检不让你过?”女孩说了。
“是,一根眉毛的不让过。”
“你跟他们好好儿说说。”女孩说。
魏马对女孩说,“是那个摄像头不让过。”
“你对他们好好儿说嘛。”女孩又说。
“说了也没有用,摄像头就是不让我过去。”
“我对你说,那你就画一根呗。”女孩小声说。
魏马几乎要大声叫起来,他根本就没想到还会有这一手。
“画一根?”魏马看着女孩,“我怎么没想到?”
“你画一根。”女孩说她这里有眉笔。
“对,那就画一根。”魏马忽然开心起来,这挺好玩儿的。
“你画吗?这个不复杂。”女孩说。
“对,给我笔。”魏马奇怪自己怎么刚才没想到这一手。
女孩把她的笔从小包里“唏哩哗啦”地翻腾了出来,递给了魏马。
“要不要镜子?”女孩又说。
“我最好还是去洗手间吧。”魏马想想,说。
“你的样子好奇怪。”
女孩又笑了,她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只有一根眉毛的男人。
“要不要我给你画?”女孩说。
“我还是去洗手间吧。”魏马看着女孩,有点迟疑,一个大男人让一个女孩当众画眉毛总是有点不好吧,再说自己还不认识这个女孩。
“我还是去洗手间吧。”魏马又说。
魏马在洗手间对着镜子给自己画眉毛的时候小铁发来了信息,说那边的雪已经够一米深了,“再继续下的话二楼就有可能就要变成一楼了。”
“好家伙!”魏马的语音短信只有三个字。
小铁在手机里发短信又说他刚才胡乱吃了个盒饭。
“他妈的,飞机又晚点了。”魏马又对着手机说了一句。
“盒饭太不像话了。”小铁在短信里说。
“怎么不像话?”魏马又发一下语音。
“一点点菜一点点饭外加一颗鸡蛋。”
……
魏马很想跟小铁说说自己现在正在做什么,这一点小铁肯定不会想到,想不到自己正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画眉毛,魏马觉得那个在外边站着等他的女孩人挺好的,而且她恰好还有支眉笔。魏马心想女人们肯定都会在小包里放一支眉笔,那个胖女人的包里也肯定会有。魏马这时候又想起那个穿红衣服的胖女人来了,想起她的那个侧面,说实话她那个侧面挺性感,人们都喜欢性感。
魏马把脸凑近镜子,再凑近,因为下边有洗手池子,他的身子朝前倾着。
魏马的眉毛差不多已经画好了,好在这时候洗手间里几乎没什么人,魏马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还不错,他退远一点又看看自己,真还不错,自己画的这根眉毛跟那根没被燎掉的真眉毛差不多,但好像是重了一点,魏马想好了,自己也要去买支眉笔,在眉毛长出来之前就每天用眉笔画一下。
魏马对着镜子画眉毛的时候很担心有人会进来,但机场的洗手间一般人不会太多,但要是碰上航班到港,洗手间里就会一下子挤满了人。魏马对着镜子画眉毛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进来了,那个年轻人朝魏马这边瞟了一眼,愣了一下,好像马上就被魏马吸引住了,这个年轻人找了好几次小便池才决定使用最靠外边的那个,因为只有站在那个便池边才能看到这边有个男人在对着镜子画眉毛。
魏马也注意到年轻人在看自己了,这是个很帅的年轻人,穿着白色的那种带帽衫,下边是一双白鞋子,后边是一个双肩包。
“我一根眉毛被火燎没了。”魏马突然回头对那个年轻人说,他想解释一下。
年轻人在听,魏马的声音可不小。
“安檢那边过不了。”魏马又说。
年轻人听着,但还是不吭声。
“我只好画一根。”魏马说真拿他们没办法。
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年轻人一直在听,并且一直朝这边看。
“没办法我只好画一根凑数。”魏马又说,觉得自己这句话很幽默。
那个年轻人一句话也没说,但一直在看他。
魏马忽然转身朝那个年轻人走过去,他要年轻人看看自己的脸,自己真是一根眉毛,“你看一下,过不了安检我只好画一根。”
那年轻人把裤子已经提起来了,但还是没说话,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你说我能怎么办?”魏马又说,“我只能画一根。”
那个年轻人还是不说话,转身朝外走了。
“眉笔是好东西。”这回是魏马自己对自己说了。
魏马又回到镜子跟前,他想好好看看自己,离近了看,那根画的眉毛可真够糟糕,但离远了看还不错。魏马听见自己又对自己说,“只要过了安检就可以。”魏马想好了,只要一登机,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到飞机上的洗手间里把这根临时性的眉毛洗掉,只要帽子戴得低一点谁也看不到自己是一根眉毛。
“或者就把另一根眉毛也刮掉。”魏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画好眉毛收拾好东西,魏马朝外走的时候心想待会儿自己过安检还用不用再从头排一次长队,他不想再排长队。出了洗手间,他看见那个女孩了。
“好女孩。”魏马在心里说。
“你真好。”他对女孩说,把眉笔还给了她。
女孩看着魏马突然笑了起来:“你画得还不错。”
“我得过安检了。”魏马说。
“你真好,谢谢你。”魏马又对女孩说了一句。
“不用谢。”女孩说。
魏马忽然又转回了身,快走两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和女孩加一下微信。魏马此刻想起了那个精瘦牙医的那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再次过安检的时候,那个年轻安检员的神情多少有些古怪。
魏马闻到了咖啡的香气,也看到了年轻安检员手边的一个小金属滤网,他知道年轻安检员在喝咖啡,也知道他手边的杯子里是咖啡。
这下你可以过了。年轻的安检员对魏马说。
进安检口的时候魏马和那个年轻安检员又互相看了一下,那个年轻安检甚至还笑了一下。
咖啡的味道可真香。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