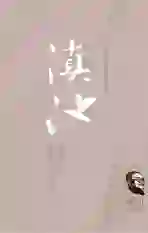螳螂川畔
2023-05-30芳菲
芳菲
1.并非都跟富民有关
写富民前,想先写一条河。
河叫螳螂川,是昆明滇池唯一的出海口。螳螂川出滇池后,一路流经安宁、富民、禄劝,最后注入了金沙江。因为金沙江的存在,高原明珠滇池里的水,有可能流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去,或者更远一些,流到太平洋里去。古滇国和大上海,高原明珠和国际大都市,东边日出西边雨,其间是否有着关联?
站在螳螂川边,如此一想,觉得这事有趣起来。
一滴水的去流轮回,尘世之间,是极细小的事情,因其卑微,又不起眼,很少有人去关注,去联想。一条河的风物、掌故、脾气和秉性,则不然。人间烟火在,民以食为天,临河而居的人家,自然会把一些情感掺杂到河里面,比如哪天河要涨水,哪天鱼要摆子,哪天河里边会突然就冒出了个水怪来。知任一县的官家,会对一条河流感兴趣,比如疏浚河道、下泄洪水,比如寻津设渡、畅通关梁。毕竟到任一方,治一域民,自然会把有司的责任和担当记存到史料里边,给自己一个交待,也给河流和田园一个交待。文人迁客则不同,处江湖之远,离庙堂之遥,寄情山水是一种常式,归隐田园同样有人在做着选择。苦闷失落时就着景致诉苦明志,春风得意时就着景语抒怀情语,若是机缘巧合,好景致遇上了好文采,便可字字珠玑,流传久远,入史入文。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何时少过江河情、他乡月、缸中酒、花间泪、柳下魂?
想来是这个理。
前往富民县,一定得到河边去走走,回顾富民艺文志,螳螂川上,还真有过一些故事。
印象中,螳螂川是有景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水质优良,清可见底,可当镜子照。河里常年能捕捞到红鲤鱼、白鲦鱼、黄鳝和小弯斯,都是当地百姓最得意的待客佳肴。弯斯这种细小的鱼吃起来别有滋味,又嫩又鲜,可煎可煮,佐一碟酸菜,或两几撮薄荷,三五截葱段,味味相生,汤汁相宜,热热地吸溜一口鲜汤,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或是极小心地夹一尾鱼干,脆生生送入口中,叫人舌尖连着牙缝美。至于河边花草,只一样就让人沉醉不已。别的季节不说,两岸油菜花开时,一川金黄,一河碧波,一天深深的蓝,简简单单搭在一块,就是一幅画。上游河道较宽,江水如带,环绕群山,风光清丽。因为流速较缓,多河曲阶地,多村落聚集,故而这个时节螳螂川畔花香四溢,招蜂引蝶,赏花者甚众,很是热闹。
再者是,螳螂川何以叫此名?一直不得其解。此行去富民,于其间正好寻一寻答案。经查《云南通志》,曾对此有过注解。说是此河自海口出安宁过富民,河中多沙洲,其状如螳螂,所以叫了这个名。但我对此有过疑问,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硕大的螳螂,这与“螳臂挡车”“螳螂捕蝉”的成语意义是相悖的,也就有些不大相信。再者,记忆中螳螂这虫是见过的。小时胆小,见到螳螂就脚软,脚软干脆就蹲在牛圈旁或是田埂上,螳螂不动我不动,螳螂一动我就跑,所以,总有机会好好地去观察这种虫。既见过绿色的螳螂,多在父亲割回的草青料里藏着,牛嘴呶过青草料,时有螳螂溜出来,想是闷在青草料里久了,焐晕了的螳螂蹩在牛嘴旁边动弹不得,我胆怯着瞎着急,生怕牛儿把它当成散落一旁的青草料。好在,后来结果还好,两不相伤,牛儿归圈时,牛嘴上的唾液还在,螳螂却不见了。土黄色的螳螂多在水田埂上遇到,儿时稻田里偷谷花鱼那阵,常见它们静静地守在埂上,借着谷穗和四叶草的遮掩伪装,猎捕一种叫土狗的昆虫。亲眼见过的螳螂,不管色泽如何,总与河中的那些沙洲难以关联上。如今细想,大概可以这样推断,因为沿河两岸土地肥沃,人烟稠密,主产稻米,物候环境相宜,田间水际多有螳螂捕食昆虫,益助农桑,共享田园。
河边,田头,螳螂多了去,所以呼称螳螂川。
更主要的,还另有一个事实存在。此虫长得虽然丑陋,三角之头,细弱之胸,“镰刀”之手,身在虫界而非害虫,守在田园却不盗食。这只不害人、不害牲口、不害庄稼的虫,这只被词典讥笑过、嘲弄过、误解过的虫,终于在中国昆明的一条河上,修成正果,为己正名。
虫事说完,再说一说文事。
富民螳螂川上是来过两个有名的文人的。
一个在明朝的月夜里来,叫杨慎。留下了《螳川独泛》一诗:月游浑似昼,水泛不知寒。星罾惊鸟跃,双枝起鹤盘。一个于清朝的午时间到,叫袁天揆。也留下了《过安宁有怀》一诗:一片螳川水,纡回入大江。浮将碧鸡色,飞上木兰艭。我甫来京口,人先去石淙。风流两地尽,惟有浪舂撞。
再往下追究,这件文事也同样变得有趣起来。
杨慎和袁天揆,一人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一人生于清乾隆庚午年,同为各自时代的文章大家、诗词高手,都有急公好义之举,悲天悯人之心。以260多年的时空跨度,隔着不同朝代,作山水之约,同赴一条河,抒怀螳螂川。
对于一条河来说,当然就变成一件幸运的事情了。
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同时,还是一个充军要犯,因為博学多才,刚直不阿,加上嘴碎,逆鳞廷杖,十天之内被皇帝连打了两次屁股,差点没活过来。一路波折,幸有爱妻千里送行,历经多难,来到不毛之地云南保山。腚没好完,人家就又急火急燎地坐下去,青灯黄卷,写史列传,气没调匀,人家偏爱游山玩水,一玩玩到了螳螂川上。清代“保山二袁”之一的袁天揆,同时,还是一个独行侠客,因为朋友众多,志趣相投,既能独行江浙为主筹资解难,又能交心各方文士,终成心中诗文巨著。在其客居昆明期间,同样来过螳螂川。
基于杨慎、袁天揆两人的人品和文采,他俩曾经为昆明螳螂川的留诗,从文化积淀和文脉传承的角度看,至今说来,都是值得记忆的,对这种关联的追思和探究,必定也是有所裨益的。
写了这里,另有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也露出头来。
杨慎谪戍的地方在保山,毕生撰写重要著述的地方在保山,而云南清代本土著名诗人袁天揆的出生地,恰恰是保山。循着文人风骨传承的脉络去梳理,去往深处想,其间可能有着一定潜在关联,也未可知。
即便此事并非都跟富民有关。
2.夜读《康熙富民志》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在富民举办的一个名为“梅香富民”的笔会。此次出门,好在遇上了燥热之后的一场及时雨,又好在有高速公路可以走。
富民县通高速是整十年前的事,早些年间走108国道老路段,从昆明普吉一路向北,过天生桥、西游洞、百花山、麻地垭口、崇德老街、大龙潭,一路绕山绕水到禄劝,车子颠簸得厉害,村庄记得就多。现在走高速公路,车子快了,却只关心交警、雷达和油站,老富民的记忆反而渐渐地远了。
富民越来越近,雨停了,我渐渐焦虑起来。
“梅香富民”,梅是引子,香是酵母,富民是主菜。摘了人家的杨梅,吃了人家的羊肉,听了人家的民歌,理所应当人人都要出作品。何玉虹、赵昌敏老师来自美协,画作刊载过《滇池》杂志,想来已是心中有底,手里不慌。
入夜,无事。
翻开《康熙富民县志》,我终于安静了。
富民不大,小县。四围俱山,较省微热,河流萦绕,虽暑不酷,无熇蒸之气,得清爽之宜。民无他营,以耕为业,终岁之计,取给畎亩。
这段话,原原本本摘自富民的老县志,短短42个文言字,已将富民县的气候特征和产业特色写得准确而又生动,且不劳心费力。
话多不甜,言多必失。小时候老人的传统教育就是这样关照的。所以,我是一个木讷的人,这是我喜欢文言的重要理由。
灯影下,书卷里,富民县令彭兆逵这个老古人让我兴奋起来。
老志书上的寥寥数语,由此关联的片言只字,他就活脱脱地站在了眼前,让人过目不忘,还有了记住他一辈子的强烈冲动。向来有一个观点,要真实地了解一个陌生的地方,阅读当地旧志是条捷径,虽然,一般人读起来会有些困难,但有两个好处倒也明明白白。一是因为时间久远,历代核证,资料可信度较高。二是因为文言撰就,言简意赅,可联想的空间就大。人世间,相信一个人很难,不信一个人容易。相信,需要岁月,不信,就一个瞬间。面对古人,认识他,相信他,近而爱或者恨,不读旧志,不查旧档,不研旧史,也就无所关联。
就拿富民县令彭兆逵来说,富民人都信他,一信就是三百年,至今没有一丝丝怀疑。他死时,一坝子的人哭着送他的棺材回原藉,他死后,富民人民为他建了“彭令遗爱祠”,就是一个见证。
史载,彭兆逵,字人淑,号陟瞻,江西赣州人,康熙丁丑进士。官山西太平县令。上任伊始,即汰冗役,革火耗杂税,苞苴(贿赂)斥绝,四境肃清。后因父丧丁忧守制。康熙五十年,服满补云南富民县令。因地抚绥,刚柔并用,民大悦服。
一位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到任,想要第一时间了解自己管辖县域的情况,看看土地和人口,查查营防和种子,却什么资料也没有,一头无绪之中,唯有那声叹息最重。好在,彭县令是个明白人,求人不如求自己,敢硬着头皮做首创。提纲挈领,新志速成,可偏偏又绊在费用上,无钱出书的难处还没解决,来自民间的灾情早已呈于案头。
康熙五十二年的五月天,富民县爆发了史上最大的一次病虫害。
这是一次大灾。同时,又算一件异事。
一坝子的虫在吃庄稼,对一个“终岁之计,取给畎亩”的农业县来说,可是天大的事情。几辈人都没见过的怪虫,黑压压逼走天上飞着的鸟,一县的人家不躲在家里害怕才怪。面对如此大灾,面对“通邑大恐”难题,彭县令如此果敢、如此沉着、如此用心地走向了田野。为安定民心,他亲自写了祭文,为快速平灾,他广泛做了动员,为表达决心,他斋戒了三日。在科技极不发达的时代,斋戒和祈祷,是消除恐惧安定民心的最佳良药。
民心安,则郡县治;郡县治,则天下平。
首修县志和重视农桑,是彭兆逵县令留给富民最大的两笔财富。前者,属于文化范畴,是创举,富民官方从此有了自己的志书,让真实的富民得以文字的形式存活到了今天。后者,属于治理范畴,是责任,富民的土地从此有了抵御虫害病害的底气。
斋戒,得有带头的人,祈祷,没有真诚的心不行。
富民事,无小事。
为官事,亦无小事。仅彭兆逵个人经历而言,他是我在老志书里认识的全中国最幸运的一个“七品”。做了两地县令:一地在太平县,一地在富民县。
想到这里,不由心底一笑。
“梅香富民”,眼前一县果飘香,杨梅红了,桃子熟了,葡萄甜了,无数的人们来了。合起手中的老志书,心底感谢着三百年前的这位老县令,他留给富民的抗灾经验,同样留在了“古滇泽国”“螳川流域”所有的土地之中。
即便今天,仍有借鉴的余地。
3.晨拜文庙
富民文庙,藏得并不深,在县城西边的卧云山下。
富民县的空气本来就很好,加上日前下过几阵透雨,现在又是清晨时段,所以想去看一看这个在昆明市域都有些名头的老文庙。
享受好空气,是它。文化探幽寻踪,也是它了。
这是采风的一个通式,新到一地一域,没见过的去见一见,没尝过的去尝一尝,吃本地菜喝本地酒聊本地事,古话里头界定为入乡随俗,现实当下叫“文化新发现”。富民县,地头不熟,人更不熟,怕坏了规矩,犯了忌讳,所以,我一直不敢离开潘兴泽老师半步。潘兴泽老师是个苗族文艺家,工作于禄劝县文化馆,地地道道的“富民通”,因为走亲访友的缘故,更主要的是比赛交流和剧本创作上的事头,富民一地他可没少来。昨晚我俩同住一屋,我看了一夜的富民老志书,他打了同胞一夜的电话。只是机缘不合,他的同胞都去省会昆明办事情了,那顿透透的酒最终没有喝成功。好在解乏提神另有一样东西在,我俩对烟草的敏感程度竟惊人的一致。两人一屋,三盒“玉溪”抽完,已是午夜时分。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所以,清晨起来,潘兴泽老师怏怏不乐的情趣似乎还在。
要不,我们去看看富民文庙?听说不远,就在山脚那边。
我试着邀约他,他却意外爽快地应了约。
年年來富民,都只会往山上跑,往喝茶处去。去一次庙就去一次庙吧,娃娃就要升学了,我们做老人的拜拜文庙,敬敬先师,自己安一安心,也替娃娃应一应事。
他从卫生间里捂着毛巾出来,我已将最后两支烟分享给了他。清晨新约的达成阻断了昨晚失约的不快。他又孩子一样高兴起来了,伴着这份情绪,我与稍显陌生的富民之间的距离正在拉近。
天放晴了,路上渐渐有了人语和车声。
富民文庙藏在富民县第一中学里头。
这个发现让我很愉悦。新城巨变、开发扩张、地价日贵的当下,如此传统的搭配还在坚守,依旧保留,执着延续。意外之外,多了敬意。
明万历四十八年始建于县城东门之外,规模甚丽,后来毁于兵燹。清康熙四十七年迁建于现址卧云山之麓。中建先师殿;左右两庑。前为大成门、棂星门、泮池;后为启圣祠,左为明伦堂,魁星阁在明伦堂之前,右为文昌宫。名宦、乡贤二祠,附于大成门外。物换星移,时光久了,眼前我们所看到的富民文庙,仅是清光绪十五年重建的部分遗存。大成门、先师殿、月台、崇圣祠等主体建筑还在,虽是破旧了些,依旧可见当年的风光。现在成了文物管理所,公布为富民县、昆明市两级文物保护单位,日日有人值班,屋屋陈列物什,时有观光接待。有人的房子就有了房子气,瓦檐不会腐得太快,柱脚不会蠹得太深,地皮和墙体就不大爱生霉菌和绿苔了。这是乡间生活的常识,也是父辈老人们的经验。
进大成门,特意记下了一副联: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兴学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大成,中国古代文化中最神圣的一个称谓,文化修为中最高的一个级别。古乐之中对其有着严格的界定,一变为一成,九变而乐终,直至九成完毕了,方可称“大成”。过此门时,我们的脚步很轻,很安静,没有说笑声。毕竟此门一过,就是先师殿。富民文庙供奉的先孔子雕像居中静立殿前台上,身前两侧为青石石刻护栏,中设台阶,一对青石麒麟左右相呼,阶间居中铺设一条青石盘龙。孔子雕塑后面,是金碧辉煌的先师殿。立门古朴雕花,立柱厚积朱丹,单檐歇山式的琉璃屋顶,想是年头久了,间生了些黄草和绿苔,无风不明显,有风时草就会动一动。
天地里,风雨中,先师孔子立于殿前,静伫台上,双手抚胸,目视前方。在富民文庙里一立就是400年,传承一县一域文脉,安定万千民众人心。
迎着东升朝阳,走出文庙之门,不经意间想起了守魂这个词来。富民文庙始建至今已经400年,供奉先师孔子已经398年,但有一点要说明,先师孔子在富民县的存在绝非这个时限,应该比这个时间要早得多。
文庙前是文昌路,像一条长长的扁担,一头挑着富民的文脉,一头担着新城的人气。这样说来,很是形象,却还是稍稍狭隘了一些。家庭生活离不开社会化,文化传承离不开社会化,城市新生离不开社会化,面对发展,“家庭之担”“文化之担”“城市之担”,其实都离不开扁担之下的众挑夫。扁担越长,挑夫就要越多,挑夫多了起来,扁担就不会断,路头也会稳很多。
走在文昌路上,思绪飘浮之中,两个艺术大师的形象终于清晰了。之所以想起他们,一来想到了“扁担和挑夫”的问题,二来关联着富民本身的文化沉淀,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人在中国艺术甚至世界艺术舞台地位上的存在。
廖新学,富民永定人。1900年出生,出身贫寒,父亲早逝,沦为牧童,坚强的母亲将他送往昆明当了学徒,学习绘画,先拜李鸣鹤先生学习绘画,后得日籍教师川吉指导学习雕塑,又经徐悲鸿学友强化素描训练,留学法国后主修雕塑和绘画。《掷铁饼者》《牧羊人》等雕塑作品十次获得法国沙龙金奖、银奖和铜奖。《巴黎报》英、法文版评价说:“廖新学是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雕塑家之一。”
乡村牧童到国际大家,富民子弟到云南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奠基者。其间跨度,同样是一条长长的扁担,家庭之担和文化之担下,母亲是挑夫,廖新学也是挑夫。
杜天荣,富民赤鹫人。1928年出生,家境贫苦,7岁失去双亲,成为孤儿,随姑母生活,后经姑母资助到昆明学习摄影。1948年,机缘巧合,杜天荣在昆明失业之际,富民同乡廖新学自法国留学归国,邀请他去自己创办的新云南照相馆工作。摄影之余,兼学些绘画技艺,终成一代摄影大家,获评“云南省文学艺术卓越贡献者”称号。《翠湖》《大观楼》《生炉子》等一大批作品,成为记录老昆明最厚重的影像留存,到了今天还拴着几代人的记忆。
面对富民文昌路,我似乎看到了文化之旅上更多不移本心的挑夫。关注是一回事,关联是另一回事,沉自己进去,就有找到本真的可能。回望富民文庙,它离我们渐渐地远了。只是有个疑惑,文庙后那山,原本叫作卧云山,不知咋个改叫美女山了。
没来由地,变得执拗起来。
回去,再找一个机会吧,重读一回富民老县志,看看当年定址迁学的那个县令还有什么故事没有,可曾有过什么别的交待?
印象中,他叫谢天璘。
4.听歌小水井
小水井,是我遇到过的最为安静的村庄。于我现有的阅历来说,没有之一。
有时我甚至认为,这种安静是无法用语言给予描述的,骨子里的东西,唯有心气可以触摸到。而这种安静,确实真切地存在于众人眼前,这是一种亲近土地和云天的安静,一种远离城市不足为外人道的安静,一种既心通邻家又心通天穹的安静。
反正,这种安静是存在的。
小水井教堂前的场院边上,我又一次遇到那位苗族老大妈。十年前,她卖了一篓野香菇给我,回家一伙朋友聚在一起吃个精光,然后才问我:哪个市场买的,咋个朵朵一个样,没有一朵烂菌,没有一朵腐菌?今天,她没有野香菇卖,因为季令已过,卖的是几篓野草莓。我笑着问她,咋个粒粒一样大!她笑着应了我:熟透的才摘,不熟的就不摘,叫它再长几天,反正就在刺蓬上,它又不会跑,过几天再去一趟,就全熟透了。
大妈,你还唱歌不?
我一边给钱一边问道。她愣了一下,笑着侧过身去,又赶紧抻手捂了嘴,虽然手握得很严实,我还是看清她已经没了门牙。我們么老了,丑了,早唱不动了!孙子孙囡们接着唱,他们唱的新歌更好听。伴着苗族老大妈稍带混响的声腔,手风琴响,教堂里的歌唱正式开始了。
6月30日这天,我们去了昆明市域最大的苗族村小水井,去听一次来自大山深处的天籁之音。小水井合唱团的故事在昆明流传甚广,一个双手沾满泥土的苗族农民龙光云,能够与美国纽约爱乐乐团同台联袂指挥,筷子与刀叉能够如此优美和谐,云南大山深处的苗族合唱团能够走上美国、英国顶级音乐殿堂,将中国云南最炫的民族风,刮到大洋彼岸的舞台上。这是近几年来云南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奇迹,这个文化现象令人着迷。
一朵野香菇,一粒野草莓,是我走近小水井村庄的媒介,依从自然,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则是这个村庄给我的最朴素的观念。
小时候在山村老家,是体验过安静的。
白天的山村没有安静,村子里头狗特别多,似乎上级安排或是约定俗成,家家养狗,不拴绳索,不套衣裙,不特意地去盖一座狗房。一有风吹草动,或是脚声人影,一村的狗儿就全叫开了,比赛一样,攻擂一般,李家咬到张家,村头咬到村尾,管你走村小贩还是公社干部,管你头戴礼帽还是脚穿草鞋,逮谁就咬谁,咬完再说。土地承包到户的政策巨变,让老辈人从此做了土地的主人,又从此多了疑心,狗儿对主人的忠贞和贴心,在那个时代最为真诚,挤不出一丁点的水分。老家的安静在夜晚,没有电,路不好,邻居住得远,若不遇上急事叫门或是走亲串戚,各家各户的门关得都早,尽管荧火虫还在忽闪忽亮,蛐蛐儿还在引伴呼朋,只要晒场上、草堆旁、河沟边的孩子们被训斥着撵回家去,村庄就变得安静了。
小水井的安静,真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安静。与城市不同,与街道不同,与校园不同,与剧场不同,与我儿时对安静的理解更是天差地别的不同。
十年前第一次到小水井听合唱,我太想看清演唱者的礼服、皮肤和嘴形,近水楼台,我选择了最前排靠左的一个小角落,侧身而立,眼睛更多地盯住指挥龙光云的手势,耳朵更多地给了风琴师张继成的伴音。震撼之中,我似乎成为教堂墙壁上楔死了的一颗木钉。今日,端坐在小水井教堂里,选择了居中最后一排座位,聆听合唱,这是最好的位置。随着指挥龙云光的手势,德国作曲家舒曼《茨冈》合唱曲开始响了起来,我轻轻闭上了眼睛。
小水井,是苗族村民的生命之源,礼唱赞诗,歌唱自己,则是小水井合唱艺术的源头。一百多年来,随着基督教的流布而传播的近现代西方文明,不着痕迹地改变着苗族社会群体的传统习惯,并且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豁然悟到了,儿时村庄里的安静,是害怕里的安静,小水井苗寨里安静,是不怕中的安静。害怕,是因為没有寻到神灵的庇护,不怕,是已经乘着歌声的翅膀。
感谢富民小水井,你用歌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答案。
抬眼远望,螳螂川玉带一样飘过富民永定镇,两岸高楼鳞次栉比,田园生机盎然,之后,就要进入另一片山区丘陵了,为了穿过陡峭的普渡河大峡谷,河流开始变得湍急起来,咆哮起来,更加富有了力量。在两岸的崇山峻岭中,深藏着像小水井一样的众多苗族村庄,漩窝塘、汤郎箐、出水箐、大松园、芹菜塘,这些村庄同样都在高高的山上,种着并不肥沃的土地,刮着冷凉的风,一到夜晚,所有的村庄都会唱歌,一到周末,很多的人都要去教堂。
滇池,螳螂川,普渡河,金沙江,沉吟之间,思绪最终落在了“普渡”这个词条上。找出三年前回老家过渡河时所发的一个微信相册,手机换了几回,里边的相册一直还在:
普渡河,一条地理概念上的河,流出峡谷四季;一条岁月空间上的河,割开大地皱折;一条佛界慈念中的河,普渡万物苍生。此间:风渡云朵,云渡苍天,山渡庄稼、村落和故园,水渡鱼虾、炊烟和迷津。有那么一刻,试问:我们能否轻轻地弯下腰,摸一摸一棵草的高度;有那么一刻,再问:我们是否愿意轻轻地伸出手去,焐一焐一粒果的温度。然后,静得下来,看看自己的心闸,有无开启的那一念。
渡?渡何?又何以渡?
与其佛说,不若自启。
螳螂川上,静静地想了许久,写下这些话,算是给一条河流、一部老志、一座文庙和一些关联不关联的村庄留下一个交待。
责任编辑 胡兴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