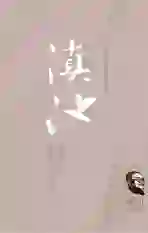浴缸里的维纳斯(短篇小说)
2023-05-30龚万辉
龚万辉〔马来西亚〕

龚万辉 197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文字创作以小说和散文为主。作品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人工少女》、小说集《卵生年代》《隔壁的房间》,散文集《清晨校车》和图文集《如光如影》《比寂寞更轻》。获颁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并被台湾《联合文学》杂志评选为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之一。
“啊!”
惠子突然背后一下刺痛,喊了一声。美术课室里所有细琐的声音,仿佛在惠子喊出那声之后,一瞬间完全退远。其实也不是因为剧痛,而是突如其来吓了一跳,以为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惠子回过头看,坐在后面的那个男生正在偷笑,手里握着一支故意削得很尖的铅笔。刚才就是那男生用铅笔戳她。
惠子这时才察觉,班上所有人都在看着她。原本在前面讲课的小林老师也停了下来,转过头,问她怎么了。惠子低下头,什么也没有说。小林老师推了推眼镜,看了看大家,又继续上课了。铅笔在画纸上拉出线条的声音,窗外吹过一阵风,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仿佛刚才惠子喊出的一声只是秒针不期的震颤,齿轮只停顿了一下,整个世界又重新运转起来。
“又是你的啦。”
坐在后面的男生,笑着把一张折了又折的纸条丢给惠子。那纸团跌在画纸上,上面歪歪斜斜写着惠子的名字。惠子把那纸条打开,里头什么也没写,只是用鉛笔涂成两圈黑色。
已经是第三张了。
三张纸条都一样,被谁涂上了黑黑亮亮的一对圆圈,铅笔的笔触溢出边缘,变成充满锯齿的形状,像是黑洞那样的一双眼睛。
惠子望了望四周,没有人接应她的目光。正是下午的美术课,同学的膝盖顶着画板,埋头画静物素描。三四十个人围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几个几何石膏模型,摆在黑布上,还打了灯光,把白色石膏的亮暗,映照得更立体分明。
天气又热又闷,课室的外面有不知名的鸟类互相鸣叫。老旧的美术课室有明亮的玻璃百叶窗,但风总是吹不进来。古老的电风扇在头顶上喀达喀达乱响,随着叶片旋转摇头晃动。除此之外,可以清楚地听见铅笔在画纸上磨擦,窸窸窣窣的声音。
到底是谁呢,接二连三地把这样不留字句的纸条传给她。
惠子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裙子的口袋里。她隐隐知道那纸张上黑色圆圈的暗示,以及无人认领的玩笑。惠子坐在静物桌的前面。她今天特地早一点进课室,可以从容地找一个适合构图的角度,不会被其他同学挡住。但她如今有些后悔,她似乎坐得太前面了,也许班上每个人都已经看到了。隔着薄薄的白色校服,其实什么都掩藏不了——
惠子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内衣。
原本早上还套着体育外套,但是到了中午真的太热了,惠子脱了外套,搁在椅背上。她一开始还没有察觉身上的校服,从背后看真的太透了,浮现出深色的内衣肩带。班上的女生有时会在校服之下再打底一件背心,但必须忍受三层衣物的闷热感,即使这样,仍隐约可以看出内衣的轮廓。那时候,女生的内衣都是白色或肤色的,不会再允许其他的颜色。因此惠子身上的那件黑色内衣,格外的显眼,在整间课室里,犹如一只黑色山羊不小心闯进了绵羊的围栅。
惠子低下头,只盯着自己膝盖上的画纸。她才刚用铅笔打了线稿,凌乱的线条擦掉了又画过。圆柱体的光影是渐层的,必须花很多时间,从亮到暗把不同轻重的笔触揉合在一起。还没到下课时间,惠子听见身后的男生们在低声说着什么笑话。他们交头接耳,却故意笑出声来。惠子假装不知道,铅笔快速地来回在纸上涂抹着。她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为何要难堪和委屈。
她只是觉得非常孤单。
画画其实也是一件孤单的事。虽然画家死了很久,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们的画作里去理解那种孤单。小林老师说。
初三的美术老师从退休的老先生换成了小林老师,惠子才开始喜欢上美术课。小林老师会说很多美术史上那些画家的故事,从此沉闷的美术课似乎也变得有趣了一些。初中仍在画铅笔素描,从石膏几何物体,到苹果和瓶子,要用不同号码的铅笔把它们一一描绘出来,没有颜色,只有光影。
面对那些静物,班上那些不自爱的男生总说:“又是静物啊,好闷啊——”但惠子心底偷偷喜欢。她不曾告诉过任何人,她喜欢这样凝视静物桌上的事物,再把它们画进纸上,那从无到有的过程。仿佛如此,终于可以自流逝的时间之中留住了什么。为了写实,画画的人必须捉住眼前静物的所有细节——那些形状幽微的不同,那些玻璃上的点点折光,细看之后皆慢慢浮现出来。
惠子也喜欢小林老师。小林老师才刚从美术学院毕业,戴一副细框的眼镜,总是把衬衫塞得很整齐,干干净净的。他有一种其他老师已经没有的热忱和笑容。小林老师会让班上的同学欣赏世界名画的幻灯片。从蒙娜丽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到一脸忧伤的梵谷……有几次画面闪现裸体的女人,那些讨厌的男生就一起发出怪叫声。但惠子却想看清楚一点,那些留着几百年前油彩笔触的裸身,肌肉、乳房到发丝的描绘,在摄影机发明之前,从画家之手拟造的真实感,那种对“重现真实”的执着。此外,似乎还有一种她不太说得出、不很理解的什么,待她要再仔细地看一看,那幻灯片却忽暗一下,咔嚓一声换成了下一张。
放学铃声终于响了,同学们都收拾了画具,背上书包回家去了。惠子今天必须留下来做值日,她不急着离开,伸手把静物台的灯光拈熄了。
“白天不懂夜的,黑——”那些男生临走出课室之前,还在惠子身后怪声怪调地乱唱,偏偏要把那“黑”字故意拉得很长。
小林老师也看到了吧。惠子心想。
美术课室只有惠子一个人了。她把一张一张木椅子叠在课室的角落,然后拿了扫把,把地上那些橡皮擦碎屑,以及削了铅笔的蝶翼一样的木屑慢慢扫拢成一堆。此刻校园里也没什么人了,远远有铜乐队在练习步操,喊着口令。课室的桌上摆了几个石膏头像,凯撒大帝、大卫和维纳斯。
小林老师曾经说过,这些雕像源自一千年前古希腊罗马时期。一千年有多远,那时的人类是什么模样,怎样生活?说什么语言?惠子没有办法想象。时间就这样过去,只有那些静止的雕像,抵住了风雨磨蚀,终究断手断脚地留存了下来。但不知为什么,课室里那些白色雕像们都是没有瞳孔的,好似它们目睹过远方和时光的消失,时间把它们的记忆都夺走了一样。
惠子仔细端详维纳斯。维纳斯有一头卷发,卷发盘在头顶上。那石膏雕像低头看着什么。不知是谁的脏手,在维纳斯脸上留下了几个灰色的指印。惠子想用抹布擦掉,却好像不小心把原本的污渍弄得更深了。
惠子想知道更多关于维纳斯的故事,但今天小林老师没有留在课室里。
惠子轻轻关上了美术课室的门,上了锁。也把几何静物,以及那些石膏雕像,锁在倾斜的光里。
放学回到家里,整个屋子暗暗的,父亲还没有回来。惠子拉开了客厅的窗帘,让傍晚的阳光照进来。对面的公寓很高,遮住了远方的云朵。今天的天空是粉红色的。这样的天色,惠子喜欢站在窗前,看着夕阳慢慢沉落到城市的背面。住在这么高的地方,好似夕阳也可以看得久一点。时间慢慢过去,看去对面的公寓,都已经零零落落打亮了一窗一窗的灯光。
斜斜的阳光刚好照到客厅挂着的一幅画。那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诞生》,女神维纳斯站在一个巨大的贝壳里,一双迷惘的眼睛,仿佛才刚刚从一场梦中醒来。她的长发刚好遮住了乳房,手遮住自己的私处,而花神和风神都在迎接她的诞生。也许要再靠近一点,才看得出那幅画其实是一幅很大的拼图,由两千枚小小的碎片组成的。也许没有人察觉,那巨大的拼图上不知为什么缺了一枚,看似谁在那幅画里凿出了一方小小的空洞。
窗外的阳光从维纳斯的裸身上缓缓地滑走了。
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和美术课室的那尊石膏雕像,是两张完全不同的脸。惠子也想过,为什么维纳斯都长得不一样。或许维纳斯还有千百张不一样的容貌,仿佛每个维纳斯都拥有不一样的故事。
惠子到浴室把校服脱下,对着镜子,注视穿着黑色内衣的自己。下午被男生的笔尖刺了一下,似乎还有些刺痛感。惠子又转身,想看背后有没有被刺出伤口。她伸手向背后,黑色内衣肩带的下面,却徒劳地碰不到那处刺点。她想起下午在课室里发生的事又沮丧起来。
但那件内衣其实并不是惠子的尺码,它太大了。罩杯松松的,只能虚掩着惠子的乳房。那是母亲忘记带走的唯一事物。
母亲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切,却忘了晾在阳台上的黑色内衣。惠子把那件内衣收了下来,塞在橱柜的最深处。有时她会偷偷地拿出来,伸手抚摸内衣上蕾丝的花纹。有时她会把母亲的内衣凑在鼻子下闻一闻。然而内衣其实早已被清洗、晒干了,只留下了洗衣精那种刻意而人工的香味。惠子已经忘记了母亲身上的气味。有时她连记忆中母亲的样子都有些模糊了,像是雾中镜子,必须要伸手擦拭一下,才能重新清楚地看见那一张脸。
惠子反手把内衣解开,和穿过的校服一起丢进了脏衣桶里。脏衣桶里面还有父亲待洗的衣服和裤子。惠子想了想,又把自己的内衣和校服从桶里掏出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把自己的衣物和父亲的分开来洗。父亲应该并不知道。母亲离开之后,惠子负责清洗家里的所有衣服,当然包括父亲的衣裤。惠子转过身,把校服和校裙丢在洗衣机里面,按了开关,洗衣机注了水,轰轰轰地天旋地转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正把一切都吞噬掉。
公寓的浴室其实很窄,转个身都要碰到这里那里。但浴室里还是硬生生地塞了一个浴缸。惠子此刻光着上身,只穿着体育短裤。她蹲在浴缸里,扭开了水喉,低头搓洗着内衣。黑色的内衣上有细巧的缕花,抚摸过去如柔软的浮雕。罩杯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蝴蝶结,每一处都无不精致。惠子轻柔而谨慎地,惟恐把内衣洗坏。她双手捧着,冲去内衣上的泡沫,那件内衣在她的手上如黑色的荼蘼花。
温水不断从水喉里流泻出来,慢慢就淹上脚趾,泡沫都盖住了惠子的脚踝。大概浴缸的疏水孔又塞住了吧?惠子关了水喉,任由洗衣的脏水以一种很慢很慢的速度流失殆尽。她拨了拨累积在疏水孔旁边的肥皂泡沫,看见一撮灰白的毛发,堵住了洞孔。惠子知道,那不是自己的头发,那是从父亲身上掉落下来的。
父亲最近总是在掉发,而浴缸也时不时就被塞住。惠子用食指和拇指钳着那堆毛发,毛发吸了水而互相缠绕在一块,垂在惠子的指尖,像是一只已经死去的生物。她把那撮灰色的毛发丢进浴室里的垃圾桶。这么多年了,浴室总有一种潮湿不散的气味。而那个浴缸也早已从原本光洁发亮的纯白色,变成了一种恍若什么日积月累地沉淀下来,永远都洗刷不去的淡黄。
惠子关了水龙头。隔着浴室薄薄的门板,整个屋子仍然一片寂静。
父亲还没回家。
惠子站在那泛黄的浴缸里洗澡,洗衣机发出旋转的噪音。她握着花洒冲洗自己的背,刚刚对着镜子也没有看见,这时却从背后感觉到一处微微刺刺的痛。想是皮肤上那个被刺戮的伤口,被水浸湿了。轻轻的痛感,像是有什么小小的虫蚁正在啃咬自己。
温热的水汽渐渐把浴室的一切变得模糊,惠子抬起头,觉得自己像迷失雾中一样。水汽结在浴室的白色墙砖上,变成一颗一颗水滴。然而似乎太久没人清洗,瓷砖之间长出了黑色的污垢。惠子记得小时候,在洗澡时,她会和父亲在那面墙上,在瓷砖纵横的方格里,用沾了肥皂泡沫的手指,玩圈和叉的井字游戏。她和父亲轮流在九宫格里画上圈圈和叉叉,父亲永远都先让她。那是很简单的游戏,却很难获胜。她总是不服气,要父亲再来一局,没完没了。
水声稀沥。惠子有时候仍会想起以前的那段时光。
惠子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从没有记忆的小时候开始,到十二岁那年,她都和父亲一起洗澡。
那时候,惠子和父亲一起坐在浴缸里,坐在一池相连着两人的水中。父亲的发,總是湿漉漉的,像退潮之后的海藻那样,搁浅在远远的发线上。浴缸里的父亲,仿佛不像日间的父亲。裸裎的父亲屈着身体坐在热水里,她可以清楚看见父亲胸膛上,那些稀落的痣。父亲脱下了眼镜,眼尾的皱纹看起来更明显了。在那雾气氤氲的浴室里,父亲用一条毛巾用力刷着后颈,然后双手搭在浴缸的边上,长长地呵了一口气。
十二岁的惠子屈着腿坐在浴缸的另一头。父亲转身、举手就掀起水波,涟漪荡到她这边,映照碎光满脸。她的手指早已经泡得发皱,看着指腹都像是一颗颗干瘪的红枣。从有记忆以来,她就这样和父亲一起洗澡。两人在浴室里花去半天时光,充满呵呵笑声。或者更早,她还在牙牙学语,看着浴缸里的父亲在浴缸里欢快地打着肥皂,泡泡很快就浮满了水面,那么多,那么地厚,父亲隐没在层层泡沫之中,让她一度担心父亲终究会像肥皂那样溶掉。
小时候觉得大如泳池的浴缸,不知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狭窄。
但父亲似乎没有察觉,这座房子到底改变了什么。这幢公寓的房子,卫浴设计其实本来是没有浴缸的。但新居装修那时候,母亲一直坚持在家一定要可以泡澡。“一个家怎么可以没有浴缸呢?”母亲不能妥协。于是在原本就不大的浴室里,父亲只好硬生生把洗手台给敲掉,十分勉强地塞进了一个长方形的浴缸。
但如今父亲已经极少提起母亲。
惠子的童年印象,恍如浴室里氲氤的水气,母亲渐渐退远成一个模模糊糊的雾影。
但她还记得,小时候她曾经和母亲一起在客厅玩拼图。两人坐在倾斜的光里,惠子看着母亲低着头,专注地在那幅未完成的拼图上。那时他们才刚搬到新的公寓,屋子空空的,说话都会有回音回荡。后来家里慢慢增添了沙发、餐桌、橱柜……原本空白的墙,要挂上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结婚照里头的父亲和母亲,穿着笔直的西装和礼服,站在照像馆的假树和假草皮的样板布景之中。那时候韩剧《冬季恋歌》流行了好一阵子,父亲竟还围着一条厚厚的围巾。而浓厚妆容之下的母亲,似乎努力撑开笑容。
父亲把几年前拍的那幅结婚照裱了框,母亲却说:“天天看着自己,那多没意思。”
隔日,母亲和惠子就一起从百货公司抱回来了一大盒拼图。盒子上是一个裸身的女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贝壳上面。母亲对惠子说:“你看,维纳斯女神漂不漂亮?”惠子并不认识画里的人物,但那盒拼图对她来说如巨大的坃具。两千片的拼图哗啦啦倒出来,堆成小山一样,惠子高兴地欢呼。
从那天开始,她和母亲每天都坐在地上,埋首在那堆山丘一样的拼图碎片里,像淘洗金砂一样,不断翻找,仔细端详每一枚拼图碎片。一枚枚碎片都长得很像——尤其是右上角的树叶,以及花神的花裙——但仔细看,原来都是有些不同的。首先要拼出图画的边缘,再慢慢地从边框四周往内延伸。偶然找到几个相连的,就先把它们拼好,再连接在那幅巨大的画作之中。
惠子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原来每一枚碎片都有着自己的正确位置,不会重复,也不会有错误。只要从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碎片之中,找到彼此的关连,如彩石补天,原本的一片空无就会慢慢补缀出天空、海浪和人的样子。有时她甚至误会了,那幅画是由自己的手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翻印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五百年前的一个画家之作品。
许多年后,惠子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终于看到波提切利的原作,才知道那幅画原来非常巨大,站在画前而一眼都无法看完。所有的细节,包括油画颜料历经几百年而龟裂的隙缝,皆让惠子觉得自己恍如再往前一步,就可以走进画中。
她记得小时候就曾经伸手触摸过画里那些繁复的细节。年幼的惠子沉溺在那幅拼图之中,她似乎乐此不疲。因为她知道,虽然旷日费时,但所有空缺的空洞都是可以弥补的,只是要花些时间把对的碎片找出来罢了。
当维纳斯女神终于从虚无中浮现出来,都已经快过了三个月。
原本堆积如山的碎片,如今在盒子里零零散散的。那幅一公尺长的拼图,摊在地上,已经完成了十之八九。然而由惠子拼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多,母亲拼的却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母亲只是坐在那里。母亲有时候会盘着腿坐在午后的客厅,望着地上那幅未完成的拼图出神。惠子拿着一枚拼图问母亲,不知应该嵌在哪里,叫了母亲几声,母亲才回过头来,抱歉地微笑。母亲摸着惠子的头,顺着头发又摸了好几回。
“惠子喜不喜欢妈妈?”
“喜欢。”
母亲想要抱一抱惠子,但惠子以为母亲要搔她痒,咯咯笑着挣开了母亲的怀抱。
那时候,惠子多么期待把拼图拼好的那一刻。但是那幅《维纳斯诞生》终于要完成的那一天,惠子才发现最后一块拼图不见了。
不见的那块,就在维纳斯的左下角,缺了一个显眼的空洞。惠子心急,在客厅里找来找去,盒子里没有,沙发底下、隙缝间也没有。惠子翻找了整个客厅,她甚至担心不小心掉进衣裙口袋,连衣柜和浴室、厕所都找过了,就是唯独缺了那一块。公寓的房子并不大,为了寻找那小小的一块拼图,才觉得屋子看不见、够不着的角落实在太多。惠子心底很难过,和母亲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如今那幅画却留下了一个洞口,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填补回去了。
惠子没有找到那最后一枚碎片。
母亲离开了家。
母亲离开家的那天,带走了一切有关自己的事物。那些旅行纪念品、照片和衣服。只有浴缸带不走,被永远地镶嵌在这个屋子内里。没有母亲的屋子,日间总是拢着窗帘。父亲如常一早就到公司上班,而惠子自己走到楼下搭校车。放学回来,惠子会从冰箱找些东西吃。她坐在客厅里,把电视打开,任由卡通片的声浪和晃动的炫光充满屋子。
那幅拼图终于还是框了起来,挂在为它留白的那面墙上。不仔细看,谁也不会发现缺了一小块。惠子把窗帘霍啦一声拉开,看着对面公寓的那些窗子。窗子里有时有人,有时没有。她耐心地等待父亲下班回来。父亲会和她一起洗澡,一如母亲还在的时候那样。
母亲曾经笑他们:“感情这么好,是不是前世的情人啊?”
父亲轻轻揉着惠子的头发,推开了浴室的门。
那个浴缸像盛载着一日潮汐。父亲每天下班,總会先在浴缸里放满热水,两人洗了澡之后,那一缸混了泡沫的水,又慢慢地从疏水孔流掉了。潮起潮落,一日复又一日。
时间就这样流失掉,惠子慢慢长高了。当惠子发现浴缸越变越小的同时,她发觉父亲也变成了一个静默的大人。
然而,像是履行着一种共同的仪式,即使母亲不在了,一直到了小学六年级,她和父亲每天仍一起挤在那浴缸之内洗澡。父亲对着雾雾的镜子说:“惠子,你看。”惠子说:“看什么?”父亲说:“你看,像不像画里的维纳斯?”惠子看着镜中模糊的自己,像融化掉一样,站立在那个浴缸之中。如果她是维纳斯,那浴缸就是浮在海面上的,那个巨大的贝壳。她想象,在雾中浴室,此刻有花神和风神在她的身边,吹拂着她的发梢,把美丽的小花不断扔到水上,就像客厅挂着那幅画一样。
有时候她也错觉了,那白瓷明亮的浴缸,就像是引渡她和父亲的小船,虽然他们从来不知道这艘小船可以把两人带到哪里去。
父亲叫她转过身来,为她洗头。惠子背对着父亲,她却可以清楚感觉到父亲的手在她的发间、头皮按抚过的触感。顺着发丝,那双手拂过她的脖子和肩背,她听见父亲轻轻地叫她:“惠。”她回过头问,怎么?父亲要她紧闭眼睛,洗发水的泡沫要跑进眼睛里去了。她低着头,却仍睁眼看见水面上,随着波浪摇晃的脸的碎影。
她看见自己的样子,总会想起母亲。
母亲穿着黑色的内衣。母亲的内衣都是黑色的。
她曾经无意间看见,那不断晃动的一抹黑色。那是父亲如常上班的日子,母亲陪她玩拼图玩了一个上午。惠子躺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了,从午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地上是散落了一地的拼图碎片。母亲在哪里呢?惠子看到母亲的房间虚掩着。她从那狭窄的门缝间看进去,看见母亲穿着黑色的内衣,被一个裸身的男人压在床上。门缝很小,她看不见母亲的脸,母亲也没有看见她。但母亲的身体不断地颤动着,似乎在忍受着什么痛苦,发出压抑的闷哼的声音。
惠子站在门外许久,仿佛中魔了而无法把目光移开。那时候,她只知道此刻绝对不能把房门推开。如果推开的话,那扇门就永远不能再关上了。
那是她第一次看见母亲的裸身。那件黑色的内衣,从肩膀滑落的肩带,缕花的蕾丝,晃动而不曾停止。
好像从那一天开始,惠子和父亲一起洗澡的时候,总会想起母亲晃动的身体。
刚刚上中学的时候,惠子仍穿着小学生那种棉质的白色背心。背心遮盖着渐渐发育的少女胸部,像是薄薄的蛋壳,其实阻挡不住将要破壳而出的初生之物。班上的女生有的已经开始穿少女内衣了,半截式的,要从背后上扣的那种。从她们的白色校服看去,可以看见隐隐约约浮现出来的内衣肩带,仿佛也是隐隐约约的一道分界,把女孩子区分成了两个界限,虫和蝶,成长和未成长之间的区别。而惠子还躲在虫蛹之中,一点都不想出来。如果可以,惠子希望自己永远不必长大。但是身体却拥有着自己的意志。所以惠子习惯了驼着背,她想把从身体上凸显的部分都遮掩起来。
父亲并不知道这些。
父亲也不知道,母亲离开之后,惠子偷偷把母亲穿过的那件黑色内衣藏了起来。
如果那一天她没有把门锁上的话……
那一天,惠子把自己锁在浴室里,脱了校服,把身上的小背心也褪下来。惠子看着镜中的自己,微微隆起的乳房、那花苞未绽一样的乳首。她尝试穿上那件黑色内衣。那是她第一次把吊带式的内衣穿在自己身上。她两只手绕到身后,对着镜子,却笨拙地怎样都扣不上衣带的小扣子。好不容易把内衣扣紧,但那件内衣似乎大了一号,挂在自己的身上,还有些松垮垮的。惠子把肩带勒紧一些,她的乳房贴在柔软的罩杯里,像是有人怀抱着她一样。
如同往日,惠子打开了热水注入浴缸,水声从浴室传出来。雾气慢慢地弥漫了整个小小的浴室。惠子站在浴缸里,有一瞬间,她分不出自己或母亲在朦胧镜中的迭影。
若是往日,父亲会推开门走进浴室,在惠子面前,从容地脱掉身上的所有衣服,霧气里一团黑黑的阴影。但那天不一样。那一天,惠子把浴室的门锁上了。她在浴室里清楚听见父亲扭动喇叭锁的声音。她没有为父亲开门,父亲也没有敲门。从门底缝间,惠子看见父亲的身影在门外站了一刻。不久,影子离开了门后,惠子听见脚步走开的声音,慢慢远去了。
从此,浴室里只有惠子一个人了。
惠子泡在浴缸里,抱着膝,眼泪汩汩地流出来。她不是维纳斯,也许一开始就不是。她只是拼图里缺掉的那块碎片而已。
那幅画里诞生的维纳斯,裸露在微风之中的身体接近一种永恒。时间仿佛被谁快转了,跳过了所有成长的挫伤和细节——维纳斯诞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少女。她裸身站在贝壳里,如一颗晶莹而无瑕的珍珠,在风神吹拂的海面上,仿佛不曾拥有记忆,不曾知道她将要面对的命运。
但惠子知道,在她把自己的身体遮起来的那一刻,她就不再是父亲的维纳斯了。
惠子觉得非常孤单。
和父亲一起洗澡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
隔着浴室房门,惠子听见一串钥匙摇晃的声响,知道父亲下班回来了。她并不想告诉父亲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她穿了那件黑色的内衣去上课,结果惹来班上男生的嘲弄。什么时候开始,她已经不会告诉父亲这些。若有什么委屈,惠子会把自己整个身体沉在浴缸的水里,就什么都听不见了。耳里只有嗡嗡低闷的声音,惠子缓缓地呼一口气,一串泡泡从鼻孔和嘴里窜出来。
惠子洗好澡,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父亲却在沙发上睡着了。客厅的电视还开着,报纸上搁着父亲的眼镜。像是日间承受了太多疲累,睡着的父亲呼吸很长,仿佛陷在很深的梦中。她轻轻叫唤父亲,打断了父亲的鼾声。但父亲还是没有醒来,惠子伸手摇了摇那副深陷梦中而沉重不已的身躯。
不知是否错觉,父亲好像越来越轻了。
许多年后,无人预知,这座城市将爆发一场巨大的瘟疫,住在公寓里的人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时间像搁浅的鲸。惠子依然无处可去。她躺在床上,拢上了厚厚的窗帘而未知日夜。她偶尔仍会梦见晚年中风的父亲,那副衰老的裸身,搁浅在浴缸里的样子。
父亲在一缸混浊的水中双手抱着膝,梦中安静地看着她,什么也没说。如果那时候,没有把浴室的门锁上的话,父亲也许现在仍然会为她梳理、吹干湿淋淋的长发,系上孩子气的双马尾,把她打扮成永远的小女孩。父亲会微笑而善良地说:“你是我永远的维纳斯。”
她也曾想过,也许就这样,自己真的可以变成一个永远不必长大的人。
其实哪里有永远呢?
几年以后,父亲在某一天的下午颓然倒下,从医院接回家里已经是一副中风之后报废的身体。惠子每天必须为中风的父亲洗澡。她伸手探进浴缸,把塞子从通水孔拔起来,浑浊的洗澡水还漂浮着几朵泡沫,顺着漩涡转啊转就流走了。浴室墙上的瓷砖和镜子蒙上了一层刚洗完热水澡之后的雾气。惠子坐在浴缸边上,看着那一缸正在逐渐流失的水,伸手撩了撩,仿佛还留着父亲的余温。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父亲洗过澡的水,污浊如山洪黄泥,奶茶那样的颜色,水面还泛着一层薄薄亮亮的油光。
每天给父亲洗完澡之后,惠子都要把浴缸洗刷一遍,用一把塑胶刷子使劲地将那些沉淀在缸底的粘腻秽物刷走。总是一个人蹲在浴缸里满头大汗洗刷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影子被日光灯拉在白色的方格瓷砖上,心里却无比哀伤地知道,父亲其实正在一点一点地溶化掉。
父亲瘫在病塌上再也没有力气撑起身体了。刚从医院搬回家的那段日子,惠子还努力地想把父亲劝下床做复健运动,然而父亲似乎陷入了一种自暴自弃的情境里,竟连轮椅也不愿意使用,一整天躺在床上,眼光光盯着天花板,任由时间虚掷而逝。
“你这样,要怎样好起来啦?”惠子有时失了耐性,一边用力为父亲擦脸,一边负气地对父亲说。
父亲似乎早已经在心底决定了什么,以一种巨大的静默和任性,拒绝了所有复健的方法和希望,日复一日任由惠子抱着下上床,重复着喂食、如厕、清洗身体的琐碎步骤。
父亲一声不吭。
每一天早上,惠子盛好了热水,先把裸身的父亲安坐在浴缸里,然后她卷起衣袖,也屈身踏进那缸死水之中。本来就狭小的浴缸硬塞了两个人,显得格外狭窄,几无回身的余地。父亲驼着背,垂萎低头。她用毛巾擦拭父亲那布满老人斑却异常白皙的背脊,沿着肋骨下去是包裹着各种故障脏器的发皱皮囊。
她抚过父亲身体的每处细节,像是在默读时间留在粗糙树皮上的密语。每一次洗澡都花去好久时间,当惠子抱着那具瘦削弱的躯体走出热气氲氤的浴室,总是自心底泛起一种虚浮的幻念,仿佛她正在懷抱的其实是一尾搁浅在沙滩上,嘴巴一张一合呼吸困难的远古棘腔鱼——那种被时间遗忘在深邃的海底,历经亿万年都不再进化或退化的史前鱼类。
随着时间过去,客厅挂着的那幅拼图,一片一片剥落,却也已经无人在意那些拼图碎片的下落了。
一如父亲也正在慢慢地溶化。
每天惠子为父亲洗身,都从父亲身上抹出一缸褐黄粘稠的沉积物。那些从苍老之躯褪下来的秽物,把原本白亮的浴缸都晕染成一层暗哑的泛黄色泽。她有时会恍惚错觉,抱在手里的父亲身体仿佛每天都轻了一些。时日长久,愈觉得沉默的父亲像是越来越轻盈了。一直到那天上午,惠子如往常一样半蹲在浴缸里帮父亲擦拭身体,父亲背对着她,一下一下地抖耸着肩膀。惠子以为浴缸的水太冷,伸手把热水喉打开,回过头,才发现父亲像个委屈的孩子那样,坐在浴缸里呜呜地在哭。父亲的脸皱成了一团,眼泪鼻涕从隙缝间漫涌出来。
惠子有些心急,起身想用毛巾替父亲揩掉脸上的泪水,却像不小心弄坏了还没凝固定型的蜡像那样,把父亲的鼻子给抹下来了。
怎么办?父亲正在溶掉。
惠子伸手触碰到的裸身皆如融蜡滴落。她只能无助地站在浴缸外面,看着父亲屈就在浴缸的身体渐渐溶解、崩坍,而至消失。也不知过了多久,一整缸浊水慢慢地流失,最后只剩下一堆灰灰白白的毛发,堵塞在浴缸的疏通孔里。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