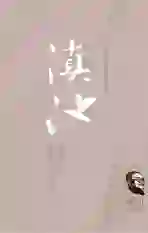卵生(短篇小说)
2023-05-30龚万辉
龚万辉〔马来西亚〕
“怕不怕?”
“不怕。”她回答哥哥。
但她并不知道哥哥这样问她,是因为此刻油棕园暗沉如幽冥结界,处处怪异尖锐的鸣叫声?还是指地上那具装在黑色塑胶袋里的狗尸?她站在那里,拿着手电筒为哥哥照明,一柱光线在油棕树之间游移,夜暗中排列整齐的树影忽长忽短,羊齿蕨从树身间隙生长,妖绕活起来了那样。哥哥说,你这样子我看不到啦。她把手上的光照去地上,哥哥在草丛之中掘了一个浅坑,挖出了许多黄土。光里弓着腰的哥哥,高举锄头,一下一下往土地刺戳,被拉长的影子晃动,一双蓝白人字拖都沾上了泥土。应该还要再深一点才行。哥哥仿佛自言自语。
她站立良久,有许多蚊子正在身边飞绕。她听见周遭嗡嗡的声音,忍不住挥手驱赶那些蚊虫。手电筒的光却引来了更多细小的飞虫,有一只褐色的蛾,甚至扑上她的T恤。蛾翅上有一双拟真的鸟眼花纹,她不敢伸手碰它,拉拉衣角才让那蛾惊动飞去。
她不曾走进深夜的油棕园,白天偶尔路过,也看不见园丘尽头。有时看见几个印度人开着罗里在采收一丛一丛的油棕果,地上散了好些红色油亮亮的果实也不捡,引来松鼠叼食。却不想这座油棕园在夜里竟充斥生灵万物,到处繁复又躁动的声音。呜——呜——,阵阵长号,如夜袭警报,也不知是猴是鸟。如果父亲在的话,她也许就不会站在这里喂蚊。她和哥哥像是那方土地上唯一的擅闯者,夜暗中有千万的眼正注目他们。但她左右看去,都只是模糊徒具轮廓的树影。尖尖的棕梠叶把月光都遮蔽,只有手电筒光照之处,才亮起一圈唯一的明亮。
这里够远了,再看不见那些住屋灯光,而且凌晨一点多,应该不会有人发现他们正在埋狗吧。她想。
刚才她坐在摩哆车后座,一手紧拉着哥哥身上的外套,一手提着塑胶袋,袋里装着死去的狗儿黑鼻。他们行过花园社区的小路上,有时转弯,车灯把住宅区那些排屋的铁门一瞬照得晃亮。都已是深夜了,一整排屋子大都熄了灯。好几辆车子停泊在门外,凉夜潮湿,车镜都蒙上一层雾气。小路徒留一盏一盏瓦数不足的路灯,昏黄的光晕在黑夜里牵出一道虚线。
路上只有哥哥的摩哆车行驶着,是那夜景之中唯一移动的光。这真是太显眼了,而且摩哆车噗噗作响的引擎声听起来格外刺耳。她想,会不会有人此刻在屋子里掀开窗帘看见,她和哥哥正要偷偷去丢狗尸?她手里还提着狗儿黑鼻的尸体。黑鼻是家里养的土狗,一身褐色的毛。早前是一只母黑狗跑到家里生下来的,一共四胞胎,父亲把黑鼻的三个兄弟都送给人了,留下的只有黑鼻。黑鼻好动又热情,每次她从学校放学回来,黑鼻都人立扑到她身上,弄得白色校裙都是狗爪泥印,惹她责骂。如今每一转弯,她都感觉到那塑胶袋里黑鼻的尸体,依着惯性力,撞上她的小腿肚,像是一团猪下水那样冰凉又沉重的触感。她只好伸直了手臂,把袋子提高,但这样的姿势让她的手臂酸痛不已。才两三公里的距离,他们却像是在浓稠如墨的夜晚艰难划行,车头灯才拨开眼前的光亮,回头看去,背后又已恢复了一整片的黑暗。
前面就是了。哥哥转过头说。
整个住宅区紧挨着一片油棕园。或者应该这么说,本来是油棕园的土地渐渐被铲平,建成了新社区。屋价远比油棕的行情上涨得更快。这里原本是垦殖地,如今也都建满了一式一样的排屋,住满了人。而那些野生的松鼠和果子狸都从林子走出来,沿着电话线杆,爬到住家里偷吃东西。有一次,她听见黑鼻在屋外狂吠不休,她好奇往外看,一只穿山甲如华丽神祇那样,一身金黄的甲冑,四只短腿支撑着矮胖的身躯,悠悠哉哉地从家门口走过,路灯下闪闪地发光。
然而狗儿黑鼻已经死了,她心底慌乱,还来不及难过。傍晚的时候她才为黑鼻洗澡,那狗老是顽皮地抖擞湿毛,水滴泼洒她一身湿透。原本都是父亲帮狗洗澡,然而父亲不在了,哥哥又什么都不管。她其实也嫌麻烦,只是狗儿的臭骚味日渐浓重,老是看它在用后腿搔虱子。不想这一回驱虱的药水倒太多了,又冲不干净,那狗一身痕痒,用犬齿啃着自己的皮毛,吃了满口的毒。她原先也不知道,放任那狗在停车坪那里玩,自己换过衣,在客厅里看电视。然后就听到屋外盆栽被推倒的声音,原以为黑鼻又在追松鼠,过了一会起身看,才看到狗儿黑鼻满口白沫,身体不由自主地,倒退着疾走。
她如今还想起黑鼻倒退走路的样子,像是暴走的时钟,以一种逆行的方式绕着圈子,重复一圈又一圈,像是永远不会停止那样。哥哥从房間出来的时候,黑鼻已经倒下了,脚仍一下一下在空中奋力划着,满地失禁的尿液和口沫。哥哥掰开黑鼻的嘴,把水管塞进喉咙里灌水,想要给它催吐。她帮哥哥按着黑鼻的头,看进黑鼻的眼睛,仿佛觉得黑鼻也正以惶恐的眼神看她。黑鼻最后乏力侧躺在地上,四支脚却笔直地僵在半空,舌头从齿间瘫出来。她蹲在黑鼻身边,却不敢再摸它。她知道黑鼻已经死了。
她不曾以那样迫近的距离凝视生命缓缓流失。即使是父亲过世那天,她从学校匆匆赶去医院也只来得及看见父亲的遗体,午后安睡那样躺在白色担架床上,恍如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急诊室都是忙碌而慌乱的人,无人察觉时间喀达了一声就静止不前了。而哥哥总是冷静,不曾恸哭流泪。哥哥从厨房里拎出一个黑色的垃圾袋,沉默而木然地将黑鼻的尸体塞进袋子里。一截褐色的狗尾巴还露在袋口,哥哥伸手又把那尾巴塞了回去。
他们一起骑着摩哆车把狗儿载到附近的油棕园里埋了。也不知为什么,她一路心虚,怕有人看见。但她心底知道那其实也没什么好值得不安的,更多附近的居民在这里乱倒垃圾、焚烧塑料。然而那不一样,她手提着塑胶袋的时候,仍然觉得死亡的气息如在手指缝间簌簌漏下。她站在油棕园里,看着哥哥把那黑色的袋子拖进坑洞里,把泥土填回去了,又用脚在那小土堆上踩了几下。她想早一点离开那幽暗无光之地,不住催促哥哥快点。
灰蒙蒙的云层厚重,看不见月光,她抬头看,不知已是什么时间。她跨上摩哆车,和哥哥依着原路回去,经过油棕园小径,都是碎石子,一阵的颠簸,石子挤压出喀嘎喀嘎的声音。她这才摇晃出一身疲惫不堪。从天黑之前到现在凌晨无光的时分,像穿越了遥远的时差,一身汗水早就风干了。她看见哥哥的脚踝上仍残留着泥土,已结成浅色的印迹。一路的虫鸣,渐渐也遗落在背后了。摩哆车在笔直的小路上开着,耳边是呼呼而过的风声。突然摩哆车拐弯闪避什么,吓了她一跳,紧抓着哥哥的肩,回头看去,路灯底下匍伏一小团事物。哥哥把摩哆车转过头,车头灯照清楚了,原来是一只青蛙。那只褐色的蛙,比拳头还小,也许才从油棕园的灌溉渠里爬了出来,却恍然不知刚刚逃过被轮胎碾死的一瞬,仍一动也不动地蹲在柏油路上。
她看着那只蛙,想起了什么,对哥哥说:“你帮我捉它。”
回家后她躺在床上,闭上眼却老是浮起黑鼻倒退着走路的样子,一夜都睡不好。哥哥依旧什么也没说,但她心底其实暗暗自责。清晨她就起床了,拉开窗帘,窗外夜色未褪,远处天际才有一抹蓝色,慢慢就要漫漶整片天空。六点十五分出门刚好可以赶上第一趟的校车。她换过一身白色的校服,也没吃早餐,拿钥匙打开了门锁。以往狗儿听见哐啷声响就会摇着尾巴跑来,如今屋外徒然一整片的寂静。她又记起了一件事,回头把拜神的供桌上一小块黑布仔细地用别针别在袖子上。父亲未过七七,她还要戴孝。那正方形的布块在纯白的衣服上格外突兀,像是白雪地上的一方黑色的洞口,又像一个清洗不去的戳记。
她走到路口,候车亭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那样很好,她想。她独自坐在晨雾之中,马路上格外宁静,不若白天喧嚣,路灯结着黄光,偶尔才有一辆汽车呼啸而过。她手指抚过膝盖,一个一个微微肿起来的蚊瘼,还有一些痒的感觉。想起昨夜在油棕园里埋狗的情景,那些细节,仿佛才过了一夜就模糊了,像一层一层半透明的影像互相重迭,像骤然梦醒徒留残破漂浮的支节。但她手里提着一个透明的袋子,恍若唯一指涉现实的证据。透明塑胶袋里盛了一些清水,装着昨天捡来的那只青蛙。
她把袋口用尼龙绳系紧,就这样摇摇晃晃地拎着走。青蛙在水里露出半个头,豆大的眼睛骨碌骨碌的,隔着袋子张望这个它原本一生无从窥见、也无从理解的繁华世界。她不时举起那袋子,隔着薄膜,用手指去戳弄青蛙。一逗它,那只蛙就在那袋死水之中奋力地划动一阵。也不知为什么,她想起自己曾经一个人在泳池里用蛙式游泳的情景,孤单又冰冷地绕着圈子,像是永远都无法突破那层看不见的薄膜那样。
巴士兜兜转转还是到了站,她和一群睡眼惺忪的中学生一起下车,校园已是明晃的光景。还没走到班上就远远听见一阵嬉闹,走进课室才看见同班的男生们都蹲在地上逗弄什么。上个礼拜生物老师交代,要同学今天带青蛙来做實验。那些男生可乐了,把青蛙当玩物,捏在手里比谁的大只,还用粉笔在地上画了线,要青蛙赛跑。那些青蛙挣扎着要从人类手心逃走,后腿在空中乱蹭。还有男生恶质地把青蛙抛在女生的座位上,又引来尖叫惊呼。早晨的课室格外喧闹,但生物课在第四节,她想,待会中文老师进来,起立行礼之后,会不会有此起彼落的蛙鸣呢?想到那情景,老师错愕又无奈的表情,她就忍不住笑出来。隔壁座位的男生阿介转过头来,问她笑什么,她又不想说了。阿介看见了她手里拎着的袋子,说:“你也有青蛙。”就跟她要了来看,看了半晌,才对她说:“这个不是青蛙啦。”
“那是什么?”
“是蟾蜍啦。”阿介又笑着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
原来还是错了。她心底这样想。
坐在隔壁的阿介笑起来总露出一颗犬齿,像电视上的陈晓东,只不过男生没有酒窝,眼睛也小小的。也许连阿介也把她当成蠢蛋了。她有些负气,想到刚才还大咧咧拎着一只蟾蜍走进课室来,想必身后的同学都在笑她,也许刚才校车上所有人都在偷笑吧。她默默地把那个袋子收进了抽屉的最里,再不想看到那只灰褐的小生物。眼前那些同学扭打笑闹的情景仿佛一瞬间和自己无关了。她在班上平凡而不起眼,总是安静又害羞。其他女生会装模作样嫌青蛙恶心,撒娇央求男同学帮忙去老街的水族店里买,但她没有。全班只有她一个女生自己带了青蛙来,结果却还是带错了。
阿介说没关系,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做实验好了。她不置可否,本来她就不特别钟爱生物课。和那些以数字和公式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化科目不一样,有时她觉得生物课本里头的事物其实都是超现实的。比如说,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胞堆迭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生命。比如有一种可以无性生殖的生物,会从自身分裂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个体出来。她总是疑惑,那么那个被分裂出来的,还是原来的自己吗?生物课仿佛就是把眼前世界重新解构,再用另一种叙述的方式缝合起来,像把花朵说成是植物的生殖器官,花朵马上变得一点也不诗意了。但她也曾经偷偷在房间里翻阅生物课本的最后一章,人类生殖系统的图解介绍。那是老师不会教,考试也不会考的禁区。她看来看去,却无从想象那些手绘的器官剖面图,卵巢、子宫、输卵管那些,是构成自己的一部分,那真的一点都不真实。再翻过一页,男生小鸡鸡被画成管线复杂交错的抽象线条,而且插满了针,标注了各个部位安如其分的学名。
下午的时候,她拿了纸笔,跟着同学走进生物实验室。实验室在那排课室的最末端,陈旧而多尘,外头的光刻意被黑色的布帘和一排排高大的橱柜遮去了,日光灯管发出一种嗡嗡低频的声音。
她记得第一次走进那间实验室的时候,那一刻的光度和气味,让她恍惚浮起一种时间静止的幻觉。主要还是因为那些标本的细节都如此纤细而真实。她看见玻璃柜里头摆着许多动物标本,那些松鼠、兔子、水鸭,也有中型走兽如狸猫、狗和四脚蛇,全都以一种活着的生动姿态被凝结在那一刻。它们毛色鲜艳,眼眶嵌着玻璃弹珠,炯炯有光,不像死去的模样,却更像是电影的停格,或者被施放了木头人咒语。而昆虫和胚胎则被盛装在灌满防腐剂的玻璃罐子里。她看见一只初生的小鸡浸在微黄的液体之中,绒毛在水中舒张,眼睑半闭半张,载浮载沉。她不确定这里陈列的是勃然的生命,还是与之相反的死亡。她那时候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草履虫,和想象中一只单细胞生物蠕蠕游动的情境何其不同,那玻片底下其实只是一堆静止的液泡,在白色的强光之中,染过色的细胞核像是发紫的腌柑桔。
如今她站在阿介的旁边,看阿介动手摆弄着那只四脚朝天的青蛙。青蛙鼓胀着肚腹一片雪白,已经浸过氯仿而迷醉不动了。阿介用四枚大头针,刺穿了青蛙的脚掌,把它固定在蜡板上。那只青蛙现在就像是献祭的祀品。她侧头看阿介,阿介专注地在听老师讲述解剖的步骤,手里还握着手术刀。她觉得阿介和其他的男生一样,对解剖青蛙这件事有一种秘而不宣、跃跃欲试的,闷烧着的狂热。
她此刻却想起父亲。
她趁老师背过身在黑板上画图解的时候,低声问阿介说,好几年前小镇上有一次怪胎展览,阿介,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应该还在念小学的时候,镇上总不时有各种各样怪异又稀奇的展览活动,在报纸地方版登个小广告,小镇人总是轻易就被蛊惑,排着长长的队伍买门票去看那些金镂玉衣、马王堆木乃伊、越王古剑……当然,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在民众会堂草草搭建的文物特展也许都是唬人的,都是草率简陋的复制赝品吧了。
但她确实记得那时有一个怪胎特展,展出了好多好多不知从哪里搜集的各种畸形、异变的人类胎儿。她记得她那时大概才七八岁的年纪,父亲带着她走进在简陋的展场里,她就看见一整排一整排像是塑胶玩具娃娃那样的人形,被塞在一个一个玻璃罐里,摆放在甬道的两旁。她那时矮小,必须仰望才看得到那些浸在防腐液的怪胎标本。双身连体的、单眼塌鼻的、猩猩兽毛脸的、手指间长出蹼膜的,也有多出一支手或一支脚的,有的脑袋爆大如外星人……她和父亲挤在人群之中,只能缓步被推移前行。那展场格外闷热,连冷气都没有,电风扇咯啦咯啦摇晃旋转。而她触目所见的所有婴孩皆一模一样有着一张发皱的脸,紧闭着眼睛,肤色都被浸渍成灰蓝色。竟然有一个孩胎,身体都是正常的,却有着一个酷似狗脸的头,微张的口露出犬齿交错,吓得她紧拉着父亲,别过头去不敢再看。她如今回想,那样恐怖的畸形秀为什么会允许小孩子进去参观呢?而父亲牵着她,走在那些在玻璃罐里漂浮的婴孩之间,像徘徊在出口遥远的幽冥之谷。
“怕不怕?”父亲这样问她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看她,仍让她牵着手,恍无目的地在那展场里张望晃走,像被什么迷惑了那样。
“不怕。”
但她其实心底害怕。她看着阿介手颤颤地把手术刀划向青蛙的腹部,有一瞬间,她仿佛错觉了身体的深处浮上来一阵一阵的钝痛。隔着裙子,她偷偷按了按小腹却佯装无事,不让阿介察觉她有什么不妥。手术刀在腹膜上划开了一道笔直的线,并不似想象中那样爆出很多鲜血,却像拉开拉链那样轻易地就剖开了。阿介俯下头看,鼻尖都快要碰到青蛙的身体了。阿介小心翼翼用镊子揭开青蛙肚腹,那隙缝间露出绿绿蓝蓝的脏器,还有一堆看不出是什么部位,细细交错的管腺。那鸭蛋绿的腹膜被大头针钉在蜡板上,她这时才惊讶地发现青蛙的心脏竟然还在跳动。“这只青蛙不是已经死了吗?”她问阿介。但那枚暗紅色的小小椭图形的肉球,正在有力地依着固定的节奏,一下一下紧缩又舒放,那么奋力,仿佛下一刻就会从剖开的那开口弹出体外一样。
阿介说:“没有啊,它只是昏过去而已啦。”
然后就轮到她了。阿介把手术刀交给她的时候,她还犹豫要不要伸手去接。但阿介只是要她帮他把青蛙的肚子再拉开一点,好让他可以把那些内脏画下来。她一手握着锋利的刀,一手拈着镊子,贴近青蛙就闻到氯仿呛鼻的气味。她把那些金属冰冷的械具伸进青蛙体腔的时候,才感觉到那些内脏皆柔软如绵絮。她刻意不碰触到那颗依然跳动不歇的心脏,逐一挑开那些细小精致的肺叶、肝脏、胸软骨和脂肪体,刀子游移到下腹却一不小心滑了手,刀尖划破了墨绿色的卵巢,一团团浓稠墨黑的汁液从破掉的卵巢汩汩流出来,一直流、一直流,像是永远都不会停止那样。
她有些慌张,看阿介用橡皮软管注水,把青蛙的腹腔冲洗干净。原本墨色的汁液被冲稀后原来是繁多细小黑色的颗粒,浮在水渍之中。这些都是卵吗?这么多的都是卵吗?她退缩到阿介身后,阿介转过头想要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她发觉阿介的目光飘移到她手臂上的那枚黑色的布章。“终究还是被发现了。”她心底想。但她不曾开口,什么也没说,只是若无其事地环抱着手臂,用手掌遮住了那一小方块的黑色,不想再让阿介看见。
放学后她刻意留晚,班上同学都走了,她才把抽屉里那只落单的蟾蜍拿出来。都过了半天,透明的袋子蒙上了一层水汽,那褐色的蟾蜍像是闷久疲乏了,或者袋子的氧气也不够了,隔着袋子,她用手指戳弄那蟾蜍,它也只是懒懒地挪一挪身体,就别过头去。她把装着蟾蜍的袋子拎到课室后面,左右看看没人,解开了塑胶袋,将那只捡来的蟾蜍倒进水沟里去了。那蟾蜍在浅水里浮了一阵,才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开始划开了四肢,蹭着长长的后腿,慢慢游向了远处。豆大的身体噗通一下潜进水里,再看不见了。但她还站在那里,日光倾斜,把她的身影渐渐拉长。也不知道那些在实验室里被解剖死掉的青蛙,此刻都被丢去哪里了?但她尽量不去想象这些。她也不想去想象狗儿黑鼻的尸体闷在垃圾袋里,随着时间而在油棕园地底渐渐化脓腐烂的景象。
她到路口的杂饭档打包了晚餐才回家,打开门就看见哥哥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眼镜流转蓝绿的折光,电视里竟是天线宝宝叮叮和啦啦在招手的模样,也不知道一个人已经看了多久。她觉得疲累极了,走进浴室,打开浴缸的热水,水柱哗啦啦流下来。她伸手试探水温,然后就任由一股一股热气慢慢从浴缸升起,把白色的瓷砖在镜子都蒙上了一层水汽。她脱下校服,反手解开内衣扣带,镜中的自己徒留模糊的影子,界线模棱的身体,什么细节也看不清楚。她打开水喉洗了手,又把手伸向鼻子嗅了嗅。不管洗了几次,手指上仿佛还是残留着实验室里氯仿的味道,也不知是不是自己心理作用。她扶着洗手盆,站在镜子前面等水注满。洗手盆上还摆着父亲的刮胡刀、绿色罐子的发蜡、牙刷和面巾,全都和她一起笼罩在一层灰白的雾中。
每次疲倦的时候,她总是喜欢把自己关在浴室,泡在浴缸里,任由身体都埋在温水之中,仅仅浮出一个脸来。此刻她躺在水里,却感觉到小腹又传来一种深处的钝痛,看见双腿胯间流出一蓬血丝,竟是月经来早了。红色的血丝在水中像是活物,伸长了触须,扭绕、妖异地散开来。她觉得自己像是正在产卵的蛙类,看着那些沉殷的血丝慢慢地在透明的水中扩散,慢慢地把水都染成了一整片粉红的颜色。那一瞬间,她错觉自己的手指间也渐渐长出了透明的蹼,身上冒出了细细的疙瘩,肤色变成一种深褐的颜色,潮湿而光滑,像是小时候看到的那些浸渍在罐子里的怪婴。她想,会不会就这样一直躺着,就这样逐渐逐渐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呢?
她把全身都沉进被自身染红的水中,鼻孔噗噗冒着串串气泡,竟也不感到窒息。也不知过了多久,她耽溺在水中却听见一下一下闷闷的回声。哥哥在浴室外面敲门,都敲了一阵。她从水中坐起身来,拨开额前湿漉的头发,再看那些从她身上冒出来的蹼膜和疙瘩,一瞬间又全都消失了。她故意用手拨着浴缸的水,弄出一些响亮水声,向那湿热蒙蒙的虚空呼喊了一声:
“好了。”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