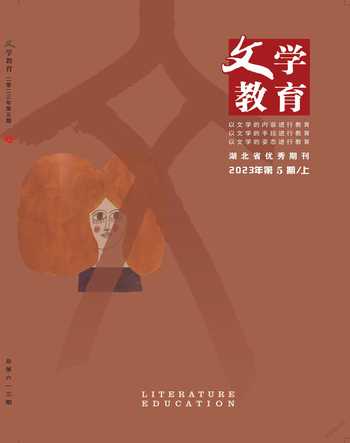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仪式及审美
2023-05-26杨金松
杨金松
内容摘要:对“他者”的关注是审美人类学一直以来的研究范畴之一。电影《赛德克·巴莱》以“雾社事件”为蓝本,展现了以莫那·鲁道为首的赛德克人为守护族群和信仰而抗争,最终被镇压而失败的故事。同时也鲜活的展示了20世纪初台湾原住民赛德克人的生活风貌,文章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对影片中赛德克族群具有“神圣/世俗”双重性的“出草”及“纹面”仪式、作为尘世到超凡的“桥”媒介以及赛德克族自身的审美制度进行探究。就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而言,关于游离在传统西方话语体系之外的“他者”文化这一问题,应该更加关注。
关键词:《赛德克·巴莱》 魏德圣 赛德克人 高山族 台湾原居民
赛德克族是台湾本土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分属于高山族的一支,主要居住在台湾的中部以及东部的山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赛德克族人因其自身居住在高山中、刀耕火种、山林狩猎、以及崇尚“出草”仪式等行为特征在1936年之后被日本的人类学家归类为“泰雅”族的一个亚群。
在当代,一部分居于台湾花莲县秀林乡以及万荣乡的赛德克族(一般称其为“太鲁阁族”)较为认可将“太鲁阁”命名为赛德克族的官方族群名称,但是另一部分居于台湾南投县仁爱乡的赛德克人则认为应该将族群名称命名为“赛德克族”,经过多年的“正名运动”,台湾岛上的赛德克族终于在2008年4月获批正名为“赛德克族”,正式成为了台湾岛内第十四个少数民族。
《赛德克·巴莱》是台湾导演魏德圣筹备了十二年之久的鸿篇巨制。该片在制作期间前后动员了20000余人参与拍摄,在台湾地区上映版本分上、下两部,总时长共计五个多小时,该片以台湾历史上的“雾社事件”为蓝本,用现代的影视手法,描述了赛德克人在与日本侵略者的对抗中寻求信仰及灵魂救赎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原始的赛德克族的一系列族群仪式。本文以影片《赛德克·巴莱》中的赛德克族为蓝本,对赛德克族的族群仪式、超凡媒介和审美制度进行了阐释,同时也论述了其对于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
一.“出草”、“纹面”——具有神圣与世俗双重性的族群仪式
“出草”及“纹面”本身是泰雅社会以及与泰雅族相近的族群共有的一种关于仲裁的猎首习俗,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适用于仲裁的习惯法。影片中对“出草”、“纹面”行为的诠释只在于其作为成人礼以及关于信仰的仪式上,但实际上“出草”这一行为也广泛存在于20世纪前的赛德克族人生活中。
在赛德克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譬如财产争端、侵犯同族财物、触犯祖先禁忌等一系列问题无法解决时,赛德克族会将仲裁权交给其信仰的祖灵,在进行猎首的过程中,赛德克人认为祖灵会庇佑占道理的一方获得首级。相反,没有得到首级的一方就会被认为是由祖灵判定其仲裁失败,在这个概念上,“出草”成功被视为行为正义的标志,成功“出草”代表着赛德克族人的行为被祖灵承认。换句话说,“出草”成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被理解为赛德克族人的价值判断,哪一方“出草”成功,哪一方就是正义的、正确的以及合理的。
同时,“出草”及“纹面”的习俗对于赛德克族的男性来说是其变为“成人”的确证。这不仅仅在生理意义上意味着由未成年到成年,在精神层面上这也是成为真正的“人”的标志。“出草”及“纹面”对于赛德克人来说是带有神圣意味的仪式,只有成功“出草”及“纹面”才有着守护部落、守护猎场的权利,而且只有经历“出草”然后“纹面”的赛德克人在死后才能踏上彩虹桥和祖灵同在,这对于赛德克族人来说是极其荣耀和神圣的。在影片开头,年轻的莫纳·鲁道在其族人的陪同下去猎杀其他部落的战士,亲手割下他们的首级带回族群内作为自己的战利品,在此之后才可以进行成人礼的第二个步骤——“纹面”,在简单的纹面仪式结束后,他就要遵循祖制,守护猎场及部族。片中这样说道:“莫那,你已经血祭了祖灵,我在你脸上刺上男人的记号,从今以后...遵守祖律的约束,守护部落,守护猎场。在彩虹桥上,祖灵将等候你英勇的灵魂。”[i]
“出草”及“纹面”的行为等同于赛德克族的族人对自己身份的确证,只有完成仪式的人才能在族群中被视为真正的人,并在死后回到祖灵栖居的地方。赛德克族通过这样的仪式来连接生理意义的人和形而上意义的人,使二者结合形成一个超越的存在。这有些类似于席勒提出的“游戏冲动”,只不过席勒认为游戏或者说审美才是使人之为人的最终途径,而赛德克人则认为这样的仪式才是最终途径。
在神圣意义上来说,“出草”及“纹面”是让赛德克族连通人神的仪式,完成这个仪式的赛德克人相当于拿到了一张死后通往祖灵之地的门票,与祖灵同在对于赛德克人来说是至善至美的,是无比崇高的。有着不言而喻的神圣意味。
赛德克人的“出草”仪式还有世俗意义上的阐释。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在其著作《神圣与世俗》中这样说道:“猎取敌人的首级、以人作为牺牲献祭和人类相食,这些都被人类所接受以便确保植物的生命。”[ii]以另一种视角来看,赛德克人的“出草”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维护。从实用角度来说,赛德克族生活在台湾岛上,依靠猎场而生,拥有着非常典型的原始民族生活方式,这就势必会遇到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自然资源过度占有和自然资源总量不变之间的矛盾。原始部族因其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要想在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就要增加人口数,以更多的人口来占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以此达到生存的目的。对于原始民族来说,人口的增长是族群强大的标志,是作为一个族群强盛与否的重要指标。但对于自然资源来说,人口的无节制增长总有一天会超过环境自身的承载力,赛德克人的“出草”行为某种意义上也为人口与环境承载力的平衡起到了作用。
同时“出草”及“纹面”也是一种确认个体强大力量并确立在族群中地位的标志。赛德克族人赖以生存的猎场并非只存在一支族群,就影片来看,就已经出现了“马赫坡”等十二支赛德克族群,每一支族群都将守护猎场、侍奉祖灵当作其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在“出草”的过程中,双方都抱有着对祖灵的敬畏以及狂热的斗志,影片中铁木瓦力斯的儿子曾经这样和他说道:“父亲,你说过最美的猎场只有最勇敢的战士才够资格去守卫,那我们和莫那·鲁道他们是不是要不断地相互战斗才能向祖灵证明自己是最勇敢的战士?那彩虹顶端的美丽猎场里大家是不是就成为永远的朋友?”[iii],能够在“出草”中获得胜利的人被证明是最勇敢的战士,拥有着非凡的地位,这一点在影片中后期,莫纳·鲁道派遣年轻人去联系其余11支族群的头领时有所体现,有一位名为“塔道”的头领说他的族群不参与这次行动,当年轻人再次劝导的时候,“塔道”头目说道:“你这个没有图腾的孩子!不要忘了你的身份!”这时四位年轻人全都哑口无言,这足以表明有没有图腾在赛德克的族群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脸上有图腾,那么在族群中的地位将会有极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本质上是由“出草”及“纹面”仪式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即神圣性与世俗性兼具的特点决定的。
二.“桥”——由尘世到超凡的媒介
彩虹桥在赛德克族中的地位是无比崇高的,它本身是作为赛德克族人死后进入祖灵之地的媒介被建构在赛德克族人心中,并形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虹一出现,就会死人,因而人们认为虹是神灵架设的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桥梁。”[iv]事实上,“桥”这一建筑本身具有十分浓重的宗教意义,就中国本土神话而言,便有许多与桥有关的超凡媒介。
首先,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传统的情人节,又叫“乞巧节”,相传牛郎和织女平日里因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天人相隔无法相见,只有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才能相见一面,而七月初七这天相见也不是平白无故就能相见,需要各地的喜鹊在这一天飞到一起,用自己的身体搭建一座桥来供牛郎和织女相会,这座桥就是鹊桥,牛郎织女便是在这座桥上破除了天人相隔的障碍得以相见。这是其一;其二,中国传统的生死观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去一个叫“地府”的地方去投胎转世,在投胎转世之前需要清除掉前世的记忆,所以需要在奈何桥的尽头喝一碗“孟婆”给予的“孟婆汤”来完成清除记忆的任务,关于奈何桥的名字有多种解释,但有其中一种解释是奈何桥的“奈何”二字取自“无可奈何”之意,刚好和人在转世投胎前对自己生前愿望未完成的不甘、对阳世家人的不舍以及自己的无奈相对应。在奈何桥喝过一碗孟婆汤之后,便会投胎到下一世并再次回到人间,所以奈何桥在中国人的认知里也是作为连接尘世与超凡的通道而存在的。
事实上,在通过“桥”时意味着生命形态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一定是生命形式的进化或者退化,但一定是“从一种生命模式向另外的一种生命模式的转变”[v]。比如鹊桥让牛郎的身上带有了一丝属神的神力,而让织女身上多了一丝属于人的人气儿,正是由于他们彼此纯粹的人、神属性被打破,参杂进了互属于对方的属性,所以才能借助“鹊桥”这一途径在天上相见。而奈何桥更好理解,来到奈何桥时是由人变鬼,走过奈何桥去投胎则是由鬼返人,这是非常明显的生命模式的转变,也正“是这种通道使从一种生命模式向另一种模式、从一种存在状况向另一种存在状况的转变成为可能。”[vi]
在《赛德克·巴莱》中,“桥”以其本身意义来说就在全片中出现了多次,除此之外,片中多次出现的彩虹也是一种类桥的概念,因为赛德克人将彩虹桥视为通向祖灵之地的通道,所以彩虹在其中也作为一种隐喻的“桥”而存在。对于赛德克族来说,彩虹桥是联通人神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彩虹桥的赛德克人才能与祖灵同在,进入到永远美好的猎场。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位赛德克人都可以通过彩虹桥达到祖灵之地的,唯有进行过“出草”仪式并进行“纹面”的赛德克人在死后才能进入祖灵栖居的地方。在上一章曾经提到赛德克族人用“出草”及“纹面”的仪式连接生理意义上的人和精神意义上的人,使之成为一位“赛德克·巴莱”,在赛德克族的语言中,“赛德克”意为“人”,而“巴莱”的意思则是“真正的”,所以“赛德克·巴莱”这个词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真正的人”。通过这个我们可知在赛德克人的认知中一个未经历过“出草”以及“纹面”的赛德克族人是不完整的,他只是一个“赛德克”但仍旧不是“赛德克·巴莱”,即是“人”但不是“真正的人”,他必须经由“出草”和“纹面”的仪式再次生成一位完整的人,这种再生成的完整并非生理上的完整,而是精神与肉体上双重的完整。
但仅仅只到这样的程度依然是不够的,成为“赛德克·巴莱”只代表在现实中获得了觐见祖灵的资格,对现世的赛德克人来说,完成了“出草”和“纹面”的赛德克人确实是完整的,因为它使生理上的人与精神上的人得到统一,但如果想要进一步使其进化,达到超人的境地,就需要踏上彩虹桥,通过彩虹桥去到祖灵栖居的地方,这时的赛德克人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纯粹的人与精神上完满的人,而是进行了生命形式的跃迁,换句话说,此时的赛德克人已经与神同在,达到了超越肉体和精神的、另一个层面上的圆满。“也许可以这样说只有通过一系列的‘转变仪式——即经过不断的入会式,人类的存在才能达到圆满”[vii],当赛德克人通过彩虹桥那一条窄窄的通道时,彩虹桥自身成为了两个世界的媒介,它沟通人间和祖灵之地却不属于两边的任意一边,兼具双方属性而又保持中立,成为赛德克人从尘世到超凡的媒介。
三.“审美制度”——关于双方冲突的审美人类学阐释
审美与制度的关系早已有人提出并研究。从概念上来说,“审美制度”是一种关于审美观以及审美活动的规范,它本身不同于有着执法效力的法律法规,而是一种“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等对人们的审美和艺术观念以及审美活动产生的非正式建构和规范。”[viii]它决定了特定时期的特定族群中对“美”的认知。
反观《赛德克·巴莱》中作为矛盾双方的两端——赛德克人和日本人,我们不难发现,赛德克人崇尚力量、血液,而日本人在片中则是所谓优雅与文明的代表。而二者在影片中的冲突一般的认知可以将其理解为野蛮与文明先天的二元对立,而赛德克族人对日本人的反击也被视为正当防卫的代表。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对其进行这样的解读,但在审美人类学的视阀下,对双方又有着不一样的诠释。
赛德克族是居于台湾岛上的原住民,它们相较于日本而言生产力极度低下,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狩猎为生的生活方式,是名副其实的原始民族。当然,这个“原始”是带有相对意义的,如果把赛德克族的生产力水平置于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那情况又将不一样,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中对“原始”有着这样的叙述:“‘原始之意是极为相对的,如果考虑到地球上人类的悠久,那么,石器时代的人就根本不比我们原始多少。”[ix]但是如果将同时代的日本作为参照物的话,赛德克族就显得非常原始了。
在文明程度方面,日本领先赛德克族人不止一个时代,从他们入侵台湾之后所做的一系列措施来看——建学校、邮局、警局,这些都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才会出现的公共设施,而赛德克族人仍然保持古老又原始的生活方式;从信仰来看,赛德克人信仰的是他们的祖灵,并且十分坚信祖灵的存在,一切的行为都为了向祖灵证明自己信仰的虔诚,为了证明自己的虔诚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日本在此时已经没有传统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取而代之的是浓重的军国主义信仰,这并非是超凡层面上的信仰,而是出自日本帝國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日本现阶段的文明发展需要军国主义的的精神力量做支撑,而非虔诚的、无功利的信仰。
在对比了生产力、文明程度以及信仰等多方面的差异后,不难发现,赛德克族人的仪式也好、习俗也好、包括最后的冲突也好,他们贯彻的都是自身族群的审美制度。“出草”仪式是为了证明自身的勇武,并对祖灵祭祀;“纹面”也是赛德克族人确证自身地位以及信仰的方式,赛德克人将这些审美活动视为崇高的和神圣的,完成这些仪式一方面是实际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其自身信仰有关的神圣意义。如朱狄先生在其《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民族的纹身意义做了以下阐释:“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一)为了避免鬼的迫害;(二)图腾崇拜;(三)引起敌人的恐怖心理;(四)表示等级的差别;(五)表示将自己贡献给神灵。”[x]赛德克人至少符合第四和第五点,如果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话,第三点也是完全合理的。
而日本因其文明程度远超赛德克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迈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貌似先进的外表下隐藏的本质是扩张与掠夺,而军国主义又为日本人的大脑中注入了狂热。在生产力、文明程度以及信仰均认为自身先进、文明的日本人自然对赛德克人的审美制度嗤之以鼻。对于日本人来说,赛德克人的仪式、纹面等艺术甚至不能归类到审美中,在绝大多数的日本人看来,赛德克族人的行为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即使有小部分的日本人对赛德克人态度相对友好,但在其笑脸下隐藏着的仍然是高傲的面孔。一方面日本不将赛德克族人视为平等的对象,对其审美制度持厌恶、反感的负面态度,另一方面由于军国主义扩张与掠夺的本质,需要他们对赛德克人赖以生存的猎场进行采伐,对赛德克族人进行所谓的“文明化”,这样的“文明化”使赛德克族人赖以生存的猎场被毁掉了,赛德克人无法继续传承“出草”以及“纹面”仪式,这一环节的缺失,使赛德克人无法“成人”,并且丧失了与祖灵同在的凭证,从根源上消解掉了赛德克族的信仰根源。同时,日本对赛德克族的奴化教育还造成了新一代赛德克族人的信仰冲突和自我身份认知冲突。这便触碰到了赛德克人自身族群以“祖灵信仰”、“族群认同”为核心的审美制度的根本。
赛德克人的审美制度在现实世界是以一种集体意象的方式来体现的,“作为反映形式,集体意象是一种极少个体烙印的、彻头彻尾社会化了的意识。”[xi]其显现形式就是赛德克族人对祖灵的信仰、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以及对猎场的守护。纵观全片,即使是受到文明教育的花冈兄弟最后也承认自己是一名“赛德克”人的身份,更不要说一直处于赛德克族生活环境下的、更为纯正的赛德克族人了。这种集体意象是崇高的、神圣的,而绝非日本人眼中的野蛮、落后。日本人对赛德克族审美制度的认知偏差和随之对赛德克族审美制度进行的毁灭性打击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双方冲突的诱导因素。
赛德克族作为文明社会视野下的“弱小者”在近代社会中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象征,但实际上他们的仪式、踏入超凡的媒介以及其审美制度都具有非常高的审美价值,《赛德克·巴莱》这部影片虽然主要的叙述主体是“雾社事件”,但导致这件事发生的诱因之一则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歧视、剥削、反感、奴役以导致的对其审美制度的彻底毁灭。透过影片故事本身,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之内,西方社会[xii]对非西方社会的文化、审美、习俗、制度歧视、忽略、扭曲甚至将其毁灭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对非西方社会中的仪式、超凡媒介以及审美制度等资源进行重新发掘、保护和再阐释,并希冀于以此来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樊笼正是审美人类学一直以来关注的问题。原始民族中的“巫术、宗教和科学都不过是思想的论说”[xiii],对于在传统美学视野之外的“他者”,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刘洁.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性别差异——以影片《赛德克·巴莱》的审美人类学解读为例[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025(001)
[2](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张芳芳.从电影《赛德克·巴莱》到伊利亚德的《神圣与世俗》——以猎首为中心[J].文化月刊.2021(2)
[4](日本)吉田祯吾著.王子今,周苏平译.宗教人类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5]向丽著.审美人类学:理论与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6](法国)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朱狄著.艺术的起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8]张佐邦著.美学人类学: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9](英国)J.G.弗雷泽著.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金枝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注 释
[i]刘洁.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性别差异——以影片《赛德克·巴莱》的审美人类学解读为例[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25(001):51.
[ii](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著. 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6
[iii]张芳芳.从电影《赛德克·巴莱》到伊利亚德的《神圣与世俗》——以猎首为中心[J].文化月刊.2021(2):163.
[iv](日本)吉田祯吾著.王子今,周苏平译.宗教人类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95
[v](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著. 王建光譯.神圣与世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4
[vi](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著. 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4
[vii](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著. 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4
[viii]向丽著.审美人类学:理论与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20
[ix](法国)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 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
[x] 朱狄著.艺术的起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70
[xi]张佐邦著.美学人类学: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35
[xii]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均和西方国家相同,故在此笔者将日本列入西方国家。
[xiii](英国)J.G.弗雷泽著.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金枝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100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