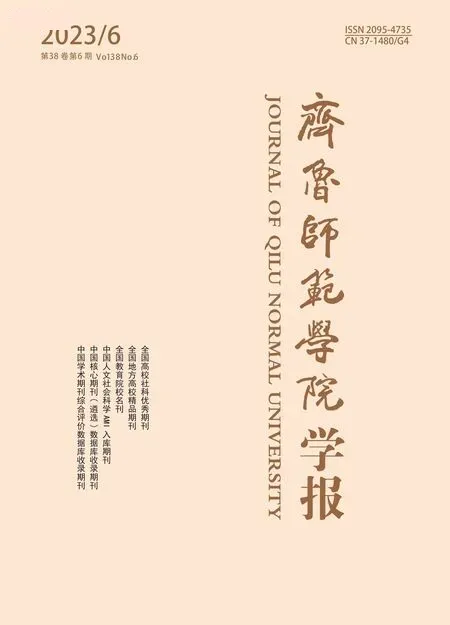弗莱美学思想的中国古典艺术渊源
2023-04-25邱蓓
邱 蓓
(深圳技术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118)
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艺术史家和美学家罗杰·弗莱是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鼻祖。他强调艺术作品的形式特征,确立了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创立了后印象主义美学。作品《视觉与设计》(Vision and Design, 1920)、《变形》(Transformations,1926)、《塞尚》(Cézanne, 1927)以及他去世之后出版的一部论文集《最后的演讲》(Last Lectures , 1939))是他对现代主义美学的杰出贡献。霍华德·汉南(Howard Hannay)指出,“罗杰·弗莱在英国文艺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1]15。作为现代主义美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倡导法国现代艺术流派,把艺术从以“再现”为目的的印象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它一种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在欧洲艺术史中从未出现过的力量。继而,他凭借自己充沛的活力、丰富的想象力、强大的号召力、卓越的见解和精彩的演讲,成为吸引年轻画家的磁石,引领英格兰艺术家们进入国际艺术舞台,使他们了解法国画家塞尚和后印象主义,并自觉加入到现代主义运动中。鲜为人知的是,弗莱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对中国古典艺术持有浓厚的兴趣,并深受中国艺术作品的启迪和影响,因此他的艺术理念中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古典美学特征。本文将阐述弗莱形式主义美学的发展脉络,并从弗莱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和研究入手探讨弗莱美学的中国渊源。
一、弗莱形式主义美学观
1910 年,罗杰·弗莱在伦敦举办后印象主义画展,他认为自己从后印象主义作品中找到了印象主义所缺乏的形式设计。印象主义及之前的艺术作品重在表现内容和对客观物体的再现。作为一位形式主义批评家,弗莱反对以摹仿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美学。他指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不是简单摹仿或者再现自然物质的形态,而是通过造型和设计元素同画家的情感融为一体[2]68。他认为那种为了追求形似对艺术作品进行简单复制的行为必然会阻碍作品的审美效果。在《艺术与设计》一书中,弗莱把视觉艺术的具象看作是对“纯粹美学反应”的干扰。
弗莱认为形式是作品的本质内容,也是作品最基本的表达形式。他指出,艺术作品的创作“必须遵从一些基本原则,不管是符合塞尚提出的所有的形状都应该趋向球体、圆柱体或锥体的准则,还是符合其他体系的准则”[3]108。这个“准则”指的是形式上的设计,如艺术作品的基本构图、布局、光影的平衡等等。也就是说,不论作品的内容是什么,它都应该具有造型设计之类的形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能够经久不衰,一定是经过精心设计、悉心安排的。“形式”和“设计”这些艺术中的基本要素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伟大的绘画作品前可以获取无尽的满足感。在他看来,形式本身能够赋予内容意义,所以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在《视觉与设计》中弗莱提出,形式是艺术作品最本质的品质。因此,衡量一件艺术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不在于艺术作品能否精确地再现现实,而是能否通过线条、形体、色彩、造型等形式组合关系中来使观赏者获得一种审美情感和体验,即作品是否具有“有意义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s)。鉴于此,艺术家应该注重作品的视觉特征,利用有意义的形式——造型和设计——而不是主题内容来进行艺术创作,这是弗莱形式主义美学的主导思想。
不过在形式这个问题上,弗莱的立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始终是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性质的症结所在,对此,我并不羞于承认,在不同的时候,我提出过不同的解决方案。我肯定不同于彼时的立场——那时我坚持纯粹造型方面的绝对重要性,而且几乎是暗示,没有别的东西需要考虑进来,而这时,我强调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绘画的戏剧性可能的东西。”[4]13弗莱早期的美学理念把以造型和设计为特征的形式作为艺术创作中唯一的考虑因素,而且坚决反对艺术再现。到了晚期,他认识到虽然再现不是形式主义艺术家追求的目标,但艺术作品的形似与形式并不是一对无法兼容的矛盾体。诚然,观赏者在欣赏艺术作品时,那些由作品所表征的、原本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物体可能会被再现出来,使观赏者感觉艺术作品是写实的。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纯粹的形式艺术分析没有生机,除了造型和设计,情感应该是决定艺术作品优劣的更重要因素。20 世纪20 年代他的美学思想进入了一个转型期,他开始从科学意义上积极探索形式在艺术中的意义与目的,通过“将再现与形式主义范式综合起来而又不放弃纯粹审美经验的理想,从而将现代主义重新整合进更广阔的艺术史传统”[5]70。
“形式”对于弗莱来说是一种观念模式,是美,是好奇心,是创造力,有时候是一种不确定的事物。他在《视觉与设计》中指出,在美学整体中,形式和它所传达的情感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分割。后印象主义倡导艺术是情感的外在表现,在创作中通过形式表现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作为后印象主义批评家,弗莱主张不仅要“重视艺术中形的观念”,还要“重视作者的主观个性,强调在作品中表现作者的主观感情和情绪,主张形式的表现”[6]77。 他把形式和情感描述为“美学视角”,提出艺术家应该从形式和情感这个美学视角来思考艺术作品的创作。这就是说,形式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单纯追求形式是不够的。艺术家不应该像印象主义艺术家那样摹仿世界、片面追求作品的内容以及让观赏者产生的真实感觉,而是应该通过构图、线条等形式来表现自己的主观情绪,表达人类自身内心的一种主观感受。简言之,艺术家应该利用形式来表达情感。作品是否具有感知力和活力才是评价艺术作品好坏的关键标准。“感知力”(sensibility)和“活力”(vitality)两个词随即成为弗莱形式主义美学最基本的批判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向与弗莱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兴趣有着很深的渊源。丹尼斯·萨顿(Denys Sutton)在《罗杰·弗莱的书信》的前言部分追溯了弗莱晚年对中国艺术日渐增长的兴趣。弗莱的好友亚瑟·维利也指出,弗莱与他的通信中多次提到中国。1920-1921 年《伯灵顿》杂志开辟专栏讨论“中国艺术的哲学”,弗莱是该杂志的频繁撰稿人。他在专著《变化》中的《中国艺术面面观》这一章中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的艺术,还在《最后的演讲》这部作品的第八章《中国艺术》中介绍了中国不同时代的艺术。从他撰写的以中国艺术为主题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艺术的热情。弗莱对中国艺术的兴趣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弗莱曾担任英国国家画廊总监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绘画馆的馆长,时常与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劳伦斯·宾庸、利·阿什顿等人探讨中国古典艺术,这些为他了解和研究中国艺术品提供了便利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以绘画、书法、雕塑与陶瓷艺术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艺术,并从中发现了足以启迪其美学追求的形式之美。同时,他又根据现代主义艺术探索的需要,进一步阐释、发挥了中国艺术,使之成为其形式美学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7]73。
二、弗莱美学中的“感知力”与中国古典艺术中的“线条韵律”
感知力是弗莱美学的核心。弗莱反复强调,艺术家应该对艺术持有一种敏锐的感知力。他在《最后的演讲》中对“感知力”的产生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感知力指的是一种审美情感。这种审美情感与其他感情不同,它决定艺术作品中的形式,又通过形式关系来表达出来,是艺术家感受到并传递到作品中、继而被观众所感受到的审美情感。按照弗莱的阐释,艺术家在创作时首先被某个场景或者某个物体的布局或者视觉效果所打动,产生一种情感反应。然后,他审视和思考这个场景及其视觉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元素变得清晰、独立,艺术家由此看到一种独特的设计和造型。这种造型可能看起来与真实场景不同。在思索这种设计以及由视觉产生的形式关系的时候,艺术家可以感受到的一种美学情感,艺术创作就是他传递、表达这种情感的渠道。通过对这种形式上的和谐关系的再创作,他把最初看到的设计和造型以及体会到的情感传递到他的艺术作品之中。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发现了形式并通过敏锐的感知力在艺术作品中实现了自我。如果艺术家能够成功地传达审美感受,艺术作品就拥有了生命。而观赏者也会因这种生命力被这个作品深深吸引。这样,观赏者就能察觉到作品中的形式关系,理解有意义的形式,看到作品表象之下的现实,并体验这种审美情感[8]108。
弗莱相信伟大的作品中都包含感知力,而西方绘画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感知力”。用他的话来说,“感知力是西方艺术家在设计和造型中无法企及的重要元素”[9]33。在钻研中国艺术的基础上,他发现这是因为西方艺术家仅追求形似,而不注重审美情感的表达。清代画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西洋画》中对西方绘画做出评价:“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这里的笔法指的就是笔触,即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笔调和风格。西方绘画艺术家擅长使用几何学,能够利用光影准确地表现明暗,利用近大远小的物理性透视空间表现远近距离。虽然他们掌握绘画技巧,但是他们只是“画匠”,不能被成为画家,因为他们不注重情感,缺乏“画风”(brush manner)。因此,他们的艺术创作只是使用透视画法、光影的透视法和空气的透视法,对景写生,力求肖似真物,还原真实存在,达到一种与原物尽可能接近的逼真效果。弗莱认为艺术中的这种现象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西方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主宰,喜欢以进取精神征服自然,因此西方艺术家也擅长使用先进的技术进行艺术创作,借助科学手段塑造酷似现实生活的艺术形象。中国艺术家则不然, 他们不把纯粹摹仿界定为艺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促使中国艺术家在创作中追求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以及物我两忘的境界。艺术家往往借客观事物抒发情感,表达内心。因此,中国画不注重写实,而注重写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弗莱反对西方绘画对真实物象如同照片一样的摹仿和照抄。他认为如果过分注重精确的几何描述、明暗对比和视角,就会分散画家的注意力,阻碍他们向更高的目标发展。所以仅仅追求画面栩栩如生是不够的,滥用西方现实主义摹仿方法必然会压制感知力。
就具体如何产生感知力这个问题,弗莱也是颇有见地。在对中国各时代艺术作品进行孜孜不倦地钻研后,弗莱对线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断言感知力是通过线条韵律(linear rhythm)产生的。中国艺术作品盛用线条,在绘画和书法中线条无处不在,但在西方艺术作品中线条不显著。在《线条作为现代艺术的表达手段》中,弗莱指出:“绘画的魅力——秩序与多样性、抽象与复杂性的冲突——不是由点而是由线条引发的。当线条具有一种明显的节奏,而非机械化的时候,感知力便应运而生……艺术的革命把艺术家从准确再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线条韵律使艺术家能够更加充分地表达自我。”[10]62他敏锐地感知到线性韵律的作用,号召艺术家通过使用线条来提升艺术作品的品质。因为线条记录的是一种姿态,揭示的是一种节奏,能够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形象,既可以是阴柔秀丽的,又可以是刚劲有力的;同时,线条韵律也是艺术家表达自我、抒发情感的重要手段,是作品是否具有感知力的决定性元素。正如谢一铭所说:“线条在传统中国画中具有造型和传情达意之功能,是中国画的灵魂。画家以线造型、以形写神,使画面气质神韵相生、神形兼备,使中国画更具生命力和感染力。线条是画家对客观景物的内心感受、是中国画独特的造型语言、是自我表达情感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画中极具审美价值,展现出中国画的灵韵之美。”[11]86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线条蕴含着独特的韵味,能够通过寥寥数笔简单的勾勒唤起生命的韵律,反映人的情绪情感,并与人类生活和情感变化交相辉映。
线条韵律是艺术家情感的流露,反映艺术家的敏锐的感知力。弗莱呼吁西方艺术家在绘画中使用线条韵律,从而提高作品的审美情感。他认为线条这种形式设计能够引发两种愉悦的情感:一种是线条自身的韵律,另一种是造型的结构意识。他在文中说:“线条韵律如此纯净和完整,给我们带来一种如跟随舞蹈家跳舞一样的愉悦感……艺术家用结构线条来表达客观的结构意识。”[10]66绘画与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它不是纯粹再现实物,也不是完全抽象。它具有形式之美,有情感与感知力,既表征实物又表现生命。另一方面,线条引发空间美感。艺术作品中的空间构造既不是凭借色彩堆积,也不是通过几何透视法,而是通过一种类似韵律的事物所引起的空间感形。确切地说,是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空间创造”。
三、弗莱美学中的“活力”与中国画中的“气韵”
弗莱形式主义美学中另一个关键词是“活力”(vitality)。弗莱在《最后的演讲》中对“活力”这个词做了阐释,他指出,活力是“那些潜意识中的部分,它们渗透到我们的意识生活中,由无数的感觉、欲望、偏好、渴望、判断以及其他构成我们精神生活的所有事物组成。它与灵魂相连,我们不知道它如何发生,然而它就在那里”[9]39。“活力”是一种难以言表、无法捉摸的品质,它不在我们理性理解的范围之内,只能通过心灵感受到。简单地说,活力是一种通过某一个意象来向我们传达其具有内在生命的力量,它潜藏在作品中,是使作品独一无二的特征。
毋庸置疑,弗莱美学思想深受中国古典艺术的启发和影响。弗莱美学中的“活力”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气韵”极为相似,可以说“活力”是“气韵”的直接翻译。“气韵生动”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术语,是中国画创作的总原则。六朝南齐人物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画有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一词汇被频繁使用。当代学者伍蠡甫在《中国画论研究》一书中对居绘画理论“六法”之首的“气韵”一词做了解释:“气——画家有度物取真的认识力或审美水平,它便随着笔墨的运使而指导着创作全程——这个贯彻始终的‘心’力或精神力量,称为‘气’;韵——风韵、韵致的表现,时常是隐约的、暗示的,并非和盘托出。”[12]78气韵就是一种流注于形象之间、无法用感官感知又神形相融的美。中国绘画艺术把追求超越外在形态视为终极目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气韵是艺术作品的灵魂,是中国画根本性的审美标准,是中国古典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历代中国艺术理论的基石。
把弗莱对“活力”的看法与中国文化中的“气韵”这个词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弗莱美学中的活力与中国艺术中的气韵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首先,两者都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审美要素。中国艺术家认为气韵无法用理性去解释、用感性来感知,弗莱也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活力如何产生或者如何与其他美学品质相关。第二,弗莱和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中国艺术家都认为艺术家要摒弃西方人提倡的人类中心主义,要培养一种警觉的被动状态以便理解这个世界的内在规律。第三,两者都反对艺术作品对真实世界中自然物体的简单摹仿。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讨论了“气韵与形似问题”,称其为“由形似的超越,又复归于能表现出作为对象本质的形似的关系”[13]。气韵是超越形似的品质,如果为了追求形似而放弃气韵,作品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相应的,如果作品具有气韵,那么作品在神似的同时一定也具有形似的效果。弗莱也认为绝对不是因为艺术作品跟真实世界中的实物相似就具有活力。他强调艺术作品要有活力,就要摒弃单纯的摹仿。如果只追求逼真的效果,而忽视了情感,作品就会令人感觉没有活力,因为它会使我们联想到作品所表征的物体,而不是艺术作品本身。
通过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和观察,弗莱发现活力或气韵在中国艺术作品中最好的表现形式是动物画。正如国画家、书法家杨雍指出,优秀的动物画形神兼备,“让人眼前一亮,当你细细品赏之后,但觉唯妙唯肖,生动鲜活,则又不忍释卷。慢慢拜读,让人惊叹若有神助之感。所谓达其性情,尤以不求形似、若不经意为妙,而难在以简驭繁,遗貌取神。笔墨自是空灵飘逸,实是让人叹服,堪为性灵之作!笔操于人,墨授于天,而蒙养可知,叹其于若不经意中得神来之笔。”[14]在专著《变形》中,弗莱阐释了气韵生动的中国动物画给他的启发。他指出,人类捕捉艺术生命力的能力通常与文化发展阶段相关,人类在早期阶段能感知动物的内心世界,但是随着人们获得文明意识,这种能力就消失了。然而,中国人没有狭隘地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同类上。他们从未忘记人在大自然中的相对位置。他们认为人物形象无足轻重,反而赋予动植物形态更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为了塑造出神形兼备、具有活力的动物形象,艺术家不应该受到先验观念的影响,而是应该让自己处在一种暂时搁置人类价值的精神状态,尽可能地抛却人类视角,停止把人类的情感和属性投射到动物身上,停止根据动物对人类生活的贡献来评价动物。可见,弗莱领悟到把心灵中“主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容”净化掉是创造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的必要条件,也是创作活力和气韵的关键[3]104。换句话说,他认为艺术家应该“保持对客观视觉印象的尊重,在超然的状态下进行细致的观察,最终从客观事物本身提炼出主旨和精神,这样才能使作品具有丰富的表现力”[15]133。
四、结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迪下,弗莱完善了他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他强调形式在艺术创作中的核心作用,认为艺术美感是由形式上的美感滋生出来的。同时,他提出美学体验与其他人类经验不同,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必须要把智力活动与情感结合在一起,在创作过程中表达他的情感,这样才能摆脱印象主义美学只强调形式、不注重情感的藩篱,赋予艺术作品形式美感,为作品提供感知力和活力。
“感知力”与“活力”作为弗莱美学理论中艺术的两大要素,两者都是形式以外的生命表现,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中国古典美学特征。弗莱对“感知力”的认识基于对中国古典艺术中由线条构成的形式的理解:线条韵律是中国艺术家对于形式的反应,是用来表达自我状态、抒发情感的关键。而在中国动物画中他发现了被他称为“活力”的审美元素,并在对它吸收和利用的基础上使之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位形式主义批评家,弗莱成功地建立和发展了他的理论。他把他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应用在后印象主义绘画中,希望艺术能达到这种境界——通过形式来激发审美情感,在形式与感受之间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