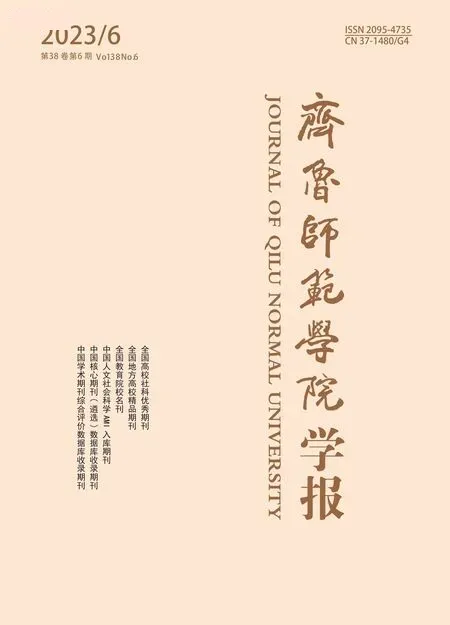“繁简”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
2023-04-25赵秒秒
赵秒秒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繁简”乃重要的为文之道,诗文理论中多有探讨,小说批评中也多有运用。以往研究,或多关注“繁简”思维[1]73,或多关注“繁简”辩证关系,且主要以诗文理论为研究对象[2]319。本文拟基于“繁简”意涵的类释和“辨体”中的“繁简”规定,以中国古代小说文本批评为依据,探讨其“繁简”之辨及其组合原理,以服务于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
一、文法与格调:“繁简”论发展历程探析
从“繁简”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经书作为不刊之正典,当为“繁简合度”的创作典范,《左传》成公十四年曰:“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3]4154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对这五例作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3]3702杜预又从总体上强调《春秋》具有“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3]3707的创作特色。可见,经学阐释是繁简论得以发生的根基。
在文学批评中,刘勰《文心雕龙》依经立义,以经书作为“繁简”理论资源①,从审美格调和行文运笔方式两大层面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繁简”批评体系。
在审美格调层面,“繁简”包含不同文体简约与繁复的体要之辨以及作者与作品繁缛与精约的体性之辨。首先,刘勰在文体论批评中,以“体要”作为核心概念,提出了“铭”“箴”“章”“表”等不同文体的繁简要求。关于“体要”,《序志》篇曰:“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4]1913刘勰以《尚书》为引,针对“文体讹滥”的现象,提出辞宜“体于要”,“体要”于此为“精约”之意。《征圣》篇曰:“《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4]47-49此时,刘勰虽依然引用《尚书》,但认为“体要”成为与“言辞”互为表里的文体概念,注重“体要”是为了“成辞”,那么所成之辞可以有“繁缛”和“精约”等多种标准,此时,“繁与简均可称之为体要。”“体要的体从原来‘体于要’的动词转化为文之大体的名词之‘体’,要则从‘要约’转化为得体与关键之意。”[5]121在《诠赋》中,刘勰认为“丽辞雅义,符采相胜”为“立赋之大体”,而自宋以来,作赋者却“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4]307,此“体要”即赋之“大体”,指与不同文体相适配或不同作家所展现出来的语言、叙述方式、体式样貌等文学形式相统一的指称,“繁简”是“体要”的具体形式表现之一。在具体批评中,刘勰论述了不同文体的“繁简”体要要求,《铭箴》篇指出:“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4]420又在“总赞”中强调:“义典则弘,文约为美。”[4]425可见,“铭”之体贵简约。又《章表》篇言:“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4]844指出“章表”的体要要求之一是需要“繁约得正”,由此才能合律。
其次,刘勰还将“繁简”与作者的创作性情联系在一起,他在《体性》篇中指出根据作者“才、气、学、习”的不同,划分出八种体貌类型,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其中,“精约者,覈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繁缛者,博喻醲采,炜烨枝派者也。”[4]1014对不同作者之“繁缛”与“精约”的体性风格进行了辨析。《镕裁》篇指出:“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竄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4]1190“分”即作者之个性,根据作者个性之不同,呈现“繁”与“略”之风格差异。在刘勰的观念中,陆机的文学创作风格较为繁缛,他在《才略》篇认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4]1813贾谊的创作风格较为峻洁,“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4]1024总之,刘勰指出由于作者情性之差异,作者之体性风格会具有“繁缛”和“精约”之差异。
在行文运笔方式层面,《镕裁》篇从意与言两大角度出发,强调“镕意裁辞”,认为:“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4]1177因此,通过“规范本体”之镕和“剪截浮词”之裁,以实现文章之“纲领昭畅”和“芜秽不生”,否则,文章便会出现“一意两出,义之骈枝”和“同辞重句,文之肬赘”的弊病。[4]1180因此,刘勰认为“镕裁”之针对对象在于“情理”和“文采”,“镕裁”之具体操作方式为“标三准”以镕意,善“删敷”以裁辞,“镕裁”之目标在于“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4]1206。
《文心雕龙》搭建了“繁简”批评体系的基本框架,之后,唐代刘知几《史通》推崇《尚书》与《春秋》之“简”②,将“繁简”引入史书批评,从史书叙事与史书载事两个层面论述“繁简”③。史书叙事侧重于“叙”,即行文用笔方式,史书载事侧重于“事”,即内容组成要素。《叙事》篇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6]156刘知几于“繁简”之态度偏于一端,强调史书尚简。又言:“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6]158引用《春秋》《左传》等书来论证“省句”与“省字”的必要性。他在《烦省》篇从“载事”的角度强调衡量史书“繁简”的标准不在于篇幅多少,事件多少,而在于叙事时不能出现“事重”和“事阙”的弊病。他认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6]246“事有妄载”为“烦”,“言有阙书”为“省”。总之,史书叙事尚简的目标为“文约而事丰”。
刘知几在行文运笔方式层面继承刘勰的“繁简”批评框架④,对史书叙事尚简之“叙”的方式作了进一步说明。但与刘勰不同的是,刘知几认为史书以“载事”为主,因此行文运笔的针对对象为“言”与“事”,而刘勰认为是“言”与“意”,“意”包含情理。这一内容要素的区分大致代表了“叙事”与“抒情”“议论”文体的分途。
宋元明时期,文章学在文法论层面对“繁简”做出进一步拓展,吕祖谦、谢枋得等人提出行文有“省文法”,吕祖谦《古文关键》在评点东坡《晁错论》时,曾言:“须看省文法,前既说景帝时事了,到此轻举过去。”[7]33指当提及前文已经论述过的内容时,后文可用省文法略叙。谢枋得《崇古文诀》在评点柳子厚《与李睦州论服气书》、钱公辅《义田记》等文时,都曾提到“省文法”,使用语境和含义与吕祖谦相同。在时文相关理论著作中,魏天应《论学绳尺》在《诸前辈论行文法》中引冯厚斋之言曰:“小讲中且要斟酌详略,恐是实事,题便要入题,最忌前后重复,或前面已详,则入题处便得省文法,或未详,则入题处却不可略。”[8]74d对时文体式的繁简笔法做出了规定。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将“繁简”纳入篇法体系之中,强调:“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9]963可见,文章学已明确将“繁简”纳入文法创作体系之中,在古文和时文评点时都突出行文时繁简笔法的运用。
总之,《文心雕龙》从言与意的关系出发分析“繁简”,其“镕意裁辞”说和“繁缛”与“精约”的“体要”说奠定了“繁简”文法论和格调论的两大批评体系。唐代刘知几《史通》将“繁简”论引入史学理论中,从言与事的关系出发突出史书对裁“事”的重视,侧重于分析史书利用繁简笔法组织事件的方式。宋元明时期,文章学明确将“繁简”纳入文法创作体系之中,在古文篇法以及时文体式层面论述繁简笔法的运用情况。
与诗文和史学中的“繁简”理论相比,以金圣叹、脂砚斋、冯镇峦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家在继承刘勰、刘知几等人的基础上,又在文法层面上对形成小说繁简风格的种种笔法进行细化,提出“极省法”“极不省法”“加倍省”“加倍增”等各种文法,在程度上加深了“繁简”的创作指向,这种差异与小说本身的功能属性相关,罗烨《醉翁谈录》曾言:“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10]5指说话人为了迎合听众的趣味,讲到枯燥和冷淡处,简单地用三言二语轻轻带过,而在情节精彩和热闹处,对听众感兴趣的情节极力铺叙和敷演。小说出于娱人的目的,热闹处用墨如泼,冷淡处惜墨如金,这种观念影响到了小说文法思想。
二、明清小说的各种“繁简”技法论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继承史书“镕事裁辞”的理论,主要从字法和句法的形式层面以及人与事为主体的内容层面,分析作者如何利用“极省法”“极不省法”“避繁法”等与繁简有关的笔法构筑小说文本意义以及架构小说的叙事结构。
在形式层面,评点家指出作者善于利用字法和句法的变化以实现叙事的繁简合度。就字法而言,脂砚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行文原只在一二字,便有许多省力处。不得此窍者,便在窗下百般扭捏。”[11]153在具体行文过程中,作者大概使用以下几类字词进行叙事:一是运用含有重复性频度意义指向的时频副词省略叙事。芥子园刊本曾评价《水浒传》用字“尽详略伸缩错综之妙”[12]329,他认为作者为宋江作传时:“但有、无有、不、便留、终日、尽力、每每、只是、如常,皆着意写两个好字。”[12]329“每每”“如常”“终日”这类字词表示相同的事情多次发生,暗含出现频率两次及以上。脂砚斋在评批宝钗说自己得了“那种病”时认为:“‘那种病’。‘那’字与前二玉‘不知因何’二‘又’字,皆得天成地设之体;且省却多少闲文,所谓‘惜墨如金’是也。”[11]153可见,“每每”“如常”“又”这类时频副词表示动作、事件等变化是经常性和多次性的,用这类字词可以省略已经叙述过的情节,避免重复。
二是运用具有概括性意义指向的疑问代词以省略叙事。如《水浒传》第三十一回写武松从头备细地向宋江讲述两人从柴进府上分别后的经历,“至十字坡,怎生遇见张青、孙二娘;到孟州,怎地会施恩,怎地打了蒋门神,如何杀了张都监一十五口。”芥子园刊本眉批认为此段话中“怎生、怎地、如何,数落得妙,三两行却像有千百句言语在内。”[12]596因武松的经历在前文中已经铺叙而出,此时向别人讲述时,若再次细细描画,则难免累赘,因此用几个疑问代词以概括性地叙述,可以节省行文笔墨,又包含无数情事。之后,脂砚斋在《红楼梦》“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中认为作者不写元春晋封等热闹情事,只叙述宝玉担心秦钟生病的情节,因此对“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朋如何来庆贺”等事都不关心,对此,甲戌本脂砚斋评曰:“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宝玉一人,连用五‘如何’,隐过多少繁华势利等文。试思若不如此,必至种种写到,其死板拮据、琐碎杂乱,何可胜哉?故只借宝玉一人如此一写,省却多少闲文,却有无限烟波。”[11]270作者以宝玉作金针,连用五个“如何”便省略一番热闹琐碎的文字,在省却闲文的时候也留下无限烟波。
三是运用自主性动词以传达叙事和写人神理,评点家将之称为炼字之法。如《水浒传》第三回写“鲁智深在五台山寺中不觉搅了四五个月”。金圣叹认为:“省文也,却用一‘搅’字,逗出四五个月中情事。”[12]107作者只用一个动词便写出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情事。又如《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写“宝玉命把煎药的银盄子找了出来。”脂砚斋指出:“‘找’字神理,乃不常用之物也。”[11]611一“找”字写尽叙事情理。另外,作者也会运用表示情态的动词以写活人物。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评、改一体,金圣叹不仅作为鉴赏者,而且作为创作者参与其中,对比其与容与堂本的差异,可以考察作者的创作旨趣。如容与堂本第四十六回写石秀当着杨雄之面与潘巧云对峙:“石秀睁着眼来道:‘嫂嫂,你怎么说这般闲话,正要哥哥面前说个明白。’”“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诤,教你看个证见。’”而贯华堂本删改为:“石秀睁着眼道:‘嫂嫂,你怎么说?’”“石秀道:‘嫂嫂,嘻!’”金圣叹于此批曰:“上只四字,此只一字,而石秀一片精细,满面狠毒,都活画出来。俗本妄改许多闲话,失之万里。”[12]858对比可知,金圣叹删改后,只用一个字便活画出石秀精细、狠毒的性情,简洁又准确。
就句法而言,作者善于使用“缩句法”、“不完句法”等用笔策略在实现叙事内容空白的基础上增强画面感,富有传神之妙。《水浒传》第五回写几个老和尚正在吃粥,但因鲁智深来得声势,于是作者于“正在那里——”突然收住,金圣叹认为:“正在那里下,还有如何若何许多光景,却被鲁达忿忿出来,都吓住了。用笔至此,岂但文中有画,竟谓此四字虚歇处,突然有鲁达跳出可也。”[12]147作者使用缩句法可以增强叙事的画面感,让读者想见正是因为有人突然而出,才有此急缩句。历代评论家对《红楼梦》中的“缩句法”也多有赞赏,如第十六回写赵嬷嬷正在叙述接驾的声势,在“说起来……”处被凤姐“忙接道”而打断,脂砚斋甲戌本夹批曰:“又截得好。‘忙’字妙!上文‘说起来’必未完,粗心看去则说疑阙,殊不知正传神处。”[11]280此处截断不仅能避免繁复,还能给予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是文字传神之处。清代王雪香在《红楼梦总评》也赞叹道:“书中多有说话冲口而出,或几句说话止说一二句,或一句说话止说两三字,便咽住不说。其中或有忌讳,不忍出口;或有隐情,不便明说,故用缩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笔。”[13]46缩句法能原汁原味地还原叙事场景,不仅能更好地描画人物情态,还能增强叙事的动态画面感。
作者不仅善于利用“炼字法”“不完句法”之简实现辞约事丰的意蕴传达,还运用“重叠”之繁使得作品生色。贯华堂本第四十四回写石秀撞见潘巧云和裴如海调情时,金圣叹增添了五个“连忙”凸显裴如海的反应,“那贼秃连忙放茶”“那贼秃虚心冷气,连忙问道”“贼秃连忙道”“连忙出门去了”“那贼秃连忙走”,而容与堂本无这五个“连忙”⑤,金圣叹于此赞叹曰:“写贼秃正要迎奸卖俏,陡然看见石秀气色,便连忙放茶,连忙动问,连忙不敢,连忙出门,连忙走,更不应,真活现一个贼秃也。”[12]834金圣叹增添的这五个“连忙”显然更能活画出和尚的心虚和石秀凛然的胆色。
在内容层面,评点家们认为小说作者在创作时,面对纷纭复杂、头绪众多的人和事,会通过调整繁简的用笔策略来组织和结构文本。与戏曲理论中强调头绪忌繁不同,小说理论侧重于从文法层面分析作者如何利用繁简笔法组织以人、事为主体的繁杂头绪。
在组织结构文本时,作者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安排组织多个以人、事为主体的情节线索,评点家认为作者善于利用避实击虚之法使不同情节线索在小说人物的对话和耳目见闻中详略并出、次序井然。如《水浒传》第一百十二回写柴进向宋江备说卢俊义攻打宣州一事,对此袁无涯本眉批曰:“卢俊义事皆以言见,以虚为实,得省文法。”[12]1400作者并未花费大量笔墨对卢俊义破宣州的情节实写,而是通过他人之口进行转述,节省行文笔墨。之后,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又进一步指出:“《三国》一书,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画家之法,于山与树之近者,则浓之重之;于山与树之远者,则轻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遥,峰岚层叠,岂能于尺幅之中一一而详绘之乎?作文亦犹是已。如皇甫嵩破黄巾,只在朱隽一边打听得来;袁绍杀公孙瓒,只在曹操一边打听得来;赵云袭南郡,关、张袭两郡,只在周郎眼中、耳中得来;昭烈杀杨奉、韩暹,只在昭烈口中叙来;张飞夺古城在关公耳中听来;简雍投袁绍在昭烈口中说来。至若曹丕三路伐吴而皆败,一路用实写,两路用虚写;武侯退曹丕五路之兵,惟遣使入吴用实写,其四路皆虚写。诸如此类,又指不胜屈。只一句两句,正不知包却几许事情,省却几许笔墨。”[14]16毛氏父子将作画与作文相比,强调为了将不同情节线索交代清楚,避免重复,作者利用虚实结合的方式,以繁笔描写此处聚焦之文,借小说人物之眼、耳、口以简笔虚叙他处之文,在节省笔墨的同时,结构不同情节线索。
作者在布局小说结构、串联人物情节时,或以一人作线描写活画多人性情,或以一事作线穿插映带多处情节,即一笔作数笔之用。《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写戴宗在寻公孙胜时,遇见欲上梁山入伙的杨林,两人在同行的过程中,又以杨林引出邓飞和孟康两人,邓飞在叙述聚义经历时又引出裴宣,对此,金圣叹评曰:“先生一人,次生出二人。却因二人,又生出一人,真是行文省力法。”[12]819金氏认为因为作者收罗一百八人是大难事,因此便以戴宗寻找公孙胜作线,顺手串出四五人,行文笔墨较为简洁。脂砚斋在评点《红楼梦》时也强调其“一笔作数笔”的高超结构笔法,第七回写薛姨妈让周瑞给姐妹们送花,甲戌本脂砚斋眉批曰:“余问送花一回,薛姨妈云:‘宝丫头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则谓是宝钗正传,又主阿凤惜春一段,则又知是阿凤正传;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之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小说中一笔作两三笔者有之,一事启两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数之笔也。”[11]162作者仅以送花一事作线,便将宝钗之英爽,熙凤之不羁,颦儿之敏感活画而出,足见作者笔法的高超。
为了使上下结构匀称统一,繁简相宜,前文所省略的情节有时又会在下文中补出,即毛宗岗所说的“添丝补绵、移针匀绣”,他认为:“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14]16利用前后文的匀补,不仅能避免前文拖沓,还能使后事增加渲染。脂砚斋又进一步认为这种补叙方式体现了小说行文的“省中实”,《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一节中英莲和冯渊的悲欢从葫芦僧口中补叙,甲戌本脂砚斋眉批曰:“英、冯二人一段小悲欢幻景从葫芦僧口中补中,省却闲文之法也。”贾雨村听完之后,又以“梦幻情缘”“薄命儿女”对两人的悲欢幻景定性,对此甲戌本脂砚斋眉批曰:“使雨村一评,方补足上半回题目。所谓此书有繁处愈繁,省中愈省;又有不怕繁中繁,只要繁中虚;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实。此则省中实也。”[11]100作者并未花费大量笔墨对英莲和冯渊的情事进行正面详细地描写,只是借他人之口虚叙补出,是省笔,而贾雨村对此事的感慨评论又进一步直击主题,因此脂砚斋认为是“省中实”。
此外,作者在结构组织情节线索时,不仅会利用省笔结构头绪众多的线索,还会花费大量笔墨对结构小说和突出人物性情的关键性情节进行极力描写,金圣叹将其称为“大落墨法”[12]20,并且举出了以下几个例子进行详细说明:第一个是“吴用说三阮”,金圣叹认为加亮说阮一番文字具有曲折迎送之能,而之所以对其进行细细描写,是因为就《水浒传》的行文结构而言,“水浒之始也,始于石碣;水浒之终也,终于石碣。”[12]270石碣村阮氏三雄即为一百八人之入水浒之开始。第二个是“杨志北京斗武”,金圣叹认为:“梁中书之爱杨志,止为生辰纲伏线也,乃爱之而将以重大托之,定不得不先加意独提掇。”因此才有教场斗武一番花团锦簇的文字。第三个是“王婆说风情”,如果没有王婆在其中的说合,西门庆和潘金莲也就失去了连接的纽带。最后一个是“二打祝家庄”,这一处情节不仅是梁山大规模对外征战的开始,也是晁盖时代向宋江时代过渡的开始。可见,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极力渲染关键的情节使小说结构环环相扣,圆合统一。同时,作者怕文字过长,出现累赘,会利用“横云断山”等方法截断、岔开文字,以避繁章法。金圣叹仍以“二打祝家庄”等情节为例,他说:“有横云断山法。如两打祝家庄后,忽插出解珍、解宝争虎越狱事;又正打大名城时,忽插出截江鬼、油里鳅谋财倾命事等是也。只为文字太长了,便恐累坠,故从半腰间暂时闪出,以间隔之。”[12]20可见,出于繁简相宜的考虑,小说结构在连断中交错并出。
最后,出于因文生事的创作原则,为顺应情节发展的情理逻辑,作者会随地生波,运用繁笔对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进行敷衍和铺叙,并且花费大量笔墨蹴起波澜,使得小说叙事波折丛生。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曾对“极不省法”进行过解释,他认为:“有极不省法。如要写宋江犯罪,却先写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写阎婆惜和张三有事,却又先写宋江讨阎婆惜,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12]21此“极不省法”指作者运用繁笔对千曲百折的情节进行叙述,即“夫耐庵之繁笔累纸,千曲百折,而必使宋江成于杀婆惜者”[12]21。作者为了实现人物和情节逻辑持续推进,利用繁笔蹴起波澜,使得叙事“曲曲折折,层层次次”。
总之,当同时叙述不同的情节线索时,作者对此处聚焦之文详细敷演,利用人物之口、耳约略点缀他处之文;在面对头绪繁杂的人或事时,以一笔做数笔之用,串联映带多处情节线索以节省行文笔墨;为使上下文结构统一,繁简相宜,前文所省略的内容会在下文补出。此外,对突出人物性情的关键性情节,作者会利用繁笔敷演以使叙事曲折丛生,波澜并起。
三、“繁简”与古典小说文本创构之适度原理
经典性文学作品的形成需要作者之意、文本之言与文体在相互作用以及互相配合时达到恰到好处即“合度”的地步。具体而言,作者之意涉及情、理、事,文本之言涉及字、句,文体涉及诗歌、史传、论说、小说等,这些文学要素在创作时需要作者经过调和以达到恰到好处的“度”。李泽厚曾认为“度”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15]10又指出:“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出现了‘度’,即是‘立美’。”[15]11刘勰《文心雕龙·镕裁》篇指出:“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翫其采,不倍领袖。”[4]1205强调文章之镕裁如制衣,需要繁简合度。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又进一步引申,认为:“寻镕裁之义,取譬于范金、制服。范金有齐,齐失则器不精良;制服有制,制谬而衣难被御。洵令多寡得宜,修短合度,酌中以立体,循实以敷文,斯镕裁之要术也。”[16]114使范金、制服、作文精良的重要因素是在实践或创作时学会“合度”,掌握分寸,实现立美。
“繁简合度”之“度”的把握和体现涉及作者创作和读者鉴赏两个层面。作者在创作时,一方面要根据不同文体之体要特征进行剪裁,以实现繁简得体;另一方面要调和“言”与“意”之关系来实现繁简合度,此“意”指作者在构思时如何通过抒发情感、经营位置、组织事类、取舍材料、突出主题等要素实现纲举目张、弥纶有序。读者在鉴赏时,以“文约事丰”“言简意赅”和“辞敷意显”作为“繁简合度”的标准,此“意”与作者创作构思层面的“镕意裁辞”不同,而是体现在作品中的“事意”“理意”“情意”。
首先,批评家们强调“繁简”之度的把控要根据文体来进行镕裁,考虑不同文体的体要和体格,作者以一种最适度的方式,即最符合文体自身体要的方式来进行剪裁。《文镜秘府论·定位》篇指出:“文之大者,藉引而申之;(文体大者,须依其事理,引之使长,又申明之,便成繁富也。)文之小者,在限而合之。(文体小者,亦依事理,豫定其位,促合其理,使归约也。)申之则繁,合之则约。”[17]1489认为文体要与事理、言辞互相配合,根据文体之大小进行引申和归约,一旦破体,则文体自身的繁简之度便会被破坏。因此清代古文家严格遵守古文简洁的体格特征,严防小说气的侵入,李绂在《古文辞禁》中认为:“一禁用传奇小说。小说始于唐人,凿空撰为新奇可喜之事,描摹刻酷,鄙琐秽亵,无所不至,若《太平广记》是也。宋元而下,泛滥斯极。”[18]4009可见,与古文相比,小说长于“描摹刻酷”,并且体格琐碎。平步青《霞外攟屑》也指出:“古文写生逼肖处,最易涉小说家数,宜深避之。”[19]559强调古文描写刻画生动处容易流于小说家路数。
其次,文本中的“言”与“意”、“言”与“事”在创作活动中要不断地相互协调以达到恰到好处的地步。刘勰在《文心雕龙·镕裁》篇中强调“镕意裁辞”,开篇即云:“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镕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4]1177刘勰在这段话中透露两个信息,一是他认为“意”包含“情理”;二是他认为繁简失度的表现是“意或偏长”、“辞或繁杂”,因此通过“镕裁”,实现“隐括情理,矫揉文采”,找到令“言”与“意”相互协调之“度”,即“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到了唐代,刘知几《史通·烦省》篇则从言与事的关系出发,扩大了作者之“意”的范围,认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6]246强调史传文要注重镕事裁辞,使“言”与“事”经过调和以合度。具体而言,在史传文书写中,方苞《与孙以宁书》指出:“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20]136方苞认为叙事“详略之权度”的掌握是要根据传主的规模来决定,不能事事皆载。刘熙载《艺概·文概》也言:“传中叙事,或叙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叙其无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与时位,而称量以出之。”[21]218强调传记叙事需要根据人之志行与时位,称量而作。
中国古代小说“繁简”理论继承史传文镕事裁辞的基本理念,强调作者在立意时注重分析作者如何合理地经营位置,如何利用恰当的言辞处理以人和事为中心的众多情节线索,如何利用繁简笔法变换描摹人物性情。小说批评家认为作者对叙事繁简之“度”的考量和把握主要根据人物的宾主地位、事件的主次轻重差别、故事的主旨内涵等因素来调控。小说繁简之“度”是要从正文与闲文、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关键性情节与次要情节、文势的缓急快慢、盛衰主题之演变以及描摹人物性情之隐与显等相反相成的因素之间的比较中来把控的。
不同作者在创作时对繁简之“度”的感知和把控是不同的,小说创作是一个需要各方面文学因素都恰到好处地相互协调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主体性和不可重复的单一性,因此,不同作者对繁简之“度”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规定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文学创作中的繁简之“度”不能被规范化和形式化,则文学之经典的评判和创作之传承也无以为继,因此,不同批评家致力于总结和归纳各种形成小说繁简的技法。
读者如何感知这种“度”呢?换言之,“繁简合度”之“度”的标准是什么?叙事多、篇幅较长的小说一定为“繁”吗?叙事少、篇幅较短的小说一定为“简”吗?晋张辅曾云:“(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一也。”[22]2063a刘知几《史通·烦省》篇认为张辅以篇幅内容多少来评判史书烦省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史书“事有妄载”才能称为“烦”,“言有阙书”才能称为“省”,史书应以“文约事丰”为工。欧阳修《进新唐书表》曾认为《新唐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23]6472顾炎武《日知录》引宋代刘器之言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24]1100《新唐书》言辞太简略,所叙之事有缺漏,因此为人诟病。具体到小说评点中,评点家赞叹作者在叙事时善于以简略之语描绘一个可以自由联想并且意蕴丰富的开放性空间。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认为:“张二官顶补西门千户之缺,而伯爵走动说娶娇儿,俨然又一西门,其受报亦必有不可尽言者。则其不着笔墨处,又有无限烟波,直欲又藏一部大书于无笔处也。此所谓笔不到而意到者。”[25]1498在西门庆暴亡后,作者以简略之笔描写张二官重复西门庆卖官鬻爵、贪财好色、聚拢帮闲的种种行径,作者虽未细细描写张二官之后的人生轨迹,但读者可以通过西门庆的结局透视张二官的人生走向。之后,脂砚斋又以“不写之写”评述《红楼梦》的留白技巧,第三十九回写一小厮向平儿告假,平儿埋怨道:“前儿住儿去了,二爷偏生叫他,叫不着,我应起来了,还说我作了情。你今儿又来了。”脂砚斋认为作者在这一处以一语闲言便补写出贾琏处天天闹热、迎来送往的种种情事,事溢于文外,读者通过作者简略的描写可以透视如冰山一角下蕴含深广的开放性空间世界。
此外,小说理论也指出作者善于在无字句处实现叙事和写人的含蓄性美感蕴含。《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写李逵骗了宋江的银子去赌博,准备赢钱请宋江吃酒,却输个精光,大闹赌房,宋江帮忙解决后,又请李逵和戴宗吃酒,李逵说道:“酒把大碗来筛,不耐烦小盏价吃。”金圣叹赞叹道:“李逵传妙处,都在无字句处,要细玩。”[12]702他指出的“无字句”即李逵一方面将大闹赌房的事情完全抛开,坐下高兴吃酒;另一方面反客为主,毫无常人对请客主人的殷勤奉承。这些描写都于含蓄处见出李逵性格的豪爽和朴实。脂砚斋也称赞《红楼梦》叙事的含蓄隽永,第五十七回写紫鹃三试玉,由此引发宝玉呆病,脂砚斋在回末评曰:“写宝玉、黛玉呼吸相关,不在字里行间,全从无字句处,运鬼斧神工之笔,摄魄追魂。”[11]626强调《红楼梦》于无字句处描绘出宝黛彼此牵挂的深情厚意,是追魂摄魄之笔。
另一方面,小说叙事的“繁处愈繁”区别于简单的“面面俱到”,作者能于常人之省处施以繁笔,能于常人之繁处用以简笔,在行文急忙处的敷演与铺叙不仅可以使情节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还能进一步影响读者的审美体验,增强审美效果。《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写武松脱过杀威棒后,众囚徒、武松以及读者都在推测后面可能会有的更重的刑罚,但作者却细细描画管营如何逐日管待,金圣叹也指出作者对武松“洗浴乘凉,如此等事,无不细细开列,色色描画”[12]525,但这种铺叙反而使叙事的惊险效果得到进一步的增强,金圣叹认为:“管营看顾后,读者便急欲得知其故久矣。忽然接入连日看待之厚一篇,烦文琐景,虽一往如在山阴道中,耳目应接不暇,然心头已极闷闷。”[12]533一系列“烦文琐景”的铺叙使读者心头闷闷,更加疑惑,急欲知下文。“繁处愈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辞敷而意显”的审美效果。
可见,讨论文章、小说、史书之“繁简”,最重要的是辨析清楚“言”与“意”的关系,此“意”即读者感知到的体现在作品中的“情意”、“事意”与“理意”,与“镕意裁辞”之“意”不同,“镕意”之“意”指在创作构思阶段作者组织作品之“意”。“辞约意丰”和“辞敷意显”当为“繁简合度”之标准。
总之,对“繁简”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不仅可以进一步从内部把握小说文本创构中的原理和逻辑,还可以从外部探讨小说与其他文体互动中显示出的文体差异和特性,对探讨小说文本创作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注:
①刘勰在《征圣》篇说道:“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以“《春秋》一字以褒贬”的例子证明“简言以达旨”,以“《儒行》缛说以繁辞”的例子证明“博文以该情”。刘勰认为在创作时若能做到“征圣”与“宗经”,那么文章会具有“体约而不芜”的效果。
②《史通·叙事》言:“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
③浦起龙《史通通释》:“此篇用意,与《叙事》三章大相迳庭,非前后违反也。彼以用笔言,此以载事言,会向此中参悟,乃可与言事增文简之法。”
④ 关于刘勰和刘知几的继承关系,刘知几《史通·自叙》篇以《法言》《文心》等书自况:“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
⑤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那和尚放下茶盏”“那和尚虚心冷气动问道”“裴如海道”“相别出门去了”“那和尚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