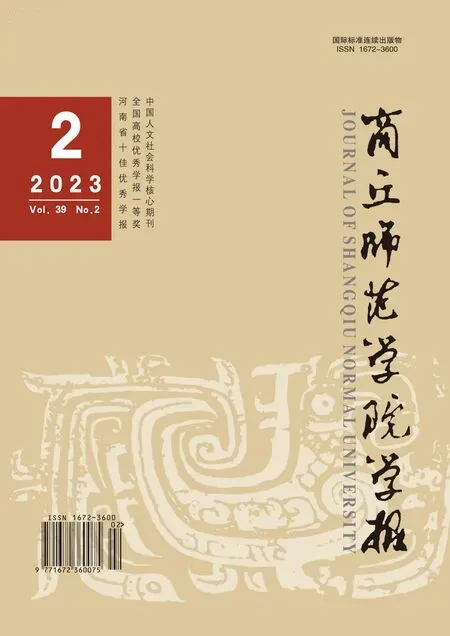2010年以来国内“亲亲相隐”制度研究述评
2023-02-22郭玲
郭 玲
(青海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人事处,青海 西宁 810016)
“亲亲相隐”,亦称“同居相为隐”或“亲属相为容隐”,简称容隐,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互相庇护除谋反、谋叛、大逆以外的犯罪行为。“亲亲相隐”由伦理观念上升为法律制度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尽管学界对“亲亲相隐”制度始于何时仍有分歧,但丝毫不影响其在史学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并且在哲学界、法学界也引起了较大的研究热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2002年以来,哲学界就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学术论争,内容涉及“亲亲相隐”观念的内涵、性质、价值合理性及现实意义等。这场论争的大部分成果收录在《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1]《儒家伦理新批判》[2]《〈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3]3本论文集中。鉴于已有学者对2010年以前“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成果进行过总结,本文着重对2010年以来的研究状况展开梳理和展望,以期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些许启发。
近10余年来,“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依然保持兴盛态势、热度不减,可谓是硕果累累。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其间出版专著1部,发表与“亲亲相隐”主题密切相关的论文近600篇。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4],就笔者目力所及,是国内首部以“亲亲相隐”为主题的专著。作者从经学、制度、生活三个维度对“父子相隐”展开探讨,视角独特,立论有据。彭婷的《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辨正》[5],以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为出发点,对“亲亲相隐”伦理文化的内涵、伦理特质与价值意义等内容进行充分挖掘,进而揭示了儒家伦理文化的历史合理性。连宏《汉唐刑罚比较研究》[6]、王娟《缘坐研究》[7]等博士学位论文中均涉及亲亲相隐相关内容,但基本都是一笔带过,未做深入探讨。概言之,现阶段史学界还没有以“亲亲相隐”制度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问世。与博士学位论文形成鲜明对比,研究“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的硕士论文数量较多,达150余篇。研究大多涉及“亲亲相隐”制度的理论基础、发展沿革、存续原因、价值分析、中外“亲亲相隐”制度比较的研究及对当代刑事法律的启示等方面。尽管硕士学位论文数量较多,但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关于“亲亲相隐”制度在古代社会中是如何运行的,对司法实践案例的分析几乎处于空白。限于篇幅,笔者主要就期刊论文部分择要述评。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渊源与流变
学界普遍认为,“亲亲相隐”制度始于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如张国钧《〈春秋〉怀疑大义灭亲而发育亲属容隐——从〈春秋〉记诛庆父及其微言大义切入》认为,《春秋》中记载的鲁国诛庆父案例,对大义灭亲持审慎、怀疑、戒惧等复杂态度,孕育着亲属容隐制度的萌芽,进而促成了汉宣帝四年明令亲属容隐成为正式制度[8]。但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韩树峰《汉魏无“亲亲相隐”之制论》以孔子“父子相隐”的双向容隐、权利义务两重属性为出发点,推测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政权从未制定过“亲亲相隐”的法律条文,唐代“亲亲相隐”制度来自北朝而不是南朝[9]。魏道明早期认为,“亲亲相隐”制度至晚始于秦律,至汉宣帝时发生重大变化,至唐代成熟、定型[10]。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流变》一文中的见解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他指出,由于学界将“干名犯义”与容隐混同在一起,在追溯容隐制度的源流时,往往以不得告父母的法条作为容隐制度开始的标志。他推论,容隐制度可能产生于西汉末年或东汉时期,最晚不超过魏晋[11]。
巫洪才《论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12]、黄英《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溯源及发展历程述论》[13]、梁霞《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嬗变及相关问题思考》[14]等文章均详细梳理了“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进程。综合学者的论述,尽管大家对“亲亲相隐”制度历史发展的表述略有差异,但大体上已达成共识:先秦及秦代是“亲亲相隐”思想先导与萌芽时期;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是正式确立与发展时期;隋唐至明清是完善与成熟时期;清末至民国是渐衰时期。
纵观“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史,我们能够看出“亲亲相隐”制度在历朝历代均有所体现,容隐的亲属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内涵与价值
现阶段,学界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伦理观念、概念已无异议。尽管魏道明早期认为“容隐”不能等同于“亲亲相隐”[10]。但其在随后的《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流变》一文中指出,容隐亦称“亲亲相隐”,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相互庇护犯罪行为[11]。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文化内涵
尽管哲学界就“亲亲相隐”的学术论争已有3本论文集问世,但“亲亲相隐”制度的文化内涵或者是其背后蕴涵的伦理观念的德性内涵,一直是哲学界争议的焦点,依然没有鸣金收兵的趋势。近10余年来,哲学界有关“亲亲相隐”问题的探讨仍然聚焦在“隐”“直”等字的理解、“亲亲相隐”相关文本的解读及儒家如何对待血缘亲情和仁义观念的探究上,以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亲亲相隐”的本质。
梁涛《“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15]《“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互相纠正错误吗?——〈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之检讨》[16]《超越立场,回归学理——再谈“亲亲相隐”及相关问题》[17]《〈论语〉“亲亲相隐”章新释》[18]等一系列文章从文字训诂和义理角度,对“直”“隐”等字词在具体文本中的确切含义详加辨析。他认为,“直在其中矣”的“直”,是真实、率直之直,而不是公正、正直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字只能做隐匿讲,而不能训为纠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指面对亲人的过错,子女或父母本能、自然的反应往往是为其隐匿,而不是去控告、揭发。
梁涛的这一观点使“亲亲相隐”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热点,引发了学术界新一轮的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一是廖名春《〈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从文献和义理两方面,论证“隐”是“檃”的假借字,解释为纠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读作“父为子櫽,子为父櫽”,训为“父亲要替儿子矫正错误,儿子也要替父亲矫正错误”[19]。杜纯梓对此持相同观点,他在《亲亲相互规正是儒家伦理的要则炯戒——“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考辩》一文中指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应读为“父为子檃,子为父檃”,“亲亲相隐”实际上是亲亲相互规正[20]。二是张志强、郭齐勇《也谈“亲亲相隐”与“□而任”——与梁涛先生商榷》,文章认为,“直在其中矣”之“直”,并非只是单纯情感流露的“率直”“率真”,而是针对不同场合、不同事件鲜明地区分人情和理性,是先秦儒家灵活处理亲情与正义等问题的直观表达[21]。王兴国也认为,“直”可以理解为正直之道,“父子相隐”的真义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规劝与帮助,从而避免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告发、指证[22]。
王晨光和黄启祥两位学者的观点为我们理解“亲亲相隐”提供了新的思路。王晨光《楚国北扩地缘政制问题与“亲亲相隐”公案新解》从论证哀公六年孔子与叶公对话时的地点、复原叶公驻扎时的地缘形势、分析楚国北扩的军事策略着手,揭示“父子”相隐,是讲族内对族外而隐,是尽力将法律制裁所带来的族群失序降到最低[23]。黄启祥《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认为,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非相互隐恶,而是指正义的家庭属性和主动的道义担当,旨在提示一条破解“孝(慈)义两难”问题的德性之路[24]。
翟学伟则是第一位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亲亲相隐”问题展开讨论的,他的《“亲亲相隐”的再认识——关系向度理论的解释》一文,借助关系向度理论,指出“亲亲相隐”背后所具有的文化预设,是“关系”先于“个人”的假定。儒家所提倡的五伦及其价值则是从其中的“固定关系”出发,向“约定关系”与“友爱关系”延展的,难以达至“松散关系”[25]。文章既不涉及作者的价值判断,亦不发表对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的看法,而是单纯探究孔子这样说的缘由,立意新颖,观点鲜明。
以上可谓是各学者就彼此对“直”“隐”“父子相隐”文化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展开的一场辩论。除此之外,程能的《论“亲亲相隐”之辨及“隐”的三种层次》[26]、宁全红《“亲亲相隐”的语境化解读》[27]、孙向晨《亲亲相隐之“隐”的机制及其本体论承诺——兼与王庆节教授商榷》[28]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解读“直”“隐”之内涵,进而探讨“亲亲互隐”的本质。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定性
李继刚、张益刚在《“亲亲相隐”的人性魅力解读》中指出,“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仁爱”的人性自然亲情,是“孝道”在法律制度中的具体表现,对于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等有其独特的作用[29]。魏道明《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价值与正当性问题》,以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为切入点,认为学界所谓容隐制度维护尊卑伦常、滋生腐败现象等观点,均属不实之词。容隐无论作为伦理学说还是法律制度,都充分考虑到了权利平等的因素。他进一步强调,容隐权是能够对抗和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权利[30]。他的这一观点与俞荣根的论点不谋而合。俞荣根在《私权抗御公权——“亲亲相隐”新论》一文中,从家庭权利的视角出发,揭示“亲亲相隐”的本质是家庭权,蕴涵着家庭私权利抗御国家公权力的功能和价值[31]。陈慧萍着重探讨唐代的“亲亲相隐”制度,她指出唐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更加强调伦理纲常,重“别异”“尚敬”,单纯强调卑幼对尊长的容隐义务,着重保护的是秩序而非亲情[32]。
与上述学者就“亲亲相隐”制度本身的价值、正当性等问题展开探讨不同,哲学界将话题延伸到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整体评价层面。刘水静在《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33]《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34]等文章中强调,“亲亲相隐”是一种合于人道主义原则的德性之善,是合于人之为人的道德良心。刘克《仁义直道与情理圆融:对“亲亲相隐”命题的新探析——从出土文物看早期儒家亲情本位的伦理智慧和价值旨趣》以亲亲相隐题材汉画为研究素材,揭示亲亲相隐是对血缘亲情的维护,对人性的尊重,亲亲相隐本身并不具备生发司法腐败的基因[35]。唐根希《“亲亲相隐”:正义还是无限正义?》的论点较耐人寻味,他认为“亲亲相隐”不是美德或腐败的问题,而是正义或无限正义的问题,“亲亲相隐”符合正义的诉求,是正义赋予的正当权利[36]。
笔者以为,韩东屏《走出僵局:亲亲相隐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37]《亲亲相隐不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吗?——答刘清平教授》[38]2篇文章,对亲亲相隐行为的价值定性比较中肯:亲亲相隐既不属于否定派所定性的恶行,也不属于肯定派所定性的善行,而是属于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但是刘清平却不认同他的这一观点。他在《再谈“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与韩东屏教授商榷》中强调,“亲亲相隐”属于坑害人的不当恶行,包含着“帮助亲人对抗社会公正”的不当因素,是现代社会某些腐败现象的源头[39]。
综上所述,现阶段学界就“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仍然未能达成共识,亦或由于各自的切入点和研究旨趣的不同,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无法达成共识。
三、司法案件探析
现阶段,有关“亲亲相隐”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司法实践的研究只有少数几位学者涉及。魏道明《清代对容隐行为的司法处置》,通过梳理、分析42 例清代容隐案件,推论容隐权只是法条层面上的虚拟权利,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40]。对此,谢红星持相似观点,他在《“亲属容隐”的制度张力与适用困境——基于文本和实证的考察》中指出,尽管表面上“亲属容隐”的立法是完整的、自足的,形成了一种具体、有配套、可操作的制度。但是,将“亲属容隐”置于传统法体系及传统司法的实际过程中,其与他项制度之间的张力、具体适用中的脱节昭然可见[41]。简单来说,谢红星亦认为容隐的法律文本与司法实践是脱节的。王东平的《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案审判中的“亲亲相隐”》,聚焦“亲亲相隐”原则在天山南路地区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指出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法律制度在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42]。
四、“亲亲相隐”制度的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对构建当代刑事法律的启示层面。概观现有研究,学者们大多从维护亲情伦理、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认为我国刑事法律应当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完善亲属包庇与拒绝作证的相关立法。
谢佑平、陈莹在《“亲亲相隐”与亲属间窝藏、包庇类犯罪的豁免》中直言,我国现行刑法全面舍弃了“亲亲相隐”制度,有违人之常情,应当在立法中构建出现代“亲亲相隐”制度,寻求法律和亲情的平衡[43]。叶萍、彭志刚、张峰认为,我国可通过确立亲属免证权规定来实现“亲亲相隐”原则的活化[44]。梅象华《刑法中“亲亲相隐”之国家本位观——以刑法不得已原则为视角》一文认为,“亲亲相隐”原则能否在现当代刑事法上得以确立,实质是国家本位观与个人本位观博弈的体现[45]。雍自元、廉彪《亲亲相隐回归刑事法律的思考》,明确给出“亲亲相隐”回归刑法的设想:在《刑事诉讼法》中赋予亲属拒绝协助抓捕权和拒绝作证权;在《刑法》中给予亲亲相隐定罪但从宽处罚[46]。尚海明以多个包庇窝藏案件司法裁判文书为素材,指出在亲属间的包庇窝藏案件审理中,法官对亲属关系因素的考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主张在立法中重新吸纳亲亲相隐原则[47]。
上述学者的见解均有其合理性,李拥军和李俊两位学者以“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关系为切入点,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更具可操作性的重构“亲亲相隐”制度的途径。李拥军认为,亲属豁免权立法可以尝试“先外围、再中心”的路线:先在民事诉讼法中作亲属作证豁免权的尝试,待成熟后,在刑事诉讼领域完全推开[48]。李俊则强调,一般犯罪维护“亲亲相隐”,恶性犯罪提倡“大义灭亲”[49]。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朱振《作为方法的法律传统——以“亲亲相隐”的历史命运为例》一文的论点令我们耳目一新。他强调,“亲亲”是对人类情感的正面肯定,容隐制并未消退,而是获得了新的制度表达并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容隐制的近代化是自身作为高次元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50]
此外,刘道朋《“亲亲相隐”之现代刑事法律人文价值分析》[51]、彭凤莲《亲亲相隐刑事政策思想法律化的现代思考》[52]、刘凡镇《亲亲相隐制度及其现代法律价值浅析》[53]、王剑《“亲亲相隐”制度在法治中国构建中的回归与适用》[54]、陆建红与杨华《现代法治条件下“亲亲相隐”制度之构建——从历史、比较研究和现实思考出发》[55]、张蓓洁《“亲亲相隐”的时代价值及其刑事法适用重构》[56]等一系列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证“亲亲相隐”制度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至关重要,并对其适用范围、适用类型、适用形式以及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等提出具体设想。
五、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相关研究或侧重相关字词的训诂,或侧重基础史料的解读,或侧重价值性质的辨析,或侧重制度设计的探讨,各具特色。总体来看,2010年以来,“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1.研究主体。一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主要集中在法学界和哲学界,虽说“亲亲相隐”制度在学术各界都引起了较大的研究热潮,但史学界发表的成果相对较少:笔者以“‘亲亲相隐’或含‘容隐’”为主题、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在知网上进行检索,共检索出400余篇期刊论文,其中:法学250余篇,哲学、伦理学50余篇,史学仅10余篇;将来源类别替换为“核心期刊”“CSSCI”重新检索,共检索出100余篇期刊论文,其中:法学60余篇,哲学、伦理学20余篇,史学仅7篇。二是研究人员层次普遍较高。范忠信、梁涛、张国钧、魏道明等国内知名学者就“亲亲相隐”均发表过数篇文章,高层次的研究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问世提供了可能。
2.研究视角。近年来,研究视角、资料的多元为“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切入点。如刘克以出土的汉代文物——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画像和铭文——作为研究素材[35],跳出了以往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限;王晨光从楚国疆域北扩及地方管理等历史背景着手,重新揭示“亲亲相隐”辩论的症结[23];朱振从作为方法的法律传统角度出发,考察“亲亲相隐”的历史命运[50];翟学伟将“亲亲相隐”的论战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借助关系向度理论赋予“亲亲相隐”全新的内涵[25]。
3.研究内容。史学界以考析“亲亲相隐”制度的思想流变及其法律制度化过程为主,多为历史性及整体性的宏观研究,研究的侧重点无外乎概念、流变及价值内涵等。“亲亲相隐”制度的断代研究、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等较少涉及。哲学界对“亲亲相隐”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直”“隐”等字的辨析,“父子相隐”文本的解读及“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上,多为商榷或回应质疑性质的文章。法学界主要围绕“亲亲相隐”制度对当代刑事法律的启示展开讨论,这一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比较研究相对薄弱。概观而论,不管哪一学界,在研究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创新不足。
近两年发表的论文数量表明,“亲亲相隐”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是否意味着这一话题的讨论将告一段落了呢?笔者以为,“亲亲相隐”的研究尚有探讨的空间。第一,加强“亲亲相隐”制度的断代史、区域史研究。“亲亲相隐”制度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受到同一历史时期、区域的思想观念、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进而具有该时期、区域的个性特征和运作实态。现阶段,除少数学者涉足唐代、清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外,大多数研究成果以通代为主。因此,从政治、经济体制等角度对某一朝代、区域的“亲亲相隐”制度展开探究是很有必要的。第二,强化“亲亲相隐”与其他制度的比较研究。笔者以为,学界之所以对“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内涵、价值定性等内容未能达成共识,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学者将“亲亲相隐”与“干名犯义”“大义灭亲”“亲告罪”等制度相混淆。所以,比较研究或许是将“亲亲相隐”研究推向更深入的途径。第三,致力“亲亲相隐”制度的司法案例研究。通过个案、类案的梳理,以案件数目、比例、性质、判决结果等为标准,一方面试图说明司法与立法在怎样程度上的契合或背离,另一方面通过探寻“亲亲相隐”案件的规律,以补充或者纠正一些不完整甚至有些偏差的观点。第四,深入挖掘新史料。目前,尽管已有学者尝试使用新资料探析“亲亲相隐”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界主要还是依赖传统文献对其展开辨论。鉴于此,今后应进一步挖掘民间文书、家规家训、碑刻、壁画等新材料,规避同质化倾向,力争使“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