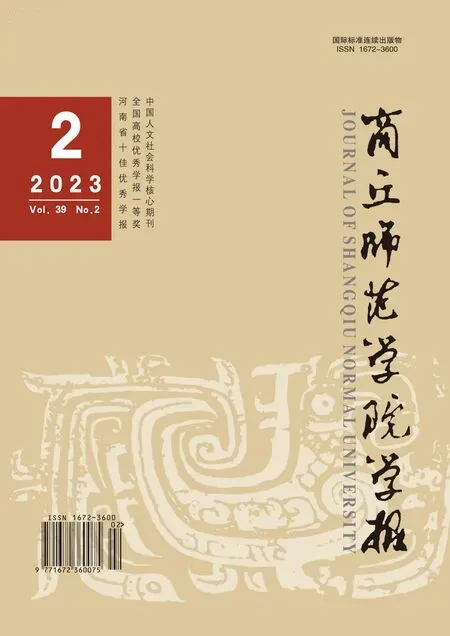突破成规一路行
——莫言小说“莫言式”言说分析
2023-02-22严运桂王甜
严运桂 王甜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莫言以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持久的探索热情等,成就了他的文学世界,并摘下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
从莫言1981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到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时间跨度40年,其文学创作取得了辉煌成就,诸如《民间音乐》《售棉大路》《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红高粱家族》《红蝗》《天堂蒜苔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晚熟的人》等多部小说,可以说部部都有惊异之处。莫言总是带给读者和评论界不同的阅读冲击。作者自己曾说,总有不同的人将他放进贴有不同标签的袋子(1)参见莫言《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如:“魔幻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寻根文学”“复调小说”“狂欢化”“生殖崇拜”“大地悲歌”“民间回归”“回忆往事”,等等。的确,莫言的小说荒诞与现实交融,故事深藏隐喻义,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定向乡土,纵情恣肆,喧闹跌荡,悲天悯人,等等。我们在他的小说中读到了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也读到了鲁迅、孙犁、沈从文、王蒙和余华等。莫言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故事荒唐离奇深含寓意。莫言荒诞不拘,道德伦理与既成体制被他用文字一一瓦解。莫言挑战传统,突破成规,大俗中蕴含大雅。莫言的小说,魔幻又现实,西倾又传统,开放又保守,繁复的结构里讲述的却是最简单本真的生命至上的人生哲理。在他的笔下,故事不只是故事,传奇不只是传奇,历史不只是历史。因此,若用比较简洁明确的概念概括评价莫言的小说特征或风格,的确有些困难,于是笔者只得把这种特属莫言的文学现象与特质,暂且命为“莫言式”言说(2)“莫言式”言说由笔者于2014年指导学生李汶檩毕业论文时提出,本论文当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毕业论文。。本文主要从言形方式与言说内容来阐述莫言的“莫言式”言说。
一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将人类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他认为,语言是从言语中抽象归纳出来的一套符号系统和一套惯用规则,而言语则是人们对语言规划的实践。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自觉遵守这套规则,因为它是社会的,是约定俗成的,同时也是个人的,只要在对方能够意会的前提下沿着语言的大框架去自由发挥,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个性表达。文学语言也是如此,作家借用自己那套独特的用词习惯和语言风格将自己超敏感觉和独特感受生动准确地表达出来。同样是写小说讲故事,莫言有别于众多作家的单纯特点,他的言语方式变化多姿,不拘一格。
莫言小说创作跨度40年,学界常将其获诺奖前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综观他的文学文本,笔者也认同这一分法,并将“诺奖”获后的创作续作第四个阶段。根据他小说的每个阶段的创作特点,可以分别命名:文学天赋初显阶段(1981—1984年)、文学创作“爆炸”阶段(1985—1999年)、文学成果辉煌阶段(2000—2012年)、文学回味沉静阶段(2013年至今)。这四个阶段,莫言不沿袭他人,不重复自己,每段都有独特的突破性精彩。
第一个阶段,是莫言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以短篇小说为主,有《春夜雨霏霏》《丑兵》《为了孩子》《售棉大路》《民间音乐》等作品。大凡初入文坛者,都会有模仿学习的痕迹,莫言也不例外。他身在军旅之中,心系小说创作,当时他接受较多的且能契合他写作因素的,是我国当代的乡土小说,尤其是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小说。其语言风格清新婉约、行文简洁,率直中包含含蓄,色彩明丽,笔触细腻,这些在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都有体现,如在描写景物时大都选用色彩明丽类的词语来描述,如雪白槐花、银灰色的雨珠、墨绿的河水等。在字里行间抒发的是一种细腻温婉的情绪,不论是描绘世事如流水而逝的淡淡忧伤,还是描述春闺少妇内心思君而来的隐隐骚动,莫言都尽力在描述过程中有所克制和遮掩,含蓄中带着内敛,读来尽是淡淡的情愫,不那么直接坦然,也不那么激烈地彰显欲念。叙述性语言也有着一股浓浓的民间乡土气息,平淡含蓄,做到了“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浅显里寓深意,质朴中兼优美。作者以抒情散文式语言,情节如散珠碎玉般淡雅精致,塑造着一个个富有抒情意味的人物形象,描绘着一幅幅云淡风轻的自然图景,营造出朦胧空灵的活泼意境。这一阶段的创作虽然被称为模仿经典阶段,但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和文字驾驭能力已不容小觑,故而他在发表《民间音乐》后,被著名作家徐怀中看中,被破格给予了参加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入学考试的机会。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新千年左右,以《透明的红萝卜》《酒国》《红高粱》《丰乳肥臀》《天堂蒜苔之歌》等为代表,这阶段可称之为莫言创作的“爆炸”阶段。《爆炸》是1992年莫言的第一部英译本中短篇小说集,“爆炸”一词含义与莫言这一阶段的言语特点颇为吻合,感性突兀、汪洋恣肆,铺排张扬,酣畅淋漓。与前一阶段相比,莫言的言语方式判若两人。有学者认为,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专业学习提供了接触各种中外文学资源的机会,在借鉴模仿的同时缺乏系统认知,杂乱无章又饥不择食,这些都决定了莫言的语言风格由纯净到驳杂的转变。”[1]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得益于他的天赋、才华和叛逆的个性品质。他竟然会在研讨会上批评当时文坛翘楚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说是从中闻到了“小报油墨芳香”[2],于是他就写出了有别于“小报油墨芳香”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诸如《红高粱家族》《红蝗》《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都带有浓重的狂欢色彩,充盈着酒、性、腥、骚、腐等杂味。
这一阶段的言语“爆炸”性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物语言粗俗不雅,“狗日的”“他妈的”等生活中骂人的话充斥文本。二是一改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等单视角叙事,叙事角度多元灵活,文本频繁切换“你”“我”“他”的视角。就拿《丰乳肥臀》来说,小说的前十章,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从第十一章开始,一会儿是“我”上官金童的视角,一会儿是“他”无所不知的视角,偶尔还有让人不可直视的“你”的视角。甚至有时候一段话里,这三种视角转来转去:“那天,与汪银枝的小红脸相遇。她用最精美的食物喂养他。喂得他膘肥体壮。我应该摘下铁手套扔给他。我没有铁手套可摘也应攥拳头呀。可是他满脸都是笑容,并且向我伸出了友好的手。你好,他说。你好,我说。接下来我竟然握住了他的手。一个戴着绿帽子的丈夫握住了给自己戴上绿帽子的手。互致问候,表示感谢。仿佛都占了天大的便宜。你这个孱头!他痛骂着自己,在霏霏细雨中。下次碰到他,决不许这样温良恭俭让,应该对准他的脸猛揍一拳,打得他眼冒金花,鼻子嘴里都往外喷血。”[3]523这种多元的视角,有时让人真切,有时让人洞透,有时让人直面,给人新颖陌生的阅读感受。三是叙事写景大肆铺垫,有的甚至惨不忍睹,可作者将它写成了景观,如乌鸦争食人尸的场面:“马车周围的草地上,乌鸦们抻着脖子吞咽着。有两只乌鸦扯着一截光溜溜的东西,像拔河一样……一只狗斜刺里扑上来,抢走了肠子,乌鸦不肯松口,在草地上打滚。”[3]61四是词语随性搭配,不讲语法,如“这封信写得七嘴八舌,交头接耳,但基本上杂乱成章,原因自然还在酒上”[4]295。这种语言有些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灵感爆发的高潮之中夹杂着一些杂质、一些混淆视听的声音。五是言说无情感倾向,常让读者失去价值方向。“作者都没有明确的道德偏向,只是通过血腥和变态的细节写出他们对各自施暴对象的施暴过程。”[5]56莫言小说对“积极意义”的颠覆,让人陷入茫然。莫言的这些言语特点,在20世纪末的小说世界,几乎都是“革命”性的,颇具“爆炸”效果,这也是莫言本人的创作追求决定的:“我觉得一个作家肯定要在创作过程当中追求变化,每一个作家如果他认为可以用过去的语言、过去的风格来写新的故事那是没有出息的……应该有这种求变的心,是一个作家还有可能进步的根本起点。”[6]也有学者称他“是那种在深度挑战、颠覆的过程中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达成文学原创性的作家,而不是那种追求适度、精致和完美的作家”[7]。
第三阶段,从新千年到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为代表,这阶段可称之为莫言文学的辉煌阶段。相比较于第二阶段的小说创作,其小说注重回归民间元素。一方面他的语言呈惯性的狂欢化,看看《四十一炮》中的这段话:“这个世界上,像您这样爱肉、懂肉、喜欢肉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啊,罗小通。亲爱的罗小通,您是爱肉的人,也是我们肉的爱人。我们热爱你,你来吃我们吧。我们被你吃了,就像一个女人,被一个她深爱着的男人娶去做了新娘。来吧,小通,我们的郎君,你还犹豫什么?你还担心什么?快动手吧,快动手啊,撕开我们吧,咬碎我们吧,把我们送入你的肚肠,你不知道,天下的肉都在盼望着你啊,天下的肉在心仪着你啊,你是天下肉的爱人啊,你怎么还不来?”[8]218小说中近乎以肉自述,戏谑地对肉的生产、品质、功用等进行说明,对食肉者的贪婪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小说内容的结构安排上独出心裁。几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小说戏剧性、剧本化特点突出。《檀香刑》一开篇《凤头部》,小说主人公如同大戏开幕一般一一走台亮相;接着《猪肚部》的故事就在已出台亮相的几个人物之间一幕幕展开,集中紧凑,戏中有戏;《豹尾部》以某人为核心,运用了充满动感和张力的对白,加之道白、旁白,既有画面感又有驱动力。莫言自己曾说:“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9]418《四十一炮》将矛盾高度浓缩,前后十几年的事情,运用主辅分合,魔幻与现实交织,在虚拟的对白和诉说中充分展开,具有可听性和可视性。两线故事一起将对食色充满欲望和贪心的人类作戏谑的表现,具有辛辣的讽刺性和夸张的喜剧性,戏剧的形式感很强。《生死疲劳》一书充满了作家的艺术探索精神和艺术灵气,借用了佛教的“六道轮回”思想,一个委曲而死的地主,相继转世为驴、牛、猪、狗、猴五种动物,五种动物的在世活动就是五幕人间喜剧,跌宕起伏,荒唐而悲伤,小说达到的深度和取得的艺术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蛙》是一部运用了书信、小说、剧本三种体裁的小说,作品在最后第五部,直接写成了九幕话剧,使得主人公万心前后思想情感的巨大变化及其深层的人性内涵,得以较为直观的呈现,浓重的仪式感对人物的发展(万心的罪感和忏悔)起到了标示作用。同时,原来由蝌蚪一人叙述的故事,话剧剧本由众多剧中人自我言说,作者欲呈现的人与事会更加明晰与生动。
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是莫言小说创作的回味沉静阶段。2020年8月,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出版,这部小说集共有12篇中短篇,它们少了莫言前两阶段小说创作的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巧的言说视角和结构及其放荡不羁的人物形象,更多的呈现出冷静平实,朴素直白的特点。小说里的人物就是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你我他,小说的世俗性和日常化特征,与前面作品的狂欢化与隐喻性判然有别。“莫言的小说叙事也从色块啸聚变成了线条缠绕,从大幅泼墨变成了工笔白描,从印象派变成了写实派……莫言的小说在表现现实生活时,由感性的挥洒变成了理智的审视。”[10]部本小说集最为突出的是莫言把“莫言”写进了小说,有11篇小说都有“莫言”,或叙述或参与。莫言在谈到这种叙写方法时说:“一个是真实肉身的人,一个是文学形象,这样一种很复杂的,既像面对镜子的关系,也像一个实体对着一个影子的关系,更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分身一样。”[11]这里的“影子”“自己的分身”都说明了小说中莫言与现实中莫言的高度关联性,这样,“莫言以‘我’作为小说的观照者、叙事者,让作品更加靠拢现实,让小说的叙事信笔写来更为自然”[12]。
莫言在言说形式上的探索既主动自觉,又超前出新,他在谈到《笼中叙事》(后改为《十三步》)时这么说:“事件是容易陈旧的,但技巧历久常新。没有永远存在的炸药,但制造炸药的方法世代流传。我不得不猖狂地宣告:这部小说是前无老师、后无徒弟,它像一块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地呆在一个角落里,向我自己证明着我在小说技巧探索道路上曾经做出的努力。”[13]1—2事实上,莫言的努力成效明显,他以多种不同的言说形式出入于各种文本之间,灵活变化的叙述角度、奇诡铺排的语言、镶嵌重叠的文本、真实虚幻的变奏、历史与现实的出入等,进行了别具一格的大统合。这种形式上的创新,“颠覆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促使读者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一切,为当代小说叙事学的发展注入了充沛的元气”[14]。
二
莫言40年的创作,由短、中、长篇小说营造了一个高密东北乡。莫言喜欢乡土,在“高密东北乡”上建立他的文学王国,却映射整个华夏民族,它是文化与人性的发源地。莫言喜欢历史,所有的故事都是散发出凝重的批判气息。莫言喜欢苦难,苦难是人性与生命上升或堕落的转折点。透过他所开辟的高密东北乡这一典型,洞见里面人物形象所具有的反礼教反传统的抗争精神,也读到了他们肆无忌惮的食与性背后的道德的缺失。人性在这里复苏,生命在这里本真呈现。他的小说俗,俗到泥土里,俗到写生、写性、写乱伦;他的小说高雅,雅到他从“高密东北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也正因如此,莫言小说的内容颇为惊世骇俗,在这里莫言完成了“由传统的实在的绝对的本体论转为个人感性生命的本体论”体验[15]。从这一点来看,莫言的创作是有所超越和突破的,超越了前人既成的审美范畴,打破了人们约定俗成的种种理论禁锢。将个人化体验上升到新的标准,用直面的底层的感性的体验来表达其独特的生命哲学。一切的伦理道德生命存在都由食与性展开,以生存、抗争、暴力为过程,以死亡为终点。这里有正直的人性,也有扭曲变异的人性,有匍匐于地的卑贱生命,也有高昂着头颅敢于牺牲的生命。正如莫言在《食草家族》中所言: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莫言的言说内容就是从这个“完整世界”一步步展开的,其小说内容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其一,怪异的人物形象挑战人们的习惯性认知。在莫言小说的完整世界里是美丑混杂的,其人物形象(除他的早期小说外)去崇高化、去道德化严重。在他的人物形象长廊里,其行为举止、心理性格,与传统文学理论、社会心理等格格不入,对文坛和读者形成极大的冲击力。如《透明的红萝卜》里单纯坚强的黑孩却因莫名的欲火中烧,伙同欺负他的小石匠,伤害善待他的菊子姑娘;《红高粱家族》里的抗日英雄余占鳌是个杀人成性的土匪、泼皮、无赖和流氓;《酒国》里代表正义的调查员丁钩儿陷入圈套,一步步堕落,死在了茅坑里;《丰乳肥臀》里伟大的母亲上官鲁氏是一个有乱性嫌疑的女人;《檀香刑》中忠于职守的赵甲是一个具有庖丁解牛娴熟技巧却又极其残忍的刽子手;《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是个心理精神与生理欲望严重错位的炮孩子;《蛙》中的姑姑是个对国家政策具有超强执行力然而又冷漠刻板的机器;《斗士》中的武功是一个眦睚必报的、凶残的弱者;《火把与口哨》中的顾双红是个复仇杀狼后绝食而死现代祥林嫂;等等。这些人物的行事不按常轨,或变异,或荒诞,或诡谲,或惨烈,既不是寻常百姓也不是典型的艺术形象,他们大多有奇能异秉,影响力或破坏力强大。如果按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因素来解释他们的言行就会常常遇阻,继而,人们就会不停地深挖,时代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等穷尽之后,再向深处就是人性因素、生命因素、动物性因素了。当人的言行受之于动物的生存性因素,那么人的一切出格的言行,好像有了合适的存在理由。
莫言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异类崛起,应该说是莫言自觉追求的结果。他生活在儒家思想统治几千年的山东,“发乎情,止乎礼” 要求的不只是男女恋爱要遵守的规范,而是引申扩充为较为宽泛的社会规范,在这种思想的浸染下,人们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欲望是不一致的,反映在文学创作里,势必出现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别的“虚假”形象,以表现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宗旨,诸如他的早期作品《民间音乐》《春夜雨霏霏》《售棉大道》等,写了较为纯朴善良的人物,他们身上也散发出了有如孙犁笔下人物的美善,这是符合当时的文学规范和审美趣味的。随着莫言视野的开阔和思想的成熟,尤其是他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后,大量接触中外作家作品,较深地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同时直接受到鲁迅作品反传统与叛逆观念的熏陶,“莫言揭开对人的本质即人性复杂性的一种思索与认同……对现代杜会表面一团和气,一切事物均被机械化、美好化地覆盖的不满和焦虑,他用自己的笔向人们传达着自己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力图通过还原民间社会的热闹、喧嚣、热气蒸腾的真实场面来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反思”[16]。他完全抛弃了高大上的人物形象模式,有时候矫枉过正了,比如《丰乳肥臀》中的沙月亮、司马库,本来是抗日将才,为什么不能向有益于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方向发展呢?后来都分别走向了国家进步事业的对立面且不得好死,所谓的理想、气节、正义等,在这些人物后期的表现上丝毫不存(沙月亮就直接成了一个汉奸),莫言小说充斥着这类人物,这是莫言对人物形象规范的突破,也是他的人物形象颇受争议的原因。
其二,肆无忌惮地写人的原欲。生命与原欲同在,这是人的动物性因素决定的。“人类所有的一切欲望之内,生存欲望和食欲之外,性欲最为强烈,要繁衍种族的欲望是‘生存意志’最为强烈的表现。这种冲动在正常发达的人类人人都有,到了成熟之后,满足这种冲动是生理和精神健康的根本。”[17]但是,性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代表着不洁、肮脏和粗鄙。上官金童这个性无能者却有极浓的性意识,他的性意识对象甚至游走在他的女性亲人之间,“为亲者讳”传统文化熏染的读者们,接触到如此人物,情何以堪!莫言作品中大量关于性的描写触碰到了人们的道德底线,导致其被攻讦不断。然而莫言并没有因噎废食,有意跳过这一禁忌。他通过写性来揭示人性。《司令的女人》中叙述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知青唐丽娟因通奸怀孕不能返城的故事,《野骡子》中讲诉的是带着妖精色彩的野骡子姑娘与父亲私奔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红高粱》也是以“我爷爷”与“我奶奶”高粱地的野合为始,《丰乳肥臀》更是从字面便能瞥见欲望的踪影,其中的女性们,总是带着原始的女人味,在丰乳与肥臀间散发出来的性吸引,使得男人心神荡漾、欲望翻滚。《生蹼的祖先们》中写女人“乳房笔直前挺”;《天堂蒜苔之歌》里的金菊有着“浑圆结实的屁股”;《爆炸》里的玉兰有着“熟透的胸脯”;《白棉花》中方碧玉有“两瓣丰满的屁股,耀武扬威的乳房”。可谓“凡是有女性出场必有乳房登台亮相”[18]。大自然生成两性,两性结成夫妻,夫妻关系孳生人伦,人伦则是最早的人性。莫言将两性视作人性存在的延续方式和人性本真宣泄的本质表现。那些底层的性欲,是原始的冲动的激情的本色描写,无关艺术、无关高雅,也无关人伦。建构的故事不过是依附本性来演绎生活与爱情,然而这种爱情不能用传统的标准来评价,在他的作品中无需忠贞不渝,也不需门当户对。《秋水》中作为千金的“我奶奶”与出身低贱的长工“我爷爷”,《野骡子》中妖精样的“野骡子”与“我父亲”,《红高粱》中余占鳌与戴凤莲,《酒国》中的丁钩儿与女司机,《金发婴儿》中紫荆与黄毛,一对对一幕幕,这些贴近人性本源的性欲追求的淋漓书写,读来确实让人羞愧和疼痛。
莫言笔下的人物对食物的渴求与贪欲也不逊色于性。《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骨瘦如柴的黑孩,对食物有一种超出常人的渴望,所以他把石头子形容成“鸡蛋黄”,把挽成一团的水草喻为“海蜇皮”,老铁匠的鼻子尖则如“熟透的山楂”,伸手淬火把手烫伤闻到的是一股“炒猪肉的味道”。《四十一炮》中写了罗通与罗小通父子对肉食的强烈期盼,“世间万物都是虚的,只有吃到肚子里的才是真实”。《丰乳肥臀》中的母亲,用自己的胃去偷藏豆子,用那混着胃液和血液的食物养活孩子。这些是生存之中求食,是生命之需、饥饿之需、子嗣繁衍之需。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需要和权利,所以莫言写吃,写他们迫切地为吃而努力,不论这种获得是否道德是否体面,对食物的需求和欲望基本是在动物生存层面。另一种吃是在生存之上,《酒国》中的烹食婴孩,《四十一炮》中的肉神节,《丰乳肥臀》中的百鸟宴,这是吃饱后萌生的新的欲望,和物质膨胀的欲望相联系,和腐败的政治、扭曲的人性等相联系,吃成了乱世之中堕落者、腐化者弥补精神短缺的幌子。人性在吃中分层分途,大多数人呈现出来的就是不带社会意义的生命性与动物性,人物形象在人性分化中呈现的大多是带有原始野性的特点。
其三,批判全视角触抵历史与现实各层面。莫言的小说在展示充满生命活力的民间世界时,以独有的批判精神,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全方位的批判,诸如从历史文化到现实政治、从草根农民到官员精英、从传统观念到现代理论、从乡俗民情到社会心理等,作者无一不予以无情的批判。这方面与鲁迅金刚怒目、横眉冷对的特征不同,莫言基本上是在戏谑嬉笑、魔幻荒诞中呈现出批评的决绝和深广度。其中最让人惊诧的是作者以民间立场解构权力制度。莫言在讲述故事时,站在官场与政治的外围,观察、呈现、剖析。他的小说对晚清以来的各个时期的管理规范都有批判。《红高粱》的曹知县明知“我奶奶”耍疯卖痴,就了断了一桩人命案,让罪犯逍遥法外,继续杀人。这让读者顿生疑惑,这是什么样的管理体系?治理者遵循的是什么章法?《檀香刑》集统治者最为残酷的刑罚展示给世人,这种封建的糟粕是“家丑”,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莫言一点也不避讳,还将酷刑实施的过程作了景观化描写。《蛙》批判的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悖制度设计宗旨的异化现象。
莫言以一种先锋时代的写作姿态对抗着流行的写作程式,他自己曾说过:“你敢跟流行的东西对抗,你敢为天下先,这就是先锋的态度。甚至在很多人都不敢说心里话的时候,你敢说就是一种先锋的态度。”他“敢亵渎所有的神灵,打破一些价值和标准”[19],其批判背后折射出的是全新的写作意识和审美,对既定秩序的冲击、拆解和否定中包含了对文化功能和审美取向的更新和重建。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更新与重建不是沿着更加秩序、更加规范、更加文明的方向,而是对所谓秩序和规范要训化和改造的人性中的原始蛮力和野性的向往。而社会秩序与规范同生命野性中的一些因素始终都是在博弈之中,常常是后者被前者驯服和同化,因此,莫言的更新与重建难成现实。但生命中的野性永远存在,不能消灭,在建的社会秩序与规范对此不得不正视和回应,因此,莫言小说中拆解和否定各种规范的意识,对社会秩序与规范的完善又不无促进之效。
莫言小说的言说内容是不设禁区的:少有美好的爱情,大多是肉欲的性交;没有温柔娴静的淑女,有的是张狂躁动的欲女;没有秩序与和谐,有的是苦难和暴力邪恶;现有成规和理论都是他要突破的目标。刘心武曾这样评价莫言:“有太多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所排斥的东西,不提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甚至不提供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不提供可供社会崇敬、学习、爱慕的形象。小说中有大量人性恶、原欲、场景的脏乱、残暴(甚至包括食婴、剥人皮及种种酷刑),还有粪便、呕吐物等原来被认为不能进入文学文本的事物。”[20]正因为此,莫言及其作品颇具争议性,即使他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现象也存在着,比如批评家李建军的文章《直议莫言与诺奖》里这样写道:“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来写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经验。”[21]那么,莫言的追求和立场呢?莫言认为,一个作家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是与他的生活经验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评价他家乡的话,“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他的童年少年都是在高密东北乡度过,那里的民间故事、田野景物、鬼怪传说等,浸染了他,故他创作的内容、视角、立场等,总是与故乡和民间天然地联系着。莫言认为,世界是美丑混沌不清的,至美极丑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伟大的小说“应该是可以被一代代人误读的小说”[4]8,“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赢得那些准贵族的欢心,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欢群吠叫。它应该是深海里的鲸鱼,孤独地遨游着”[22]。学界的批评,莫言的系列论谈,使我们明白了莫言为何能独树大旗,除了生逢其时能充分吸纳世界文学的养分外,还有他自身的因素,诸如成长经历、耽于幻想、有语言天赋、有叛逆天性、有悲悯情怀、有独立人格等。陈思和曾给予他充分肯定,“莫言之所以获得世界性认可,在于其勇于为中国农民代言,在于其激发了民间最富生命力的理想性,在于其继承发扬了拉伯雷式的世界文学优秀传统,在于其艺术地创造了一系列开放多变的文学文本”[23]。正是“开放多变的文学文本”,读者们见仁见智,“误读”现象不断,同时它们也获得了别样的命运,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莫言小说“莫言式”言说,烙有中国传统儒释道的印记,也贴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他以魔幻的方式来写民间,借助中国悠久的叙事传统和西方文学的技艺,语言戏谑又狂野,事物描绘既素朴又诡谲。他一方面显示“示丑”之能事,让人感到尴尬,一方面用负载了民族感情的语言来表达他对中国这片热土爱得深沉。有人说:“莫言高举艺术叛逆大旗,蔑视文学创作成规,这是把双刃剑,这几乎是他小说叙事获得激赏与遭受批判的根源。”[24]他的小说既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也有乡土文学的特征,同时还兼具了黑色幽默的讽刺风格,然而又不同于三者。如果简洁地表述“莫言式”言说的含义,还是引用莫言自己所说的一句话:“创作就是突破已有的成就、规范,解脱束缚,最大限度地去探险,去发现,去开拓疆域。”[25]他的这句话正好诠释了“莫言式”言说的基本含义:突破规范,开拓疆域。“莫言”两字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名字,当它与其文学文本联系在一起时,它就是“莫言式”言说,它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将随着学界对莫言及其文本的不断研究愈加丰富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