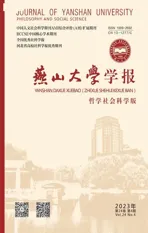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而译的外来译者
——兼评《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
2023-02-10党梁隽
黄 勤,党梁隽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引言
中国翻译史上,无论是绵延千年的佛经翻译,还是长达数百年的科技翻译与西学翻译都离不开外来译者的重要作用[1]57,新中国国家叙事的对外传播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外来译者的主导作用。国家叙事指叙事学视野下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传播,旨在对内凝聚共识、引导认知,对外展现国家形象,以此获得国际认可[2]94,而对外展现国家形象主要是通过国家翻译实践,即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而实现的[3]93。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三个国家翻译机构中,那些从域外而来、拥有母语优势、与本土译者通力合作,甚至从事独立翻译的外来译者群体,在国家翻译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较于本土译者,国内学界对这一特殊译者群体的翻译研究明显不足。
任东升、王芳等的新著《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以下简称《沙博理研究》)是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协调机制重大课题“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的结项成果。该著以外来译者典型代表沙博理为个案,基于语料库分析、数据统计分析、文本对比分析和译者对比分析等多种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十章从多个维度深刻阐述了沙博理的翻译艺术及其对新中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贡献。本文结合对该著的介评,重点探讨外来译者的译者身份、国家叙事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如何共同呈现以及外来译者研究路径四大问题,以期为外来译者研究和在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这一群体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作用提供启示。
二、外来译者的译者身份
在新世纪,翻译研究已实现以“原文/作者”为中心,到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再到以“译者/社会”为中心的转变[4]143,开始探究译者身份、角色与译者行为的关系。如周领顺认为译者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前者指译者以译者身份呈现的语言性转码行为特征,后者指译者角色表现的社会性表演特征,角色是隐性、可变和无限的,而身份则是显性、稳定和有限的[5]21。任东升、高玉霞[4]144则认为译者身份在不同翻译环境中可具体化,如在制度化翻译环境和市场化翻译环境中,译者身份表现为制度化译者和市场化译者。
制度化翻译是指由国家权力机构和统治者当局发起和推动,服务于国家政治价值目标实现的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有监控的翻译活动[6]19,其译者作为制度化翻译执行机构中一员,在由国家形塑的环境中翻译,享有独特地位和权力,呈现明显“制度化”特征,即制度化译者[4]144。作为制度化翻译的实践主体,无论是本土译者还是外来译者,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和译者——“国家公务员”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他们的制度化翻译的译者行为均以国家意志为导向。但本土译者主要保证语义的准确传达,外来译者因具有天然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身份,能保证译文符合目的语规范。总体而言,制度化译者的社会属性要高于语言属性,在译者行为上表现为务实性高于求真性。
《沙博理研究》第一章总结了外来译者沙博理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化译者身份对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作用。沙博理(Sidney Shapiro)成长于美国,1947年来到中国,1963年加入中国籍并定居于中国直至2014年在北京家中逝世。5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翻译和编译中国文学作品达200多部。沙博理卓越的翻译成就,除归功于其双重文化身份外,更与其所处翻译环境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化译者身份密不可分。沙博理翻译生涯可划分为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和新时期二十六年(1976—2002)三阶段[7]4-5,其主要译作集中在第一阶段。在此阶段,沙博理所供职的外文出版社隶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负责对外宣传和出版,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共171部[8]26,发挥了国家翻译实践在机构翻译和制度化翻译上的优势,将部分国内最新文学讯息迅速传播到国外。该社出版的69部英译小说中有14部为沙博理独译,多为中国当代红色小说。可见,沙博理是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中重要一员,积极参与了制度化翻译。
作为制度化外来译者,沙博理是新中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实施者。《沙博理研究》第七章对此深度阐述。通过对比分析茅盾《农村三部曲》沙博理英译本(以下简称沙译本)和叶君健英译本,端木蕻良《雪夜》《鴜鹭湖的忧郁》沙译本与葛浩文英译本,阐明了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译者行为的异同。制度化译者沙博理在翻译中尽量显化原文语义,其译者行为倾向于社会-政治性务实总原则指导下的语言性求真;市场化本土译者叶君健译文偏向目的语语言习惯,更多考虑读者因素,译者行为倾向于社会性务实;市场化外籍译者葛浩文则以市场为指标,在翻译中尽量推进原文语义,译者行为偏重社会-市场性务实。
以上分析为深入探讨外来译者的制度化译者身份对其译者行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制度化译者受国家机构资助,服务于外宣,是国家声音对外传递者,其译者行为受制于机构命令,政治考量重于文学艺术的雕琢。制度化译者虽在权衡翻译内外因素时会更为看重国家叙事对外传播,但其并非“翻译机器”,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性选择仍依赖于译者。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中,外来译者是与本土译者互补的一个译者群体,如沙博理一样译作等身的外来译者不在少数,如来自英国的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詹纳尔(William J.F.Jenner)、班以安(Derek Bryan)和来自美国的吴雪莉(Shirley Wood)、罗慕士(Moss Roberts)、平卡姆(Joan Pinkham)等。他们皆是在政府建立的正式翻译机构内从事指派的翻译任务的译者,外译语种多样,体裁和题材广泛,他们的译者身份均为制度化译者。但目前对这些外来译者的研究多限于对其译作翻译方法与策略的分析,鲜有探讨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对其国家翻译实践译者行为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外来译者研究中,可以先明确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及该身份所赋予这一特殊译者群体的翻译目的,基于此,再进一步深入探究他们译者行为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因素。
三、国家叙事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
对外来译者制度化译者身份的界定,为深入探讨制度化翻译语境下,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提供了前提条件。广义上的译者行为包括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超越翻译的社会性非翻译行为[5]25。外来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译者行为则具体表现为其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取如何受国家叙事的制约。
(一)对翻译文本选取的制约
影响译者翻译选材的因素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有人认为赞助人左右翻译选材,译者多表现为被动配合与顺从。[9]39对于参与到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而言,其赞助人便是国家机构,但国家机构赞助的译者的选材取决于国家机构赞助翻译的目的而非个人兴趣[10]55,译者的翻译活动,包括翻译选材会受主流意识形态操纵[11]39。
外文出版社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主要机构,向外输出的作品主要是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文学作品。[12]45《沙博理研究》第十章阐述英雄叙事革命历史小说是沙译本选材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他本人偏爱历史题材外,更多受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影响。沙博理的第一个翻译阶段是建国初“十七年”,他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编辑部作为制度化译者从事中国小说英译,彼时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一样上升到国家行为,且被完全体制化[13]89,成为构建国家叙事的重要一环。外文出版社的翻译选材直接服务于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目的。英雄叙事革命历史小说在当时中国文学场域逐渐被经典化,被纳入国家翻译实践选材的目的之一是抵抗美国的负面中国叙事,之二是建构中国自我形象[7]233,其文本内容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和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契合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政治诉求。沙博理翻译的小说题材主要涉及革命战争、工农和少数民族三大类,皆与当时主流文学导向和外宣政策符合。
由此推及,与沙博理同时期的外来译者群体的翻译选材亦与彼时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密切相关。上文提及的多位外来译者,如杜博妮曾任外文出版社编辑,英译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詹纳尔曾供职于外文出版社,英译了《西游记》等;班以安、吴雪莉、罗慕士等均曾应外文出版社之邀英译中国文学。其中,班以安英译了《山乡巨变》等,吴雪莉英译了《苦菜花》等,罗慕士英译了《三国演义》等,平卡姆曾参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著作的英译。这些外来译者都是在政府建立的正式翻译机构内从事以上指派的翻译任务,为新中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服务。因此,如何从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视角审视他们的翻译选材,有助于深入探讨这一译者群体的翻译选材与国家的政治需求、叙事目的等的关系。
(二)对翻译策略与方法选取的制约
1.长篇小说萃译策略
传统意义上,翻译策略一般指归化与异化。但《沙博理研究》在第三章,基于对沙博理的《水浒传》等7部长篇小说英译本和吴雪莉的长篇小说《苦菜花》英译本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同处于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这两位外来译者译作中均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其总结为“萃取翻译”,简称“萃译”策略,包含萃取、合译和雅化三个过程,萃译旨在通过提升原作叙事品质、审美价值和政治地位,为目的语读者提供权威化译本。[7]46-48
萃译脱胎于变译理论,但有其特性。“萃”含“择优而取”之意,囊括操作目的、操作标准、产出效果等多方面,是全面立体的译本呈现手段。[14]126萃译是制度化外来译者普遍使用的翻译策略,因为从事国家翻译实践的译者都会进行“文化自我过滤”[15]39,在翻译时删去或编译甚至改写部分内容,避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内容外流,更好地完成国家叙事之目的。萃译能增强小说整体性和文学性、优化原文叙事结构,使译文更符合特定时期国家外宣要求。“萃译”这一全新翻译策略概念的提出超越了对翻译策略传统意义上的理解与表述,开启了深入解读国家翻译实践中外来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及其动因的新思路。
2.叙事重构策略与方法
叙事是人类经验和社会活动的符号呈现,具有建构个体与群体社会身份的功能。英国翻译理论家蒙娜·贝克(Mona Baker)最早将社会叙事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叙事[16],强调翻译在政治冲突中的重构作用。译者内嵌于文本叙事中,翻译是译者重构并传播叙事的过程[7]94。
《沙博理研究》第五章就外来译者如何重构原文本的元叙事、空间叙事和公共叙事进行了详细探究。对于元叙事重构,选取国家叙事特征明显的袁水拍政治讽刺诗的沙译本,政治讽刺诗的政治维度扩大了叙事差异,翻译的难度增大。而沙博理借助元叙事,采取重构叙事框架、定位人物身份、增设叙事情节等翻译策略,保持了原诗政治叙事的建构性,关照了目的语读者,同时实现了中国政治叙事的国际表达。[7]93对于空间叙事重构,基于社会空间、接受空间和文本空间分析了《铜墙铁壁》等两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沙译本,阐明沙译本结合历史语境和读者接受,运用修辞和增删等翻译方法,朝着符合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方向重构了两译本的叙事空间。对于公共叙事重构,选择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小二黑结婚》等3部小说,阐释了沙译本如何运用标签化建构、时空建构、文本萃取式建构等策略再现原文本中反封建的公共叙事,使西方读者全面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元叙事、空间叙事和公共叙事是国家叙事的三种主要形式。它们在译文中的重构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因此,在探讨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翻译时,应重视探求他们是如何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来重构这三种主要叙事,从而对外构建正面中国国家形象的。
四、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共同呈现
方梦之指出,翻译家有艺术家的气质和禀赋,有着艺术和科学的完美结合[17]12。对于国家翻译实践中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的研究,除了探讨他们如何对外传播国家叙事,也要关注他们在翻译文本中所表现出的翻译艺术。小说翻译过程中的叙事方式、语篇结构和文体风格的处理与调适是译者翻译艺术的体现,这三方面也直接影响国家叙事在译文中的表达。因此,如何让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在译本中合理共现是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必须重视的问题。下面结合《沙博理研究》,探讨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
(一)叙事方式转换与翻译艺术
英汉语结构差异导致中英小说叙事规范话语层面的差异。叙事方式涉及叙事结构,即叙述语篇呈现的表层结构、叙事视角,即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和叙述话语方式,即用来叙述一个事件或情景的话语形式。根据实施叙述话语的主体,叙述话语方式包括以作者为言语行为主体的“作者叙述话语”和以作者笔下主人公为言语行为主体的“主人公叙述话语”[18]18。在翻译中只有借助不同叙事转换方式,才能使译文既保留原文文学性,又准确再现原文叙事内容。
《沙博理研究》第四章以红色小说《平原烈火》沙译本为例,探析了如何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叙述话语三个层面对原文本合理转换。就叙事结构而言,原文本采用了故事内人物对话与故事外全知叙述结合的块状叙事结构,沙译本则呈现出人物话语与叙事者话语分离的叙事趋势[7]63,译本在结构上进行了段落的合并、分解与删节,不仅呈现出原文的叙事效果,也更符合目的语文化语境,继而达到叙事交流的效果。同时通过对如革命歌曲等内容的保留等处理方式,在目的语世界中实现“自我合法形象的塑造”[15]36,进而实现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目的。就叙事视角而言,原文叙事视角为故事内人物有限视角,因汉语句子主语缺省不影响语义,而英语句子需要主语,沙译本将其转化为全知视角,顺利传达故事情节。就叙事话语方式而言,沙译本将原文中直接引语的引述语主要转化为通过形容词引出引语的方式,既遵循目的语诗学,又忠实原作精神和情感态度,传达出原文塑造革命英雄的内涵,符合树立国家新形象的目的。
沙译本对以上叙事方式的转化,是身处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主体性在忠实讲好中国故事和英语读者取向间取得平衡的表现。外来译者群体具有天然母语优势,面对英汉叙事结构差异,他们是如何在上述三个叙事层面进行合理转化,使译文既实现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又展示翻译艺术的,这无疑是外来译者研究要深入探讨的又一重点。
(二)语篇重构与翻译艺术
语篇结构表现为上下文逻辑连贯。英汉语篇结构差异导致在翻译时需要适当调整语篇结构。《沙博理研究》第四章探析了《小城春秋》沙译本对原文自然段结构和叙事结构的调适与重构,阐明在遵循国家外宣政策基础上,沙译本对原文有些章节“大刀阔斧”删改,看似不忠实原文,实则体现不拘泥于原文,偏重艺术表达的翻译思想,其表达方式和结构更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原文艺术性,达到了制度化译者“外从内调”的平衡。[7]82
鉴于语篇重构方式多样,不同的外来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会采取不同策略来处理原文本语篇内容的再现和翻译艺术表现间的关系,只有对此进行客观与系统的探讨,才能深入探析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好“忠实”与“接受”的关系。
(三)文体风格的再现与调适
风格是作者从能表达相同内容的语言形式中选择的结果。反映文本风格的语言形式多种多样,如文化专有项,“由于译语读者文化体系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与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其“功能和含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困难”[19];乡土语言,反映作者写作风格,对人物描写、情节推进及主题烘托也起重要作用;小说题名,除本身含义外,还有联系读者与作品的“非词语价值”和满足读者审美的“超词语价值”[20]14;标点符号,既可以分隔语篇中小句,还可以表达情感和语气,体现小说风格。
文体学关注文学文本中具有文学价值的语言表达形式。[21]《沙博理研究》第六章使用文体学分析方法,深度阐释了以上几种风格的语言表现形式在多部小说的沙译本中的再现。如对于《月牙儿》等3部小说中的文化专有项,沙译本增添“译者声音”补偿原作的“文化缺省”,虽不如原作简洁含蓄,但再现了原作文化内涵,保持了原作自然流畅的叙事特征。[7]83对不同小说的题名,沙译本采取了承袭原文、灵活再现、显化主题、巧用标点等多种英译方法,达到了原汁添新味、传义更传神的艺术境界。[7]112对《新儿女英雄传》等3部小说中的乡土语言,沙译本根据语境分别选用了表层等值模因、深层等值模因、语用等效模因和社交语用等效模因等来传译,体现出翻译艺术。对于小说《星》中频繁使用的破折号和省略号,沙译本采取了删除冗余部分、简化和转换不能照搬的标点和增译标点等不同方法,准确再现原文标点符号的语义、语法和衔接三大功能。
外来译者群体在国家翻译实践中,所涉原文本题材与体裁各异,其文本风格的语言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虽然《沙博理研究》仅探讨了上述几种典型的小说风格的语言表现形式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但其深入细致的分析为探究外来译者群体如何在国家翻译实践中,根据具体语境,采用合适翻译策略与方法再现不同语言形式表现的原文本风格提供了有益启示。
五、外来译者的研究路径
《沙博理研究》对外来译者沙博理进行了多维度立体式描写与探析,为研究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群体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多方面提供了启示。对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研究,在研究路径上可进行以下几方面探索。
(一)研究对象丰富化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少的外来译者参与到国家翻译实践中,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功不可没。鉴于目前对这一译者群体研究的数量有限,与他们对于国家翻译实践的贡献不相匹配,我们应采取各种途径,广泛收集参与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外来译者个案,建立完善的外来译者群体国家翻译实践档案库,全面探求这一群体所表现出的外来译者群体性译者行为特征和个性化译者行为差异,深入阐释其译者行为共性与个性形成之动因,客观公允地评价这一群体对我国不同时期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作用,总结其翻译艺术与翻译思想。既丰富外来译者理论研究和翻译史研究,也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国家叙事的对外传播和国家翻译能力的培养。
(二)研究视角多样化
目前对外来译者这一特殊译者群体的研究存在视角单一的问题,《沙博理研究》在此方面有了较大突破,兼顾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从不同理论视角深入探讨了不同题材、体裁和语言形式的英译,较为客观地呈现了沙博理的外来译者整体形象,值得借鉴。
在宏观层面,第一章、第七章和第十章等将沙博理的翻译活动置于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宏大背景下,探索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翻译选材的影响因素及他们对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作用;在微观层面,第三、四、六、九章等章节从叙事学、文体学、模因论和创造性写作等视角对沙译本的乡土语言、女性话语、小说题名及标点符号等各方面进行细致剖析。最后一章引入“中国英语”这一新概念视角,论证“中国英语”是服务于中国经典英译的较理想的翻译语言;在中观层面,第一章针对沙博理的特殊人生经历,确立其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制度化译者身份。第七章具体对比沙译本与其他译者译本,阐述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对译本的影响。三个研究层次有机相连。如在微观层面对沙译本中“中国英语”成因与意义分析后,将其重要性上升到宏观层面,明晰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责任,为建立“中国英语”体系,实现“中国英语”的语言战略目标提出了开拓性建议。
因此,未来的外来译者研究,不仅要针对不同译者、不同翻译语境、不同文本体裁与题材采取不同研究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深入开展对国家翻译实践中的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的译者行为研究,更要注重研究层次间的关联性,尽可能客观全面地探析翻译内外因素对外来译者行为的影响。
(三)研究内容全面化
外来译者群体在国家翻译实践中产出了丰厚译作,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某个译者的一部或几部较有影响力的小说翻译或诗歌翻译等,未能全面呈现这一群体在翻译中所表现的翻译艺术、翻译思想以及译者行为的共性与独特性,对全面探究他们对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贡献及动因形成了阻滞。
《沙博理研究》内容丰富,覆盖了沙博理的 28 部译作,既有沙译代表作《水浒传》,也有关注度尚缺的政治讽刺诗等的英译,涉及小说、诗词、民谣、歌曲、散文等体裁。既包括对多种语言现象如小说题名、标点符号、特殊句式等英译的分析,也涵盖对语篇结构和叙事方式等转换的探讨,更上升到对翻译语言“中国英语”的阐释和对沙博理以“中国人”文化立场解读所译中国作品,以“文化间”双重身份操纵翻译,以“英语读者”视角把握译文表达的“一人三体”译者模式的归纳。
因此,应站在国家翻译实践的高度,以丰富的研究内容来审视外来译者作为制度化译者的译者行为,以使研究结果尽可能趋于可靠与全面,尤其要重视目前研究不多的外来译者在国家翻译机构内进行的政治文献和科学文献的翻译,总结出他们在翻译中的译者行为的规律性特征,以期为新时代的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叙事对外传播提供借鉴。
(四)研究方法科学化
《沙博理研究》采用了以下多种研究方法,使其研究过程更科学、得出的结论更令人信服,值得在以后的外来译者研究中借鉴。
1.多种方式的定量定性结合研究法
与传统定量分析不同,《沙博理研究》采用了数据统计分析和语料库分析等多种定量方法,如第二章对《水浒传》第47回原文本和沙译本、赛珍珠译本与杰克逊译本的段落分布和叙事方式进行了大量数据统计与对比分析,更客观全面地阐述了三译本翻译策略的异同,也验证了沙译本为公认的佳译;基于自建《水浒传》平行语料库,发现并阐释了沙译本的“中国英语”特征。第三章基于对外来译者所译8部小说萃取比例的统计,归纳出萃译这一特殊翻译策略,继而对《我们播种爱情》等2部小说沙译本中的萃译再定量统计并多维度定性归因,由此较客观科学地论证了萃译在外来译者群体的国家翻译实践中使用的普遍性。
毋庸置疑,对于外来译者研究,采取多种形式的定量研究方法,将使在此基础上的定性研究结果更具可信度,进而能更为客观地评价外来译者行为的诸多方面。
2.多个维度的对比研究法
《沙博理研究》拓宽了对比研究的维度。如第二章未囿于对《水浒传》几个典型译例的三译本对比研究,而是对第47回的原文本和三译本的段落分布和叙事方式整体分析,以揭示沙译本特点及成因。第七章既对制度化译者沙博理与市场化译者叶君健和葛浩文分别对比分析,还对同为外来译者的班以安与沙博理进行了对比研究,由此剖析了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与不同类型市场化译者以及同为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的译者行为的异同。
以上多维度的对比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沙博理的译者主体性、译者行为及翻译艺术的认识,尤为重要的是对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群体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启发研究者尤其要深入探讨这一群体内不同译者在翻译同一题材或同一体裁的原文本时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以及所产生的不同传播效果,并进行归因分析。
(五)译本传播效果多渠道考察
考察译者的译作在译语语境的境遇,是研究中译外作品必不可少的一环。目前对于译者及中译外作品传播效果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对境外读者阅读情况的调查分析,继而影响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成效的评判。[22]197《沙博理研究》同样缺乏对境外读者译本阅读情况的深入调查与反馈,因而在探讨沙博理译作海外传播效果时略显不足。
外来译者的中国作品英译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可从译作在海外销售情况、权威媒体评价、海外专业读者及一般读者的书评量及内容以及世界图书馆藏量和西方学界相应引用与参考等方面来进行调查、统计与分析,再从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传播途径等多方面分析传播效果的成因。基于此,才可能深入系统地探讨外来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译者行为特点与效果以及对国家叙事对外传播所作贡献,为新时代国家翻译实践提供镜鉴。
六、结语
《沙博理研究》对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和翻译艺术而译的外来译者沙博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书中的一些新概念、新观点和新方法独具匠心,在拓宽译者研究尤其是外来译者研究视野的同时,更能孵化出相关翻译研究领域的成果。当然,书中也不乏上文提及的少许瑕疵。瑕不掩瑜,该著从国家叙事对外传播高度,对外来译者沙博理的译者身份、译者行为和翻译艺术等进行了有益探讨,增强了沙博理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也有助于完善国家翻译实践理论体系建构。
外来译者作为一个特殊译者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翻译实践中对我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贡献重大,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与方法运用、翻译思想阐发、翻译艺术呈现等译者行为上既有共性,也存在个体差异,这些方面应成为今后外来译者群体研究的重点。我们应充实研究对象、采取多种研究方法,针对丰富研究内容进行多视角深度探析,客观公允地评价这一群体的译者行为,丰富翻译史上的译者群体研究。这对探索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