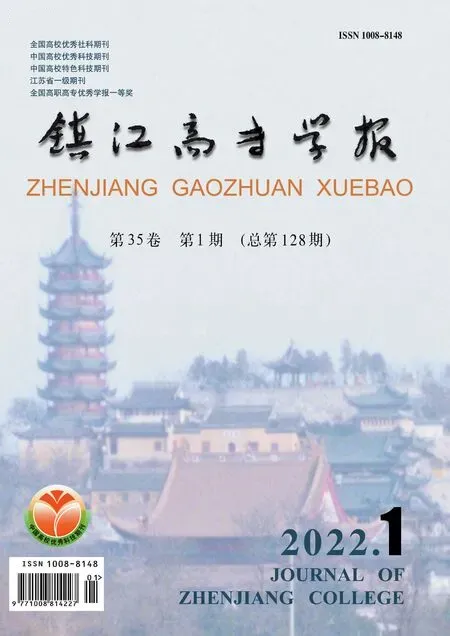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从肯定到否定
2023-01-10李阳
李 阳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1 方法论源起:从巴门尼德到笛卡尔
西方哲学肇始于前苏格拉底时期。人们对哲学的看法一开始是流变的,赫拉克利特是代表。他的哲学重点关照“成为”(becoming),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现实就像一股不断流动的溪流,没有什么东西会片刻静止不动。事物的实质是变化,在时间的每一个瞬间,组成事物的物质已经有所改变,旧的逝去,新的元素从另一个来源涌入。赫拉克利特的观念被总括为“万物皆流”(everything flows)。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里,万物都是变化的,“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1]59。但这种对事物变化的探索在后来的哲学思考中隐匿了,哲学更倾向于在不断流变的现象中寻找永恒不变的基础,在罗素看来,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的学说使人感到生命的有限和虚无,因此,哲学家用更大的毅力追求某种超越时间领域的东西,这种追求始于巴门尼德[1]66。
与赫拉克利特相反,在巴门尼德看来,没有什么事物是变化着的。他给出了哲学上绝对化的命题,即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2]23。巴门尼德思想中的“存在”并非是经验世界中具体事物的存在,而是纯粹的存在,即仅凭借自身而在的在。经验世界中的存在是感性的存在,是以表现的形式出现的,其总是变化的、多样的,因此这种存在实际不存在,只有依据自身而在的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巴门尼德主张,不去描述存在者,存在者是流动而多变的,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存在本身。然而存在具有先验性,无法在经验世界中现身,为了能探索到存在,在存在外在于自我的前提下,巴门尼德给予了另一种确定存在的方式,即通过现象和存在的辩证互补关系来把握。凡属于现象的,就是非存在,而存在的就是非现象,巴门尼德由此提出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方法,即通过思想和语言推论存在者。在罗素看来,巴门尼德为后世哲学所接受的最为重要的观点是“实体的不可毁灭”[1]70,实体是不同谓词之间永恒不变的主词。因此,哲学发展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二人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巴门尼德对永恒的追求。对柏拉图而言,“理念”是巴门尼德所言的不可毁灭性实体,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是超越性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是其所是”(the what it was to be)和“是其所见”(the what it is),前者是本质,后者是表象。永恒不变的实在居于意识无法到达的本质之中。
但这种追寻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存在矛盾。本质与现象是对立不可通约的范畴,而人的有限性无法直接观看本质,必须通过现象,这就意味着,本质无法真正进入人的意识,对本质的追寻并无自明性,只是通过纷杂的表象看本质。本质无法在意识中呈现,故无法证明对本质的把握是确实的。
为探索形而上学确定明白无误的方法论基础始于笛卡尔。笛卡尔认为经院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教义包含一个基本错误,即对形而上学真理获得的不可靠性,因此,他缔造了另一种哲学体系。笛卡尔对哲学的思考带有鲜明的17世纪科学方法论的影子。在笛卡尔看来,哲学要获得明白无误的基础,首先要怀疑一切事物。笛卡尔首先怀疑表象的真实。他在《第一哲学沉思录》(FirstMeditation)中说道:“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为真实的东西,都是从感官获得的。”[3]但他很快指出“在理智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先前在感觉中产生的”[3]看法是童年偏见的结果:“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受到感官的引导,去寻求利益,避免身体的伤害。因此,当我们长大成人时,我们‘沉浸’在身体和感觉中,因此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即感觉是学习现实本质的基础。”[3]
笛卡尔否认通过感官可获得事物的本质,认为必须把心灵从感官中解放,才能够获得牢靠的真理。他说:“我还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我碰到什么可靠的东西……如果我有幸找到哪管是一件确切无疑的事,那么我就有权抱远大的希望了。”[4]34在第2个沉思中,笛卡尔确实发现了他所追求的确定性基础,即我思(cogito),“所以,在对上面这些很好地加以思考,并且仔细地加以检查之后,最后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必须把它当成确定无疑的,即有我,我存在这个命题。每次当我说出它来,或者在我心里想到它的时候,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4]35。我思作为第一原则给予沉思者,沉思者在我思中的第一直觉就是上帝的存在。而上帝是必然存在的,笛卡尔援引了形而上学的一条原则,即“在有效的和全部的原因中至少必须有与那原因的结果一样多的现实性”[4]35,他将这条原则应用为一个代表无限的意旨需要一个无限的存在作为它的原因。因此,他得出结论,一个无限的存在,即上帝,必然存在。由此,上帝存在保证了我思的清楚明白和真实性,而上帝的存在又是因为沉思者清楚地感知到了这一点(1)我思与上帝的关系呈现一种循环论证,后世讨论颇多。如Loeb认为,笛卡尔的目标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确定性,而是关于一个独立于心灵的世界,而仅仅是寻求一套内在一致的信念。参见LOEB L. The cartesian circle [M]//COTTINGHAM J.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escartes. Car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因此,在能够确信上帝的存在之前,已经能够确信,清楚而明显地感知到的一切是真实的。
我思成为形而上学也即第一哲学奠基性的概念,从我思出发,其余的方法都可通过逻辑进行推理判断,而不是依靠杂多的现象,我思的地位不容拷问。遵守严格逻辑命题,笛卡尔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哲学,或者说,人文科学。这种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在《谈谈方法》中初现端倪。《谈谈方法》作为《屈光学》《气象学》《几何学》序言的总论,呈现了鲜明的自然科学特征。在《谈谈方法》第2部分,笛卡尔给出了步骤:“第一,凡是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绝不把其当作真实去接受。第二,将所要检查的每一道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尽可能分解成许多部分,以作为妥善解释这些难题的要害。第三,依照次序引导我们的思想,由最简单的、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最复杂的知识。第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的考察,尽量普遍的复查,做到确信无遗漏。”[5]16笛卡尔通过确定一个明白无误的非感性基础对事物进行逻辑推论的方法论形式明显是自然科学的(2)“我思”的问题在康德那里得到进一步回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笛卡尔的命题延展为:“我思必然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B131)这是极为主观性的判断,即康德所理解的“意识的整体性”(the unity of consciousness)。在康德看来,我的能力与现象的关系不是前者符合后者,而是后者契合前者。但康德对知识与能力的认识存在疏漏,即可以认为如果大脑具有两种不同属性的功能分区,那么我将以这不同属性功能分区的功能认识不同属性A,B两种事物,而非是我可以认识A,B两种不同事物意味着大脑具有两种不同属性功能分区。康德的这一理论与18,19世纪的颅相学(Schädellehre)有某种相关性,而他本人也在遗书(AA XV/2, AA XXI: 1802-1803)中表达了这一点,参见Marco Duichin:Anatomists,philosophers,“head hunters”:Gall,Kant and the early days of phrenology.。然而重要的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虽有所相似,但更多的是差异。对自然科学而言,事物的发展是可重复性实验且不断规划为简单、抽象的概念,更多的是空间意义的,缺少对感性生命的经验化理解和历史隶属性的接纳,而人文科学的独特性正在于此。
笛卡尔通过严格的逻辑推论给予形而上学明确的基础和规整的方法,体现了人文科学进一步向自然科学靠近,而在后来的研究发展中,人文科学力图获得独特领地,与自然科学区分开,其探究方法也一转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模仿与屈从,以其生命性和历史性与自然科学相区分。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使人文科学具有了独特的方法意识,但因过度关注人自身和追求绝对性真理,使人文科学依然走在与自然科学本质相同的道路上。
2 从说明到理解:德罗伊森对实证主义的反驳
德罗伊森(J.G.Droysen)是19世纪普鲁士学派的著名历史学家,《希腊化时代史》《普鲁士政治史》等是蜚声后世的史学作品。不仅在具体历史事件上,而且在历史学或者说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德罗伊森有重要进展。在德罗伊森这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相区分,拥有其独特性。
德罗伊森的方法论构建体现在《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他1857年开始讲授的“历史知识理论”课程的教学大纲由其外孙徐本芮(Rudolf Hübner)收集并整理出版。书中,德罗伊森在时空意义上区分了自然和历史。在自然和空间中,事物是静止的,可通过概念被概括,但在历史和时间中,事物最大的特征是流变,每一事件都是独特的,无法通过某一普遍概念概括。由此,德罗伊森得出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与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的差异——“根据人类思想的对象和性质,3种可能的科学方法(wissenschaftlichen):神学或哲学的、物理的、历史的,其本质是:意识(erkennen)、表达(erklären)、理解(verstehen)”[6]11。
在德罗伊森看来,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是“理解”,这是其区分性的标准。实际上,德罗伊森关于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历史知识理论》之前已初步建构了(3)如尼佩尔认为,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与同时期的《普鲁士政治史》交相呼应,是后者的副产品。换言之,为了使《普鲁士政治史》中的观点更能站住脚,德罗伊森进行理论建构和补充。参见胡昌智.译介德罗伊森书评:《提升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J].台大历史学报,2013(51):187-188.。德罗伊森关于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神学哲学的讨论更早出现在书评《提升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中。1859年,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HistoryofCivilisationinEngland)德文版出版,德罗伊森在《史学杂志》上发表书评。书评中,德罗伊森批判了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他说:“一位法国研究人员针对这些学问的工作的描述,一语中的,他有个句子经常被引述:‘只要能把一个与有生命力相关的现象纳入物理的范畴,它就是科学领域里一项新征服之举’……这样的看法已经广为接受,但却令人忧心……人类其他领域的知识都必须先把生命力的现象纳入物理的范畴,才能成为科学的知识吗?”[7]
为了反驳以自然科学的方式研究人文科学,德罗伊森提出“历史科学”[7]。历史科学不同于数学和物理学,具有独特性,即理解。对于“理解”这个概念,德罗伊森提出一个独特的限定性定语,即“探索的理解”。伽达默尔指出,正是因为探索的理解,使德罗伊森的方法论不仅摆脱了艺术的完美理想,更与自然科学脱离关系[8]278-279。
在德罗伊森看来,自然科学同样是不断进行探索的,但自然科学的探索是可重复性的,探索者不断探索自然领域,获得普遍意义上的方法,从而现象重复性出现。同时,由于不断进行研究和探索,“科学被设想为进入未知领域就越多”[8]278-279。人文科学的探索有别于自然科学正是在此,“这里一定有另一种无限性不同于未知世界的无限性”[8]278-279。德罗伊森给予人文科学的路径是不断探索,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自我给予性,探索性的理解意味着除了探索就不能得出别的结论。人文科学的探索是探索历史中的感性存在物,而并非抽象化的经验,人们在历史的无限性中,只能不断地探索历史流传物对当下的影响,从而在一个新的理解基础上继续理解、探索精神现象。
虽然德罗伊森把人文科学的方法定义为无尽的探索,但依然不可避免地回到了方法论必须面对的问题,即普遍化的真理如何可能?如果探索本身是无尽的,那么对过去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会因为探索而产生不同的观念,因此,价值成为相对的标准,而不是永恒的真理。为了填补开放性探索导致的真理相对化,德罗伊森最终把人文科学的探索旨归于一种直接的终极性,即上帝。1829年,德罗伊森在一封信中声称:“经验知识的对应物不是玄思(speculation),而是绝对知识,即只属于上帝的知识。人类的探索可以发现历史中的规律(law),但不能发现规律之规律(lawoflaws),即上帝。”[9]28他确信没有上帝的意志,“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下来”[9]29。德罗伊森最终把探索的研究所面对的人文现象看作“那不是光,却要为光作见证”[6]37,而光与真理本身属于永恒的上帝。这也使人文科学方法论最终陷入对恒定不变事物的追求,德罗伊森的上帝,依然是形而上学的上帝,他内心葆有一种对恒定不变的事物的渴望。此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发展中,虽然以精神性和生命特质区别于自然科学,但对永恒的稳定真理孜孜以求,这就使人文科学的真理意识被禁锢在单一自我意识之中。人文科学的真理不能只停滞于对属人意识的探索上,而要承认绝对化的他者,与他者共同参与无限敞开的真理。
3 神秘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与敞开
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以“理解”区分于自然科学的“说明”无疑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次进展,但没有放弃对人文科学稳定真理性的追求。在祈求获得稳固真理的方法论意识中,隐含人自身的权力意志。人通过理性建构一切,同化一切,对对象的理解是同化性的理解,力图把他者纳入自我意识,理解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永恒价值的踪迹。对价值的追求使人不再谦卑,而是一味地沉溺于自我的伟大。这也使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再次滑向自然科学,人们坚信,事物之间具有确定无疑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必然会被人的理性所认识。20世纪以来,这种对人文科学的理性考量愈来愈明显,如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仿照语言学,把文本拆解成浅层和深层的不同构架,由小单元构成大单元。各个单元不是他在的经验,只是可被拆解的意义零件,它们共同构成某种永恒不变的原则,即规律的可得性。在追求自我理性的传统权威中,另一种方法论的要求被逐渐关注,那就是感性的经验方法和对观念研究的拒绝,对洞见、智慧和穿透性的瞬间感悟,即神秘主义的方法论[10]10。
神秘主义的方法论并不是在20世纪以来价值失落和上帝已死的语境中才被提及的,实际上它有着极为古老的源流。在罗素看来,追求形而上学真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的,另一种是神秘主义的[10]3。神秘主义(Mysticism)起源于希腊语“μυω”,意思是“我隐藏”,是“相信洞见、反对零散的分析知识:它们相信一种智慧的、突然的、穿透性的及强制性的方式……所有能专注于一种内在的强烈感情的人,都间或经历了那种奇特的关于普通对象的非实在性感受……怀疑普通知识,并为接纳一种看似更高级的智慧扫清障碍,许多熟悉这种否定性经验的人并没有超越它,但对神秘主义者来说,它只是通往一个更广阔世界的入口”[10]32-33。罗素对神秘主义的界定点明了这种方法论的特点,即对理性中心的放弃和对无法言说的超越性经验否定式的回应。这也从世俗性的人的角度转移到他者的角度,要求人不再关注仅与自我有关的世俗真理,而是参与普遍的宗教情感。
神秘经验涉及对隐藏性真理的直觉理解与认识。拉尔森(Larson)认为:“神秘体验是对存在意义的直观理解和实现。”[11]144神秘主义认为,存在、真理、实体等努力要去理解的概念,是无法言说的,只能通过沉默来言说。狄奥尼修斯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无言的方法论,在《神秘神学》的开篇,他连用3个“超”(hyper-)修饰上帝,这一结构在一切的言说和本质之外,于是从有界转向无界,从肯定转向否定。狄奥尼修斯进一步探讨了语言在面对真理时的局限:“它是超出心灵的心灵,超出言说的言道,它不能由任何言谈……所理解。”[12]3狄奥尼修斯深感言语的贫瘠,只要开口言说,就会意识到真理的缺席。因此,他采取一种拒绝言说的方式,只有不言说,才能保留对隐藏的、无法到达的本质的神秘期待和自我对他者的谦卑。上帝象征永恒的、无法通达的真理,面对绝对化的存在时,神秘主义要求人们恢复真理的绝对他性,拒绝理性言说的框定,这在后现代价值失落的语境中呈现了更为重要的方法论特质。
神秘主义呈现的否定性方法论,恰恰是解构主义最终的旨归。随着价值的失落,理性意义为中心的方法论成为虚假的形而上学,而解构主义正是为了拆解具有确定价值的世界。德里达这样描述解构主义的方法:“解构分析只有在某种力量败北之后,才能够变得可能,这使得它不过是对一种已经成型的和已经构筑的已经创立的东西反省,因而它注定是有历史的、末世的和黄昏的。”[13]42而学者对解构方法的诟病很大程度上也基于此,解构只意味着对成型事物的不断拆解,而不解答拆解后的出路。艾布拉姆斯在《解构的天使》中指出解构主义使得文本的阐释成为一种虚无主义。他把德里达的文本解读看作一个封闭的回音室,意义被降格为无休止的符号滑动[14]139。艾布拉姆斯的讨论点明了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即放弃价值观念,追求无中心、无差异[15]367。但解构主义对价值观念的放弃并非是虚无的享乐主义,相反地,它是对当下社会极为严肃的思考。解构本身并不意味彻底的毁灭,而是从肯定走向否定的过程,解构意味着从普世化的意义失落中拆解人为的意义,面对他者,以拒绝的方式与他者共同参与开放的意义。因此,解构的方法并不是完全的放弃意义,而是毫无期望地等待神秘意义或形而上实体的突然来临,解构主义不承诺解读,这意味着开放性、事件化,由此形成面对未来的勇气。
在德里达看来,对人文科学理论性方法的建构陷入了“视觉中心主义”。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追溯了“理论(theory)”的词根“theoria”,其原意是“看”。因此,“看”也被德里达称作“理论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theoria)[16]86。“光”与“看”是西方理论的古老传统,“自柏拉图以来,无论是从可感知的光还是从可以理解的太阳发出的光,据说是所有存在的条件”[17]47,由此,“通过光,世界才会被给予,被领会”[17]49。所有的理论(theory)都处于“看”的阴影(4)在“看”的光照下有阴影,是因为在德里达看来:“正如人们经常注意到的那样,光的核心是黑色的。”参见JACQES D.Writing and difference[M].Chicago: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86.德里达把光与暗的关系理解为一体的,这已然揭示纯粹理性之光对视觉造成的“盲点”。下,只有通过光的充盈,人们才能看到。然而,以理性之光探寻真理的方法,在德里达看来,恰恰揭示了理性的盲点。在《盲者回忆录》(MemoirsoftheBlind)中,德里达描绘了视线的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上的看,人们不仅通过眼睛看外在的事物,还会借助望远镜、眼镜、照相机等工具来看,这种看是机械的看。第二层次是理性的看,但这种看有局限性,即永远只能凝视一处,而除此之外的地方陷入了晦暗。“我们人类越是洞见可能越是盲目,因为我们总是集中在一点上而忽视了其他的。”[18]这种看造成了自我的盲视,尽管看的那一点被理性之光所充盈,但看之外的他者隐匿在不可见处。因此,德里达认为,对理论的构建一直在追求永恒不变的“一”,强调对世俗意义的构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只见自我的盲视,他给出了“看”的最后一种,也是唯一的可能,即盲人的视线。“就像所有的盲人一样,他们必须前进,前进或承诺自己,也就是说,暴露自己,在空间中奔跑,就像在冒险。他们对空间感到忧虑,他们用自己摸索、徘徊的手来理解它,他们以一种既谨慎又大胆的方式在这个空间中作画,他们计算,他们依靠无形的东西。看来,这些盲人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在绝对的流浪中迷失自己……这些盲人在他们看不见、再也看不见或还看不见的地方探索和寻求预见。盲人的空间总是把这三种时态和记忆的时间结合在一起。但却是同时的。”[19]17
盲者的视线意味着拒绝观看的看,这看似是悖论,但揭示了某种神秘的感性经验。正如德里达所言:“去你无法过去的地方,去那你无有可能到达的地方,确实,这是来来去去唯一的路径。”[20]325盲者的视线并非是对观看的逃避,而是对理性之光同化的拒绝,对内部逻辑框架的挑战,对自我理性建构的拆解。当我们以主体性的眼光去观看时,总期待获得同等的价值兑换,因此,看使他者被自我的价值同化,成为看的回应。被要求的回应限制了我们自身,交换的逻辑让人类遁入一种对他者的全然遗弃,我们所观看的,不是客体,而是在我们眼中应该被给予某种期望的客体。在看的逻辑中,人们越陷越深,却无法追求到真理,只能在上帝已死的场域下委顿地承认真理已然消失。
因此,唯一的方法是放弃以理性之光观看真理并诠释真理,以盲者的视线在拒绝观看中观看,承认真理的绝对他性,并参与真理。对绝对事物的观看又非仅仅是向其敞开,这是一场相互(interactive)的观看,在盲者的视线中,观看不是在观看,也并非建构,唯一的方法是透过观看本身去感受“我”与“你”的互动。
4 结束语
正如狄尔泰所言:“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人文科学注重对事物的经验化理解,注重过去发生事件对现在的意义。但人们对事物的探寻从神圣转移到世俗之后,更注重已研究的与自身利害攸关的事物,很少关照自我以外的他者。因此,所有客体都成为人对自我认识的未完成态,它们一一被理性之光照亮,被人以分析的方式理解(verstehen),尽管理解是感性的,但理解却只被限定在与人相关的事实之中。理性方法上的成功与进步使得人在另一种认识上是缺乏的,“过分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丧失生命”[10]32-33,因为对自身生命过度的关照,使其丧失了对其他事物本源上的感知,生命丧失了许多给予其最高价值的事物,而最为显著的就是他者的屈从。因此,对人文科学真理的追寻或许可以转向另一种可能,即不把自身的善恶意识强加于他者的方法,不追求人的最高善的实施,而是参与外部善。放弃对自身永恒真理的建构,从肯定性的逻辑定义到否定性的开放,解构主义致力于的方法论正是另一种可能,即对自然科学式的概念性追寻的拒绝和对真理的敞开性的参与。
“进化论尽管求助于特殊的科学的事实,但并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哲学,这既因为……它对伦理的过分关注,也因为它对我们的世俗关切及命运有一种压倒性的兴趣,一门真正的科学的哲学将是更谦恭的。”[10]32-33
进化论象征着科学,以理性为中心的科学方法运用到哲学时,因为过于注重属人的理性而无法探寻真正可能的真理形态,只是一味地以人自身的意志框定绝对的可能,也就框定了人的关注视线——他只能关注他的眼睛所看到的事物,而对眼睛以外的他者采取漠视。当人文科学从自我中心的方法走出,并且与他者共同参与永恒的剧目时,真理之路才有可能彰显。在理解中拒绝理性的观看,以盲者的视线看向空无,从而也就看向外在于自我的他者。理性之光的消失,意味着放弃同质化他者的意图,他者并不是“首先作为他我(alterego)的组成部分,即另一个自我”[21]637,而是完全外在于我的存在,因此,人文科学的方法更多体现于共同参与真理的过程,在不断地探索中,我的视域与他者的视域相融合,从而走向无限展开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