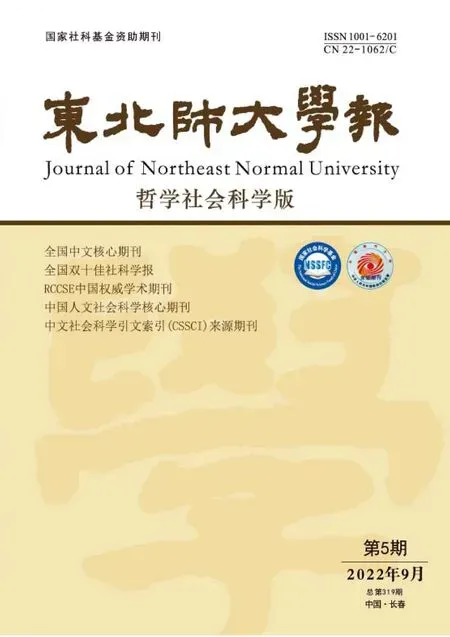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面容与爱欲:一种列维纳斯式解读
2023-01-04王嘉军
王 嘉 军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出生于沙俄统治区,从小浸淫于俄国文化的列维纳斯,深受俄国文学的影响。他坦承:正是俄国文学向他揭示了哲学的本质性问题(1)列维纳斯:《脸的不对称性:列维纳斯与荷兰电视台记者弗朗斯·居维的对话》,张尧均译,见于高宣扬主编:《法兰西思想评论》第三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在所有俄国文学大师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列维纳斯谈论最多,恐怕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他曾说道,“我们对于悲怆的品味,我们的感性,被基督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滋养”(2)Emmanuel Lévinas,“Difficile liberté”,Paris:Albin Michel,1976,pp.105.。在列维纳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谈论和引用中,主要涉及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这两个文本也是研究二者思想关系时被讨论最多的文本。本文试图从《白痴》这部作品中,通过“面容”和“爱欲”等概念,揭示列维纳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上的合流和共振。
一、面容的召唤
《白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命名为“面容的故事”,面容总是在小说最关键的地方闪现,决定了小说的走向,也呈现了小说最为深刻的伦理和神学蕴意。各种不同的面容环绕着这部小说,形成了神圣的光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圣像和面容是很难分开的,几乎所有圣像的灵魂都在于面容,神性的光芒也总是从面容中射出,而反过来说,陀氏也时常是以一种几近描绘圣像的态度来刻画小说中主要人物的面容的。“陀氏多次以面孔(oбpaз)来指代圣像画(икона)中圣人的图像。”(3)俞航:《俄罗斯东正教圣像学与现代性——兼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圣像学的现代性反思》,《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51页。面容和圣像在这里都代表了陀翁对人和人性的具体刻画,以及其中透露出的精神性和神圣性。在《白痴》中,娜斯塔霞的面容对于公爵来说就具有这种圣像般的魔力。
在小说中,当阿格拉雅带着即将与她成婚的白痴梅诗金公爵,去与她的“情敌”娜斯塔霞“开战”,并对她进行言语羞辱时,正是娜斯塔霞的面容让公爵做出了放弃阿格拉雅,转而与娜斯塔霞结婚的决定。书中如此描写了娜斯塔霞在遭到阿格拉雅的侮辱后极端愤怒和无助的面容,及其带给公爵的冲击:“他只看到自己眼前是一张失去理智、不顾一切的脸,有一次他曾向阿格拉雅透露,看到这样的脸他的心就像‘给永远刺穿了’一般。”(4)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644页。后来,公爵在与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的对话中回顾了当时的情景和娜斯塔霞的面容带给他的震撼:
“您不知道,那天当她们俩面对面站着的时候,我看到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脸上的表情,实在受不了……您不知道,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他神秘地压低嗓门说,“……我实在不忍看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的脸……刚才您谈到在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家举行的晚会时说得对,但是还有一点您漏掉了,因为您不晓得:当时我望着她的脸!那天中午时分我从照片上看到就老大不忍……例如薇拉·列别杰娃的眼睛就完全不像她那样;我害怕看她的脸!”他十分恐惧地附加说。(5)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55页。
正如公爵在上文中所交代的,实际上,甚至在见到娜斯塔霞的真人之前,他就被娜斯塔霞的面容所打动了。这种打动不只是因为娜斯塔霞绝世独立的美貌,更是因为娜斯塔霞的面容唤起了公爵的怜悯。“这张美得异乎寻常而且另外还有其不同凡响处的脸,现在使他更吃惊了。这张脸仿佛蕴含着无比的傲慢和轻蔑,差不多是憎恨,同时又有一种信赖的表情,一种天真得出奇的东西。如此鲜明的对比令人瞧着这面庞甚至会产生某种同情。”(6)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91页。娜斯塔霞的面容是一种召唤,召唤公爵不得不去担负“为她”的责任。公爵当着众人对初次见面的娜斯塔霞说道:“不久前我看到您的照片,我好像认出了一张熟悉的脸。我立刻觉得,您似乎曾经召唤过我……”(7)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191页。正是在这种责任的召唤下,公爵才做出了后来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毅然向这位才见了两三面的女士求婚。因为他必须将娜斯塔霞从她不情愿或对她有害的“婚约”中解救出来——加尼亚娶娜斯塔霞的企图更多基于利益考量和报复心理,而罗果仁虽然挚爱着娜斯塔霞,然而公爵早已看出这种强烈的爱情会使得二人都陷入疯狂和毁灭。
娜斯塔霞的面容与公爵的关系,几乎与列维纳斯对“面容”的阐释完美契合。在列维纳斯那里,面容就是“我”与他者之间首要的话语,换言之,“我”与他者之间的伦理话语是由面容所开启的。面容以其赤裸和真诚首先把他者呈送给“我”,而这种赤裸,以及赤裸显现出来的脆弱,旋即也就唤起了“我”的责任——“我”必须要为他者负责。面容显现的不是他者的景观,而是他者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既是对“我”责任的召唤,也是对“我”的命令,使“我”必须担负这一为他者的责任。面容以不可回避的目光揣度“我”、穿透“我”,使“我”必须去回应它。列维纳斯说道:
这恳求和要求着的目光——它只是因为要求着才恳求着——这因为有权得到一切才被剥夺一切的目光,这由人们通过给予而承认(一如“人们通过给出事物而质疑事物”)的目光——这目光恰恰是作为面容的面容的临显。面容的赤裸是贫乏。承认他人,就是承认饥饿。承认他人——就是给予。但这是给予主人,给予主宰者,给予这样一个人:我将之作为位于高处的“您”(vous)来接近。(8)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1页。
因此,他人的面容正是通过那一恳求的目光而显现的,它所显现的是他人的赤裸、脆弱和贫乏,他人就像一个毫无防备的受伤者甚至濒死者在恳求“我”的给予。这种给予不是施舍,而是奉献,由于“我”不得不为他人负责,不得逃离自己对他人的责任,“我”必须向他者尽义务,因此他人成了“我”的主宰者。在面容向“我”下达的命令面前,“我”无可逃遁,我们的关系就此变成了不对称的,“我”需要无尽地向他者负责,“我”需要向他人负责的总比他人要向“我”负责的更多。于是,面容和他人就处于比“我”更高的位置,“我”对他/她必须以“您”而不是“你”相称,因此也就不能进行“我—你”之间的平等对话。在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中,首要的主体间关系是回应、负责和义务,而非交谈和对话。在伦理学中,他者必然高于自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交互的,因为“我”无法用“我”对他者的要求来抵消他者对“我”的要求,“我”首先要做的总是回应他者的要求,而不是以“我的要求”去置换“他的要求”,否则这一切就成了交易,而不是伦理。
这种不对称性明显地体现在公爵对于娜斯塔霞的感情中。他对娜斯塔霞的“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娜斯塔霞疯狂的个性和行为,另外一方面更是由于他无法回应的召唤,也即为娜斯塔霞负责的要求。这一要求不是由娜斯塔霞主动发出的,恰恰相反,自尊心极强的娜斯塔霞一直抗拒公爵的怜悯和“施舍”,然而她的面容和眼光,却直接向公爵发出了伦理吁求。书中如此描述公爵对她的这种惧怕:“过了几天,公爵才想起在这昏头昏脑的几小时内,自己面前差不多一直出现她的眼睛、她的目光,自己耳畔不时可闻她的话语”(9)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36页。,“看到这样的脸他的心就像‘给永远刺穿了’一般”(10)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44页。。我们当然可以将公爵由此的不安理解为一种良心或良知的扰动,然而良心毕竟是内在的和自我的,而且是通过自省来运作的。良心时常暗含了一种“偿还性”,因此才有所谓的“良心发现”——似乎因为做错了某事才懊悔和自责。然而,公爵的不安却是由外部和他者的召唤所引起的,而不是经过自省而来的,这一不安也与公爵自己的行动毫无干系。公爵面对娜斯塔霞时的负罪感并非来自他自己的行为,而是来自一种无法回避,也无法完成的责任和义务。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不安甚至不源于某一个具体的事件,而仅仅源于一张面容,更准确地说,一张面容的照片所展现出来的悲伤。这里的关键在于,首先,“召唤”总是来自外部和他者的召唤,而不是来自倾听内部——良知的声音,不是自己召唤自己,就此伦理学也永远是由他者所触动和决定的,而不是主体的“良知”或“实践理性”所自决的;其次,这种召唤是感性的,感受性的,而不基于理性,也不具因果性,甚至也没有来由——似乎由于某种原因,“我”才要去回应他者,为他者负责。相反,召唤是没有缘由的,它可能是突然响起的,就像娜斯塔霞的面容突然向公爵显现一样。因此,尽管他还未熟识娜斯塔霞,就已经深刻感受到了不安和责任。所以,由面容所开启的为他者之责任是无条件的。
二、面容与伦理抉择之紧迫
这种无缘由和无条件的召唤和回应的要求,体现了一种紧迫性。由于紧迫,主体不得不回应,无从前思后想,无从进行理性的考量。列维纳斯伦理学的一大要义,就在于这种与他者遭遇的猝不及防和无可逃遁,这种紧迫性和例外性。面容临显的瞬间就将主体置入了这样一种不可回避的情境中。在此情境中,除了回应他者,别无选择。这种紧迫性从何而来呢?为何如此紧迫?我们必须把情境推至极端,才能理解它,这也是我们理解列维纳斯伦理学的必要方法。什么才是最大的紧迫性?对于一个脆弱的他者而言,这种紧迫性只能来自:他者会死,他者将死,因此,“我”必须马上营救他、回应他。对此,列维纳斯说道:“死亡,作为所有神秘之源,只在他人那里呈现;并且只有在他人那里,它才紧急地把我唤往我的最终的本质,唤往我的责任。”(11)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3页。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在娜斯塔霞和阿格拉雅两位他所爱的女人之间,公爵最后选择了娜斯塔霞。事后,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质问公爵道:“当时您的心在哪里,您的‘基督式’的心?当时您明明看到她的脸:她的痛苦难道比不上另一个女人,比不上您的那个拆散好事的女人?”(12)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54页。
确实,在阿格拉雅和娜斯塔霞的“战争”中,在公爵拒绝阿格拉雅这位即将与他成婚的小姐的那一刻,阿格拉雅也无比痛苦,她的面容反映了这一点:其时的公爵“在阿格拉雅可怕的目光下哑口无言。这目光流露出这么多的痛苦,同时又表现出无限的憎恨,致使公爵做了个绝望的动作,发出一声惊呼向她跑过去,但已经晚了!阿格拉雅对他的犹豫连一眨眼的工夫也不能忍受,所以用双手捂住面孔,叫了声:‘啊,我的上帝!’”(13)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44页。。对于这样一张同样痛苦且他所挚爱的面容,为何公爵不选择去回应呢?答案在公爵自己对于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的回答中已经揭晓了:“是的……是的,我应该……可是这样她(娜斯塔霞,笔者注)会死的!她会自杀的,您不了解她……”(14)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54页。“幸福?哦,不!我只不过结个婚罢了;她要这样;我结婚又算得了什么?我……反正这没有关系!要不然她一定会死的!”(15)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55页。相比阿格拉雅这位娇小姐而言,娜斯塔霞尽管性格强势,但她属于真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她经历了家破人亡,被人收养玩弄又遗弃,以及旁人的蔑视和舆论的指责等女性所难以承受的一切痛苦。公爵深知娜斯塔霞遭受了更多的苦难、更多的屈辱,也离“死”更近,因此他必须为她负责,为她的死负责。
列维纳斯曾指出,在面容所开启的伦理话语中,首要的话语就是“不可杀人”。你不可杀死他人,这是他人首要的诉求,也是首要的命令。面容也以此来对“我”进行审判:“冒犯是作为审判本身产生的,当它在他人的面容中注视着我、控诉着我的时候——他人的临显本身是由他人所承受的这种冒犯形成的,……当意志对死亡的害怕转化为对进行谋杀的害怕时,意志便处于上帝的审判之下。”(16)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34页。在列维纳斯这里,上帝的审判就是伦理的审判、他人的审判,他人在与“我”相遇的每一刻都向“我”提出伦理要求,并从而审判“我”。当然,这种审判最终又会转化为“我”对自己的审判,审判“我”自己是否达到了他者的要求。但归根结底,这种要求和审判是由他者首先发出的,而且审判的标准也在他者那里而不在“我”这里。所以,在“我”对自己的审判中,“我”其实永远也不能知晓是否达到了要求,就此审判就是无尽的,他者的要求也就是无穷的。这种审判是在他人面容的显现中“开庭”的,面容“注视着我,控诉着我”,控诉“我”的担当不够,控诉“我”的漠然,控诉“我”未尽的义务。这种控诉对于“我”的主体性形成了“冒犯”,而从更深层次来说,这种对“我”的“冒犯”又来自于“我”对他者的冒犯。这里的冒犯并不是说“我”真的在实际行动中冒犯了他人。在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中,“我”未对他者负责,或“我”对他者尽责不够,本身就已经是对他者的冒犯。
从更极端的角度来说,“我”的存在已经是对他人的冒犯。列维纳斯早年曾经说过,自由“不是自我否定,而正是凭借他人的相异性,让自身的存在获得‘宽恕’(pardonner)”(17)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王恒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这样一来,也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这是一种伦理的自由、承担的自由、负责的自由、赎罪的自由、艰难的自由。回到小说中,公爵显然感受到了对娜斯塔霞的冒犯,因为他不能承担对于娜斯塔霞的责任,不能“解救”娜斯塔霞。由于娜斯塔霞的“疯狂”,他很多时候选择的是逃避娜斯塔霞,逃避他不得不尽的责任。然而,在面对可能会使得娜斯塔霞死去的选择时,他意识到了自己不仅仅是不能承担对娜斯塔霞的责任,还面临着谋杀她的可能。如果他因选择阿格拉雅而离弃娜斯塔霞,导致后者的自杀,那他的选择便无异于谋杀。因此,此时公爵的伦理意识就体现为上述列维纳斯所说的“对进行谋杀的害怕”,而此时的他和他的一切行为也就处于他者和上帝的审判之下。
不过,如果我们仅仅通过“面容”概念来解读《白痴》也是不充分的,因为“面容”在列维纳斯那里指向一切他人,指向他经常用来指涉他人和邻人的那些弱者,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穷人、陌生人、寡妇和孤儿”(18)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36页。。然而,《白痴》中的面容却首要地指向“爱人”。“我”与爱人的关系不只涉及伦理,还涉及爱欲,或者说这是一种作为爱欲的伦理。因此,我们要完整理解这部作品,除面容之外,还必须求助于列维纳斯对爱的阐述。通过列维纳斯的视角,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理解“爱”这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永恒的主题。这一主题在《白痴》中可能远比他的其他作品复杂。与《罪与罚》或《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以犯罪、破案、惩罚、赎罪等为主线不同,这部小说的主线就是爱情。在《白痴》中,主人公和其他人物也不停在问这个问题:什么是爱?公爵对娜斯塔霞的爱到底是爱还是怜悯?公爵对于娜斯塔霞和阿格拉雅的爱又是一样的吗?(19)莉莎·克纳普指出:小说中“这两位女性不仅代表着美的理想,而且代表着潜在的拯救力量。这是由她们名字的希腊语词源暗示出来的,阿格拉娅(Aglaia)的意思是‘灿烂’(radiance),娜斯塔霞(Anastasiia)的意思是‘复活’(resurrection)。因为这两个名字充满了象征意义(光明和复活)……所以人们期待着梅什金帮助这两位女性……他要使纳斯塔霞·弗利帕夫再生和复活,使阿格拉娅开始光辉灿烂的新生活。”(莉莎·克纳普:《根除惯性》,季广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遗憾的是,这两项任务梅诗金都没有达成,而且结局最终朝向其反面发展。
三、爱之两可性
在与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的对话中,公爵说到他对娜斯塔霞和阿格拉雅“两个人都爱”,叶甫盖尼转而嘲讽道:“阿格拉雅·伊万诺夫娜对您的爱是一个女人的爱,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灵魂。您可知道,我可怜的公爵:很可能,您既不爱这一个,也不爱那一个,从来也没有爱过!”(20)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56页。公爵对此答道:“我不知道……也许如此,也许如此……”(21)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57页。事后,叶甫盖尼暗中思忖:“他那么害怕而又那么爱的这张脸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要是没有阿格拉雅,他也许真的会死,那么,阿格拉雅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公爵何等爱她!哈哈!怎么能两个都爱?以两种不同的方法爱吗?这倒很有意思……可怜的白痴!”(22)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57页。
真的可能两个人都爱吗?或者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爱之方式吗?这一问题很接近于列维纳斯对“爱之两可性”的探讨。列维纳斯指出:“需要与欲望的同时性、色欲与超越的同时性,这种可明言与不可明言的相切,构成了爱欲的独特性;在这个意义上,爱欲性乃是卓越的歧义性。”(23)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45页。爱既是最为身体性的肉欲,又是最为精神性的爱欲,既是对他者的欲求,又是求之不得,既想占有他者,又是对于占有的超越。“没有什么比占有更远离爱欲的了。在对他人的占有中,只要他人占有我,我就占有他人;我同时是奴隶与主人。快感会在占有中消失。”(24)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57页。这里的“快感”特指的是情欲的快感,或者说性快感,是情欲之乐(volupté)。情欲的极乐正在处于一种既满足又不满足的状态,一旦需求满足、欲望不在,爱也就不再,所以在情欲之乐中,占有是不可能的,占有恰恰意味着这种快感的消失。柏拉图早就在《会饮篇》中说过,爱乃是贫乏神和丰富神的孩子,因此,爱既是富足,又是贫乏(25)列维纳斯的爱欲观,显然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不过他指出,遗憾的是,柏拉图并没有从这一特殊的爱欲概念出发来思考女性角色(参见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90页)。列维纳斯指出,“爱作为对超越者的享受——就其表达方式而言几乎是矛盾的”(26)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45页。,这种矛盾体现在:享受指向的是可以被自我所同化、占有者,例如“食物”,而他人,作为绝对的他者,作为超越者,恰恰是不可被同化和占有的,而在爱欲中,自我却想要去享受这种超越者,享受这种与超越者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一种歧义。“就他人来说,这种既显现为需要的对象同时又保持住他的他异性的可能性;或者换言之,(就自我来说)这种享受他人的可能性……构成了爱欲的独特性。”(27)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45页。这就是爱的两可性和歧义性,它也是《白痴》中反复回旋的主题。在《白痴》中,这种歧义体现在旁人对公爵之爱的质疑上,也体现在他对自己的反思上,更体现在公爵之爱与罗果仁之爱的对比上。
公爵心底里一直不能确定自己对娜斯塔霞的情感,他一直对旁人说,他不爱娜斯塔霞,而是怜悯娜斯塔霞。公爵的这一情感之谜,某种意义上反映的就是这一两可性。他不能区分爱和伦理,因此他对于娜斯塔霞的感情,到底是爱还是怜悯,才会令他困惑。在小说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公爵区分了情欲和怜悯两种“爱”,这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对他与罗果仁之对话的反思中:
难道罗果仁做不到光明磊落?他说自己不是像我那样爱她,说自己身上没有同情,“根本没有这种怜悯”。诚然,后来他又说:“也许你的怜悯比我的爱情更伟大,”——但他是在诽谤自己。罗果仁在读书,——这不是“怜悯”是什么,不是“怜悯”的起点是什么?单是桌上有这本书不是已经证明他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对她的态度吗?还有刚才他讲的那个故事。不,这比单纯的情欲要深刻得多。她的脸难道只能激起情欲?即便是这张脸,难道现在还能激起情欲?它激起的是痛苦,它把你整个灵魂紧紧揪住,它……一阵灼热的、令人肠断的回忆忽然在公爵心头掠过(28)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263—264页。。
在这里,脸/面容再次出现,而很显然,公爵认为面容激起的不是情欲,而是怜悯,是一种“把你整个灵魂紧紧揪住”的触动。这种触动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他者的召唤、要求和命令,及其对“我”的审判。但罗果仁对娜斯塔霞的爱更多的是一种情欲,至少他自己不承认除了情欲之外还有怜悯,而公爵却一直相信他本性中善良的部分。只可惜这种善良最终随着情欲的疯狂一起燃烧了,公爵说:“罗果仁在任何事情上只看到另外的原因,只看到情欲的原因!多么疯狂的妒忌!”(29)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264页。由于情欲过于激烈,由于妒忌,妒忌本质上来自于情欲中对他者之占有欲,罗果仁自己也陷入了疯狂,因此才向公爵拔刀相向,最终则杀害了娜斯塔霞。
反观公爵对娜斯塔霞的爱则完全不同,公爵如此分析自己对娜斯塔霞的爱:
而他——公爵——若以情欲去爱那个女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是残忍的、不人道的。对,正是如此!应该说,罗果仁是在诽谤自己,他有宽广的胸怀,既能受苦,又能同情。一旦他了解全部真情,一旦认识到那个受损害的、精神失常的女人有多么可怜,——那时难道他不会宽恕她,把旧账一笔勾销,忘掉自己所受的种种折磨?他难道不会成为她的仆人、兄长、朋友、天命!恻隐之心会使罗果仁自己明白过来、受到教育。恻隐之心是整个人类存在最主要的法则,可能也是唯一的法则。(30)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264页。
在这里,公爵已经断然否定了自己对于娜斯塔霞的爱是一种情欲。对于娜斯塔霞,情欲是不人道的,因为情欲指向的是占有和享受,而非悲悯和责任,而娜斯塔霞已经被这个世界过度地占有和损害过了。面对脆弱的“受损害的”“可怜的”娜斯塔霞,公爵认为对娜斯塔霞的爱应当是要成为“她的仆人、兄长、朋友、天命”。这呼应了列维纳斯对于爱的阐释,“爱指向他人,指向处在虚弱中的他人……爱,就是为他人而怕,就是对他人的虚弱施以援手”(31)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46页。。而在爱中,他人、爱人是以女性的形象显现的:“(女性)爱人的临显,与其温柔的支配方式(regime)合而为一。温柔的样式,在于一种极端的脆弱,在于一种可害性。……而在这种逃避中,他者是他异的,是陌异于世界的,陌异于那个对于它来说过于粗鲁和过于伤人的世界。”(32)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46页。娜斯塔霞不就是这一女性爱人吗?不就是那“虚弱中的他人”吗?她的面容正是“极端的脆弱”和“可害性”的临显,她一直陌异于这个世界,这个不断损害和侮辱她的世界。
娜斯塔霞是一位更悲惨也更勇敢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安娜的悲剧很大程度来自于她自己的爱情选择,而娜斯塔霞一直没有选择的权利。与此同时,娜斯塔霞也比安娜更加具有反抗意识,她以一种近乎自我亵渎的方式来反抗这个亵渎她的世界,这就是她的疯狂。然而,公爵深知,娜斯塔霞只不过以这样的方式加倍地惩罚自己,她以这样的方式来加深自己的负罪感,并从中获得一种自虐的乐趣。
她每时每刻都在大声疾呼,说她不承认自己有罪,她是人们的牺牲品,是一个淫棍和恶贼的牺牲品;但不管她向您说什么,要知道,她自己首先不相信她自己,相反,她凭着自己的整个良知相信她自己是……有罪的……您可知道她离开我逃跑的目的是什么?恰恰只是为了向我证明她是卑贱的……您可知道,这种不断意识到耻辱的心情对她来说也许包含着某种可怕的、反常的乐趣,就像是对某人进行报复。(33)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491—492页。
正是比别人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娜斯塔霞这种极端的脆弱和痛苦,因此公爵也比别人更为深刻地“爱”着娜斯塔霞。尽管公爵多次说他对娜斯塔霞所抱有的不是爱,而是怜悯,然而这真的不是爱吗?真爱所意味的不就是爱人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吗?而娜斯塔霞对于公爵不正是不可取代的吗?为了她,他甚至放弃了阿格拉雅。在《总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确实区分了由面容所开启的伦理和“超逾面容”的爱欲。所谓的“超逾面容”,指的是此时自我不仅仅服从于他者之面容所颁布的伦理命令,还试图接近他者、享受他者,并解蔽他者、亵渎他者。“亵渎”一词的含义在这里是中性的,它所指示的就是那一与他者不断接近、不断祛除他者(她者)的神秘性,甚至欲求看到和爱抚他者的“裸体”的过程。这在爱欲关系中既是一种冒犯,更是一种亲近。尽管这是一种不可解蔽的解蔽、不可亵渎的亵渎,因为他者之所以为他者就是由于她/他永远神秘,永远不可被把捉,从而也永远保持“贞洁”。所以,列维纳斯说道:
“你不应当进行谋杀”这一原则、面容的有所表示本身,看起来与爱欲所亵渎的并且昭示在温柔之女性状态中的神秘相对立。在面容中,他人表达出其卓越,表达出他由之下降的高的维度和神圣的维度。他的力量和权利在其柔和中显露出来。而女性状态的虚弱则激发起(人们)对于那在某种意义上尚未存在者的恻隐,激发起人们对于那在无耻中炫耀自己并且尽管炫耀却并没有揭示自己者的不敬,亦即对于那自我亵渎者的不敬。(34)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53页。
所以,在这里,列维纳斯其实区分了面容显现——说话,也就是伦理关系中的“神圣”状态。在其中,主体处于一种接受状态之下,他所接受的是他者之诫命和原则:“你不应当进行谋杀。”尽管这种诫命来自于面容所显现的他人之脆弱性,但这一接受状态却显现了他人的神圣而不可侵犯。与此相对,爱欲昭示的“温柔”状态,却与在面对面容时所处于的被动状态并不完全相同,这种状态更为主动。因为爱欲中昭示出的“温柔之女性状态中的神秘”,激起了主体对于他人(爱人)进行亵渎的欲望,一种对于他者的“不敬”,或者说这种神秘本身就是以不断亵渎却又不可亵渎的方式显现的。此时,他人并不是绝然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是,亵渎也不会完全抹杀他人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因此,列维纳斯紧接着又提醒我们:“但是不敬己以面容为前提。”(35)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53页。言下之意,爱情除了情欲、性欲之外,同时也是伦理的,否则所谓的亵渎或不敬,就会完全是占有性的,在其中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快感和“情欲之乐”。因为在这种绝对占有性的把捉中,他者只是供我满足私欲的工具,它并不神秘,不会激起“我”不断接近它的欲望,也不会显现出爱欲中那种既满足又不满足的歧义状态。
所以,爱欲并不与伦理绝缘,而且伦理恰恰是爱欲的前提。在更后期的作品中,列维纳斯几乎完全将爱与伦理之间的隔膜撕掉了,此时爱就是伦理。更准确地说,伦理的爱才是完美的爱,至高的爱。所以,他说:“责任是对他人的脸给我的律令——即无偿的爱的回应,他人的脸意味着我作为让渡自身者和被选者的独一性。”(36)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页“第二版前言”。可见,在这里,脸/面容所发出的律令,已经被列维纳斯视为“无偿的爱”,伦理这个时候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列维纳斯还说道:
我必须为他人负责,然而我在如此为他人负责时却不可期望着他人对我负责。这是一种并非相互关系的关系,是一种对邻人的爱、一种不带肉欲的对邻人的爱。(37)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10页“前言”。
责任并非一种冷冰冰的法律意义上的要求。这责任是对邻人的爱——那不带肉欲的爱——的全部凝重性。“爱”这个被用滥的词的原初示意就基于这对邻人的爱,各种形式的文学中对爱的升华和庸俗化也都基于这对邻人的爱。(38)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257页。
此时,爱已经“不带肉欲”,是对邻人无私的爱,是至高之爱,也是本质之爱,这种爱可以通达宗教和上帝。
毫无疑问,这种爱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常以“怜悯”和“恻隐”来描述这种至高的爱,不过按照列维纳斯的观点,以“回应”“责任”和“给予”等概念置换“恻隐”恐怕更为恰当,因为“恻隐”和“怜悯”还不足以形容公爵对娜斯塔霞的这种爱。“恻隐”和“怜悯”,也即同情,同情是由“我”所发出的,是要以己度人,或者与他者连接在一起,从而感同身受。然而,对于公爵而言,他恐怕永远不能真正对娜斯塔霞的痛苦感同身受,他的同情也不是由他所主动发出的,而是在看到娜斯塔霞的照片和面容的那一刹那,灵魂就被“攫住了”,就成了娜斯塔霞的人质,这里有一种列维纳斯所说的极致的被动性。这也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替代。替代不是同情,它不来自于一种主观或主动的意愿。在替代中,自我承担他者的受难和罪过并非基于一种自愿的选择、自我的决断,而是一种毫无主动性也无法拒绝的被拣选,被他者不断地纠缠(obsession)。列维纳斯本人明确论及了这种“爱”与“替代”的关系:
这是无肉欲之爱。超越是伦理性的,而主体性根本上并非“我思”([尽管]它乍看起来是),并非“先验统觉”的统一性,而以对他人负责的方式,是向他人的臣属。这个我是比一切被动性都更加被动的被动性,因为一上来它就是直接宾格(accusatif),就是从来不曾是主格的宾格的我(soi),就是受到了他人的控诉(accusation)的——尽管它并无过错。(这样的一个宾格的)我是他人的人质,在听到命令之前就已服从命令……(39)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114页。
从纯粹情欲的角度讲,公爵或许确实如叶甫盖尼所说,既不爱娜斯塔霞,也不爱阿格拉雅。公爵对于阿格拉雅的爱,更接近于常人。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爱更接近于一种“友爱”。按照公爵的自陈,他之所以给阿格拉雅写那封情书,是因为他在与娜斯塔霞那段互相煎熬和消耗的日子里想起了阿格拉雅,阿格拉雅让他感到了温暖。“情书?我的信是情书?这是一封极其恭敬的信,这封信是在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从我心中流出来的!当时我像回忆光明一般想起了您……我……”(40)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489页。这里的“回忆光明”呼应了阿格拉娅(Aglaia)名字的寓意“光明灿烂”。公爵在初次与阿格拉雅见面时就在众人面前盛赞了她的美,并且说她:“非常漂亮!”“几乎跟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一样,虽然容貌完全不一样!”(41)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88页。不过,对于公爵这一圣徒式的人物,我们也难说在这对美的颂赞中包含情欲。与此同时,我们也已经说过,他对于阿格拉雅的爱也不乏怜悯、责任和亏欠,只不过相比之下,公爵对娜斯塔霞肩负的责任更加沉重,也更加紧迫。实际上,公爵对于任何人都怀有这种责任,也怀有这种爱,这正是列维纳斯阐述的伦理主体之特质。公爵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遵照的是同样的训诫:“我们每一个人在所有的人面前都是有罪的,而我是最大的罪人”(42)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1页。——这是列维纳斯经常引用的一句话。阿格拉雅对于公爵的质问,显明地体现出了公爵的个性和伦理原则:“此地有些人甚至不配弯下腰去拣您刚才掉在地上的手绢儿……您为什么要贬低自己,把自己置于所有人之下?”(43)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390页。当公爵把自己置于所有人之下,公爵就已成为所有人的替代和人质。所以,公爵对娜斯塔霞的爱,才是列维纳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中最为纯粹的爱。在小说中,公爵也以这样的方式爱着可怜的贫穷少女玛丽,爱着已病入膏肓却不断挑衅世人的伊波利特,甚至爱着他的情敌——最终杀害了娜斯塔霞的罗果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