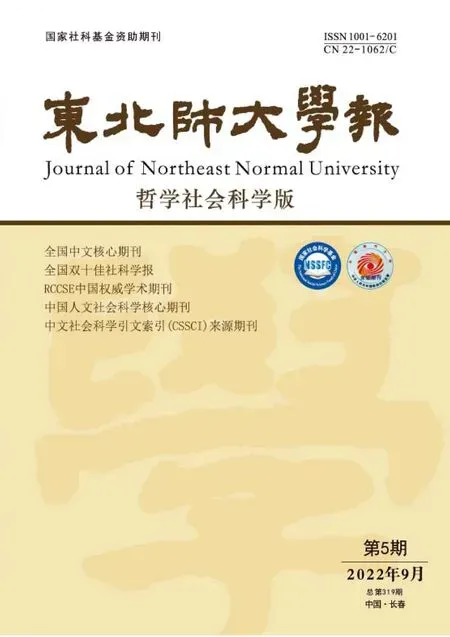文化线路视域下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研究
2023-01-04言唱
言 唱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全长近3 200公里,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大运河的开通和漕运的发展,不仅加速了人口、物资、信息和财富的流动,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塑造了独特的运河文化景观及沿线区域范围内特有的风俗习惯、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等,形成了一条汇集多种遗产类型、促进地方文化互动与跨区域传播的文化线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大运河文化线路的重要遗产单元。其形成和发展于运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和漕运的历史背景之中,在大运河文化线路的语境下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并呈现出整体价值与共性特征。
一、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并无统一标准。荀德麟强调,这部分非遗与运河之间“有着内生、发展、演变和传承的必然联系”(1)荀德麟:《京杭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序言第2页。。李永乐、杜文娟将“内容反映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和“形成、传播依赖于运河环境”(2)李永乐、杜文娟:《申遗视野下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及其旅游开发——以大运河江苏段为例》,《中国名城》2011年第10期。作为运河非遗的重要判断依据。田青则认为,“运河流经地区那些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节庆等都是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田青:《流布与融合——中国大运河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天下》2015年第15期。。大运河巨大的时空跨度、庞杂的遗产资源和开放式的文化体系,给大运河非遗的界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上述理解和阐释尽管角度不同,但非遗与运河的关系始终是定义的核心。
(一)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本文所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产生或流传于大运河流域,在沿线地区居民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形成并世代相传,且其形成、发展、传播、传承或演变受到运河本体及功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并反映着这种联系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作为大运河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大运河非遗既具备非遗的基本特征与核心要素,在分布与生存空间、形成和发展机制以及内在文化属性上又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首先,它们分布于大运河沿线区域的空间范围内,“在大运河流域广大民众中间世代相承”(4)顾希佳:《杭州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2页。;其次,它们的生成、发展或演化与运河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即由运河或漕运发展所衍生、塑造或推动,与运河及沿线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地域文化生态密不可分;最后,它们是大运河文化基因的载体与大运河精神内核的外化表现,在大运河文化线路的语境中彼此关联且相互作用。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不同于“大运河沿线(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大运河××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其所指称的并非分布于大运河沿线区域范围内的所有非遗。“大运河沿线区域”没有绝对的物理界限,非遗所属的空间范围也不是唯一的判断依据。第二,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分布在某个河段的具体非遗项目,而是大运河非遗这一整体。“运河”是大运河文化的核心动力要素(5)王加华、李燕:《眼光向下:大运河文化研究的一个视角》,《民俗研究》2021年第6期。。运河流域特有的空间格局、资源环境、聚落形态,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网络,人们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以及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诸要素共同构成了运河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生态。大运河非遗既受到运河生态的影响,又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界定大运河非遗的关键在于非遗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及其与运河生态和大运河文化线路之间的关联性,即是否受到运河环境与功能的影响,并承载和反映运河历史与文化。
(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延
大运河非遗种类丰富、形态多样,囊括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非遗类型(6)此处的非遗类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依据,参照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分类标准。。按照非遗与运河的关联层次及运河对非遗作用机制的差异,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圈层:
一是在大运河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与大运河本体及其原始功能直接关联的非遗。主要包括:因大运河开凿、疏浚、通航、维护和漕粮运输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系列工程技术与实践技能,如闸坝构筑、漕船制造、漕仓营建、船舶过闸、引水/分水/蓄水/泄洪技艺等;以大运河及其附属设施、沿线重要水域(水源地)和古镇、相关建筑遗迹、地方风物及历史人物等为主题或背景的民间文学,如高邮镇国寺塔的故事、隋炀帝传说、白英老人传说、天津漕丁谣、运河船工歌谣等。它们与大运河的形成、变迁及其原生性功用有直接渊源,是运河水工文化、航运文化、建筑文化的表现,最为鲜明地反映出大运河的内容要素与功能特征。
二是由大运河漕运及沿岸生活所派生的非遗。其中,既有主要流传于运河沿线,反映运河流域地域风貌与乡土人情的故事、传说和歌谣,如梁祝传说、白蛇传传说、吴歌、桐乡蚕歌等,也有展现河工、船工、渔民生活习惯与生产方式的音乐和舞蹈,如南闸民歌、故城运河传统架鼓、武城运河船工号子、通州运河龙灯等,还有与运河或漕运密切相关的各种风俗和节庆活动,如通州开漕节、东岳庙庙会、运河元宵灯会、含山轧蚕花等。它们记录了运河流域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沿岸居民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精神信仰及其发展变迁,是地方性传统与运河水文化、漕运文化、民俗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
三是在大运河交通或漕运的助推下产生或发展的非遗。依赖运河航运的便利条件而发展兴盛的传统美术、技艺与医药,因漕运带来的人口和物资流动而产生需求、获得发展动力的体育、杂技和游艺等皆属于此类。前者如杨柳青木版年画、湖笔制作技艺、临清贡砖烧制技艺等,后者如中幡、口技、戏法、吴桥杂技、临清肘捶等。运河的开通和水运的发达,是原料和成品运输以及手工匠人们南北迁移的物质基础;同时,运河码头、沿岸城镇作为往来人口、物资的中转地和集散地,为各类杂技表演和游艺娱乐提供了活动场所与生存空间,也增加了财物押运的需求,带动了当地武术运动的发展。这类非遗或因运河而生,或因运河而兴,又随运河的淤塞、改道、废弃而逐渐衰落,见证了运河变迁的历史进程。
四是在大运河沿线地区形成或发展,依托运河进行传播和传承的非遗。包括所有沿大运河传播和传承,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运河环境及漕运功能影响的工艺美术和手工技艺,如苏绣、玉雕、宋锦织造技艺、淮扬菜制作技艺,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形式,如京剧、昆曲、梆子戏、古琴艺术等。它们的形成与大运河并无必然联系,但运河为其提供了发展和传承的物质载体、社会环境与文化空间,推动了地方性艺术的对外传播,以及不同地区间知识技能与文化艺术的交流,在其发展、传播、传承、演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运河文化线路
从遗产形态、空间尺度和结构来看,大运河属于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可以理解为“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7)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初论:突破与压力》,《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相较于点状遗产,其空间跨度更大、所涉范围更广、包含的遗产种类更为多样、内涵层次也更为复杂。而大运河不仅仅是呈带状分布的景观廊道或点状遗产资源集合,更是具备特定主题与动态交流功能的文化线路。大运河文化线路所包含的非遗元素庞杂而分散。尽管它们与运河关联的方式和层次不同,但都反映着线路的主题与功能,并具备某些与运河空间环境和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特征。
(一)大运河文化线路的主题与功能
文化线路是线性遗产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也是遗产整体性保护利用的一种理念和方式。这一概念由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于1964年首次提出。根据《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线路宪章》的定义,文化线路是服务于特定、明确目的,以其特有的动态和历史功能性为特征的陆路、水路或其他类型交通线路,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产生于并反映人类的相互往来,以及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乃至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相互交流;②促进文化交流,并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反映出来;③基于线路所形成的历史关联和文化遗产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8)ICOMOS,“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 (2008)”,https://www:icomos:org/images/DOCUMENTS/Charters/culturalroutes_e:pdf,2022年3月28日。。文化线路分布于世界各地,表现为不同的尺度和形态,涉及多种功能类型和广泛的文化主题,如作为国际商贸通道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乳香之路,发挥交通运输功能的印度山区铁路,见证地中海农业文明的橄榄树之路,以及记录新艺术运动发展的新艺术运动网络等。
文化线路的认定基于五个要素:文脉或背景(Context)、内容(Content)、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Cross-cultural significance as a whole)、动态特征(Dynamic character)和环境(Setting)(9)ICOMOS,“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 (2008)”。。换言之,“文化线路”的理念强调线路的文化主题、历史意义和交流功能,且线路的整体价值大于个体价值之和:它不是历史城镇、文化景观等物质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无形的历史精神”(intangible historic spirit)将分散要素联结为一个整体(10)ICOMOS CIIC,“Madrid:Consider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cientific meeting on the conceptual and substantive independent of cultural routes in relation to cultural landscapes”,http://www:icomosciic:org/CIIC/MADRID2002_ingl:htm,2022年3月28日。;它所关注的不是遗产的静态分布,而是遗产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文化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动态演化。这一理念的运用能够将那些见证历史发展、体现文化多样性并共同构成线路完整性的分散的遗产项目整合到一个体系中加以表述和保护(11)吕舟:《文化线路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网络》,《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为粮食运输而修筑的重要交通线路和水利工程。它通达南北、辐射东西、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承担着物资集散和财富流动的核心使命,还加强了沿线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是大一统国家社会繁荣与政权稳固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体系内部循环的重要通道和中外交往的前沿地带。其核心功能是交通运输,而“漕运”以及由此而产生和发展的跨越时空的文化流动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构成了它的主题。在开凿至今2 5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孕育和滋养了众多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码头、桥梁、漕仓、钞关、名人故居、商会会馆,以及与运河相关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戏曲、手工艺和民俗等,作为重要的遗产单元和内容要素,反映并见证了运河的存在与漕运的兴衰。而运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不仅决定了大运河的物质属性与空间结构,也为文化线路的形成建立了基本框架,为丰富多样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大运河文化线路具备整体价值、系统功能和活态属性。流动的运河像一条巨大的绸带,将沿线的地理空间、景观和资源串联起来,并维系着人口和物质的交流与循环,成为推动信息、知识、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多向传递与融汇整合的文化走廊。而运河廊道、沿线文化景观及其周围环境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运河文化生态系统。运河流域的遗产群落呈链状分布,“具有共同的产生背景、关联要素和象征意义”(12)孙华:《论线性遗产的不同类型》,《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年第1期。,既丰富多样,又彼此连贯和统一,呈现出典型的线性特征。它们在运河的联系下产生跨地区的交流与互动,并随着时代变迁而赓续与演化,形成一条纵贯空间和时间的文化脉络。这种持续、动态的交流功能,使得大运河文化线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这也是它与静态的线性遗产最本质的差异。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审视大运河非遗,不仅有利于其整体文化意义的凸显和文脉的传承,而且能够充分展现文化的多元性以及不同文化间互动、融合及演变的动态特征和历史进程。
(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运河文化线路的关系
大运河作为一条文化线路,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还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是大运河非遗产生、发展和传承的空间环境与文化背景。非遗与运河之间密切而深刻的内在关联,赋予其独特的内涵与意义。
首先,大运河文化线路衍生与塑造了与运河直接相关的非遗形态,并通过这些要素实现多维度、多层次的延伸和扩展。“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13)吴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报》2018年2月5日。。运河的开凿与漕运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常年在运河上劳作的渔民、船民、河工和负责漕运事务的官吏,其生活习惯、工作方式和社会关系等皆与运河功能和特征相适应,一系列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实践技能、节日庆典等应“运”而生。沿河而居的人们,其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运河影响,并通过当地特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伴生的各种习俗和仪礼等表现出来。通州开漕节是为首批漕粮运抵通州而举行的大规模庆祝和祭祀活动。作为大运河文化线路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遗产元素,它既是漕运制度与运河祭祀信仰的直接反映,又是通州当地传统民俗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漕运的兴盛又催生和滋养了码头、集市、会馆、寺庙、商业和娱乐街区等功能众多、形态各异的文化空间,推动了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的发展,为表演艺术、手工技艺、宗教和民俗活动等提供了载体和容器。大运河文化线路为地域文化注入了“运河基因”,孕育了独具运河特色的文化表现形态。而大运河非遗在反映运河功能属性与环境特征的同时,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生动演绎和诠释着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充实和拓展了大运河文化线路的内容体系。
其次,大运河文化线路既促进了非遗的传播与传承,又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建构与完善自身的动态系统。运河的开通打破了地域隔阂,将江南地区的雕刻、丝织、制瓷技艺,音乐、舞蹈、戏曲艺术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又将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传播到运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并融汇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与建筑风格。戏班、手工匠人、杂技艺人、拳师和镖师等沿运河走南闯北,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经验、技能以及所传承的职业态度、艺术理念和行业精神播撒到新的土壤中。运河的流动加速了非遗向其他地区的转移和扩散,并促进了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为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充足的养分。而非遗自身改进与创新的需要,也促使其主动向外寻求扩展,进一步推动了运河沿线的商品流通、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运河非遗的代表性项目昆曲,正是以昆山为中心,沿运河向南北拓展并逐步扩散至全国,通过与不同方言、曲调和乐器的结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声腔系统和风格流派。运河交通的便利及盐运的兴盛为昆曲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沿线商会会馆所设的精美戏台,皆是其发展和传播的见证,充分印证了“商路即戏路”的说法。大运河文化线路的交流功能和动态特征,使非遗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而非遗跨越边界的流动与整合,不仅维系着运河文化的活态属性,也强化了大运河文化线路的系统动态性。
最后,大运河非遗既是大运河文化线路的一部分,又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二者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共同演化。一方面,大运河非遗是运河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命历程始终与大运河的变迁轨迹紧紧缠绕在一起。它们有的因运河的开通和漕运的兴盛而生机勃勃,尤其是与运河直接关联的知识与技能、风俗和礼仪,以及在运河交通的助推下传播的各种艺术形式等;也有的因运河的改道、废弃和漕运的衰落而日渐式微,如隋唐大运河永济渠、通济渠段,由于黄河泛滥、河道湮没、经济重心南移和海运的开辟而逐渐废弃,其流域范围内的传统技艺、艺术和民俗等失去了生存土壤,也随之衰退乃至消失。另一方面,大运河非遗既是大运河文化线路的细胞单元,也是地方文化的符号表征,它们所代表的地方性生活方式、思想传统、审美习惯等不断汇聚到文化线路之中,使大运河文化的基因信息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地方传统的融入和新的非遗形态的出现,更新了大运河文化的表现形式,拓展了运河文脉的层次与结构,衍生和延展出丰富的精神内涵。
三、文化线路语境中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特征
大运河非遗生存和发展于运河流域的地理空间和大运河文化线路的语境之中,由运河环境与水系格局所塑造,受到运河功能及漕运发展的影响,呈现出空间分布和价值属性上的整体性特征。
(一)线性分布:呈现文化景观的南北分异
大运河非遗以运河廊道为载体,既具有空间上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又呈现出显著的南北分异。大运河纵贯京、津、冀、豫、鲁、皖、苏、浙八个省市,穿越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六大文化地理单元。杭州的运河元宵灯会、扬州的剪纸、泾县的宣纸制作技艺、洛阳的宫灯、聊城的武术、吴桥的杂技、北京和天津的相声等,沿运河轴线南北延伸,绵延数千公里,形成连贯的线性文化景观,与运河空间共同构成一个流动的文化带。以运河主河道为中心形成的带状空间,“犹如一个剖面清晰地展示中国大地景观的南北分异”(14)俞孔坚、李迪华、李伟:《京杭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地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2期。。各种非物质文化景观也在地域分异规律的作用下,折射出运河流域的空间环境特征和文化群落差异,呈现着大运河文化的空间演变。扬州、苏州、北京的玉雕,苏州和嘉兴的端午习俗,以及沿线各地的运河船工号子和歌谣等,其工艺流程、仪式环节、艺术风格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和个性化表现,是同一非遗类型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独特叙事。而非遗的地域差异又构成了其彼此互补的前提。由于历史积淀、人文传统、区位条件和工商业基础的差异,南运河、会通河段以民间文学、生活性技艺以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居多,传统美术、生产性技艺和民俗则集中分布在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段,总体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非遗资源结构。而表演艺术类非遗则是运河沿线地域文化性格最鲜明的代表,从抒情、婉转、“死板活腔”到叙事、高亢、“死腔活板”,其语言、腔调、曲式和风格南北各异、互衬互补。
(二)流动开放:维系活态遗产的发展动力
大运河非遗以运河水系为依托,始终保持流动与开放,维系着遗产的活态属性与传承动力。大运河的流动性是其功能与价值的起点,也是大运河文化的生命力所在。运河水系连接与沟通了不同的地理区域,而漕运的发展又为地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发展空间。分布在沿线不同地区的非遗,因运河的流动而呈现出跨地域的相似性或相关性。妈祖信仰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又沿海河、北运河、南运河在河北、天津一带传播。流布于宁波、杭州、济宁等地的梁祝传说,沿运河传播的京剧、昆曲和各种地方戏曲等,都是大运河非遗流动性的生动体现。大运河与长城同为线性文化遗产,但后者是封闭性的军事屏障,而前者则是对外开放的文化通道。在流动与开放的环境中,非遗得以不断吸纳新的元素、拓展内涵与形式,并通过与异质文化的相互作用而发生转化与更新。正是大运河的功能属性,为非遗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根基与动力,使其在流变的过程中“随语境变换而消长盈虚,始终保持着伸缩张力与动态发展”(15)蔡丰明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图谱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21页。。京剧、木刻版画、制瓷和丝织技艺等在运河流域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博采众长,以开放的姿态融汇了不同地区的曲调和唱腔、风格和技法,演化出新的样态或衍生出不同分支和流派,于自我更新之中延续了生命活力。
(三)多元融合:支撑线路整体的跨文化意义
大运河非遗以运河功能为纽带,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融合性,以及线路的系统价值与跨文化意义。“多元统一”是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整体格局,也是大运河非遗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大运河非遗分布在大运河文化线路内部不同的亚生态圈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圈群结构”特征。它们既反映着与运河相关的水利、建筑、饮食、服饰、音乐、戏曲、工艺、纺织、冶炼、祭祀等文化类型,又体现着多种地方性传统和文化模式,显示出百花齐放的格局。沧州武术、临清肘捶等受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朴实、粗犷的风格,反映出勇武、信义的地域性格与精神传统;而昆曲、苏州评弹、江南丝竹等曲调优雅、唱腔细腻,蕴含着浪漫、诗性的文人传统,与江南的人居、饮食和服饰文化等“有着共同文化土壤与精神底蕴”(16)郑锦燕:《昆曲与明清江南文人生活》,苏州大学,2010年,第205页。。另一方面,多元的非遗形态又始终统一在大运河文化的体系之中,以运河为纽带产生互动与整合。大运河非遗既代表着不同的地域文化与城市性格,又“具有文化基因同源性”(17)霍艳虹:《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京杭大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天津大学,2017年,第145页。。它们在大运河文化线路的作用下,相互借鉴与吸收,彼此交织与渗透,产生多维交流与融合演进。桃花坞年画在题材、构图和风格上承袭了江南文人画的传统,“装饰意味和审美情趣共存”(18)王克祥:《“图说画映”——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叙事性研究》,《艺术百家》2016第6期。,将清雅、诗性的苏式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朱仙镇年画刻线苍劲有力、色彩夸张强烈、人物形象朴实粗犷,透露出中原地带浓郁的乡土气息。杨柳青镇位于南北交通要道,南方精致的纸张和颜料经由运河输送到北方,许多知名画师也沿运河北迁,漕运的发展更是促进了南北方刻绘技巧和表现风格的交流与融汇,使杨柳青年画呈现出形式多样、南北交融、雅俗共赏的特征。
四、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任何一种非遗形态,都有其“所依赖和因应的结构性环境”(19)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在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特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了地方独有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构成一个复杂的地域文化生态。大运河非遗在大运河文化线路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空间中生存与发展。其形成、发展、传承和演变都与运河两岸的地理环境、聚落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场域等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具有鲜明运河特色的文化生态系统。
(一)自然空间:非遗与运河流域的地理环境相适应
自然地理环境是形塑非遗的基本要素。大运河非遗生长并依存于运河流域特定的自然空间与地理环境之中,呈现出与其所处环境相适应的形貌特征与精神气韵。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平原广布、水网稠密,家家户户种桑养蚕,形成了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桐乡蚕歌、含山轧蚕花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形态——“蚕桑丝绸”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江南运河水系的发达,推动了丝织品的流动和蚕丝织造技艺的传播,滋养了包括传统技艺、民间歌谣、节俗活动、蚕神信仰等在内的整个蚕桑文化体系,使得与之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皆带有鲜明的江南水文化印记。地形与气候特征、自然资源禀赋、水系分布格局等塑造了运用沿岸居民的生活习惯与生产方式,并影响着他们的语言结构、社会观念、审美情趣和精神信仰,决定了运河文化景观的共性与个性表征。
(二)社会空间:非遗与运河两岸的市镇生活相渗透
非遗的传承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民众的共生关系中”(20)郭新茹、陈天宇、唐月民:《场景视域下大运河非遗生活性保护的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51期。,民间性与生活性是其活态属性的来源。大运河非遗根植于沿岸居民的生活、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地方民众和市镇生活构成了其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绍兴位于浙东古运河边、水网密布,民居多临水而建,乌篷船往来其间。傍水而居的生活习惯和以船代步的出行方式孕育出水乡社戏(21)水乡社戏是一种以戏剧表演为核心的民俗活动,普遍流行于绍兴地区,在承担高台教化任务的同时,发挥着重要的民间娱乐功能。社戏大致分为年规戏、庙会戏、平安戏、偿愿戏等几种类型,表演的剧种包括绍剧、越剧、新昌调腔、诸暨西路乱弹等。社戏的舞台分为庙台、祠堂台、河台(水台)、街台、草台等几种。其中,河台(水台)是一种后台在岸上、前台在水中的伸出式舞台,极具水乡特色。这一民俗活动形式。每逢社戏,村民们聚集在岸边或摇着乌篷船汇集在河面,呈现出水上、岸上同时观看演出的热闹景象,构成绍兴独有的文化景观。而网船会(22)网船会流行于浙江省嘉兴市王江泾镇,于每年清明、中秋和除夕举行三期。网船是苏南、浙北一带多用一种艏艉不足尺宽的柳叶舟,须夫妻协同作业、脚蹬手桨并用。清人顾禄《桐桥倚棹录》称:“每出操小舟,以丝结网,截流而渔,俗称‘丝网船’。”则是祭祀元代灭蝗将军刘承宗的水上庙会,兼具宗教和娱乐性质。庙会期间,长年漂泊在运河上的渔民和船民驾船汇聚于莲泗荡,进行祭祀、会亲、娱乐和商品交易,联络感情并发展社会关系。这一活动不仅是运河流域“蝗神信仰”的具体体现,也是沿岸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载体,具有突出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劳作、祭祀和娱乐都从运河水系延展开去。与运河相关的各种非遗形态,载录着群体记忆和生活细节,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获得了内蕴与生机。
(三)文化空间:非遗与运河沿线的文化场景相交织
文化空间作为一种“时空伴随的文化实践复合体”(23)萧放、席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与保护原则》,《文化遗产》2022年第1期。,能够奠定非遗的氛围基调,并丰富其精神意蕴。大运河非遗与运河沿线的各种文化空间生息与共,构成了大运河文化线路中的独特场景。首先,大运河非遗所处的文化空间,既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环境,也是其内涵表达和价值呈现的文化语境。庙会、灯会与沿岸的寺庙和商贸集市,织造、烧制技艺与临河分布的工坊和瓷(砖)窑,以及表演、游艺与商会会馆和娱乐场所等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共同讲述着运河故事,传递着运河记忆。其次,大运河非遗与同一文化空间中的各种文化符号相互勾连且彼此依存,在特定的文化场景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与完整的意义。在符号学理论的视角下,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符号体系,是“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24)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页。。运河流域的传说、歌谣、戏曲、手艺,与沿岸居民的语言、服饰、饮食,以及当地的村落景观、土产风物、乡风民情等,构成了基于特定背景的“非遗事象链”和“文化符号网”。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场景之中,非遗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生成和延续。扬州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兴盛的盐运培育了发达的工商业文化和深厚的休闲娱乐传统。扬州的剪纸和漆器、弹词和评话、淮扬菜和富春茶点、传统修脚术和理发技艺,以及茶馆、会馆、浴池、商业街区和老字号店铺等,与悠闲、安逸的扬州人—同构成扬州民俗和休闲文化的完整图景,凸显出“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地域特色与文化性格。
五、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文化属性
作为大运河文化线路的重要单元,大运河非遗具有典型的运河文化属性。大运河文化在巨大的时空跨度和深厚的历史积淀下形成和发展,是“以运河为载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线的众多地方性文化的集合”(25)连冬花:《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的路向考察》,《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是“运河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运河城市的兴起、文学艺术的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26)姜师立:《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分类研究》,《中国名城》2019年第2期。所形成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大运河非遗在展现地域民俗特征的同时,也载录着大运河的文化基因,延续着运河文脉,呈现出运河水文化与漕运文化、城市文化与地域文化、农业文化与工商业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核心价值,蕴含着中华文化丰富多元、交流融通、和谐共生之深刻内涵。
(一)运河水文化与漕运文化的生动体现
《管子·水地》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27)管仲:《管子》,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45页。大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四通八达、河海交融的格局。水是贯穿大运河发展进程的主线,也是大运河非遗生命活力的源头。运河流域文学艺术、手工技艺和风俗习惯的形成、发展和传播,皆离不开发达的运河水系。而“人水和谐”是“天人合一”理念在水文化领域的体现(28)史鸿文:《论中华水文化精髓的生成逻辑及其发展》,《中州学刊》2017年第5期。。运河上的渔民、船工和沿岸居民依赖水、利用水、信仰水,是对“人水和谐”自然观的最佳实践。水文化蕴含着“和谐”之思想和永续不竭的内在动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也是大运河精神的根脉和灵魂所在。而漕运是大运河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功能,漕运文化体现了大运河文化的本质属性。与运河直接关联的民间文学和传统技艺,以及由漕运所派生的各种音乐、舞蹈和民俗事象等,代表着以漕运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折射出与漕运相关的审美心理和精神信仰,是漕运文化最典型的表现。
(二)运河城市文化与地域文化的集合与互动
丰富多样的大运河非遗凝聚着运河沿线不同城市和地区的文化传统。首先,大运河非遗是彰显运河特色的城市文化符号,勾勒出运河城市的独特风貌。大运河形塑了周边城镇的空间格局,也推动了沿岸村落的城市化进程。扬州、苏州、淮安、临清、济宁等城市沿运河水陆网络扩展,“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29)刘士林:《大运河城市文化模式初探》,《中国名城》2011年第7期。。而与运河伴生的各种非物质文化景观,是运河文化与城市精神融合的产物。明清时期的临清,得益于发达的漕运而一跃成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都会。经由运河大量输往北京的临清贡砖,凝聚着临清古城的手工业传统和匠人精神,也见证了漕运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其次,大运河非遗既是地方性的重要表征,又融入并作用于大运河文化体系。竹马戏、赛龙舟、开河节与台儿庄南北交融的古镇风韵,园林(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评弹、缂丝技艺与精致典雅的苏式意趣,相声、时调、妈祖信俗、杨柳青年画与津门开放包容的商贸传统和五方杂处的码头文化……如同无数条支系汇入大运河的干流中,为大运河文脉注入了充满活力的城市因子和丰饶的地方记忆,对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的传统农耕文化形成了补充。
(三)运河农业文化与工商业文化的交融
大运河非遗见证了运河文明的发展变迁,既显现出农业文化的底色,又折射出商业和手工业文化的因子。一方面,大运河非遗根植于农业社会,是运河流域农业生产方式的见证和农耕文明的缩影。漕运的开通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农业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运输、灌溉、防洪等运河功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保障了农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稳定。运河流域的许多传说、歌舞和祭祀活动,都是围绕耕种、渔猎、气候、水源、岁时节令和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如微山湖传说、运河秧歌、径山茶宴等。另一方面,大运河非遗又蕴含着商业文化基因,反映出运河沿线的手工业和商贸传统。运河的贯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社会,但却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植入了平等交易、自由竞争、开放交流的种子。纺织、锻造、制瓷等传统技艺及其衍生出的行业文化,庙会、灯会、杂技、游艺等大型集会和休闲娱乐活动,以及妈祖信俗等民间信仰均反映出运河沿线手工业的兴盛和商贸的繁荣。而江南地区蚕桑丝绸的产业模式与格局,更是运河助推下农业、工业和商业文化集中显现与交汇融合的典型。
大运河的流动和漕运的发展,模糊乃至消弭了地理空间的界限,也打破了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壁垒——联通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文化圈,调和了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也在农业与工商业文化以及帝王、士人和市民文化之间形成了连接,建立起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阶层的“大运河文化共同体”。而这种文化的互动与整合,正是伴随各种文学、艺术、技术和实践形态的多维度交流,通过不同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而不断推进和深入的,不仅延续着运河文脉的精神内核,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循环更新与多元发展。
六、结 语
从文化线路的视角理解和阐释大运河非遗,能够充分体现其整体价值与共性特征,以及与运河之间的系统关联,从而揭示大运河非遗的独特内涵与意义。大运河非遗根植于运河生态,凝聚着运河精神,其生成、发展和演变代表了一种制度的具体化、一个知识体系的丰富化和一系列生活方式的渐进化。它们在承袭地域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延续着大运河的文脉和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反映出大运河文化线路的系统功能与活态属性。
新时代背景下的大运河,是一条鲜活的文化展示、教育科普和旅游休闲的文化线路。而大运河非遗的发掘、保护和利用,对于活化运河遗产、赓续运河文脉、实现大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以及强化沿线地区间的文化联系、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大运河非遗的保护、研究、阐释和利用,应当以大运河文化线路为背景和语境,“贯穿和编织起较全面完整的框架结构”(30)李麦产、王凌宇:《论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及活化保护与利用——以中国大运河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7期。,在展现非遗地域特色和文化个性的同时突出其不同于点状遗产的线性特征和跨文化的交流、互动与融合,并梳理非遗与大运河文化线路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内在关联,挖掘其所蕴藏的运河文化内涵与基因密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大运河非遗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的连接,实现其载体创新、功能延展和价值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