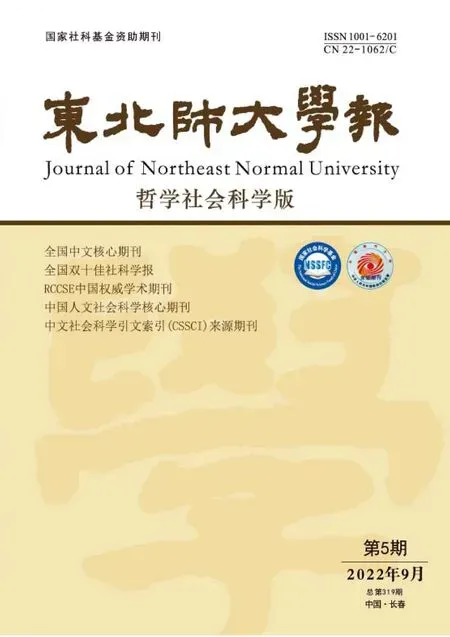人称与中国新诗审美的现代转型
2023-01-04倪贝贝
倪 贝 贝
(江汉大学 期刊社,湖北 武汉 430056)
纵观古诗到五四白话新诗的发展,中国诗歌经历了由含蓄隐晦到直白晓畅表达方式的转变,这其中,人称代词由隐到显的状态转变功不可没。得益于清末民初个体启蒙意识、科学思维模式及语言文化运动的促进,新诗里大量涌现出在古代传统人称和各类方言、外来词汇基础上改造衍生的人称代词。人称代词作为中国新诗词汇中的新元素,不仅是新诗内容与语言形式变革上的一种外在体现,其背后折射出的诗人个体意识更参与了新诗诗思建构的全过程,反映了诗歌创作观念和构思方式的现代转型。尽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批判和反思五四时期新诗的直白叙事,现代主义诗歌以多人称视角的迭变转换造成诗歌语义的复义朦胧倾向,但本质上仍是以现代汉语语法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审美范式调整,其叙事路径与古诗存在根本性生成差异。通过对人称代词与新诗的诗思建构及表意模式关系的探讨,可发掘人称代词在新诗审美功能现代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一、人称代词与新诗的诗思建构
人称代词首先参与了新诗观念的变革。五四以来,对自我个性的张扬引导新诗实现了由“无我”到“有我”、由“泯然众我”到“个性独我”的转变,诗歌风格特色化、诗歌主体人称的个性化成为诗人创作的重要目标。康白情认为,“‘我’就是宇宙底真宰。我想完成‘小我’以完成‘大我’”(1)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年,第41页。;陈梦家呼吁,诗人“要从灵感所激动的诗写出来,他要忠实于自己”(2)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册),第148—149页。。可见,在对现代新诗诗体形式的探索建构过程中,个体性自我已深植于诗人头脑之中。与此同时,人称代词作为诗人主体意识的外化形态,代表诗人在诗歌中发声,诗歌开始注重个性化抒情主体的多样化呈现。仅以个体第一人称“我”为例,从具体诗人的创作来看,既有“我的恋人的眼,/受我沉醉的顶礼”(戴望舒《三顶礼》)的忧郁型抒情人称,也有“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富于昂扬激情的奔放型主体形象,更不论其在不同诗歌情境中所产生的多重形态变奏。现代诗人针对人称代词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为人称代词作为新诗中的重要建构因素确立了正式身份。
人称代词贯穿了现代诗人诗意生成与建构始终。不同历史阶段语言文字的形成与发展,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及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诗人以其所处时代的标准化语言作为自身创作表达的基本工具,反观之,语言文字本身的句法思维构成模式及其内部所透射出的大众思维烙印,又在无形中影响甚至改造了诗人的诗思建构方式。个体人称的凸显打破了古诗长期以来隐藏主体的含混状态,使诗歌由务虚向写实的方向转化,促进了理性科学的现代诗思方式的形成。在此基础上,现代理性思维对严密逻辑性的追求,又促使诗人在诗歌构思上由传统的“字思维”完成了向现代汉语以严密的语法结构为特征的“句思维”转型(3)此处观点参考郭绍虞对传统汉语和西洋语言语法本质比较的论述,具体可见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前者善以词性的相互转化替代词汇本身的形态变化,可产生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相互之间多种词性转换与借用的可能性,句式大量省略非中心词却并不影响语义表述,对人称及虚词的留白有待于读者的自主性补足,故而形成以字词为平行单位相互黏连的“字思维”,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子夜吴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春夜喜雨》)诗句全由名、动、形等词组成,其中存在多处词类活用的现象,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严密,为读者往其中填充抒情主客体人称提供了空间。与之相异,在句法结构上更多借鉴西洋语法的现代汉语无法如古代汉语那般存在多处省略与空缺,对动词的看重致使其须与其他词汇产生关联来完成整个句式的表达。而在现代汉语语法规则里,引导谓语动词完成其行为动作的主体行为人多为名词和人称代词,由此形成以动词为核心、以名词或人称代词为主语和宾语构成“主语+谓语+宾语”为基本句式并向外部辐射扩展的“句思维”。在此思维模式的督导下,现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为人称代词预留了位置,并在主题内涵和形式表达上均得到体现。
人称代词蕴含了新诗表意的态度倾向。作为诗人寄托于诗中的行为动作主体和话语代言人,人称代词因直接指向诗歌抒情主客体,自身即被赋予了主体情感上的可言说性。对人称的差异性选择折射出诗人或抒情主体对诗中各种人物不同的情感态度,如:“妈妈醒了,/伊底心就会飞到我底船上来,/风浪惊痛了伊底心,/怕一夜伊也不想再睡了。”(应修人《小小儿的请求》)以“伊”指代诗中的母亲,投之以温柔怜爱之情。“得!就算咱拉车的倒霉了!/……/谢谢!挣您二斤杂货面儿!”(闻一多《天安门》)“咱”用于车夫自称,“您”表示车夫对乘客的尊称,以此体现二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此外,人称代词不同形态各有其自身所适用的语气系统,诗人对人称代词的选择无形中受具体诗歌语境的限制,反过来又凭借人称的语气功能推动诗歌语意的表达。试看以下诗例:“(你)口渴了么?——/井下有无量的清水;/便是冰块,/也可以烹作我们的好茶。”(刘半农《敲冰》)首句疑问语气中采用的是第二人称的零主语形式,被省略的人称“你”倘若换成“我”,无论是在句式本身还是诗歌上下文语境中都讲不通。“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闻一多《死水》)末句中的人称用“你”比“您”要合适,因为“‘您’后整体成分在语用上常具有听者[+受惠]的特征,或至少是中性、即不具有明显损益性的事象”(4)朱敏:《汉语人称与语气选择性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3页。。“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徐志摩《残诗》)其命令式的语气与“您”表敬称的用法产生矛盾,刻意营造出一种揶揄效果。当诗人对人称的选用超出其在现代汉语语法规定的语气功能之外时,讽刺调侃色彩便随之产生。
对比古诗对人称的有意屏蔽,人称代词的明确使新诗开始有着各自准确的定位想象,“我终能获得光明,因为有觉醒的‘自我’在”(5)郑伯奇:《会员通讯》,《少年中国》1920年第2卷第1期。。在张扬自我个性的前提要求下,诗歌不再是表现普遍性感受与经验的产物,而开始凸显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在对个体精神的呼吁下,人称代词在新诗中应时出现,使行为动作的施受人空缺被填补,挑破了以往欲语还羞的面纱,带来传统诗歌“物我合一”叙事策略的转变。由此,不同人/事物有了各自对应的指代人称,诗歌主客体的各自身份得以明朗化。我们读“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冯至《我是一条小河》),“黄昏时孩子们倦着睡着了,/后院月光下,静静的水声,/是母亲替他们在洗衣裳”(刘半农《母亲》),很容易便能厘清其中的“我”“你”“他们”等人称的意向所指。人称的凸显省略了传统诗歌借外部景物来传情达意的曲折过程,使诗歌话语叙述由“抒情主体—意象—抒情客体”的曲线表达转变为“抒情人称—抒情人称”的直陈对话模式,诗歌表义由含蓄朦胧转向清晰明确。
人称代词的直露式表达随之引发新诗审美范式的转变。大量人称代词的投入使用,使诗歌由以物象为主导的叙事传统转向以人为主导。同是写花,古诗表现为“花”意象的主动呈现:“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梅花》)以人称的消隐换取“人物相融”的空灵之美。而新诗却将之拟人化并与抒情主体产生对等性交流:“月月红在风中颤抖/我的心也伴着伊颤抖了。”(汪静之《月月红》)人称代词“我”与“伊”的情感互动,彰显抒情人称的主体性感受与情感体验。古诗含蓄敦厚、欲语还休的审美典范被外露张扬、强调有我的现代审美所取代。另外,现代诗人在诗歌中对人称代词的有意安排,使之融入了诗人或诗歌主体人称的理性观察与思考。如卞之琳在《睡车》中从“我”之视角进行俯视:“睡车,你载了一百个睡眠;/你同时还载了三十个失眠——/我就是一个,我开着眼睛,/撇下了身体的三个同厢客,/你们飞去了什么地方?”此时“我”的思维及视线脱离了作为失眠者的“我”的身体,居于高点来审视同厢客“你们”及“我”之肉体本身,人的理性意识的参与推动了诗歌富于逻辑性缜密思维的智性审美追求。
二、人称代词与新诗抒情模式的个性化
就大多数古诗而言,诗歌主人公并未主动站到台前,而多是隐藏在诗歌背后,企图以意象本身的感染力打动读者。与之相比,诗人将“我”之情感体验直面交付与读者,使诗歌的自我表现更为直观。在表述功能上,有了诗人之“我”与读者之“你”的对话交流,才使得诗歌中情绪由创作生成到书写传达过程的最终完成。多种人称代词进入新诗,使后者的个性化抒情主体得以全面凸显,诗人个体的情绪感受可借由多种抒情人称的叙述得以传递。同为赠别之作,古诗与新诗中抒情人称的表现及其情感传递路径大相径庭,古诗往往将“我”之惜别之情寄于景物之上,其情感传递的轨迹多呈现为诗人(潜在的“我”)——景物(显在的“它”)——对象人物(潜在的“你”或“他”)——读者(潜在的对话者)的长曲线单向传递。由此一来,诗中的人物皆处于隐身状态,取而代之的是景物的自主活跃表现。加上古人强烈的社会身份意识、对文学敦厚柔和的古典审美追求以及格律诗严格的平仄对仗性原则,导致人称代词在诗歌中被隐藏。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人在陈述个体情感时,习惯性地以比兴手法“顾左右而言他”:明明是要向抒情对话人倾诉离别之情,却只言“朝雨”“柳色”等景物,几乎不直呼“你”“我”,哪怕内心满蕴强烈的感情,也只是以“劝君更尽”来淡然道出。在这种力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和心境的要求下,古诗含蓄内敛、沉郁隐忍的诗歌风格由此生成。与此不同,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加上现代诗人力求对传统旧诗格律模式的颠覆,促使新诗乐于将多种抒情人称予以主动展现。同时,诗人在表达上将“说者”到“受者”之间的交互路径缩短,实现直接由抒情主体“我(们)”“咱/俺(们)”到抒情客体“你/你(们)”“他/她/它(们)”的短线或点对点式的直线传递。试看徐志摩《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穆旦《赠别》(一):“等你老了,独自对着炉火,/就会知道有一个灵魂也静静地,/他曾经爱你的变化无尽,/旅梦碎了,他爱你的愁绪纷纷。”殷夫《别了,哥哥》:“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上述现代诗中的抒情主客体的交互路径即分为:抒情主体“我”—抒情客体“康桥”(徐志摩《再别康桥》,这里的康桥并非诗人借景抒情之景物,而是直接与“我”产生互动交流并接受“我”之眷恋不舍之情的客体对象);抒情主体“他”—抒情客体“你”(穆旦《赠别》);抒情主体“我”—抒情客体“你”(殷夫《别了,哥哥》)。和古诗相比,新诗省略了抒情主客体之间的种种转述程序,而以更直接的方式将诗人个体内心感受主动陈列出来,直面显性的读者。据此,情感传递路径的变化带来了诗歌由曲折典雅的传统诗风向直白外露、倾泻奔放式的现代诗风的转变。
个性化抒情人称在新诗中的凸显,打破了古诗类型化的情感表达方式。诗人因此得以表现独特性的个体情感体验,是新诗在延续古诗“言情”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一大步(6)张凯成:《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2019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江汉学术》2020年第3期。。诗人通过对人称代词的自由选择和灵活处理,使其创作呈现与其他诗人迥异的个性化风格特征。同时,人称代词在不同诗作中的独特表现,又使诗人的创作风格趋于多元化。人称代词对新诗情境的有机构建推动了新诗独特情感体验方式的建立生成。现代语境对个体个性化的彰显,允许现代诗人在思维方式上摒弃传统的“趋同”倾向而开始转向“求异”思维的发展,鼓励现代诗人敢于在诗歌素材和形式表述上寻找异于他人的独特性。“真正的新诗,是诗人个人独到的经验,同时人人能得其传达。”(7)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陈均编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从不同诗人个体来看,出于各自创作表达的需要,现代诗人在人称词汇选择及排列组合方式上各有不同,同一题材下所作的诗歌也因此显现出诗人对事物的不同感受与独特情感体验。以初期白话诗人写月夜的诗歌题材为例:
明白干净的月光,
我不曾招呼他,
他却有时来照着我;
我不曾拒绝他,
他却慢慢的离开了我。
我和他有什么情分?
——沈尹默《月》(8)沈尹默:《月》,《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期。
窗外的闲月,
紧恋着窗内蜜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恼了,
他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
回头月也恼了,
一抽身儿就没了。
月倒没了,
相思倒觉着舍不得了。
——康白情《窗外》(9)康白情:《窗外》,《新潮》1919年第1卷第4期。
就诗歌主题表现而言,上面两首诗可谓极为相似,且语言的纯熟程度不分高下。但我们依然能判别出这是两个不同个性的诗人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两者对人称视角差异性选择及处理上。沈氏选用“我”和“他”两种人称:“我”即诗人本人或带有其情感意愿的抒情主体,“他”指代“月光”。此时,“我”和“他”均为诗中的动态角色,两者主动发生一场直面式对话演出给读者“你”观赏。至诗尾,主角之一——月光“他”淡出视线,仅留抒情主体“我”在舞台上向读者发问:“我和他有什么情分?”此时读者“你”代替月光“他”被拉进诗中参与这场表演评判,使诗歌染上戏剧化色彩。不同于沈诗,康氏以第三人称“他”来指代主体意象“闲月”,将主动权交付之,使传统“我”与“月”的对话模式转变为“闲月”与“相思”两个第三人称视角意象之间的交流,而诗人则处于旁观者位置来观察两者互动。值得玩味的是,“相思”是谁的相思呢?可能是诗人自身在诗中的内化形象“我”,也可能是诗人未曾明言的抒情人物“他/她”。主体情感对象化无形中增加了诗中抒情人称的数量,为诗歌带来了更多的玩味空间。
人称代词在新诗中表达路径的多重可能,促使诗人突破自身擅长的固定创作模式,开始主动尝试人称代词在其创作中的多种形态变形,带来诗歌风格由单一化向多面化的转变。如以新诗战将面貌出现在新诗史上的诗人郭沫若,尤其擅长通过人称代词的重叠连环使用,造成诗歌狂飙宣泄式的情感气势,以此形成独具五四激进个性的诗歌特色。其代表诗例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沤!”(《太阳礼赞》)人称“我”和“你”在诗句中的连绵铺陈和直面对话,使诗人的情绪如潮水般汹涌而出,几乎不给读者片刻喘息的间歇。然而,郭沫若诗作并非一味地自我叫嚣,其对人称代词的转换使用使其甚至出现了由狂放激昂向舒缓平和的转变。以《天上的市街》为例:“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虽然这首诗的主体人称依旧是“我”和“你”,但在表述上不再是“我”的炙热情感对“你”的直接倾诉与灌注,而转为“我—你”两者之间的平等探讨式对话。“我想”“你看”等“人称代词+动词”的短语化句式的运用,造成句式的缩短和语气的中断,使诗歌带有一种商讨性的语气。整首诗的情感表达因此柔和清浅,显现出与前述郭诗截然不同的艺术特色。
三、人称代词与新诗客观写实的叙事化
从新诗的题材内容来看,人称代词的凸显不仅扩大了诗歌的抒情表现功能,同时开拓了现代叙事诗的抒写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社会现实题材和新鲜事物的不断更新涌入,传统的诗歌抒情已经无法满足现代诗人对当下的书写需求,“‘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虽然表面上好像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可是在底层的新的文化运动的意义上,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10)茅盾:《叙事诗的前途》,见王永生:《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一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2页。。多种人称的出现打破了古诗“物我交融”、以物象代替人物发声的传统抒情言志套路,增强了诗歌中人物(事物)的相互对话性与叙事意味,扩大了新诗的题材范围和表达范畴。由此,诗歌“旨在言情”的诗学观念被打破,带有现代叙事意味的诗歌抒写模式开始被广泛纳入诗人的创作表达中,实现了对传统抒情诗占据诗坛主导地位的突破。
作为指向诗歌主体人物的语言符号,人称代词在新诗中的叙事性讲述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型:一是以第一人称作为主体人称对所述事件进行直接观察和评判。如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我吃着研了三番的白米的饭,/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以“我”的视线观察为出发点,诗歌事件的叙述者和经历者往往趋于合一状态,可使诗歌在叙述性讲述中随时穿插人物对所讲述事件的态度看法及情感评价,有利于诗歌书写模式在叙述、抒情和议论等之间灵活转换。二是以第二、三人称为主体或在诗中直接录入人物(事物)的对话。如卞之琳《古镇的梦》:“更夫在街上走,/一步又一步。/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哪一块石头高,/哪一家门户关得最严密。/‘三更了,你听哪,/毛儿的爸爸,/这小子吵的人睡不成觉,/老在梦里哭,/明天替他算算命吧?’”此时,叙述观察者“我”和事件中的人物处于分离状态,诗中发生的事件经由“我”的眼睛观察后被间接转述给读者,故能以一种旁观者的立场来对其中人物(事物)及整个事件的发展走向加以客观的整体把握和全面叙述。三是多人称交叉进行互动,使诗歌中出现类似小说的故事情节或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如俞平伯《鹞鹰吹醒了的》:“说你俩真是爱我!/不知随谁们底喜欢,/我却容易有了丈夫,这也还是爱我?/我不认得他,/谁叫我把全心去伴他?/我不爱他,也讨厌他,/谁把我当作娼妓般去媚他?”多个主体人称的背后隐含的是主体人物的连环动作行为,突出了新诗的叙事化倾向,造成了新诗由感性抒情化向客观写实化的转变。
就诗歌表达的语言工具来说,与传统古诗相比,现代新诗所用的“现代汉语似乎天生具有一种‘散文性’,它的连贯性、流动性使它更易于叙事和描述,而不是诗意的抒情……为适应现代语法逻辑严密的要求和出于单一明了、不生歧义的语义目的,现代汉语在句子结构上远较古典汉语复杂,增加了较多人称代词、连词和一些表示关系性、分析性的文字”(11)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我们读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会发现两句由六个平行意象组合而成,词汇与词汇之间缺少必要的语义黏连,其中的“人迹”是抒情主人公“我”的?还是别人留下后被“我”看到的?仅凭诗句所透露信息全然无法断定,只能依靠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行补足和理解。这正符合古诗推崇的空灵朦胧之美的标准。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的思维方式来对上述诗句加以转述,可表现为:“(我听见)鸡鸣,(知道天将破晓)(我抬头看见)茅店(上空的)月,(我低头看见我的[抒情主人公]/你的[对象化人物]/他的[不在场的对象化人物]/别人的[不确指对象化人物])人迹(留在)板桥(上),(因为桥上有)霜。”人物及意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瞬间清晰明朗,原诗混沌含糊的表达被缜密明晰的现代话语叙述所替代。由此可见,人称代词等词汇及现代表达方式的进入,填充了古汉语在古诗中刻意营造的留白之处,带来诗意的完整和逻辑上的严密。
人称代词在新诗中的凸显,使诗歌在表达过程中常出现如下情形:不同的人物主体在主体人称叙述时跳将出来,打乱或中断诗歌的单一化视角叙事,以插入自身对所述事件的看法。由此一来,诗歌的整体推进过程得到放缓,避免叙述走向自语式的抒情或独白。换言之,诗人在新诗中的情感表述,仅靠“我(们)……我(们)……我(们)……”口号式的呼喊是无法实现的,要想对读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需得“用事实说话”,在对事件客观冷静的叙述中无形地灌注自身见解,以哲理性或智性化的思维模式和语言叙述表现诗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如宗白华《小诗》:“生命的树上/雕了一枝花/谢落在我的怀里/我轻轻的压在心上。/她接触了心中的音乐/化成小诗一朵。”虚无缥缈的哲思被人化为极具女性柔美气质的意象“她”,传统的抒情言志模式在“我”与“她”的情感互动下得到冲淡中和,继而以一种平淡节制的口吻道出,显得神秘幽丽而情趣盎然。多个人称在诗中的主动发声,推动诗人加大对智性思考的投入及对情感盲目抒发的克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实现了新诗智性化的转型。
四、人称代词与新诗的复义思辨倾向
从新诗的纵向发展来看,推崇智性化发展道路的主智派诗歌逐渐取代纯粹的抒情诗开始占据诗坛的主要位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称代词在新诗中的多种形态呈现。与古代理趣诗、哲理诗对描述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哲理性内涵的挖掘不同,现代主智诗更多借鉴了西方现代哲理诗的概念,关注的是诗中多重人物(事物)关系带来的话语的多种阐释可能。人称代词因其对主体和对象性人物的指向功能,在新诗智性化的转型过程中以多个人称视角的切入带来诗歌的多义性。
人称代词在新诗中的多重叙事性讲述,意味着一首诗中可同时容纳多个人称主体的存在。各种人称在诗歌中的身份立场和叙述视角的不同,形成多层次观察和叠加叙事的效果,使主体人物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和诗歌的逻辑关系趋于复杂化。以刘半农《卖萝卜人》为例,诗歌主人公“卖萝卜人”因所住破庙标卖遭到警察驱赶,这一场景被路边玩耍的孩子们目睹并引发了各自不同的思考。与传统诗歌抒情模式相比,这首诗对所述事件的时间、地点、出场人物及进展情况有着清晰的描述展现,整个事件穿插了“他”“你”“我”“他们”“我们”等多个人称的交叉叙述,使诗歌类似于一场两幕的诗剧。在这场演出中,卖萝卜人既是“我”——自身行为及内心活动的掌控者,也是驱赶行为的受动者——“你”和事件中的被看者——“他”。与此对应,孩子们——“我们”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同时也以“他们”和“他”的对象化身份被叙述者和读者所审视。诗歌因此出现了多层级的“看与被看”关系:一条以卖萝卜人为主线,即卖萝卜人的内心自视(“我”)—警察看卖萝卜人(“你”)—叙述者看卖萝卜人(“他”);一条以孩子们为主线,即孩子们看卖萝卜人和警察之间的互动(“他”)—十岁孩子对孩子们群体的自述(“我们”)—叙述者看孩子们(“他们”)—叙述者看七岁孩子(“他”)。层层关系的套叠模糊了诗中卖萝卜人、警察、孩子们等主体人物之间演出者和观看者的界限,他们既是某个行为的发出者,又是另一行为的接受者。人物群相的互动淡化了诗歌的个体主导性,诗歌因而不再是某个人的独自感受的抒发,而是由多人物共同发声构成的多面化叙事。多人称的交叉使用,使不同主体人物能够针对诗中事物和事件进展发表不同见解,对诗歌主体叙事进行补充和完善,诗歌由此显现出复合透视的客观理性特征。
新诗重视语言表述带给读者的复义效果和多重解读空间。当多个人称代词同时出现于一首诗歌中时,由于主人公于诗人掌控之外具有相对独立性,“自我意识作为塑造主人公形象的主导成分,要求创造这样一种艺术氛围,要能使得主人公的语言自我解释,自我阐明。……一切都得让人感到是讲在场的人,而不是讲缺席的人;一切应是‘第二人称’在说话,而不是‘第三人称’在说话”(12)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04页。。人物对象的各自发声促使多声部叙述模式的形成,造成诗歌话语的套叠和语义含混朦胧的表达效果。代表性范例如卞之琳的《酸梅汤》,全诗看似叙述人称“我”一个人凌乱的片断式话语陈述,实际上先后指向了几个不同对话人。对应诗歌的具体内容,我们可大致分辨出诗中有如下主体人物的存在:诗歌说话人为洋车夫“我”,“可不是?这几杯酸梅汤……树叶掉在你杯里了。”对应的对话人为买酸梅汤的老头儿。“哈哈,老李,你也醒了……保你有树叶作被。”说话对象是洋车夫老李。“哪儿去,先生,要车不要?”则是问向路过的行人。至第二节,除开括号中的插入叙述是针对买酸梅汤的老头儿,“不理我,谁也不理我……啊哟,好凉!”可视为“我”的自语。诗中出现了多种人物声音,但诗人并未直接言明这些话语背后的说话人身份,而是“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立场上借助发话者与回话者对某一人生事件的不同态度,在彼此的差异形成的碰撞当中呈现人生意蕴的复杂性”(13)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6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将叙述话语中人称引领的多个完整句式从中截断转到下句,如“我想,/你得带回家去”“你说,/有什么不同吗?”“你再睡/半天”,以强行分行的办法将平行视觉感受转为纵式,有意增加读者的视觉停顿,人为设置阅读障碍,使含混效果更为明显。
由于新诗语言本身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其多义性的产生并非如古诗那般源于作者的有意留白和读者对行文跳脱之处心领神会的感悟,而往往与其所处的具体诗歌上下文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境指向语言上下文和情景上下文两个层面,即“言辞环境,包括词语、句子、段落及篇章等内部诸关系”和语言社会环境,甚至可扩大到“与我们诠释某个词有关的某个时期中的一切事情;在历时性上,表示一组同时复现的事件”(14)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结合诗歌上下情境来解读叙述人称的话语,往往会出现字面意义与诗人要表述的深层意义不符甚至截然相反的反讽意义。如闻一多的《飞毛腿》,这首诗显在的主体叙述人是“我”,其中还包含有潜在的对话人物“你”和被描述的对象性人物“飞毛腿”——“他”。从叙述者“我”的口中,我们得知“飞毛腿”是一个“别扭”、爱喝酒、邋遢、整天胡思乱想的“混”日子的人。但若仅理解到此,显然就错会了诗人要表述的真正含义。透过“我”略带调侃性的话语,叙述人对“他”实际上展开了一场明贬实褒的话语描述——“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拉着人谈天儿”“窝着件破棉袄”“还吹他妈什么箫”,体现“飞毛腿”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性格;对“天为啥是蓝的”和“曹操有多少人马”的追问,正是其不甘平庸生活状态下对精神世界和形而上生命意识的渴望探求;不爱擦脸爱擦车,透露其爱车胜过爱己、勤劳朴实的生活习惯;“车擦得真够亮”“和他那心地一样的”正道出“飞毛腿”内心的纯净善良。至诗尾,在“我”看似轻描淡写地对“飞毛腿”的惨死进行叙述的背后,流露的却是叙述人对年轻美好生命轻易消逝的深深同情与痛惜。当新诗开始运用人称代词表达丰富的深层话语内涵时,诗歌就不再拘泥于传统抒情与简单的叙述,而被赋予了多层话语表述空间。
人称代词作为新诗中被大量使用的一种新鲜语素,一方面因关涉到诗歌叙述者的缘故,渗入了诗人的情感意识,参与了新诗的诗思建构,同时增强了诗人在诗歌中的话语发声,引导诗歌抒情模式走向多样化;另一方面,其对抒情主客体的指称同时赋予了诗中人物及意象的主体能动性,打破传统以诗人个体抒情为主导的单一态势,诗中因而具有了多重话语讲述的可能,客观化、多义化叙事模式由此生成。人称代词以其自身丰富的可言说性,促进了新诗审美范式的现代转型与多样化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过多使用人称代词对诗歌语境做尽乎细微的过度阐释,一定程度上给新诗带来了意蕴浅露、诗味不足的弊端。对人称的刻意强调有时会缩减诗歌的想象空间,部分新诗因此过于平铺直叙而为后人所诟病,也值得引起警醒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