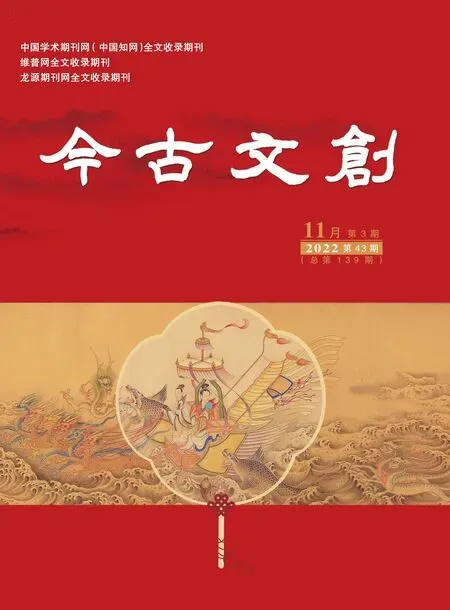陆贽骈文成就及文学史意义研究
2022-12-17王德军征玉韦
◎王德军 征玉韦
(1.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0 2.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技工学校 贵州 铜仁 554300)
陆贽是中唐著名的骈文家和政治家,在骈文创作上,他上承“燕许”,下启两宋,风格独特,成就巨大,在骈文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作品评价很高:“盖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名,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1]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唐朝四六文作者,能摆脱约束,自由发挥政论,只有陆贽一人。”[2]
一、陆贽生平及著述
《全唐文》中记载:“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大历八年进士,中博学宏词科,又以书判拔萃,补渭南尉,迁监察御史。德宗立,召为翰林学士从驾幸奉天,转考功郎中从幸梁州,转谏议大夫还京,转中书舍人。贞元七年拜兵部侍郎。八年为中书侍郎同门下平章事。十年罢知政事,除太子宾客。十一年贬忠州别驾。顺宗立,征还,诏未至卒,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3]陆贽一生的黄金时期,是协助德宗运筹帷幄,扫平叛难。当时被人们称为“天子私人”和“内相”。后虽时局变化,受到佞臣馋谤,君臣生隙,但陆贽始终秉承着“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的誓言,竭忠尽智,铮骨铁胆。贞元七年春,陆贽为兵部侍郎权知贡举,主持科考,首用通榜法,录取贾稜、李观、韩愈、欧阳詹等二十三人,因该榜所录之人多成伟杰之士,功名显赫,此榜被誉为“龙虎榜”。贞元十一年,陆贽被罢相,谪居忠州,据传记载, 陆贽谪居忠州十余年,为了避免别人议论,经常闭门不出,也不著书,无人能识其面,专门学习医方,编《陆氏集验方》五十卷。
陆贽的《翰苑集》(又名《陆宣公奏议》),是其唯一幸存的著作。《翰苑集》中所载文章,共141篇,有的宣扬“推诚纳谏、宽仁责己”的为君之道;有的力推“均节赋税、损上益下”的理财之法;有的主张“任将息兵、讨判和戎”的安邦之道;有的讲述“轻赋散财、体恤人民”的养民之法。它们涉及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才学睿智,充分凸显了骈文“经世致用”的价值。
二、陆贽对骈文的革新
(一)正实切事,深刻透辟
陆贽对骈文最大的贡献就是“正实切事”。他的文章谈古论今,总是缘事而发,不为空言,言必中当世之过,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陆宣公奏议,评以四字,‘正实切事’。”[4]苏轼赞扬陆贽的文章“论深切于事情”[5],他们的评价确实非常中肯。
陆贽总是针对具体事件,进行深入剖析,稽古证今,使利弊不言自明,说服力很强,不至于流成空言。当时陆贽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德宗“治乱”,在他的奏议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治理国家、朝代更替的历史事件,陆贽常常详述史实的始末,没有将历史事件凝练为典故,没有特意运用大量排比以获取形式之美。如《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一文,德宗刚愎自用,猜忌功臣,造成李怀光等将领不满:“怀光怨恚,故意屯军不进;河北田跃、王武俊、李纳闻奉天围解,叛志动摇,意存观望,唯朱滔与兄泚遥相呼应。淮西李希烈自恃兵强,仍伺机掠地。”[6]自是德宗居奉天,朱泚据长安,两个皇帝隔渭相持,直至年末。时局悄然变化,德宗皇帝束手无策,派人向陆贽寻求解决办法,陆贽高瞻远瞩,思想敏锐,他意识到解除危机的关键在于争取人心。陆贽建议德宗皇帝要了解情况、体谅下属,一致对外,方能获得民心。他在文中抓住要点,指出“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与“理乱之本”的联系,说理精当。除此之外,陆贽的《论缘边守备事宜状》《论关中事宜状》《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等骈文都是正实切事,议论精当透辟。
(二)融散入骈,运单成复
一般来说,骈体散体各有优长,骈句使文章凝练而整齐,散句使文章参差而疏畅,所以,刘勰主张“迭用奇偶”,包世臣在《艺舟双辑》对骈散作如下概括说:“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7]清末学者章太炎也说:“骈文散文各有体要,骈文散文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则所谓辞尚体要矣。”[8]陆贽勇于打破骈散的分野,根据行文需要,当骈则骈,当散则散,融散入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他对骈文的变革,为骈文创作开辟新的道路,给骈文注入新的生命力。
举事用骈,叙事用散。在陆贽的骈文中,历举前朝典故以说理,事事相对,多用骈句,在《兴元请抚李楚琳状》一文中劝唐德宗胸怀宽广,以史为鉴,以汉王刘邦对待陈平、韩信、蒯通、雍齿的态度为例,两两对举,一目了然。陆贽融散入骈,一方面以散行之气运排偶之辞,另一方面在文中运用了较多的散行句式,特别是叙事时多用散行,如《论裴延龄奸蠢书》中说:“由是蹂躏官属,倾倒货财,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馀,愚美朝廷,有同儿戏。诸州输送布帛,度支不务准平,抑制市人,贱通估价……”[9]这段文字叙述奸臣裴延龄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民不聊生的情况,不仅叙事简洁,而且气势流畅。
散句双行,运单成复。王闿运在《王志》一文中称陆贽以散句双行的方式为“运单成复”,两个散句组在一起虽然不是对偶句,但双行起来却自然流畅,富有节奏感。近人吴曾祺曾说:“惟陆宣公之公文,间于不骈不散之间,善以偶语寓单行者,实为自辟畦盯。”[10]他概括出了陆贽骈体文的特色,“善以偶语寓单行”,即“运单成复”的独创性成就,这是陆贽的一大创造。如《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中陆贽对德宗深刻阐述了“爵赏刑罚”作为“国之大纲”的重要性,“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巨大的冲击,唐玄宗轻爵滥赏造成恶果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文章开头的八句是工整的骈词俪句,自“爵赏刑罚”以下的十四句则主要采用“运单成复”的形式,他有意识地将单行散句组成整齐的双行,上下句字数相等、两两成双,很像骈句的整齐,但不讲对偶和声韵,具有散句灵便、疏畅的特点,显然,陆贽吸取了骈句、散句的长处,有排宕偶俪之美,无呆板僵滞之弊。
(三)不尚藻饰,少用典故
骈体文的重要特征除了讲究对偶与声律,还讲究藻饰和用典。初唐时期,骈文沿袭六朝文风,绮靡浮艳,多用典故,典故过多或者用典生僻,致使文气淤塞不畅,主旨难显,陆贽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他在《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中就表明了自己求通求变、审时度势、不拘泥于书的思想,其意在“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其文不尚藻饰,少用典故,既可深入议论,又使文字平易,这是陆贽对骈文的又一大贡献。如《奉天论赦书事条状》一文写道:“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昔成汤遇灾而祷于桑野,躬自免别以为牺牲,古人所谓割发宜及肤,翁爪宜侵体,良以诚不至者物不感,损不极者宜不臻,今兹德音,亦类于是悔过之意,不的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以不广,润泽不可以不宏,宣扬郁湮,不可不洞开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荡去瘢痕,使天下闻之,廓然一变,若披重昏而睹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11]这段文字陆贽用成汤之事劝德宗要真诚罪己悔过,建议德宗皇帝赦文以认错,全然不尚藻饰,但是意思表达清楚明白,再如《奉天改元大赦制》发布之后,权德舆在《陆宣公翰苑集序》说:“故行在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议者以德宗克平寇乱,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资文德腹心之助焉。及还京师,李抱真来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时,山东士卒闻诏书之辞,无不感泣,思奋臣节。臣知贼不足平也。’”[12]《资治通鉴》记载:“赦下,四方人心大悦,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上表谢罪。”[13]陆贽的骈体文通俗平易,在骈文史上很罕见。现代文献学家张舜徽说:“唐代经世之文,有出之以骈偶而为后世所宗仰者,自以《陆宣公奏议》为独步……所异于六朝骈俪者,在于不用典故,朴实说理,明白宣畅,令人易解。施之论政言事,览者一目了然。”[14]陆贽骈文也会引经据典,借古劝今,但是他不如六朝骈文家用典深奥难懂,他使用典故少而精,多为常见之典,力避冷僻。
三、陆贽骈文在骈文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一)陆贽对六朝骈文的新变
莫道才在《骈文通论》中说:“骈文就是基本由对偶的修辞格句子组成的文章,进一步说,骈文是从修辞学角度划分出的散文分类概念。”[15]骈文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里说:“它萌芽于先秦、起于汉魏、大盛于六朝,至隋唐余风尚炽。唐宋以后,以至明清之世,写作者仍不乏其人。”[16]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先秦到汉魏六朝,再到陆贽时期的中唐,骈文经历了很多次变化,骈文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在此发展过程中,有克服,亦有保留,但无论怎样,骈文总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缺点向更高一级程度上发展。据前所述,骈文萌芽于先秦诸子文章中的骈词俪句,两汉时期,文格渐变,辞赋一体,文章骈化程度增加,特别是随着赋的兴起,骈的成分更多,魏晋时期,骈文逐渐成熟,重视形式和技巧,出现唯美主义倾向,六朝时期,骈文在形式上则完全成熟,俗话说“物极必反”,此时骈文出现了不顾内容、单纯追求形式之美的现象,过度讲究对偶、藻饰用典和声律,达到顶峰,由六朝到隋唐,此种文风相沿不绝,隋朝李愕、初唐陈子昂、“四杰”、盛唐“燕许”诸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呼吁并实践骈体文革新,骈体文才由华而不实逐渐走向清新、自然、清新、经世致用,到陆贽手中,骈体文彻底完成了这种转变。
(二)宋代文学家对陆贽骈文的推崇
宋代的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汪藻等文学家学习、模仿的主要对象就是陆贽。“宋人章奏,多法陆宣公奏议……易短为长,改华从实,笔文互用,工为驰骤,而宋人利其朗畅,以为楷模,飞书驰檄,其体最宜。”[17]钱基博的这番话道出了宋人心中陆贽公文的地位。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在其主编的《新唐书》本传云:“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18]《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陆贽文十余篇;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亦重视陆公之公文,采其奏疏三十九篇,“上下千年,所取无多于是者,经世之文,斯之谓矣”[19]。
在宋代,苏轼学习陆贽最为自觉,受陆贽影响,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他最推崇的就是陆贽,苏轼曾说:“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20]苏轼入朝为官后,亲自参与《陆宣公集》的校正,在评论陆贽的奏议文章时,苏轼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蛰。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21]他把这些奏议文作为治世良方上奏给哲宗皇帝,希望哲宗皇帝师法陆贽,以致太平。苏轼在晚年仍好陆贽之文,并大力传播,可见陆贽对苏轼影响何等深刻。
(三)陆贽骈文对清代骈文家的影响
入清后,骈文创作迎来了中兴局面,名家辈出,比如陈维崧、毛奇龄、吴绮、吴兆骞、汪中、阮元、曾国藩等人,乾隆继位之初,孙嘉淦上有“清代第一奏疏”之称的《三习一弊疏》,提醒皇帝要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与陆贽《论裴延龄奸蠹书》《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吏状》等有异曲同工之处。曾国藩也十分推崇陆贽,他说:“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广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决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22]他进一步提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反对门户之见。
总之,陆贽是中唐文坛骈文革新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对六朝以来的骈文形式和骈文文风进行重大变革,融散入骈,骈散结合,符合骈文发展的内在规律,意义非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六朝以来骈文过度追求对仗工整、辞藻华丽的文风,使骈文正实切事,经世致用,取得了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巨大成就,开拓了唐代骈文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