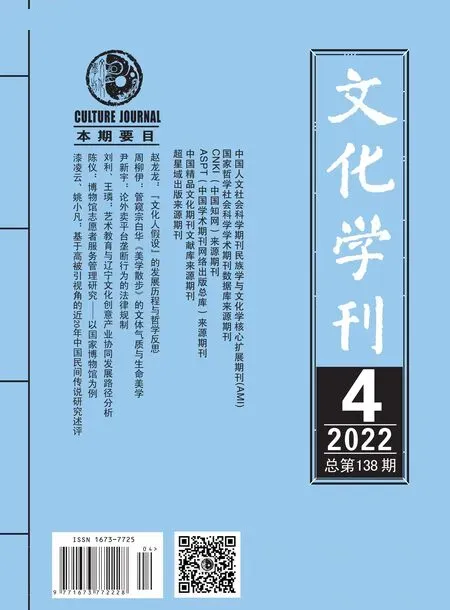论余华《兄弟》的翻译形象塑造
——以何碧玉译本为例
2022-12-07唐小璐
唐小璐
形象学与翻译学的结合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其源头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传统的研究视角,其核心问题是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构建。当代形象学的代表人物德国学者狄泽林克曾强调:形象学的研究重点是探讨形象建构的过程及其原因,而非追究形象的真伪。翻译活动则是用目标语言构建源语言文化下的群体、种族和民族形象,其结果并不一定完全呈现原文本所构建的形象,但翻译作品在目标语言文化空间中的传播可以在其中形成一种对源语言文化的固定的认知。因此,翻译可视为他者形象构建的重要载体。在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战略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到西方国家,其中很多作品的法译本是先于其他语种的译本出现的。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便是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法国译介成功的典型,其法译本由法国汉学家何碧玉、安必诺合作完成,于2008年在法国获得首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并引起《费加罗报》《世界报》等法国主流报纸的高度关注。
本文将以中国当代作家余华的小说《兄弟》的法译本为例,以形象学为理论框架,结合法国主流报刊对其评价情况,从文本层面出发,主要探讨作者构建的男性和女性形象之间的差异,同时结合中国的时代特色,对其法译本进行分析,探究所呈现的内容(如文章大体脉络、修辞手法等)与原文本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兄弟》在法国的译介和接受又会有怎样的影响,从而探析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与中国文化形象塑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一、男性形象的构建:“身体叙事”的平衡
纵观余华的小说作品,在其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创作中,“身体叙事”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兄弟》中男性人物占据的是主导地位,以最主要的两位人物——因家庭重组而成为异父异母兄弟的李光头和宋钢为主线。小说一开始便以大量的笔墨描写李光头过早萌芽的成人意识。大量直白描写与西方读者对中国人一贯的认知——内敛而隐晦地表达身体欲望大相径庭。文学批评家陈思和也曾指出:“作者在《兄弟》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另类的美学,与主流趣味略有差异。这部小说的出现,在一些文学评论者看来,是对他们自尊的挑战[1]。”作为法国专研余华作品的汉学家,译者何碧玉也曾对开篇反复再现的有关男性的欲望描写感到不适。从《兄弟》法译本的接受情况来看,法国媒体和读者虽也有同样的感受,但都表现出了理解和赞赏的态度。《兄弟》中大量的粗鄙描写与法国16世纪拉伯雷的《巨人传》中诸多渲染人类本能欲望、夸张离奇的表现手法不谋而合。因此,法国媒体也称《兄弟》中的李光头角色为“拉伯雷式的人物”,这与法国人心目中经典的文艺复兴时代作品产生了联系,契合了法国读者潜意识层次中的文化印记。除了与法国文学审美范式对异化和恶的关注[2]有关之外,《兄弟》法译本受到广泛认可与译者出于“自觉意识”对原文的再创造也有一定的关系。“文学形象的产生,大都源于作者对自我与对他者的理解,对本土环境与海外环境关系的认知,通过某种内在意向的自觉意识表现出来,虽然这种意识有时较为微弱[3]。”经过对《兄弟》原文文本和法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兄弟》原文本中大量重复的身体词汇,在法译本中被处理为了宾语人称代词,或者以省略名词、用形容词替代的方式呈现,弱化了带有粗鄙性因素的身体描写,同时也减弱了大量重复的人体隐私部位词汇给读者造成的心理冲击,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文对男性形象的贬损。
翻译对于作者的价值观有一定影响,它可以通过改变叙事话语(如引用隐喻的手法)来影响原文,使其原本建立的道德伦理出现偏差。它也可以改变故事层面的元素,以此来改变作者的伦理态度[4]。余华文笔的显著特征:弱化感情色彩,注重残忍的细节。
对于法国读者来说,形象化的比喻似乎比原文的表达更能带来一种视觉震撼,同时改变了原文本叙事时的冷漠、旁观者的基调,注入了一定的悲壮色彩,更能引发读者对这名坚忍的父亲的同情。不难看出,《兄弟》的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本中的身体叙事根据不同的形象塑造需求进行弱化或者强化,最终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主流研究可以接受的范围中,严格控制语言的异质性,并尽量结合法国读者的生活环境和背景,使其更容易被法国读者接受[5]。
二、女性形象的构建:“女性主体意识”的归位
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处于一种男权统治下的附庸状态。《兄弟》中塑造了两个主要的女性形象:李光头的母亲李兰和宋钢的妻子林红。前者生性坚强,在丈夫被迫害致死后,为夫守节竟七年未洗头,作者以此情节来褒扬她的忠贞不渝,也代表了传统的男权文化对女性最大的期望;后者是刘镇男性争相占有的对象,先嫁给自己所爱的宋钢,后出轨李光头,断送了兄弟二人的亲情之后自甘堕落。作者以她的不幸结局来印证女性放纵欲望的恶果,而沉迷于身体欲望、背叛兄弟、做事荒诞不经的李光头却成为了亿万富豪,得到了善终。截然不同的结局暗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自然欲望的压抑和主体思想的缺失。
法国媒体的相关评论中也较少涉及《兄弟》中的女性形象,2008年5月9日,《世界报》一篇题为《历史逆境中的生活》的评论指出:“《兄弟》这部小说的核心是性以及围绕这一核心的竞争,通过对刘镇最美丽的姑娘——林红外貌和体型的描述,小说的脉络徐徐展开,作者采用隐喻和暗喻相结合的手法,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个人主义思想的萌芽,并在最终将这一切归结为林红[6]。”该评论某种程度上抬升了林红在小说中的地位,而原文本中林红的出现虽然主导了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的亲情关系,但却始终只是被物化的男性欲望对象。法国媒体的评论之所以和原文本的意图有所偏差,还应归因于译者赋予了原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一定的主体意识。他者形象在翻译作品的呈现方式主要基于主体形象的展示,通过对主体的筛选以及操纵,他者形象便完美呈现在读者眼前了[7],何碧玉和安必诺主要对故事层面的女性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进行适度改写,从而达到了提升女性主体意识的效果。例如,在描写林红见到宋钢遗体的表现时,译文将原文中林红自责的心理状态转换为了旁观者的叙述,并且将主客体进行了置换:“自己害死了宋钢”变为“宋钢因她而死”;“她心里涌上了很多委屈”变为“她所遭受的一切屈辱回到了她的记忆中”。减弱了原文施加在人物身上的罪恶感,并且强调了人物内心的苦衷:虽导致悲剧的发生,却也是受害者,而原文中的“委屈”反而暗示着林红内心为自己的放荡不羁找了借口。由此可以看出原文对人物形象的贬损和译文对人物形象的抬升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并进一步窥见译文叙事者的女性立场和态度。
三、时代特色形象的构建
关于时代特色形象,形象学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一些情节、主体的呈现中,它们或已经定型化,或者具有程式化,通常蕴含着包含地域特色的象征意义。在某一特定时期、某种特定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储存了一批能够直接或间接传播他者形象的词汇。这些文本大多是词语群、词汇网和语义场,尽管在数量和描述精确度上略有差别,但这些内容相互交错糅合,共同构成了作家以及庞大的读者群体之间共有的观念以及情感抒发的宝库[8]。在《兄弟》中,中国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在异国注视者文化中是不可想象的,也是颠覆了异域观者潜意识中存在的有关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即透过他人的间接信息产生的模糊认知和感受。而《兄弟》则把这种“颠覆”直白地袒露在法国读者面前,并进一步填补了他们相应的认知空白,符合他们的阅读期待。
一部文学作品除了审美价值,还承载了诸多的文化信息。《兄弟》法译本中有二百多条有关特定文化词汇和双关语、谚语的注释以及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同时在反映历史场景的片段中也尽量用与原文本相近的句式进行重现,让法国读者体会到作者的叙事节奏和原文本强调的狂欢而荒诞的氛围。例如译文将原文中“童铁匠”“余拔牙”的称呼简略为姓氏,其身份改为同位语,以阶梯递进式的语句结构代替原文中近似对仗的句式,即每个分句都是十六个汉字。在处理类似的情节时,何碧玉曾经表示:“法语是将所有的句子成分重组,汉语相反,不会出现普鲁斯特式的不加拆分的长句,对于译者而言,最难的是让译文和汉语表达习惯契合……并保持韵律[9]。”何碧玉和安必诺作为译者,在尽力保持对原作的忠实性的同时,对于汉法两种语言结构差异、中法两国文化差异等造成的翻译障碍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处理方式,既没有完全直译,也没有贸然用西方意象和概念来替换,避免了中国文化形象的淡化和迷失。
在《兄弟》的下部,余华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全景式”的描写手法一一列举,形成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效果,给读者一种宏大却又不失逻辑的感觉,将中国两个极端性的众生万象一一呈现在法国读者面前,迎合了法国社会的阅读倾向,即同时具有社会性、批判性、政治性的反映时代特色的作品。不仅在法国,《瑞士时报》也在2008年5月24日题为《中国四十年聚焦了西方四个世纪》一文中指出:“阅读这篇小说,让读者身临其境,以一种上帝般的视角,从全方位的维度细细品味这幅史诗般壮观的画作,而这幅画作的主题便是:当代中国[10]。”
四、结语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转换为对象的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翻译研究通常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的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主要关注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中各民族特性的维护问题。结合翻译研究,致力于探索翻译过程中的多重呈现方式和传播路径(扩散传播、传染传播和登记传播等),对于文学、文化以及民族形象等内容多加关注。在跨文化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形象学主要在两个方面起作用。一是在对我国经典文学(如四大名著、《流浪地球》等)的外译的过程中重视中国文学,突出文化形象和身份的展示;二是通过对目标语文化群体的整体认知度和环境背景、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进行研究,探索在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方面的最佳方式[11]。
从《兄弟》的法译本在法国的传播情况来看,法国读者和媒体给予的赞赏和关注表明了《兄弟》法译本塑造的同中国有关的形象符合目标语国家社会读者的期待,也表明译者在忠实原作基础上做出的“再创造”较好地平衡了“符合目标语国家读者的语言习惯及心理预期”和“保留中国特色、中国文化符号”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往往会受到各国读者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历史的关注程度、对中国社会探知的好奇心以及认知角度的影响。而译者发挥的作用更加不能忽视,通过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本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目标语的角度对中国文学、文化形象的塑造进行反观和自省,另一方面可以给未来中国文学在世界层面的传播和中国国际文化形象的塑造带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