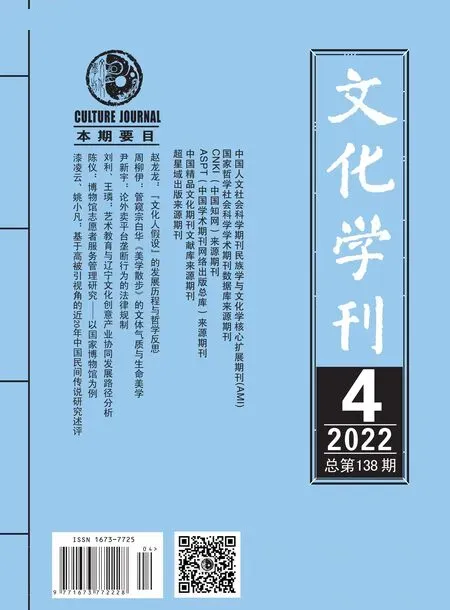朱希祖《云南两爨氏族考》与《云南濮族考》学术写作研究
2022-12-07李春宏
李春宏
朱希祖是20世纪的杰出史学家之一,其“史学成果仍值得当下的人们学习继承[1]。”学界对其史学思想做出了许多研究总结,比如他特别注重经世致用,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2]。”史料搜集整理上朱希祖“在搜集各类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地史料辨析注重史料的科学化[3]。”学者指出,“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对于我们现在的治学研究是有着启迪借鉴作用的[4]”既往对于朱希祖的研究,多关注于他的学术与思想,而对他如何进行论文写作,学界的研究略显不足。现如今如何进行论文写作俨然成为了不少青年学者所面临的难题,《云南濮族考》与《云南两爨氏族考》皆为朱希祖晚年所著,此时朱希祖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文章写作模式,通过对朱希祖文章整个写作流程的爬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归纳朱希祖的写作方法并寻找值得青年学者们借鉴的经验。
一、写作缘起
纵观朱希祖的一生,其在历史领域著述丰瞻。《云南濮族考》与《云南两爨氏族考》是其晚年所著文章,朱希祖撰写这两篇文章是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章太炎的学术影响、西南民族史研究热、为江应梁撰写论文审查报告。这三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朱希祖撰写了两篇有关“云南民族学”的论文。
(一)章太炎对朱希祖的学术影响
朱希祖留学日本时便拜入章太炎门下,二人有着深厚的感情。1936年6月14日,随着章太炎去世,朱希祖接手了大量底稿。如1936年8月27日,“整理先师遗墨,得《辞东三省筹边使咨文》底稿,及《陈诉巡警总监吴炳湘非法拘禁妨人迁徙状》底稿,皆于先师史迹有关极为可贵[5]691。”此外,在审查江应梁文章前不久,朱希祖正受孙鹰若之邀,计划整理出版《太炎文录》。1938年7月9日,“接孙鹰若寄来先师太炎先生书札数百通”[5]904。朱希祖在12月16日阅过《云南僰夷民族研究》后写下“先师章先师《太炎文录》有《西南属夷小记》,言‘濮夷’由‘濮水’得名(见《汉书·地理志》)[5]960。”朱希祖在《云南濮族考》开头便提到了章太炎“先师章先生《西南属夷小记》,言……”[6]。
朱希祖通过对章太炎文稿的整理,对于章太炎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章太炎所做的民族学研究又正好与朱希祖当时的研究方向相近,所以朱希祖在收到《云南僰夷民族研究》后,立刻联想到了章太炎所做的相关研究,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对朱希祖文章的写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西南民族史研究热潮
当时整个学界对于西南民族的研究热情是促使朱希祖写作的另一契机。从1905年到1950年间,全国共有约70位专家学者以及20多个相关机构展开了对民族史相关的研究[7]。朱希祖撰写有关云南民族史方向的文章,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抗日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许多高校及学者受战乱的影响南迁到了云南,这使民族学的有关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江应梁回忆道:“这一时期,集会在云南的全国学者,其中不少是民族学专家。对他们来说,来到云南诚然是如入宝山。此外还有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他们过去虽然不专门从事民族学研究,但一到云南,也为这个多民族的地方特点吸引住了,情不自禁地走到少数民族的研究与调查中来[8]。”可见在1938年,云南民族的相关研究正是学术界的热点课题。此外除了本文所谈及的两篇文章,朱希祖在重庆时还写有许多有关西南历史方面的著作,如《古蜀国为蚕国说》《蜀王本纪考》《夷越夷濮考》等。朱希祖一生中有关民族史的研究也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可见,云南民族研究热是影响朱希祖撰写文章的另一大契机。
(三)撰写论文审查报告
在影响朱希祖撰写文章的诸多因素中,起决定影响的当属为江应梁撰写硕士论文的审查报告书。1938年12月16日,“夜审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硕士学位考试论文,题为《云南僰夷民族研究》,江应梁撰,系教育部所委托审查。共厚两册,先阅一过,拟作审查报告书[5]960。”以此日为节点,朱希祖开始了对江应梁论文的审查。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朱希祖对于云南历史并不陌生,早在1933年朱希祖就已接触了大量的云南史地史料,1933年1月4日,“三日前云南昆华图书馆方臞仙先生寄来《云南府志》二十册,《元江志稿》十二册……《云南通志凡例分类纲目》及《县志纲目》《修志概要》各一册[5]196。”可见收到江应梁论文时的朱希祖对云南的史地知识并非浑然不知,而是已经有了一定了解。
1939年5月10日,朱希祖收到了罗香林的来信,“午刻接香林来信,言江应梁君之《云南僰夷调查报告书》,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拟请将余所撰审查报告书印于其上。而余报告书中言别撰文一篇,言云南濮族夷变迁,因循未果,今拟整理材料以撰成之,兹先撰《云南两爨氏族考》[5]1053。”这天以后朱希祖便开始动笔写作,由此可见,江应梁的这篇毕业论文的确是极大影响了朱希祖撰写这两篇文章。
在审查《云南僰夷民族研究》的过程当中,朱希祖已经逐渐将治学重心转向了对云南民族学的研究,加之此时朱希祖已经通过整理章太炎遗稿接触到了章太炎有关西南地区的一些研究,以及当时整个学界“民族研究热”的影响,这三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朱希祖撰写文章的契机。在正式撰写文章之前,朱希祖做了大量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并对有关学术史进行了梳理。
二、搜集史料与了解学术史
史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史料并不等于史学,但在某种程度上史学是由史料所决定的,史料承载了史学的生命[9]。通过观察朱希祖撰写文章的整个经过我们可以发现,在朱希祖的学术写作中史料搜集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史料搜集从始至终贯串于他的研究进程。并且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朱希祖还会对有关学术史进行梳理。
(一)梳理学术史
从朱希祖两篇文章的写作经过来看,梳理学界已有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朱希祖第一次审查江应梁论文时,便联想起了章太炎有关西南民族学的一篇文章,但朱希祖并非专于民族史学,其对于云南的民族史了解不深。所以朱希祖在审查论文过程中还对学界已有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
12月22日,“夜阅本日在商务印书馆所购:《秦代初平南越考》(法国鄂卢俊撰,冯承钧译)[5]962。”12月23日,“至图书馆借书,中有日本人斋田农八所撰《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内载古代华人关于棉花、棉布之知识一篇,考哀牢国之帛叠布特详,阅之终篇。午后又阅其《南蛮考》一篇。……夜阅《云南地理》,参考《嘉陵一统志》[5]962。”可见在收到论文后不久,朱希祖便开始网罗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这一过程持续时间很久。1939年1月19日,“午后二时进城至中华书局购:《云南史地丛考》一册[5]978。”
在这一阶段朱希祖通过借阅与购买的方式搜集了不少中外学者有关云南方面的著作,通过对学界已有研究的总结归纳,朱希祖对于同时期中外学者有关云南民族的看法观点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了解,这为日后朱希祖自己动手撰写文章做了前期准备。
(二)整理史料
朱希祖在梳理学术史的同时还会对史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其中江应梁的文章是朱希祖的一个重要史料来源,在审查期间朱希祖曾多次对江应梁的文章内容进行摘录。12月26日,“上午阅江应梁《云南僰夷民族研究》,结论中有《论云南西境边防》一节,甚属重要[5]963,”12月29日,“上午补录《云南西境土司之行政组织》[5]962。”1939年 1月12日,“夜补抄《僰夷土司制度》[5]974。”1月13日,“夜补录僰夷调查材料,并阅《南德化碑》全文[5]976,”1月27日,“夜腾写《审查意见书》三条及《史学系教授会议审查意见》[5]980。”朱希祖在其后所撰的《云南濮族考》一文中便引用了江应梁的观点,“据江应梁君《云南僰夷民族研究》谓详察今日僰夷社会制度及经济阶段,实为封建大地主之社会[6],”通过对江应梁文章的摘抄,使朱希祖在加深对文章了解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有关云南民族方面的史料。
1月28日,“午后撰《江应梁<云南僰夷研究>审查报告书》及《王兴瑞<海南岛黎人研究>审查报告书》[5]980。”在文章的审查报告撰写完毕后朱希祖并没有停止对史料的搜集。2月2日,“五时乘车至中央大学,夜阅《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全篇,并阅夏光南《云南史地丛考》中《东爨西爨考》[5]990。”2月9日,“夜阅《唐书·南诏传》及《两爨传》[5]999。”可见朱希祖在撰写完审查报告书后没有停止史料的搜集,仍继续着云南民族的有关研究并搜集相关的史料。
总结朱希祖搜集史料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他对史料的搜集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注重梳理学术史。朱希祖参阅了不少中外学者的著述,如日本学者斋田农八的《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法国学者费琅的《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与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国内学者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等,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朱希祖对于民族史研究的内在理路有了了解,洞悉了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为其后续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对收集到的史料并不是简单采用,而是在辨别真伪后方才引用,通过这样的方法所运用的材料更加具有真实性。
三、写作与修改
朱希祖总共用了八天便完成了两篇文章的写作。5月10日,“而余报告书中言别撰文一篇,言云南濮夷变迁,因循未果,今拟整理材料以撰成之,兹先撰《云南两爨氏族考》[5]1053。”5月11日,“续撰《云南两爨氏族考》,至夜十时,全篇撰成[5]1053。”从10日到11日,朱希祖仅用两天便完成了《云南两爨氏族考》初稿的写作。写完《云南两爨氏族考》后,朱希祖同样又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云南濮族考》的写作,5月13日,“午后撰《云南濮族考》[5]1053。”5月14、15、16、17、18日,“皆续撰《云南濮族考》[5]1054。”可见,《云南濮族考》的初稿写作朱希祖也仅用了六天的时间。
在两篇文章都写完后,朱希祖才进行修改,他先修改的是《云南濮族考》。5月19日,朱希祖找来金毓黻修改文章,“金静庵来阅余新作文[5]1054。”金毓黻在日记中对于这件事也进行了记述,可以佐证金毓黻这天所阅的正是《云南濮族考》这篇文章“朱逖先先生近撰《云南濮族考》一文,中兼及越族,所谓百濮、百粤是也,濮之一名,屡见[10]4319。”之后朱希祖自己又对文章进行了修改,5月22日,“夜补削《云南濮族考》[5]1055。”
至于最早写完的《云南两爨氏族考》也于5月23日定稿。“午后校正《云南两爨氏族考》,系菊女所录,一篇以寄香林,一篇预备登中央大学《新民族学刊》[5]1055。”从11日写完到23日邮寄,可见对这篇文章的修改时间不会超过十二天。5月28日,《云南濮族考》与《云南两爨氏族考》的写作与校定就都完成了,两篇文章的写作与修改大致经历了十八天,朱希祖能在18天写完两篇文章,得益于之前对史料的搜集以及学术史的梳理。
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云南濮族考》与《云南两爨氏族考》直到1939年9月与1943年9月才正式发表。正因文章发表周期的延长,朱希祖对早已定稿的文章做了再次修改,在这之中罗香林对于文章的修改发挥了巨大作用。朱希祖与罗香林曾就《云南濮族考》与《云南两爨氏族考》中的部分观点展开讨论。罗香林在信中写道:“奉读近作《云南濮族考》及《云南两爨氏族考》,言百濮即僰夷及爨为汉姓,实发前贤所未发。……鄙意既称僰、濮为同一民族,则不如匆称之为羌人。不知尊意以为有当否也[11]213。”罗香林的来信,使朱希祖对文章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朱希祖在7月26日给罗香林的回信中写到“君此疑问,于余颇多启发,此等疑问亦深有益于学术也[11]213。”此后朱希祖又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写罗香林书,附《蜀布考》及修正《云南濮族考》数条,答罗香林问《濮族非羌种书》[5]1074。”此时文章早已完成多日,可见即使朱希祖文章已经定稿,但在收到有关文章建议后还是会积极采纳修改的。
从朱希祖对两篇文章修改的经过来看其修改文章具有两个特点。朱希祖会找学者一同检查修改,如朱希祖先后找过金毓黻与罗香林来修改文章。金毓黻是当时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罗香林作为中山大学的历史教师也具备不俗的史学素养,文章在经由三名史学家校阅后,其文法与误字之类的简单错误可以有效规避,并且文章在知识内容上的不足也得以获得一定程度弥补。
四、朱希祖治学思想启示
朱希祖是一名杰出史学家,他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财产。近些年,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成为了研究生中的一员,而不少研究生对于如何研究是一知半解的。基于这种大的时代环境,本文希望通过考察朱希祖文章具体的写作过程,为当下青年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一)学术研究应当勤奋刻苦
在朱希祖的学术生涯之中“勤奋”可谓贯彻了朱希祖整个的治学过程。朱希祖在撰写《云南两爨氏族考》以及《云南濮族考》的同时,还兼顾着对《汲冢书考》的相关的研究,朱希祖在进行云南民族史学研究的同时还写了四五万字的《汲冢书考》,这样勤奋治学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刻苦”是朱希祖另一熠熠生辉的学术品质。朱希祖此时所居的重庆,是抗日战争中日军空袭最为频繁的城市,而此时的他也已年过花甲且疾病缠身,但是不论是日军的轰炸还是身体的不适都没有阻碍朱希祖研究的步伐。1939年5月3日,“午后一时有空袭警报,旋闻重庆市有轰炸声及高射炮声,又见烟焰数起,及飞机坠落声。……续写《汲冢书考》[5]1042。”时下青年学者们的学习环境不知比抗战时期的重庆强了多少倍,但是这其中有些学者的治学热情却远不如正在经历抗战的朱希祖,这是值得广大青年学者们去警醒的。学术研究不是简单的上课做笔记或者期末考试,而是功夫在课外,要利用课余时间去进行自主的学习积累,多写多想才是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根基
治史当以史料为先。朱希祖在搜集史料过程中,既重视传统的基础史料,又关注同时期中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目前,互联网的发展有助于青年学者们掌握中外最新的学术动态,但与此同时其操作的便利性也使青年学者们在探寻史料时过于依靠网络检索,搜集的史料大多是依靠搜索引擎。这种史料搜集方式的局限性很大,很多时候,文章所需要的史料是要靠自己从浩如烟海的书目中摘寻的,靠检索直接搜索出来的资料是良莠不齐的,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地去搜集精华部分,辨别无用的或者假的史料。朱希祖给予我们的另一个治学启示是,史料搜集要善于积累,功夫做在平时。青年学者们搜集史料往往是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导向性和目的性非常明显,这虽然能够搜集到与自身研究相关的文献。但另一方面,在日常未进行论文写作的时候,同样要注意对史料的积累,在平常阅读文献的时候,就要对自己感兴趣的与自身研究方向有关联的史料进行摘录,这会比日后再去专门搜集史料更省时间,涉及的范围也更广。
(三)学术研究需要文化自信
朱希祖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参考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论著,但朱希祖并没有视西方学说为圭臬,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看法。朱希祖抨击了当时学界对外国学术观点盲从的现象“吾国学者震于其名,翕然从之,以为昔日爨即今日之倮儸矣。是皆不知中国历史,而言者盲然也[12]84。”朱希祖之举在当下也极富启示意义,现如今虽然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的研究的确领先于中国,但是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因此盲目迷信西方的学术理论。部分青年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将引用西方文献、西方理论视为自身文章的“皇帝新衣”,认为只要有了这些,自身的文章就是好文章,就能显示自身的学术造诣如何之高。这就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完全照搬西方理论,显然不能完全贴合中国实际。朱希祖在面对西方学者作品时展现出了极度的理性,会去对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进行考证核验,做到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是十分值得当下青年学者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