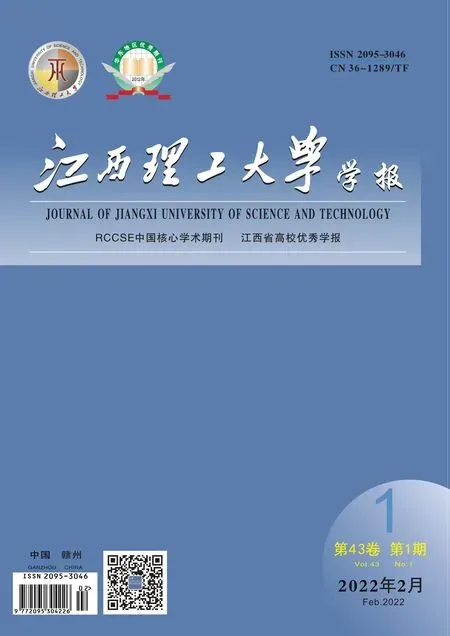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空间美育想象
2022-11-25廖光发闫宁
廖光发,闫宁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昆明 650000)
202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为文学经典在教材中的再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文件指出,学校美育以“大中小幼”为工作对象,对提高中小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强化学校美育育人功能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翘楚,鲁迅的作品入选语文教材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却存在“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语文教育困境。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史。在以往的语文教材中,鲁迅往往被解读成“孤独战士”的形象,造成了“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的认知[1],这不利于构建鲁迅与美育的桥梁。
诚然,鲁迅有“斗士”的一面,但“斗士”的文本解读,已经难以适应当代中小学教育的美育要求。因为,它很难贴合中小学学生现有年龄的理解能力,难以对“斗士”“孤独战士”产生具象化的理解,反而沦为一种口号式标签。所以,转变文本解读思维,才能更好地促进鲁迅的作品传播,从而搭建鲁迅与美育的桥梁。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聚焦于回忆的空间,展开了对空间的文化构建,其文化内蕴为当下作品解读提供了一个新方向。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一个儿童的成长,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的问题”[2]。鲁迅笔下的回忆,不仅为儿童描摹了一种独特的成长空间,还给成年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力。散文中的文化内涵,将在空间叙事学理论下得到阐释。而空间的文化内涵,不只是对“政治鲁迅像”[3]的反拨,更是对中小学空间美育的新尝试。
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空间”美育缺位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发表至今,相关研究数不胜数,尤其从2007年至2020年的十三年,其研究规模已经取得量的飞跃。将它们进行系统总结,能够归类出三种主要的研究取向:主题研究、形象研究及儿童视角研究。进入21世纪后,开展的景物描写、语言品析和结构分析等中学教学研究大多基于这三个方向。
其一,主题研究。该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两个方个方面:一方面是“热爱”说,佟乐泉认为,散文表达对童年自由生活的热爱的主题[4];这一学说止步于“热爱”,并未深度探讨自然之后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是“封建教育批评”说,在1956年的教学大纲中,它将封建教育指定为唯一主题,批判了封建教育对儿童身心的戕害,并将其指定为唯一主题[5]。在当下的教学过程中,两种学说演变成对立的观点,但大多数仍采用“封建教育批评”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学说不符合教育美育的要求。
其二,形象研究,并聚焦于“美女蛇”和“私塾先生”的形象。其中,聂国心对“美女蛇”研究比较透彻,他将美女蛇解读成同一时代里攻击鲁迅的文人和当权势力,并且指明美女蛇的故事是一种封建迷信[6]。而“私塾先生”的形象研究,呈现出两种对立的形象解读:封建的代表与负责任的教师代表。对于前者,孙慎之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讲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孙慎之认为,私塾先生是封建教育的执行者[7]。这一观点曾在20世纪得到广泛认同,并且在当代课堂中仍有延续。而钱梨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私塾先生是先进的象征,是一个负责任的教师代表[8]。这一观点在提出时曾遭到多方反对,但随着鲁迅研究“去政治化”的趋势,也逐渐得到一定的认可。从封建到先进,理论上是一个进步,但是,教材设计却有意避开私塾先生的具化形象,往往设置“你认为私塾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设置导致私塾先生的形象模糊化。
其三,随着儿童文学理论的译解,在21世纪初,儿童视角得到了研究者的一定青睐。解泽国从小鲁迅的儿童体验出发,立足于品析散文中的童真、童心与童趣,兼具学术性与鉴赏性[9]。但是,因国内的儿童文学理论尚处于发端阶段,理论尤为欠缺,即使有一定的理论素养,也难以避免鉴赏性解读。因此,儿童视角的研究仍然留有较大的空间。
自20世纪末以来,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解读,逐渐定位于中学教学探究①数据在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得出,根据检索结果的可视化分析显示,中学教学学科分布81.92%。。但是,中学教学探究偏好于如何教,因此,在散文的解读上,几乎遵循了上述三个方向。2019年,全国小学、初中统一使用部编版语文教材,鲁迅的几篇作品残存在新版教材中,但教材对于鲁迅的解读是一种偏见性的过度阐释,这种阐释造成了文本解读与教材改革的脱节,难以达到当代美育的要求。而对鲁迅散文中的空间文化研究,恰好是对这种脱节的修补。空间的审美解读,不仅能使“政治鲁迅像”得到一种挽救,还能破解鲁迅作品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困境,更能重新挖掘民族空间的美育审美。
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空间文化构建
空间叙事学理论下,一个作品的产生必然包含两个空间: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故事空间,指文本中发生故事的空间;而所谓“话语空间”,是“叙述者所在的空间,包括叙述者的讲述或写作环境”[10]。作家在创作时,话语空间中的新经验融入了故事空间,而新的经验参与了故事空间再叙述,使故事空间呈现出新的内涵。这两种空间,与诺伯格·舒尔兹的“存在空间”②诺伯格·舒尔兹在《存在·空间·建筑》中曾这样论述空间,空间是以自己为中心,同时不断地变化,但是变化的空间形态依旧被主体图式同化,在主体新的体验中,空间形态也会因新的体验而有所修正,因此形成新的意义。相类似,空间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同时又跟随着人的转移而转移,在两种空间的对照中,作家完成了对空间的文化转码。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创作中,故事空间即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话语空间即当时厦门大学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一)百草园的“原风景”文化意蕴:话语空间向“精神田园”的转换
百草园作为散文的故事空间,它存在于故乡,不仅是鲁迅的童年回忆,还是一种对自然的原初体验。20世纪70年代,日本作家奥野健男就曾提出“原风景”的概念:“原风景”产生于童年的经验,它是一种关于故乡的原初体验,这样的体验往往发生于故乡,承载的多为对根的探寻,涉及对历史、民族和文化的理解[11]。同时,“原风景”的创作存在一个悖论:童年阶段无法获得对原风景的文化认知,直到长大后再回忆时,“小时候不理解的那些风景或形象的意义会逐渐得到理解”[11]。这一概念贴切地说明了鲁迅的创作情况。
百草园“是我的乐园”,它蕴含了鲁迅对原风景的自然体验。在百草园的自然风光中,小鲁迅经历了一场听觉与视觉的狂欢盛宴:蝉像人一样长吟,油蛉像人一样低唱,蟋蟀们像人一样弹琴;至于植物,不仅有“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和“紫红的桑葚”,还有如人形的何首乌。百草园满足了小鲁迅对自然的想象,动植物更是“活”了起来,仿佛组建了一个灯光、音效俱全的音乐盛会,而鲁迅正是这场盛会的享受者。读者沉浸于鲁迅描写的欢快氛围之中,往往遗忘了成年鲁迅在话语空间的体验,而百草园的“原风景”文化意蕴,也正是通过回忆与话语空间的对话而得以实现,在这样一场对话中,鲁迅完成了对话语空间的超越。
在话语空间中,不但有“离奇和芜杂”[12]的景象,而且鲁迅正面临着“四面是荒地,无屋可租”[13]的境况。1926年的某个夜晚,鲁迅“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面对“石屋”“大海”和“古书”,百草园的“回忆在心里出土”[12]。在一个破败压抑的话语空间,鲁迅并没有用文章抒发消极情绪,更没有用犀利的笔法,化悲愤为抨击,而是主动地将精神领地转向童年体验,在百草园的“原风景”中,找到了一种激励精神的力量。鲁迅面对“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13]的自然环境,主动选择了欢快、天真的百草园。话语空间和故事空间呈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景,前者荒凉、凄惨,后者生机、愉悦。鲁迅回忆故乡的原风景的过程,即消解话语空间的过程,而这也正是成年鲁迅再回忆时,对童年原风景的再体验与再理解。同时,这样的再体验与再理解,又反作用于鲁迅超越话语空间。
在空间的对话中,鲁迅不但超越了话语空间,而且完成了话语空间向“精神田园”的转换。这样的转换,将在古典“田园诗”的文化传统中得到印证。在古代的田园诗学中,无论是书写《四时田园杂兴》的范成大,还是创作《田园作》的孟浩然,抑或是描写“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陶渊明等,他们都曾有过相似的经历。这些文人志士,有的少年不得志,而选择隐居田园;有的老年不得志,而寄情于田园。古人在不得志的沉浮中,往往将精神空间入住山水田园,并且也把生活住进了山水田园。但是,鲁迅更加真实,显得略胜一筹——他并不躲避话语空间,而是在两种相反的空间中随心往返。
在鲁迅抵达厦门前后的这段时间,鲁迅眼前何以“只剩了回忆”[12]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时的厦门,不仅自然环境令人咋舌,社会环境也让鲁迅向“精神田园”漫溯,清醒又克制。在鲁迅前往厦门前,他遭遇了诸如“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以及莫名“被通缉”等。后逃至厦门,厦门也非清净之地,又遭遇了同事的冷漠、恶劣的自然环境等等。鲁迅在“芜杂”的话语空间中,往返于百草园的田园风光,鲁迅也不愿被“荒凉”渲染,于是从田园美学中汲取精神力量,让其反作用于话语空间。在这样的空间转换中,鲁迅以传统的田园风光为嫁衣,采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最真挚的情感,但却对陶渊明式的“身隐”做出了反叛,将田园的原风景内蕴转化为一种精神食粮,这是鲁迅“对风景的审美观和价值观”[11]的独特体验。正如鲁迅所说,“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11],童年的“原风景”“是充满感情色彩的风景”,它也因此“常常作为文学的出发点而表现在作品当中”[14]。话语空间中的鲁迅,甘愿向故乡的原风景回首,也逐渐形成了“鲁迅式”的“精神田园”,在每一次回首中,鲁迅从田园的“原风景”内蕴中,完成了对伤痛的自我治愈。
(二)三味书屋的双层文化空间:学堂崇仁与小园尚真
作为第二个故事空间,三味书屋又包含两个小空间:学堂空间与“小园”空间。学堂空间以求知为主,学生在这里求学,老师在这里授课;对于“小园”空间,鲁迅描写到,“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抑或“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12],小园承载着儿童的课间乐趣。三味书屋对小园和学堂的并置,实际上是为了学生在天性与教育的互动中成长。
1.学堂空间:崇仁
在三味书屋的学堂空间,鲁迅回忆了“入学行礼”“询问怪哉”以及“读书”事件。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实则隐含了一条探讨“仁”的线索,而这一条线索,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当小鲁迅从难以割舍的百草园转入三味书屋时,首先迎来了“入学行礼”。行礼过程,第一次拜孔子,第二次拜先生,礼毕,即是孔子的弟子了。私塾先生在新生中设置入学行礼,这样一个“行拜”过程,将求知神圣化、庄严化,既让学生体验求知是件严肃的事情,又传达给学生“我们”以孔子为师,孔子即仁,“拜孔子”即崇尚仁的观念。
在结束“仁”的行礼后,鲁迅又对“仁”进行发问:“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太平广记·卷四七三》记载,“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讲述了汉武帝曾问一种虫,东方朔答道,这是“怪哉虫”,虫由秦朝百姓怨气所化,需行仁政才能化解。然而,私塾先生却没有作答,鲁迅便写“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私塾先生更希望鲁迅自己来探索仁、发现仁,回答的留白是对“仁”的最好阐释。而后,先生“给我的书渐渐加多”[12],先生希望鲁迅能通过阅读经典,亲身感受仁,而不是将“仁”以答案的形式固定化。
“仁”的探索,最终在“读书”事件中走向高潮。当学生们放开喉咙读书时,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等,而当学生们静下来时,只有先生大声吟咏着“铁如意……千杯未醉嗬”,鲁迅“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而实际上,它们都是极好的文章。第一句出自《论语·述而》,告诫人们,想要到达仁,仁就能达到;第二句出自《幼学琼林·身体》,讲述人在嘲笑别人牙齿不全时,自身也露出了不全的牙齿,告诫人们包容他人的缺点;第三句出自《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采用李克用为满足一己之权欲,连年征战,涂炭百姓的故事,劝诫为权者应行仁政。从“我”到同窗,再到先生,看似嘈杂的课堂,实则传达了学生对“仁”的讨论热情,它所进行的是一场关于“仁”的讨论。在讨论之后,正是学堂崇仁的体现:教之以仁,施之以仁。
2.小园空间:尚真
作为三味书屋的辅助性空间,小园空间装载着“童真”,而“童真”依靠于先生的“存真”得以实现。小园空间“虽然小”,但足以变成学生的乐园。当学生们习完课堂知识,趁着课间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可以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也可以“捉了苍蝇喂蚂蚁”。如此童真,正是小鲁迅在百草园中享受的,学在三味书屋,也能与大自然密切接触。当学生醉心于小园的童趣时,先生却“着急了”。每当这时,先生就在学堂里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学生闻声,“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但是,先生在大叫之后,即使有“戒尺”和“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然后对着学生大声道“读书”[12],先生便立刻进入课堂状态,一个外严内慈的先生形象跃然纸上。在这形象之后,是先生对空间的“存真”思考。
“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本性;本原”[15],先生对私塾空间的设置,既有求知空间的学堂,又有娱乐性质的小园,这为保存儿童的本性、本原提供了可能,在这个前提下,学生在课间才有释放童真的条件。也就是说,从学生进入三味书屋的那一刻,先生就已经准备好应对学生的爱玩天性。所以,当学生玩到忘记时间,先生也仅仅表现出“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先生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又构成了第二个“存真”。在三味书屋的空间中,先生以老师身份自居,老师对事物、行为的喜好,直接影响学生对事物的认知,尤其是对事物尚未有明确认知的低龄学生。先生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外刚内柔,无疑是默许了学生的童真,而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有导向作用,这或许也是鲁迅在成年后,既有老夫子的一面,又留存童真浪漫一面的原因之一。
当抛去话语空间,纯粹地从故事空间解读三味书屋,学堂崇仁与小园尚真却显得有些突兀。鲁迅为何从繁多的回忆中选择回忆“三味书屋”?又为何仅仅描写三味书屋的“仁”与“真”?这仍然需要话语空间的对照。1926年,当鲁迅写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鲁迅在厦门大学正经历了“浅薄者之多”[13]的情况。厦大教员并未与鲁迅“交好”,这不仅体现在人事变动上,就连“国文系尚且如此”[13],在厦大的教学也让人不如意。白天,鲁迅要面对教员与教员之间、教员与学生之间的隔阂;夜里,还要面对“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13]的境况。所以,鲁迅在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将精神扎入美好的书屋回忆,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从而消解了话语空间中的消极因子。
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空间文化的美育想象
百草园的空间,蕴含着“原风景”的文化意蕴;三味书屋的空间,蕴含着“崇仁”与“尚真”的文化意蕴。而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积淀,它蕴含着民族的审美传统。美育,即是一种审美活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美育”是一种“以培养审美的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为主要任务的教育”[15]。但是,审美也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它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内涵。
(一)传统教育空间与现代教育空间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作者认知活动的结果”,也具有“文化与知识指向”的功能。其中,空间文化的美育,不仅体现于“百草园场景中的自然美”,也存在于“三味书屋场景里的社会人情之美”[16]。三味书屋作为一种传统教育空间,它蕴含着传统私塾对空间的独特审美,也是鲁迅对教育空间及空间中教师角色的反思。
三味书屋作为一个过渡性空间,从“百草园”过渡到“三味书屋”,也即“儿童天性”向“受教育”的过渡,它对空间的审美,是对教育规律的认知,也是对儿童主体的放大。前教育阶段,儿童尚未形成对自然、人及社会的正确认知,更多通过视觉、听觉、触觉来沟通外界,视觉和听觉的特征,已经在百草园的书写中得到验证。当儿童正享受于百草园的乐趣时,人的成长必然要求接受教育,但儿童却对受教育持一种排斥情绪,正如鲁迅在散文中写道,“Ade,我的蟋蟀们!”[12],这是一种对自然的难以割舍的情绪。为了处理好“儿童天性”与“受教育”两个阶段,三味书屋并没有为了教育而将两者完全割裂,而是在空间的审美中,设置了学堂与小园两种空间,儿童既能在释放天性中得到教育规劝,又能在教育中释放儿童天性。三味书屋对空间的审美,不但是对具象化教育规律的认知,而且是对儿童主体的放大。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教育却淡化了这种空间审美。一方面,现代教育空间,现代化的硬件的确在普及,并且不断朝着这种趋势发展。当教育空间铺满硬件,诸如滑滑梯、跷跷板、电子白板等等,自然的空间却逐渐消失匿迹。这种“硬件式”的审美取向,必然影响儿童对自然的感知,从而导致儿童对自然的审美能力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教师在教育空间中的导向作用也不容忽视。在上述论证中,私塾先生作为教育的执行者,对“儿童天性”采用了严慈并济的策略。对于学生“爱玩”的天性,先生没有过度批评,也没有太多惩罚,这是先生对教育的独特认知。相反,在现代的实际教育中,尤其是儿童教育,却存在诸种扭曲,如变相体罚、持续减少的课外时间和缩减的童趣空间等。教师对教育的审美,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审美;同时,这一审美行为“非主动”地引导全社会接受这类审美。长此以往,必然造成传统教育空间与教师角色的审美放逐。
(二)远去的“田园”与重建的“田园”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田园不仅指代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更指代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状态。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往往在人生受到挫折时,才更能凸显它的审美意义。当鲁迅在话语空间遭受生活的“夹击”时,他被迫离开上海,又被新的团体排挤,在漂泊之中,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虽然当下是这么“离奇”和“芜杂”[12],但是,鲁迅并没有因为现实的苍凉而精神低落,而是从“田园”的空间中汲取精神力量,并在话语空间中进行自我治愈,从而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传统的田园诗人,往往因为现实的不堪而抨击现实,表达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样的“田园”动机,在鲁迅这里已经被终结;同时,他重建了一个自己的田园,开拓了“精神田园”的美育高度。
当下,城市正朝着景观同质化的方向发展,诸如“百草园”的田园逐渐消失。城市的定居者,他们很难接触到传统的自然空间和民间文化空间,而对于城市空间,又充满经济压力与神经紧张;城市景观过渡面——农村,虽坐拥“田园”,但田园已经生活化,难以感知“精神田园”背后的文化审美,反而厌倦其贫穷、落后。也因此田园的存在状态构成了“现实”与“精神”的矛盾:人对所处的空间普遍缺少归属感。这样一种生存困境,必然招致对民族身份与自我身份的不认同,最终引向“精神空虚”。城市发展处于不可逆的趋势,空间中的原初田园必将减少,但精神田园重建不晚。而鲁迅先生,也正是在“精神田园”中完成了话语空间的自我治愈,这便是文学的美育力量。
中华民族自古对“田园”有独特的审美,其美的情操产生了隐逸的田园诗人。但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联系愈加紧密的环境下,以“身隐”取“精神田园”之乐,这是一种“伪田园”“反社会”的田园、逃避生活的田园,并不值得提倡。更应该提倡“鲁迅式”的“精神田园”:它以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主动地调和人与现实的关系。即使话语空间存在诸种不顺,也都将被它消解,不仅带给人精神上的愉悦,而且使人在“原风景”的内蕴中获得幸福感,从而发现美的生活,爱上美的生活。鲁迅对“原风景”的文化体验,既是对田园文化的继承,也是对田园精神的创新,他提供了一种突破传统田园精神的新的“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17],而这种审美倾向,应该作用于成年人,更应该在儿童美育中得到培养。
美育,是“一种以审美活动(包括艺术活动)为主要方式与手段的教育活动”[18],存在于各种审美活动中。鲁迅对传统空间的审美发现,是“记忆过程的主动作用”和“心理活动的整体性”[19]的结果,鲁迅在话语空间和故事空间对照中,完成了对空间传统的再创造。当空间朝一种“狭隘化为物质景观的建设”,“传统文化空间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与纪念价值”却得不到发现的发展趋势[20],应当从“被动性”的接受转为“主动性”的创造。而鲁迅的空间审美,既是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再尝试,又是对空间传统的美育再发现。传统文化与鲁迅血脉相连,更是鲁迅的精神后花园,鲁迅于“普遍”中“超脱”[21],在日常化的空间中,完成了对传统田园、教育空间与教师角色的审美理解,为当代空间美育提供了一种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