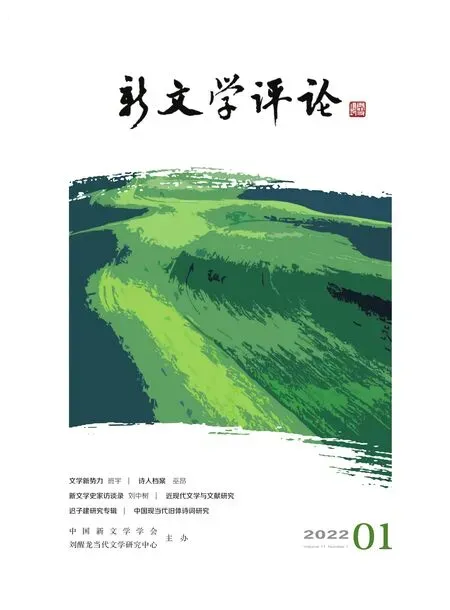走向公共写作:清中晚期旗籍闺秀诗选政
2022-11-16□严程
□ 严 程
清代闺秀诗人的成就超轶前代,前人研究多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江南闺秀,然八旗女子在有清一代特别是清中晚期的诗坛表现,亦有其包含政治地位与性别身份双重属性的特殊之处,值得留意。虽然闺秀诗作大多以别集的形式流传,但要考察其社会影响和自我认知,选政即诗歌选本的编纂活动就成了很好的研究入口。不同于传抄、家刻及大量非公开发行的别集刻本,诗选总集常常带有更强烈的编纂动机和传播意图,而作者对自己作品入选总集的态度及与编者的互动,亦可反映当时的社会心理与文化风尚。在包含闺秀作品的总集编纂中,这一互动更加微妙。总的来说,清代中晚期的旗籍闺秀诗坛,经历了由抗拒选政传播的私人化写作,到贵族化小范围传播、主动投贽,乃至主动以公开显扬为目的的闺秀总集编纂这一转变过程。与此过程相关联的内在因素,是旗人闺秀创作观念之转变,而更重要的外在因素,则需联系清代中晚期特别是咸同年间旗人身份的危机与重建。
乾隆年间,在江南与北京分别掀起的选政风波,可以视作江南闺秀诗坛风尚与八旗文学身份建构的首次碰撞。这次碰撞,一方面确认了女性在八旗诗坛的参与,另一方面亦开启了闺秀诗坛南风北渐的先声——尽管这一开启是从抗拒开始的。
“当时袁简斋树吟坛于江左,铁冶亭操选政于日下,太夫人闻有以女子诗投贽者,咸相与非笑之。其时风气如此,不独太夫人然也。”①这是活跃在乾隆后期的女诗人完颜金墀《绿云轩诗集》序言中的一段话,记录者是她的外孙女那逊兰保。其中提到的袁枚与铁保,正是当时分别在江南和北京操选政的一时名家。袁枚编选女弟子诗集的举动,即使在当时风气较为松动的江南闺秀诗坛,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正是这一震荡,使得越来越多的江南闺秀诗走出闺阁,进入公共视野。铁保所编《熙朝雅颂集》以及稍早的《白山诗介》,则带有更多的官方意味,系统地展示了清初至乾隆年间旗人诗坛的整体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乏旗籍女性的作品。按体裁划分单元的《白山诗介》甚至并未将“闺秀诗”单独列出,只是在次序上置于各体所采男性作品之后。
然而,相比于有幸被《熙朝雅颂集》《白山诗介》收录的少数闺秀诗人,失收的数量可能更多;与江南闺秀诗风之盛相较,旗女崭露头角者更可谓寥寥。那逊兰保在《绿云轩诗集》的序言中记录了这种现象:“我旗籍中士大夫以诗鸣者不可更仆数,而闺阁中则蔡、高两夫人外寂寞无闻。”其中“蔡、高两夫人”指的是活跃于康熙年间的汉军旗闺秀蔡琬、高景芳二人,皆为铁保所著录。蔡琬字季玉,高文良其倬继室,封一品夫人②,有《蕴真轩诗钞》;高景芳是浙江总督高琦之女、世袭一等侯张宗仁室,有《红雪轩集》。这两位诗人颇具代表性。蔡氏贵为一品夫人,其才名随身份得以彰显。高氏亦出身高门,且受到江浙一带闺秀诗风早盛的影响,康熙年间杭州的诗礼之家,大都有家族吟咏的传统,并涌现出蕉园诗社等以亲缘为纽带的闺秀诗人群体。高氏一门风雅,不但父兄工诗、婚后夫妻唱和,且能诗的母亲也成为她吟咏的榜样③。显然,二人能够为操选政者所注意,未必全因高才,与其身份及家族氛围亦不无关系。而更多擅诗的旗籍闺秀则湮没无闻。
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的旗籍闺秀写作仍具有极强的私密性。当时,不少八旗贵族的女性教育水平颇高,“女子入塾诵读,多与男子等,特以风俗懿美”④,但她们的读者仅限于至亲,甚至聊以自娱,不愿公开自己的作品,乃至“及笄后,其尊长率不令治诗词,即间为之,亦相戒勿令外人见”。这样的写作观念,使得这些女性或动辄焚稿,或秘不示人,如法式善母韩氏“工韵语,顾有所作,秘不示人,投稿古罂中,值朔望辄引火焚化”⑤;又如宗室养易斋女史“偶有所作,辄焚弃,罕有存者”。即使像《金墀别集》这样侥幸保留下来的文稿,若非后人整理,亦不会有机会刊刻。尊贵如一品夫人蔡琬,其别集仍然“藏于家,不使外人见”⑥。这些只言片语的记载,皆忠实反映了当时八旗女子私密化写作和抗拒读者的心态。
嘉道年间,恽珠、沈善宝等寓京江南闺秀的到来,不但使得南方闺闱的吟咏风尚北渐,甚至将闺秀诗坛选政的中心北移。这一变动触动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八旗知识女性,为她们带来了满汉融合的诗友群体,也改变了她们的创作甚至传播观念。
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以下简称《正始集》)二十卷以空前的规模收录了有清一代的闺秀诗作,甚至不避时人。在长达数十年留心闺阁诗作的收集过程中,恽珠经历了从母家阳湖到随宦地北京再到就养地汴京的人生轨迹,也因其嫁入完颜氏的汉族才女的身份,在吟咏交游中促进了江南闺秀诗坛风尚的北渐。她在汴京度过的人生最后十年,正是她借助长子麟庆之力集中编纂修订《正始集》的时期。不同于选自《熙朝雅颂集》等来源的前朝闺秀诗人,这段时期所收录的旗籍女诗人,大多与麟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十八卷中的友菊,夫婿与麟庆同门受业;十九卷的一品夫人他他拉氏,其夫与麟庆同榜;又如二十卷著录的高凤仪,是麟庆师友高鹗之女;陆费湘女婿赵贞复,是恽珠诸孙的受业师,程启、李敬华则分别为麟庆幕僚的妻、女等等。按照恽珠的说法,重启《正始集》的编纂正是出于大儿麟庆的请求,而且有赖于他的广为搜求。这些间接寻访的诗人中,旗籍闺秀占据相当的比例,而恽珠早年直接交往的作者,则以汉族特别是江南闺秀居多。于是,嫁入旗籍家族的恽珠,在编纂诗选的过程中通过夫家及子女的社会关系同更多满洲闺秀建立了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正始集》收录的诗作,不再仅源于见闻经验,更多的来自闺秀家人甚至作者自己的主动投贽。恽珠母子的征集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麟庆所收集的闺秀诗中,有相当的数量即来源于此,甚至有他的幕僚从家乡携来自己女性亲属的诗,请他献给正在编纂总集的母亲。当恽珠晚年已无力继续《国朝闺秀正始续集》时,投赠诗稿仍源源不断地寄来,因而不得不由她汉军旗的儿媳程孟梅以及孙女佛芸保、妙莲保、金栗保接替她未竟的工作。孙媳汉军旗蒋重申亦能诗,并于咸丰间重刻毁于兵燹的祖姑遗稿⑦,可见恽珠于完颜氏闺秀吟咏家风之影响。
在《正始集》收录的时人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关注的作者——多罗贝勒奕绘侧室西林春,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顾太清⑧。如果说恽珠带来的江南吟咏风尚是沿着家族内部的亲缘关系播撒开去,那么顾太清则成为满汉闺秀诗人以诗订交、吟咏往来的重要联结。自她于道光十五年同阮元子妇许延锦(云姜)⑨、钱仪吉子妇李介祉(纫兰)⑩以及许乃嘉室石珊枝法源寺一晤,便从此与江南闺秀频相唱和,此后又陆续迎来延锦妹许延礽(云林)、许氏姊妹好友沈善宝(湘佩)、许乃普继室项紃(屏山)及延锦娣钱继芬(伯芳)等江南诗友,并偕妹西林旭一同加入诗友之列,结成秋红吟社。道光二十一年,顾太清的一子二女先后议婚,她与姻亲富察蕊仙、栋阿少如及其姊栋阿武庄又结为诗友。栋阿姊妹即前文提到的《熙朝雅颂集》编纂者铁保之女,她们的母亲莹川是著名的满洲闺秀诗人,亦为恽珠《正始集》所著录。翌年春,顾太清邀约她的九位满汉诗友齐聚天游阁赏海棠,结为秋红吟社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诗课。

同治年间,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在京旗人似乎迎来了短暂的“中兴”,这一“中兴”不仅发生在政治上,亦于文化上有所体现。这一时期,那逊兰保的旗籍闺秀诗人选政具备了性别与政治上的双重属性,并显示出明确的公众传播动机。

尽管未能见到这部书稿,但通过追索那逊兰保和友人集中留下的蛛丝马迹,仍能发现这次选编的动机和对于时政的回应意味。自同治十二年那逊兰保对选集小有所成的叙述向前追溯十年,正是她的挚友百保因节烈获旌之时。萨克达氏百保字友兰,早寡,独抚丈夫妾氏遗腹子麟趾成人,并在咸丰六年太平军围困金华时以“教子作忠,不宜临难苟免”为由拒绝留京。其子赴任金华知府,百保毅然随之,最终于咸丰十一年自沉以殉,其子亦战死。百保的获旌,不同于此前因自守贞节而获得褒扬的大部分节烈女子。在太平军围困、其子作为地方官员战死的情况下,节妇兼英雄母亲百保的殉死使得旌表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那逊兰保得知友人的遭遇后,主动整理重刊了友人的遗作,汇入此前二人的通信,并为作序,在序言中讲述百保的故事,称之为“我旗女子之光”,并陈述自己整理友人别集的动机:“即此以存夫人,使后世传列女者有所考镜。”在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内忧外患之后,满洲旗人心态亟待重塑,与政治危机伴随而来的还有自我认同的危机。这时,列女之于志士、旗女子之光之于民族之光,当然地成为满洲知识女性重建自身信仰的武器。
然而,一向被视为私密写作的闺秀诗何以走向公众视野?又如何以汉字承担满蒙八旗的民族认同?这些回答也在选家留给我们的文字间。事实上,当那逊兰保将自己与百保的私人通信编入集中,以俟“后世传列女者有所考镜”时,她们的写作就已经走出了私密空间。这些诗札不仅表达了挚友间的离情与牵挂,更记录了作为公共事件的围困鏖战中女性个人的生命体验。如果说恽珠《正始集》的编纂仍面向闺秀强调女教与妇学,期待她所选取的才德兼备的女诗人可以成为读者的榜样,那么那逊兰保的编纂,则因其在性别之外另举满洲的旗帜,很可能期待面向一个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强调具有政治意味的旗人身份认同。汉字对于满蒙知识界的意义,在当时亦已全然不是问题。身为黄金家族传人、生于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那逊兰保,嫁入清宗室,可谓满蒙贵族知识女性的典型代表。在自己的诗集中,她留下了这样的自述:“无梦到鞍马,有意工文章……问以啁哳语,逊谢称全忘。”故国鞍马、啁哳乡音,都已为京华文章所取代。这已经不是乾隆时代令袁枚惊愕“虽司军旅,无不能诗”的“满洲风雅”了,而是深入骨髓、“故国为殊方”的文化认同。可以想见,此时的旗人面对统治地位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危机,已经退无可退、别无选择。当然,那逊兰保只是万千闺秀作家中的一员,她的选择无法代表当时广泛的社会风尚。但她通过整理亲友别集、编纂诗抄所做出的走向公共写作的努力,显然包含着政治与性别身份的双重动机。尽管这部总集很可能功败垂成,或者已经散佚,但她的工作之于时代的意义仍然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哪怕短短的一瞥。
清朝统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旗人的消失。事实上,晚清乃至民国,仍有大量的旗人艺文目录、总集、诗文评涌现,旗籍知识分子也在历史变迁中默默承担着书写与记忆的使命。而旗籍女性的声音,却似乎更加微弱了。也许正如单士厘《国朝闺秀正始再续集》《清闺秀艺文志》,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等编者所著录的那样,她们在政治的风暴结束后,依旧回到了“女性”这个身份之下,等待着后来者拂去历史的尘埃,认识她的名字、阅读她的故事。
注释:
①那逊兰保:《〈绿云轩诗集〉序》,完颜金墀:《绿云轩诗集》一卷,光绪初年刻本。
②永名:《〈蕴真轩诗钞〉序》,蔡琬:《蕴真轩诗钞》二卷,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③张宗仁等:《〈红雪轩稿〉序》,高景芳:《红雪轩稿》六卷,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④那逊兰保:《〈绿云轩诗集〉序》,完颜金墀:《绿云轩诗集》一卷,光绪初年刻本。下同。
⑤法式善:《韩太夫人行状》,端静闲人:《带绿草堂遗诗》一卷,嘉庆二年刻本。
⑥法式善:《八旗诗话》,《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页。
⑦蒋重申:《〈红香馆诗草〉跋》,恽珠:《红香馆诗草》一卷、《诗余》一卷,咸丰十一年刻本。
⑧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二十卷,卷第二十,叶第一,道光十一年红香馆刻本。
⑨许宗彦、梁德绳女许云姜,名延锦,阮元子阮福室。
⑩李纫兰名介祉,又字诵冰,昆山人,钱仪吉子钱保惠(子万)室。西林春著,金启孮、金适校笺《顾太清集校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7页)以为长洲李纫兰名佩金者,误。时长洲李纫兰已下世,同书下册第444页有《木兰花·题长洲女士李佩金〈生香馆遗词〉》,编年在道光十五年(乙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