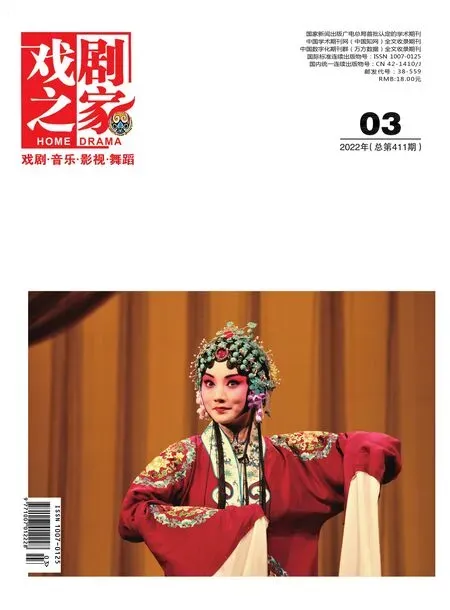“以象罔得玄珠”
——观电影《推拿》中的众生相
2022-11-12史佳琪
史佳琪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庄子《天地》篇中这一则寓言,可以说是他提出的一种“得道方式”。“有形和无形”相结合的“象罔”超越了言辩、理智,成为了通向万物本源——“道”的最佳载体。宗白华先生也在《美学散步》中提及:“‘象’是镜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镜像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艺术作品正是通过对可见的“有”加以表现,来获得以小见大,以有限启无限的效果。在“有无相生”中,通过艺术意象,来把握万物真谛。
一、从“无”到“有”——文字到视听语言的转化
电影《推拿》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原著共计两万五千字,作者毕飞宇的语言风格偏向于意识流,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精妙入微。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品味文字间的未尽之意是获得审美愉悦的重要来源,但是当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字转化为影像实体时,如何保留这种美感却实属不易。但是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讲述对象的特殊性,也就是导演如何将视障者的视角还原出来?如何表现“看得见黑”,这成为影片最核心的美学问题。
(一)“盲视角”的运用——“看得见黑”
视障者“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必然和我们有着不同之处。因此,电影则必须在摄像层面尽可能地贴近视障者的视角,即“盲视角”,通过白天和黑夜的两次同位拍摄,再根据声音的变化后期剪辑,达到黑白光影的转换,这是一种方式。另外手持摄像的晃动也增加了这种“盲视角”的纪实感,视障者对周遭环境的试探,小心翼翼地触摸,不可避免的磕磕绊绊,这些颠簸的镜头将银幕前的观众代入画面中,颇有当今VR 技术的意思。
爱情是电影的重头戏,许多在小说中散乱的、破碎的感觉都被整合起来,通过爱情线索传达给观众。虽然影片整体呈现出纪实性的平淡风格,但是其中两场情事的拍摄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味道。一场是老王和他的“另一张嘴”小孔,这场戏的画面简直是黑成一片混沌,只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两条纠缠的影子;另一场是小马和小蛮,在电影画面的处理上,只展现了两人“事后”的场景,但是这段短暂的肌肤相亲却出现了全片最难得一见的暖光源,柔光是温暖的,打在皮肤上,身体也有了温度。这段画面在书中的描写也很有意思,小马在一场情事过后,陷入了对自我的寻找,他在心里问“我是谁?”这个问题小马一直在问自己却得不到答案,小蛮用手指接住了小马眼里的一颗泪,这颗泪像是多角晶体的光芒,在此刻照亮了她的床。那么由此看来,此刻的光源,更像从小马内心中折射出的一束光,照亮了眼前的世界。
我们看见的是银幕中五彩斑斓的世界,天是蓝的,草是绿的,日光洒在地板上是白的,黑夜是黑的。如果说电影的色彩表现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没有颜色的颜色”的缺席。小说中的小孔和王大夫都是B-1 级,即全盲,没有光感。对于他们来讲,世界就是未知,“黑色”也是无法被想象的。对于所谓的“正常人”来说,我们无法感知到他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影片的独特美感正是在于“还原”了视障者朦胧模糊,似有非无的临界状态。晃动和不安,恐惧和寂静,这同样也是万物本源“道”的混沌状态。
(二)“通感”的弥补——“声音先行”
对于视障者来说,视觉的缺失是“无”,但正是由于视觉的“无”,使得其他的感觉器官变得更加敏感。“沙宗琪推拿中心”停电之后,前台高唯作为一个可以视物的“正常人”却需要小孔的搀扶,在真正的黑暗面前,健全人反而成了瞎子。世界仿佛遵循着一种严格的能量守恒定律,在视障者的生活中,声音是信息的主要来源,除了触摸,他们通过声音和周遭气流的细小变化捕捉空间中的动态。因此在电影中,声音元素的运用多元复杂,弥补了虚焦镜头的模糊,补全了破碎缺损的画面信息。
“雨声”出现在电影中的每个角落,带着南京空气中的湿气,氤氲在屏幕上。同样的雨,落在不同的时空就有了不同的意味,一场雨落在小马和小蛮的相会时,雨声焦躁急促,落在衣服上黏黏腻腻,小马留了下来;一场雨下在午后的清闲时,小孔和金嫣在屋里开着女人间的玩笑,雨声闷闷的被关在了窗外,老王和泰和在屋檐下“连襟”一样分吸同一盒香烟,“淅淅沥沥”的雨声又跑了出来;一场雨下在小马和小蛮出走后,饭菜和洗发水的味道混合着空气中泥土的芳香,规律的雨声让人想要沉沉地睡去,是家的节奏。
一些细小的道具声,在沉默的空间中显得更加突出。小马总是给他的小闹钟上发条,“吱吱嘎嘎”的声音;老王在无措时喜欢用夹子夹手指,“咯哒咯哒”的声音;风铃被风吹过,被手指拨弄,“叮叮铃铃”的声音……这些细节各自有他承担的象征意义。比如说小马的钟,象征着时间,在原著中,小马是在心里把玩时间,时间的行走就是“咔嚓咔嚓”的声音,所以“他吃饭的时候会把米饭吃得咔嚓咔嚓的,他呼吸的时候也能把吸气和呼气弄得咔嚓咔嚓的。如果冷,他知道冷了多少个咔嚓,如果疼,他也知道疼了多少个咔嚓。”在文字向电影的转换时,内心丰盈的活动被一只永远在上发条的钟外化了。
声音的发出更多的时候显现为一种嘈杂的内心状态,由于视觉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通过声音确定周遭事物的存在。然而当声音落幕,一切喧嚣化为尘土,世界从无序走向统一,在万籁俱寂中化为一片虚无。
二、从“有”到“无”——以象罔得玄珠
(一)命运无常——小马的失而复得
影片对小说最重要的改动是小马复明的桥段以及他与小蛮的爱情延宕,这个改动对于电影的意义非同小可,绝不仅仅是情节的增加,也不是所谓的中国式团圆大结局。伴随着lensbaby 移轴画面的出现,虚实镜头在小马和小蛮间不停切换,影片最后只留下了复明小马的闭眼微笑,他作为全片中唯一一个重回光明的人,在获得爱情那一刻,却选择“闭上眼睛”,重回黑暗和虚无。这一系列操作是整部影片中最耐人寻味的,就像是小说中隐隐约约的象征意味一样,充满哲学性。导演也许正是通过这种戏剧性的处理,来表现全人类的共同命题:爱情。正如片尾曲唱的那样“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会在第一天就闭上眼,然后什么都看不见。”当小马学会了关注小蛮后,他的钟掉在了地上,时间已经将他抛弃了,再也没有响起来。小说中写到“在时间面前,每个人都是瞎子。”影片中则隐晦地向观众传达了“在爱情面前,人人都是瞎子。”
无论是作为小说还是电影,《推拿》始终都是一部群像戏,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是“人人生来皆平等”的。不管是被视障者视作鬼神的健全人,还是作为老板的视障者,他们的命运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摆弄着,可是到了电影中,上帝的天平唯独偏向了小马,从“有”到“无”的剥夺,从“无”到“有”的恩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命运的无常,没有人能够逃脱。
(二)沙宗琪的渴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沙老板叫“沙复明”,可是他却没有复明。在所有的人物中,沙老板是最渴望“看得见”的,也是最想要融入“主流社会”的。短暂的青春期爱恋曾在少年的沙复明心上开了一个口子,从这个口子看出去,作为一个视障者的沙复明窥见了所谓的“主流社会”,他倾尽一生都想要进入那个“世界”。那个留在过去的姑娘用“冰”和“手”刻下了他永生都逃不脱的枷锁。沙老板喜欢都红,也是因为健全人夸她“美”。所以“沙复明”没有复明,不仅仅是其生理的原因,他最终将自己搞成那副样子,是因为他自我的存在永远依赖于他者,只有在别人的目光中,沙复明才是“有”,才存在这个世界上。
在沙复明被都红拒绝后,他一边以头撞墙,一边朗诵三毛的《如果有来生》,诗中是这么写的: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荫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从不依靠,从不寻找”,这何尝不是沙复明一生都在追逐而不得的东西呢,沙复明和小马是两个哲学家,他们一个问出了“美是什么?”另一个问出了“我是谁。”但是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所追逐的无非是如幻似影的虚无罢了。
三、结语
“命是看不见的,盲人也看不见,所以,盲人离命运的距离就格外的近。”视障者闭塞了一条与外界的通道,脸上的眼睛虽然看不见,心里的眼睛却看得更明白。无形的“大道”早已内化在中国人的生命智慧之中,融入到艺术作品的每个角落,让我们这些旁观者来一探究竟。
小说是文字的国度,电影是视听的旅途。一个万丈高楼平地起,从开始便打好地基;一个戏罢离场,只是人间一场没有来头的游戏。从文字到视听,这其中的转换和取舍就像是冒险和奇遇,又像是能量的守恒,是两个侠客不动声色的交手,更是两个江湖隐而不宣的秘密。从毕飞宇的原著到娄烨的电影,看不见的文字和江湖都变成了看得见的画面。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所以“有无”“虚实”都是辩证统一的存在,庄子用“似有非无”的“象罔”求得了“玄珠”,那么对于《推拿》来讲,就是用“不敫不昧”的艺术意象求得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叶郎:《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 年版。
③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④李蓓蓓(录音整理).对话电影《推拿》主创——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推拿》映后主创交流会.数码影像时代,2014 年第12 期。
⑤毕宇飞:《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