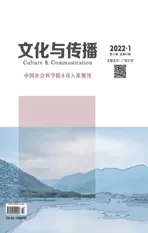福柯治理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美学指向
2022-11-07谭嘉仪
谭嘉仪
福柯的治理思想中将权力在政治领域的展布溯源至希伯来牧领权力的隐喻之中,希伯来文献中大量的“牧羊人—羊群”隐喻显示了治理思想的雏形。随后,经由基督教大量修改的牧领权力与政治—法律权力互相融合,并正式踏入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域,形成了“被权力控制得天衣无缝的恶魔国家”。在福柯所言的恶魔国家之中,基督教的牧领制度、国家理性、自由主义等治理形态逐一显现,最终完成了西方社会治理谱系的建构。
一、国家治理与生命政治
作为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形式,国家理性与自由主义都被福柯放置在生命政治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在治理过程中,国家理性逐渐意识到人口并非国家的附属品,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人口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质量。因此,人口在18世纪正式成为国家理性的治安目标。然而,由于国家理性的“过度治理”,19世纪以来,人们将“管得太多”的情况与“权利和安全被剥夺”所带来的危险相联系,维护和保障人们权利与安全的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而在“自由与安全性的游戏”中,福柯仍然将自由主义安置在生命政治的框架之内展开分析。他将19世纪出现的这一基本现象称为“权力负担起生命的责任”。这是“对活着的人的权力,某种生命的国家化,或至少某种导向生命的国家化的趋势”。可见,在19世纪,至高权力已然受到生命权力的影响而变更其原有的存在意义。过往,至高权力通过生杀大权对国家进行统治;而后,生命政治则更倾向用各种治理手段来提高生命的质量。当生命权力替代了至高权力,人在国家层面就不可能再被治理所无视,人被正式纳入治理范畴中,生命政治随之正式回归到治理范畴当中。
生命政治的出现是牧领权力在国家治理中蛰伏已久后的回归。实际上,“生命政治(Biopolitique)”并非福柯的原创概念,但他却赋予其全新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后期,福柯的研究中心从“规训权力”转向“生命权力”。借此契机,“生命政治”被重新激活与再度定义。有别于科耶伦、纳粹主义在“生命统治”意义上的定义,福柯将生命政治定义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并指出其核心特征就是对“生命权力”的使用。福柯本人也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明确谈及这种新的权力结构模式:“如果说,在19世纪,权力占有了生命,如果说,在19世纪,权力至少承担了生命的责任,那么也就是说通过惩戒技术和调节技术两方面的双重游戏,它终于覆盖了从有机物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随后,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具体谈论了生命权力自17世纪以来发展出的两种主要形式:其一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即“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规训机制;其二是“人口的生命政治”,即“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调整控制。可见,肉体层面的规训机制与人口层面的调整控制,构成了生命权力发展的两个极点,通过二者的联结介质——“性”在惩戒与调节中的表现,逐步形成现代国家的生命政治模型。
生命权力是通过规范的内化,对生命行使着全方位的管理职能。由此看来,生命权力不再以死亡威胁生命,至高权力的绝对法律也逐渐被生命权力的现代规范所取代。可见,福柯此时所关注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展布的微观政治,这也意味着福柯关于治理的研究从国家治理层面进入个体治理层面。同时,由于规训权力转向生命权力的发生,国家政治也随之转向了生命政治。
二、个体治理与身体规训
“‘治理’并不只涉及政治结构或国家管理,它也表明个体或集体的行为可能被引导的方式——孩子的治理、灵魂的治理、共同体的治理、家庭的治理和病人的治理。”可见,治理所覆盖的领域具体且广泛,无论是在组织结构还是主体行为的层面,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都是获得“官方认可”的。因此,除了针对组织政治、经济等合法构成形式展开管理外,治理还被视为对个体可能性行为的组织实践,即“个体治理”。它有别于国家治理的权力实践,指的是权力在进入微观的个体层面后,对个体实施的引导、调节等干预性实践。作为覆盖他人可能性行为模式的实践,个体治理涉及人的灵魂与身体两个重要方面。
管理灵魂并非个体治理的最终目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最终实现身体规训。因为,对身体的规训才是国家治理与个体治理所追求的更高目标。但个体治理实践得以发生是需要以国家治理实践为前提的,所以个体治理仍服务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也作为个体治理的实践基础而一直存在。与国家法律权力对主体的压制不同,规训权力塑造并生产主体。
一方面是国家规训的运作。“以权力—知识装置为基本治理机制,以身体的解剖政治学为特征,在不同历史社会条件下,针对个体进行管控的治理技艺”的规训权力生产“驯顺的身体”,为国家治理与发展服务。从基督教时期,牧领权力对个体灵魂的管理与自我形式的摧毁,到国家理性中,将生活和人口的质量视作是其治安目标,生产“驯顺的身体”,再到自由主义中,将个体的安全与权利作为规训的目的,而后逐渐演变为投资生命的权力为个体提供福利,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都无法避免权力—知识装置的运作。可见,规训权力得以延续至今,其不断演变的运作方式与贴合时代的实践目的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是关于个体化权力的展布。福柯并未将过往探讨理性化与权力之间联系的方法(分析主体经验与各种权力技术之间的关系),用于开展对“个体化权力”的研究,而是对“与‘个体化权力’问题相关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进行独立的研究。因为福柯意识到权力关系正在发生转变,而这一转变的结果,正逐渐地形成一种与“趋向集权国家的演进过程”相对的权力技术,其以个体作为发展方向,并“旨在以一种连续、持久的方式统治个体”。福柯将这一个体化的权力技术称为“牧职”。它的现实表现形式是牧领权力,核心是通过救赎式的教义,使个体的灵魂主动接受基督教的管理,并且在基督教的治理之下摆脱自我。此时的牧领权力是得到个体认可的,并与其受众群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同时,通过个体化权力在身体领域的运作,个体被塑造成多样的主体。所以,无论是疯癫主体、罪犯主体、疾病主体甚至是性主体的构建,都是权力在个体身体之上展布的结果。为了摆脱权力对主体的规训,福柯在构建生存美学的过程中,就十分强调“身体”与“体验”在审美经验之中的重要位置,这也为生存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三、自我治理与主体自由
“国家理性以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针对整个人口实施治理,市民社会展开各种文化与政治的集体性治理,个体运用自我技术展开主体性的治理。”治理并不仅是在国家或个体的层面之上运行,权力的运作使其能够广布于社会生活中。在转向微观权力研究后,治理被福柯视作一种观照自我的美学实践。
1980年,福柯的研究对象发生转变,他重点关注的不再是“个体如何被治理”,而是开始着重探讨“个体如何进行自我治理”。同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开设课程——对活人的治理,该门课程主要讨论了公元2世纪以后基督教的自我治理艺术。福柯认为,关于“自我治理”的深入研究,首先应该溯源至其表现最为突出的基督教忏悔实践中。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对人的治理不但体现在其信徒具有遵守和服从等行为,而且还特别要求其信徒具有“真理行为”。而所谓“真理行为”的实践,除了遵守教义、服从教会等规则外,还要求主体坦白自身的过错与欲望、揭示自身的主体与灵魂状况等真相,这被视作是实现个体的自我治理的必要行为。对此,福柯敏锐地察觉到,基督教提出“真理行为”的目的实际上并不是为了个体能够确立自我的绝对主权,而是试图通过技术的运作,使信奉其教义的人们摆脱自我、摧毁自我,最终屈从于其牧师权力之下,以巩固宗教在人们思想当中的权威性,进而维护权力所有者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可见,人们试图借助基督教的治理方式来实现自我治理是不可行的。人要实现自我治理是需要借助自我技术的。所谓自我技术,即“无疑是存在于一切文明中的对个体进行建议或规定的一系列措施,为的是按照某些目的、通过自我控制或自我认知的关系,去确定个体的身份、保持这种身份或改变这种身份”。福柯在自我治理的研究中,一直不断寻找能够在国家理性的治理框架内使人成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和实践。最终,他在生存美学的研究过程中找到了突破口——人对自我的关注与为自由而实践。而关于“主体问题”和“自由问题”的讨论早已遍布福柯的治理思想中,他甚至坦言其研究的总主题就是主体,治理作为其研究的一部分,对于主体的讨论自然必不可少,而自由则被称作治理得以发生的基础。因此,对于二者的考察与探讨,有助于我们从治理思想中找寻到其隐匿的美学内蕴,以便更为直观地在美学视域之下对治理思想进行再挖掘,从而对福柯的生存美学进行更具体的反思。
四、生存美学与审美治理
无论是在治理思想的探讨中,还是在生存美学的阐释中,福柯对主体的关注都使得他不得不去考察自由问题。在他关于治理问题的论述里,自由并没有站在治理的对立面,相反,正是基于对国家理性的反思与批判,自由主义才得以正式生成,并最终成为治理实践的重要运作机制而存留至今。然而,在对福柯治理思想的诸多探讨中,自由常被等同为审美。自由总是被认为游离在治理及其实践之外,并被视为秩序与规范的不和谐音调;审美同样游离在治理之外,并且占领着纯粹自由的领域。实际上,福柯的生存美学中潜藏着一种隐喻——自由是外在于治理却内化于审美的效果,即审美的目的是自由,治理不与自由对立,审美与治理二者互不冲突,但也绝不能将二者等同。在生存美学的理论探索过程中,也涵盖着自由实践与自由思考等重要部分。福柯在生存美学中所倡导的实践就是一种以“关怀自我”为核心的生活、实践方式。福柯试图通过重构生存美学,在当代现实世界中建立一个既基于又异于古希腊的审美乌托邦。这并非鼓吹人们摆脱治理,而是使人能够宣告自己的要求——不应该被“那样”治理。所谓的“那样”治理,指的是通过道德、法律等否定性的外力方式规训人,从而使他们能够“循规蹈矩”地接受组织机构的治理。为了使这些外力方式更有效,西方国家会通过教育引导人们将这些管理机制内化成习惯。然而,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使所有人都接纳管理。因为美学的光一直照射着资本主义的幽灵。福柯的生存美学更是直接揭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伪善,在福柯看来,治理的出现应该是推动人的自治。也就是说,生存美学倡导一种美学化的自我管理,并要求人们最充分地实践这一生活方式。
至此,治理思想与生存美学的内在逻辑逐渐清晰。福柯所言的治理实际是唤醒人们回归自我治理的先声,而自我治理则是生存美学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因此,治理思想的思考与研究是福柯晚年得以对生存美学展开深入探讨的重要基础。通过主体对自身发展与自由的关注,人的主体性得以在自由主义的治理实践中被塑造。这一塑造不是道德、权力乃至知识的规训,而是蕴含对话机制的诉求实现。人最原始的主体性中并不存在接受治理的能力,对治理的理解与接受的能力,是需要培植和训练的。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平衡伦理道德与知识规范的新型生活方式,人也逐渐在其中丧失自由实践与自由思考的能力,在屈服与反抗的拉锯中变得麻木,逐步成为统治者权力框架内的重要组成元素。福柯对治理思想的再现与生存美学的重构,对个体起到一种唤醒与引导的作用,使人能够更加积极充分地参与到其自身发展过程的管理与监督之中,使其更加具体地感受到主体性的存在,从而能够实现关怀自我的审美生存核心。
五、结语
福柯对治理的研究虽未深入实证层面,也并未在其后期生存美学的研究中对治理与审美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充分阐释,但福柯治理思想的轨迹——从前期对权力的迷恋转向后期对自我的关注,在文化政治意义层面具有的美学指向,为理论的后来者提供思想遵循轨迹,继续对治理与审美的关系展开研究。托尼·本尼特正是基于对福柯治理思想的全面考察,梳理出治理与审美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实证层面的“审美治理”概念,为治理的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具体方案和有效路径。“治理”的理论指向也从文化政治层面进入美学实践层面,成为具有批判功能的现代美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