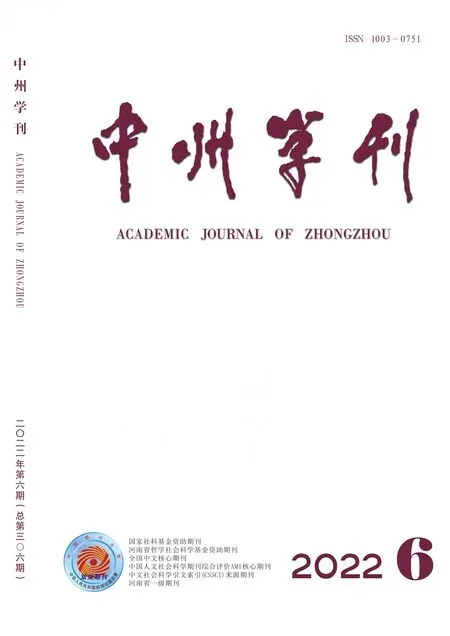文本差异与思想分歧*
——《韩非子》与《孔子家语》“重文”现象研究
2022-11-04杨玲
杨 玲
《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与周秦汉典籍多有“重文”现象,学界对其与《说苑》《礼记》《新书》《荀子》及相关出土文献的“重文”研究屡屡见之,但是关于《家语》与《韩非子》的“重文”研究却很少。即使是一些持《家语》乃拼凑而成观点的学者,在论及《家语》所“抄袭”的典籍时也不会想起《韩非子》。这是因为《家语》与《韩非子》的“重文”很少,只有五组,不过千余字。但是,就研究价值而言,这五组“重文”非常值得重视。作为法家和先秦学术的集大成之作,《韩非子》没有遭受焚书之厄,流传有序,文本的真实性、可靠性非常高。这就意味着以它为“标准文本”对《家语》进行“重文”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将更加客观、准确,这无论对《家语》还是《韩非子》均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三组低相似度“重文”的对读和分析
《韩非子》与《家语》的“重文”有《治国者不可失平》《子路餐民》《三公问政》《饭黍啖桃》《不以容言取人》五组,依相似度高低,可将其分为两部分:《治国者不可失平》《子路餐民》《三公问政》属于文本差异显著、相似度较低的三组“重文”;《饭黍啖桃》《不以容言取人》属于文本差异微小、相似度很高的两组“重文”。下面分别对其进行对读分析。
1.《治国者不可失平》
《治国者不可失平》分别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和《家语·致思》,同时还见于《说苑·至公》。《家语》和《说苑》的记述差异非常小,而《家语》和《韩非子》的记述差别却很明显。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曰:
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跀者守门。(1)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者曰:“尼欲作乱。”卫君欲执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2)子皋从出门,跀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问跀危曰:“吾不能亏主之法令而亲跀子之足,是子报仇之时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于子?”跀危曰:“吾断足也,固吾罪当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狱治臣也,公倾侧法令,先后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狱决罪定,公憱然不悦,形于颜色,臣见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悦而德公也。”(3)……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说明:引文中所标序号乃笔者所加,为突出构成对比的内容,下同。)
《家语·致思》曰:
季羔为卫之士师,刖人之足。俄而,(1)卫有蒯聩之乱,季羔逃之,走郭门。刖者守门焉,(2)谓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逾。”又曰:“彼有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罢,季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断足,固我之罪,无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君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悦君也。”(3)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可以看出,《治国者不可失平》在《家语》和《韩非子》中的中心环节相同,都是说孔子的一个学生子皋(子羔)做狱吏时对一个违法者施刑,后来此人有机会报复子皋,但他不仅没有报复,反而出手相救危难中的子皋。原因是他理解当初被施刑是自己罪有应得,也是子皋为维护国家法律不得不为之。但在细节上,《韩非子》和《家语》的记述有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与《韩非子》相比,《家语》起首没有“孔子相卫……”这句话。
第二,《家语》的记述中,事情的起因不是《韩非子》所说的有人诬陷孔子,而是因为蒯聩之乱。《说苑校证》说:“孔子未尝相卫,子羔亦未尝为政,《家语》虽晚出,于事未合。”又就《韩非子》中所言“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解释说:“乃孔悝之难传闻之误。”孔悝之难即蒯聩之乱。由此可见,《家语》的记述更符合历史事实。
第三,《家语》所记季羔逃跑过程比《韩非子》要详细得多。《家语》中,守门人先是让季羔翻墙以逃,又让其钻洞逃跑,季羔都以君子耻于此类行为而拒绝。后来守门人让他躲到密室里,他才答应。而《韩非子》中对子皋(即季羔)的逃跑过程只一句“子皋从出门,跀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完结。
第四,两书末尾均有孔子对子皋的评价,但评价内容不同。《家语》中孔子的评价是“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韩非子》中孔子的评价是:“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这个不同与上文第三个不同鲜明体现出《家语》和《韩非子》思想上的分歧。季羔不肯逾墙、钻洞,是因为这种举动有失君子风范,所以不为。这体现出他在危急时刻仍不忘维护君子尊严,是儒家士子的典型表现。但《韩非子》恰好没有这一段描写。孔子对季羔行为的评价体现的正是他对法治的看法:即使不得已要使用刑罚,也不能忽略仁爱。《韩非子》所引孔子评价表现的则是韩非的法治思想:治国最重要的是公正公平,而官吏执法就是公正公平的关键表现。二者虽然都是称赞子羔,但是《家语》侧重称赞子羔执法不忘仁德,《韩非子》侧重称赞子羔执法坚持公平,不因情害法。此外,二书句式也明显不同。《家语》的句式多用语气词,读起来迂曲舒缓,与《论语》风格很相似。《韩非子》的句式对仗工整,简短有力,干脆利索,正是典型的《韩非子》散文的风格。
2.《子路餐民》
《子路餐民》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家语·致思》和《说苑·臣术》。《家语》和《说苑》的描述差别极小,与《韩非子》则有明显的细节不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述如下:
(1)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当此之为,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2)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餐之?”(3)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礼也!女之餐之,为爱之也。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4)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
《家语·致思》的记述如下:
(1)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其民修沟渎。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一箪食、一壶浆。(2)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3)子路忿然不说,往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匮饿者,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廩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4)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矣。”
《韩非子》和《家语》关于这则故事记述的中心情节依然相同,其不同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韩非子》说此事发生在季孙相鲁、子路做郈令时,《家语》所记则发生在子路为蒲宰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子路治蒲的记载。《荀子·大略》亦言:“晋人畏子路不敢过蒲。”《家语·辩政》亦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但子路为郈令却史无记载。《说苑校正》说:“《韩子》载此事作‘为郈令’,非也。《史·孔子世家》《弟子传》皆言‘为季氏宰’,郈乃叔孙氏邑,与季孙氏无涉。而《韩子》下文言‘季孙让之’。尤为抵牾,当以本书(指《说苑》)为是。”《说苑》与《家语》的记述相似度非常高,这就说明在细节真实上,《家语》《说苑》均胜于《韩非子》。
第二,孔子反对子路的做法,让子贡去阻止,对此《家语》的描写非常简单,仅“使子贡止之”一句。《韩非子》的描写则要具体生动得多,既有行为描写“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又有言语描写“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餐之”,通过言语行为的详细刻画来体现韩非本人对子路僭越之行的反对和批评。
第三,二书中子路和孔子发生争论时所说话语不同。《家语》中,孔子只是说子路的行为有彰君恶、显己德之嫌,同时教导子路,这件事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提醒君主去赈济民众,而不是自己直接出面去帮助他们。虽然是批评,但孔子的言语并不激烈,而是比较和缓。《韩非子》中,孔子对子路的批评则异常严厉。他将子路的行为上升到不知礼、不守礼的高度,而且还特别指出子路的行为有僭越之嫌。其中体现的正是《韩非子》对礼的认识和重视。《韩非子》认为礼的核心内涵就是不逾越,不逾越不仅仅指职权,还包括施恩,超出职责范围的施恩就是夺爱,是一种变相的越权。依《韩非子》的观点,越权是为臣之大忌,是君主不能容忍的行为。
第四,二书对子路所为产生的结果记述不同。《家语》中故事终止于孔子对子路的批评,至于是否有人怪罪子路,文中没有描写。《韩非子》中则是孔子话未说完,季孙的使者就已经赶到,对孔子及其弟子大加指责,于是孔子离开鲁国,子路的行为导致了严重后果。这一情节恰和开头“季孙相鲁”首尾呼应,故事结构完整紧凑。将《子路餐民》和《治国者不可失平》联系在一起,我们发现,它们在《家语》和《韩非子》中的文本差异恰好与各自所属典籍的思想倾向一致:《韩非子》中独有的内容表现的是法家思想,《家语》中独有的内容表现的是儒家思想。
3.《三公问政于孔子》
《三公问政于孔子》见于《韩非子·难三》《家语·辩政》《尚书大传·略说》《汉书·武帝纪》《说苑·政理》及《后汉书·崔骃列传》所载崔寔《政论》。《汉书》及《后汉书》所载没有详细故事情节,只是寥寥数语把三公问政一事概括出来而已。如《汉书·武帝纪》:“盖孔子对定公以徕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韩非子》《家语》《尚书大传》《说苑》中的记述则对话详细,情节完整。《韩非子·难三》的描写如下:
(1)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2)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3)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4)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
《家语·辩政》的记述如下:
(1)子贡问于孔子曰:“昔者齐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谕臣’;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悦近而来远’。三者之问一也,而夫子应之不同。然政在异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4)齐君为国,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伎乐,不解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节财’。(3)鲁君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诸侯之宾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2)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此三者所以为政殊矣。《诗》云:‘丧乱蔑资,曾不惠我师!’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又曰:‘乱离瘼矣,奚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岂同乎哉?”
二书记述的不同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开头部分不同。《家语》开始于子贡的一段回忆性发问:“昔者……?”《韩非子》则直接以三公与孔子对话开始,对话结束,“三公出”,子贡才向孔子提问。很显然,《家语》的叙述更符合实际,《韩非子》的叙述则更富有故事性。楚国的叶公、鲁国哀公、齐国景公同时“问政”于孔子史无记载,在现实中也不太可能。
第二,《家语》和《韩非子》关于三公问政的顺序刚好相反,对三公的称呼也不同。《家语》中的问政顺序是齐君、鲁君、叶公,《韩非子》中则是叶公子高、鲁哀公、齐景公。《说苑》、崔寔《政论》与《汉书》《尚书大传》所记问政顺序和对三公的称呼都与《韩非子》相同(除《武帝纪》应是疏忽把叶公误为定公之外)。研究《说苑》《家语》与相关出土文献“重文”的学者发现,《说苑》比《家语》更接近出土文献。由此说明,在三公问政顺序和对三公的称呼上,《韩非子》保存了文献原貌。而《家语》的编纂者从儒家礼的角度考虑,认为叶公非国君,所以特意称鲁哀公、齐景公为鲁君、齐君以示区别。从叶、鲁、齐三地的位置来说,齐、鲁属中原之国,叶地属楚,是蛮夷之国,因此不能把叶置于齐、鲁之前;就实力而论,齐最强,鲁次之,叶地是叶公的食邑,又次之,所以《家语》以齐、鲁、叶为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引证《三公问政于孔子》的诸书中,《家语》是典型的儒家典籍,但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诏书中引用的《三公问政于孔子》却和《家语》不同。笔者以为这种不同正说明一个事实:武帝时《家语》尚未编纂成书。否则,以武帝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不可能忽略这一儒家经典。而《韩非子》虽然在汉代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境地,但批判也是一种宣传。武帝应是从《韩非子》中看到《三公问政于孔子》,进而概括引用到自己诏书里,使得《汉书·武帝纪》中武帝所引《三公问政于孔子》的顺序及对三公的称呼均与《韩非子》相同。







从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三公问政于孔子》在《家语》和《韩非子》中的差异也多与它们各自表达的思想一致。特别是《家语》引诗一段,尤能显示其儒家特色。而《韩非子》中这一则故事借助文辞变化对法家思想的申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治国不可失平》和《子路餐民》那么显明,但略加分析后发现它并不逊于前两者。
二、两组高相似度“重文”的对读和分析
相比较上文所论三组“重文”,《饭黍啖桃》和《不以容言取人》的相似度很高,差异比较小。《饭黍啖桃》是《韩非子》和《家语》中相似度最高的一组“重文”。《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的记述如下:
孔子(1)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2)请用。”仲尼先(3)饭黍而后(4)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5)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家语·子路初见》的记述如下:
孔子(1)侍坐于哀公,赐之桃与黍焉。哀公曰:“(2)请食。”孔子先(3)食黍而后(4)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为(5)食之也。”孔子对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谷之长,郊礼宗庙以为上盛。果属有六,而桃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庙。丘闻之,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之下者,是从上雪下。臣以为妨于教,害于义,故不敢。”公曰:“善哉!”

从词语的使用区别可以看出,《韩非子》中的用词比《家语》丰富准确。先秦时期,“食”的对象比“饭”宽泛,“饭”主要针对五谷杂粮而言。《家语·饭黍啖桃》和《韩非子·饭黍啖桃》对“饭”“食”的使用正与此吻合。《韩非子·饭黍啖桃》中两次使用“饭”字均与“黍”相连。另外,《韩非子》中还出现了“啖”,与其相连的是“桃”。而“啖”作为吃时的本义就是“咬吃硬的或囫囵吞整的食物”。除了“食”和“饭”,《韩非子》中还有一个表示吃的词“用”,它表示“吃”的含义时是婉辞,“请用”是鲁哀公对孔子说的话,比起《家语》中的“请食”,显然前者更符合哀公的身份。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饭黍啖桃》在《韩非子》和《家语》中的记载没有思想内容上的差异,但从字词上可知,《家语》的时间更早,更质朴。而《韩非子》所用词语不仅丰富,而且在准确生动上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不以容言取人》是《韩非子》与《家语》中一组被忽略的“重文”。此组“重文”在两书中表达的思想完全相同,都是强调不能以貌、以言取人,言辞上二者差别也不大。《韩非子·显学》的记述如下:
(1)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2)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家语·子路初见》的记述如下:
(1)澹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辞,而智不充其辩。(2)孔子曰:“里语云:‘相马以舆,相士以居,弗可废矣。’以容取人,则失之子羽;以辞取人,则失之宰予。”
通过比对发现,《韩非子》比《家语》多了“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几个字,少了“里语云:‘相马以舆,相士以居,弗可废矣’”之句。前一个变化使《韩非子》的行文更加详细生动。“几而取之”是说孔子初见澹台子羽、初听宰予之言时对澹台子羽产生极好印象;“与处久”后,认识则发生截然变化,前后对比明显,由此突出《韩非子》一向倡导的在实践中培养、检验人才的观点。《韩非子》中删除《家语》“里语云:‘相马以舆,相士以居,弗可废矣’”之句,是因为增加“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这几个字后意思已完整。相比之下,《家语》的语言比《韩非子》要朴质许多。《韩非子》句式整齐,对偶非常工整,雕饰痕迹明显,应该经过加工和修改。

通过以上对《家语》和《韩非子》五组“重文”的对读分析我们发现,《治国者不可失平》《子路餐民》《三公问政》在二书中最显著的不同恰好与儒法思想的分歧一致:凡是带有明显儒家色彩的文辞,在《韩非子》中都没有;凡是带有明显法家色彩的文辞,在《家语》中也没有。《饭黍啖桃》宣扬的贵贱有别思想、《不以容言取人》提倡的实践检验人才的标准,是儒法两家都赞同的,恰好这两则寓言在二书中文本的相似度也最高。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问题:《家语》和《韩非子》“重文”的这种异同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家语》中尤能表现儒家观念的细节在《韩非子》中恰好被省略?《韩非子》中尤能表现法家观念的细节在《家语》中刚好缺失?《饭黍啖桃》和《不以容言取人》表述的思想为儒法二家共同所持,恰好它们在二书中的记述言辞差别也最小。这些是偶尔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三、《家语》与《韩非子》“重文”产生的原因

从前文对五组“重文”的对读分析可以看出,《家语》关于《治国者不可失平》《子路餐民》《三公问政于孔子》三章的记述没有前后矛盾或不合历史事实之处,而在《韩非子》中,三者均存在与历史事实明显不符的细节。另外,关于《三公问政于孔子》,《家语》的记述比《韩非子》完整详细得多,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家语》对这三则故事的记述早于《韩非子》的依据。从《不以容言取人》可以看出《家语》的记述比《韩非子》更质朴,因此也可以证明《家语》在时间上应早于《韩非子》。最重要的是,从上文对《饭黍啖桃》用词的分析来看,《家语》所记比《韩非子》早毋庸置疑。所以,不存在《家语》抄录《韩非子》的可能。

排除了前两种原因,《韩非子》和《家语》“重文”产生的原因只能是第三种,即二者使用了相同文献。如此一来,我们需要继续追问并解决以下问题:这些文献从哪里来?韩非如何看到?《家语》的编纂者又如何看到?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从根源上知晓《韩非子》和《家语》“重文”的原因。而要解开以上谜底,关键在韩非的老师、孔孟之后重要的儒学大师荀子。


这些举动一方面说明荀子已着手辨析真“孔子言”和假“孔子言”,另一方面说明荀子已收集、过目了相当数量的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资料。如没有这一前提,辨伪、批判、弘扬等围绕着孔子及孔子弟子言行进行的活动均无从谈起。


二是有意通过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情节,增加所述内容的故事性,突出故事的虚构性,使其与文献原貌——真正的历史事实区别开来。譬如《治国者不可失平》开篇有意虚构“孔子相卫”之事,使故事的起因由子羔变为孔子,一方面可以借助孔子的名气增强故事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与结尾孔子对季羔的评价相呼应,同时也提醒读者,这是寓言故事,而不是历史史实。同样的做法也体现在《子路餐民》中。这个故事开篇即把原来的“子路为蒲宰”改为“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而实际上子路从没做过郈令,而且郈是叔孙氏的封邑,与季孙无涉。《三公问政于孔子》中“三公出,子贡问”一句也提醒读者这是寓言故事,而非历史。
韩非是一个写作态度认真的学者,他不会无缘无故混淆寓言故事和历史史实。孔子是韩非重视的一个历史人物,《韩非子》一书中,孔子出现四十余次,韩非有时批驳他,有时又称他为圣人。这是因为虽然孔子的某些观点不被韩非认同,但也有一些观点,如君臣观念、等级观念,给了韩非很大启发,被他汲取融入自己的法家思想中。韩非师事荀子,不可能连孔子和声名卓著的孔门弟子如子路、子贡的基本经历都搞不清楚。孔子是否在卫国为相,子路是否在郈为官,子贡是否见过三公同时问政于孔子,诸如此类的事情对于博学多才的韩非来说不可能搞错。所以,韩非笔下此类“错误”是他把一般的历史故事改编为解说、论证法家思想的寓言故事的需要。《韩非子》中《子路餐民》的结尾,孔子话音未落,季孙的使者即到,首尾呼应,与《家语》相比,故事情节更加完整,改编痕迹非常明显。有时,通过改编可以使词语更加准确丰富。这点在《啖黍食桃》中体现得最显著,前文已论,此不赘。


我们还可以用前文已分析的第五组“重文”《不以容言取人》中的一个细节进一步证明上述结论。《韩非子》和《家语》中关于澹台子羽的事迹记载有误,而且二书居然错得完全相同,都认为澹台子羽貌美,但言行低俗、品质低下,以至于孔子发出以貌取人不可靠的感慨。但是《论语》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记却恰恰与此相反。《论语·雍也》记载:

孔门弟子子游在武城做地方官,孔子问他有无发现人才,子游高度评价了澹台灭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从中可以看出,澹台灭明是一个不惧强势、正直勇敢的儒士。尽管这段话民间传说的意味很浓,但传说往往有其现实基础。而且澹台灭明能入孔门七十二贤弟子之列,其操守应该不差。综合以上论述可知,《家语》与《韩非子》的记载是错误的。上文已论《家语》和《韩非子》之间不存在互相抄录的可能,那么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它们使用了相同文献,源文献记载有误,因此二书也就跟着都错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今本《家语》和《韩非子》“重文”的原因是它们使用了相同的文献。这批文献由韩非的老师荀子收集、整理,后辗转流传至汉,成为《韩非子》《家语》《说苑》等典籍共同的素材。《孔子家语》的形成不可能早于汉代,汉初成书的可能性较大,其后很长时间一直处于改动、增补中。《韩非子》寓言有一部分是通过改编历史故事而成,其改编的一般方法就是把所用历史文献中与法家思想不合的内容删除,增加符合法家思想的细节,同时有意增强其故事性,通过一些细节说明它们与历史文献本貌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