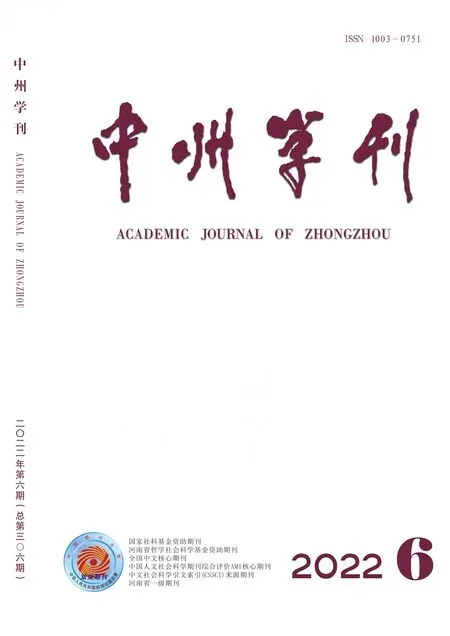蒲松龄的夜读书写及其苦乐传达
2022-11-04张含
张 含
在科举制度非常成熟的清代,应考入仕是很多书生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三更灯火五更鸡式的挑灯夜读更是其生活的常态。大半生都在应考和设帐教书中度过的蒲松龄对夜读感触尤深,他将夜读生活的酸甜苦辣写入作品中,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夜读书写。夜读不仅是《聊斋》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场景,也成为其诗歌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往研究者关注到了《聊斋志异》时间设置的“夜化”问题和蒲松龄诗歌中的暮夜书写,但尚未集中关注其“夜读”叙事的效果和意蕴。本文拟结合蒲松龄的诗文和小说创作,运用知人论世、精神分析、诗稗互证等方法,对其作品中的夜读书写及苦乐境界的营造展开深入探讨。
一、蒲松龄的夜读生活及其诗文中的苦境投射
蒲松龄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落魄不偶。他19岁考中秀才,胸怀大志,希望能够成为举人进入仕途,为此他时常深夜苦读,为参加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做准备。但他时运不济,在科举道路上奔走了三十多年,屡试不中,尝尽了辛酸苦辣,直到71岁才补上了一个贡生。他在创作《聊斋志异》的四十余年中,大多数时间用在了孤寂无聊的应试读写上。
从蒲松龄一些零散的记载可见,其读书生活紧张而辛苦,时常读写至“夜分灯火”,不敢有丝毫懈怠。例如,康熙三年春,“李子希梅,与余有范张之雅。甲辰春,邀我共笔砚,余携书而就之。朝分明窗,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时赵甥晋石在,假馆同居,谓余曰:‘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焉。’余曰:‘善!’遂集十数叶,借晋石籍而授之。”又如《聊斋自志》所言:“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每当暮夜来临,他置身于萧瑟的书斋,面对幽暗的烛光、冰冷的书桌和不得不做的功课。蒲松龄的读书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情感生活也缺少应有的温度。
这种生活、学习方式对蒲松龄的文学叙事与书写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入夜后,当大多数人开始休息时,忙碌一天的蒲松龄思绪却非常活跃,甚至会出现陆机《文赋》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状态。在本应安静读书的夜晚,他却经常心绪起伏,感慨“文字逢时悲老大”;在本应安心备考的时刻,他却满怀沮丧,“揽镜忽看白发盈”。有时,本应读书作文的主人公非但没有夜间苦读,反而处于随黑夜而来的困顿中。他的很多诗歌言说了傍晚或深夜时的心境和行为,尤其是夜不成眠的生活场景和情绪变化。如《夜坐》细致描写了蒲松龄“夜坐”时的思绪和夜深时刻孤独寂寞的心境:“短榻凝寒客思清,时闻里落短长更。松阴破碎秋光漏,髭影婆娑短烛明。文字逢时悲老大,晓床欹枕笑平生。年年落拓成何事?揽镜忽看白发盈。”又如《秋斋》:
高斋独坐思依依,回首生平事事非。狂态招尤清夜悔,强颜于世素心违。沾霜槲叶红犹湿,着雨林花倦不飞。处士萧然仍四壁,少年那不羡轻肥。
在一个孤独、寂寞的秋天雨夜,他孤身独坐,回望一事无成的人生,为自己曾经的“狂态”而深深懊悔,看着自己“萧然仍四壁”的贫困处境,不胜唏嘘,谁不向往富足美满的生活呢?白日里强颜欢笑应对世人,只有夜晚才能直面家徒四壁的窘境和困顿的内心,这该引发出多么惆怅的情绪。全诗未曾道一个“冷”字,却时时透射出诗人内心的孤寂和冰冷。
这种孤寂、清冷的心境浸染着蒲松龄的夜读生活,在静默中撕扯着他的情绪,使他的创作沾染上一种纠结、悲凉的情感。如他在孤愁萦怀、难以入眠之际创作的《夜小雨》:“短更长更愁絮絮,三点两点雨星星。雨声不似愁难断,颠倒匡床月入棂。”诗人以雨喻愁,愁思绵绵,愁之深重反倒激发了他的审美感受力。与《夜小雨》呈现的忧郁之美相比,在另外一首描写大雨的诗歌《夜电》中,蒲松龄驰骋想象,塑造了一个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抒情主人公的愤懑形象。《夜电》之一云:
青石裂破碧天漏,郁郁浓烟蒸宇宙。玉女无声迸线条,一夜乾坤亦应瘦。胸中垒块如云屯,万盏灯光和酒吞。醉中披发作虎叫,天颜辄开为我笑。
诗人首先对划破天际的闪电和激起水雾的倾盆大雨做了十分细致的描写,“裂”“蒸”两个动词,分别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带给读者极大的心理冲击,乾坤变瘦,天地狭小。在这极端的天气里,抒情主人公(蒲松龄)也“胸中垒块如云屯”,更加郁闷。酒后入醉的他,散发狂叫,如虎作声,竟然产生了惊天地的力量,一道闪电汹涌而至,撕裂天空。诗人在暴雨之中、闪电之下的散发怒吼,一定是热烈、直白的。这是多么悲壮而又疯狂的场景啊!由此可见,蒲松龄内心之压抑与烦闷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这种情绪必然也会映射在他的夜读之中,尤其是《聊斋志异》的创作中,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如果说《夜电》之一通过自然环境而聚焦于作者自己,那么《夜电》之二便转向夜读时的环境书写来衬托内心的痛苦:
夜深有鼠大如驴,咤咤霹雳啮破书。疾风窗户自开掩,若有人兮来荏苒。鬼母啾啾狐狸啸,摄魄摄魂梦惊魇。城头隐隐鸣鸱枭,闯然一声闪红绡。
风雨中窗户被刮得一开一合,好像有人来回走动,说明他居住的书斋条件非常简陋。更加让人不堪忍受的是,“大如驴”的老鼠趁着雨夜更加肆无忌惮地啃咬书籍,整个居住环境充满了令人不适的破败感。尤其是,梦中还有“鬼母”“鸱枭”一类凶恶的角色出没,他不断被噩梦惊醒。诗人在孤独之外生出巨大的恐惧,肉体和精神同时饱受摧残。
夜读书写会排解蒲松龄的苦闷,有时因为文学想象而丰富孤独的内涵。随着夜幕的降临,在白天生成的愁苦情绪会因为漫漫长夜而更加凸显,甚至被放大。蒲松龄对夜晚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在万籁俱寂的深沉夜色中,他对自我的认同与反思变得异常清晰、强烈,不论是“沾霜槲叶红犹湿”的婉转凄美,还是“神龙怒气嘘九垓”的壮美景象,都无一例外地让他在“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后,又迅速回到自身,勾起他那始终难以排解的孤愤情绪。如《读书效樊堂》其二写道:“狂情不为闻鸡舞,壮志全因伏枥消。寂寞荒园明月夜,蕉窗影里度清宵。”在月夜之中,身处荒园的蒲松龄如同祖逖、曹操一样勤奋自砺,忍受着孤独、寂寞之苦,壮志却不断被消磨,孤独乃至绝望时常占据他的夜晚。所谓“狂情”,应是被孤独、寂寞压抑的那份狂放之情,是那深藏胸中的奋发向上之情。他经世有为的志向不被认可,心情暗淡,只能沮丧地伴着孤灯清影度过漫长的夜晚。又如《夜微雨旋晴,河汉如画,慨然有作》:“神龙怒气嘘九垓,叆叇撑天惧天摧。帝遣封姨吹商律,虚声带寒入窗户。夜搔短发哭歧途,狂歌击剑声呜呜。歌阕粉绿扫重云,天开星眼泣露珠。”此诗作于雨过天晴之时,抒写的重点却是伴随着“神龙怒气”而来的愤郁、无奈和失落情绪。黑夜里的狂歌悲啸能使重云散去、天开星眼,现实中的作者却无路可走、壮志难酬。
二、化苦为乐的幻象救赎
与蒲松龄诗文中多表达夜读之苦不同,《聊斋志异》涉及夜读这一行为时,对于夜读生活的清苦、孤独、寂寞往往是寥寥带过。他在小说虚幻的世界中展开丰富的想象,努力摆脱现实的苦闷,化苦为乐,借助那些美丽、多情、神异的花妖狐魅实现精神救赎。那些花妖狐魅往来于他的书斋,装点了他的夜读生活,暖化了他的心灵,也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成为他解除苦闷的一剂“良药”,为他黯淡、落魄的生活带来一些亮色和欢愉。它们常常在书生夜读时制造邂逅,陪伴、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缓解孤愤、逃离苦境的最佳方式。
在蒲松龄的笔下,那些美好如“仙子”的花妖狐魅是他超越平庸、平凡的理想寄托和艺术投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为一种人的复杂的精神活动,“由记忆影响到外在世界所建立的知觉仿同——不过只是形成愿望达成(这是经验认为需要的)团团转的途径而已”。以此来审视蒲松龄小说的艺术世界非常恰当,其更深厚、宽广,更具有人性和美的魅力。


在一次次的思念、幻想之后,众多美丽的花妖狐魅前来陪伴书生孤独的夜晚,慰藉他们孤寂的心灵,并发生一段段浪漫而又奇幻的故事,形成《聊斋志异》叙事中最为生动的故事主体。《小谢》讲述了书生陶望三与花妖狐魅曲折的爱情故事。小谢、秋容通过“偷书”与陶望三认识,随后,三人开始熟悉起来。作品通过小谢、秋容在书生夜读时的恶作剧描写书斋中的欢乐:“长者渐曲肱几上,观生读;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即已飘散;少间,又抚之。生以手按卷读。”陶望三还通过教两人习字、学书,与她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读书是贯穿整个故事线索的重要因素和主体内容,小谢、秋容的可爱性格以及与书生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被描写,陶望三多姿多彩的夜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得以表现。

与蒲松龄笔下书生与花妖狐魅之间这种亲昵、美好的关系相比,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精心构设的书生与花妖狐魅的故事,读来却让人紧张、恐惧。如《滦阳消夏录》(四)第八篇,山长前巴县令陈执礼夜读时,一位香艳又诡异的女子从上面缓缓垂下,露出姣好的容颜偷觑他,并有意挑逗、魅惑他。他虽“自恃胆力,不移居”,但其仆人却中招而亡。如此“艳”鬼,令人惊悚无比,由此可见纪昀眼中的男女之情。又如《滦阳续录》(四)第一篇,写“老儒于灯下写书寄家,忽一女子立灯下,色不甚丽,而风致颇娴雅。”在女鬼熄烛威吓老儒时,老儒大怒,扬言要以墨印为记焚女鬼的尸体。此中的女鬼与书生形成对立关系,并未有情感故事发生,反而有剑拔弩张之势。相比之下,蒲松龄致力于两性之间的细腻美好,而纪昀专注于教化说教的创作观念,这种分野非常清晰。这与纪昀高中进士、仕途平坦、生活相对安逸有关,他并不像蒲松龄那样迫切需要想象若干“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旖旎故事来抚慰心灵,不需要借助文学创作来弥补落魄书生的挫折感和失败情绪。
在《聊斋志异》夜读书写中,除了与书生产生男女之情的女性花妖狐魅外,还有一些不涉及两性情感的角色。这类角色以狐、仙居多,大多聪慧非凡,有的还身怀绝技,对书生的助益体现在方方面面。如《郭生》中塑造的狐狸,主要是帮助书生备考。狐狸在夜里潜入郭生的房间用墨水涂抹书卷,看似是在搞破坏,实则是在帮他批改文章。这里明确指出了郭生所作并非寻常诗文,而是备考的文章。可惜,狐狸遇到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考生,他始终不能辨识好坏,后来竟然不再听从狐狸的暗示。作品没有描写狐狸的样貌或性格,而是将其塑造成一个灵异者、预言者、侠义者。即便最后郭生拒绝它的帮助,它也只是留下最终的预言,悄然而去。蒲松龄通过肯定狐狸的才能、品格与书生的品行形成对比,这与《阅微草堂笔记》的构撰旨趣截然不同。纪昀借助狐狸形象的工具性作用书写官场生活的倾轧不断,如《滦阳消夏录》(四)第十三篇中,前来借宿的李庆子偶然听到狐狸认为与董曲江同宿的友人俗气逼人,不可共室,他大肆宣扬,使人皆知,董的友人“衔李次骨,竟为所排挤,狼狈负岌返”。
三、夜读书写的“反读书”叙事
《聊斋志异》中的夜读多是作为一种引入角色的叙事方式与话语范式,为故事发生提供一个时空场域,作者的重点则是对书生的关怀慰藉、人生指导及相应故事的演绎。在夜读书写中,蒲松龄很少刻意交代读书的细节或内容,作品的叙事重点不在读书本身,而在于读书者的身份,以及因读书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如《鲁公女》写道:“一夕,挑灯夜读,忽举首,则女子含笑立灯下。”之后,文中再无提及与读书、吟诗等相关的情节。又如《聂小倩》中,宁采臣陪聂小倩夜读《楞严经》,只说是“今强半遗忘。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但后文并未因此产生后续情节,只是从这方面暗示聂小倩的聪慧与好学,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罢了。再如《沂水秀才》中,一个俗不可耐的秀才“课业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言,各以长袖拂塌,相将坐,衣耎无声。”“课业山中”暗示了书生的日常生活,即白天黑夜备考,但作者没有继续深入,而是重点描写了二美人对书生的“考验”:“少间,一美人起,以白绫巾展几上,上有草书三四行,亦未尝审其何词;一美人置白金一铤,可三四两许;秀才掇内袖中。”在“文字”和“银子”面前,秀才见钱眼开,毫无书生的斯文。于是,作者无比感慨:“丽人在坐,投以芳泽,置不顾;而金是取,是乞儿相也,尚可耐哉!狐子可儿,雅态可想。”作者讥讽、批判的剀切溢于言表,夜读叙事发挥了重要的社会能指作用。
蒲松龄的夜读叙事,具有一种“反读书”倾向。他反对的是那些束缚人、让人失去伦理品格和人生境界的科考书,而不是表达人的性情、沟通人的情感的诗词之类。在蒲松龄的笔下,科举考试要读的经书、策论之类的正经文字很少被提及,与考试关系不大的诗歌却频繁进入故事的叙述中,甚至具有“治愈”的作用。如《白秋练》中,读诗、吟诗乃至抄诗、作诗成为白秋练和慕蟾宫精神交流的桥梁,乃至救命的良药:

反对急功近利目的的读书,也是蒲松龄“反读书”的宗旨。《书痴》中的郎玉柱,痴迷于书的目的是“实信书中真有金粟”。机缘巧合,这些目的竟然一桩桩达到了,织女颜如玉也从书卷中走出来,成了他的红颜知己。不过,让他的实现理想的《劝学》《汉书》等经典著作,并不能使其科考成功,就如颜如玉所言:“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耳。试观春秋榜上,读如君者几人?”直到郎玉柱真正弃绝读书,通晓了人情世故,才终于考取功名,成为世俗社会的显贵,因读书而获得的红颜知己却因之陨丧,批判锋芒暗隐其中。《白于玉》则直接表达了对科举的拒绝。仙人白于玉并非普通的花妖狐魅,因此他可以与吴青庵“共晨夕”。在读书、论学过程中,二人亦师亦友,“忻然相得”。在他的引导下,痴迷于科举的吴青庵逐渐摒弃了世俗中的功名利禄和婚姻子嗣等诉求,坚定走上成仙之路。作者对这样的人生选择持肯定态度。通过“反读书”叙事,蒲松龄突出了那些活跃在夜晚书斋中的真正“自我”,关注那个被读书的功利目的束缚后而希望处于放松状态的人,更批判了那些因为读书而成为“少年进士”者内心的龌龊、灵魂的卑微,人情、人性之美丑因此而昭然若揭。
四、夜读叙事的“乐境”营造及诗情画意美

一般讨论传统叙事文学,人们关注的重点无外乎时间、地点、人物。夜读叙事的时间、氛围值得重视。中国古代小说有夜间叙事的传统,“夜”的朦胧、诡秘对于营造鬼怪精灵类的故事具有特殊意义。人的“昼出夜伏”和鬼的“昼伏夜出”正好对立,夜间发生的故事因此更具有神秘的特点、玄幻的氛围,以及恐惧的体验。魏晋时期的小说如《搜神记》等,因此而很难获得真善美的审美体验。但《聊斋志异》中,在阴郁的夜色下发生的却不一定是恐怖的故事,纷至沓来的花妖狐魅往往比人更可亲、可爱。《青凤》中,故事发生的老宅“怪异,堂门辄自开掩,家人恒中夜骇哗……荒落益甚……或闻笑语歌吹声”。到了夜里,耿去病在老宅中探索时,“闻人语切切。潜窥之,见巨烛双烧,其明如昼”。整个环境的氛围在夜色中充满着诡异、灵异,令人不寒而栗。可当耿去病邂逅美丽的青凤后,一家人亲密交谈,共进餐饮,一段走向圆满结局的爱情故事负载了人世间难得的温暖亲情。《阿英》中,独自在匡山僧寺读书的甘玉,与阿英、秦娘子一行人邂逅,发生了一串彼此互相帮助的报恩故事,其中体现出的贞毅、果敢和善良体现了人世间难得的真善美,这才是作者摹写的重点。夜色中的神秘、玄幻不过是塑造形象的手段,而惊悚、恐惧从来没有参与到阅读者的审美体验中。
在《聊斋志异》中,夜读的地点作者格外关注。寺庙、空斋、郊外居所等僻静的所在,多是书生备考的常选之地,设帐之家孤独的教书者也往往独自栖息于一隅。因此,书斋成为花妖狐魅最易出现、最常光顾的场所。在聊斋诗集中,对书斋的称谓多是“高斋”,往往充盈着凄苦的情绪。如《咏怀》中的“谋生计拙类鸠巢”中的“斋”是狭小、简陋之斋,《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中“冷雨寒灯夜话时”的“斋”是孤冷之斋,《夜电》中“疾风窗户自开掩”的“斋”是破败之斋。但这类描写及相关情绪没有直接出现在《聊斋志异》中,对于书斋类居所,小说中往往极写其旷废、荒置、无人的特点,以突出故事发生的环境,如《荷花三娘子》中,宗湘若称自己的书斋为“荒斋”,《胡四姐》中,尚生住在“清斋”里,《彭海秋》《狐梦》等则仅称之为“别业”。
立足于空间的环境描写是蒲松龄营造诗意氛围时经常使用的手段。不过对于书斋的具体环境,小说中往往少有提及;对于斋中的具体陈设以及带有描述性的夜读场景,通常也是一笔带过。这种有意的“忽略”当是因为他描写的重点不是书斋本身,而是书斋中的那些“人”。因此,他情愿自我催眠一般钟情于那些具有美好性格和品格的花妖狐魅,并将之转换成对自己的慰藉。如《雨钱》中,“滨州一秀才,读书斋中。有款门者,启视,则皤然一翁,形貌甚古。”叙事的重点依然是发生在斋中的故事,只不过这里的书生是个假秀才,狐仙老翁反而是个真书生。当秀才希望通过老翁不劳而获时,老翁很生气,二者之间原本高雅的交往关系断裂:“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便如秀才意,只合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求真求雅的狐狸为书斋赋予了应有的意义。《聊斋志异》写了那么多的花妖狐魅,读者不觉其阴冷可怕,反而认为其善解人意、温暖可爱,甚至体现了人伦社会正在逐渐失去的价值。蒲松龄通过夜间书斋发生的故事畅写爱情、亲情、友情,夜的美好因此得到呈现,书斋的意义也因此被发现。
在《聊斋志异》的夜读叙事中,吟诗具有营造“乐境”的特殊作用,不仅标识男女主人公的才学、风度、性情,同时也渲染了环境、美化了夜色。在以才子佳人为主要特征的故事范型中,少有世俗烟火气,多的是高雅的诗歌与精神的理解、认同。故事中联结男女主人公的往往是诗歌,如《连琐》中,女鬼连琐与书生杨于畏的相识、相知来自连琐的吟诗,二者约会的信号也是诗歌。后来二人谈论诗文,读诗之乐胜于男女之情。作者集中表达了二人的趣味相合、心灵相通,“如得良友”“剪烛西窗”均非世俗可以领会。读书写诗乃至琴棋书画是两人沟通的主要方式,也是爱情发生的根本原因。这种纯粹的精神追求,也是蒲松龄一生所崇尚和追寻的。如此“才子佳人”的形象设置,强调了连琐的诗性气质,也增强了夜读的诗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