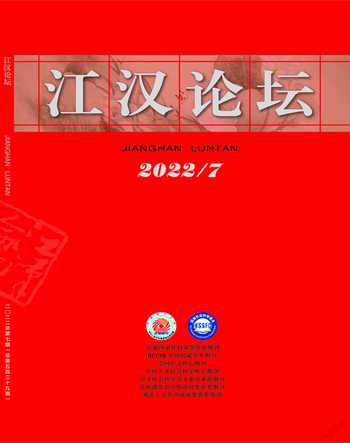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 及其效应差异
2022-07-13陈伟东姜爱
陈伟东 姜爱
摘要: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
关键词:资源传导;社区治理;居民自治;治理效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层党建引领辖区单位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研究”(20BDJ030)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7-0134-05
一、问题的提出:一个社区扶贫故事引发的思考
2016年,H市CS镇政府购买Y社工机构的专业服务为五保户提供社会救助。Y社工机构介入前,扶贫物资都是由村委会亲自送到五保户家里,有时村委会上门服务晚一点还会遭遇五保户的抱怨。Y社工机构介入后,通过摸底调查,将该镇五保户分为两类:行动不便的和有行动能力的。对于行动不便的五保户,社工机构送物资上门。对于有行动能力的五保户,采取渐进式的赋能策略:从引导五保户自行领取物资,到提建议奖物资,鼓励五保户关心村庄发展和治理,再到激励五保户根据兴趣自我组建“闲人俱乐部”,促进五保户间的相互关联,最后将“闲人俱乐部”带向公益,五保户参与房前屋后环境治理,获得公益积分,以公益积分兑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Y社工机构的赋能策略使五保户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在家里“等靠要”,到彼此关联互助,再到参与村庄治理。不同的资源传导机制,产生了不同的治理结果:一是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挤出居民参与,出现资源诅咒效应,陷入资源养懒汉的境况。二是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破解资源诅咒,居民參与转入组织化和民主化赛道,基层社会活力得以增强、秩序得以内生。那么,为什么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诅咒效应,而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带来资源护佑效应,这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资源诅咒理论来源于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发现很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都经历了失败的发展——经济增长变慢(甚至负增长)、贫困率上升、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似乎资源诅咒了发展。1993年,理查德·奥蒂(Richard M. Auty)首次提出“资源诅咒”概念,他通过对玻利维亚等资源出口国的案例分析,发现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是福音而是一种诅咒。① 2007年,世界银行发起了一项全球性活动——“加强资源诅咒的政治经济分析”,以解决资源丰裕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政治、经济问题。随着资源诅咒理论应用场景的拓展,其内涵不断扩展,成为对资源开发引起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统称,如收入分配不平等、教育投资不足、物质资本积累下降、体制不健全、寻租、腐败、内乱等问题。② 如,有学者就提出了“政治资源诅咒”概念,认为我国市场化改革初期,旧的政商关系中的腐败活动和设租行为,降低了市场竞争、挤出了创新资源和扭曲了企业投资结构。③ 资源诅咒理论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资源诅咒效应,多数学者认为资源挤出逻辑(挤出人力资本开发)、经济政策的失误、政府治理能力低下、政府寻租等是产生资源诅咒的根本原因。
目前,学界关注资源输入与社区治理的关系问题,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外部资源输入促进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如,杨继龙研究了资源输入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影响,认为外部资源输入带动基层内生资源开发,能增强各治理主体间的认同感,促进社会协同治理④;姜振华认为,资源输入增强了基层的社会资本,基层的社会资本促进了国家与公民的合作⑤。二是外部资源输入带来底层群众处于被支配地位。如,陈锋认为,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乡村形成了分利秩序,资源输入再生产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配关系,进入基层社会的资本往往与权力相互结合,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社会组织管理者没有真正发掘公众需求,反而将服务对象及其需求工具化,导致服务对象处于利益结构底层⑥。自然资源是被动性资源,是被人配置的对象。与自然资源不同,社会资源无论是制度资源、金融资源、人造的物力资源(房屋、设备等)、人力资本等都是能动性资源,社会资源的配置与开发是人为设计和选择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在资源输入基层的过程中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的塑造与缺失差异、基层社会资本的增加与消解差异、主体间的合作与冲突差异、社区治理的持续与夭折差异?要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讨论不同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所带来的不同效应。
人是治理的决定性因素,治理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人力资本的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尤其稀缺的,人力资本质量的差异,最终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社区治理绩效的差异。社区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从外部获取资源、能量,这是社区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外部资源无论是公共资源、市场资本、专业知识、慈善资源等的开发和输入,都应该以尊重居民主体地位和发展居民自治能力为目的。也就是说,坚持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制度逻辑,应该把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理解为居民主体性的彰显过程和居民自治能力的实现过程。本文将围绕居民主体性和自治能力这个中心,从产品结构、能动性、人力资本开发三个维度来分析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和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的内涵及其效应的差异性。
二、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及其“诅咒”效应
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是把居民当作施舍对象的一种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它遵循的是一种慈善逻辑:政府购买或爱心人士捐助服务—专业机构提供服务—居民等待服务。它对居民的态度和行为存在偏差:把居民当作客人而不是主人,把居民看成“治理负债”而不是“治理资本”,偏好于满足居民的一次性消费需求而不是全面发展需求,营造了一种“等靠要”的治理场景,资源下沉阻碍了居民参与。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之所以会导致资源诅咒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内在的慈善逻辑所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
根据功能不同,外部输入的社会资源可分为消费产品和能力产品。消费产品指的是供人一次性消费的资金、生活用品、娱乐活动、设施设备等。能力产品指的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参与的观念、知识、流程和方法等。外部资源输入基层社会,只有在资源约束条件下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才会达到资源的可持续配置,居民参与和社区治理才可持续运转。消费产品与能力产品的投入结构对居民参与和社区治理的影响是:当消费产品大于能力产品时,输血多于造血,会增加服务索取的易得性,出现“免费无治理”问题;当能力产品大于或等于消费产品时,造血多于输血,居民在参与中学会参与、在参与中增强自治能力,建构体现“互为主体性”的生活世界。
1. 非均衡的产品结构阻碍居民参与。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是消费产品投入大于能力产品投入,过度的消费产品输入会使居民滋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懒汉思想,吞噬居民主体性,减弱居民参与意愿,导致社区治理难以持续。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经常出现在政府购买服务、慈善救济等社会服务中,成为一种“被复制的社会实践”,即“相似的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个系统形式的结构特性(规则和资源)”⑧。比如,专业服务机构把“做项目”当成了目标,把服务多少居民、给予居民多少物品、为居民搞多少次活动、媒体报道多少次等作为行动指标。受制于“成本约束”和“指标约束”,社工机构倾向于组织趣味性活动,通常这类活动的特点在于难度小、耗时短、费力少、见效快,而不愿意组织培育居民公共精神和公共参与能力的活动,通常这类活动的特点是难度大、耗时长、费力多、见效慢。
2. 非均衡的产品结构的传递效应是不情愿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是能动性资源。吉登斯认为,能动者是指“有能力为社会世界带来影响的行动者,能动者拥有权力”⑨,人的能动性是通过参与来实现的。制度化的“假参与”无法培养积极行动者却会增加消极行动者。卡罗尔·佩特曼认为:参与是人们直接参与决策活动,不只是影响决策而是作出决定。政治平等是指在决定政策结果方面的政治权力的平等。他在区分决策影响与决策权力的基础上,依据工业民主实践经验,归纳诸多学者的观点,将参与分为三种类型:“假参与”、“部分参与”和“充分参与”。“假参与”包括以下情形:一是个人只是参加团队活动,但不参与作出团队活动的决定;二是个人在影响他的决策得到实施前被告知有关的消息;三是个人出席一个会议,但没有影响力;四是管理者说服被管理者服从决策,被管理者实际并未参与决策活动;五是管理者营造一种参与氛围,让被管理者对已经作出的决定提出质疑和讨论,但不作出新的决定。“部分参与”是指双方或多方在决策过程中相互影响,但最终的决定权只归其中的一方。“充分参与”是指“决策整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平等地享有决定政策结果的权力过程”,它存在于自我管理的团队,团队成员对每天的工作流程可以自己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具有不平等决策权的“双方”,存在的只是一群平等的个人,他们可以自己决定工作如何分配、如何实施。⑩ 社区是基层群众自治的主要场域,是居民直接参与决策的最佳领域。居民不愿意参与社工机构组织的活动,根源于居民自主性被吞噬。人是自主创造的生命体,尊重人的自主选择是对人的最大尊重,也是社会治理和社会工作的基本伦理,更是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和主人翁意识的前提条件。而一些社区组织的活动,每次需要发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是小礼品邀请居民来参与。这类活动对于居民来说犹如“嗟来之食”,居民宁愿选择自由,也不愿选择参加活动,这也是居民能动性的体现。专业服务经常出现“供需适配偏差”,居民常常有一种“被服务”的感觉。{11}
3.“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的传递效应是挤出社区人力资本再生产、居民等待服务刚性化和非均衡产品结构固化(居民期盼源源不断地输入消费品)。我国《“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首次将志愿服务与公共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并列,作为社区服务的主要内容。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是评判一个社区人力资本开发状况的核心指标,其重要价值在于:一是满足人的内在需要。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使每个人感受到自己被他人和社会所需要、被尊重,同时“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志愿者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改变这个世界”{12},实现个人作为社区居民和城市市民所应有的价值。二是生成社区公共精神。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能培养有公益精神的好公民。“情感缺钙”是现实社区的深层次问题,人居住在社区但心里无社区,人生活在社区但不关心社区。没有参与就没有归属。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是促进人们从私人参与(为私人利益而参与)转向公共参与(为公共利益而参与)的有效路径,使人们在公共参与中真正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可以协调的、兼顾的、统一的。三是实现社区活力与秩序的内在平衡。“一个好的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13} 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中存在活力与秩序的张力,社区的活力与秩序平衡不可能是外部力量强制的结果,而是社区自组织生成的结果。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对建构社区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使每个人真正做到关照自己、关照他人、关照社区的内在统一,能有效地抵御市场逐利行为对社区共同体的侵犯,也能有效抵御行政包办行为对居民自治的侵蚀。四是储备社区应急管理的良性资产。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是社区快速应对突发事件必不可少的社会资本,一个地区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影响着该地区能否以最小的防疫代价换取最大的防疫效果。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无法促进社区志愿服务的常态化。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既需要外部持续输入政策资源、知識资源等,更需要内部形成自主决策和自我运行机制。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由于缺少对社区志愿者这一核心人力资本的开发,居民及其家庭拥有的闲暇时间、闲置物品、闲置技能等未发挥服务和治理效用,个人和集体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基层治理存在“盲点”。
三、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护佑”效应
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是把居民当作行动者的一种人力资本开发方式。它遵循的是一种行动者逻辑:政府购买或爱心人士赞助服务——社工机构传播专业技能——社区工作者和居民合作生产。它主张社区居民研究他们自己的社区,甄别自己社区的问题,发现自己社区的需求,自己行动起来,改善自己社区的福祉。{14} 在对待居民的态度和行为上,行动者逻辑与慈善逻辑存在根本差别:一是秉承“人人是资源”的思想观念。政府和社会把居民当资源不把居民当包袱,积极开发居民资源,向居民传递社区参与的知识、流程和技巧,成为社区人力资本开发的外推力;居民自身体验到自己是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资源,成为社区人力资本开发的内驱力。二是秉承“人人有爱心”的思想观念。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取向,促进居民间的关联。居民在彼此关联中组建草根型互助组织,使居民摆脱原子化状态,获得个人的社会身份,发挥个人的社会功能,也使基层社会保持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三是秉承“人人能自主”的思想观念。政府和社会把居民当主人不把居民当客人,着力唤醒居民的主体性,发挥居民的首创精神,向基层民众赋权。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营造了一种“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社会步入资源再生和治理效能递增的轨道。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之所以产生资源护佑效应,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内在的行动者逻辑所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
1. 均衡的产品结构促进居民参与。促进人全面发展的能力产品投入等于或大于一次性消费产品投入,居民参与和社区治理方可持续。之所以要投入促进人全面发展的能力产品,加强对社区工作者和居民骨干的自我组织能力培训,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从我国居民参与的实践经验看,居民容易自发形成自娱自乐团体,但难以自发生成公益性、互助性的志愿者团体。公益性、互助性的志愿者团体需要培育,需要专业力量的支持。在我国,志愿服务主要有两种形态:活动招募型志愿服务和组织孵化型志愿服务。前者是根据活动主办方的需要临时招募志愿者,通过短期培训,提供短期志愿服务;后者是根据志愿者的特长,结合社会需求,培育志愿者组织,通过长期培训,提供常态化志愿服务。前者是对人力资本的临时配置,志愿服务持续性弱,对志愿者赋能弱;后者是对人力资本的长期开发,志愿服务持续性强,对志愿者赋能强。志愿服务需要以社区为场域进行培育发展,为此,国家民政部专门出台《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3年)》,强调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大力培育发展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我国基层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习惯并擅长自上而下地组建工作网络(如居民小组长、楼栋长、单元长等低组织化的松散的工作网络),但不习惯也不擅长横向地组建居民互助网络。加强社区工作者和居民骨干自我组织能力的训练,增强居民自治能力,是新时代社区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的需要,也是新时代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通过学习和掌握参与知识,实际地拥有平等参与权,真实地共享高品质生活)。人身上承载的有用的能力、知识、技能以及健康等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在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下,社工机构引导社区工作者和居民骨干实践新的工作理念:“重要的不是我为居民做了多少事,而是我组织居民做了多少事”,其用意是让社区工作者和居民骨干理解“社区是居民的”、“不要把居民当客人,而要把居民当主人”、“不要把居民當包袱,而要把居民当资源”。社工机构向社区工作者和居民骨干传授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流程,引导参与者学习自主选择团队、自主订立公约、自主策划活动等决策方法,其目的是要让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做到自我赋权、自我赋能。
2. 均衡的产品结构的传递效应是“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充分参与”的最佳场域是社区志愿者团体,它体现了“小的就是好的”,具有决策成本低、决策收益高的优势。其具体表现:一是微团体具有人数规模小、组织认同高的特点。微群体人数一般在6—20人左右。尽管微团体内部成员的身份结构、职业结构、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等存在差异性,但他们是基于相同的公益服务需求和相同的公益服务意愿而集聚起来的。二是微团体容易组织起来。微团体对组织的目标和任务容易达成共识,较少有分歧,容易组织起来,形成紧密互动的社会集体。三是微团体容易采取自治行动。群体规模小使每个人在公共参与中的收益高,每个人贡献后的自豪感和效能感强,每个人偷懒意愿低且彼此监督成本低。{15} 微团体基于沟通、信任、互惠,更容易建构自治程序:自主寻找伙伴、自主分配职责、自主开展活动、自主筹集资源,从而内生自治秩序。四是以公益为导向的微团体容易订立合道德、合法律的微公约。微团体在公益行动中培育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把遵纪守法观念带入集体行动中,将社会公德和法治规则嵌入微公约,在自治程序中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居民的主体性应该体现在团体组建和运行的全过程决策上,包括团体的自我组建、需求的自主表达、活动方案的自主设计、活动实施的自我组织、活动成果的自我体验等。作为能动者,社区工作者和居民的能动性来源于全过程参与中的自我组织、自我决策、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3.“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的传递效应是人力资本开发以及资源共享递增。“如果非政府组织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共同体发展设计和实施努力中,不能有代替参与的东西”;不能把参与看成战术和方法,“参与必须是要完成的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关注的重点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寻求解决个人和集体问题”,“追求个人和集体的抱负”。{16} 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需要解决资源的分散与短缺问题。社区是个体与个体、组织与组织的共生体,共生体依赖资源共享。赋能式传导机制有助于塑造彼此关联、彼此尊重、彼此担责的共同体,实现基层社会资源不断增多,基层治理效能逐步提升。
四、结论
公共参与是确保居民主体性、提升居民自治能力的有效路径。公共参与的必备要件包括参与知识和方法(需要持续的教育培训)、参与集体行动(最佳形式是直接参与团体决策)、参与效能(解决个人和集体问题以及实现个人和集体抱负)。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和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塑造两种根本不同的社区治理结构。从确保居民主体地位和发展居民自治能力角度看,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塑造“能力赤字结构”,社区居民因制度环境被客人化,成为治理中的“躺平者”,等待服务,等待救济,等待解困;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塑造“能力扩展结构”,社区居民因制度环境自我主人化,成为治理中的“冲浪者”,主动迎接挑战、应对风险,协作提供服务。
注释:
① 马宇、杜萌:《“资源诅咒”发展历程及其传导机制文献综述》,《产业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② 赵伟伟:《相对资源诅咒理论及其中国的实证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页。
③ 蒋长流、江成涛、郑德昌:《新型政商关系能打破企业创新的政治资源诅咒吗?》,《软科学》2021年第6期。
④ 杨继龙:《资源输入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以N市H区为例》,《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7期。
⑤ 姜振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⑥ 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社会》2015年第3期。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页。
⑧⑨[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186页。
⑩[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6—67页。
{11} 倪咸林:《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供需适配偏差”及其矫正——基于江苏省N市Q区的实证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7期。
{12} [美]德鲁克基金会主编:《未来的社区》,魏清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1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论丛》第3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2页。
{14} 陈伟东:《社區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政治学研究》2018 年第1期。
{15}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16} [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9页。
作者简介:陈伟东,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武汉,430079;姜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