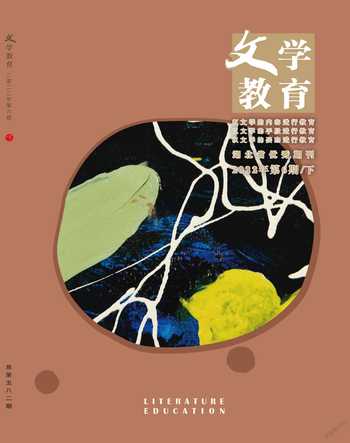例谈霍米巴巴的后殖民叙事视角
2022-06-28杨子茶张之俊
杨子茶 张之俊
内容摘要:著名学者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突破二元对立的藩篱,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话过程并非一直处于泾渭分明的对抗状态,而是存在许多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表达空间。本文以《鲁滨逊漂流记》和《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两部殖民叙事的经典之作为例,分别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视角叙事着手,探究殖民叙事的矛盾性。本文指出,殖民双方在文明认知、情感表达和身份定位上自相矛盾。这种矛盾性根源于双方互为“他者”的事实,使之对另一方产生了既抗拒又吸引的矛盾心态,充分体现了殖民叙事处于摇摆不定的动态变化中。
关键词:霍米巴巴 矛盾性 后殖民叙事视角 《鲁滨逊漂流记》 《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
殖民统治贯穿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与亚非拉国家沦陷、斗争、独立的民族解放历程息息相关。殖民统治颠覆了东西方力量对比,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同时促进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诞生。
自有殖民行为以来,就有针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反殖理论源远流长。在理论发展早期,民族主义作为反抗殖民主义最有力的工具,成为反殖思想的第一面旗帜。但民族主义仅仅是对殖民主义的逆向解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身份仍置于二元对立之中。随着理论发展,后殖民主义更进一步,超越了这种简单对立。(赵稀方 2009:33)[11]后殖民理论的开山鼻祖萨义德批判西方以想象任意塑造东方,挑战东西二元论。他的理论虽然认识到了二元论的局限性,但是他从西方内部研究话语呈现,完全忽视了东方的话语权,其理论仍然不免本质主义立场,落入非此即彼的理论窠臼。(赵稀方2009:103)[11]
真正成功挑战殖民主义二元论的是与萨义德、斯皮瓦克并称后殖民理论“圣三位一体”的霍米巴巴。霍米巴巴借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法,开创性地提出“時差”、“杂糅”、“模棱两可”等一系列术语,指出殖民者与被殖民之间的对话过程更接近论战性而非对抗性:恰恰是两者互为“他者”的身份塑造了双方摇摆不定的心态和模棱两可的表达。一方对另一方总是既渴望又排斥,因此双方的对话并不完全是相互对立的,存在许多暧昧不清的表达空间。(Bhabha1996)[1]
福柯(1999)指出:权力和话语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8]在资本主义兴盛时期,西方垄断话语权,殖民地沦为萨义德(1999)笔下“沉默的东方”。[11]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被殖民者终于得以发声讲述本民族的历史。殖民叙述不再是西方的自说自语,而真正转变为双方的对话过程。
《鲁滨逊漂流记》[7]与《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6]分别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视角对殖民历史展开叙述。《鲁滨逊漂流记》是18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代表作。全书以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为背景,讲述了志在冒险的资产阶级中层鲁滨逊偶然流落荒岛,二十多年间克服困难顽强求生,期间成功驯服野蛮人星期五并建立荒岛殖民帝国的故事。萨义德(1999: 36,89)对其评价道:“这非一个单一的冒险故事,这是一个欧洲的冒险者在新世界创建的自己的海外殖民地,他是基督教和白人,这是工业革命后的海外扩张意识在小说中的体现,这是欧洲殖民者海外掠夺的先声之作。”[8]《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则是20世纪著名的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代表作。全书以主人公奥贡喀沃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描绘了非洲传统部落伊博在未受西方侵略时的风土人情,以及白人殖民者如何步步渗透、瓦解传统社会,反映了非洲传统部落文明以及被殖民的过程。作者将被殖民者置于叙事中心,凸显被殖民者视角。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被殖民者真实精神面貌,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
作为反映殖民统治的经典之作,国内外学者都对小说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于解读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诺瓦克(Novak)通过分析作者的阶级立场,指出《鲁滨逊漂流记》反映了其政治上的精英统治理念(1962)、[4]经济上的“小国寡民”乌托邦建设期望(1963)[5]和宗教上的原罪意识(1961);[3]邹宏、王福娟(2021)从多维度分析鲁滨逊的殖民者形象。[15]姚峰(2011)分析《这个世界土崩瓦解》的反殖民书写和作者的反殖民思想;[13]诺罗梅(Nnoromele2000)分析主人公奥贡喀沃形象,强调作者对非洲悲剧英雄的形象塑造。[2]众多研究佐证了两部作品作为殖民文学的典型性。与此同时,两部作品分别代表殖民叙事的一方,共同构成了殖民对话过程。
本文旨在通过对《鲁滨逊漂流记》和《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的详细分析,具象化霍米巴巴的后殖民叙事视角。互为“他者”的事实塑造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摇摆不定的矛盾心态,双方在文明评价、情感表达和身份区间上的叙述自相矛盾,展现了模棱两可、充满矛盾的殖民叙事空间形成过程。
一.混乱的时差
马基雅维里在其著作《君主论》中提出:目的总是为手段辩护。(1985)[10]为了合理化侵略行为,西方大肆宣扬文明线性发展观和人类进步主义,强调文明总是处于发展进步中,并引入一系列量化指标如技术的等级、财富的多寡、观念的开放与保守作为判断文明先进与否的标准,所有民族的发展都置于这一线性阶梯之中。(Bhabha1996:243)[1]现代化成为“资本主义化”的代名词,世界各地的“时间”都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为衡量标准,不符合西方文明尺度的文化一概斥之为野蛮、传统,许多仍停留在原始社会的民族便沦为落后者,理应对西方文明俯首称臣。
而霍米巴巴提出的时差理论,则是对线性叙事的反抗。“时差”本是地理上的概念,指的是不同地区由于空间差异而形成的时间差异。霍米巴巴提出的“时差”理论,强调不同民族由于空间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发展面貌,各民族具有一套独具特色的文明衡量尺度。(Bhabha1996:244)[1]霍米巴巴指出,在文明孤立发展时期,各民族相安无事;但是当来自不同文明的民族相遇时,就会引发“时差的混乱”。(Bhabha1996:245)[1]各文明主体在最初阶段习惯以自己的时区时间衡量“他者”文明,本能产生排斥和抗拒。但是“他者”文明的出现同样打破了单一的评价体系,双方不得不尝试着接受对方的尺度衡量文明。(Bhabha1996:245)[1]不难看出,霍米巴巴以寻求差异的方式突破同质的线性叙事方式,以“时差混乱”形象地传达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面对“他者”文明所处的状态,为双方对待“他者”文明初而抗拒、继而接纳的矛盾反应提供了合理解读。
《鲁滨逊漂流记》集中体现了殖民者对原始文明矛盾的评价。鲁滨逊作为资产阶级中层,深受西方文明教化,本能对吃人行为感到极端厌恶,小说中多次重复他对原始部落食人传统的鄙夷:“对于他们那种互相吞食的灭绝人性的罪恶的风俗是那样的深恶痛绝”。(126)①在看到带血的人骨头和残渣碎屑后,更是引起生理上的反感。“我觉得胃里阵阵作呕,几乎要晕倒,终于把胃里的东西都翻了出来。”(126)但是,在运用“比较冷静的头脑去考虑”(130)时,他想方设法以被殖民者自身的文化发展轨迹考量其行为“这些人并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这种事既不违反他们的良心,他们的良知也不会责备他们。他们并不是明明知道这是违背天理的罪行而故意去犯罪,像我们大多数文明人犯罪那样。他们并不认为杀掉一个战争俘虏是一般犯罪行为,正如我们并不认为吃羊肉是犯罪行为。”(130)以西方文明为参照,吃生肉是野蛮落后的行为,但是放在原始部落的文明参照轴上,这只是生活行为的一部分。对待原始文明,鲁滨逊既因为其不符合西方规范难掩厌恶,又在代入本土视角思考后表达出理解,展现殖民者对异域文明充满矛盾的宏观感受。
被殖民者同样以自身为尺度构建文明评价体系。《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从社会秩序和人情往来入手,以大量篇幅描述非洲独特的文明性,反抗西方的线性文明观,展现本土人民对非洲文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村民恩格巴弗和丈夫乌佐乌鲁的矛盾不是通过基层机构干预调解,而是由神灵进行调节审判的,(102)②纵然决断方式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也是经过理性思考与协商后构建的行之有效的裁决制度。部族人民格外注重情谊与礼尚往来。在奥贡喀沃流亡期间,好友尽心尽力、不求回报为其照管耕地(164)为了答谢母族照顧,奥贡喀沃临别时以盛大的宴会款待父老乡亲。(188)事实证明,非洲部落并非西方眼中茹毛饮血、自相残杀的食人族,非洲文明虽与西方迥乎不同,但并无高下之分。人们在自己的“时区”中按部就班地生活。然而当西方传教士携着福音书降临这片土地时,平衡就此被打破。出于对本土文明的高度认可,西方文明首先受到了部族人民的强烈抵触。这种仿佛来自天外的文化让他们十分费解,无法共鸣。在他们看来,神祗存在于是世间万物之中,“是地母,天神、雷神阿玛底奥拉”。(169)白人的上帝有子无妻、全知全能,与他们熟悉的神灵截然不同。当白人宣传“真正的上帝只有一个,天、地、你、我以及所有人都属于他。”(169)氏族人民对此报以冷笑。然而西方文明中蕴涵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真善美,同样在不知不觉中吸引着他们。当传教士放声歌唱,围观的人们听得入了迷。“那是一首愉快而活泼的福音歌,有一种能拨动伊博人那沉寂蒙尘的心弦的力量。”(170)歌词讲述了黑暗中的人们寻求光明、迷途的羊羔寻找归途的故事。(170)引人入胜的故事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窥探基督文明的窗,人们对基督教不再全然排斥:“白人的宗教也许不像表面上那样疯狂,而其实是有点道理的。”(203)西方文明与氏族文明处于不同的发展“时区”,氏族人民夹杂在两种文化中,对于西方文明既抵触又着迷,摇摆不定。
由此观之,线性叙事下西方文明优越性仅仅是一种假象。不同时区有着不同的时间刻度,不同的文明具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和衡量标准。当来自不同文明的主体相遇,两种价值观碰撞,引发时差的混乱。双方对“他者”文明分别使用自己和对方的时间尺度衡量,产生既抗拒又吸引的摇摆心态。文明评价不止停留在单一的维度,而是呈现出矛盾性。
二.矛盾的情感
随着殖民深入发展,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互动日益频繁,不再停留于远远观望,产生了实际的沟通和交往,此时双方的叙事中开始表达出对“他者”的情感态度。霍米巴巴注意到,殖民主义类型话语中往往体现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2]例如,在《黑暗的心》中,黑人是低贱的:“像蚂蚁一样来回移动着。”(康拉德2011:23)[9]是丑陋的:“所有那些人的干瘦的胸脯一起随着气息起伏。”(康拉德2011:20)[9]宛如行尸走肉:“带着野蛮人的彻底的、死一般的冷漠”;(康拉德 2011:20)[9]但是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黑人是高尚的,“他整个的神态中有着一种自尊和威严,然而也结合着信任和谦逊的质朴。”(斯陀夫人1998:22)[12]是健壮的:“体格魁梧、胸部结实”(斯陀夫人 1998:22)[12]表情生动、有血有肉:“特点是有种与忠厚善良相结合的严肃、稳重、通情达理的表情。”(斯陀夫人1998:22)[12]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总结:“一个黑人,既是一个食人的生番,也是最忠诚、勤劳的仆人;既是滥交的嗜欲者,又如孩子一般纯洁:他是神秘的,未开化的,懵懂的,又是世界上闻名的撒谎大师和社会颠覆力量”。(Bhabha1996:82)[1]
为了解读这种矛盾,霍米巴巴借用心理学说弗洛伊德的拜物教观点,指出矛盾情感源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双方互为“他者”的事实。(Bhabha1996:77)[1]按照精神分析法的观点,“主体”对“他者”往往会出现又爱又怕的矛盾情感。一方面,他者具有神秘性,是主体渴望的对象;另一方面,他者是完全异于自己的陌生对象,也是主体恐惧的来源。由此主体对他者产生了爱恨交织的情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外表形象迥然不同,生活方式天差地别,社会背景大相径庭,价值观念相互冲突,双方皆视对方为神秘而未知的“他者”,往往展现出矛盾的情感倾向。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对待原始部族人民前后表达出不一的情感。他们既是可恶的食人生番,茹毛饮血,野蛮凶狠;又是可亲的忠诚奴仆,聪明能干,温和恭顺。在看到其他人类足迹后,鲁滨逊简直吓坏了,一路逃向自己的避难处,魂不守舍。待发现这些脚印系对面大陆的野人所留时,未知的“他者”使鲁滨逊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前来,把我吃掉;就算他们找不到我,他们也会找到我的围墙,把我的谷物通通毁掉,把我的羊只通通劫走,最后,我只好活活饿死。”(119)鲁滨逊面对与他截然不同的人类充满了不安与焦虑,来自未知的恐惧在持续的负面想象中不断丰满。因此即使两者尚未正面交锋,鲁滨逊也难掩憎恶之情。
然而待他解救、降服野人星期五后,他对同为野蛮人的星期五的描述又充满了溢美之词。从外表上星期五五官端正,没有狰狞可憎的样子,“脸上带着一种男子汉的英勇气概,可是又具有欧洲人的和蔼可亲。”(157)性格上星期五温和顺从,知恩图报:“他一瞧见我,就向我跑来,趴在地上,用各种各样的手势和许多古怪的姿势,表示他的恭顺感激的心情。”能力上星期五出类拔萃,聪明伶俐:“他比什么人都学得快,而且老是那么高高兴兴,老是那么用心学习。”星期五作为“他者”的身份并未改变,但是臣服于鲁滨逊的他,不再具有威胁性,反而因为其原始、神秘的秉性吸引了鲁滨逊探索、驯化的渴望。
《鲁滨逊漂流记》采用第一人称,主人公鲁滨逊是故事的唯一叙述者。受人称视角所限,我们无法洞察星期五的内心状态。在鲁滨逊眼中,星期五对他只有奴仆对主人的尊敬。然而果真如此吗?《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中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人以主人公奥贡喀沃的视角进行殖民叙事,直观呈现被殖民者的心路历程,读者得以窥见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矛盾情感。对于最初闯入的“骑着一匹铁马的”白人,“那些最先见到他的人吓得逃开了”。(160)面对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交通工具,原始部落人民下意识地退让躲避,将其视为不祥的征兆。长老们听从神祗,判定这个奇怪的人会毁灭他们的氏族,给他们带来灾难,于是当众杀了白人。虽美其名曰“请示诸神”,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氏族人民共同做出的决定;传说中的白人是可恶的侵略者,“能把黑人抢到海那边去做奴隶”。(162)氏族人民下意识地判断:象征着“他者”的白面孔昭示着未知的灾祸、劫难,远远避之方为上策。但是同时,白人作为神秘莫测的“他者”也时时刻刻吸引着氏族人民。传教士来临时,因为其中有一个白人,“所有的男男女女都跑出来看这个白人。”(166)由于关于“这些怪人的传闻越来越多,所以,人人都想来看看”。(166)未知滋生的不仅是恐惧,也是一探究竟的欲望。当恐惧被证伪,“他者”的魔力得到无限渲染后,抵触畏惧随即转向吸引向往。在白人传教士在受诅咒的凶森林中幸存下来后,教堂立刻多了几个信徒。(174)。
如霍米巴巴所言,差异的存在既滋生恐惧与抵触,又催生吸引和向往。双方处于矛盾的立场并且在不同立场之间滑动,展现出爱恨交织的情感倾向。这一点体现在两者之间模棱两可的表达和若即若离的交往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并未筑起一道爱憎分明的藩篱,相反,更像似陷入一道摇摆不定的情感旋涡之中。
三.双重的身份
殖民统治真正确立之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形成一种新型关系模式。传统二元论下,这种关系被解读为一种静态对立关系。殖民主义将西方塑造成手持福音的文明传播者,被殖民者则是接受教化的原始人。而民族主义则与之针锋相对,声称殖民者是十恶不赦的压迫者,而被殖民者是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的受压者。这两种学说揭露了部分客观事实,但皆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服务于政治目的,有意简化了双方身份和关系的复杂性。霍米巴巴以西方自由主义开山人物密尔为例,作出反驳,指出殖民者可能会集文明的创造者与贪婪的掠夺者为一身。(Bhabha1996: 93)[1]密尔在写出《论自由》等阐述自由主义经典之作的同时,担任东印度公司的新闻检察官,这一现象颇令人深思。用曼修莱的话来说:(殖民者)既是当地人的父亲又是压迫者,就公正又不公正,既谦逊又贪婪“。(Bhabha1996: 95)[1]
为了阐释这种现象的源头,霍米巴巴借用了拉康关于“自恋性”和“侵略性”的理论。拉康赞同黑格尔关于“承认”的解释,认为人的本质是欲望,这种欲望只能在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即每个主体都渴望他者的欲望,也即渴望他人的认可。但是每个主体又不愿意认可他人,因此对内表现出自恋性,对外表现出侵略性。希望获取认可的一方既要吸引对方的关注,又因为不愿认可对方而展现出攻击性。(Bhabha1996: 77)[1]在西方殖民者身上,自恋性是西方内部的现代性,而殖民性则是外在的侵略性。(Bhabha 1996:78)[1]西方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促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茁壮成长,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资产阶级陶醉于自我的现代化进程,对资本主义相关的制度、文化、精神产生了高度认同。因此他们不满于仅仅在内部发展的欲望,决心对外扩张,激进的冒险精神,疯狂的海外开拓,不远万里的传教活动都是扩张性的实际体现。资产阶级高度的文化认同和获得认可的渴望,使得殖民者不自觉地扮演着“父亲”的身份,以強势输出换取被殖民者的认同和信任。但是殖民者又不愿认同“低人一等”的被殖民者,排斥任何构建平等对话的可能,因此所有“施惠”都是以占有为前提,使之具有压迫者的属性,形成了双重的身份特征。
《鲁滨逊漂流记》开篇即介绍了鲁滨逊的资产阶级身份和与生俱来的冒险开拓意识。鲁滨逊出生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从小便充满了遨游四海的念头,一心想干出一番出人头地的大事业。他不甘在家乡度过安稳的一生,几度扬帆起航,希望在海外世界有所作为。自恋性与侵略性双重叠加,塑造了鲁滨逊“父亲”与“主人”的双重身份。成功驯服星期五后,以西方的礼仪教导星期五,以基督教开化星期五,以新式工具和武器提升星期五,力图在他的身上播下资本主义文明的种子,俨然一位开化启蒙的“父亲”。但是,这种帮助又是建立在“他者”的臣服之上。他骄傲地声称,“全岛都是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具有一种毫无疑义的领土权。第二,我的百姓都完全服从我:我是他们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186)面对外来的船长,他以统治者自居,“在你们留在这岛上的期间,你们决不能侵犯我在这里的主权, 同时必须完全接受我的管制。”(198)在不同的认知驱动下,殖民者扮演着不同的身份。
《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中展现出被殖民者同样在不同的认知阶段游离于不同的身份区间。作为“父亲”,西方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明和丰富的精神文化,氏族人民对殖民者产生了“孩子”般病态的依恋之情。白人建立商店,原料成为高价商品,殖民者的商业活动带来滚滚红利,人们品尝到不为生计发愁的美好滋味。教会的收留使得贱民不再流离失所,越来越多不被氏族认可的边缘群体向西方教会寻求庇护。(165)西方种种“扶助”麻痹了氏族人民的神经,一个一个地倒戈西方,老一辈奥比埃里卡不无哀叹“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儿子都已经加入了那陌生人的队伍。他们信奉了他的宗教,帮助他建立了政府”。(200)他们没有察觉到这一切并不是平等互惠的关系,殖民者的施惠仅仅建立在氏族人民沦为奴隶的基础上。氏族人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最终成为了白人的私产,他们建立政府、设立法庭、兴建教堂、开办学校,违反白人法律的黑人一律被丢进监狱,罚做苦役。黑人逐渐在自己的社会中丧失了话语权。当主人公奥贡喀沃认识到这一事实,他不由地发出愤怒地控诉“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呢?他们没有刀枪吗?我们一定要同那些人战斗,把他们驱逐出去。”(200)作为昔日的部族英雄,他率领众人摧毁教堂,反抗白人差役,体现了被殖民者向反抗者的身份转化过程。
正因为殖民者既渴望承认又抗拒平等对话,使之扮演着矛盾的角色,既是“施惠”的“父亲”又是高高在上的“主人”。被殖民者在糖衣炮弹下不由地被西方文明吸引,甚至自愿加入成为西方的代理人。但是他们真正的地位却是沦为白人的奴隶,当清醒的少数人认识到这一点,将抵抗威权付诸行动时,被殖民者的身份又随即向反抗者转化。霍米巴巴指出,两者既抗拒又吸引的矛盾心态,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也使得双方的身份处于不断地动态变化中。
后殖民理论著名学者霍米巴巴继承法侬、萨义德等人的理论基础,兼采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学分析方法之长,挑战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出发构建的二元对立关系,提出后殖民叙事是模棱两可、充满矛盾的对话过程。《鲁滨逊漂流记》和《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作为文坛两部关于殖民叙事的经典之作,分别代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视角,展现了两者在殖民进程中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嬗变过程。本文通过剖析两部作品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文明认知、情感表达和身份区间上自相矛盾的叙述,举例说明互为“他者”的事实如何塑造了双方既抗拒又吸引的矛盾心态,推动了充满矛盾的殖民叙事空间形成。论述直观呈现霍米巴巴后殖民叙事视角核心观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并非处于一种静态对抗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摇摆不定的动态变化过程。这种新的认知有利于促进对殖民主义的反思,并且为第一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后殖民时期面对文化杂糅现状,构建多元一体的现代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Bhabha, H. K. 1996.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2]Nnoromele, P. C. 2000. The Plight of a Hero in Achebe s “Things Fall Apart”[J]. College Literature 27(2): 146–156.
[3]Novak, M. E. 1961. Robinson Crusoe’s “Original Sin”[J].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1(3): 19–29.
[4]Novak, M. E. 1962. Crusoe the King and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His Island[J].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2(3): 337–350.
[5]Novak, M. E. 1963. Robinson Crusoe and Economic Utopia[J]. The Kenyon Review 25(3): 474–490.
[6]阿契貝.2014.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M].高宗禹.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7]笛福.2002.鲁滨逊漂流记[M].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8]福柯.1999.规训与惩罚[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康拉德.2011.黑暗的心[M].黄玉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0]马基雅弗利.1985.君主论[M]. 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1]萨义德.2007.东方学[M].王宇根.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2]斯陀夫人.1998.汤姆叔叔的小屋[M].王家湘.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3]姚峰.2011.阿契贝的后殖民思想与非洲文学身份的重构.外国文学研究[J].33(3):9.
[14]赵稀方.2009.后殖民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5]邹宏,王福娟.2021.《鲁滨逊漂流记》的后殖民主义解读[J].中国电影(2014-3):98-99.
注 释
①笛福.2002.鲁滨逊漂流记[M].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此书的引文随文标注页码.
②阿契贝.2014.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M].高宗禹.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以下此书的引文随文标注页码.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