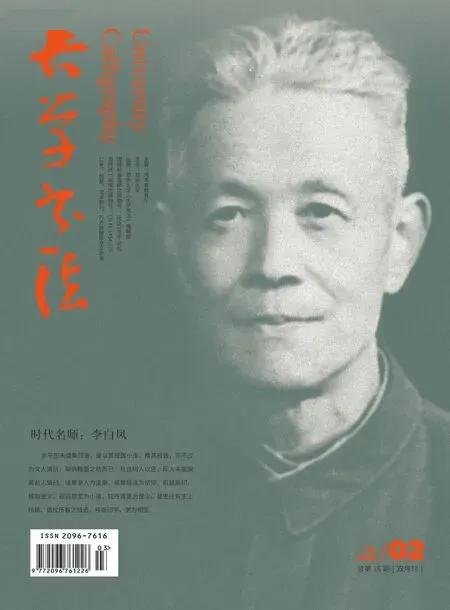“魏碑体”“北凉体”“写经体”关系再考
2022-05-20古飞
⊙ 古飞
介于“魏碑体”“北凉体”“写经体”三者关系的阐述,苏叶曾在《“魏碑体”“北凉体”“写经体”衍生关系刍议》一文中认为这三者首先是存在着一个衍生的关系,“衍生”即演变而产生,这种关系链中势必存在着一个“母体”,她认为“魏碑体”包含“北凉体”,“魏碑体”即为“母体”;“北凉体”影响着或在一定意义上衍生了“写经体”,“北凉体”即为“母体”;同时又认为“魏碑体”与“写经体”相互影响。这三者的关系真是如此吗?笔者对此持质疑的态度,并进行重考。
一、“魏碑体”“北凉体”“写经体”的定义综述
厘清这三者的关系之前,对其定义的述析是极有必要的,其中“魏碑体”的概念,丛文俊认为:“所谓‘魏碑体’,即北魏刻石书法中作为主流、有其楷书典范样式的作品类型,以洛阳周围出土的皇家和元姓贵族墓志为代表。”[1]丛先生认为“魏碑体”是以洛阳楷书典范的类型为主。刘涛先生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曾定义了“魏碑体”的概念,“清朝碑学家所说的‘魏碑’‘碑体’,是指北魏的刻石书迹,而且是指‘真楷’,康有为所谓‘今用真楷,吾言真楷’”[2]。然而还有一种与此相异的说法,即“所谓北碑,一般是指北朝碑版文字的统称。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其中,尤以北魏为最,所以北碑习惯上又称为魏碑”。[3]“魏碑体”的概念从“真楷”的基础上被放大至整个北朝碑版体系书体的范畴,众所周知,北魏时期的“魏碑体”系以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为主流,“从大的时间概念讲,大同(古时称平城)魏碑可以称为早期魏碑,洛阳、邺城魏碑乃至齐、魏、隋北朝铭刻书迹则是中晚期魏碑”[4]。在早期的碑石中,有一些书体的面貌是以隶书呈现的。如1965年在大同市石家寨村出土的《钦文姬辰墓铭》,结体宽博开张,横画的起笔和收笔都呈现上翘的形态,尾端作“雁尾”状,隶书意味浓重。
“北凉体”的概念最早由施安昌先生提出:“鉴于此书体在四世纪末期和五世纪前期的古凉州及以西地区盛行,又在北凉的书迹中表现最为典型(如《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故称之为‘北凉体’。”[5]施先生通过对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发现的20种书迹进行综述比较,发现这类书体存在着“字形方扁,上窄下宽,尤横画的两端上翘,书体为隶楷之间”的共性。“北凉体”以文物所见的可分为写经、佛塔、造佛寺碑和墓表四类,在《北凉体书迹叙录——兼谈铭石书与写经书》一文中施安昌详细表述了这四类文物形式,于此就不一一赘述。还有对“北凉体”书体定义为隶书的观点,华人德认为:“‘北凉体’是魏晋时铭石书演变至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形成的一种形态较独特的隶书,应该是一种隶书的时代风格。”[6]刘涛将“北凉体”归属为当时的“正体隶书”。[7]

杨阿绍造像碑题记拓片 选自线装书局《汉魏六朝碑刻校注》
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是在东汉。《魏书·释老志》中记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8]随着佛法的传入,译经、经书传抄的活动兴盛起来,“写经”成为一种职业。郑汝中对“写经”的理解较为具体,“所谓‘写经’,是佛教为弘布流通经典,用纸墨抄写,进行宣传的一种活动形式。我们从敦煌经洞发现的写经中……其中包括:经文、经目、注疏、释文、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等可以统称为写经”[9]。早期的写经有一定的格式规范,行间均以乌丝栏区划之,其书写的特点是“横画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多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10]。我们目前能见到最早的写经本则是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所用的技法亦是如此。类似于此种“书法样式上,于六朝时代系以一种所谓之六朝体(如隶书、八分书等)书之,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体——‘写经体’”[11]。
关于写经书法,华人德与郑汝中持两种不同的观点。华先生注重的是写经书法的保守性,“僧尼、经生和信众在抄经时,须按照旧本体式抄写,不羼入己意。这样,魏晋时的写经书体就一直沿袭下来,变化很小”[12]。而郑汝中着眼于写经书法的变动性,他认为:“写经是一种古代的书法形式,敦煌写经是遗书中的一个内容,它本身并未形成书体。写经的书体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中的书体。”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写经书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写经书体确实经历了“隶——隶楷——楷”的嬗变过程,它是符合书体演变规律的,只是由于写经书体本身就带有佛法的光环,须持虔诚之心,而不掺入己意,有一定的程序化形式,无疑会有很强的滞后性和稳定性。
二、“‘魏碑体’包含‘北凉体’”论再考
苏叶所持“‘魏碑体’包含‘北凉体’”的观点源于殷宪对“魏碑体”的认识,殷先生认为完整的“魏碑体”体系应当涵盖凉州体、平城体、洛阳体。[13]以苏叶看来,凉州体确为或者包含“北凉体”,然而,苏叶又提出“北凉体,即北凉地区的地方体”的观点,[14]实难自圆其说。在上文曾提出,施安昌先生曾对20种在十六国时期出现的书迹加以比对。发现除了三四件以外,其余的书迹都颇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气势,并将“北凉体”形成的时间考证为4世纪末期和5世纪前期,北凉的书迹只是其中一个典型,整个论述的过程并没有将“北凉体”只置于北凉地区出现的迹象。
对“北凉体”形成时间与地区的误读,类似“‘魏碑体’中的‘北凉体’”观点的提出。施安昌先生在《“北凉体”析——探讨书法的地方体》所举的20种书迹中,在敦煌发现的《维摩诘经》考证时间为后凉麟嘉五年,即393年,据其书迹的特征、形成时间可归属为“北凉体”的范畴。根据上文对“魏碑体”定义的解析,若以整个北朝出现的碑版形式都可统称为“魏碑体”的角度去理解,北魏是北朝的始端,“魏碑体”形成的年份不会比386年更早。而在北魏时期的魏碑书法中,平城魏碑书法又可视为一个早期的魏碑书风体系。在早期的平城魏碑体系中按时间又可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为道武帝定都平城到献文帝拓跋弘时期(398—476)、孝文帝太和元年至迁都洛阳(477—494)、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15]按时间的先后来论,具有“北凉体”特色的作品较平城早期的魏碑体出现得更为早些。故而“‘魏碑体’包含‘北凉体’”的观点明显是不成立的。
再看2000年在山西大同市智家堡村出土的《王斑》《王礼斑妻舆》墓砖,其被考证为明元帝永兴元年(409)的产物。根据上文“北凉体”的形态特征来看,《王礼斑妻舆》中的“王”“礼”“舆”字都是呈扁形,上窄下宽,并且横画的末端有略上扬之意,但并不明显。这些可疑的迹象是否也可以认为“北凉体”反而是影响了“魏碑体”呢?
“北魏的铭刻书法与北凉是一以贯之的”[16],北凉与北魏的国俗相近,北凉毗邻西域,其“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深受佛法教化。北魏时期,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举国尊崇佛教,兴建石窟,如平城时期的云冈石窟、洛阳时期的龙门石窟。而北魏刻凿造像,其所征用的工匠多数来自凉州地区,“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后,将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余家迁徙到平城,这中间就有许多高僧与擅长刊刻造像的工匠。主持营造大同石窟的就是来自北凉的昙曜”[17]。如立于北魏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佛道造像碑》,同样采取了“北凉体”式的横画两端上扬,并且翻翘得更为夸张,而且结体的形态稍有灵活,不止于扁平状。又如刻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的《杨阿绍造像碑》,结体方中带扁,横画的两端同样呈翻翘状。这说明即使北凉灭亡后,以北凉书迹为典型的“北凉体”风格继续存活在北魏时期,而并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来认定“北凉体”影响了“魏碑体”。
三、“‘北凉体’影响着或在一定意义上衍生了‘写经体’”论再考
佛教最早是在东汉传入中国,写经本最早可见的是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且是“写经体”的雏形或源流。而苏叶在《“魏碑体”“北凉体”“写经体”衍生关系刍议》一文中认为的“北凉体”是北凉地区的地方体。全览整篇,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有力的实证,若依作者的本意,北凉的立国时间是公元397年至公元439年或460年,比《诸佛要集经》出现的时间更晚一些。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北凉体”也影响不到先出现的“写经体”,故,“北凉体”影响或衍生了“写经体”的观点实有商榷之处。
沈乐平在《敦煌遗书百讲》第二十辑中提到“敦煌‘写经体’的第一阶段,即晋末至北周的二百年,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品,若升平十二年(368)的《道行品法句经》……等皆可为典范”,其中《道行品法句经》的缮写时间远比北凉建国早,说明在北凉建国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写经体”,所以,苏叶的观点自相矛盾,实为荒谬也。
北凉铭石刻迹与写经书面貌中可寻得相似之处,从两种书体的风格确实可见一斑。薛龙春列举在甘肃出土的《酒泉马德惠石塔刻经》(426)、《酒泉高善穆石塔刻经》(428)、《酒泉田弘石塔发愿文》(429)等大量铭石刻迹与写经书的风格极为相近。薛先生认为:“大量的北凉铭石书刻中,这些写经书法的体式被完整地吸纳了。”反而可以认定为“北凉体”的风格一直深受着“写经体”的影响,如果依据时间序列的逻辑来推测,这种观点的提出似乎榫接得完美无缺。若以其风格的延续来判定二者母体与子体的衍生关系,所有的论证都将显得苍白无力,究其因,“北凉体”与“写经体”的书体面貌都存有浓厚的“隶意”,虽然写经本最早见的是《诸佛要集经》,以“写经体”面貌出现的写经书法比“北凉体”书风要早一些,但很难去寻得在同一时间内出现的两种书体作品加以比对,我们也没有见到“北凉体”最早期的作品,况且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敢雄辩地鉴定哪一幅书迹或铭石刻迹可代表着“北凉体”最早期的风格。因此笔者认为,“写经体”的体式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对“北凉体”有些影响,而它们二者并不存在衍生的关系。

钦文姬辰墓铭拓片 选自线装书局《汉魏六朝碑刻校注》
四、“‘魏碑体’受‘写经体’的影响”论再考
苏叶所持的这种观点深受丛文俊先生的影响。在《魏碑体考论》中有这样的观点:“从现有资料看,写经与‘魏碑体’的关系最近。”而他也进行了解释:“‘魏碑体’自通俗的类于写经的书法时尚中规范、脱化而出。应该看到,在佞佛的风气中,书法取尚上下趋同,这对‘魏碑体’的迅速成熟,形成一定的通行样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鼎盛的佛教和写经活动作为媒介,在不暇讲习文字,也不重视书法的北朝,能使北方广大地区的各类刻石书法面目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是不可想象的。”[18]丛先生站在了一个很宏观的角度来透析“魏碑体”与“写经体”之间的关系受着佛教的影响,又根据“魏碑体”中能隐见出写经书法的风格再次确立了“‘魏碑体’深受‘写经体’的影响”的观点。如西魏《贤愚经》,他说:“一旦加以刀斧之迹,即会与同时的造像记、碑志中的某些作品无异。”[19]通过对棱角进行修饰,会成为“魏碑体”中的佳作;再如晋人《第五十三品释论》,“字势倾斜而略成梯形,用笔方折而平直带过,已初备‘魏碑体’的基本特征”[20]。总的来说,丛先生认为“魏碑体”是借力于写经书法,并加以棱角修饰、凿刻改造而完成的。
可在华人德看来,却对“‘魏碑体’受‘写经体’影响”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魏碑体”不同于“写经体”。并在《魏碑体》一文中解释道:“(写经体)正处于汉末由带有波磔的隶书即‘八分书’和不带波磔的简率隶书向楷、行书过渡的阶段。”[21]而“写经体到南北朝时,与当时世俗流行的楷书是有明显区别的”,“写经体含有隶意,隶书的横画一般不带斜势。‘写经体’与带有明显斜势的‘魏碑体’是显然不同的”[22]。华人德通过“写经体”与“魏碑体”的风格不同来认证二者存在着区别,同时这也与当时抄经的经生也有很大的关系,“抄经的人大多为寺院僧尼和以抄经为职业的经生,这些人一般是看不到名家手迹的,他们习书的范本就是前人抄写的经卷,当他们抄经时又须依照旧本抄写,不掺入己意。这样,魏晋时期的写经书体就一直沿袭下来”[23]。笔者认为华人德的分析可圈可点,在当我们以“求真”的心态去剖析丛先生所提及的写经书迹时,会发现最终的结论是不符合丛文俊先生初衷的。
通过比对,西魏的《贤愚经》与北魏时期的《张黑女墓志》倒是有几分相似,尤其是《贤愚经》中的“大”与《张黑女墓志》中的“太”的捺画状,如出一辙,而且结体都呈扁平状,究其时间的先后,北魏的建国时间较西魏更早,《贤愚经》出现的时间较《张黑女墓志》更晚些,倒是可以反推为此时的“写经体”受着“魏碑体”书风的影响也不为过分,如北魏正始元年(504)的写经《胜鬘义记》,方峻的笔画,带有棱角的捺画,结体紧凑,明显呈现的是“魏碑体”的特征。
再说晋人的《第五十三品释论》,我们从中很难读出“初备‘魏碑体’基本特征”的迹象,也没有魏碑书体结体左低右高、笔画紧结、横画呈斜势的标志性特点。所以丛先生的举证难免过于牵强。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虽然苏叶在《“魏碑体”“北凉体”“写经体”衍生关系刍议》一文中阐述过华人德与丛文俊先生之所以有此不同的见解,是因为他们对“魏碑体”的概念较为含糊,又指出“魏碑体”的风格较为多样,其概念较为宽泛,但“魏碑体”的概念早在清代康有为时就做出了诠释,并且刘涛的《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又对“魏碑体”的概念进行了综述,以为整个北朝可出现的碑版等都可谓“魏碑体”。其所言的“多样、宽泛”只是源自殷宪对魏碑体系的理解,然而并没有给出有据有理的实证。即使我们用辩证的态度去看待“魏碑体”,“魏碑体”的形成时间最早不及北朝的确立时间,这是一个事实。那么“魏碑体”便会具备着“横画倾斜、结体紧结、左低右高”等的楷书基本特征,即使是早期的魏碑书风含有隶意,那也只是经“隶书”书体演变为隶楷的阶段,而并不会受“写经体”的影响。所以,在有些确凿的事实面前,无凭据或只持一家之见很难撼动权威。而且没有依全面的论据来进行论证的观点,无怪乎会被方家视为一种噱头。
结论
一、“魏碑体”的称谓首见于康有为的著述,其所涵盖的范畴不外乎北朝的碑版刻石,并且“魏碑体”是在整个书体演变的规律中形成的,是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的新生儿。所以早期的魏碑书风隶意极为浓重,似“北凉体”或“写经体”,但“北凉体”与“写经体”只是书体演变史中的分支,并不受“北凉体”“写经体”任一的影响。
二、写经书风的形成较“北凉体”书风早些,而且从甘肃出土的铭石刻迹来看,关于“写经体”的特征在这些铭石刻迹中都有汲取。只能说在一定的时期,“写经体”的体式曾被“北凉体”所吸纳过,但是其二者并不存在“衍生”的关系。
注释:
[1]丛文俊.魏碑体考论[J].中国书法,2003(3):42.
[2]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33.
[3]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34.
[4]殷宪.北魏平城书法综述[J].东方艺术,2006(12):22.
[5]施安昌.“北凉体”析——探讨书法的地方体[C]//施安昌.善本碑帖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242.
[6]华人德.“北凉体”刍议[J].书法研究,2004(3):65.
[7]刘涛.中国书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372.
[8]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25.
[9]郑汝中.汉字的演变与佛教的写经、刻经[J].书画世界,2003(7):13.
[10]华人德.论六朝写经体——兼及“兰亭论辩”[C]//华人德.华人德书学文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47.
[11]尚荣.佛教书法“写经体”与写经生[J].民族艺术,2013(3):151.
[12]华人德.论六朝写经体——兼及“兰亭论辩”[C]//华人德.华人德书学文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48.
[13]苏叶.“魏碑体”“北凉体”“写经体”衍生关系刍议[J].中国书法,2017(20):50.
[14]胡愚.试探平城时期魏碑体书法[D].北京:中国民族大学,2010:1.
[15]殷宪.北魏平城书法综述[J].东方艺术,2006(12):7—20.
[16]薛龙春.论北魏洛阳体的成因[C]//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295.
[17]薛龙春.论北魏洛阳体的成因[C]//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296.
[18]丛文俊.魏碑体考论[J].中国书法,2003(3):44.
[19]丛文俊.魏碑体考论[J].中国书法,2003(3):44.
[20]丛文俊.魏碑体考论[J].中国书法,2003(3):44.
[21]华人德.魏碑体[G]//华人德.六朝书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67.
[22]华人德.魏碑体[G]//华人德.六朝书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68.
[23]华人德.魏碑体[G]//华人德.六朝书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