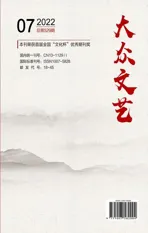农耕文明场域中山水诗与山水画融合的研究*
2022-04-26仇恒佳
张 敏 叶 琦 仇恒佳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苏州 215008)
山水诗与山水画是中华文明特有的艺术形式,其萌发、生长,以及最后走向融合,无不与所生出的中华大地农耕文明场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一、农耕文明场域中山水诗与山水画的兴起
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的黄河、长江,一北一南由西向东奔腾不息注入大海,两条巨龙般的大河孕育了华夏农耕文明。大约在一万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分别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开始种植稷、粟、稻等农作物,开始了聚族而居的定居生活,也开始了文化的创造。
农耕文明以农业为本,农业生产需要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阳光、丰沛的降雨,大自然为农耕文明场域里的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人们守望田园,企盼风调雨顺。因此,相较于工商业为主体的海洋文明,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对大自然更具依赖性和亲和性,农耕文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和观念,并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走向。
发现于云南沧源的崖画《村落图》,“经科学手段对染料和覆盖在画面上的钟乳石等遗迹鉴定,岩画作画年代为距今三千年之前。其时的社会形态,大约已经进入原始农业经济的氏族社会末期阶段。”《村落图》不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可视为中国山水画萌芽的胚胎。该图幅超过一米见方,场面巨大,以村落为中心,连接左右延伸的道路。“画面以散点透视表现全景的构图形式,描绘出村落暮归的场景。”《村落图》这种对村落与道路关联场景的刻画,传达出农耕先民对家园,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也在源头上奠定了中国山水画不同于域外风景画的根基。
距今三千多年历史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主要记载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诗经》中,自然山水并没有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存在,只是比、兴的材料。比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彼泽之陂,有蒲有荷”的句子,借自然山水以起兴,从中可窥见先民对美丽大自然质朴的亲近和向往之情,其间蕴含了山水诗萌芽的种子。
中国山水诗与山水画的真正兴起要待历史的车轮走到汉末魏晋六朝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时代,在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看来,不仅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在精神史上却是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山水诗与山水画同时兴起于这样一个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的。
魏晋六朝是中国农耕文明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代,战乱频仍,王朝更迭瞬息万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这个苦难时代的一个写照。险恶的政治环境,名士少有全者。“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心之忧矣,咏啸长吟”,“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些诗文传达了文人士大夫在残酷的政治倾轧下朝不保夕的生命忧叹。无常的命运和人世间的悲伤,引发了人们对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探索,促使了“任自然”的魏晋玄学取代了系统化教条化了的儒家纲常名教,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这是一个“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文人士大夫隐居山林,悠游山水,不仅为了全身远祸,更是在纵情自然山水中感受到自由的实现和人格的超越。顾恺之眼中的会稽山川“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嵇康则在“游山泽,观鱼鸟”中,放下忧惧之心,而“心甚乐之”。
这一时期,因战乱而出现的门阀士族割据,催生了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也为魏晋人士终日在庄园中饮酒作诗、纵情自然山水提供了可能。石崇金谷园中的“娱目欢心之物”齐备,而谢灵运的山居以其无所不备,竟可以“谢工商与衡牧”。谢灵运建园则“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自然之神丽”实为自然山水之美。“质有而趣灵”的自然山水开始进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诗、山水画兴起于魏晋六朝这样一个深于情、浓于艺的时代。在兴起之初,就朝着相互融合之路而日渐行进。
二、农耕文明场域中山水诗与山水画的渗透融合
1.在结构布陈上“俯仰自得”的开阖节奏
农耕文明场域中的人们在天地自然山水间生活劳作,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全息全方位地呼吸自然、感受自然,与大自然的节律同一脉动,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乾坤观、天地观、山水观,深深地影响了山水诗和山水画的结构布陈。
山水诗、山水画在空间结构的布陈上相互影响,呈现出“俯仰自得”的开阖节奏。正如《中庸》上说:“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这种上下察也的俯仰结构视角在山水诗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在山水诗作《初去郡》中这样写道:“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诗人涉溪登岭,仰观高天,一轮明月朗照天宇;俯瞰旷野,沙岸一片空寂明净。诗画兼善的王维在《山居秋暝》中所写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也妙用了俯仰的开阖结构,仰望东升的明月将一束青光洒在松林间;俯视脚下,一泓清泉在清澈见底的河床上潺潺地流淌着。山水诗人在宇宙天地的俯仰间,将自然万象吐纳于心胸。正如孟郊所言:“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这种物象由我裁的俯仰自得的山水诗的开阖结构,在山水画的布局剪裁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明山水画家“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身所盘桓,目所绸缪”的山川景物并非如西方风景画所采用的“定点对景”的焦点透视,而是采用“俯仰自得”的散点透视法,据情剪裁,移步换景,尺幅之中写千里之景,从而形成中国山水画所特有的多重视轴,使得观者可以从上至下或从下至上,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同时欣赏画家心目中的山水世界。一般在观赏山水画时,往往抬头所见的是巍峨的山峰,背后是朦胧的远山、云雾等,然后由远至近,层层向下,窥见深远的山谷,再转向画家或观者所流连盘桓的水边林下。
中国山水诗人和画家用“俯仰自得”的眼光来欣赏宇宙、摹画山川,直参造化,与化同游。
2.在色彩上“以色貌色”的绚丽多姿
自然山川充满绚丽迷人的色彩,而色彩的感觉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具有传情达意,抒发情感的作用。农耕文明场域中生活的人们对大自然的缤纷色彩更具敏锐的觉知力与感受力,因此无论是画家还是诗人都非常重视色彩的捕捉与表现,诗之情画之意,色彩的运用起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国古代曾用“丹青”一词来称谓绘画,由此可以看出色彩在绘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宗炳在《山水画序》中提出了“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绘画原则,意是说以山水的本来之色,来表现为画面上的山水之色,也就是说绘画要客观地再现大自然的美,必须通过色彩来完成。浅绛山水、青绿山水、金碧山水等,就是用或淡雅或浓烈的色调将绚烂多姿的自然山水之美表现出来。天才少年画家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是青绿山水画中的一幅巨制杰作,全卷以青绿重彩设色,画面青山叠翠,气势雄浑壮阔,不仅表现了山河的壮美秀丽,也传达了天才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而水墨山水画则通过焦、浓、重、淡、清的五色之墨,来表现随着阴晴和季节的变化而有不同呈现的山水之色,更耐人寻味,更有余韵。
山水画的多彩色调对山水诗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山水诗是语言的艺术,虽然不能像造型艺术那样直观地将色彩呈现出来,但可以通过语言的抽象表述和描写,引发读者无限的联想和想象,同样可以给人一种绘画美的享受。山水诗人往往都是善于运用语言进行调色的大师,笔下瑰丽的文字生发出五彩缤纷的色调来。谢灵运的“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王维的“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杜甫的“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等等。这些诗句对色彩的捕捉和把握细致入微,白、绿、红、紫、青、黄等颜色的配搭,犹如山水画中绚烂夺目的色彩,生动形象,楚楚动人,使读者感受到既旷大高俊又妩媚多姿的自然山水之美,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
3.在意境上“情景交融”的悠悠韵致
意境是山水诗和山水画共同的美学追求。意境的创造离不开“情”与“景”的融合,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方能成就艺术境界。山水诗和山水画在情景交融上互启互发互摄,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晋人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诗缘情”的诗歌理论。“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而自心灵而出的情思是要通过一定的媒介物才能得以释放安怀。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诗人“以景写情”,在对自然山水的观照描摹中寄情咏怀。被苏轼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其田园山水诗充分体现了“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的诗作里,诗人以其精妙的语言文字,为人们呈现了苍翠寒山、潺湲秋水、渡头落日、墟里孤烟这样意境深远的画面,折射出了诗人幽居山林,超然物外的淡泊情致。
绘画作为空间造型艺术,虽然摹景状物为其主要特征,但在画家笔下所描绘的不是纯客观自然景物,而是心物相照、物我合一之景,是融汇了画家心灵感触、深契着主观情思意趣之景。山水画家“融情入景”,使本无情的山水皆融我之情感,皆著我之色彩。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指出山水随四时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情感意态:“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笑、滴、妆、睡,是形态,也是意态,著上了人的情感色彩,所以“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山居图》,以清润的笔墨描绘了初秋富春江两岸浩渺连绵的秀丽景致,营造了一种绵邈简远的意境,犹如优美的乐章、如歌的行板,余音袅袅,令人回味无穷。这是黄公望心灵中的山水,是可栖居的精神家园。
诗中景,画中情;景生情,情融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交融,呈现出意蕴悠悠的韵致。
三、山水诗与山水画融合的现代价值
山水诗与山水画自魏晋六朝兴起之日,就朝着融合之路走来。到了宋代,随着文人画的兴起,山水诗走进了山水画,两者实现了真正的融合。时至今日,作为山水诗与山水画融合之载体的文人山水画,也已走过了千年的历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1.自由人格的塑造
文人画实质是一种全新的艺术生命境界,它为文人提供一处心灵的家园,一种诗意的精神栖居。美国著名艺术史家卜寿珊就直接称文人画为“心画”,实为文人画家的心灵表达与寄托。文人画家多寄情山水,在自然山水间牧放性灵,追求生命的自由和人格的超越。清代画家石涛在题画诗中写道:“我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为我开,江水随我起。”在对自然山水的摹画创绘中,画家体验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欢然自由之境。石涛在其绘画理论著作《苦瓜和尚画语录》中表达了“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的追求。在文人山水画的创作和欣赏中,在自然万物的陶冶涵泳中自然而然地扩大自我的胸襟与气度,这对自由人格的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2.生态伦理的建构
文人画家笔下的自然山川充满和谐悠然之气,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温暖亲和的关系。这在明代吴门画派的开山者沈周的山水画中有着生动的体现。沈周一生不仕,悠游林下,他的画有着“平和”的风格。“在沈周身上体现出中国历史后期发展中士人所崇尚的一些精神气质:轻视物质,重视人间温情,亲和世界,以及于一草一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在典雅细腻的生活中感受世界的美。”沈周笔下的《青园图》《东庄图》《云际停舟图》《京江送别图》等,以各种皴擦点染的生动笔墨描绘了或淡远、或清丽、或俊逸的山川树石林园,在这静穆优美的自然环境里,人们或读书、或郊游、或渔猎、或送别,人与自然是那么的亲和无间,那么的悠然自得。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智慧,对在工业文明时代人对自然的征服、破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关系的建构,无疑是起到重要的观照、启迪和反思的作用。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诗画一体的文人画,包蕴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凝结着儒、道、禅传统哲学思想和美学理念,生动地传递着农耕文明孕育、滋养的中华民族的气质与精神。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与弘扬。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人山水画可以说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壬寅春晚播出的创意音舞诗画作品《忆江南》,以新技术手段,实现了与《富春山居图》跨时空的互文与对话,不仅带给了受众视觉上的审美盛宴,更给受众以栖居山水、回归自然的人文精神价值的熏染。这不仅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更有助于增强文化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总之,农耕文明场域中生长出的山水诗和山水画,虽然艺术形式不同,但两者在结构布陈、色彩、意境上相互影响、启发和渗透,最终融合形成了诗画一体的文人山水画。对于自由人格的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的建构,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