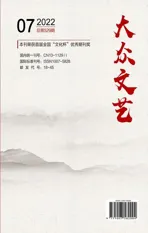五四启蒙与庐隐的女性书写
2022-04-26孙洁
孙 洁
(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山东青岛 266003)
近几年,“女性文学”越来越多地跃入人们的眼中。然而,“什么是女性文学”却是一个几近模糊的空白。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作家和教育家埃莱娜•西苏,在她的著作《美杜莎的笑声中》,采取了解构的策略,试图在文化上建立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而不是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国内的女性文学评论家孟悦、戴锦华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也在文学领域内,运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拉康精神学说等多种方法来对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探索。事实上,无论“女性文学”怎样定义,它始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在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机遇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这几乎成了中国的女性文学区别于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重要特征。庐隐便是接受这一新的文化理论的作家之一,她出生在五月四日这一天,生为五四时代的女儿,她在二十三岁便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成为五四时期第一个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女作家。茅盾先生称她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第一人”。可以说,从《海滨故人》开始,女性意识开始在庐隐敏感的内心中觉醒。
一、智慧与勇气的最初探寻
(一)机智聪敏:知识女性的独特魅力
激烈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培育了一代智慧之女,她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新知识的甘露;“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的大旗被一批又一批的出走的女儿们高高举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知识女性的象牙之塔是在“五四”这个崇尚“科学”与“民主”“理性”与“智慧”的充满大智勇者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对于“五四”时代的叛逆的女儿们来说,知识与智慧成了她们照亮愚昧、无知的封建的黑暗王国的一枚火炬,是她们出走家庭,叛离角色,追求理想的一盏明灯,更是她们决绝否定“女人是花瓶”,“女人是玩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的传统性别规范的坚定的理想信念。
庐隐曾为自己少时的愚笨无知而深深痛苦过,家人也因为她的笨拙而冷落呵斥她。正因为如此,童年的庐隐孤僻成性,过着悲苦的寄人篱下的生活。童年的厄运终究因为庐隐自己的奋斗而打破,知识的增多也令母亲和亲戚们对她赞赏有加。更为重要的是,在求学的过程中,由于文艺的熏陶和新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庐隐改变了童年时拗傲孤独的坏脾气,一代机智聪敏的知识女性正在长成。
庐隐自身的求学经历在冥冥之中暗合着“五四”的时代大潮。尽管妇女解放的道路还有待深掘,然而敏感的庐隐清楚地看到,只有智慧与知识才是悲苦女性自救于苦海的阶梯,才是在新的多元文化时代争取女性独立话语权的关键。所以在庐隐的小说中,总有几个颇具才情且机智聪敏的优雅的叛逆少女,在窗前的紫藤花架下,在落日的余晖里,或是在“左绕白玉之洞,右临清溪之流”的海滨小屋旁,畅谈着人生究竟的问题,诉说着离愁别恨的伤感情绪。敏感脆弱的亚侠,尽管遭受着心脏病和失眠症的折磨,却依然在被病痛折磨得不能入睡的夜晚,偷偷地读着探问人生哲理的诗,把笔作书地写下流露自己心绪的文字:“我一生的事情,平常得很!没什么可记,但我精神上起的变化,却十分剧烈;我幼年的时候,天真烂漫,不知痛苦。到了十六岁以后,我的智情都十分发达起来。我中学卒业以后,我要到西洋去留学,因为种种的关系,做不到,我要投身作革命党,也被家庭阻止,这时我深尝苦痛的滋味!”从亚侠的这一段自述中,我们寻着了一代知识女性投身时代洪流,追求智慧人生的机智聪敏的美丽身影,她们渴望在“五四”这个崇尚自由与平等的大时代里,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完成对自我的拯救,进而完成对社会、对民族的拯救!
(二)果敢决绝:叛逆女儿的永恒姿态
五四时代为我们塑造了两座永远不会为女儿们所遗忘的美丽的塑像,定格了她们反叛传统、出走家庭时果敢决绝的人生姿态,那便是娜拉与子君。
可以说,娜拉与子君几乎代表了新文化新女性价值观的全部标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注意的文化现象。尽管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便是回来”的残酷现实,子君在叛离叔父的家庭之后却在不自觉中落入婚姻家庭的藩篱的悲惨处境,但这却并不影响“五四”的时代之女们不顾一切地逃离那个禁锢自己的父亲的家门。事实是,时代已停不住前进的脚步,不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现实里,叛逆的女儿们都已在娜拉式的精神、子君式的思索的指引下,果断决绝地迈出了她们区别于旧女性的第一步。
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女儿们已经觉醒并且毫不畏惧地进行了反抗。正如和庐隐同处“五四”时代,同样是叛逆的女儿,同是对旧式婚姻家庭决绝反抗的冯沅君在她的代表作《隔绝》和《隔绝之后》中写道的那样:“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毋宁死”,“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走去看海去”,这是何等果敢决绝的叛逆姿态呢!在庐隐的笔下,露沙和她的伙伴们同样被赋予了这种性格:虽然清瘦,但却十分刚强;脾气爽快、但心思极深。同伴们都评价她为“短小精悍”。因为相同的志向和理想,露沙不顾外界的压力和反对,爱上了已是有妇之夫的梓青。她喜欢研读他的散文,喜欢和他通信互换各自对事件的见解,心灵的沟通使他们“从泛泛的友谊,变为同道的深契”。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清醒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叛逆的女儿渴望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然而却更渴望她们作为女性个体的精神独立和主体自由。她们机智聪敏的独特魅力,她们果敢决绝的叛逆姿态,与其说是由爱而生发,不如说是为了她们作为“女性”这一主体的挣扎和应有的权利的探索而熠熠生辉,永不磨灭——在历史舞台上缺席了两千多年的美丽身影在这一刻重新开始了对智慧与勇气的最初探寻。
二、爱情神话的破灭
(一)人生究竟的终极追问
露沙们常常喜欢写信给朋友来交换彼此对于人生的看法。“人生究竟有几何?穷愁潦倒过一生;未免不值得!”露沙甚至因为在上哲学课的时候思考“人生到底做什么”的问题而饭也不吃不好,觉也睡不着。这便是“五四”的时代大潮退却后留给叛逆的女儿们的无尽的困惑与迷茫。露沙们可以在风云激荡的“五四”时代为奔走国事而忙乱,她们可以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在天安门开民众大会,去总统府请愿,于十字路口演讲,却无法承受时代的激情退却后留给她们的生命之轻。她们以超越现实的方式和规避时代的姿态去思考整个人类的有关问题,并试图将这些问题上升到人生观的高度进行思考。露沙最终留书而去,“今行有期矣,悠悠之命运,诚难预期,设吾辈卒不归,则当留此庐以飨故人中之失意者”;云青更是“出世之想较前更甚,将来当买田造庐于山清水秀的地方,侍奉老母,教导弟妹十分快乐”;“游戏人生”的亚侠在疾病缠身的夜晚中不自觉地幻想出了人间之外的美丽花园,“比较人间无论那一处都美满得多”,却仍然在对人生究竟的终极追问中迷茫不堪,自尽于银花闪烁的湖心,“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生悲戚之感”,苍凉悲苦的氛围,至死都未散去。
露沙们善于思考,却也迷茫于思考。显然,她们的探索以失败而告终,她们执着的追问也没有得到时代的回答,最终淹没在历史的一片苍茫之声中。她们已无法从思考中探寻到人生的真实意义,只能陷入无尽的迷茫之海,甚至以死亡这样沉重的字眼来承担这份时代大潮退却后留给她们的人生之轻。
(二)情智不谐的文化死结
理性精神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先驱者们所积极提倡的,自觉地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追求理性的精神,也是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思潮的一种反映。然而吊诡的是,在庐隐的笔下,理性与知识却成了她们悲愁哀苦的源头了。这是露沙的感叹,这是云青的疑惑,这更成了宗莹的懊悔。对知识和理智的巨大怀疑,成了姐妹间的不言自明的共同默契,甚至成了她们迷茫困惑的最有力的借口。当她们不约而同陷入爱河时,“理智”不合时宜地跳了出来,阻挡在“感情”的面前,竟令她们“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
露沙生性孤僻倔强,却偏偏是个感情丰富的女儿,动人心魄的爱情来了,她自然要为情所战胜,“至于平日故为旷达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如何的呻吟”。当她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去爱梓青时,她依旧深信精神上的爱高于一切。可悲的是,在理性大旗高扬的“五四”时代里,在父亲的大门对庐隐的露沙们关闭之后,困境中徘徊的女儿们是否该义无反顾或者说只能做一道对于她们来说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踏进婚姻的大门,或者,回到父亲的家。一向理智强于感情的云青,在面对爱情的来势汹涌时,竟也果敢反抗父母的包办,令爱人蔚然托人提亲。然而当面对父亲的否定和拒绝时,却也在情智不谐的矛盾中委屈妥协,宁可“自苦一辈子”却也不能很好地调和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冲突。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意会到,在庐隐的笔下,理智成了父亲们约束女儿们的强有力的武器,“于是乎理智便成了某种意义上对父母意愿自觉的顺从(或对某种社会规范的自觉遵守)”。这种顺从显然是以牺牲女儿们的意志和自由为代价的,它压抑了女性内在的情感需求和欲望,最终导致了女儿们情与理的冲突,使她们徘徊于父亲的大门与婚姻大门之间,在狭窄的缝隙里,将她们引向万劫不复的文化死结和历史深渊。
三、爱情世界的悲叹者
(一)摒弃爱情
父亲的大门关上后,女儿们猛然发现她们曾为之不惜生命也要得到的爱情,在此时此刻也成了要圈住她们的围城和囚笼。一旦触动那座围城的大门,婚姻的囚笼之锁将为她们紧紧锁闭。露沙们在即将跨入婚姻的那天“似醉非醉,似哭非哭的道:‘宗莹!从此大事定了!’”;本来活泼近来却憔悴的雯薇,在跨入婚姻后只感到劳碌、烦躁,甚至连女儿的出世都成了捆住她人生的柔韧的彩线,厌烦,却无法解脱:“雯薇结婚已经三年了,在人们的观察,谁都觉得她很幸福,想不到她内心原藏着深刻的悲哀”;已为人妻和人母的沙侣在侍候丈夫、照看孩子、整理家务的琐碎的事情中消磨着原本昂扬向上的人生,“但仍不时地徘徊歧路,悄问何处是归程”。
(二)挣扎着的矛盾体
在爱情世界里挣扎着的悲观的女儿们放弃了进入仍存在压迫和强权的男性世界的选择。至此,婚姻的大门也对女儿们关闭了,留下了那声沉重的闷响在历史的上空来回飘荡。曾经贵为天之骄女的女儿们在这一刻成了“父亲的大门”和“婚姻的大门”这道狭窄的空间内的孤魂,游走在凄冷的人世间,看不到转世的希望。
女儿们再次回到挣扎悲叹的状态。悲观绝望的亚侠选择了“游戏人间”,用一种近似自虐的方式去完成对男性世界的施虐行为,只是这“游戏人间”的结果仍然摆脱不了“被人间游戏了我”的悲凉意味。继续在爱情世界里苦苦挣扎着的亚侠们、丽石们、松文们、兰田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死”,只是死亡的背后,消失了的只是女儿们的无辜宝贵的生命,缠绕她们的矛盾与欲望却不会死,“这是‘五四’意识形态的一个魔障,是女性的历史与文化的一个死结,死亡也莫奈何于它。”
结语
女儿们在“五四”新思潮的感化和召唤下瞬间觉醒,却又在觉醒后深陷情智不谐的历史文化困境,在追问人生究竟的漫长之路上挣扎与悲叹!她们放弃了跨进男权世界的污浊,决心经营自己纯洁的女儿国,然而却始终得不到世人的认可,于是只能在爱情世界里挣扎与悲叹。妇女解放道路的任重而道远,被二十世纪初的女作家们揭示。于是,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先驱们用自己的笔为这个文学命题书写故事,寻求答案,文学史上也留下了她们浓墨重彩的一笔。幸运的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善良勇敢、独立聪慧,拼搏上进,时代的进步让她们接收到了更多的知识和思想,同时也带领她们走出了困惑和迷茫,即使遭受到了命运的不公正对待,她们也可以不用再像从前那样陷入挣扎和孤立无援的困境。更令人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男性作家也开始关注女性书写,他们用平等的姿态介入到女性题材的创作中来,用深刻的故事或细致的情节来建构起关于女性主体的觉醒之路,女性主体的生命情感体验在他们的作品中得以展现。物质的发展为女性解放的道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新的时代为我们对“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的担忧作出了解答:经济独立的女性群体在新时代的社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她们可以与男性一样平等且自由地在社会中工作、生活、实现人生价值;而一百年前作家们揭示出的女性主体的精神独立,便理所当然成了新时代作家们亟待关注和解答的命题。五四启蒙为我们打开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大门,剩下的道路正是在这个神话不断破灭、梦想不再美好的痛苦的过程中越走越宽,女性意识也会在不断地内省和反思中被更多的作家看见和书写,从而在更多的人心中生根发芽。我想这正是女性书写之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
注释:
①庐隐.海滨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第97页.②庐隐.海滨故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第160页.
③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41页.
④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