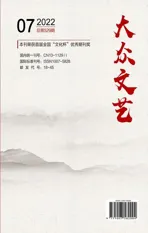刺绣的锦心
——论《天香》中女性日常的“抒情”
2022-04-26陈璐
陈 璐
(国立成功大学,台南 701401)
一、前言
王安忆于2011年又推出长篇大作《天香》。小说以晚明到清初的上海为背景,围绕富绅申家四代人的婚嫁丧娶、情缘纠葛写开。申府男性秉性趣向迥异而不慕传统士大夫功业,投身造园、制墨、四时节庆及应景的意境布置,从俗世中获得雅趣,也于园林建筑、书画弦乐、美食饰品等“物”中寻得自然物理人情,体悟人生。申家女性多兰心蕙质、坚韧重情,她们通过刺绣表情达意,安顿自我,应对变故乃至持家谋生。三代女性的锦心慧手、传承创新创造了物用、文华兼具的天香园绣。申家在精致奢靡用度中走向没落,申家女性的刺绣却于此环境中发展到顶峰,并在民间开枝散叶,显出另一派生机。
起源于诗经楚辞的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精神,在陈世骧、高友工及晚近学者的探究、建构下,别于西方史诗传统的“抒情传统”存在日渐清晰。在高的“抒情美典”构设下,文学史、传统诗学、本体论等研究视角日益丰富,展现了强大的诠释力,各式抒情文学美典的建构潜在着丰富的文学审美、批评资源。“抒情美典是以自我现时的经验为创作品的本体或内容。因此它的目的是保存此一经验。而保存的方法是‘内化’(internalization)与‘象意’(symbolization)”。高友工在《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中强调了创作者内化、内省生命经验的过程,是经过“知性解释”的“感性过程”。能纯粹、完整地传递自我彼时真切的体悟、意志,正是中国抒情传统中美学典范的特质,“抒情的本质也即是个人生命的本质”。
抒情是王安忆小说惯有的美学特质,尤其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沉淀出恬淡、温和的抒情风格。这与王注重心灵世界创作的理念紧系:“小说绝对是由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他自己创造的,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由于知识分子启蒙式的责任感与悲悯意识、深切的人文关怀,王安忆的小说叙述具有其思想、精神底蕴。此外,女性对生命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人世情感的体悟及深厚的语言功底等因素也促成其创作的抒情特质。顾绣史上大家女红沽价鬻市的逾矩触发了王安忆此创作,其中隐含了探寻彼时女性生存空间的可能,并由性别牵连起历史、地域文化等多重向度。尽管王安忆在《天香》中节制、冷静地记叙了大量的史料、物质文化知识,叙述主体的抒情视角依旧有迹可循,书写围绕刺绣活动的女性日常更以多样的抒情笔法传神地呈递女性的生命经验,书写出一部有情的刺绣史。
二、《天香》:晚明上海历史的“抒情”
在章节开篇,作者多以洗练、具有文言韵致的白话记叙时年、月的朝廷、上海要事。在具体历史时间标注下,接续在冰冷史实后是蕴藉抒情的风土人情,令概括性的军政大事退成远景,浓烈的情景氛围也淡化了推进的时间感。
在第一卷《造园》(《桃林》)中,开篇“嘉靖三十八年”上海造园风潮后,落笔在莺飞草长映衬下蓬勃的江南士风,前后呼应、两相烘托。在《疏浚》中,着笔隆庆开春应天巡抚海瑞组织疏浚吴淞江,细述人们对巡抚身量形貌上的猜测,止笔于万舸云集、集市繁荣的氛围。第二卷《绣画》(《武陵绣史》)中,作者插叙了三月里上海遍传白鹿的吉兆,随后工笔描摹了佛诞日寺庙敲钟燃烛、桥岸边牛马嘶鸣、鱼虾跳跃的欢腾。第三卷《设幔》(《遍地莲花》)以“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立国与朝廷调兵遣将开篇,聚焦将领之一乔公子在腹背受敌情况下仍英勇战斗,轻笔捕捉“回顾”“遥望”“拜三拜”等动作及“吾不负天子!”再现其跳崖尽忠场景,坐骑“步后尘腾空一跃”的视觉意象更添壮烈悲情。随后,细述地方人们热烈反响,万众一心修忠义祠,以“桅船林立”“人潮如涌”“诵经声遍地起”等丰富的视听形成的隆重哀悼氛围作结。
小说章节开篇往往始于新政颁布、筑城抗倭、疏浚等大事,开辟出宏大的气象,然后延展到细腻、有声有色的生活场景,大气、深邃且富有实感,叙事与抒情笔法相得益彰。叙述视点由宏达凝重的历史大事跳转到气韵生动的地方日常,王安忆对历史转折激荡或仅有波及日常生活的余韵颇为倾心,聚焦、放大上海市井风貌、市民生活肌理,欣赏之情蕴藏在绘制声色光影的“工笔”中。根据《辞源》的介绍,“皴”是国画绘法之一,指先勾勒出山石树木的轮廓,再以诸种侧笔层层叠叠地或勾勒或渲染出纹理脉络。王对皴法有叙事美学认识与实践。在《天香》中,王安忆多用“皴”笔加层抒情,使地方风情图徐徐展开。小说由捐桥之举敷衍开,作者从造桥方位、坐落河流到桥名、样式、祝语等多层次、多角度勾勒出水上众桥林立的立体图景。“先是南边”“再是西边”“接着,城里也开始了”,顺序短语与方位词搭配,带来叙述视点紧凑地移动,凸显造桥之速及地方城建日新月异的动态景观。聚焦桥状貌,不断增生、衍化的平整句,写极桥之繁盛。而明快平缓的节奏迭合叙述声音,如“听听”“等等,等等”及拟人的情状,透露出叙述主体“内化”的美感经验及内敛欣喜。细腻密实的皴笔烘托出上海水上建筑蔚然大观、日新月异、焕发生机的气象,传递出务实而仁义、乐善好施的民风。结语是叙述者积蓄而发的感言,应和着皴笔,是缘物抒情,礼赞了“轰轰烈烈”的城市气象。
三、《天香》:女性日常的“抒情”
王安忆推崇个人性、切实的日常生活,她强调“从冗长的日复一日的生计中,提炼出的精华,在它的日常面貌下,有着特殊的精神,于是,这‘家常’才成为审美的对象”。《天香》中,女性的日常实践活动围绕着两性与其他家庭人际关系开展,少去精致美学、士道文化的附着,也不拘于物质性、生物性的生存,指向日常生命经验中的个人性与主体意识,构成仁义、坚韧的女性世界。
(一)“繁”笔中的物与情
作者多用繁笔写制物活动,一道又道工序,在舒缓节奏中酝酿人物的情感,剖露内心。
在制作糨糊时,小绸与丈夫两人“一送一递地筛起来”。人与物逐步合拍,“额上都出一层薄汗,一罗面也筛完了”,聚焦移物,也包含人物内心视点。“先是罩在水上,然后慢慢沉,沉,沉下去,停住。”原来心有龃龉的两人,情绪也与物一般沉淀、平静,暗示言和。
小绸与镇海媳妇两人同行同止,叙述视点合二为一,制桃酱“剥皮去核、上笼蒸熟、和上饴糖……”复杂工序娓娓道来,饱含二人的精心、轻松心境与默契,亲密关系与深厚情谊含蓄传递。
(二)“轻”笔中的人事变故
作者记叙女性日常生活状态,情变、难产、夫亡、家变等变故轮番出现,受挫女性的生命经验是重要表现内容,循环往复,表现为封建宗法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境况。
婚姻无疑是封建宗法社会中女子最重大的事,紧系着她们的命运、生存,也是其生命价值的核心。由婚姻延展出的波澜牵动女子的心,《天香》中的女性情感跌宕、心绪流转多有浓缩于视觉意象的“轻”笔中,内蓄的情感力量、生命信息感染、召唤着读者。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出“轻”的美学概念与价值,阐释了“轻”的不同面向:“有通过削弱语文结构表达意义的语言轻巧,有借助思绪或高度抽象的心理叙述之轻,有寄托象征意义在‘轻盈’的视觉意象的轻”。本节借“轻盈”的视觉意象来探究女性遭际叙事中的抒情。小绸与柯海的少年夫妻情谊在前文虽有铺叙,然由柯海远游到归家中小绸一系列的心理变化即达到酝酿效果。
“满屋子的绫罗帐幔,都写着柯海给起的字:绸!小绸念着自己的字,忽觉出一丝不祥,这‘绸’可不是那‘愁’?雪打在窗户上,沙沙地响,响的都是‘愁’字”。
主观意志“内化”了外界,所见所闻都浸润了心绪,化时间幅度为空间幅度,深切地传递小绸的期盼、忧思、焦虑、不安。
“重新挂好帐幔,展平铺盖,柯海的大枕头,换上丫头的小枕头。……小绸着人将饭菜用攒盒送到屋里来,正喂丫头吃饭。柯海张了几下口没说出话,眼泪却下来了”。
小绸前文曲折的心理活动描摹累积起厚重的情感力量突然收笔于“轻盈”的视觉意象,越发叩击人心。看似平静的整理床铺动作、轻松的喂饭动作背后是小绸心底的波涛汹涌。包举复杂的情感内涵之日常举动,举重若轻,让读者深入、强烈地体味到她强行压抑的情感冲突,领会她当下失望、悲伤、怨恨等复杂心绪。
柯海临时起意将闵纳进门,不想破坏了与小绸的感情,便也无心于闵,常出门远行,留闵一人独守空房。他待闵没有心灵、思想的交流,对闵而言唯有“凉凉的”感知。闵嗅着丈夫的气味,努力重温仅有的感知联系,想象他的存在。闵思君、孤单等隐秘心理经过提炼包藏在下意识的“嗅”动作中,在重复中渲染闵的悲凉处境。
戥子原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因遭家变而成为申府的使唤丫头,然后被蕙兰要来张家帮忙绣活。比起在大户人家帮佣,戥子更亲近寻常人家,喜欢针线里的日常生活。小说叙述了某日她带张家孙子灯奴出门闲逛时路过从前住家旧址,一系列紧凑连续的动作捕捉,反映着戥子的情感波动、心绪起伏。“转过”“经过”“跑一段”“扑开门”等表现了戥子的急切、激动,她目睹了落败的场景后,“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弯腰”,“哭了”,反应剧烈。事情经过主要通过动作记叙,淡笔写来,浓缩了戥子复杂的情感,构成“轻”笔,引人体味家庭变故对她的重创。年幼无知的灯奴的一系列动作与之形成对照,天真无邪与经历人事变故的年轻生命并置,更显天地不仁,而两人相互安慰则流露了作者的悲悯。经历激烈的家变创伤反应,最后擦擦眼泪是告别过去、直面现实的坚韧,呈现一份生命的轻盈。
王安忆笔触纳妾、守空房等封建宗法社会中女性一般的生命经验,也涉及如难产、家变等威胁女性生存的代表性题材,寄寓了她对彼时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怀与悲悯。此份情结合“轻”笔触碰女性日常生活中潜在的幽微心理,将无限的心底波澜浓缩于视觉意象/动作之淡笔上,传神地表现“当下此刻的心境”,发人体味与深思。
四、《天香》:刺绣的锦心
作者的有情表征在《天香》的抒情视野中,将申府女性们的生命创伤经验转化为刺绣的锦心,使她们由刺绣活动联结、发展成一个可以抵御天命、封建宗法文化压制的自足女性空间。
(一)“物我交融”抒情中的女性的主体性
申府女性们藉刺绣表情达意,安放自我,应对日常挫折,俨然形成一个主体性昂扬的女性空间。“园子里的声息都偃止了,野鸭群夹着鸳鸯回巢睡了,只这绣阁醒着,那窗户格子,就像是泪眼,盈而不泻。一长串西施牡丹停在寿衣的前襟,从脚面升到颈项,就在阖棺的一霎,一并吐蕊开花,芬芳弥漫”。镇海媳妇与小绸是患难之交,有堪比夫妻的深厚情谊,而镇海媳妇对闵有解围之恩。她因生产而体弱病逝,小绸与闵为她没日没夜地赶织绣寿衣。所绣的花样是雍容典雅、绚丽生姿的西施牡丹,寄寓了“当归”的深切哀思。浸透了创作主体的强烈意志,绣品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物我交融,主体间际会,栩栩如生,表呈良愿。蕙兰丧夫后,把对丈夫的情谊、怀念倾注到素色佛绣上。她也曾担心成为寡妇后空虚的存在感,幸而她以刺绣表情、守志延续原来的情感寄托,在物我相容中,感知物的生成替换流逝的时间感,保持充实的主体感。
《天香》中,刺绣不仅是申府女性展现才思、张扬主体性的方式,也是底层女性谋生的手段。在作者的抒情视野下,刺绣是彼时女性应对坎坷人生的生存方式,是一种积极的生存姿态,为逼仄空间下生存的女性开拓出新的生命图景。
(二)仁义与坚韧的锦心
天香园绣由织工技师女儿闵开创,在小绸的诗书底蕴下得到发展,然后由才华卓绝的沈希昭带入画意推上艺术顶峰,再由慧手慧心的蕙兰推广到民间,在戥子、乖女手上勃发生机。刺绣者的生命创伤经验与精神气质濡染着绣品,与绣品质量紧密相关。在夫亡家败时,蕙兰绞发明志,誓与婆婆相扶持。那承载了仁义与坚韧的短发,成就了蕙兰不凡的髪绣,“轻盈盈,又沉甸甸,凉凉又暖暖,分明是个物件,却又连着骨血!”镇海媳妇与小绸相互依偎、生死不渝的情谊铸就了绝品刺绣。戥子、乖女在底层挣扎求存的顽强为高格而式微的刺绣注入活力,一起创出“字字如莲,莲开遍地”的绣字。
王安忆推崇作品彰显人性诗意,“我对自己只是有标准,是一个审美的标准,我告诉自己:是一些关于高尚、美好、你应该提炼人性中的诗意。作家应该有一个审美的标高,纯洁的观念,不是以责任来命名”。她塑造理想化的刺绣者,凸显她们仁义与坚韧的质量,经过提纯、简化的创造主体精神成为刺绣的锦心,方才撑起天香园中抒情的女性空间。
结语
王安忆结合大历史叙事与日常抒情笔法呈现《天香》的历史社会环境。在聚焦上海地方风貌时,作者擅借“皴”笔抒情,渲染生机勃勃、民风热情的气象,为女性自足空间的生成创造可能。在女性日常生活叙事中,作者倾向用“繁”笔描摹人物间进行的物质性活动而悬置活动中人物的感情,含而不露引人沉思。作者倾向用“轻”笔承载沉重的女性挫折经历,或以“轻盈”的视觉意象浓缩幽微波折的女性心理,或捕捉女性动作淡笔写来,意味深长而愈发感人。抒情主体的意志还表现在将女性挫折经验转为刺绣的锦心,支撑她们围绕刺绣形成了自足的女性空间。在物我交融的抒情笔法中,女性的主体性得到彰显,而在理想化塑形中,人性的仁义与坚韧得到渲染,共铸锦绣辉煌。女性日常在抒情视野下展现诗性,王安忆寄寓其中的悲悯与期许紧系刺绣的锦心。在王安忆交用的“繁”(“皴”)笔、“轻”(“淡”)笔抒情中,《天香》延续了90年中后期以来含蓄、温和的抒情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