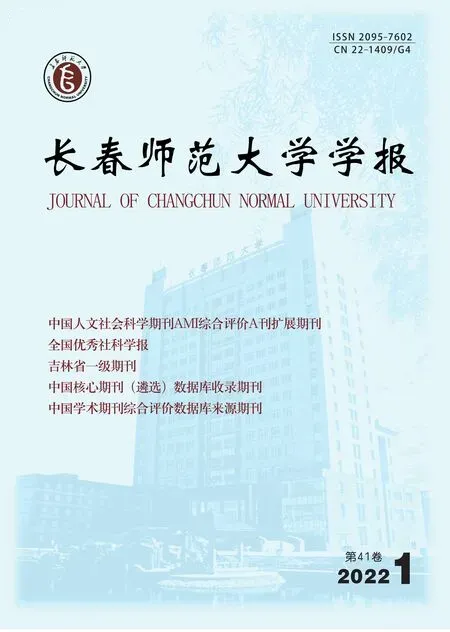谢榛《四溟诗话》“气格”论
2022-03-18樊荣
樊 荣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在谢榛《四溟诗话》中,“气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评价概念。“诗文以气格为主,繁简勿论。或以用字简约为古,未达权变。善用助语字,若孔鸾之尾,不可少也。太白深得此法。”[1]1138对谢榛《四溟诗话》“气格”的论述尚显薄弱,有必要深入探讨。
一、“气格”说形成的文化背景
“气格”有“气”与“格”之别。在《四溟诗话》里,对诗歌创作“气格”的提倡,重在合理使用“神气”与对“声调”的分析上。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所说的“气格”,是指诗文的整体贯通之“气”和整体艺术风貌之“格”,是深得诗歌创作三味后的经验教训之谈,与前人所说的“诗法”“诗格”具有内涵的区别。《四溟诗话》卷一曰:“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唐人诗法六格,宋人广为十三。作者泥此,何以成一代诗豪邪?”[1]1149谢榛此说,并不拘泥于诗格局限。
“气”有自然之气和人伦之气之分。道家偏重自然之气,儒家偏重人伦之气。老子《道德经》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论述,视气为万物的本原所在。 《淮南子·本经训》中的“天地和合,阴阳陶化,万物皆乘一气也”,揭示了宇宙变化及运作的漫长过程。
《论语·季氏篇》在谈到“气”时,提倡的是人应具有“中和之气”。孟子发展了儒家学说,把“浩然之气”作为人品修养的崇高境界,重视主观精神对道德修养的重要影响。孟子的“浩然之气”更为重视主观意识和内在气质的培养,崇尚豪放之气,是对儒家中和审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融自然之气与人伦之气为一体,开启了曹魏时期曹丕《典论·论文》 重视创作主体意识、重视作者精神气势的先声。
由于唐宋时期的诗歌作品,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创作经验和教训,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已不斤斤计较于诗格的“体”“式”“势”等概念的理论建构,而是在“神气”和“声调”上重视学习唐诗气势雄浑的成功创作经验,总结宋诗忽视神、气的创作教训,以便对诗歌写作予以理性的指导和矫正。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三”《谢榛传》曰;“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各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盛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合力摈榛,其称诗指要,实自榛发也。”[2]7376首先,谢榛提倡写诗时重视神气、声调,是其“气格”说的核心内容。谢榛崇尚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崇尚对诗歌创作神韵的追求。重视声调、韵律,源自我国诗学具和乐功能的优良传统。元代音乐文学的蓬勃发展、明代民间文学的兴起促进了歌诗文学的繁荣。其次,谢榛年少成名,得益于“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的创作经历。万历元年冬季, 《竹枝词》和按而谱之的“新词十四阙”,均为乐府诗歌。最后,南宋郑樵尊崇《诗经》,把“声”作为诗的核心内容进行研究。他认为,情为诗之本,声为诗之用。“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诗者,乐章也。”[3]883,887这种诗乐合一的审美诉求,是对宋代以来在理趣背景下对诗乐分离的有意矫正。
二、“气格”说的思想基础
《四溟诗话》所倡导的“气格”,具有引导当时文坛创作风气的重要意义,体现了谢榛儒道兼宗的思想基础。“气格”指在最求性情高古的前提下诗歌应有的神气和声韵。在创作诗歌时,“气格”以崇尚性情高古、格韵简古、骨象奇古为审美标准,以高其格调、充其气魄、变俗为雅、易浅为深、句平意远为诗歌正宗。这些观点是对当时文坛轻视乐府诗歌创作倾向的明确表态,也是诗人经过长期诗歌创作后的智慧结晶。《四溟诗话》卷一曰:“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虽其逸诗,汉人尚不可及。”[1]1149《诗三百》抒写内容高雅古朴,声情并茂,无鄙俚浅陋之失,是先秦歌诗的典范之作。
《四溟诗话》卷四曰:“予以奇古为骨,平和为体,兼以初唐胜唐诸家,合而为一,高其格调,充其气魄,则不失正宗矣。若蜜蜂历采百花,自成一种佳味与芳馨,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蕴。”[1]1217《四溟诗话》推崇性情高古的《诗经》、气象浑厚的汉魏古诗和翻新出奇、音律铿锵的盛唐律诗,以其高古的格调、浑厚的气魄、含蓄的风味和丰富的底蕴为诗歌正宗,为解决明代中后期诗歌创作的雅俗之争提供了深受朝野欢迎的理论指导。
儒家思想以“和”为本,以“古”“正”为雅;道家思想以“清”为本,以“奇”“逸”为雅。两家虽见解不同,却均具文化贵族心理。明代中后期,文坛出现了淡化雅俗对立、否定贵雅贱俗的倾向。《四溟诗话》卷四曰:“自我作古,不求根据,过于生涩,则为杜撰矣。”[1]1137追求诗风古朴,不应以语词生涩、难以猝读为“作古”代价,而应该寻求内容高古、气象浑融和语言流畅的完美统一,以利于科学处理雅与俗的辩证关系。同时,也不应该语词过于直白,影响诗歌整体的性情抒发起点。如“杜牧之《清明诗》曰:‘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作宛然入画,但气格不高。”[1]1152这就涉及谢榛论诗,并非把通俗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尽力谋求俗中有雅的韵致,以高其格调、充其气魄、变俗为雅为评判标准的结果。“气格”是《四溟诗话》追求的精神灵魂。如何避免片面地顺从世俗,也是在写作诗歌时应该注意的客观问题。
三、“气格”说中的“神气”
“神气”即一首诗歌的神情、神态、精神、气韵、气魄和神妙之气。诗人必先“养气”,才能写出有“神气”的诗歌作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代诗人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把读书作为“下笔有神”的必要前提。谢榛亦深刻地认识到“熟读之以会神气”的重要性。“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蕴乎内,著乎外,其隐见异同,人莫之辨也。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惠春兰,奇绝如琼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学者能集众长合而为一,若易牙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矣。”[1]1180“气”有“清”“浊”之分,性情不用,气质不同,则诗歌风格不同,气势有别。谢榛所养之“气”,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是精神内蕴的外在表现。
所谓“神气”,即能集众长于一身,针对不同的主题抒写出神气盎然的作品。《四溟诗话》的“养气”之说,明显受到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雄浑、高古、绮丽、典雅、劲健、清奇、飘逸、旷达等诗歌品评标准的影响,突出了诗歌创作时应该具备的阳刚之气,为“神气”说的内涵、外延作了客观的界定。
《四溟诗话》卷二曰:‘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以‘气韵’论诗,称:‘文章以气韵为主,虽有辞藻,要非佳作也。’‘气韵’,亦即书中所谓陶渊明之‘天成’、李白之‘神气’、杜甫之‘意度’、韩愈之‘风韵’、苏轼之‘海上风涛之气’,要皆诗人‘逸思妙想所寓’,而‘非绳墨度数所能束缚’,并须‘题外立意’,含蓄隽永。”[1]1155陈善论诗,偏于创作主体审美意识之探讨,偏爱“格高”“韵胜”之“古人旨趣”,出尘绝俗,以“自然”标准评诗,以意境取胜,在探讨艺术规律上多有所得。谢榛崇尚含蓄隽永风格,欣赏具有“题外立意”、耐人回味的构思,对陈善过于强调创作主体审美认识予以拨正,同时还要注意对“大海奔涛”“孤峰峭壁”“层楼叠阁”等审美客体对象充分重视,才能写出其神韵逸气。优秀的具有“气格”的诗歌,应该具有令人精神振奋,甚至血脉喷张的艺术效果。“诗无神气,犹绘日月而无光彩。学李杜者,勿执于字句之间,当率意熟读,久而得之。此提魂摄魄之法也。”[1]1164有神气的诗歌,往往气势雄浑,胸怀博大,内容充实,如日月之光照大地,具有可感而不可言喻之艺术魅力,具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迈气魄。假如忽视对诗歌神韵的追求,忽视对意境的观照,不仅达不到预想效果,还会适得其反。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诗人应重视自身品质的修养,具有优良的品德。欲写出有“气格”、有“神气”的诗歌,诗人须充实自己,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借助诗歌展现个人魅力,展示个人“气象”。《四溟诗话》卷四曰:“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敢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古人制作,各有奇处,观者自当甄别。”[1]1211因此,多读经典,充实人生,是写作诗歌的必备前提。欲在写诗时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须在“德”“才”上多下功夫。“德”犹人生之舵,实乃立身之要。“人非雨露,而自泽者,德也;人非金石,而自泽者,名也。心非源泉,而流不竭者,才也;心非鉴光,而照无偏者,神也。非德无以养其心,非才无以充其气。心犹舸也,德犹舵也。鸣世之具,惟舸载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1]1190在“德”与“才”之间,应该德才兼备,重视提高道德品质修养。
谢榛“每惜弥衡《鹦鹉》一赋,而遽戕平生,可为恃才傲物者戒。”[1]1190东汉弥衡才能卓绝,具有“奇姿”“殊智”,自以为被“闭以雕笼,剪其翅羽”,过的是“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的不自由生活,终因性格刚直高傲、恃才傲物而招致杀身之祸。西晋陆机殷切盼望重振门庭威望,渴望光宗耀祖,恃才而骄;南朝刘宋时期谢灵运自以为“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既有孤芳自赏的情调、政治失意的牢骚,又有进退不得的苦闷、对政敌含而不露的怨愤,自负清高,露才骄人,德不盛才,犹若泛舟中流,舵失其主,终至船翻人亡。陆机尽管文章冠世,有“太康之英”的名望,最终遭谗遇害,被夷三族。谢灵运任性妄为,大兴土木,放荡不羁,侵扰百姓,仅四十九岁即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在广州杀害。
四、“气格”说中的“声调”
“歌咏之以求声调”,是谢榛《四溟诗话》“气格”说的另一重要内容。其诗学中的“声调”,主要涉及诗歌与音律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谢榛在其诗歌创作过程中身体力行,并贯穿始终。其十六岁时所作乐府商调,流传颇广,后刻意创作歌诗,以律句绝句见长,功力深厚,重视择韵调韵,句响字稳,以声律成就而闻名于当时。谢榛对“声调”的追求有着严格的标准,大致可分为声调与虚实之用、声调与结构安排、声调与择韵三类。
谢榛重视在诗歌创作时虚实字的合理运用。“律诗重在对偶,妙在虚实。子美多用实字,高适多用虚字,惟虚字极难,不善学者失之。实字多者意简而句健,虚字多者意繁而句弱。”[1]1147如《榆河晓发》中的颔联、颈联“朝晖开众山,遥见居庸关。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外”“间”既对偶工稳,又妙在虚实之间,能把虚字用到意简句健的美学效果,可见谢榛对语言、声调的把握之功。“写景述事,宜实而不泥于实。有实用而害于诗者,有虚用而无害于诗者,此诗之权衡也。”[1]1149谢榛《晚眺》诗:“寒日下西陵,漳河晚渡冰。孤城归猎骑,双树隐禅灯。野眺心何远,岩栖老未能。翻怜戎马日,愁思坐相仍。”写景叙事用典而不觉用典,似实景而可引发无限遐思,实中有虚,虚中蕴实,虚实交相辉映,使韵律与诗情画意揉为一体,堪为五言写景抒情杰作。
声调与结构安排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可以使充沛的感性认识具有理性的冷静思考特征。“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1]1154,1162如咏物诗《绣球花》:“高枝带雨压雕栏,一蒂千花白玉团。”起句响亮,意境清澈,骤然爆响,毫不拖泥带水。《秋日怀弟》结句“秋天落木愁多少,夜雨残灯梦有无。遥想故园挥涕泪,况闻寒雁下江湖。”“秋天落木”“夜雨残灯”“故园悠远”“寒雁悲鸣”,意境萧瑟,情感幽怨,言已尽而余味无穷,达到了情趣、音调与意境的完美结合。
声调与音韵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声调要妥帖和平,必须重视诗歌音韵的和谐。“凡作近体,诵要好,听要好,观要好,讲要好。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此诗家四关。使一关未通,则非佳句矣。”“行云流水”“金声玉振”“明霞散绮”“独茧抽丝”四关,是诗歌音韵通畅的重要条件,也是对南齐谢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创作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谢榛推崇先秦两汉盛唐文风,对唐诗的浑融气势、浑成无迹、高古气格尤为推重。“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大历以下,稍有旁出者。作者当以盛唐为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加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也。”“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可以协丝簧,谐音节。晚唐格卑,声调犹在。”[1]1138,1143,1146
然而,假如认为谢榛无选择地推崇盛唐诗歌,则也未必绝对如此。在谈到对偶、用韵或用字时,他有着严格的取舍保准。如评价杜甫的排律结句,称其“排律结句,不宜对偶。若杜子美‘江湖多白鸟,江湖有青蝇’,似无归宿。”谈用韵:“凡作诗以‘青’字为韵,鲜有佳者。”谈用字:“诗中罕用‘血’字,用则流于粗恶。”“凡诗用‘恩’字,不粗则俗,难于造句。”因此,谢榛认为,“诗易择韵。若秋、舟,平易之类,作家自然出奇。若眸、瓯粗俗之类,讽诵而无音响;若锼、搜之类,意在使人难押。”[1]1172,1204,1212,1140理性分析有助于在以后的诗歌创作过程中,绕过暗礁,回避失误,出现影响“气格”,有损“神气”或“声调”效果的败笔。这是谢榛诗歌创作的教训之谈。没有过苦心孤诣的诗歌创作,不经历一番诗歌创作的艰辛历程,是得不出如此独具只眼的观点的。
五、结语
《四溟诗话》所倡导的“气格”,以“神气”和“声调”为主要内涵,即优秀的诗歌应该意蕴耐人回味,气势高古雄浑,神韵动人心魄,内涵充实高雅,同时应在阅读时朗朗上口,音韵铿锵悦耳,既具有通俗文学的易读性、可接受性,又具有高雅文学的华贵典重风格。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符合当时审美情趣的诗歌,才是谢榛心目中的理想诗歌标准。
当然,由于时代、个性的局限,后七子之间观点认识不一也属正常现象。谢榛在性格和诗歌创作上也并非完人。但是,如李攀龙之《戏为绝交谢茂秦书》:“二三兄弟爱才久矣,岂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以从其淫,而散离昵好,弃天地之性?”其明目张胆地以谢榛的生理缺陷而发难,心胸狭隘,则有失君子之风。王世贞《艺苑卮言》在评价谢榛诗歌创作时较为客观,认为“其排比声调,为一时之最,第兴寄小薄,变化差少。仆尝谓其七言不如五言,绝句不如律,古体不如绝句。”在谈到其拟李杜长歌时,王氏却显示出对谢榛要求苛刻的另一面。“谢茂秦年来益老悖,尝寄示拟李杜长歌,丑俗稚鈍,一字不通,而自为序,髙自称许,其略云:‘客居禅宇,假佛书以开悟。暨观太白少陵长篇,气充格胜,然飘逸沉郁不同,遂合之为一,入乎浑沦,各塑其像,神存两妙,此亦摄精夺魄之法也。’此等语何不以溺自照。”[1]1063,1066这类评价语言,有失大家风范。诚然,谢榛像其他人一样,有时自傲,有时自馁,但是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官僚,如明代“后七子”中的李攀龙、王世贞,调侃谢榛曳裾王门之状,侮辱其生理缺陷为“一眇君子”,痛斥其“老悖”“何不以溺自照”,就已经远不属于诗歌批评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