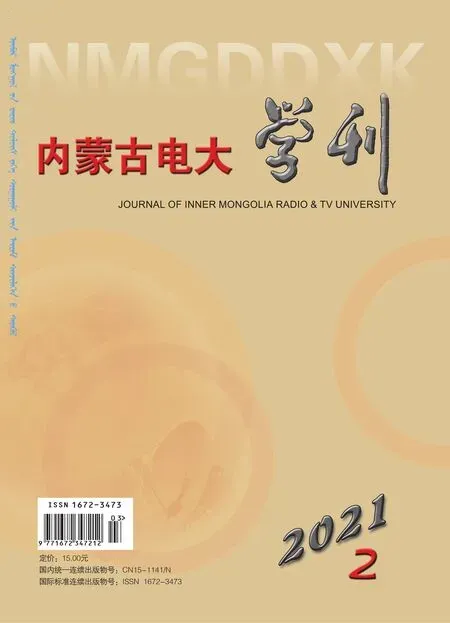《四库提要辨证》纠误四库馆臣证补
——以《唐子西集》提要辨证为例
2021-12-31袁一舒
袁一舒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余嘉锡(1884-1955)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抱着“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1]的态度,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提要进行了作者生平、版本源流、内容真伪、议论是非等多个方面的考察辨证,建立在广泛取材和细心考校上做出的辨证,让后学对《总目》中四库馆臣出现的失误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本文将从余先生对《总目》中《唐子西集》提要的辨证入手,整理馆臣编写提要时出现的知识性错误和观念性错误,并进一步考证和补充,再对馆臣看待唐庚偏见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究。
一、唐庚及其著述概况
唐庚(1071-1121),字子西,眉州(今四川眉山)丹棱人,宋绍圣元年(1094年)进士。大观四年(1110年)蔡京倒台后,唐庚作《内前行》,刚刚拜相的张商英欣赏他的才华,推荐他任提举京畿常平。张商英被罢相后,唐庚也受到牵连,被贬惠州。政和五年(1115年)遇赦,复官承议郎,后提举上清太平宫。[2]因与苏轼同为眉州人,又都曾被贬惠州,兼之文采风流出众,在当时便有人称其“小东坡”。宣和三年(1121年)唐庚归蜀,道病卒,年五十一。
唐庚卒后次年,其弟唐庾将他的遗文编纂为集,但卷数不详,今已亡佚。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惠州州学主管郑康佐收集整理了当时流传的唐庚作品,编刻为诗文集三十卷。唐玲的博士论文《唐庚诗集校注》中考察了今存的唐庚诗文集刻本,除四库本《眉山集》二十二卷外,还有宋绍兴饶州刊本二十卷、明嘉靖任佃刻《唐先生集》七卷、明万历潘是仁辑刻《唐眉山诗集》七卷、清雍正汪亮采南陔草堂活字印本《唐眉山集》二十四卷。与唐庚同时的强行父,著其论诗文之语录为《唐子西文录》。此外,唐庚还著有《三国杂事》二卷,颇具史才。
《唐子西集》提要称该集“诗十卷、文十二卷。文末缀以《三国杂事》二卷,共二十四卷”[3]。经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唐子西集》二十四卷仅存名目与提要,集中诗文见《四库全书总目》第1124册《眉山集》二十二卷,另有提要一篇;《三国杂事》见《总目》第686册。
二、提要舛误的两大类型及辨证
馆臣编写提要时出现的舛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知识性错误,一类是由主观偏见导致的观念性错误。
为便于叙述和理解,下文将先引《唐子西集》提要原文,再引《四库提要辨证》中对该篇提要进行辨证的原文,最后进行相关考证和补充。
(一)知识性错误
1.“《读书志》《书录解题》均载《唐子西集》二十卷。《宋史》庚本传亦同,《文献通考》则作十卷。”[3]
余先生订:“《郡斋读书志》著录《唐子西集》实只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始作二十卷……《通考·经籍考》之例,虽晁、陈并引,但于卷数不同者,多从晁不从陈,而此书乃作十五卷,疑衍一‘五’字……《宋史·艺文志》有《唐庚集》二十二卷。”[1]
余先生认为《文献通考·经籍考》在遇到《读书志》和《书录解题》著录书籍卷数不同的情况时多采用晁公武的说法,因此《经籍考》中《唐子西集》卷数应为十卷;经查,《经籍考》著录《唐子西集》实为十五卷,而非十卷。此外,《宋史·艺文志》还收录有唐庚别集三卷。
2.“惟绍兴二十一年郑康佐序,乃称初于鹅城得文四十五首、诗赋一百八十五首。”[3]
余先生订:“郑康佐跋云‘政和中,先君寺丞赴官潮阳,道出鹅城,谒国博唐公,一见倾盖如平生。自是书札往来,无非论文评诗,未尝以及俗事也……得唐公之文凡四十五首,诗赋一百八十有五首’。”[1]
实际为《唐子西集》作序的人是郑总,绍兴二十一年其子郑康佐作跋;唐庚诗文为郑总于鹅城与其相见及两人别后书札往来,并非郑康佐得于鹅城。
3.“续得闽本文十二首、诗赋一百十有一首。又续得蜀本文一百四十二首、诗赋三百有十首……晁、陈诸目所著录者,殆即所谓闽本、蜀本。”[3]
余先生订:“进士葛彭年以所藏闽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诗赋二百八十七首……又得蜀本于归善令张匪躬之家,凡文一百四十二首,诗赋三百有十首。”[1]
据郑康佐跋,真正的闽本与提要中提到的闽本文、诗赋数量均不符合;经查,《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均未提及所收《唐子西集》为蜀本或闽本,不知馆臣的结论从何得来。
4.“自《闻东坡贬惠州》一首,及《送王观复序》‘从苏子于湘南’一句外,余无一字及轼。”[3]
余先生订:“实则庚之称述苏氏者,不止如提要所举三篇已也……《乙未正月丁丑与舍弟棹小舟穷西溪》……此盖庚在惠州,因泛舟出游,而追怀东坡也……《书大鉴碑阴记》云:‘曹溪大鉴禅师碑,元和中柳柳州文,绍圣中苏定武书,前长老辨公立石。’……庚此文颇赞东坡书法,故不称东坡或子瞻而成定武者,所以避时忌也……卷二十八《书宋尚书集后》云:‘……东坡所谓字字照缣素,讵不信哉!’”[1]
前人查出唐庚其他提及苏轼的诗文还有:《到罗浮始识秧马》“行藏已问吾家举,从此驰君四十年”[4];《初到惠州》称惠州是“老师补处”,以苏轼学生的身份自居;《水东感怀》之“碑坏诗无敌,堂空德有邻”[4];在苏轼曾品泉之地作《卓锡泉记》,称东坡为“知水者”。笔者仅在信手翻阅《眉山集》时,便发现《遣兴二首》其二中提到苏轼的《东坡酒经》“酒经自得非多学”[4]。
除了作品中谈及苏轼,唐庚许多诗中都化用了东坡的词句典故。苏轼《次韵段缝见赠》“须知力穑是家传”句中的“力穑”,在唐庚《有感舍弟端孺外甥郭圣俞》中“力穑供输莫待催”句出现;《东邻二首》其一“白蜜已输仍节近”的“白蜜”,出自苏轼《次韵程正甫同游白水山》“恣倾白蜜收五稜,细斸黄土栽三桠”[5];《天马歌赠朱庭玉》中“一朝不直半束刍”化用苏轼《黄牛庙》“青刍半束长苦饥”;《杂咏二十首》中许多诗里都能看到苏轼的影子,如其一“蛤吠明朝雨”句“蛤吠”,出自苏轼《宿余杭法喜寺怀孙莘老学士》中“稻凉初吠蛤”;其三“便归良不恶,未去亦随缘”[4]化用苏轼《雷州八首》其四“得归良不恶,未归且淹留”[5];其五“手香柑熟后,发脱草枯时”[4]化用苏轼《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的“髻重不嫌黄菊满,手香新喜绿橙搓”和《春菜》的“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5];其十七“相对各苍颜”引苏轼《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与子甥舅氏,催颓各苍颜”[5]句。可见苏轼对唐庚影响之大之深。提要写“二刘所言,未详考也”[3],认为刘克庄、刘夷叔评价唐庚善学东坡之言是没有详加考证得出的结论,但事实恰恰相反,未能详考的是四库馆臣。正是因为唐庚对苏轼的推崇和学习,才使得他在当时就有了“小东坡”的美誉。
5.“及《送王观复序》‘从苏子于湘南’一句外,余无一字及轼。”[3]
余先生订:“所谓从苏子于湘南者,非谓东坡,乃子由也。子由以元符三年(1100年)二月移永州安置,其四月移岳州,王观复盖尝从之游耳。”[1]
经查,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逝于常州,崇宁元年(1102年)黄庭坚被贬湖北宜城,此时苏辙在湖南永州。王观复在宜城与黄庭坚交往时,苏轼已经去世,他所从的“苏子”应是苏辙。
6.“《宋史》称庚谪惠州,遇赦北归,卒于道,年五十一。”[3]
余先生订:“《宋史·文苑五·唐庚传》云‘商英罢相,庚亦坐贬,安置惠州。会赦复官乘议郎,提举上清太平宫,归蜀,道病卒,年五十一。’是庚明明卒于归蜀之时,何尝言其北归卒于道哉?”[1]
经查,《宋史·唐庚传》与《东都事略》都记载唐庚卒于归蜀途中,提要说法相异,应是馆臣未认真核检《宋史》原文所致。
7.“是修卒之时,庚方五六岁,断不相及。”[3]
余先生订:“案集中《六一堂》诗有‘虽不及抠衣’之句,则子西不及见欧阳文忠明矣……提要不知出此,而喋喋然考庚之生卒,已为词费,乃其所考又多谬误。欧阳修没于熙宁五年(1072年)壬子,非六年也。庚生于熙宁四年(1071年)辛亥,修没之时,庚才两岁耳,非五六岁也。”[1]
认真检核原书就能发现的问题,提要不仅费力考证且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出现如此粗浅的错漏,可见馆臣对待该篇提要的态度并不认真。
(二)观念性错误
1.“似庚於轼、辙兄弟颇有所憾。殆负其才气,欲起而角立争雄,非肯步趋苏氏者。”[3]
余先生订:“《文录》存者三十五条,其涉及东坡者凡八条,记黄门语一条,已过全书五分之一,不得不谓之多所称述。”[1]
经查,《唐子西文录》中涉及苏轼的有“论《居士集》序”条、“六一堂”条、“《病鹤诗》”条、“忠州潭”条、“诗律”条、“隔句对”条、“《南征赋》”条、“观书用意”条。从这些论诗之言来看,唐庚对苏轼推崇备至,更说苏轼“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6],可见他对苏轼心悦诚服,未曾有过自觉才气了得就想与苏轼争雄的意图。
2.“诗中深著微词,序中亦颇示不满。”[3]
余先生订:“其《闻东坡贬惠州》诗云:‘元气脱形数,运回天地内。东坡未离人,岂比元气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辄有碍。低头不得仰,闭口焉敢颏。东坡坦率老,局促固难耐。何当与道俱,逍遥天地外。’味其言,盖伤东坡以言语文字讥切当世,为世所不容,而不欲明言,不得已,乃归之于天矣……其悲之也深矣,何尝着一微词耶?”[1]
经查,唐庚与苏轼仅在元祐八年(1093年)见过一面,当时唐庚二十三岁,苏轼已经五十八岁。次年,苏轼被贬惠州,唐庚进士及第。意气风发的唐庚骤闻苏轼被贬的消息写下此诗,表达的是悲凉、感伤之情,甚至是为苏轼鸣不平,绝非不满。
3.“《上蔡司空书》,举近代能文之士,但称欧阳修、尹洙、王回而不及轼。”[3]
余先生订:“庚所上书之蔡司空,乃蔡京也。人非至愚,岂有誉苏轼于蔡京之前以挑其怒者乎?”[1]
在偷习苏门诗文的官员被不断弹劾、处分的高压下,谁敢在上书中推崇苏氏?在元祐旧臣已所剩不多的情况下,蔡京依然对所谓“奸党”打击、迫害,苏轼被视为元祐一党的代表,唐庚又岂敢对他大肆吹捧?再者,唐庚在《上蔡司空书》中已经表达了自己对苏轼的态度:“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间亦有知此道者,而时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见于世。宜稍稍收聚而进用之,使学者知所趋向。不过数年,文体自变,使后世论宋朝古文复兴自阁下始,此亦阁下之所愿也。某久不谈世事,感阁下屡记其姓名,敢复一言。或行或否,惟阁下裁之。”[4]在如此严苛的时局还坚持委婉进言,实属不易。
4.“《读巢元修传》一篇,言苏辙靳惜名器太甚,良以是失士心。”[3]
余先生订:“夫称子由謇謇有大体,是谓其有古大臣之风,誉之者至矣;靳惜名器,正见其公正无私,非憾词也。士大夫因而诋之,此小人不得志者之所为,庚昌言其过,所以罪熙丰之党,为子由鸣不平也。”[1]
《读巢元修传》表达的是对不阿附权贵的独立人格的赞美,对某些士大夫落井下石之卑劣行径的批评。称述苏辙有古大臣之风,是推崇而非诋毁。
三、馆臣评价失实原因探究及小结
由于王士祯(1634-1711)的著述总体上符合清代官学思想极其审美判断的要求,馆臣在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常常参考他的评价和观点。李厚琼的《四库馆臣评价唐庚之考辨》提到《带经堂诗话》中记载“庚生三苏之乡,又前后与东坡贬惠州,而集中无一字及之,盖庚起家为张商英所荐,其贬惠州亦以商英连染,视韩子苍异趣矣,宜其不为眉山之徒欤!”此外还有王士祯引王弱语:“唐子西议论文章,皆苏氏绪论,顾以党禁方严,而子西附张商英以进,其著作多不及苏氏,止《题巢元修传》及之,大致讥贬。《上蔡司空书》论当世文学之士,止言尹师鲁、王师甫,其趋时也如此。然亦何救于贬谪哉!”对比提要几处内容,可见四库馆臣对于唐庚及其与苏氏一门的评价,与王士祯的观点如出一辙,即认为唐庚处于苏氏的对立面,从而对唐庚进行批评。这完全是馆臣们建立在主观印象之上,并未对唐庚的原文进行仔细阅读和考察得出的错误结论。
元祐初, 张商英与同乡的三苏关系密切,他当时与苏轼多有诗歌唱和,苏洵去世后还写了《挽苏老先生》表达哀悼之情。司马光去世时,他曾作《祭司马光文》极尽褒扬。但在新党重执朝政后,迁任右正言的张商英作为新党集团的重要羽翼,开始猛烈批判旧党,其《论司马光等朋党讥议奏》等言论,不仅使元祐旧党被贬外放,甚至连已故人士都被剥夺谥号、追贬官衔。对于苏轼这个曾经私交甚笃的朋友,张商英则以“论祭天地非是”的罪名将他黜知英州,后来又将他贬到惠州。这些前后不一的行为导致对张商英人品的负面评价历代相沿,也使馆臣对与张商英过从甚密的唐庚产生了偏见。
在蔡京弄权的时势下,唐庚对张商英推崇新政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大加赞扬,是出于热衷报国的诚心,而非靠《内前行》趋炎附势、以求上位。他对张商英是对师长的情谊,而非将其当作前途的依附,后来更因与张商英关系密切,受到政治核心集团的种种打压。四库馆臣不详加考证,想当然地将唐庚与苏轼划归到不同阵营,又想当然地贬低在他们看来与苏轼处于对立面的唐庚,实在是“不捡之甚欤”[1]!
单从《唐子西集》的提要来看,《四库全书总目》舛误产生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实性的考据失察,一类是观念上的偏见。余嘉锡先生在对提要进行辨证时,不仅进行了知识性的考订,也对馆臣的观念进行了纠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馆臣们能够加以利用的资源、条件、手段和现今相比过于匮乏,且收录和用于参考的书目实在庞杂,加之编纂时间有限,提要的撰写又以简洁为要,因此对作家作品的考辨评论往往浅尝辄止,出现种种漏洞也在情理之中。但对馆臣自称“精心勘误,八行细检朱丝”[3]的态度是需要提出质疑的,如果馆臣真的核校了《眉山集》的原书或相关文献,很多舛误根本不会出现。
《四库全书总目》并非完美的作品,它的缺陷有着时代必然性,其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厘清,许多文学观念、学术观点也需要更新换代。如何突破评论框架和传统观念,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进行考证、取舍,如何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探讨文学和文学史,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