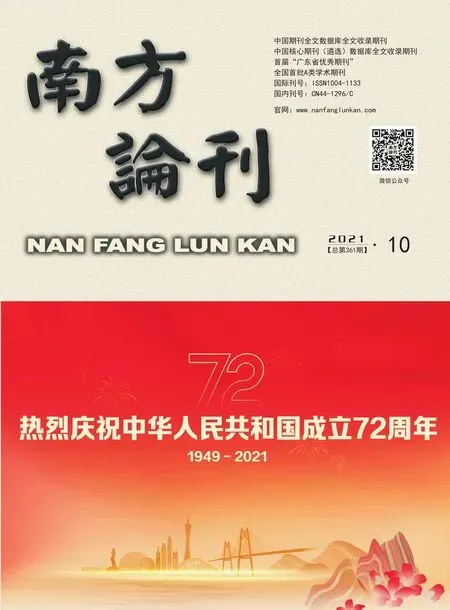以自食兴奋剂为切入点对兴奋剂入刑的冷思考——基于批判入刑观的视角
2021-12-29黄晨宾李恒
黄晨宾 李恒
(1.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福州 350001;2.福州大学 福建福州 350001)
一、问题的提出
1988年汉城奥运会百米运动员本·约翰逊以9秒79的成绩夺得了当时该项目的奥运冠军,但只不过得意数日就被查出服用兴奋剂,成绩金牌名誉一切作古;1994游泳世锦赛中国女子游泳队夺得12枚金牌一时之间风头无两,同年亚运会狂揽23枚金牌傲视群雄,但随着国际泳联的调查和众多游泳运动员飞行药检未通过,当时中国女子游泳队被查出集体服用兴奋剂;2005年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被查出服用兴奋剂;2014年俄罗斯运动员集体使用兴奋剂导致全国运动员被禁赛;2016年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曹磊、刘春红均被查出服用兴奋剂;2018年土库曼斯坦的摔跤运动员纳扎罗夫被查出使用兴奋剂禁止其参加亚运会;2021年孙杨因兴奋剂时间被判禁赛四年三个月。随着体育行业的利润逐渐增加、商业气息逐渐浓厚[1],越来越多的兴奋剂甚至集体兴奋剂事件出现,这些现象破坏纯洁体育风气、影响体育的健康发展、违反体育健身功能之虞,为了避免这些现象入刑论时有发生,此是现今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虽有真知灼见,但不乏可商榷之处。刑法固然可以规制犯罪现象,起到遏制犯罪源头的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合法化,但是对于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不可一概而论。兴奋剂入刑是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但是刑事立法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不能盲目寻求刑法规制,应当积极采取非刑法规制的手段维护社会合理秩序。刑事犯罪需要符合违法的行为结果以及主观因素,是否入刑更需研究其对社会的危害性,过往研究认为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对社会危害性极大并且影响体育的健康发展,但是并没有基于违法的行为结果和主观因素考量,也无深入挖掘运动员自食兴奋剂与其他兴奋剂行为是否可以一概而论。
综上而言,笔者试图寻求突破,分析兴奋剂入刑这一行为的内含和外延以运动员自食兴奋剂(运动员主观上自己服用或注射兴奋剂,不包括有组织的、他人强迫等情况)为焦点探究其不入刑的合理合法性,通过刑法必要性原则连接违法的行为结果、主观因素和社会危害性。基于此,从批判入刑论的角度界定兴奋剂入刑的限度,阐述兴奋剂入刑标准构建,提出兴奋剂入刑的活性化处理,综合考量兴奋剂不入刑的合理性以期促进体育健康发展、完善国家法治体系的功能。
二、兴奋剂入刑的合理限度
(一)比较法研究
当今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适用刑法规制部分兴奋剂,如奥地利用欺诈罪论处,其刑法第147条规定“实施欺诈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体育中为使用兴奋剂,通过反兴奋剂条约所列举的禁止药物或者方法,实施欺诈,造成严重损失的,给予实施欺诈者同样的处罚[2]。”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使用兴奋剂来获得金钱、财产、服务或者利益等行为也同样以欺诈罪论处[3]。
意大利作为一个较早将兴奋剂行为入刑的国家,在兴奋剂刑事立法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意大利在兴奋剂问题上的法律制度,对完善我国反兴奋剂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其专门制定了《体育活动的完整性和反兴奋剂法》,该法第9条规定,“对于运动员提供违禁药物的人(包括医生、教练、运动队的负责人等),处2年以上6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以及5000欧元以上7000欧元以下的罚金[4]。”鉴于此,通过对域外各国家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各国对于兴奋剂的规制较为分散,其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较大,每种规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不符合当今体育的国际化发展。
(二)兴奋剂入刑的合理性分析
兴奋剂始终是一项阻止体育健康发展的顽疾。第一、在使用过量的情况下会危害运动员身体健康;第二、会危害体育公平性,影响其健康发展;第三损害国家形象,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俄罗斯田径队因被证实大规模使用兴奋剂致使100名运动员被国际奥委会禁赛,俄罗斯残奥代表团更是被全员禁赛而无缘里约残奥会[5]。无疑将俄罗斯的大国形象推向风口浪尖,成为俄罗斯体育历史上的舛误。
201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为《解释》,这一司法解释立足于刑法的规定和现实实际,对于兴奋剂犯罪相关定罪量刑问题进行了规定,解决了司法机关迫切需要指导性标准的问题。可以说,这一司法解释有效地解决了当前实践中存在着的缺乏规范性文件的问题,对实践的开展有着显著地推动作用。
(三)兴奋剂入刑限度的理论阐释
对于刑法是否应当规制兴奋剂行为,当前学界有“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3种观点。(1)肯定说是指赞同兴奋剂行为被刑法所规制,主要反对兴奋剂的行业自治:(2)否定说主要赞同体育行业自治,反对兴奋剂行为被刑法所规制;(3)折中说指应当由刑法和行业自治或非刑法,分别调整不同的兴奋剂行为,关键在于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必要条件,应尽量采取非刑法的方式考虑各案的相适应性[6]。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兴奋剂行为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应该介入,或适当介入极少存在不介入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虽然其情节没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长期适用行政性规章处理,其层级低、软法居多、强制性弱的特点反而“纵容”了兴奋剂行为,使其数量不降反增,波及范围逐渐扩大,因此具有可受刑法控制的性质[7]。也有学者十分决断,认为必须采取刑法规制[8]。有学者则持中立立场认为,必须从体育犯罪刑法边界的争论焦点探寻体育犯罪的应然边界,界定体育犯罪刑法规制的合理范围[9]。由此可见当前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立场,主要是对于兴奋剂行为刑法规制的限度不同,如果不能合理规制刑法限度,则不可避免刑法对兴奋剂行为的不当介入。
(四)对兴奋剂入刑限度的分析
基于学界大部分理论偏向于兴奋剂入刑肯定说,需要认真分析刑法规制兴奋剂的合理限度,即遵循刑法的必要性原则,以防刑事立法不当对体育领域造成不健康的影响。
首先体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是一个呈现精彩对抗,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行业,需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有一个强壮于常人的身体,兴奋剂就可以很好地帮助运动员达到这样的条件。就如健身行业,类固醇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兴奋剂药品,也不断有古典健美运动员承认使用类固醇,但他们奖牌、成绩并未作古,可以看出该行业是允许其存在的,因为运动员使用过后之时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损害,并未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并能提高行业观赏性。此行为也引发思考:运动员自食兴奋剂是否造成的较小的社会损害,不应当与他人强迫、教唆使用兴奋或使用兴奋剂考试作弊等行为同日而语呢?
第二,对违规行为应当考虑行为人主观心理、客观事实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以及与合规行为的偏差度,综合考量是否需要刑法规制。现行机制评价不足是指现行法律法规对“滥用兴奋剂”的处罚与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不等价,不能达到有效抑制、防止此种行为出现的效果[10]。如行为人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则应相应犯罪论处。行为人实施这些行为本身具有主观故意的心理,并且实施法所不容的客观行为,走私、非法使用等行为对社会危害性极大,更遑论与合规行为的偏差度,理应受到相应处罚。唯有这种严重的兴奋剂行为予以合理的刑法规制,才可以使体育逐渐健康发展。
第三、若刑法过度干预竞技体育,则影响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目前兴奋剂行为愈演愈烈,需要借助行业自治进行优化治理,需要更专业的专家、法规来规范专业的体育竞赛。基于竞技体育的行业特点,应当慎重考虑其刑法规制。
三、兴奋剂入刑的标准的必要性原则
合理确定刑法介入兴奋剂边界具有重大意义,如何在竞技体育的观赏性和刑事秩序之间择其优劣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此,寻找兴奋剂入刑的合理范围需要借助刑法的必要性原则考虑其谦抑性。
(一)必要性原则的内涵外延
我国的传统观点一直强调刑法的必要性原则,具体表现为强调非犯罪化,强调凡是可以用民事方法处理的都不能用刑事方法处理,强调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强调刑法的处罚范围越窄越好[11]。兴奋剂犯罪理应受到法律惩罚,但必须在明确其犯罪本质的基础上加以确定,欲洞察事物的本质,必先从现象开始[12]。
犯罪的刑法界限应以必要性原则为界限,即不具备极大社会危害性危害全体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不能使用刑法规制,危及全体公民基本权益即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时必须用,但必须对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侵害尽量少,主要起到抑制、威慑的作用。兴奋剂犯罪应当是行为人实质上具备主观过错,实质上实施客观行为且具备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以往的入刑纷争往往是没有考虑刑法的必要性原则,将社会危害性和法律违反性片面的作为入刑的标准。必要性原则包括三个方面:(1)刑法的补充性:只有在其他手段的规制不能遏制源头的情况下才可以动用刑法,(2)刑法的宽容:刑法只规制社会危害性极大,影响公民人权的情况、(3)刑法的不完整性:刑法的宽容性恰恰是刑法的不完整性,未将所有侵害法益的行为定为犯罪。
(二)兴奋剂入刑的必要性原则判断
本文将主要探讨自食兴奋剂的必要性原则判断。自食兴奋剂虽然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前提是在服用至一定的量上时才会导致的。但该行为也只是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并不会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亦不会危害公民权益,更不会影响体育的健康发展。因此不应该使用刑法消弭,充分考虑到刑法的宽容即只针对社会危害性极大、影响公民人权的情况。如果自食兴奋剂造成了比赛的不公平可以通过收回奖牌、废除成绩、禁赛、罚款等方式处罚。对于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国家已经出台《解释》对该行为予以规制,充分考虑到刑法的补充性亦体育行业自治不能遏制犯罪源头,需要刑法加以规制。刑法的必要性原则主要是强调处罚当罚的情况,减少对行为人的人权伤害,起到遏制源头的作用,因此通过非刑事处罚可以起到良好抑制的违规行为则不适用刑法消弭。
四、兴奋剂入刑的活性化处理
从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制度以来,随着刑事和解、坦白从宽以及宽严相济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我国俨然形成一种犯罪活性化处理的实践现象,也可谓是一种刑法私法化现象[12]。当前不断存在兴奋剂司法实践滥觞,更应该提倡兴奋剂活性化理念。而且学界当前并未有人将该机制运用于兴奋剂行为研究,偶尔涉及也只是浅尝辄止。
(一)自食兴奋剂不入罪的合理性
自食兴奋剂行为与走私、非法使用以及非法经营则略有不同,虽然行为人具有使用兴奋剂的主观故意但该行为只对自身健康有所伤害并不具备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且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当前法律未有对自食兴奋剂行为的刑法规制,因此较轻微的自食兴奋剂行为应该免除或适当免除处罚。但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应当依法规制,这样既符合依法治国、依法治体的基本要求,也保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和竞技体育的纯洁、健康发展。
(二)增设财产刑、资格刑条款
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模式存在着“重自由刑而轻其他刑罚种类”的缺陷。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兴奋剂犯罪的刑罚种类往往更为多样,刑罚的配置也和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的轻重、主观心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社会大众起到的震慑力更为显著,如希腊就规定采用兴奋剂获利的应当没收全部财产[13],这种“倾家荡产”的惩罚自然要比一两年的有期徒刑更有震慑力,也更为科学。由于体育领域的特殊性,行为人多为教练员或运动员,其犯罪行为是出于利用他人谋取私利,所以从业禁止可以更好地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14]。但是,在我国当前刑事法律对于兴奋剂犯罪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能够通过刑法典来确定一个具体的规定来处罚兴奋剂犯罪,而刑罚种类配置的科学化自然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采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是一种目的理性的刑法解释论,本质上是以预防主义为导向的解释论,注重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产生影响,可比较理性的确定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软化刑法刚性的功能[15]。功能主义刑法可以更好地履行国家的保护义务以及确定刑法的边界[16]。是符合现代社会法律治理体系发展趋势解释论。的但也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可能会导致刑法过分温柔或过分暴力两种极端。
鉴于此面对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应该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兴奋剂行为构成相应具体犯罪的同时,可以采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理性解释所构成的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将无足轻重的法律行为排除在刑法惩罚的范围之外。当行为人不具有一定要被刑法惩办的理由时,可以对行为人作出免刑或非刑事的处罚,绝不可为了遏制源头,过分侵害行为人的法益,这是对人权的绝对践踏。
在兴奋剂行为中更应该适用该理性的功能主义解释论。与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行为不同,运动员自食兴奋剂的行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小,产生的影响力较弱,只有在服用过多剂量的同时才会对身体产生损害,较少剂量的兴奋剂对身体的伤害都处于可逆的状态。鉴于此,自食兴奋剂不应该处于非刑法惩戒不可的行为内,可以较好地适用刑法功能主义解释论,较理性的分析其犯罪构成在给予相应惩罚力度的同时,努力保护运动员的法益。
五、结论
纵观世界各国仅有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少数国家将自服用兴奋剂的行为认为是犯罪行为并将其写入刑法。因此大部分国家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首先,我国刑法中并未对运动员自主服用兴奋剂的行为作出详细的规定,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兴奋剂违规运动员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针对兴奋剂违规运动员,亦有相应的行业自治对运动员予以规制。对运动员来说,参加比赛相当于他们的职业,对运动员实施禁赛处理相当于将剥夺运动员在一定时间内的从业自由,在竞技体育职业化的今天,禁赛等于取消了运动员从业的资格,剥夺了其进行正当业务行为的自由,与刑法中的“从业禁止”惩罚力度相当,具有可预期的严厉性。因此,无需对自食兴奋剂进行刑事追究;
最后,要从根本上控制兴奋剂的使用。运动员生活在一个相对被保护较好的“空间”内,能自主接触到兴奋剂的可能性较低,大部分是由教练员、队医等人员引诱、威逼、强迫的。相较于运动员自主服用,在竞技体育领域这类情况发生的更多。因此应该通过刑法遏制源头使该情况予以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