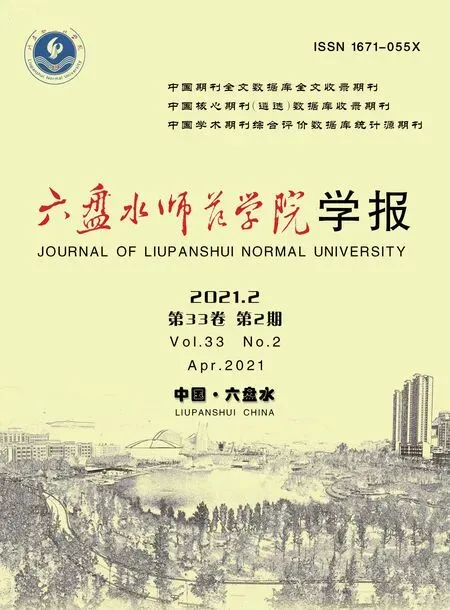“ 葫芦庙 ” 的隐喻性解读
——兼论甄士隐贾雨村二人的象征意义
2021-12-28杨和为卫佳
杨和为 卫佳
(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1)
《红楼梦》既是写实的小说,但也充满了隐喻和象征。仅从人物及其居处的命名言之,就充满了隐喻的玄机,值得我们深入探索。曹雪芹通过大量的谐音双关表达了其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抽象观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过程中的历史自觉和艺术自觉。正因此故,《红楼梦》这一小说文本既有形而下的具体故事,又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蕴,前者是对于传统章回小说的延续与递进,后者则使其超越于故事之上,而具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与隐喻性,这一自觉的努力使其创作超越了某一具体时代和某些具体人物,而获得了某种近乎永恒的普世意义。例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姐妹谐音 “ 原应叹息 ” ,冯渊谐音 “ 逢冤 ” ,千红一窟谐音 “ 千红一哭 ” ,万艳同杯谐音 “ 万艳同悲 ” ,秦可卿谐音 “ 情可轻 ” ,蘅芜苑谐音 “ 恨无缘 ” ,诸如此类,人所共知。学界对此盖已达成共识,然似犹有未尽者,如 “ 葫芦庙 ” 及甄士隐及贾雨村二人的象征意味,似乎还有研讨的必要。
一、 “ 葫芦庙 ” 的地理位置与命名玄机
按《红楼梦》第一回所写, “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 ”[1]7。曹雪芹运用由远及近的手法,渐次交代了 “ 葫芦庙 ” 所在的地理位置。因上文 “ 十里街 ” “ 仁清巷 ” 等地名的象征意味,及小说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再提及 “ 葫芦 ” , “ 葫芦庙 ” 便格外引人注目。而且,《红楼梦》整个故事可以说正是从这个 “ 葫芦庙 ” 拉开大幕的,这就使得 “ 葫芦庙 ” 变得格外重要。或许, “ 葫芦庙 ” 正是我们打开《红楼梦》这座艺术迷宫的第一把秘钥。
清代王希廉曾对 “ 葫芦庙 ” 的命名发生过兴趣,其在《红楼梦回评》中评第一回说: “ 葫芦庙有二义:葫芦虽小,其中日月甚长,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书虽是小说,而包罗万象,离合悲欢,盛衰善恶,有无数感慨劝惩:此一义也。此书虽是荒唐,却是实录其事,并非捏饰,所谓依样葫芦:此又一义也。……或曰:‘尚有一义。’余问:‘何义?’答曰:‘葫芦音同胡卢。人生若梦,幻境皆虚,离合盛衰,生老病死,不过如泡影电光。书虽实录其事,而隐藏真迹,假托姓名,演为小说,以供胡卢一笑耳:此亦一义也。’所说亦有意味,因附记之。 ”[2]585-586按王希廉的意见,似未得其真诠,不过虚晃一枪,流为皮相。
“ 葫芦庙 ” 乃是十里街内仁清巷里一座古庙。按 “ 十里 ” 谐音 “ 势利 ” ,甲侧批语说: “ 开口先云势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 ”[3]4而 “ 仁清 ” 则是谐音 “ 人情 ” ,甲侧批语说: “ 又言人情,总为士隐火后伏笔。 ”[3]4以此观之,苟依全息论的观点,所谓 “ 葫芦庙 ” 也者,乃是最具 “ 势利人情 ” 的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 “ 葫芦庙 ” 乃是一座古庙,作为《红楼梦》整个故事的发生地,居然只有一个 “ 人皆呼作 ” 的诨号,而没有一个正规正式的名字,以曹雪芹对于人物、器物、建筑及地名的命名自觉,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其有象征意味不言而喻。但究竟具有什么象征意义呢?我们认为,似可从两个方面深入:
第一, “ 葫芦庙 ” 乃是一个 “ 古庙 ” 。 “ 古 ” ,盖言其历史悠久,但究竟有多古,书中并未具体详说。 “ 庙 ” ,盖为寺庙之称,但 “ 庙 ” 在古代并非只指寺庙,还可指称 “ 庙堂 ” 。
第二, “ 葫芦庙 ” 之所以被称为 “ 葫芦庙 ” ,乃是因为 “ 地方窄狭 ” 。但若仅仅是因为 “ 地方窄狭 ” ,似不足以必然被命名为 “ 葫芦庙 ” ,称之 “ 土豆庙 ” “ 蜗角庙 ” 等名亦未为不可。
比较而言,第一层 “ 古庙 ” 之说乃是共名,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模糊的象征背景,第二层 “ 葫芦庙 ” 之说才是殊名,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二、 “ 葫芦庙 ” 的隐喻及其推扩
“ 葫芦庙 ” 的象征意义很大程度上从 “ 葫芦 ” 而来,其次跟 “ 庙 ” 息息相关。先看 “ 葫芦 ” ,葫芦古称瓠、匏或壶,又写作壶卢、蒲芦、胡卢等。古人以壶、瓠、匏三名皆可通称,初无分别。据考证,葫芦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距今已有7 000多年。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壶字,呈葫芦形。《诗经》中的 “ 幡幡瓠叶,采之亨之 ”[4]341“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 ”[4]39“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4]180等,都是最早记载葫芦的文字。此为 “ 葫芦 ” 本义。但 “ 葫芦 ” 的隐喻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略加梳理,发现 “ 葫芦 ” 至少有如下七种隐喻义:
(1) “ 葫芦庙 ” 以 “ 葫芦 ” 命名,是因为 “ 地方窄狭 ” 。这是《红楼梦》第一回中的说法,但需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作者曹雪芹的说法,而是姑苏城阊门外十里街仁清巷当地人所取的诨号。曹雪芹的看法实际上是隐藏着的,需要我们从其他方面深入探索。
(2) “ 葫芦 ” 是 “ 胡卢 ” 的谐音,有让人胡卢一笑的意思[2]585。
(3) “ 葫芦 ” 用来比喻三千大千世界,包罗万象[2]585。可为什么 “ 葫芦虽小,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 ” 呢?按《后汉书·方术列传》曾载费长房故事,或可说明一二。东汉时有费长房,某日正在酒楼上喝酒,看见 “ 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 ”[5]。费长房很奇怪,就买来酒肉拜见老翁。老翁领着费长房一起跳入壶中,如同仙境。费长房遂拜老翁为师学习方术,成了一代名医,后世因以 “ 悬壶 ” 作为行医的代称。至今还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俗语 “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 ,也与此有关。顺便提一下,《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嫫嫫说: “ 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 ” 贾琏道: “ 这何用说呢!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 ” 甲侧批云: “ 一段闲谈中补出多少文章,真是费长房壶中天地也! ”[3]160-161可见 “ 费长房壶中天地 ” 乃是读书人熟知的典故。
(4)孔子曾对葫芦发出过 “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6]的感慨,后世遂以 “ 匏系 ” “ 匏瓜 ” 比喻无用之物。另据《庄子·逍遥游》记载: “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7]26-27惠子的意思是大瓠用来盛水浆,坚硬程度不能保全自身;剖开做瓢,又太大无处可放。惠子借 “ 大瓠 ” 这种容器来比喻庄子,是讽刺庄子的学说大而无用。庄子的回答是: “ 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7]27庄子借葫芦为喻,说明无用之大用。
(5)葫芦本身形态各异,造型优美,无须人工雕琢就给人喜气祥和的美感,古人认为它可以驱灾辟邪,祈求幸福。很多道观及佛庙常在屋脊或顶上放置瓷质或陶制的葫芦,因此葫芦又有了辟邪驱鬼、保佑平安的作用。此外, “ 葫芦 ” 还是道神或仙人最具特征的伴物,如八仙中的铁拐李、跨鲤渡海的琴高、太上老君等身边都有配挂。
(6)葫芦果实圆润饱满,结子繁多,又与 “ 福禄 ” 谐音。而且葫芦是草本植物,其枝茎称为 “ 蔓 ” ,而 “ 蔓 ” 与 “ 万 ” 谐音, “ 蔓带 ” 与 “ 万代 ” 谐音。 “ 福禄 ” “ 万代 ” 即是 “ 福禄寿 ” 齐全,因而葫芦成为吉祥的象征,被国人看作繁茂美满、人丁兴旺、幸福如意的吉祥物。
(7) “ 葫芦 ” 乃是宋元时民间俗语 “ 葫芦提 ” 一词的省语,有时也写作 “ 胡卢提 ” “ 胡卢题 ” “ 葫芦蹄 ” 。据杨子华先生的考证, “ 胡卢提,即葫芦提,糊里糊涂,不明不白。明汤显祖批注《董解元西厢记》:‘葫芦提,方言,糊涂也。’清杭人翟灏《通俗编》引宋程大昌《演繁露》:‘葫芦提亦释作 “ 糊涂 ” 。今江浙一带方言仍有此语。’‘葫芦提’这个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方言,自宋以来就一直在杭州人的口头上流传,而且也被宋元话本小说所广为运用 ”[8]。
从《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看来,之所以命名为 “ 葫芦庙 ” ,并非当地人所认为的 “ 地方窄狭 ” 之故,而是暗含糊里糊涂之意,是以脂砚斋批语说: “ 糊涂也,故假语从此具焉。 ”[3]4一般认为脂批的这一说法表达了曹雪芹隐藏的意思。但以曹公用笔的狡猾,似乎还隐藏着更多的深意(但愿我们不是过度阐释),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 “ 糊涂 ” 一词的理解有多深入。所谓 “ 糊涂 ” ,一般认为就是糊里糊涂、不明事理的意思,但这样的解释未免有些含混和笼统。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地方的方言里, “ 糊涂 ” 一词还用来指糊状的面食,如河南是用小麦面、玉米面加入其他粮食颗粒或者地瓜、南瓜等精心熬制而成,山东及江苏赣榆一带则是用玉米面或白薯面加水煮成汤,而在鲁西南地区,糊涂是用小麦面、玉米面、白薯面或各种豆面加入其他粮食脱皮颗粒或者地瓜、南瓜等精心熬制而成。按照词义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引申规则, “ 不明事理 ” “ 胡乱 ” “ 模糊 ” 等意思不过是在 “ 糊状面食 ” 这一本义基础上的引申义而已,我们从 “ 糊状面食 ” 这一具体物象中或许更能理解 “ 糊涂 ” (也即 “ 葫芦 ” )的深层隐喻。
先看 “ 糊涂 ” 的本义。纵观一部《红楼梦》,我们发现,跟 “ 糊状面食 ” 最为接近的形象竟然是 “ 泥 ” 。贾宝玉关于 “ 泥 ” 和 “ 水 ” 的说法向来被认为是《红楼梦》中最精彩也最具颠覆性的一个比喻。小说第二回,作者借冷子兴之口,道出了贾宝玉的这句名言: “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1]28同是在这一回,作者又借贾雨村之口,道出了甄宝玉的名言: “ 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 ”[1]31一贾一甄,却都跟 “ 糊涂 ” 密切有关。细揆文意,曹雪芹简直是将 “ 糊涂 ” (也即 “ 葫芦 ” )与男人画上了等号。
再看 “ 糊涂 ” 的引申义。第十九回,袭人曾这样说贾宝玉: “ 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 ”[1]263也即是说,在贾宝玉看来,世间有一些糊涂人,不但自己糊涂不解圣训,反而混编纂出一些书来让后来者愈加糊涂,所有这些糊里糊涂 “ 读书上进 ” 的人不过是 “ 禄蠹 ” 而已。所谓 “ 禄蠹 ” ,字面意思就是窃食俸禄的蛀虫,比喻那些贪求官位俸禄的人。究竟哪些人可算作这样的 “ 禄蠹 ” 呢?第三十二回,写贾宝玉不愿出去见贾雨村,史湘云这样说宝玉: “ 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 ” 宝玉听了道: “ 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 ……宝玉道: “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 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 “ 这原是混帐话。 ”[1]432贾宝玉何以看不上贾雨村?因为贾雨村从本质上来说就是 “ 禄蠹 ” !推而广之,在贾宝玉看来,凡是热衷于科举功名和仕途经济的人,他们就是糊涂,连袭人和湘云让他去学些 “ 仕途经济 ” 的话也成了 “ 混账话 ”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深藏其中的隐喻线索: “ 葫芦 ” 即是 “ 糊涂 ” , “ 糊涂 ” 则隐喻那些热衷于科举功名仕途经济的男人!那些糊涂混账的男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糊涂混账地判案,也即第四回所谓的 “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 !其中, “ 葫芦僧 ” 不仅指门子(原是葫芦庙里一个小沙弥,后来蓄发当了门子),更是指 “ 一向加官进禄 ” 的贾雨村之流!如此一来,曹雪芹笔下看似极不经意的 “ 葫芦庙 ” ,竟隐藏着嘲讽功名批判皇权的思想。
那么 “ 庙 ” 又有什么样的隐喻呢?难道仅仅是一座 “ 古庙 ” 那么简单吗?我们认为,从隐喻学角度观之, “ 庙 ” 并非仅仅指 “ 寺庙 ” 之 “ 庙 ” ,也可以指 “ 庙堂 ” 之 “ 庙 ” ,乃一字而蕴二义。如果说, “ 葫芦 ” 意为 “ 糊涂 ” ,乃是语音上的双关,那么我们可以说, “ 庙 ” 既指 “ 寺庙 ” ,又指 “ 庙堂 ” ,这是语义上的双关。表面上在说 “ 寺庙 ” 之 “ 庙 ” ,其实隐藏着 “ 庙堂 ” 之 “ 庙 ” 。所谓 “ 寺庙 ” ,也就是《红楼梦》第一回实笔所写之 “ 古庙 ” ,乃是贾雨村寄居其中,甄士隐住在隔壁,后因 “ 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 ”[1]16而烧掉了的 “ 古庙 ” 。所谓 “ 庙堂 ” ,则隐指朝廷而代称帝王(庙指太庙宗庙,堂指殿堂明堂),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所云: “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9]按此 “ 葫芦庙 ” 之 “ 庙 ” ,因热衷于功名仕进、 “ 一向加官进禄 ” 的贾雨村之流寄居其中,遂使之成为朝廷帝王乃至国家政治体制的隐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曹雪芹在 “ 庙 ” 前加一 “ 古 ” 字,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国家政治体制由来已久,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整个历史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的这一观念,曾借石头之口作了相当的暗示: “ 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1]4-5盖曹公之意,中国古往今来的历史,就其 “ 事体情理 ” 而言, “ 皆蹈一辙 ” ,大抵如是。作者仅凭寥寥数语,便使小说的历史内蕴大大推扩,而不拘囿于一朝一代,这就是 “ 古庙 ” 一词的隐喻。
总括起来说就是,曹雪芹以 “ 葫芦庙 ” 明写和尚炸供烧掉的那座 “ 古庙 ” ,其实却是隐指贾雨村之流寄居其中以求功名 “ 福禄 ” 的糊涂世界,而这个糊涂世界,就其空间而言,乃是隐指贾雨村这样的禄蠹们趋之若鹜的庙堂,由此推扩而隐指皇权控制着的整个天下;就其时间而言,则隐指古往今来的整个历史。吊诡的是,这皇权控制着的整个天下,在曹雪芹看来,其 “ 地方窄狭 ”[1]7,究其实不过一 “ 葫芦 ” 而已,颇有点《庄子·则阳》中 “ 蜗角 ”[7]677的意味。
三、 “ 葫芦庙 ” 内外:贾雨村与甄士隐臆说
“ 葫芦庙 ” 的隐喻既明,我们对于贾雨村和甄士隐这两个跟 “ 葫芦庙 ” 有甚深渊源的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按书中第一回所写,贾雨村乃是 “ 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 ”[1]11者, “ 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 ”[1]11。贾雨村一出场,曹公即以谐音的方式做了诸多隐喻。据甲侧批,贾化谐音 “ 假话 ”[3]7,时飞谐音 “ 实非 ”[3]7,雨村即 “ 村言粗语 ” “ 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 ”[3]7。至其籍贯 “ 湖州 ” ,则谐音 “ 胡诌 ”[3]7。这几乎已成红学界共识。至于甄士隐,本是葫芦庙旁住着的一家乡宦, “ 姓甄,名费,字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 ”[1]7。据甲侧批,甄费乃 “ 真废 ” 之谐音,甄士隐则是 “ 真事隐 ” 之谐音。这似乎也已成为红学界共识。值得注意的是,脂砚斋批语固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红楼梦》文本,却未必不是我们更深解读《红楼梦》奥义的一个障碍。脂砚斋对于《红楼梦》的解读,未可视为唯一正确和唯一圆满的解释。在我们看来,因为 “ 葫芦庙 ” 独特的隐喻性质, “ 葫芦庙 ” 内外所住的贾甄二人,便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更深的隐喻意义,这是需要我们不囿于脂批而必须超越的地方。
《红楼梦》开篇即以 “ 葫芦庙 ” 作为整个故事的现实起点,而特意设置甄士隐贾雨村二人,并让 “ 进京求取功名 ” 的贾雨村寄居于葫芦庙内,让 “ 不以功名为念 ” 的甄士隐住在葫芦庙旁,在构思上别有深意,值得深入挖掘。贾雨村之 “ 贾 ” 既谐音 “ 假 ” ,甄士隐之 “ 甄 ” 既谐音 “ 真 ” ,也就可以说,在曹公的潜意识里,似乎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 “ 求取功名 ” 者(如贾雨村)每寄居于葫芦庙之内,而 “ 不以功名为念 ” 者(如甄士隐)则住在葫芦庙之旁。 “ 葫芦庙 ” 既隐喻 “ 皇权控制着的整个天下 ” ,则甄贾二人的隐喻意义不言自明:那些在皇权体制之内者,即是 “ 进京求取功名 ” 而 “ 假 ” 者,而那些 “ 不以功名为念 ” 者,则是自觉疏离于皇权体制之外而 “ 真 ” 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 贾雨村 ” 不只是 “ 假语村(言) ” 的谐音,亦当是 “ 假语存(焉) ” 的谐音。与此相类, “ 甄士隐 ” 也不只是 “ 真事隐(去) ” 的谐音,亦当是 “ 真士隐(去) ” 的谐音。如此解读甄贾二人,似乎更能窥见曹公写作《红楼梦》的本意,不仅是为 “ 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 ”[1]1的闺阁立传,亦是对古往今来那些热衷于功名的 “ 禄蠹 ” 之流进行批判。更让人深思的是,小说开篇还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甄贾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贾雨村淹蹇寄居于葫芦庙内,还是靠了甄士隐资助盘费才得以进京赴考而踏上仕途的。当他踏上仕途之后,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 “ 生情狡猾,擅篡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 ”[1]22,典型的一个靠 “ 假语 ” 而 “ 存 ” 者。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贾雨村明知被拐的女孩就是大恩人甄士隐之女英莲,却因门子一番利害分析,竟置恩人于不顾,胡乱判了此案。其徇私枉法,放走薛蟠,以为进身之阶的一系列举动,正是其依 “ 假语 ” 而 “ 存 ” 的本性使然。饶有意味的是,门子跟 “ 葫芦庙 ” 亦有很深的渊源,他 “ 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热闹,遂趁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 ”[1]57。在 “ 葫芦庙 ” 中修行的小沙弥 “ 耐不得清凉景况 ” ,而蓄发充了门子,给贾雨村大谈特谈护官符之妙用,其实也正是 “ 葫芦庙 ” 作为皇权社会扭曲和戕害人性的一个隐喻性表达。
四、结语
从隐喻的角度切入《红楼梦》文本,小说的意蕴更加深邃广阔。就 “ 葫芦庙 ” 及甄士隐和贾雨村二人的隐喻意义而论,曹雪芹大抵悲慨于这样的社会现实:那些热衷于功名的贾雨村之流依靠他们的 “ 假语 ” 混得风生水起,但像甄士隐这样一些不以功名为念的 “ 真士 ” 却悄焉隐退,终身游离于皇权体制之外,看似 “ 神仙一流人品 ” ,终究只落得个晚景凄凉的境地:先是爱女失踪,继之以房屋被焚,不得已而投奔岳丈,又因 “ 不惯生理稼穑等事 ”[1]16,贫病交攻,境况潦倒,终被跛足道人度脱出家,彻底逃离红尘。曹公对于世间那些靠 “ 假语 ” 而 “ 存 ” 者,固多揶揄批判,其对于那些处境日渐艰危的 “ 真士 ” 而 “ 隐 ” 者,则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并让他们成为智慧与洞达的化身。曹雪芹悲慨于世间真假之淆乱,不独以甄贾二人揭开全书序幕,并通过甄士隐所梦太虚幻境的牌坊对联 “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1]10,自然过渡到 “ 真 ” 与 “ 假 ” 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上升到 “ 有 ” 与 “ 无 ” 之形而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