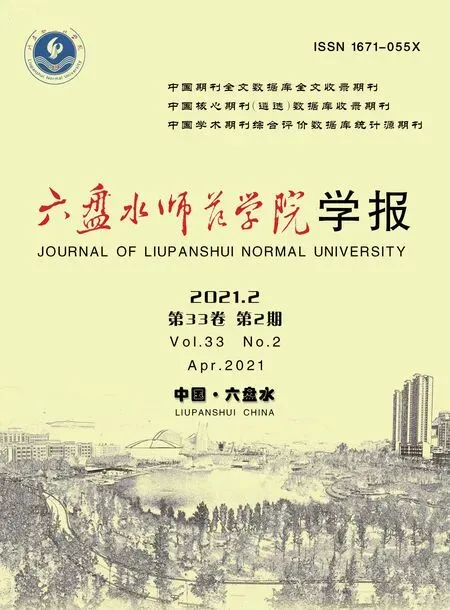“ 张千 ” 小考
2021-12-28孙若琪
孙若琪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在元明时期的戏曲中,衙役的称呼不止一个, “ 张千 ” “ 李万 ” “ 祗候 ” 等都曾用来指称衙门差役,其中 “ 张千 ” 的使用频率最高;随从的称呼也不止一个, “ 张千 ” “ 小厮 ” “ 祗从 ” 等都有指代随从的作用,但是祗从和小厮所跟随的主人并未有身份上的限制, “ 小厮 ” 有着年龄上的限制,一般都是对出身低微的未成年男仆的称呼。如此,这些称呼就与 “ 张千 ” 区分开来了,既能指官府衙役又能指官员随从的、且最为常见的称呼非 “ 张千 ” 莫属。
目前有关 “ 张千 ” 的研究文章仅有2篇[1-2],且考察对象都仅是元杂剧中的张千形象,都是在梳理了元杂剧中的 “ 张千 ” 类型之后,举例说明其在元杂剧中所发挥的作用,相较于对同类型称呼 “ 梅香 ” 的研究,对 “ 张千 ” 的研究显然不够深入。现有的两篇论文未考察 “ 张千 ” 这一称呼的来龙去脉,未将其放置于历史长河中进行总体考量,关于 “ 张千 ” 是如何具有固定意义的以及这种意义在后续小说戏曲中是否有发展和演变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空白。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研究空间与价值,因此本文便以 “ 张千 ” 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意义的来源以及发展进行分析,并总体考察其在古代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一、 “ 张千 ” 溯源
任何一个固定化了的符号都有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 张千 ” 在刚开始出现在小说戏曲中时也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后来它的意义才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具有指代性意义的称呼,而并非仅仅是某作品中的某个人物。
唐朝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并未出现 “ 张千 ” 。最早给 “ 张千 ” 安排差役身份的应该是话本小说《简帖和尚》, “ 走出转弯巷口,叫将四个人来,是本地方所由,如今叫做‘练手’,又叫做‘巡军’,张千、李万、董霸、薛超四人。来到门前,用钥匙开了锁,推开门,从里面扯出卖馉饳的僧儿来,道:‘烦上名收领这厮。’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领台旨。’ ”[3]11据《宋元语言词典》所述, “ 巡军 ” 就是地方上巡查捕盗的兵卒,这个时候的 “ 张千 ” 还是名姓。到了宋朝,说话和说唱艺术日益繁盛,但宋元话本几乎仅见于明人刻印的集子中,如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的《古今小说》与《警世恒言》等,而他们对其中的作品并未进行确切的朝代区分,所以后世对其具体的时代归属有不同看法。在目前基本能确定时代的话本中,将 “ 张千 ” 作为 “ 厮役 ” 来使用的只有《简帖和尚》与《曹伯明错勘赃记》。许政扬的《话本征时》中据《元史·兵志》考得巡军的设置为元代新创,因此认为本篇应该归入元人作品;同时,他也指出,篇中尚保留一些宋元时的制度和习俗,所以创作时期应离宋亡还不是十分久远,这种说法是得到了广泛认同的。而且,宋杂剧与金院本并未有文本留存,因此,就目前所存文献资料看来,姑且可以认为,《简帖和尚》是现存最早的为厮役起名为 “ 张千 ” 的通俗文学作品。
随后,创作者们不约而同地为笔下的角色安排了 “ 张千 ” 这个名字,并在之后将出现的张千默认为具有官员随从或官府衙役身份的人物,使之具有了指代类型人物的作用。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应是以下几个原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张是常见大姓,且在宋本《百家姓》中位列第24位,在宋朝时,张姓大约有49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3%,为宋朝第三大姓,据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发现, “ 自宋朝以来,李、王、张一直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三大姓氏,李姓和王姓的人口在不同时代各有不同,排序经常在伯仲之间 ”[4]222。人口多,具有代表性,所以在为普通市井人物起名时,会优先考虑这三大姓氏,比如 “ 张千 ” “ 李万 ” ,也比如 “ 张三 ” “ 李四 ” “ 王二麻子 ” 等。另外,《说文解字》记载 “ 张 ” 的本意为施弓弦,据《通志·氏族略》记载,相传黄帝之子少昊青阳氏的第五子名挥,发明了古代重要武器弓矢,因此被赐姓为 “ 张 ” ,后来张姓便又被称为 “ 军武之姓 ” 。而不管是官员随从还是府衙官吏,一般都是需要会武的亦或者说身强力壮的,如此才能执行收押捉拿等公务,为上级奔前忙后。那么, “ 张千 ” 姓 “ 张 ” 也是很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姓名与社会地位的贵贱有关,士大夫阶级常以名字标示自己的地位,而普通人是没有起正名的权利的。清人俞樾在《春在堂随笔》卷五中言, “ 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 ”[5]64。再加上古人奉行多子多福,但老百姓又文化水平低下,所以为图方便,经常以排行次第或数字为名。这在宋元时期,也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宋朝洪迈的《夷坚志》中便记载了许多以数字命名的人物,如符离人从四,风州民彭六、周三、李二十一,新城民范十五,陇州人王二,杀鬼的朱二、不孝的杜三,削香像的张八,等等。同时, “ 三 ” “ 四 ” “ 千 ” “ 万 ” 等都有多的意思,用他们为笔下角色命名,这正体现了 “ 张千 ” 在作品中的特点: “ 张千 ” 这个人物,并非是出类拔萃的,而是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分子而存在的普通人,以 “ 千 ” 为名减弱了它们作为名的特指性,具有了一般性。同时,之所以 “ 张千 ” 能成为 “ 厮役 ” , “ 张三 ” 不行,或与 “ 厮役 ” 的地位有关。他们是公人,他们是官员的随从,他们的地位比起普通老百姓稍高,因此为他们取名 “ 千 ” “ 万 ” ,而不是 “ 三 ” “ 四 ” 。这点从作品中也能够得到印证,在元杂剧《黄花峪跌打蔡纥褡》中,小厮与张千同时跟随着蔡衙内上场,二者并非一人, “ 张千我儿,你的眼最乖,你驾着鹞子朝天望着,有鸟儿过时就拿下来挦了与恁爹下酒……小厮,打这狗骨头 ”[6]1838。以 “ 我儿 ” 唤张千,但直呼小厮为 “ 小厮 ” ,这也可见,虽二者都是随从,但 “ 张千 ” 的地位是比普通 “ 小厮 ” 稍高的,二者并不相同。
宋元时期,有千户、千牛以及千人等官职,均是武官。同时梁朝萧子显的《南齐书》卷二十六列传第七提到一位名张千的将军, “ 左军将张千战死,追赠游击将军 ”[7]494。宋蹇驹《采石瓜州毙亮记》提到了校尉张千, “ 是日,金人命伪参政李通跪台上,口占辞为伪诏,遣张千校尉驾小舟来谕王权,谓将提兵往瓜洲,又似与权有先约 ”[8],此人此事在《资治通鉴》《三朝北盟》等史传类书籍中均有记载。总之,史书中的张千均是武官,但都是配角,并未有专门的文章为他们列传。这种看似巧合的事情出现次数过多,便很难再说是偶然,而且在宋及之前的杂集史书中就没有叫张三或者李四的武役,所以 “ 张千 ” 这两个字与 “ 武人 ” 的联系便建立在了饱读诗书的文人潜意识中,在他们想为笔下的重要人物安排一个身强体壮、会武艺的跟班时, “ 张千 ” 这个名字便会很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他们脑海中了。
总之,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创作者们不约而同地选用了 “ 张千 ” 二字来为自己笔下的官员随从以及官府衙役命名。现存宋元话本中,《曹伯明错勘赃记》的 “ 张千 ” 已经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了, “ 话分两头,却说曹州州尹升厅,忽东平府发文书来取曹州东关里开客店的曹伯明正身到来,急唤张千,‘你可取捉拿曹伯明来’。无多时,到阶前跪下…… ”[3]148前文并未介绍张千是何许人,此处突然出现州尹唤张千的剧情安排,若张千是一个具体的个体,那这种安排便会显得莫名其妙。而若 “ 张千 ” 已经具有了固定性意义,拥有了约定俗成了的代指差役的作用,那 “ 张千 ” 二字的出现也就显得非常自然了。在元杂剧中,有很多这样的 “ 张千 ” 。现存元杂剧大约有210种,出现张千这个角色的约有63种,其中的张千有的还是特指某一个人的名姓,有的已经具有了指代类型人物的意义。比如《观音菩萨鱼篮记》中的张千, “ 这个小的是张千,早晚家私里外衙门中,则是他跟随着我 ”[9]册六八3。对张千的身份职责进行了介绍,也就说明这里的张千还不具有指代性意义,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姓名。但在《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十探子大闹延安府》等杂剧中, “ 张千 ” 已经是类型人物了。
小说戏曲中对 “ 张千 ” 如此广泛的使用积淀了传统,令 “ 张千 ” 从一个具体衙役的姓名,变得具有所指性,逐渐能够作为此种类型人物的代表而出现。 “ 张千 ” 就在这样不断地使用中逐渐固定了意义,到了明初,王骥德明确指出 “ 张千 ” 就是此种类型人物的代表名称, “ 凡厮役皆曰张千 ” 。如此,它的指称性意义真正确定了下来。
二、 “ 张千 ” 的意义发展
在 “ 张千 ” 的意义固定下来之后,它的指代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同时,戏曲不同于小说,戏曲中的故事是通过各脚色的扮演来叙述的,而脚色之所以被称为脚色,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们所扮演的人物具有相似的形象特点,因此,既然 “ 张千 ” 也具有指代类型人物的作用,那么从脚色的角度来对 “ 张千 ” 进行考察就是有必要的了。
元朝戏曲分杂剧与南戏两类,南戏中几乎未出现张千,元杂剧中则频频出现。元杂剧中的 “ 张千 ” 指的就是官员随从或官府衙役,因为元代的公案杂剧的创作非常丰富,所以 “ 张千 ” 多存在于公案剧中,指的也多是差役。同时, “ 张千 ” 在元朝杂剧中还被当作脚色来使用。《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中的张千是官宦子弟葛彪的随从,《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中的张千是县令吕蒙正的随从,《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陈州粜米》等剧中的张千都是衙役。同时,很多元杂剧都会在剧末附上 “ 穿关 ” ,表明角色的服饰穿扮,尤其是《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所附的 “ 穿关 ” ,非常详细具体。根据 “ 穿关 ” ,可以看出 “ 张千 ” 的服装扮相是统一的,比如《狄青复夺衣袄车》《十探子大闹延安府》《女姑姑说法升堂记》《观音菩萨鱼篮记》等剧作后都有 “ 穿关 ” ,都说明了张千的服饰是 “ 攒顶,圆领,项帕,褡膊 ”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中表明, “ 张千 ” 在扮衙役时,是 “ 攒顶,圆领,项帕,褡膊,衙杖 ” ,为了判案假扮成货郎时,是 “ 攒顶、圆领、项帕、褡膊,挑担儿,拿不郎鼓 ”[9]册二二20。为 “ 张千 ” 提供了统一的装束,并再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加上特定的道具。此外, “ 张千 ” 还具有表演程式,比如 “ 摆头踏 ” “ 抬书案 ” “ 喝撺箱 ” “ 排衙上 ” 等,而程式化的服色和表演程式与脚色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在张千的科介中,并未表明是某脚色扮张千,而直接是 “ (……张千上……) ” 。另外,明初王骥德在《曲律·论部色第三十七》中曰:
“ 又按:元杂剧中各色不同,末则有正末、副末、冲末(即副末)、砌末、小末。旦则有正旦、副旦、贴旦、茶旦、外旦、小旦、旦儿(即小旦)、卜旦——亦曰卜儿(即老旦)。又有外,有孤(装官者),有细酸(亦装生者),有孛老(即老杂)。小厮曰徕,从人曰祗从,杂脚曰杂当,装贼曰邦老,凡厮役皆曰张千,有二人则曰李万,凡婢皆曰梅香,凡酒保皆曰店小二。 ”[10]168
他在论及张千时,将其放在 “ 部色 ” 中,并将其与 “ 旦 ” “ 末 ” 等并列,也就是说,他认为 “ 张千 ” 与真正的脚色 “ 旦 ” 或 “ 末 ” 有着同等的地位。可见,元杂剧中的 “ 张千 ” 基本上是被直接当作 “ 脚色 ” 来使用的。但是事实上,与元杂剧中的 “ 驾 ” “ 卜 ” “ 孛 ” “ 徕 ” “ 邦老 ” 等类似,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脚色,他们虽然具有了表示类型人物的稳定的意义,但 “ 不具备脚色舞台表演时的象征与过渡符号意义 ” ,而元杂剧中的正旦、正末 “ 是在舞台表演的象征与过渡符号意义上体现其脚色特征的 ” ,所以它们并非脚色,可以称其为 “ 亚脚色 ” 或者 “ 类脚色 ” ,即 “ 既非脚色名称,又非一剧中的特定人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 。而且,他们不是 “ 由演员固定扮演 ” 的,同时 “ 脚色扮演的对象虽然有大致范围,但并不完全相同,可以扮演多种类型的人物:但亚脚色则不同,只能扮演某一身份的对象 ”[11]276,比如真正的脚色正旦可以是上厅行首,也可以是大家闺秀,而张千只能表示官府衙役或者官员随从。
到了明朝时,创作者就为 “ 张千 ” 安排了脚色扮演,不再像元杂剧中那样将其直接当作脚色来使用了。明传奇中,在《六十种曲》里,《八义记》《寻亲记》《义侠记》三部作品中用到了 “ 张千 ” ,而这些剧作都表明了扮 “ 张千 ” 的脚色,分别为 “ 丑 ”[12]36“ 末 ”[13]14以及 “ 小丑 ”[14]51。扮演张千的脚色既不固定,也就可以印证上文所述 “ 张千 ” 并非是真正的脚色这一结论。明杂剧里有关张千上场的科介虽仍有些模糊,但在《虬髯翁》中也出现了 “ (扮张千上) ”[15]11这种明确的表述。这些足以表明 “ 张千 ” 已经脱离了元杂剧中那种 “ 脚色化 ” 的倾向,而仅将其作为类型人物来使用。
这种改变与明戏曲尤其是明传奇脚色行当分类的多样化、细致化以及脚色规制和程式的完备化有关。严格来说,元杂剧中仅有三个脚色类型, “ 末 ” “ 旦 ” 以及 “ 净 ” 。而传奇吸取了南戏的脚色分类,并进行了增添,王骥德云: “ 今之南戏(即传奇),则有正生、贴生(或小生)、正旦、贴旦、老旦、外末、净、丑(即中净)、小丑(即小净)。共十二人,或十一人,与古小异。 ”[10]168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也有所记载: “ 梨园以副末开场,为领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谓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贴旦四人,谓之女脚色;打诨一人,谓之‘杂’。此‘江湖十二角色’。 ”[16]146脚色的丰富使得传奇不再需要将 “ 张千 ” 作为脚色来使用,而可以根据张千不同的性格特征,为其选择相应的脚色。同时,传奇具有了情节更加复杂的故事以及愈发多的出场角色,脚色往往需要根据自身形象特点扮演不止一个身份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者们对脚色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认知,只能表示衙役或者官员随从的张千便无法跻身脚色之列了。
此外,正是因为明清时人对 “ 脚色 ” 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不再将 “ 张千 ” 作为 “ 脚色 ” 来使用,所以 “ 张千 ” 才不必拘泥于差役或官员随从这一类脚色框架中,才使 “ 张千 ” 具有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指向意义。其所指代的人物类型比元杂剧中更为广阔,他们不仅仅是衙役或者官员随从,在有的剧作中,非官员的随从甚至是女性的随从也是 “ 张千 ” 来承担。如《春波影》: “ (杨夫人领张千、梅香上云)今日初春天气,早去请冯二娘小青娘湖上耍子,此时将到,张千,可曾完备酒船否? ”[17]6在这里,女性的随从也用 “ 张千 ” 来指代。不过,由于传统的充分积淀,以及 “ 小厮 ” “ 祗从 ” 等也可以指代 “ 随从 ” 的名称的存在,所以在绝大多数的作品中, “ 张千 ” 还是具有与在元杂剧中相同的指向。
明清杂记小说中的 “ 张千 ” 也是如此。其官府衙役的身份指向一直未有改变,且相当一部分作品中的张千所指代的都是衙役这一类型,如明《水浒传》, “ 差两个防送公人,无非是张千李万 ”[18]468-469,如清《续金瓶梅》, “ 知府大喜,即忙出票拘拿,无非差的张千李万 ”[19],等等。但是同时,作为随从时,张千所跟随的主人并非全是官员、甚至可以不是人类,还可以是仙,清朝《韩湘子辩》中云, “ 世传韩湘子为八仙之一,……惠潮所在昌黎庙,亦塑湘子像乘云在侧,并有所谓张千、李万者作布雪状,谬妄相寻,不可解也 ”[20]。不过,从宋元到明清,张千所跟随的对象虽然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
总之, “ 张千 ” 在戏曲中,从一个具体的姓名,发展为元杂剧中的 “ 类脚色 ” ,又在明清时随着脚色制的愈加完善,逐渐成为只指代类型人物的名称。另外,在古代小说戏曲中, “ 张千 ” 所指代的人物类型多是官府差役,也能作为随从而存在,且随从的主人在元朝时基本上都是官员,但到了明清,他们跟随的对象还可以是具有其他身份的角色,其指向意义有所扩大。
三、 “ 张千 ” 的作用
“ 张千 ” 在古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中,常常并非是一个完整而具体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具有指代类型人物的意义。他在作品中的主要价值并非是他这个较为程式化的形象本身,他的作用体现在推动情节发展、标示身份和标示场景上。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张千具有相对来说比较个性化的特点,这些或正面或反面的张千形象衬托了其主人的形象,推动了情节剧情的发展,有时还起到了插科打诨、活跃气氛的作用。
不同于同类型的 “ 梅香 ” ,张千并不具备丰富的个人特点与文化内涵。即使在 “ 张千 ” 最为活跃的元杂剧中,也只有不到20个剧作中的张千是具有较为清晰的个性的,大部分作品中的张千都只是应声传话,甚至有的连念白科介都没有。还有的剧作中有多个张千的存在,比如《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中就有5个张千。张千之所以会被设置于这些作品中,主要是为了使情节合情合理化,换句话说,这些张千都是工具人物。
张千一般都是随主人一起上场,基本依附于主人而存在,他们的作用在于标示特定人物阶层的身份以及标示情节发生的场景。如有身份地位的官员在上场时身边一般都会安排一个张千以彰显威严,并随时等候吩咐,这时的张千甚至可以不用念白与科介。如《救孝子贤母不认尸》的第一折开场, “ (冲末扮王脩然领张千上云) ” ,张千跟王脩然一起上场就衬托了王脩然大兴府府尹的地位。再如《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第四折开场, “ (外扮包待制引从人上,诗云)……张千,你分付他两个孩儿同两个女儿,明日往云台观烧香去,老夫随后便来 ”[21]756。然后包待制便下场了,张千全程未有表演,但他的出现使得包公的身份地位得到了彰显,同时通过让包待制吩咐张千去做事简单带过不重要但又不可缺少的情节,使下文 “ 他两个孩儿同两个女儿 ” 之所以会在 “ 明日 ” 去了 “ 云台观烧香 ” 这个情节合理化,使前后情节得到了衔接。此外,张千能够标示场景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公案剧中,张千作为衙役的上场以及张千 “ 排衙 ” 的动作,标示了目前是在衙门这个场景中开展的剧情,当然同时也衬托了主人的身份地位,烘托了公堂上肃穆的气氛。
小部分具有特点的张千常见于公案剧中。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公案剧中,衙门或者官场都是常出现的场景,张千作为官员随从或公门中人,虽然本身权力不大,但与有权势之人关系密切,因此他们作为半个参与者,很容易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点。有反面张千为虎作伥、仗势欺人,如孙仲景《河南府张鼎堪头巾》武力胁迫、欺凌弱小,威胁苦主 “ 休言语,你但言语,我就打死你 ”[9]册二二8,这种形象正是在自己主人的助长下才形成的,反衬出令史的糊涂与罪恶;也有正面张千同情弱小、善良可爱,如《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中的张千为吕洞宾求情,后来还见韩魏公年老体弱,不忍再拘押他;如《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中韩飞卿冒失闯入官家小姐府内后花园,张千遇见了也只是做好分内之事,并未对他施加暴力,反好心劝他离去, “ 你快出去,则怕老相公回来了也 ”[21]19,张千的这种行为侧面体现出了王府尹的御下之严以及他本身的板正清廉;《观音菩萨鱼篮记》中的张千细心又忠诚,他两次发现观音身份的异常,向主人张无尽示警,即使刚开始的时候张无尽并不相信他,后来也正是因为他示警的成功,推动了剧情发展,才有后面张无尽让观音去打扫花园落叶,才能遇到布袋和尚,让张无尽得以修成正果。
有时个性化张千的出现还使元杂剧产生了喜剧效果,营造了轻松活泼的气氛。比如《包待制陈州粜米》中的张千,随包待制一同去往陈州,路上嫌弃饭食,想借官势弄点酒肉,包待制听到了,问他何为 “ 肥草鸡儿 ” 和 “ 茶浑酒儿 ” ,张千慌忙搪塞,竟显出有趣的急智来, “ 我才则走哩,遇着个人,我问他‘陈州有多少路?’他说道‘还早哩’。几曾说甚么‘肥草鸡儿’? ” “ 我走着哩,见一个人,问他‘陈州那里去’?他说道线也似一条直路,你则故走。孩儿每不曾说甚么‘茶浑酒儿’。 ”[21]45令人莞尔,张千这种念白的设置也让本平凡无奇的故事生动有趣了起来。《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中的张千被店小二戏弄,但又碍于上司的面子有苦难言,强吃下冰似冷酒以及滚开热酒的表现也十分具有喜剧效果。
明清传奇中,张千出现的频率不高。但相较于元杂剧中大部分只会说 “ 理会的 ” 的张千,明清传奇中的张千在应声传话中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价值取向。如《八义记》中,张千上场时道, “ 只争几句闲言语,害了多多少少人,张千回话 ”[12]50。也会唱道 “ 【前腔】思量起无非昧心,三百口一齐杀尽…… ”[12]51。这些语句表现出,虽然自己是屠岸贾的随从,但是内心却完全不认同这种做法,甚至有谴责之意,体现了他的善良,也从反面衬托出了屠岸贾的凶残与奸诈。同时,也有助纣为虐、毫无愧心的张千,如《寻亲记》中末扮的张千,他在张敏对周维翰的敲诈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更是挑唆张敏杀死保正黄德,并将尸首移置周维翰门外来陷害他。此剧中的张千在剧中的戏份不少,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上场时即念道, “ 簇簇花街远,潭潭华屋深。忽闻呼唤语,侧耳听清音。员外有何分付 ”[13]14-15,这种作为土豪随从的趋炎谄媚之相立刻就立起来了,他们为解主人之忧,胆大包天,无不可为之事。下场诗也可见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丑陋嘴脸, “ 索钱说合只凭伊,只为佳人美貌奇。不施万丈深潭计,怎得骊龙颔下珠 ”[13]16。可以看出,由于传奇鸿篇巨制的篇幅以及众脚皆可唱等特点,明清传奇中的张千常常通过上场话或者下场诗等来表现自己的态度,如此就显示出了比元杂剧中的张千更加鲜明的个性特点,既对主人公的形象有所衬托,也以自身独特的形象特点使得剧作具有了更加丰富的人物群像。当然,也有完全作为工具人物而存在的张千,如《义侠记》中的张千,他的出现只为应身,并无念白或唱词,他们在传奇中起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剧情合理化。
可见,在不同的时代中, “ 张千 ” 的含义以及用处有所区别,其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有所不同。但是,总的来说, “ 张千 ” 大都作为工具人物而出现,所具有的意义以及所发挥的作用也大都是作为一个固定性的符号所产生的。具有个性化的张千形象不多,甚至可以说,他们在所有使用到 “ 张千 ” 的古代小说戏曲作品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小的。但是,这些个性化的 “ 张千 ” 在念白、曲文中显现出来的独特而生动的个性特点,使得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的人物群像。
四、结语
“ 张千 ” 由于 “ 张 ” 与 “ 千 ” 的字词含义、元明时期的起名传统以及历史上同名武官以及官职等原因,成为众多创作家笔下衙役或官员随从的名字,又随着作品中的大量使用以及传统的积淀,它逐渐具有了指代类型人物的意义。这种意义在元朝与明清时具有不同的发展,在元朝时被当作 “ 脚色 ” 来使用,在明清时则具有更广泛的指向意义。同时,大部分 “ 张千 ” 都是没有个性特点的符号,但在作品中并非就毫无建树,他们在推动情节发展合情合理化以及标示身份与场景等方面都有所作用;而少部分具有独特性格特点的 “ 张千 ” 则有着衬托主人形象以及突出喜剧效果的作用。
对 “ 张千 ” 源流、发展过程以及作用的论述,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看待作品,同时,通过 “ 张千 ” 这一同时存在于小说与戏曲中的固定称谓,也能帮助研究者们更清晰地看待小说戏曲等各通俗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其中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