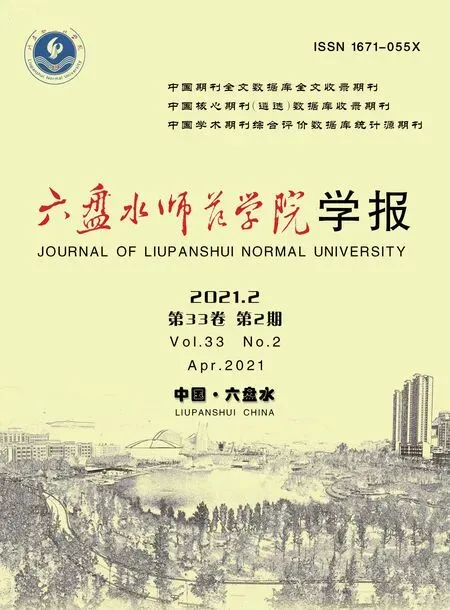《文苑英华》选录杜诗诗题异文研究
2021-12-28李青
李青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文苑英华》成书于宋初,去唐未远,彼时所见唐人文集尚多,故其为规模最大且保留至今的唐人文学作品总集。《文苑英华》选录杜诗三百余篇,其数量和比例在唐人中仅次于白居易与李白,但关于《文苑英华》选录杜诗的研究,学界现有成果寥寥①。
杜诗作为古典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从唐五代到宋的流传过程中版本众多,由于主要以手抄流传等原因,产生大量的异文。郭在贻先生认为,唐诗异文多,以杜诗为甚,这一看法有其数据依凭。据邓亚文统计,杜甫存诗1 448首,异文诗1106首,占76.4%,而李白存诗971首,异文诗436首,占44%[1],远低于杜甫。郭先生对杜诗异文进行考索,将其分为六种类型:一是由于浅人的妄改而造成;二是因同音假借而造成异文;三是因声音相同相近而造成异文;四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异文;五是异文双方为同义词或近义词;六是异文的各种写法为同一连绵词的不同变体[2]86。学界对杜诗文本异文持有较多关注②,甚至有专门研究杜诗异文的硕士论文[3],但将杜诗诗题异文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情况较为少见,而诗题作为杜诗文本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异文形成有较为复杂的历史因素,不可忽视。与宋初其他杜集版本异文相区别的是,《文苑英华》作为分门别类的大型文学总集,注定了其编纂者不仅是完成收录杜诗的工作,还有以门类的标准对杜诗进行选择并合理归置的过程,而诗题作为诗歌的标示性特征与分门别类的形式因素直接挂钩。因此,《文苑英华》选录杜诗诗题的异文,其相当一部分乃是在人为编纂过程中对杜诗原诗题的调整与 “ 规训 ” ,并非文学史上的无心之举。正如田晓菲所言: “ 异文并不都是抄写者无心的错误,而完全可能是有意的改动,是对文本自觉地进行编辑整理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北宋编辑们在准备印刷一部书籍时所做的事情。 ”[4]9程章灿先生对此早有认识,其认为 “ 对诗题进行类化、简化或同化,是《文苑英华》这部总集在文献使用和编纂体例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其影响及于诗歌之流传、阐释与接受,更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其对个别作品的占有、支配甚至再创作的权力 ”[5]。故本文以《文苑英华》选录杜诗诗题为研究对象,比较其与早期杜集《宋本杜工部集》存在的异文,并对这些诗题异文进行分类并辨析其可能产生的原因。
一、《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基本情况
《文苑英华》成书于太平兴国(982)九月至雍熙三年(987)十二月,历时四年余,比王洙宝元二年(1039)编纂杜集领先52年。其书撰成后几经修订,藏于秘阁之内,至南宋经周必大与彭叔夏等人之手再度修订才得以于吉州雕版印刷,是为吉州刻本。《文苑英华》得名于梁萧统编选的诗歌总集《诗苑英华》或二十卷《文章英华》,体例上也参考了《文选》的分类标准,将文体分为三十八大类。在编排方式上,《文苑英华》沿袭《文选》先赋后诗的文体次序,总体编排方式为先分体次分类,然其编者却单独将 “ 歌行 ” 从 “ 诗 ” 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类。林心治认为,历代诗论家所言之歌行,一是指乐府诗中作为乐府题目即篇章名称的歌行,兴起于汉代;二是指作为诗歌体裁的歌行,最早由中唐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首次提出[6]。《文苑英华》将歌行作为独立于 “ 诗 ” 部 “ 乐府 ” 的存在,显然是将其视为一种诗歌体裁并对其诗体地位进行确认②。《文苑英华》选录作品的时间范围,大体而言继《文选》之后收录梁及唐五代的诗文作品。此外,《文苑英华》还参考《艺文类聚》的分类,其有不少类目与《艺文类聚》完全相同,如 “ 奉使 ” 类等。《文选》与《艺文类聚》相较,前者是文学总集,后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子部类书类,而《文苑英华》也呈现出总集与类书的性质,程章灿先生认为《文苑英华》 “ 是一部大型的类书式总集 ”[5],凌朝栋先生更倾向于将其界定为一部诗文总集[7]80。
《文苑英华》全书共一千卷,其中, “ 诗 ” 一百八十卷, “ 歌行 ” 二十卷。是书选录杜诗分布于 “ 诗 ” 与 “ 歌行 ” 两类中,据中华书局1966年版《文苑英华》篇名总目统计,《文苑英华》 “ 诗 ” 部选录杜甫诗歌194首,具体情况为:天部33首,地部7首,朝省7首,乐府24首,音乐2首,人事8首,释门1首,隐逸2首,寺院8首,酬和4首,寄赠13首,送行15首,留别3首,行迈14首,军旅1首,悲悼16首,居处22首,郊祀3首,花木3首,禽兽8首。 “ 歌行 ” 选录杜诗53首,其中天部3首,四时1首,征戍1首,音乐1首,酒6首,草木1首,书1首,图画5首,杂赠4首,送行3首,山3首,石2首,佛寺1首,楼台宫阁1首,经行1首,兽5首,禽4首,杂歌10首,两类合计选杜诗247首,其中 “ 歌行 ” 收录杜诗与 “ 诗 ” 部重出者5篇, “ 诗 ” 部中天部于杜甫《九日登梓州城》诗题下误收张均《九日巴丘登高》一诗,故去其重出与讹误者,实收杜诗241首③,约为现存杜诗数量的十六分之一。
《文苑英华》收录诗文,按体分类,每一体下按照诗文题材内容再分大类目,各大类目下还可再细分为小类目,最小类目下为具体作品,程章灿先生将《文苑英华》各层次的大小类目称为 “ 大题 ” ,各篇诗作的题目称为 “ 小题 ”[5];大题统摄小题,各小题在内容上相互关联,共同支撑大题,此种编排方式与类书相似。《文苑英华》选录杜诗亦在此种编排方式之下,据笔者统计,在《文苑英华》所录241首杜诗中,其诗题与《宋本杜工部集》诗题相异的至少有63首(包括歌行在内,《八哀诗》计为一首),约占所录杜诗的五分之一。至于两书存在部分意义差别不大的杜诗诗题异文,如《文苑英华》卷二六九《送梓州李使君赴任》、卷三四一《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赴上都》与《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三《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卷八《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仅为 “ 赴 ” 与 “ 之 ” 的表达选择不同,差别甚微,故本文不予讨论。除此之外,《文苑英华》与《宋本杜工部集》的诗题异文具体情况各异,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二、诗题与题下自注混同
自注,即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注释。自注最早起源于史书,后来逐渐运用到文学作品中,六朝时已出现了谢灵运《山居赋》、张渊《观象赋》、颜之推《观我生赋》、鲍照《芜城赋》等带有作者自注的赋作。自注在唐代更为完善成熟,这种阐释方法被许多唐代诗人采用,杜甫诗中就有多处自注,即 “ 公自注 ” 。杜诗自注大多数在题下,即题下自注,也有在句中和句末的,数量较少,而且难以辨别是否为后人所加,故暂且不论。《文苑英华》选录杜诗诗题与《宋本杜工部集》诗题存在差异之处相当一部分为诗题与题下自注相互混同的现象,即二书或将杜甫诗题的末尾部分视为题下自注,或将在另一书中属于题下自注的内容归入杜甫诗题本身,因而形成杜诗诗题的不同面貌。
按照古代传统的书写方式,题下自注常以双行小字置于标题之下,《文苑英华》成书于宋初印刷业尚未普及的年代,文本多以抄本形式流传,而在传抄过程中由于题下注与标题位置较近,不太容易辨别,极易混入原诗诗题;而原诗诗题通常都标以大字,按常理而言不太容易混入题下自注中,但寻检《文苑英华》与《宋本杜工部集》的杜诗诗题,常可发现两书的诗题与题下自注往往有彼此错位互异之处。考虑到《宋本杜工部集》成书晚于《文苑英华》五十二年,且后者编成后藏于秘阁之内,王洙等人收集杜诗时未能参阅。王洙《杜工部集记》叙其编集所见杜诗: “ 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矣。收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一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 ”[8]可知其并未参考《文苑英华》所录杜诗,故二者为相互独立的杜诗早期文本,其诗题的差异性可能为各自参照杜诗文本的差异所造成,折射出杜诗在唐五代流传文本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④。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 “ 旧蜀本杜诗,并无注释,虽编年而不分古近二体,其间略有公自注而已。 ”[9]703陈尚君认为,严羽所言旧蜀本或即王洙所据本,疑出于五代前后蜀所刊行[10]307,可知早期杜诗已有 “ 公自注 ” ,《宋本杜工部集》或承此自序而来。
以《宋本杜工部集》(以下简称《杜集》)为参照,《文苑英华》(以下简称《英华》)将前书杜诗题下自注作为诗题正文的案例如下:《杜集》卷十二《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题下注 “ 得风字 ” ),《英华》卷二一四人事类题作《陪章侍御宴南楼》;《杜集》卷十《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题下注 “ 相国制文 ” ),《英华》卷二六九送行类题作《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杜集》卷九《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题下注 “ 庙有吴道子画五圣图 ” ),《英华》卷三二零郊祀类题作《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杜集》卷八《醉歌行》(题下注 “ 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 ” ),《英华》卷三三六歌行题作《醉歌行》;《杜集》卷四《丹青引》(题下注 “ 赠曹将军霸 ” ),《英华》卷三三九歌行题作《丹青引》。此外尚有与上述相反的情况,即《宋本杜工部集》中的诗题正文在《文苑英华》中作为题下自注,兹举数例如下:《杜集》卷九《赠韦左丞》,《英华》卷二五一寄赠类题作《赠韦左丞》(题下注 “ 济 ” ),至于 “ 文 ” 与 “ 丈 ” 之异文,郭知达《新刊校订集注杜诗》、旧题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父子《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宋本杜集皆作 “ 丈 ” ,可知此盖为《杜集》之形近而误,同属此误的还见《杜集》卷一《醉时歌》,其题下注为 “ 广丈馆博士郑虔 ” ,此类之误过于显明,当以《英华》为是;另如《杜集》卷十《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英华》卷二六九送行题作《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题下注 “ 三十韵 ” );此类现象在《八哀诗》中更为集中,如《杜集》作《赠司空王公》,《英华》题为《赠司空王公》(题下注 “ 思礼 ” );《杜集》作《故司徒李公》,《英华》题为《故司徒李公》(题下注 “ 光弼 ” ),该组其后关于李邕、苏源明、张九龄三诗皆如此,人物的名字在《英华》中皆作为题下自注的形式出现。此外还有较为特殊的一例长题,见《杜集》卷十《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英华》卷二八四送行题作《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然此诗于篇末注曰 “ 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 ” ,篇末与诗题相隔较远,混淆的可能性不大,故若非后人据《宋本杜工部集》诗题增补至《英华》末尾的话,可能杜甫诗集文本之一的面貌即是如此。
三、类化产生的诗题异文
《说文解字》第十篇上释 “ 类 ” 曰: “ 种类相似,唯犬为甚。 ” 段注云: “ 类本谓犬相似,引申假借为凡相似之称。 ”[11]476即 “ 类 ” 的本义为 “ 类似 ” 。类化作为动词,即通过某种手段使某些本不相同或相似程度较低的事物显现出相同或相似的特征。《文苑英华》采录的杜诗诗题与《宋本杜工部集》多有出入,原因之一在于其编纂者对大量杜诗诗题进行刻意的、并无其他文献支撑的文本改动,属于人为的类化整合,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减省语词
减省即通过删减原诗题中与本卷类目不切合的、多余的语词来实现类化的目的。《英华》相较于《杜集》诗题有所减省的诗例如下:《杜集》卷十二《春夜喜雨》,《英华》卷一五三题作《春夜雨》,二诗题的差别在于 “ 喜 ” 字。细检《英华》卷一五三 “ 天部三 ” ,可知该类下设 “ 雨 ” “ 喜雨 ” “ 对雨 ” “ 苦雨 ” “ 杂题雨 ” 五小类, “ 喜雨 ” 一类下已选录杜甫的《喜雨》一诗,而将《春夜雨》一诗归于 “ 杂题雨 ” 类下,乃是编者为了避免此诗题与前一类目相矛盾而造成分类的错乱,故删去原诗题中的 “ 喜 ” 字,使之趋近 “ 杂题雨 ” 的特征,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人为改动。又如《杜集》卷十《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英华》卷一五八天部题作《至日遣兴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诗题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少了 “ 奉 ” 字。此诗位于《英华》 “ 天部 ” 之下, “ 天部 ” 在此卷中突出要素为节候时令,诗题中 “ 至日 ” 二字已切合此卷要求,故《英华》编纂者于诗题中将 “ 奉 ” 字省去。再如《杜集》卷三《前出塞》《后出塞》在《英华》卷一九七中均题为《出塞》;而《宋本杜工部集》中将这两组乐府诗题为《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英华》对这两组诗分别九取五、五取三,不仅对原组诗有所割裂,而且还将两组诗诗题同化,以便将其归属于刘孝标《出塞》诗题之下。
《英华》除了割裂杜甫组诗之外,其编纂者选录杜诗时还将本非同一组诗的作品强行合为一首,并对诗题进行简化,如《英华》卷二零九中作为一组诗出现的《骢马行二首》,在《杜集》卷一中实作两首,分别题作《骢马行》与《高都护骢马行》,且两首诗之间间隔二十余首诗,并非相邻排列,《英华》将其合为一组,实因此二诗题共有的 “ 骢马行 ” 元素,并省略了《高都护骢马行》中 “ 高都护 ” 这一在此类中纯属多余的人物提示部分,为更符合此卷 “ 骢马 ” 的主题。
《英华》中删减杜诗诗题以求类化的例证尚夥,如《杜集》卷二《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英华》卷二一零乐府题作《苦热》,其卷苦热诗排列次序如下: “ 苦热,梁简文帝;同前,任昉;同前,何逊;同前,刘孝威;同前,王筠;同前,庾信;同前,杜甫…… ” 可知此处的诗题减省乃是为了迎合梁简文帝《苦热》一诗,而原诗题中 “ 早秋 ” “ 堆案相仍 ” 则为多出的部分而被舍弃。有意思的是,杜甫此首 “ 苦热 ” 诗之后收录的刘长卿《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仍呈王员外》及释皎然《五言酬薛员外谊苦热行见寄》就诗题来看皆长于杜诗,却未被删减成 “ 苦热 ” 二字,皆保留原诗题,值得玩味。
此外,《英华》编纂过程中还减省部分杜诗诗题韵数及首数:如《杜集》卷九《上韦左相二十韵》,卷十《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卷十二《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卷十三《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在《英华》中,作为提示该诗句数、篇数的要素均被删去,但杜甫在诗题中标明句数、字数、篇数、用韵等乃是其拟题的特点之一,此承六朝诗题而来, “ 六朝人作诗还有一个新风气,便是喜欢在诗题中标明所作的诗歌体制与形态特点。如陈后主的《立春日泛舟玄圃各赋一字六韵成篇》……这类诗题标志着当时人们对于诗歌形式的重视与自觉的态度 ”[12]69-70。杜甫集前代诗歌之大成,具有高度自觉的拟题意识,其诗题长短古近兼备,题中标明诗歌体制实属常见,如《自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曲江二首》《曲江三章章五句》等及其众多分韵诗,乃是其诗题之特点,若删减此类要素,则前举《曲江二首》与《曲江三章章五句》可径题为《曲江》,从诗题上看就无法对这两组诗加以区分。
(二)增加语词
除了删减杜甫原诗题中与《英华》大题不切合或不相关的语词以实现其类化目的之外,《英华》编纂人员还偶尔扩充杜甫原诗诗题或选择性地使用更为切题的题下注作为诗题,以求杜诗诗题与本卷内容的整合与统一。如《杜集》卷八《望岳》,《英华》卷一六零题作《望南岳山》,现录其诗前十六句如下(据《英华》本,以下所录杜诗皆同):
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歘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则亡。洎吾隘世网,行迈越潇湘。渴日绝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嶪相望。
首句即言此山为南岳,故诗中多用南方意象与典故。杜集中,题为 “ 望岳 ” 诗有三首,分别为《望岳》(岱宗夫如何),《望岳》(南岳配朱鸟)及《望岳》(西岳崚嶒竦处尊),分咏泰山、衡山、华山,《英华》所录此诗位于地部 “ 南岳 ” 之下,杜诗原题 “ 望岳 ” 所指有三首,若采用原题则所咏山岳指代不明,故将杜甫咏南岳的《望岳》诗题扩充具体为《望南岳山》,如此改动则诗题更切合本卷内容。又如广为流传的《蜀相》一诗,《英华》卷三二零题作《蜀相庙》,此诗为杜甫始达成都谒武侯祠而作,浦起龙曰: “ 因谒庙而感武侯,故题止云‘蜀相’。 ”[13]615故此诗重心为感怀武侯其人,并非吟咏蜀相庙。然此诗收录于《英华》郊祀类 “ 祠庙 ” 之下,若直书原题,则 “ 蜀相 ” 与 “ 祠庙 ” 并不切合,故于题后着一 “ 庙 ” 字,使之切题,且杜集中另有《诸葛庙》一诗,《英华》编纂者或依此改题也未可知。
《英华》对杜诗诗题进行增补多集中于卷三三一至卷三五零 “ 歌行 ” 类中。《杜集》卷二《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英华》卷三三六题为《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行》,后者比前者多出 “ 行 ” 字,因此诗收录于歌行 “ 酒 ” 类之下,诗题中须同时体现 “ 歌行 ” 与 “ 酒 ” 两个要素, “ 酒 ” 已表现在诗题中的 “ 宴饮 ” “ 醉 ” ,而大题 “ 歌行 ” 的文体要求在杜诗原题中未有直接体现,故《英华》编纂者于原诗题后加一 “ 行 ” 字以突显其为歌行而非近体的文体特征;与此类似的如《英华》同卷 “ 酒 ” 《晦日贺兰传杨长史筵醉歌》一诗,《杜集》卷一题作《乐游园歌》,题下注曰 “ 晦日贺兰杨长史筵醉中作 ” 。此诗两题在字数与内容上差异较大,实为《英华》编纂者的有意改动,将更为切题的题下注录为诗题。从总集编纂者对诗题的随意更换与改动,可见其对作品秉持的 “ 权力 ” 之大。
(三)置换语词
《文苑英华》对杜诗诗题的类化还体现在其对杜诗诗题语词的更换及顺序的调动之中。《杜集》卷九《上韦左相二十韵》,《英华》卷二五一题作《投赠韦左相》,后者将原题中的 “ 上 ” 改为 “ 投赠 ” ,标明诗歌句数的 “ 二十韵 ” 也不见录。此诗位于《英华》 “ 寄赠 ” 类之下,故其对诗题语词的改动乃是为切合大题 “ 寄赠 ” 之举。又如《杜集》卷一《天育骠骑歌》,《英华》卷三三九作《天育骠图歌》,此诗首句为 “ 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今之画图无乃是 ” ,则其诗所咏对象为骠骑图,此诗位于歌行 “ 图画 ” 类下,故《英华》将 “ 骠骑 ” 改为 “ 骠图 ” 乃是为切题而作,且较原题更为精准。再如《杜集》卷十八《铜官渚守风》,《英华》卷一五六题作《守风铜官渚》, “ 守风 ” 二字的顺序在两书中的位置稍有差异,检阅其余宋元本杜集皆与《宋本杜工部集》一致,作《铜官渚守风》。此诗于《英华》中位于天部 “ 风 ” 之下,既然无其他文献的异文,则此处的差异可能为编纂者为了使 “ 守风 ” 切合题目 “ 风 ” 的要求做出调整,从而将其位置提前。
四、类化之外的诗题异文
《文苑英华》杜诗诗题除以上所言诗题与题下自注混同及类化目的的人为改动两种情况外,还保留着纯粹的杜诗诗题异文。如《杜集》卷十三《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英华》卷一五五天部作《院中晚晴省西郭茅舍》,《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杜工部草堂诗笺》《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除于 “ 院中 ” 下注 “ 一作‘使院’ ” 外,皆无有与《英华》同例者。从此诗的创作背景来看,黄鹤将此诗系为 “ 广德二年秋作 ” ,时年严武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杜甫从阆州返回成都客于严武幕下。院,即节度使署府,西郭茅舍,即成都西郊杜甫浣花草堂,实为两地,齐翀曰: “ 此公不乐居幕府而作。盖公抱用世之志,而羁栖幕府,束缚蹉跎,抑抑不自得,因自笑其吏非吏,隐非隐。托于花者,旨远词文,诗人之义也。 ”[14]3266据诸家注解及杜诗文意来看, “ 怀 ” 更能表现杜甫由于仕途抑塞的郁闷心境而唤起对草堂隐居生活的遥思,强作自我疏导,故 “ 怀 ” 似乎比 “ 省 ” 更为妥帖。
又如《杜集》卷十八《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英华》卷一五五天部题作《舟中夜雪怀卢侍郎》。卢十四侍御,即卢岳,《杜甫全集校注》引黄鹤言曰: “ 盖公又有《舟中怀卢十四侍御弟》云‘朔风送桂水’,则是其冬在潭州作。卢侍御乃公之祖母卢氏姪孙,故呼为弟。 ”[14]5901《英华》卷九三九穆员《陕虢观察使卢公墓志铭》曰: “ 有唐贞元四年,夏六月,陕虢都防御观察转运等使、陕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范阳卢公寿六十……府君讳岳,字周翰……以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始佐湖南观察之政……既真拜,又稍迁殿中侍御史。 ”[15]4936可知卢岳曾为侍御史。按唐制, “ 侍御 ” 可为御史台三院官职之别称,唐赵璘《因话录》卷五言: “ 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见宰相及台长,则曰某姓侍御,知杂事,谓之杂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三曰察院,其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监察。 ”[16]98由上可知,卢岳任监察御史,杜甫诗题称其为 “ 侍御 ” 则为唐人习见用法,与历史及卢氏身份相符;唐代侍郎为尚书之副,官阶高于监察御史等职,考《陕虢观察使卢公墓志铭》可知卢氏未曾担任侍郎一职,且杜甫同时期潭州诗《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亦作 “ 侍御 ” ,故此处诗题应以《宋本杜工部集》为是,《英华》误。
再如《杜集》卷十《紫宸殿退朝口号》,《英华》卷一九零朝省 “ 趋朝 ” 作《紫薇殿退朝口号》,紫宸殿为大明宫三殿之一,《唐六典》卷七云: “ 宣政北曰紫宸门,其内曰紫宸殿。 ” 注云: “ 即内朝正殿也。 ”[17]77《新五代史》卷五十四《李琪传》曰: “ 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阁。 ”[18]618可见紫宸殿为唐代群臣上朝之地。北宋前期东京朝会六殿之一崇德殿,于明道元年(1032)更名为紫宸殿,《英华》成书于雍熙三年(987),此时崇德殿尚未改名为紫宸殿,故《英华》编纂者或因疏于唐制而有可能将 “ 紫宸殿 ” 误录为 “ 紫薇殿 ” 。
例四,《杜集》卷七《西阁曝日》,《英华》卷三一四居处 “ 阁 ” 作《西阁曝背》,今录其诗如下:
凛冽倦玄冬,负暄嗜飞阁。羲和流德泽,颛顼媿倚薄。毛发具自私,肌肤潜沃若。太阳信深仁,衰气歘有托。欹倾烦注眼,容易收病脚。浏漓木梢猿,翩翻山巅鹤。明知苦聚散,哀乐亦已昨。即事会赋诗,人生忽如错。古来遭丧乱,贤圣尽萧索。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
此诗为大历元年杜甫居西阁时所作,首两句点题, “ 飞阁 ” 即高阁,此指西阁, “ 负暄 ” 即背向日,此即《英华》所题《西阁曝背》之由来。然全诗并非只是曝背,第五、六句 “ 毛发具自私,肌肤潜沃若 ” 为冬日晒太阳全身产生的温暖舒适之感,仇兆鳌于九、十两句下注曰: “ 毛发六句,皆德泽之浃身者。注眼、收脚,坐久而起行也。地倾注视,恐脚病偶蹉,忽而举步容易,则暖气流畅于足矣。 ”[19]1563此后的 “ 浏漓木梢猿,翩翻山巅鹤 ” 则为诗人远望所及之景象,而猿之浏漓,鹤之翩翻,皆与冬之 “ 曝日 ” 这一情境相关,故此诗以 “ 曝日 ” 为题更能兼容全诗诗义。纵观历代杜集版本,除《英华》外皆无以《西阁曝背》为题者,此诗题或为编纂馆臣据首句改题亦未可知。例五,《杜集》卷三《羌村》(题下注 “ 三首 ” ),《英华》卷三一八居处 “ 村墅 ” 作《荒村三首》。《杜甫全集校注》云: “ 黄鹤曰:‘此诗当在至德二载秋,至鄜州时作。’蔡梦弼曰:‘《鄜州图经》:州治洛交县。羌村,洛交村墟也。’羌村旧址在今陕西省富县茶坊镇大申号村。 ”[14]934富县,即古之鄜州,可见《宋本杜工部集》所题之羌村确有其村,此乃实指,而非《英华》所题 “ 荒村 ” 之不定指,此盖为 “ 荒 ” “ 羌 ” 字形、字音相近之误;然此诗所写确为羌村荒凉之景,其一 “ 柴门鸟雀噪 ” ,久荒而鸟雀至也;其三 “ 群鸡正乱叫 ” “ 黍地无人耕 ” 所写正是农村破乱、园田荒芜之景,故若从内容上看,题作 “ 荒村 ” 亦无不可。
五、选录杜诗诗题异文之原因
《文苑英华》选录杜诗诗题异文之成因,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早期杜诗文本以抄本形式传播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异文作为原始文本的衍生形态,本是任何传世文献都无法规避的结果,且在二王本《杜工部集》编刻之前的唐五代至宋初,杜集赖以流传的主要形式是手抄本而非刊刻本,五代后晋开运(944—946)官本有可能为杜集首次刻本。据李贵先生研究,王琪于嘉祐四年(1059)在苏州刻印《杜工部集》前后,北宋人阅读的杜集在21种以上,而这些杜集版本的特点之一即 “ 俱为写本,文字多歧 ”[20]211-212,可见此时杜诗异文之多。相较于刻本,抄本更容易滋生异文, “ 由于同一版的印刷书籍全都一模一样,印刷可以限制异文数量的产生;与此相比,每一份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可能产生新的异文,这样一来,比起印刷文本,手抄本就会大大增加异文的总数 ”[4]8。抄本时代,作品一经作者之手产生,其后的流传过程便是一个文本 “ 失控 ” 的过程,身份各异的读者出于偶然或必然的原因,参与了作品的再创造,而再创造的成果,将以再次传播的方式实现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文苑英华》成书早于王琪刊刻杜集七十二年,其书编纂者以资参校的杜集应多为抄本,故《文苑英华》中诗题与题下自注混同及类化之外的诗题异文即体现了杜集文本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此种异文在杜诗校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在从不同维度提供关于杜诗诗题的信息,有助杜诗的整理和校勘,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仇兆鳌在校勘杜诗的过程中就曾参考了《文苑英华》收录的杜诗,今人编《杜甫全集校注》也把《文苑英华》作为宋代杜集重要版本之一。但由于《文苑英华》篇幅巨大,且集中在较短时间内成书,编纂人员又几经调动,在诗题及文本文字上难免会产生疏漏和阙虑之处,部分异文乃为编撰者讹误生成,需要加以辩证地看待。
原因其二,异文的产生很可能为《文苑英华》编纂者对杜诗诗题的有意整改。《文苑英华》对诗题所做的整改,在总集编纂中实为常见现象,程章灿先生曾分析过总集对选入作品的改动: “ 总集之名,无论是‘总’还是‘集’字,本身已意味着某种汇聚整合的权力。在汇聚整合的过程中,总集并不只是简单的抄录,也不只是单纯的选取或汰除。实际上,在编辑过程中,总集不仅对诗题进行整合与类化,甚至为了切题而对诗歌文本进行某些剪裁。 ”[5]总集所录诗题未必尽出作者之手,有可能为后人拟题,从而影响我们对诗歌之题材、类型、风格、主属、作者创作倾向等的认定与理解。《文苑英华》编纂者对杜甫诗题的改动正好体现了总集强加于作品之上的整合与类化之力,其所追求的是人为构建的文本秩序而非还原文本的 “ 真 ” ,原始文本须服从于类编总集以类选诗的规则与秩序之下。而总集赋予编纂者行使的 “ 文学史权力 ” ,最终可能影响后世对杜诗诗题的接受与理解。据吴承学先生所言,杜甫诗歌制题风格大致有精致与漫与两种,前者承六朝而来,后者颇有先秦汉魏诗题遗风。杜诗制题按体量可分为长题与短题,前者细叙情事,体兼诗序,下开宋人长题之风;后者或精到准确,或摘取随意,为李商隐无题诗的先河。杜诗拟题之法,既是传统制题艺术之集大成,也是对此前规范的突破,体现出杜甫独特的美学追求[12]73-75。《文苑英华》编纂者对杜甫诗题的类化与改动在此后的杜诗接受史中无疑会以总集的优势影响后世杜诗诗题的接受,如宋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 “ 技艺部 ” 录有杜甫《天育骠图歌》;清康熙年间官修大型辞典《佩文韵府》,其卷四十六之一及卷九十三之一引杜甫《望岳》(南岳配朱鸟)一诗皆题作《望南岳山》,显然参考《文苑英华》的诗题著录;且诗题的改动还可能干预后人对杜诗题类型与风格的体认,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解。
注释:
①目前学界关于《文苑英华》选录杜诗研究仅见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冯淑静《<文苑英华>所录杜甫诗歌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对《文苑英华》所选杜诗的基本概况进行了数据统计,其结果为 “ 在数量上杜甫和李白并居第二 ” ,随后该文分体对所选五古、近体、七古从内容主题和风格展开基础的分析;王茸《<文苑英华>选录杜诗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一文从题材、内容、风格、体裁对所选录杜诗进行分析和总结,得出宋初杜诗的接受乃于白体诗风的辐射下进行此一结论。
②学界对杜诗异文成因总结的论文还见胡绍文《杜诗异文辨析》(《求索》,2008年第9期),该文列举杜诗异文产生的四种原因并举例说明;从文化层面研究杜诗异文的有胡绍文《杜诗异文所折射的文化现象》(《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透过杜诗异文分析其背后所折射的社会文化信息,及阮丽萍《杜诗异文传播中的本色保存与文化增殖》(《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将杜诗异文现象视为杜诗文化价值与意义增殖的过程;涉及杜诗异文考辨的有李成晴《<翁批杜诗>对杜诗异文的考辨》(《杜甫研究学刊》,2015第4期)、陈道贵《杜诗异文考辨二则》(《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1期)等文。
②林心治认为,《文苑英华》将 “ 歌行 ” 独立于 “ 诗 ” 的原因有三:其一,编录者已注意到这类诗歌具有不同于传统古体诗和乐府诗的独特品性,不宜与之混同;其二,表明编录者对唐代歌行大兴、成就斐然事实已有明确的体认;其三,表明编录者对白居易等人提出的 “ 歌行 ” 诗体新概念的赞同,见《<文苑英华>歌行体性辨》,《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另,关于歌行的起源及其与乐府的区分,参见葛晓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论著。
③据何水英(《<文苑英华>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统计,《文苑英华》收杜诗194首,此数据未包括杜甫的歌行之作;冯淑静统计《文苑英华》选录杜甫诗194首,歌行52篇,共246首。据其自述,歌行各门类选诗数量分别为 “ 天部1首,四时1首,征戍1首,音乐1首,酒5首,草木1首,书1首,图画5首,杂赠4首,送行3首,山3首,石2首,佛寺1首,楼台宫阁1首,纪行1首,兽5首,禽4首,杂歌9首 ” ,然各类相加实为49篇,冯统计有误;王茸统计《文苑英华》选录杜诗176首,歌行52首,共228首。其各类选诗相加结果虽无误,然其诗部统计杜诗多有遗漏,如天部、地部、人事、乐府、寺院、居处六个门类均有所阙;且二人均未减去 “ 歌行 ” 中重出的5首杜诗及《九日登梓州城》题下误收的张均《九日巴丘登高》一诗。
④据凌朝栋考证,《文苑英华》的文献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一、从后周宫中藏书继承下来的图书;二、从削平后的各割据政权获得的图书,其中最多者是南唐与后蜀;三、下诏征求与抄写图书;四、借助其他工具书如《唐登科文选》。见其《<文苑英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