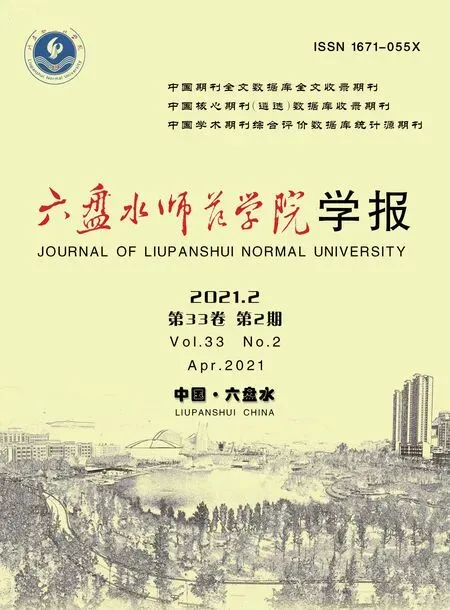清末川剧《贪欢报》研究三题
2021-12-28巫宁
巫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0)
《贪欢报》又名《孝女坊》《九人头》,但实际上,《孝女坊》为《贪欢报》的前本,是川剧公案戏之传统剧目。依据《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及《中国曲艺志·贵州卷》等文献记载,除川剧外,贵州弹词和楚剧存此剧目。1949年后,许多传统剧目被改编,《贪欢报》亦列于其中,改编本被收入《川剧传统剧目选集》第7辑中出版。与川剧《贪欢报》剧情相类的贵州弹词《贪欢报》与楚剧《九人头》也有着相同的命运,惜今已难见早期楚剧与贵州弹词本《贪欢报》的样貌,而川剧原本却得以留存,《俗文学丛刊》所收录的《贪欢报》为现今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全本,具有较高的文学与文献价值。
《俗文学丛刊》所存录的《贪欢报》属刻本,分为上下两本,页码为267-373,皆白口,黑鱼尾。上本封面竖题大字 “ 九人头 ” ,首页右侧竖题 “ 贪欢报 ” ,首页右下位置处有篆形方章。每半页十行二十一字,上书口题 “ 贪欢报 ” ,书口下题页码,内容包括 “ 看灯散闷 ” 至 “ 诉情哭别 ” 十个部分。下本为福记木刻本;封面有花形图纹边框,中心竖题大字 “ 贪欢报 ” ,字下以略小字号自右往左书 “ 全本 ” ,左侧以小字竖题 “ 批发处福记 ” 。在正文首页右栏上方自右往左横题 “ 九人头 ” ,下以大字竖题 “ 贪欢报 ” ;每半页十行二十六字,唱词停顿处由空白隔开。
一、情节关捩与 “ 果报 ” “ 奇孝 ”
《贪欢报》的情节关目包括三次捩转。男女风月造成的人命大案是《贪欢报》的第一重情节,陈金贵冒吴廷秀之名与杨凤姣花园相会,因误会凤姣与人有私,愤而取下卧寝凤姣房中的朱朝佐夫妇的首级、并藏于南门外梧桐树下。禁卒与桂姐掺入案件使得情节关目出现了第二次捩转,桂姐之 “ 奇孝 ” 成为《贪欢报》第二层情节的重点,县官一番盘查之下,将并不知情的吴生下到狱中,侄女桂姐随母探监,听信狱卒 “ 只要有头首便可救叔 ” 的胡言,归家后自缢献头救叔。县官为桂姐孝行所感动,认为案件存在冤情,决定重新勘察。桂姐之孝行让案件有了转机,将剧情引向更为错综复杂的境地。禁卒恶行的绞入造成了情节关目的第三次捩转, “ 果报 ” 为此重情节所昭示的事理。禁子先是胡言误引桂姐献头,后又因贪赏杀害无辜,使得案件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最后窃贼陈七七的突入,窃出关键罪证定罪陈金贵,恶魁禁卒也得到了应有之报,至此,这场疑窦丛生的凶杀案终于拨云见日。总的看来, “ 奇孝 ” 与 “ 果报 ” 成为《贪欢报》三次情节转关的突出之义。
该剧本事不详,渊源已不可考,今所见最早刻本为日本东京大学双红堂文库①所藏清同治十二年梨花街文义堂所刻之《孝女坊》,实为《贪欢报》之上本,与俗文学丛刊本《贪欢报》仅在字句上有细微差别。此外还有民初时期的刻本十余种②[1],据此推测,该剧最迟产生于清末同治年间。故事本源亦难考证,今有部分戏曲与之相类。
首先是题名为 “ 报 ” 、宣扬因果报应的戏曲,如叙徐生钱贪吞妻弟家产,又诬陷其杀人致使发配,最终自身得报倒毙的清末传奇《三缘报》③;叙占寡嫂家财并欲杀害侄女的赌棍薛光耀得报被雷劈死的温州乱弹《雷公报》;讲述两兄弟屠牛而为牛索命,来世投胎牛腹的《屠牛报》④[2];讲述义犬报恩,使谋夺主人家财又设计冤狱的无赖王恩得到恶报的《恩怨报》;以及讲述安道全贪欢,而被张顺使计,被迫上梁山医治宋江的同名水浒戏《贪欢报》等。此类剧作均产生于明清时期,以宣扬果报为己任,叙悲欢离合,描摹人情事态,间或穿插审案线索。而此本《贪欢报》以风月姻缘为主线,人命大案牵涉其中,清官断案在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这类以 “ 报 ” 为名的戏曲中独树一帜。
其次是以 “ 孝 ” 为主题的戏曲,《贪欢报》以大量的篇幅讲述桂姐舍头救叔的情节,反复渲染其孝行,从双红堂所藏之前本《贪欢报》被命名为《孝女坊》也可窥见该剧 “ 孝 ” 的主题。自古以来民间孝戏流行,宣扬孝道的目连戏演出遍及全国,早至南宋时期,《东京梦华录》便有 “ 自过七夕,便搬演目连救母杂剧 ”[3]的记载。明清两代,最高统治者提倡顺孝文化,明太祖言孝为风化之本;清代皇帝也奉 “ 孝 ” 为圣训,并以孝治天下[4],在官方的鼓动下,出现了大量宣扬 “ 奇节之孝 ” 的戏曲[5],如明成化年间邱浚的《伍伦全备记》、隆庆年间高濂的《节孝记》、万历年间沈璟之《十孝记》,清代的孝道剧更是不胜枚举:如叙黄向坚徒步万里寻父的《万里圆》,叙双娥刺血书佛经、割股疗母、尽孝自缢的《兰桂仙》,割耳拒强娶以尽孝的《四美记》等。这类剧作借割股、剪肉、埋儿等极端孝行以宣扬顺孝理念,以起到教化百姓之功用,从这点看来,《贪欢报》在愚孝之行上与此类戏曲别无二致。但从 “ 奇孝 ” 的对象上来看,此类孝戏均为侍奉父母,而《贪欢报》却着力表现桂姐 “ 孝叔 ” 之举。在各种戏曲、小说、民间故事中, “ 孝叔 ” 情节较为少见、而该剧中桂姐不顾及 “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 的传统观念,其对叔叔的孝让步于侍奉母亲的意念,这与传统的孝行戏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此外,讲述因恶人冒名私会而错斩人头的戏曲也有迹可循,如京剧《法门寺》,剧中有媒婆之子刘彪恋慕玉姣夜至其家中,误会玉姣与人有私而误斩玉姣舅父母人头引发人头案的情节;另外冯梦龙之《智囊》所载 “ 临海令 ” 条目下叙卖婆之子冒充书生夜往与女相会,因女子房中客舍一对夫妻,便断二人首级而去的案件[6],这与《法门寺》《贪欢报》剧情有相类之处;再如同为川剧的《三匣剑》在故事开头也与《贪欢报》有着相似的情节:该剧叙述吕三官与车二姑于途中邂逅,一见倾心,被冯氏旁窥,冯氏之子听母亲谈及此事,便冒吕三官之名来会车二姑,第二晚带剑闯入车家误杀二姑之姐姐与姐夫,从而引起一连串的凶案故事。
《贪欢报》《法门寺》《三匣剑》均以恶人冒名顶替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相会,又因女主人公房内卧寝他人而误以为女主人公与人有私,愤而杀人,从而致使男主人公冤诬受害,引起之后的清官断狱与其他情节。但此后故事的开展,《贪欢报》与二剧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与风情:《法门寺》所着重展现的是巧姣之智慧勇敢及皇室权臣对冤情的洗刷;《三匣剑》着意于展现侠客之行侠除恶与公衙断案形成合力、斩恶除奸[7];而《贪欢报》虽在风月故事与公案的组合上与二者相类,但具体的情节开展及故事主题却大相径庭。该剧以冒名杀人之固定模式,糅合进明清时期流行的奇孝故事与清官勘狱线索,没有上至宫廷权臣、下至江湖侠客如此广阔宏伟的社会图景,它所描绘刻画的人物都是下层官员与底层百姓,真实地再现了普通百姓在政治上权利的缺失,被冤诬受害后生命任人宰割的现实情境,以及表现底层百姓对司法之陌生以及市井无赖的贪婪、愚昧及罪恶,因此在同类故事中有着不同寻常的风貌与品质。
二、剧本特色与故事意趣
从语言上看,该本《贪欢报》具有浓郁的地方性色彩,叠词的使用与方言谐音、俗语的运用是其鲜明的表征。好用重字叠语是西南地区如四川、贵州等地方言的特色之一,文本中有着大量的叠字叠语,如 “ 圈圈 ” “ 竿竿 ” “ 边边 ” “ 罐罐 ” 等。此外,还有许多方言俗语、谐音的使用,一类是富有乡土风味,贴近市井生活的称谓,如 “ 娘母 ” (母女)、 “ 娘屋 ” (娘家)、 “ 叫化婆 ” (乞丐婆)等。另一类是以谐音表示的方言如 “ 不消 ” (不必)、 “ 房圈 ” (房间)、未存(未曾)、 “ 吃活 ” (吃喝)、 “ 伸唤 ” (呻吟)等。此外还如 “ 天色尽了 ” (天黑了)、 “ 好多 ” (多少)、 “ 烧烟 ” (抽烟)、 “ 丧德 ” (作孽)、 “ 完求了 ” (完了)、翻稍(回本)、 “ 溜得很 ” (滑得很)、 “ 二一世 ” (下辈子)、 “ 张格 ” 等较为独特的方言表达。这些方言俗语的融入,不仅显示出以四川、贵州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市井观众的审美口味,还使得剧本亲切活泼,俏皮幽默,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喜剧风味,显现出《贪欢报》面向俗众、俚俗浅显的 “ 俗文学 ” 品格。
在人物角色方面,该剧主要有旦角、生角与丑角,其中旦角扮演有杨凤娇、王氏及喻金花,生角扮演吴廷秀,丑角扮演命案真凶彭金贵、禁子及窃贼陈七七。值得注意的是,剧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两个人物——桂姐和县官,文本中均未说明由何种角色扮演,在部分场次还出现生角、丑角以姓代指的情况,这种现象可能与早期《贪欢报》剧本形制不完善有关。
此外,剧中的各色人物均切合现实,多棱立体,并且沾染上了浓厚的地域色彩,其中人物展现出蜀地儿女生动鲜明的性格特征,也折射出川地普通民众的审美价值取向。如剧中女主角杨凤姣,因灯会上对吴生一见倾心便立刻主动出击,修书与生相会以谋划二人终身大事,其书信云:
……恐终身配作那无志儿郎,修书信约今晚花园来往,
以拍掌为会处通知情详,奴不是许姻亲送赐银两
皆因是秋桂月去赴科场,作路费奴愿你名登金榜
请媒来与母亲说合天长,奴沾你洪福恩泽光万丈……[8]353
凤姣之大胆之举虽于礼有违,但其书信却有节有度,既直接表明自己对吴生的情意,又丝毫不显得放肆轻浮。书信中言赐银之举并非是因 “ 许姻亲 ” ,而是为了助力吴生金榜题名,行文措辞得理,既尊重了吴生的感受,亦表现出风姣热心有义、心思缜密的性格特征。
凤姣不仅果敢有勇、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还深情重义,泼辣赤诚。在知晓因自己的书信引出祸端、造成吴生的侄女桂姐丧生后,毅然自尽;在得知吴生将罹受灾祸之时又抛去前嫌,化为魂魄前去搭救,从中足见凤姣对爱情的坚贞与勇敢。凤姣与吴生二人感情虽因凶案而几经波折,但最终仍有情人终成眷属,展现出蜀地观众对冤案昭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期许。
再如桂姐的孝义形象的塑造亦十分成功。孝女桂姐因年幼无知,误信禁子 “ 有头便能救叔 ” 的戏言,悬梁自尽,留下血书舍头救叔。 “ 修书自缢 ” 一场中桂姐义行感人肺腑:
(唱)……儿同母亲把叔望,禁子伯伯说端详
若有人头命不丧,若有人头相抵伤
你儿归家自思想,因此小房去悬梁
恐当着遇邪那遭枉冤望母亲切儿人头到公堂
大老爷见头必要放,搭救叔爹出监墙
二封书拜上多拜上,叔叔叔叔看端详
不幸爹爹命早丧,堂前丢下寡母娘
你儿一死会别望,另眼看照母亲娘
肚饥与娘把饭赏,冷来与娘添衣裳,
莫做人在人情在,人死恩情一旦忘
倘若叔爹出罗网,与儿接个二婶娘,
叔爹若把儿思想,衣架上还有两件旧衣裳
血书本得多写上,血手疼痛语又长
若要侄儿重相望,除非南柯梦一场[8]314-315
桂姐之血书虽质朴无华却感人肺腑,其孝叔义举可谓感天动地,义薄云天。桂姐所修第一封书写给母亲以陈明事由,第二封书写与吴生,期盼叔叔今后善待母亲,文辞简明,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两封血信将三人间深挚的情感及桂姐之赤诚孝顺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桂姐的 “ 孝 ” 更接近于蜀人所尊崇的 “ 义 ” ,孝义的结合正体现出蜀地百姓的价值追求。
此外,《贪欢报》的丑角亦颇有特色,剧中丑角并非脸谱化、平面化的功能性人物,而是立体饱满,鲜活生动的人。彭金贵、禁子以及窃贼陈七七三位丑角皆以调笑为职,以自我暴露、讽刺揭露为目的,即使是作为反面人物,但亦有着良善的一面。其中彭金贵虽为杀人真凶,但却并非自始至终都是穷凶歹恶之人,他对同窗吴生彬彬有礼,对吴生之女桂姐亦是爱护有加。禁子对犯人并不施以虐待盘剥,对于身陷囹圄的吴生及前来探望的桂姐母女亦是以礼相待;陈七七虽为窃贼,但性格天真活泼,十分有趣。这种多棱立体的形象塑造更加贴合实际,为蜀地普通民众所亲近,符合现实真实。
从砌末道具上看,该剧的主要道具有 “ 书信 ” “ 六指 ” “ 人头 ” “ 金匣 ” 等,其中,其中 “ 六指 ” 与 “ 人头 ” 比较特殊。严格说来,六指作为一种生理畸形,本不应属于砌末的范畴,但在《贪欢报》中,六指对于推进戏剧情节、帮助演员完成表演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剧演中需要演员穿戴装饰,因此亦属于 “ 随身砌末 ” 。 “ 人头 ” 亦为该剧中较有特色的道具,一般说来,为避免观众感到血腥与恐惧,人头一般会用红布包裹或以无翅纱帽戴替代。经统计,在整个剧作中,作为砌末道具的凤姣之书信共出现三次,六指出现两次,人头出现三次,金匣两次。
川剧善用道具伏脉,此剧的砌末每次出现均串联起闺中女子、书生、窃贼、乞丐等各色人物并推动剧情的一次次突转。首先是金贵 “ 六指 ” 砌末的设置。六指砌末并未在彭金贵一出场时便予以说明,而是在其冒名吴生与凤姣相会之时,通过凤姣之口才予以点出。借凤姣之眼窥见六指为后文县官二审凤姣时供出此细节并以此定彭生之罪做好铺垫。其次是人头道具。禁卒的一番胡言,让年幼的桂姐献出自己的头首,尔后狱卒为冒领赏银又滥杀无辜取得两个头首。这三颗与原来案情无关的人头作为剧中的重要道具,其出现让原本出现转机的案情再次陷入僵局,促成了案中含案的连环套层结构,使得剧情得以悬置,跌宕起伏。最后,书信砌末的设置也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作为剧中重要砌末的凤姣之书信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时现时隐、辗转于多人之手,先是被丫鬟遗失,再被金贵拾得使之产生犯罪之念引发命案悲剧,又兜兜转转被陈七七窃走,最后又被带到公堂之上,成为案情得以水落石出的重要物证。书信的离奇再现使之成为巧合的连接点,将彭金贵与凤姣串联起来,得以引起县官的注意,带出原本隐匿在暗处的彭金贵,从而使得吴生无罪开释,善恶得报,天理得彰。不仅如此,在这场疑窦丛生的凶杀命案之中,一封小小的书信竟能引发凶案,最后又四两拨千斤地巧解命案真相,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在鸿毛之轻与沉重命案间形成极富张力的叙事趣味。
《贪欢报》中砌末道具独具匠心的设置与使用,令剧情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使得戏剧得以在家庭、公堂与社会间游走,显现出底层小吏与百姓的妍与媸、愚与恶,更为全面地再现了社会底层的样貌与生态。
三、《贪欢报》与元宵剧演民俗
元宵节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具有热闹性与狂欢化的特征。正如陈熙远所言: “ 元夕纵容人们逾越各种风教俗成的甚或法律明定的界域,颠覆一切日常生活的规律——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雅俗之分到贵贱之别。 ”[9]人们于元宵节释放个性,僭越礼俗,纵情欢乐。观灯、祭祀、宴飧等均为人们庆祝灯节的重要活动,同时,剧演也是元宵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元宵节素有剧演的习俗,早在明代,便有关于四川地区元宵演剧的记载,如 “ 元夕张登放花结彩棚,聚歌儿演戏剧 ”[10],清代以后,四川地区 “ 灯戏 ” 开始繁盛,灯戏成为元宵必演节目,乾隆时《苍溪县志》载: “ 上元放花灯、演灯戏。 ” 可见灯戏已成为元宵节演剧的习俗,同治时期《新宁县志》中亦有 “ 惟元宵前后,竟尚灯戏 ” 的记载……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知蜀地元宵节日剧演活动的郁勃。《贪欢报》不仅描绘出社会底层各色人物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现了众生百态,还为我们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清末民初四川地区的元宵剧演情况及民俗文化。
《贪欢报》中,元宵节作为戏剧的开场时间,亦是戏剧情节推进的重要背景。 “ 大放花灯 ” “ 看灯散闷 ” 两场戏皆设置为正月十五元宵灯节,戏剧的重要情节皆缘起于剧中人物元宵赏灯的活动。吴生带桂姐赏灯以排遣愁怀;凤姣在这晚冲破礼俗防线,大胆追求自主的爱情,修书邀生花园相会;金桂亦于该日生出歹心,露出其罪恶的一面……在元宵狂欢的特殊背景下,不同人物的真实性情得以展露无遗,而在血腥凝重的死亡悲剧尚未发生之时,街上却是好一片繁华热闹之景象,在 “ 大放花灯 ” 这场戏中穿插着一段看似与情节无涉的吹打乐:
你们办(扮)的是啥?
介:扮的大排朝。
介:大排朝有皇帝,就等你们皇帝先上
(上皇帝唱戏)
王出宫又只见锣锅罐罐两廊下摆的是鸡毛竿竿
樵楼上是王的金銮宝殿十八间任心随驾游两边
五朝门两岸上文武参见议事亭设朝房大墙边边
花子营是王的三宫六院孤老院是王的历代祖宗
王食的珍馐味苕叶稀饭王穿的大红袍席子秧廌
腰拴着玉扣带温江钱吊头顶着九龙冕草帽圈圈
脚穿着满朝靴过江袜线王又把快乐处细表一番
炎热天避暑亭樵楼下面寒冬天羔子皮火龙当先
这是正享清福难以并及历代来祖宗辈须表祥端……[8]278-280
该段作为 “ 戏中之戏 ” 存在的吹打乐曲牌为 “ 大排朝 ” 。 “ 大排朝 ” 主要应用于一些活泼欢快的场景,通常以锣鼓唢呐伴奏,于此处烘托元宵佳节热闹气氛恰好适宜。从形式上看,该段乐词以十字为一句,总共三十四句,类似民间的 “ 打油诗 ” 。从内容上看,主要是铺叙皇帝出宫之所见所闻、其吃穿用度、衣着服饰以及所喜所忧,似乎与戏剧的剧情发展无涉。剧本以大量的篇幅来铺排这段游离于情节之外的戏中戏,让戏剧时间在此刻停滞,看似不利于剧情的纵向发展,但却能够烘托元宵佳节闹热、狂欢、躁动、混乱的氛围,为后文凤姣冲破礼教防线修书与生、彭金贵心生恶念埋下伏笔,还有利于戏剧的悲喜跌宕、冷热调剂,亦有助于我们横向挖掘《贪欢报》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及所传递的民间话语的价值取向。
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论述在节日中国王成为被群众嘲弄殴打的对象时言: “ 如果说人们一开始把小丑打扮成国王,那么现在当他的王国结束后,人们又给他‘滑稽改编’成小丑模样。 ”[11]从《贪欢报》中以插科打诨的丑角扮演九五至尊的帝王的角色设置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狂欢化场景的荒诞与滑稽。狂欢化式的世界感受、狂欢化的氛围进入文学中,暂时取缔社会等级,建立起别具一格的、民间诙谐的 “ 狂欢式 ” 世界[12]。文本中的皇帝尊严与高贵不再,他吃的是 “ 苕叶稀饭 ” ,戴的是 “ 草帽圈圈 ” ,住的是 “ 花子营 ” ,拜的是 “ 孤老院 ” ,喜的恨的皆为市井琐事,而无关江山社稷,且语言俚俗,与其帝王身份间形成极富张力的权力空间……在《贪欢报》民间话语的叙述中,皇帝已然被拉下神坛,成了普通民众消遣的对象。而川剧中此类解构帝王权威的剧目比比皆是,如叙述 “ 正德微行 ” 故事的《周元献鸡》《皇帝访贤》与《皇帝打烂战》等,这些戏剧皆为元宵剧演的常演剧目,其中的皇帝与《贪欢报》中的帝王一样, “ 从中心隐退,让位到了边缘 ”[13],成为被民间话语体系戏弄嘲讽的对象。在这类于元宵搬演的戏剧之中,代表着正统、权威的帝王威仪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滑稽、丑陋与狼狈。这正体现出元宵节狂欢的背景下,普通民众通过观赏这类俗化、贬低帝王戏剧的方式来表达对正统、秩序、规范的挑战与消解。
从历史上看,民间的这类搬演帝王的戏曲存在对权威的丑化、嘲弄的现象而屡遭官方明令禁止,如明嘉靖九年颁布禁令 “ 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谤仙古今,违者拿问 ”[14],对于常在元宵灯节搬演并蕴含不少 “ 违逆 ” 思想的灯戏亦被政府明文禁止: “ 禁止演唱灯戏,遏淫风也。……只宜演忠孝节义之事……乃川省另有所谓灯班者,所演多系淫亵屋里,备极形容,男妇聚观,毫不知耻,坏人心而导淫邪,莫此为甚。今责成地方官将灯班严行禁绝,毋许演唱。 ”[15]虽然官方试图以森严的禁令控制民间剧演,但事实上,这类民间剧演的分散性、临时性、隐蔽性使其自身很难受到约束与管控,反而愈演愈盛。而《贪欢报》产生于清末时期,流行于民国年间,清末社会动荡,思想松动,统治阶级更是无力钳制普通百姓的观剧剧演活动。并且,《贪欢报》所采取的将悖逆权威的元宵闹戏糅合进以孝义为主旨的戏剧之中,也反映了普通观众的多元价值取向。
四、结语
《俗文学丛刊》收录此《贪欢报》为民国初年之成都福记坊刻本,民间刻本直接面向社会俗众,直至20世纪30年代,普通民众在街头仍可随处买到这些通俗的刻本,说明这种坊刻本与民众生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贪欢报》所叙故事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才子佳人的风月爱情戏码,公案戏与爱情戏的结合、节日应承喜剧的穿插与大团圆的结局投合了百姓之喜好。戏剧本身无关庙堂之高、无涉江湖之远,完全为普通民众与底层百姓的真实写照,所刻画的人物也均为真实丰满的市井之民,为普通百姓所亲近,展现了社会底层百姓的妍媸百态与民俗风貌;人物唱词真朴活泼、通俗易懂,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对于了解清末民初蜀地民众的审美趣味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双红堂文库原为日本法政大学长泽规矩也先生积藏中国明清戏曲小说,后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 双红堂 ” 之名源自长泽规矩也先生曾得明宣德十年(1435)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崇祯本《新镌节义鸳鸯冢娇红记》,而小说《娇红记》一名《双红传》,遂名其斋曰双红堂。
②据《四川坊刻曲本考略》载民国年间成都和记书庄、成德堂、荣丰堂书局等曾刊刻过《贪欢报》十余种(刘效民.四川坊刻曲本考略[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203-206.)。
③清末成都剧作家罗梅江所作《红雨绿雪楼三种》之三。
④《屠牛报》有两个故事系统,此依《车王府曲本总讲》所载 “ 屠牛报总讲 ” (郭精锐等.车王府曲本提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