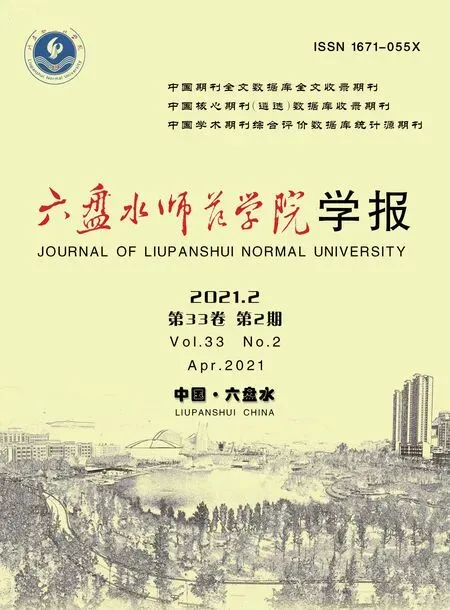师友对姚薇元史学素养的影响
2021-12-28韩笑笑
韩笑笑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姚薇元是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鸦片战争史见长。他的《鸦片战争史实考》[1]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鸦片战争史的基本读物,《北朝胡姓考》[2]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必备参考书[3]149-150。他遗留的学术遗著中,有一本《中国史学史概要》[1],该书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史学史,史学和史观并重。他还写有《廿四史解题》《中国近代史简编》《鸦片战争》等专著,发表40多篇学术论文[4]2。姚薇元能获得以上成就,除了自身刻苦研究,还与各位师友的教诲密切相关。对此学术界只有萧致治的《姚薇元教授的治学之道》[3]149-150和姚薇元几个学生的文章有论及,本文将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从姚薇元本科、研究生、工作时期的相关经历入手,就姚氏史学素养的形成与师友关系展开论述,以期能对历史学年轻学人提供借鉴。
一、本科时期:郭廷以、蒋廷黻、罗家伦引导姚薇元走入史学研究之门
1926年,21岁的姚薇元在高二时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于大二时(1927年)因对中国近代史产生兴趣转入历史系①。在本科期间,他在郭廷以、蒋廷黻、罗家伦等老师的教诲下,研究鸦片战争史,掌握了研究历史的基本能力。其本科毕业论文《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于1942年初次出版,载有蒋廷黻、郭廷以先后在1933、1935年为其所作的序言②。1955年,姚薇元对此书做了重要修改,改名为《鸦片战争史实考》[1],现在流通的是1983年校毕、1984年出版的修订本[3]149-150。
郭廷以于1928年9月随罗家伦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到清华大学第二年(1929年初)开始和罗家伦合开中国近代史课程。当时姚薇元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他为了弄清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先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史着手研究[3]149-150。当时,郭廷以上课的主题正是 “ 鸦片战争 ” “ 魏源的海防思想 ” “ 洋务运动 ” 等[5]142-143。姚氏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得以出版,与其在郭廷以课堂上的受教及私下请教有着密切关系,萧致治在回忆姚薇元的治学之道时所讲 “ 在郭廷以的帮助下,将研究成果汇编为毕业论文 ”[3]149-150应该指的就是这段学习经历。
应罗家伦邀请,蒋廷黻于1929年5月进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他曾经掀起历史系的改革浪潮,成为当时清华历史研究的中心人物[6]。作为老师,蒋廷黻曾将自己的著作及藏书借给姚薇元参考使用。1932年9月26日,蒋廷黻致罗家伦的书信中提到, “ 姚君借用书二部及拙稿一部(二册),已由邮挂号分三包寄呈,不日定可到沪矣 ”[7]185。另外,如前所述,1933年6月蒋廷黻曾为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作序,序中特别提到 “ 姚君薇元费了两年的功夫来考订这篇道光洋艘征抚记。他参考了很多的中西史料,把魏默深的原文逐句的加以研究……姚君这种工作可算有功于史学 ”[8]2。由此可知,蒋廷黻逐字逐句地阅读了其论文,他对姚薇元的指导是从初稿写作一直延续到书籍出版。
罗家伦给姚薇元的帮助主要体现于提供研究资料方面。罗家伦在1928—1930年间任清华校长和历史学系教授[9]。根据郭廷以回忆,当时的清华图书馆 “ 西文书不少,中文书很少,罗先生第一年就大买中文书,增加一倍不止 ”[5]142-143。罗家伦的这一行为并非专为姚薇元所作,但清华所藏丰富的鸦片战争史资料是他研究和写作的主要资料来源[10],姚薇元是罗家伦的这一举措的直接受益者。其次,罗家伦还专门为姚薇元写作《鸦片战争史实考》提供过很多西文论著。对此,姚薇元在出版时特此表示了感谢, “ 罗先生借给许多重要西籍,尤为难得 ”[8]10。另外,1942年出版的《鸦片战争史实考》的书名是由罗家伦所题写,这既是罗家伦对姚薇元学术的认可,同时也是姚薇元对罗家伦表示尊敬的一种形式。由于罗家伦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想必在专业层面上也给姚薇元提供过很多帮助,只是限于史料,无从得知,待考。
在郭廷以、蒋廷黻、罗家伦的引导下,姚薇元开始研究鸦片战争,令人疑惑的是,因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转入历史专业的他为何研究生期间转学中国古代史,没有选择蒋廷黻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呢?根据记录,陈寅恪在姚薇元之前仅有朱延丰一位学生,因资料有限,待考。另外,从他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看,他并没有对中国近代史失去兴趣,除了继续研究鸦片战争外,还开始探索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甚至利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
二、研究生期间:陈寅恪对姚薇元的教导
1932年,姚薇元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③,在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指导下,他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在史学研究和个人品质方面对姚薇元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史学研究方面,由于陈寅恪的引导,姚薇元走上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道路,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深受陈寅恪史学方法的影响,在学术上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方法。在个人品质方面,陈寅恪坚持学术自由,处理教学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姚薇元也继承了这些品质。
首先,从史学研究方面来看,姚薇元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离不开陈寅恪的影响。陈寅恪于1926年正式进入清华大学教书,1930年起指导研究生,姚薇元是陈寅恪的第二个研究生。姚薇元之所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源于 “ 陈寅恪先生上课时在黑板上开列了一大批研究课题,要研究生们自己在这些课题中找研究方向 ” ,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融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产生了兴趣[3]149-150。选定题目后,他便开始搜集资料,为了探索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过程,他从考究北方各民族的姓氏变化入手,经过5年的认真研究,他撰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研究胡姓的专著《北朝胡姓考》。此书被翻译成多种外文,陈寅恪对此书予以一定的认可,并且亲为作序。后来在大夏大学、贵州大学等大学任教期间,姚薇元仍从事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教授多门魏晋南北朝相关课程。1937—1947年间,姚薇元先后发表了《藏族考源》《唐代诸帝享年考》《北朝帝室氏族考》等30多篇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④,他的研究不再只限于魏晋南北朝史,还研究唐代的财运、府兵制、藩镇等,还考证欧阳修集古录,甚至出版了一册《廿四史解题》。
其次,姚薇元继承了陈寅恪的全面占有史料的史学方法,并形成自己对各类史料 “ 反复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 的史学研究方法[3]149-150。陈寅恪的治学方式偏向于考据学中,并且擅于原料扩充[11],姚薇元继承了陈寅恪的这种治史方法,他认为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和依据,搜集资料时要尽量做到完备,只要有线索可寻就要排除万难去尽力查找,只有详细占有资料才能为奠定史学研究的坚实基础[3]149-150。在研究北朝胡姓时,姚氏依据史书纪传和姓氏专书的记载,参照碑铭、石刻、文集、说部、韵书等材料以及近代内外学者有关姓氏的论著,对《魏书•官氏志》里193个胡姓作了深入考证[4]2,弄清了他们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分析研究要 “ 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 ,他教导萧致治: “ 要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就需要把收集来的资料反复分析研究,剔去虚伪的东西,留存真实的材料。真实材料中有粗有精,这就需要根据自己的识力,认真分辨精粗,才能去粗取精。 ”[3]149-150针对他出版的书籍,他还一直在寻找新的材料,现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北朝胡姓考》是他病逝前最终校订的成果,他花费了五年时间,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方法对这些资料鉴别和分析,精选可信的史料并吸收史学界研究成果中的真知灼见,不断地对原有的材料加以补充和修改[1]3。识别材料是最基本的,他认为资料、分析研究、结论是学术研究中三个互相连接、缺一不可的环节,研究历史需要做到 “ 六何 ” :何时?何地?何人?是何?为何?如何?可见,姚薇元这时已经不只是考订工作,而是研究历史科学。
第三,陈寅恪坚持学术自由的品质,也启迪了姚薇元,他认为学术应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大学生需要独立研究学术。陈寅恪曾在1931年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文中写道: “ 此文撰述的主旨是倡导学术之独立。 ”[12]之后陈寅恪正式走上了学术独立的道路,不仅是他,当时的清华大学也从留洋预备学校转变为学术独立学校,姚薇元就是在这个时候投入陈寅恪师门。1935年,姚薇元在《独立评论》发表《大学研究院与学术独立》,针对当时的留学政策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与日本的教育对比,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标榜学术独立但徒有其名,事实上中国所有大学仍然是留洋预备学校,他还认为教授要注重引导大学生进行自主研究,培养他们的研究兴趣和能力,毕业后推荐他们到研究所深造[13]。
第四,受陈寅恪的影响,姚薇元对待教学工作与学术工作都很认真负责。陈寅恪即使后期眼睛失明,每周照常授课,据他的学生回忆,陈寅恪一堂课也没有缺过[14]前言1,姚薇元对待教学工作也是如此。经过 “ 文革 ” ,姚薇元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 但他仍对工作充满饱满的热情,积极从事教学工作,又招收了两届鸦片战争的研究生 ”[4]3。无论是学生的日常学习还是论文指导,都有他认真负责的身影,学生许增鋐回忆道: “ 在我现在保存的1979年4、5月间所作的读书笔记中,就有姚师和致治师分别用红、黑铅笔所作的旁批。 ” 并且许增鋐的毕业论文一稿、二稿,二位导师都仔细审读,标点符号、错别字等都不放过[15],研究汉唐史的张泽咸曾言因课上笔记仅几行字被姚薇元大批并被罚站。可见姚薇元指导学生的认真、严肃的态度。 “ 文革 ” 后招收第二批鸦片战争研究生时,姚薇元已经77岁高龄,但为了让学生更了解鸦片战争,他陪学生去福州、泉州到广州查勘了虎门要塞,再从杭州、镇江、南京、上海[16]。另一方面,他对待学术工作也极其认真。他曾为湖北人民出版社编写了通俗读物《鸦片战争》,即使是一本通俗读物,他也仔细考证。1982年受人民出版社之邀,他与萧致治准备合写一部《鸦片战争史》的专著,有出版社跟他们预约该专著并希望三年内出版。他们因时间仓促拒绝了,认为研究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必须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后再着手撰写[17]。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准备这本书,到1985年2月25日他辞世时,他们已经制定出了全书的撰写计划,并开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动笔即不幸辞世[4]1-4。
三、工作期间:朱希祖、李达、萧致治与姚薇元的学术交往
1937—1953年间,受战乱等因素影响,姚薇元先后在几所大学之间辗转任教。在这期间,他与朱希祖通过学术探讨产生了深厚的友谊。1953年,姚薇元随李达调到武汉大学,并任历史系教授和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此后,姚薇元一直在武汉大学执教。他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受李达的影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将其用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日常授课。晚年,姚薇元在萧致治的协助下又开始研究鸦片战争。
(一)朱希祖与姚薇元之间的学术交往
朱希祖从1926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但他与姚薇元之间的学术交往主要是在姚薇元读研究生时期。朱希祖受姚薇元的论文启发而作《西魏赐姓源流考》,还曾给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提了一些建议,被姚薇元采纳。《朱希祖日记》中有他自己的相关著述活动和围绕姚薇元的学位论文《北朝胡姓考》与之交往的一些记录。
朱希祖对西魏赐姓这个题目早有兴趣,并且搜集了相关的资料,而动笔成文可能是受到了姚薇元论文的启发。1936年3月11日,因读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一文[18],朱希祖对李唐氏族国籍问题产生兴趣并开始阅读有关西魏赐姓的书籍,但是由《朱希祖日记》相关记录可以发现,他当时还没有写西魏赐姓的计划。直到1936年9月9日,姚薇元以其《北朝胡姓考》初稿与朱希祖交流后,次日朱希祖开始撰写《西魏赐姓源流考》。
朱希祖阅读了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初稿后,与他讨论初稿中存在的问题,后来姚薇元也听取朱希祖的建议作了修改。1936年10月3日,朱希祖劝姚薇元改《北魏胡姓考》为《〈魏书•官氏志〉广证》, “ 因陈毅有《〈魏书•官氏志〉疏证》,故云‘广证’,姚君以为然 ” 。除了书籍的名字,朱希祖在仔细阅读后发现姚薇元书中若干误处并提出建议。例如,10月4日,朱希祖在日记中写道: “ 夜阅《〈魏书•官氏志〉广证》,颇觉其中误处甚多,嘱姚君改正。 ” 同月14日写道: “ 午后姚微(按:薇)元来,讨论《〈魏书•官氏志〉广证》,余劝其改正高氏、李氏、王氏诸条。 ”[19]701-705后来姚薇元将该稿进行扩充,并以《北朝胡姓考》之名出版(科学出版社,1958年),引用书目里还列入陈毅之书。朱希祖给女婿罗香林的书信中也记载了二人关于《北朝胡姓考》的交往记录,书信写于1937年6月21日。信中写道: “ 余近来所撰《西魏赐姓源流考》及驳陈寅恪二篇,皆与唐代姓氏有关,想已阅及。……姚薇元撰《北魏姓氏考》,余嘱其改为《魏书官氏志广证》,大体尚精博,然衍陈寅恪凿空臆测之谬法,论据多未精确,已指出数十处,劝其大加修改,颇见采纳。唐代姓氏与此书大有关系,惜其书未付印,不能供参考,然陈毅《〈魏书•官氏志〉疏证》亦颇佳。 ”[20]177-178由此看来姚薇元听取了朱希祖的若干意见,修改了文章的诸多谬误处。
朱希祖除了当面给姚薇元指出其文问题外,还在其《西魏赐姓源流考》一文中表达了他与姚薇元关于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从《西魏赐姓源流考》一文来看,朱希祖多处征引姚文,文中有两人相关辨证的记录,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里采纳并修改了几处原来的论述。如姚薇元初稿中,《北史•乙弗朗传》云 “ 其先东部人也 ” ,姚薇元认为 “ 东当为西之误 ” 。朱认为姚此说有误,乙弗有东西两部之分, “ 乙弗朗之先为东部人,东非西之误。自吐谷浑率部西迁,已弗部人或亦有从之而西,就有了西方部族 ”[21]1693。
(二)李达校长对姚薇元的教诲
李达是从 “ 实业救国 ” 向 “ 政治救国 ” 转变的著名学者[22],他为唯物史观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传播过程中,他将唯物史观延伸到政治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赋予了唯物史观多种形式和丰富内涵[23]。他《现代社会学》一书中系统总结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4]。
1950年,姚薇元开始接受李达的唯物史观指导。他们是在湖南大学认识的,姚薇元于1950年上学期在湖南大学开始上业务课,那时,湖南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很少,他教授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两门课,整日备课讲课,最后他感到吃力[25]。学生反馈了姚薇元上课的一些问题后,李达亲自到教室听课,课后肯定姚薇元并且敦促他学习理论,以便更好地分析历史问题。后来他去拜访李达时,请教了李达怎样学习马列主义这件事情。不过,姚薇元当时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 “ 只限于联系历史上疑难问题,力图把理论学习的收获,落实到改进教学上 ”[25],而不是纯唯物史观研究。
1953年,受李达教益,姚薇元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学史。当时姚薇元随李达调往武汉大学,在听了李达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讲授后深受启发。之后,在李达的进一步指导下,他对于马列主义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对此,他曾深情回忆: “ 作为解放前长期受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解放后能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胜任历史教学,饮水思源,我不由得感谢李校长的教导……通过李老的教导,解放后我较早地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培养,使我能在后半辈子为我国的历史科学做出贡献。 ”[25]
由此,姚薇元开始关于史学史的研究。首先,姚薇元阐述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划分的观点。1956年,他参加了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研讨会,并连同他人起草了新大纲的初稿,同年7月,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在研讨会上,他阐述了对中国近代史三个时期、九个阶段划分的看法,并就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特点及其阶段性问题作了论述[26],后整理成一文于1958年发表,本文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来阐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阶段性[27]225,他认为只有对近代史进行科学的分期,才能发现社会现象中的固有联系,从而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应用到实际。其次,1962年,姚氏发表《评介刘培华编写的〈鸦片战争〉》,通过他的评价发现他初步形成自己关于唯物史观的见解,他的方法是先用马克思主义论证文章内容合理性,再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在他1963年发表的《王船山史学理论初探》中,通过分析王船山 “ 道统与治统 ” 的思想,他认为王船山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唯物主义传统,而且别开生面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把我国封建时代的哲学和史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通过对王船山的史学研究,姚氏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结合时代条件来评价历史事件的得失,并且不能忽视它的必然趋势、偶然因素以及历史人物的意图和事件的影响效果等,要设身处地地进行思考。在此之后,姚薇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教学编写了《中国史学史概要》。他主张史学必须研究史学史,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最终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传统的中国,从而更深入、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自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1-4。
(三)萧致治协助姚薇元开展学术编撰与教学活动
萧致治,1929年生,1960年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开始在武汉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萧致治以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及相关的中西关系为核心,发表了诸多有影响的著作。截至目前,萧致治独立完成、主持或参与撰写著作23部,发表230多篇学术文章。就鸦片战争的研究而言,1996年出版的《鸦片战争史》(上、下册)是萧致治数十年来研究鸦片战争的总结性成果,该书被列为1978年后鸦片战争史研究的三大代表性成果之一[28]234。在辛亥革命研究中,萧致治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研究黄兴,他认为黄兴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仅次于孙中山,他先后编著多部相关的书籍和论文。在萧致治的不懈努力下,武汉大学已成为全国黄兴研究的中心[29]。
萧致治的成功得益于姚薇元的教导与培养。他到武汉大学不久,便开始协助姚氏进行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1966年,61岁的姚氏任武汉大学研究生导师,萧致治 “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曾做过他的助教,改革开放以后又协同他培养过两届研究生 ”[3]149-150。1978年至1981年间,萧致治协同姚氏招收了三位专攻鸦片战争为研究对象史的研究生,许增纮、丁济康、杨维。1982年至1985年间,又协助姚氏招收了第二批该方向的两名学生,杨卫东、李少军[3]149-150。杨卫东曾回忆当时上课的场景, “ 除副课外,主课都是在姚先生家里上的。一杯茶、几盘干点,是一种聊天式、讨论式的上课……每一次的上课如同聚会,都是萧老师事先安排好,大致程序是我们先汇报近期学习情况,读了什么书,有一些什么见解和疑惑,然后一起讨论或由两位老师进行点评 ”[30]。
姚氏与萧致治是亦师亦友,两人合作完成了多篇文章。1981年,姚氏与萧致治一起发表《孙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伟大贡献》。在萧致治协助下,姚氏后期又对鸦片战争研究进行多次修改补充,两人在1982年合力完成了《鸦片战争研究》。姚氏逝世后,萧致治挑起研究鸦片战争的重任,于1996年完成《鸦片战争史》。
姚薇元从大学开始就在郭廷以、陈寅恪、李达等名家的指导下进行史学训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本科论文出版为《鸦片战争史实考》,此书被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费正清认为 “ 是一本有详细的注释而且有判断力的书 ” 。研究生毕业论文出版为《北朝胡姓考》,成为我国史学界进行胡姓研究的开山之作,陈寅恪也认为 “ 其当日所言,迄今犹有他人未能言者 ” 。工作后,他的中国史学史课程讲义——《中国史学史概要》颇具学术价值,在其逝世后,此书与《鸦片战争史实考》合刊出版。从他的学术经历来看,姚薇元继承了陈寅恪全面占有史料的方法,力求史料资源的详尽完备,这使其历史研究通常需要排除万难才能搜齐资料,研究成果也往往需要多次校订。而且随着新的史学方法的出现,仅仅靠考证已经不能全面地分析研究历史。在李达的教导下,姚薇元在原有考证的基础上开始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资料,最终形成自己 “ 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 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地提出 “ 六何 ” 研究范式。姚薇元在本科、研究生期间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训练,工作后又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这使他既拥有扎实的考证功夫又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这也启迪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史料和史学方法两方面都应下功夫。
四、结语
姚薇元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鸦片战争史见长。在他史学研究的道路上,郭廷以、罗家伦、蒋廷黻、陈寅恪、朱希祖、李达、萧致知等师友给了他不同程度的帮助,有的是教会了他考证等学术研究基本功,有的是指导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展学术研究,有的是就某些具体的问题展开讨论交流。从中可以看出,史学研究者不仅要重视专业素养的训练与培养,还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这一点在当下尤为重要。
注释:
①查阅《清华同学录》(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1937年印),姚薇元于1926-1931年在清华大学就读,历史系1926年新生吴宣易、周振鹤、钟道铭、罗香林等7人均于1930年毕业,而清华历史系的学制为4年,所以姚薇元多学了一年。又因姚薇元在《学生生活之部清华学生生活大纲(征文第二)》(《清华周刊》1927年27卷11期)提到,在清华差不多一年,星期四有物理课,报纸1927年4月出刊,推测姚薇元大一还在学物理,他在大二时(1927年)转入历史系,1931年毕业。
②第一版时易名为《鸦片战争史事考》,原题《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作为副标题,1942年初版。
③参见《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姚薇元1932-1936年就读清华研究院历史学部,但是《姚薇元教授的治学之道》,2004年11月12日,萧致治提到姚薇元1931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部史学门,待考。
④姚薇元在中央大学、大夏大学、贵州大学等大学任职期间,发表30余篇文章。主要有:1937年,发表《欧阳修集古录目考》。1940年,发表《中华民族的统一性》。1941年,发表《可汗称号源出中国说》。1943年,发表《唐代诸帝享年考》(1943)。1944年,发表《五四运动新评价特辑:五四运动之历史意义》《北朝帝室氏族考》《成吉思汗之死期及地点与葬地》《藏族考源》《隋代之民风》《廿四史解题》《匈奴四姓考》。1945年,发表《与钱宾四论唐藩镇胡籍》。1946年,发表《唐代的财政与国运》《学术论著:唐代府兵制度考(附表)》。1947年,发表《独孤即屠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