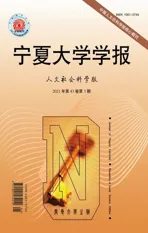《汉语大字典》引敦煌文献献疑
2021-12-25高天霞
高天霞
(河西学院 文学院,甘肃 张掖734000)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九卷本,以下简称《大字典》)征引的敦煌文献主要涉及字书、变文、歌辞等类别,也有少量的社会经济文献。从征引目的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集存字形为目的的征引,此类主要以《敦煌俗字谱》为依据,直接摘取其中的某个俗字作为字头,然后指明该俗字同某正字。如《大字典》“”字下曰:“同‘可’,见《敦煌俗字谱》”。另一类是以集存字形并概括义项、列举例证为目的的征引,此类主要以当时所见敦煌文献整理本为依据,立字头、设义项并征引其中的文句作为例证。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后一类。
据《汉语大字典主要引用书目表》,《大字典》在编纂时所参考的敦煌文献主要是王重民先生整理的《敦煌变文集》和《敦煌曲子词集》二书。此二书均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当时条件所限,学者所见敦煌写本图版有限且不甚清晰,在录文整理、字形辨识方面难免有疏误,而《大字典》本身涉及内容广泛、编纂任务繁重,编纂者很难一一对照图版对所征引的敦煌文献予以核实。再者,《大字典》的编纂者在研读征引敦煌文献时,对个别文句意义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偏差。这使《大字典》中以《敦煌变文集》《敦煌曲子词集》为材料来源的个别条目存在字头、义项等方面的问题。兹结合现已公布的比较清晰的敦煌文献图版以及前辈学者的校勘整理成果,对《大字典》征引《敦煌变文集》和《敦煌曲子词集》中的部分问题略作分类辨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所立字头与写本字形不符
《大字典》中个别字头是根据《敦煌变文集》的录文设立的,而录文本身在校录时存在字形辨识方面的疏失,所以,《大字典》据此设立的字头形体与写本实际并不相符。如:
按:敦煌遗书中存有8个卷号共七种《维摩诘经讲经文》[2],《大字典》本条所引为S.4571号。查该写卷的图版发现,《大字典》所据《敦煌变文集》录文中的“鳅”,写卷实作“泥秋()”(《英藏》6/146上/10。注:“《英藏》6/146上/10”表示所征引字句的图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版《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第146页上栏第10行。下皆仿此,其中《法藏》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图藏》代表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该写卷上还有一处含有“泥秋”的句子,“□信自性浑浊,如泥秋()鱼,将身入清水,水亦变浑浊”(《英藏》6/145下/14),《敦煌变文集》亦校“泥”为“”[3]。由此可见,在“泥秋”一词的校录上,《敦煌变文集》校“秋”为“鳅”可取,校“泥”为“”则未必准确。张涌泉先生说:“‘秋’字或可校作‘鳅’(‘鳅’为‘鰌’的后起改易声旁字),而‘泥’字则决不可臆改作‘’。盖鳅鱼常钻在污泥之中,故称为‘泥鳅’。‘泥’字本无须再加鱼旁,更何况以前的字书并无‘’字……故‘’字实系《敦煌变文集》编者臆造,宜删”[4]。不仅《大字典》如此,《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及《中华字海》“”字头下也都引《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的“鳅”为证。现在看来,既然《敦煌变文集》的“鳅”之“”属于误校,那么《大字典》等工具书据此设立的字头“”及其相应的义项和书证在未来修订时就应该删去。
《大字典》本条所引语句出自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核查写卷图版,原文作:“又《太公家教》:‘孝子事亲,晨省暮省(参)(注:此‘省’字罗振玉藏敦煌本《太公家教》作‘晨省暮参’[6])。知饥知渴,知暖知寒。忧则共戚,乐即同欢。父母有病,甘不飡。’”(《法藏》13/305上/17-19)其中的“甘不飡”,《敦煌变文集》录文作“甘(羹)不飡”,将“”楷定作“”并校作“羹”[7]。《大字典》据《敦煌变文集》收“”字并释义。按:从字形看,将“”楷定作“”并不十分准确;同时,参比文义及其他写本看,“”字也并非“羹”的俗字。
二 据误字而设立义项
敦煌文献在书写方面的一个特点是俗写讹字较多,整理者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不同写本之间的比较以及写本与传世文献的互参,准确校勘这些俗讹现象。但由于早期整理者缺乏便利的检索手段,所接触的图版也不如现在全面,使得敦煌变文中的个别误字在《敦煌变文集》中没有得到准确校勘。《大字典》在设立义项时,恰好又以这些漏校的文句为例,这就出现了据误字而设立义项的现象。如:
【乘】
佛经中用作第一人称。《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又休(沐)谈杨(扬)决乘怀。”蒋礼鸿通释:“乘,就是我,第一人称。”按: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云,此经文“乘”字系草书“我”字抄写之误[12]。
与《大字典》相似的解释也见于《大词典》。《大词典》“乘shèng”字义项:
通“朕”。我。《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乞慈哀,赴乘情成察乘怀。”蒋礼鸿通释:“本篇下文说:‘千万今朝察我怀。‘’察我怀’和‘察乘怀’句例正同,这里的‘乘’应该解作‘我’是无可怀疑的……用古韵来说‘,乘’‘朕’本是同部,‘乘’可以说是‘朕’的假借”[13]。
综合《大字典》和《大词典》的释义与例句可见,在敦煌本《维摩诘经讲经文》中,至少有三处“乘”被解释为“我”,即:“又休(沐)谈杨(扬)决乘怀”和“赴乘情成察乘怀”中的“乘”。蒋礼鸿先生认为这三处“乘”都是“朕”的假借,因为“乘”“朕”古音同部(详参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张涌泉先生则认为,这里被释作“我”的所谓的“乘”字,其实都是“我”字草书的误识。比较写卷图版可见,张说更妥当。
《大字典》和《大词典》所引《维摩诘经讲经文》实即《维摩诘讲经文持世菩萨卷二》,今敦煌遗书中保存有2个写卷,编号分别是BD05394号和P.3079号。《大字典》所引“蒙宣法味令斋解,又休(沐)谈杨(扬)决乘怀”中的“乘”字,BD05394作“”(《国图藏》72/305/17),P.3079作“”(《法藏》21/252上/19)。《大词典》所引“乘道力,乞慈哀,赴乘情成察乘怀”(按:“赴”为“副”之误,“成”为“诚”之误。详参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889页、第899页)中的三个“乘”字,BD05394均作“”(《国图藏》72/305/20),P.3079均作“”(《法藏》21/252上/22)。张涌泉先生认为,就P.3079与BD05394的关系看,后者是据前者抄写而成的,且抄写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很多,比如P.3079上的“”“”本来都是“我”字的草书,而抄手在据以抄成BD05394时,由于不识草书,于是将它们抄成了“”“”(即“乘”字)[14]。此为定谳。
综上所述,《大字典》《大词典》引BD05394《维摩诘经讲经文》“又休(沐)谈杨(扬)决乘怀”“乘道力,乞慈哀,赴乘情成察乘怀”这两句中可以理解为第一人称代词“我”的“乘”,其实都是“我”字的草书误识,工具书不应该据误字而设立义项。
另外还需补充一点,蒋礼鸿先生“乘”与“朕”通假而理解为第一人称代词的观点在敦煌本《维摩诘经讲经文》中虽然行不通,但若置于上古文献,确乎存在此种可能。白于蓝《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有“”通“朕”之例,如郭店楚简《老子》乙:“喿(燥)苍(沧)”;郭店楚简《老子》丙:“战则以丧豊(礼)居之”;此二例中的“”,帛书《老子》乙本均作“朕”[20]。(此例蒙西南大学文献研究所何义军博士见告,谨致谢忱!)这说明蒋先生就古韵看“乘”通“朕”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只是此类通假限于上古文献,且目前简帛文献用例是“朕”通“”,而非“乘”通“朕”,因此,工具书在“乘”字下设立“通‘朕’。我”这一义项的条件还不成熟。
【稳】
弄好,搞端正。《敦煌曲校录·洞仙歌》:“嬾寄迴文先往,战袍待稳,絮重更熏香”[21]。
按:《大字典》此处据《敦煌曲校录》征引的《洞仙歌》,在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中也有收录,其中“战袍待稳”一句,《敦煌歌辞总编》校录作“战袍待”[22],甚是。该《洞仙歌》是S.1441《云谣集杂曲子》中的一首,表现的是妇人对戍边征人的思念之情,其下片作:“寄迴文先往。战袍待,絮重更熏香。殷勤凭驿使追访。愿四塞来朝明帝,令戍客休施流浪。”(《英藏》3/49/4-5)“”即“懒”的俗写,“懒”又是“嬾”的后起俗字。《说文·女部》:“嬾,懈也,怠也,一曰卧也。从女,赖声。”段注:“俗作懒。”故《敦煌曲校录》将“懒”录作“嬾”有道理。然将“战袍待”照录作“战袍待稳”,忠于写卷用字但失于校勘。联系下句“絮重更熏香”可推知,“战袍待稳”的“稳”当为“”的形误。
三 词义理解不够准确
【陵】
按:“陵”字确有“上;升”之义,上引义项下所列前4条例证均能说明这一点。但“阎罗索命难求嘱,积宝陵天无用处”的“陵”却并非“上;升”义,而是“迫近;接近”义。
《禅门十二时曲》见于两个敦煌卷子,其编号分别是S.427和BD07310,《大字典》所引语句出自该曲子的“正南午”章。S.427曰:“正南午,正南午,人命由(犹)如草头露。火急努力勤修福,弟一莫贪自迷悟。阎罗伺命难求嘱,积宝天无用处。”(《英藏》1/191/16-18)BD07310曰:“正南午,正南午,人命由(犹)如草头路(露)。火急努力勤修福,弟一莫贪字(自)迷悟。阎罗思命难求嘱,积宝天无用处。”(《国图藏》96/156/11-12)显然,前者作“凌天”,后者作“陵天”,二者同义,均指近天、接天,“积宝陵/凌天无用处”谓命尽之时即使堆积的珍宝迫近天际也没什么用处。
从汉字形义关系看,“陵”“凌”均得义于“夌”。《说文》:“夌,越也。”故“陵”“凌”均可表示超越,引申为登升、侵犯、迫近。《禅门十二时曲》中的“陵天”或“凌天”用的正是“迫近”义。用“陵天”或“凌天”表迫近天际,文献习见。如唐李华《含元殿赋》:“刬盘冈以为址,太阶积而三重。因博厚而顺高明,筑陵天之四墉”[24]。唐程彦先《大周故处士程先生墓志铭并序》:“由是冠盖蝉联,风徽不绝,长波栝地,高构凌天”[25]。又如“凌晨”指迫近天亮,文献亦有写作“陵晨”者,如韩愈《戏题牡丹》:“幸自同开俱隐约,何须相倚斗轻盈。陵(一作凌)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26]。
《大字典》“陵”字下无“迫近”义,加之编者以为敦煌写本《禅门十二时曲》“积宝陵天无用处”的“陵天”为升天义,于是最终出现了例证与义项不合的结果。建议今后修订时,在“陵”字下补充义项“迫近”,将BD07310号《禅门十二时曲》“积宝陵天无用处”作为其例证之一,并注明此“陵天”在S.427《禅门十二时曲》中作“凌天”。
另外,据上文引BD07310和S.427“正南午”章的相关文句可见,《大字典》引《禅门十二时曲》“阎罗索命难求嘱”的“索命”,写卷实作“伺命”或“思命”。查任二北《敦煌曲校录》,“阎罗索命难求嘱”的“索”字下注:“‘索’原作‘思’”[27]。按:此校不确,写卷“伺命”“思命”均当为“司命”之音借,“司命”与“阎罗”都是管命之神。S.427“阎罗伺命难求嘱”、BD07310“阎罗思命难求嘱”均当校作“阎罗司命难求嘱”,谓命尽之时即使请求阎罗和司命关照也无济于事。
敦煌遗书中存有标题相同而句式和内容不同的两种《燕子赋》,《大字典》此处所引者,《敦煌变文集》称《燕子赋(一)》,共有8件写本,《敦煌变文集》以P.2653为底本,以其他写本为参校本进行了校录。今核查图版,《大字典》所引语句,P.2653作:“遂乃嗢本典曰,徒沙门辩,曹司上下,说公白健。”(《法藏》17/108/29)P.2491、P.3666、P.4019等写本均作:“遂乃嗢本典,徒少问辩,曹司上下,说公白健。”据此可知“嗢”又作“嗢”。该词何义,需根据上下文及其他文献予以考证。
在《燕子赋》中,雀儿不仅强占燕子之宅,而且辱骂殴打燕子,于是官府将雀儿拘禁了起来,“雀儿被禁数日,求守狱子脱枷,狱子再三不肯”(《法藏》17/108/24-25),于是雀儿便给管事吏员说好话。所说好话的内容,《敦煌变文校注》录作“遂乃嗢本典,[徒(图)少问辩]:‘曹司上下,说公白健,今日之下,[乞与]些些方便,还有纸笔当直,莫言空手冷面。’本典曰:‘你欲放钝……’”[29]校记曰:“‘本典’即负责本案之典吏”[30]。项楚先生亦曰:“本典:主管本案的吏员。《太平广记》卷三八〇《张质》(出《续玄怪录》):‘检状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本典决五下,改追正身’”[31]。是《燕子赋》中的“本典”指负责本案的官吏。既然如此,那么《大字典》将《燕子赋》中“嗢本典”之“嗢”释作“整个儿吞下”就是讲不通的,因为此义无法与“本典”搭配。
《大字典》作为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汉语语文辞书,在字形罗列、义项设立、例证选取等方面都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这说明敦煌写本在辑录汉字字形、保存词义用法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由于写本本身的俗写讹误、文献整理过程中的偶然疏失以及字典编纂者对个别敦煌文献句义理解的偏差,《大字典》中个别以敦煌文献为主要材料的条目在收字释义上并不十分准确。因此,对照写卷图版并参比其他资料对《大字典》所引敦煌文献加以细致考订,将有助于《大字典》的修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