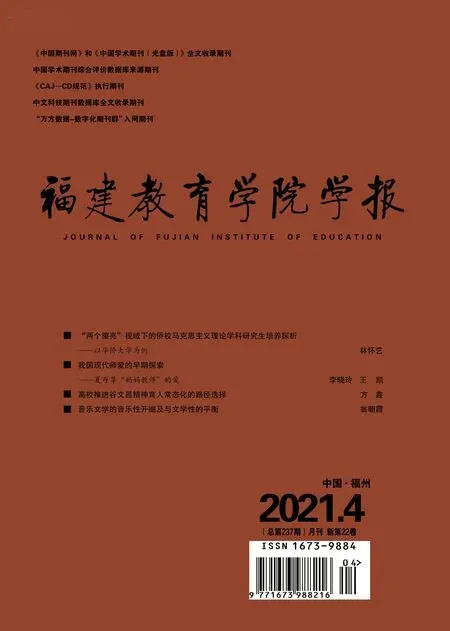音乐文学的音乐性开掘及与文学性的平衡
2021-12-08翁朝霞
翁朝霞
(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音乐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特殊文学样式,跟文学的各个子集——散文、诗歌、小说等文体明显不同。它是以音乐化的语言文字为工具,运用符合音乐节奏和歌曲结构的语言句读结构和曲式结构,以形象来创造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自然风物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其文本符合听觉特性,以歌唱来诉诸人们的听觉。它与曲调、歌唱高度结合,音乐性特征非常明显。音乐文学狭义的叫法是歌词,虽以文字形式呈现,但其文学性却特别“节制”,呈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立特征。它通过动态平衡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注重以“情态”的表现方式来反映人生百态,时时让听众“生情”,给听众提供联想的“媒介”,既写出人们眼中所能看到的“美”和“情”,也能指向人们眼中看不到的想象的“美”和“情”。这种“情态”需要自然生发,需要节制语言,避免语言过深或过散,往往通过一个人、一个物件、一种情绪、一种氛围去传递或营造一种抽象、复杂的思想、情感、境界。文章试图通过对该文学音乐性的开掘及与文学性的“平衡”的重要性和实际运用的分析,来揭示这一特殊文学形式独特的审美特性和创作规律。
一、注重汉语语音修辞,开掘语言的音乐性,以音乐化语言来提高入歌能力
文学对音韵的追求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对此早有论述。早在六世纪南朝文学家刘勰就在《神思》中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他又在《声律》中说:“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1]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仄之分,词之声韵还有双声叠韵之别,需要穿插着用,如连用平声或仄声,不是声沉欲断,则是气飘不降。而双声和叠韵词要连用,中间不穿插其他字,如穿插则会产生“吃文”现象,很拗口。要想听到“玲玲如振玉”“累累如贯珠”的声音效果,则要注意“异音相从”(平仄声调和)“同声相应”(押韵)。足见那时起人们就认识并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有了理论的研究。明王骥德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他在《方诸馆曲律》卷二《论平仄》第五中谈到四声平仄,说:“四声者,平、上、去、入也……乖其法,则曰拗嗓。盖平声声尚含蓄,上声促而未舒,去声往而不返,入声则逼侧而调不得自转矣。”[2]说明四声的不同性质,必须安排在适当的位置,才使歌唱不致拗口。这样,歌者利于转喉,听者感到悦耳,因此作者们才自觉经营,不惜忍受种种严格限制。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艺概》卷四《词曲概》提出“词家既审平仄,当辨声之阴阳,又当辨收音之口法。取声取音,以能协为尚”[2],对语言的听觉分辨在理论上又有了进一步阐发。
以上论述,让我们感受到音乐文学的语言是需要精心设计的,它必须在听觉上形成鲜明的韵律感,让声调和谐流畅、明亮悦耳,有意去组合适合音韵流动的字眼,使之形成特别的听觉效果。音乐性是其自有的重要特性。无论是歌词、歌剧唱词、戏剧唱词还是曲艺唱词,都与“歌唱”紧紧相连。从作品创作伊始,这个文学样式就充分考虑音乐的元素,考虑适合听与唱的特性,所以它使用的并不是汉语的全部语言(因为不是所有的语言都适合唱与听),而是有限定的适合听与唱的音乐化的语言,它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来精心营造。
每一个汉字都有声、韵、调,合理组合声、韵、调,会产生不一样的声响效果。比如双声、叠韵、叠字、押韵的运用,不仅能改变汉字的音响效果,影响声音的响度、色彩,字音的高低起伏等,也能影响人们的情绪,这些语音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但能快速增强语言的乐感,还直接影响旋律的走向和歌唱的效果;文字平仄声调的交替使用可使词句产生抑扬顿挫的音乐性,从而影响旋律的流畅度。
从双声、叠韵、叠字的使用来看,所谓双声是指两个声母相同的字组成的双声词,如“大刀”“火红”等;叠韵是指两个韵母相同的字组成的合成词,如“丛中”等;叠字是指两个相同的字连缀使用,如“星星”“依依”等。早在《诗经》中,古代先民就已熟知音乐化语言的妙用,他们运用各种手法增强语言的入歌能力,如“参差”“踊跃”等双声,“委蛇”“绸缪”等叠韵,“京京”“烈烈”等叠字的运用,富于音乐性。宋代柳永更在其《乐章集》中变化运用双声、叠韵,有连续用、间隔用、句头用、句中用和句尾用,不拘一格,灵动异常,给听觉上带来异样的美感,也使他成为北宋最有名的“流行音乐家”,其一生创制许多新词,音韵变化之大、之丰富,是后代许多词作家无法企及的。
从调整文字的平仄声调和注意押韵来看,足见古人对文字音韵的极致追求。押韵,指某个固定句子最后一个字的韵母要相同或相近,使朗诵或咏唱时产生铿锵和谐之感。周人立国之初乐歌中就出现押韵的歌词,今天的歌词押韵得益于《诗经》,其中一章之中转韵的如《关睢》二章、《行露》三章,句中用韵的如《小星》二章,今天流行歌词中常用的句句押、隔句押、隔数句押或不押,《诗经》中无不具备。在对平仄的要求上,平仄声常连用,如《汉广》一、二、三章,《鹊巢》首章等。《诗经》后的古体诗格律较宽(除骈文外),到唐后的近体诗则要求严些,词的用韵较古诗、近体诗复杂得多。拿近体诗来说,律诗的平仄只有平起、仄起两种格式(要求句内平仄相间,句间平仄相对),词与律诗相比丰富很多,其格律有很大变化,相应的平仄更是五花八门,既讲究声韵、四声(平、上、去、入),也分阴阳及发音部位,宫体诗的许多格律限制都进一步发展,词的声律进一步完备,唐宋词作中押韵位置不像诗只限于偶句押,而是随着音乐变化要求语言错落参差,音节和谐。音韵学把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贯穿整个音节的音高变化为声调。歌词创作中,汉字声调的走向、跨度的大小,都会影响到旋律的走向,两者相对一致的就比较协调,反之则有碍听觉的流畅。
音乐化语言需要特别注意语音修辞的运用,作者要时时注意声、韵、调的变化与音乐的关系,不断调整,不断哼唱,使语言声调抑扬顿挫,并配合音乐旋律的起伏和律动来感受语言、调整音调,从而使入歌性大大增强,把听众紧紧拽进音乐连贯的情绪中,让乐曲间的衔接与过渡更自然,并给作曲和歌唱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想象空间和音韵空间。
二、开掘语言结构的音乐性,使语言节奏更好地契合音乐结构和节奏的要求
开掘语言结构的音乐性的目的是更好地与音乐契合。歌词的语言结构分为篇章结构、句式结构、音节断句(句读结构)等。歌词的篇章结构对应于音乐的曲式结构。唐词里的“遍”“阕”“段”都是根据音乐分段,词的分片在今天看来就是曲式结构,上下两片结构不同的就是二段体结构A+B;也有分三片、四片的,如各片句读结构不同,就是三段体、多段体结构;如四片相同,就是一段体的分节歌。当时词牌上的引、令、近、慢都与音乐息息相关,从而区分音乐的节奏和段体。词牌即音乐的词调,分片即分段,各种词牌都规定了固定字数、格式、句子长短等,完全是为了应歌需要,取得音乐与文学的相融,这使每一词牌的句式都有定型。今天歌曲常用的曲式结构有一段体、二段体、三段体和多段体四大类,每个大类又分为不同的连接方式,如二段体的AB、A1A2B、AB1B2、A1A2B1B2……三 段 体 的ABC、A1A2BC、AB1B2C、ABC1C2、A1A2BC1C2、A1A2B1B2 C1C2 等结构连接。各种曲式结构的连接构成歌曲的篇章结构,歌词的篇章结构必须以曲式结构为结构,才符合歌曲要求,容易谱曲。
歌词句读结构与音乐的节奏关联密切,这也是音乐文学文体的特殊性决定的,句读结构要随音乐进行而对应设计,要有强大的应和音乐能力,才能应对音乐节奏的无穷变化。就算远古相对规整的二言、三言、四言诗,为应和音乐,也得添加衬词以增强应歌能力。如伏羲时《网罟之歌》:“吾人苦/兮/水深深。网罟设/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网罟设/兮/山不幽。”[3]整首歌词共二章,句式以三言为主,形成三字式+语气词兮+三字式的结构,前后三字通过中间的“兮”字形成对称。再如夏商时大禹的情人在涂山之阳等候他归来时唱的情歌“候人猗兮”,也巧妙地在二言双音词后添加虚词“猗兮”,使之能与音乐更好地契合。《诗经》基本句式多为四言一句,为了入歌,不少诗句突破四言定格,间杂二、三、四、五、六、七、八言,让我们从整齐中感受到参差之美。
从入歌上看,《诗经》的语言句读节奏虽有一定的自觉,但还不及楚辞来得彻底,楚辞汲取南方楚地民歌句式,采用散文化长句,长短相间,灵活多变,创造出比较自由的格式,很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如,三字式+虚词+三字式的句式(如《国殇》中的“子魂魄/兮/为鬼雄”),三字式+虚词+二字式(《湘君》中“捐余袂/兮/江中”),三字式+虚词+二字式+虚词结构(《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四字式+虚词+四字式结构(《山鬼》中“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四字式+三字式结构(如《天问》中“师望在肆/昌何识”),如果我们将三字再次拆解,并去除虚词后,则形成一字式+二字式+二字式的句式,它大量使用动宾词组的用法,使三言诗被分隔成许多的单音字,这在诗体看来是很不精严的(如《涉江》中的“被/明月;佩/宝璐;驾/青虬;骖/白螭;登/昆仑;食/玉英等动词的使用[4]),但诗体的格式却不可能这样,它非常严格,比如汉代的五言诗和七言诗,常见的句型只各有两种,如五言的2+2+1、2+1+2 和七言的2+2+2+1;2+2+1+2结构,无论五言还是七言诗,其单音字绝不可放于句首,这是诗的禁忌。从这点上看,楚辞中的很多格式更近似于音乐文学,因为对于音乐来说,单音字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问题,音乐的节奏都可以解决,如放句首可以用半拍的节奏开头,形成弱起小节。一个五字式的句子结构可分为1+2+2,2+2+1,2+1+2,还可以分为1+1+1+1+1,4+1,1+4,2+3,3+2,5 等不同结构,没有任何禁忌,这也让我们看到音乐文学与诗体句读格式上的不同追求。
对于音乐节奏来说,如与之相配的语言句读节奏过于规整,音乐则显得呆板、单一、缺乏生气,反之就鲜活。汉代后至唐精严的诗歌体式的单一,非常不利于抒情,不利于音乐的发挥。唐代的雅乐都是一字叶一音,旋律异常单调,节奏平板而少变化,所添之辞多为五、七言古诗(见《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与之相反,唐燕乐形式却异彩纷呈,变化多样,为解决入歌问题,唐词人开始对诗体进行一系列改革,采用加和声、添虚词和增添新字等方法来打破律诗绝句的规整结构,如有的重复诗句末尾三字,有的在末尾添加音韵相似的新字,有的进行断句重复,目的是增强应歌能力,使词曲相应,声字相融,他们的努力终于推动了词体这一文学样式的形成,使长短句成为当时应歌的主要形式。但遗憾的是,当今许多歌词从业者仍没明白这个道理,其歌词句式还是套用五言或七言的诗体格式,或简单写几段排比句、对偶句,以为这就是歌词,其实这样的句式对丰富的音乐节奏来说,无疑是一种限制和伤害。歌词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来变化语言的节奏,使之形成节奏上较为灵动的风格。
众所周知,节奏是音乐的基本骨架,在音乐中,无论是五字一顿、四字一顿、三字一顿、两字一顿还是一字一顿,都可以在一拍的节奏中给予解决,既然音乐节奏能够解决这么多元的语言断句,我们何必抱着规整的语言节奏不做改变呢?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去调整句式结构,以应对音乐自由的节奏变化,时时保持一个创作者高度的音乐性自觉。
当我们能够把对语言节奏的追求上升到“音乐性”的高度时,作曲家才有可能藉由语言节奏而进入新的音乐节奏,才能更好地变化和表现音乐。这种对句读结构音乐性的“极致”追求恰恰是音乐文学有别于诗文的重要标准。今天白话文歌词在句读结构上的变化灵活,其断句方式可用单音字、词组、成语、短语结构等断句法,甚至运用结构重复来加长句子,或通过倒装、变形语言、活用词性等方式来改变句式单一的结构形式等。但无论怎样变化,都要注意,不可信马由缰,不加节制,虽然歌词句式结构变化大,可让音乐变得灵动,但如变化太大、毫无节制,又易变成现代白话文诗的结构,不易入乐(白话文诗歌难谱曲,就在于句式、字数的长短没有规律)。歌词的字式(指几字一式)、句式一定要注意在规律中找变化,在变化中找规律。
我们创作歌词时,要根据音乐节奏的长短、形态、曲式结构、体裁类型、和声表现等,来安排句读结构和篇章结构,选择语言色彩、表现手法,营造不同的情境,使文字之“足”可适音乐之“履”。
三、精心安排语言文字,使作品达到有利于歌唱的特殊要求
我们知道,歌唱的发声与普通的说话有很大的区别。普通说话可以不大注重声音的质量,对音色、音高、音量都没有什么要求,但歌唱需要有亮度、有质量有情感的声音的传达。史宾赛在《音乐的起源与功能》中提到:“音乐起源于人类感情和祭祀时声音的抑扬顿挫。”声音的起伏是因为情感的波动。人们通过声音的长短(节奏)、高低(旋律线条起伏)、强弱(轻重)、快慢(速度)等要素来表达情感,而不同的情感需要运用不同的声音要素去表现,声音的千变万化需要运用各种技术去展现。作为歌唱重要的语言基础,如果句读、语言声调、风格色彩、情绪浓淡不利于演唱,就会影响歌唱技术的发挥和情绪的完美呈现。歌词创作者首先要考虑到歌唱者发音的自然规律,把每一个字都安排得恰当而妥帖,使之能顺利地发音、咬字和归音,不至于拗嗓或改变字音。
在演唱中,有的歌手对某个声母掌握不好,如f、h不分,zh、ch、sh 掌握不好;有的歌手对一些韵母驾驭不熟练,如前后鼻音分不清,前后an 分不清;有的歌手技术不到位,开口音闭口音老唱不好;有的歌手对不同唱法的咬字问题老搞不清楚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要求歌词创作在面对不同歌手时要善于规避其声音技术短板,针对不同唱法的咬字特点开掘语言的音乐性。比如笔者曾看过一首歌词,开头即用:“掬一缕……”这就很为难演唱者,因为这三个字的韵腹都是闭口音,口腔开口度都非常小,连用在一起,口腔都打不开了,特别拗口。
汉语的声母大都是辅音,它框定了字音的走向、力度、轨道、形状,其发声部位(双唇、唇齿、舌尖、舌面、舌根、翘舌、平舌)、发声方式(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都有清轻重浊之别,由于发音部位的不同,对咬准字音有着重大的关系。我国的民族唱法,非常注意字正腔圆的歌唱效果,咬字分为字头、字腹、字尾,又特别注意归韵,需要精心组合。笔者曾为解放军政治部文工团、青歌赛金奖得主王丽达创作歌曲《幸福葡萄》,特别根据她的声音特点,设计衬词“哎哩呐嘞,哎哩呐”,连用三个相同的韵母“来采摘”等,不断凸显其清亮、甜美的音色,使之把歌唱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汉字中,吐字的过程主要由韵母展现,汉字的每个单音节均可表意,能赋予该音节以一定的情态、色彩和指向。配合不同的唱法要求,就会展现出不同的声音色彩。如气声唱法,以气带声,要求发声前气息先从声门透出,再将字送出,有如叹息和抽泣,音色细腻、变化多样。对应的歌词在语言选择时要特别注意音乐化语言的使用和语言色彩的搭配;又如美声唱法,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程志说:“美声是运用意大利语言的方式唱,意大利语言只有a、o、i、e、u五个元音,没有不易送出的字,根据这个原理,在美声唱法中不归韵即可保持腔体一致,唱出明亮的音色来。”美声歌唱要以演唱元音一样开放的、明亮的行腔来咬字,与说话差别非常大,讲究字音一下子达到“明亮、圆润”的效果,前后音色一致,气息连贯不断,对应的歌词不能选听觉上太尖利、闭口音太多的语言。
汉字读音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在歌唱中非常凸显,甚至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语句、语气、语境和唱法中,其咬字过程都有变化。汉字的韵母丰富多样,有单韵母、复韵母、鼻韵母等,复韵母中由两个甚至三个音节组成的情况很常见,有的后面还跟着浊辅音,如“n”或“ng”,甚至碰上儿化音er 等。这些复杂的韵母构成对歌唱的咬字和吐字的影响很大,要熟练掌握并合理组合运用。对语言要有选择,听觉上感觉不协调的也要调整。要研究各种唱法和不同歌手的声音特点、技术能力、情感表现,设计不同的语言,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响度、亮度等声音特点,展现特色,抒发情感,从而塑造出成功的音乐形象来。
音乐文学还可通过语言技法的运用来服务歌唱。比如添加衬词衬句,可通过添加虚词来增添地域色彩、提升音乐性。如湖北民歌《龙船调》:“正月里是新年哪咿哟喂/妹娃儿去拜年哪呵喂/金哪银儿梭银哪银儿梭/阳雀叫哇抱着恩那哥”,这里的“哪咿哟喂”“哪呵喂”等衬词比比皆是,如果没有它们,歌词就失去了特别的听觉美感。
又如反复的手法。这种手法自古就有,如《诗经》中的《周南·芣苢》的整章重复、《王风·采葛》中部分字、句的重复等,给人带来复迭回旋之美。当今歌词对重复的变化运用也很多。如佘致迪的《辣妹子》:“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吊一串辣椒碰嘴巴/辣妹子从来辣不怕/辣妹子生性不怕辣/辣妹子出门怕不辣/抓一把辣椒会说话/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妹子/辣辣辣……辣出的汗来/汗也辣呀/汗也辣/辣出的泪来/泪也辣呀/泪也辣……”该词以“辣”字打头和结尾,从字、句到段逐一重复,包括运用顶针手段进行句子间的连缀重复,促进了音韵的和谐,也增强了歌唱性。
四、善于“节制”作品的文学性,使之与音乐性完美平衡
对音乐性的开掘,给音乐文学的文学性提出了音乐化语言、结构体式、语言句读节奏形态和歌唱性语言设计等诸多课题。在文字创造的强烈音乐性的框架下,留给文学抒发的空间是有限的。文字不仅要担负给曲作者和歌唱者音乐上暗示的任务,还要充分生动地表现音乐的“情感”,帮助音乐外化其抽象的“符号性语言”和“精细、分层的情绪”,不断平衡文学表现与预设的音乐节奏的关系,使音乐表现的情感变得可见,并给予听众联想的空间,使之自觉生发出情感。
这种节制,这种控制和平衡的能力,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一首歌词看似淡淡的,不着全力,我们往往简单地以为它不如诗歌有深度、酣畅淋漓,但其实这恰恰是音乐文学的魅力。它就像一幅水墨画,有选择、淡雅、有致地展现情思,不急不躁,但又让人一眼就感受到情和美,瞬间被击中,并在与音乐的水乳交融中魅力独显。要达成这样的效果,词作者必须在创作中不断平衡音乐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合理地安排曲式结构、句读结构、语言音乐化等“音乐性”要素与“文学性表现”之间的比重,并在自己预设的音乐化框架下传递相应的情绪,让曲作者、演唱者和听众看懂、听懂自己的音乐化暗示和情绪暗示。如此,通过有意识的控制,看似“节制”了文学性,实际上通过文学对音乐恰如其分的引领和契合,反而提高了歌曲的整体魅力。
可以这么说,每一首歌词作品都必须暗合音乐的形象,适合“歌唱”的发声,符合听觉审美。音乐文学对音乐起解释作用,其形象指向性明确,能让曲作者和演唱者感受到形象,让听众看懂乐曲描绘的形象。它框定了整个作品的音乐形象,使所有人围绕这个“形象”走。所以,要使歌词塑造的形象与音乐形象相契合,创作时必须在脑中把大家往自己预设的形象上带。至于这个形象最终能被曲作者和演唱者感受到多少,或被听众感受多少,一部分取决于初设形象是否集中、鲜明、动人,另一部分也取决于后者个人的经历、文化程度和感受力。这就是艺术独有的魅力,千万人可以得出千万种结果,好的艺术是提供联想的最好媒介。
与音乐文学相比,其他文学样式对音乐性没有特别要求,对文字的要求各有侧重,甚至追求陌生化和深度,因此在文字的自由度上相对较高。音乐文学作品只是声乐作品生产流程的一个环节,等待着曲作者、演唱者和听众的检阅,它后面任一环节发生问题,作品都可能胎死腹中。在传播环节的“听觉的介入过程”更是流动的,速度很快,很直接,需要瞬间让人感受到形象,所有的理性、说教、灌输、口号都容易带来阻碍,必须让“情态”尽快呈现,让情绪尽情流淌,让人们入情入境,并在情境中去探索感受。因此,如何提供让人们入情入境的氛围,如何含蓄地呈现主题和哲思,让它随情思流动而沁入听众的心田,这才是音乐文学需要完成的“文学性”任务。
在一首歌词作品中,音乐性与文学性是高度交融的。其语言既需符合曲式结构、音乐节奏和发声的要求,又需让人轻松地听清文字的意思,还能快速打动其内心。作为在一定时间中展开的听觉艺术,音乐稍纵即逝,时间上的制约明显。音乐文学在篇幅上必须力求简短而生动,有利于审美,故事和具有美感的内容最容易让听者产生联想。情感、美感和简单缺一不可,光有简单,没有情感和美感,无法让听众联想,索然寡味;光有情感和美感,但流于复杂,也会让曲作者、演唱者和听众感到累。所以,要短得合情合理,又让人回味,这就要求歌词凝练而富有张力,对文学性的要求很高。
需要说明的是,在语言、结构上进行精心设计,看似多了限制,实际是在白话文语境下,为音乐文学这个文学种类开拓了更为多变和多元的广阔空间。音乐文学形象的动人,要靠听众在限定的时间内“听和想”来完成审美过程。作品如一味铺陈不知节制,或过于直白没有回味,难以产生丰富的联想,难有空间的扩容和情感的“再生”,都降低了文学性,自然也称不上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