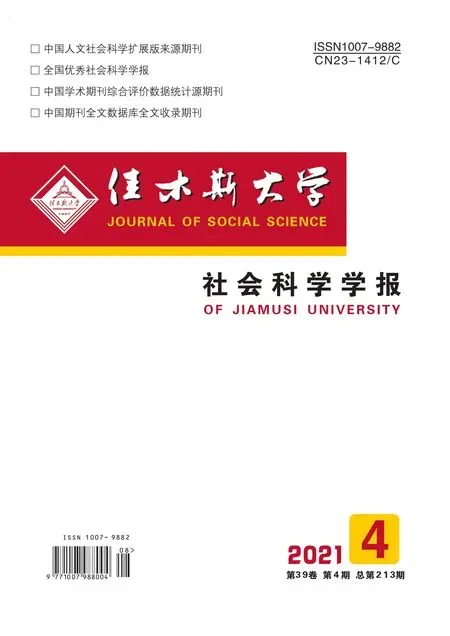绅士的分裂*——试析阳大鹏之变
2021-12-07屈嘉文
屈嘉文
(青海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青海 西宁810001)
一、前言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军与英军的激战已过去了两年,过去清人眼中“英夷”用枪炮使清朝皇帝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所签订《南京条约》及此后各国所追加附约,除了开设口岸外,亦使得清廷承担着沉重的赔款负担,对清廷的财富汲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时在中国社会内部原有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满人入关后基本沿袭明代的税收制度,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以农业作为立国根本,保证了普通民众生计和国家的稳定税收。至康熙时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人丁作为常额,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因而所控制的田稅收入逐渐固定下来,此后无太大变化。倪玉平对道光时期各省地丁钱粮的奏销钞档进行了统计,指出在当时清廷地丁银收入约在2000-2500万两之间。[1]英国所要求赔款则是两千万两,这一沉重财政负担依靠原有税额无法满足,因而清廷只能增加杂税,加大对民众剥削来弥补当前亏空。
以湖南耒阳而言,地方上的漕粮与浮费使民众承受着很大负担,监生阳大鹏或作杨大鹏,联合地方绅士向官方呈请要求减少这一费用,耒阳知县叶为珪将阳大鹏弟弟阳大鸠逮捕,此举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暴力活动。阳大鹏带领民众围攻耒阳城,湖南巡抚陆费瑔派提督石生玉与永州镇总兵英俊率军镇压,后阳大鹏败走杉木岭,事后被捕押往北京。此次事变对清廷造成了极大震动,甚至数十年后,咸丰帝仍询问骆秉章太平天国中杨秀清和阳大鹏二者是否存在着亲属关系?[2]234中外业已有学者对这场由下层绅士所发动的事变展开了讨论,在传统革命视角下,阳大鹏被塑造成对清廷黑暗统治的反抗者,傅衣凌指出在当时抗粮运动中的主持者,差不多都是一般的士绅分子,……其出身的社会层均大别于一般农民,他们本是清朝封建政府的拥护者,现在却群起而作了分裂的活动。[3]81而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变的这一思路下,孔飞力将此事件被视作是中国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农业集体化最为开始的尝试。[4]83本文并不打算对该事件性质做进一步探讨,而是要对该事件事实与背景重新进行梳理,以及在阳大鹏之变后时人的看法,藉以认识在太平天国前夕中国社会中绅权额扩张,多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二、鸦片战争后的耒阳
阳大鹏家世居在耒阳西乡哑子山,本姓欧阳,阳大鹏有兄弟阳大鸿与阳大鸠,阳大鹏早年获得监生功名,但不清楚其是否通过了科考,抑或是捐纳所得?史书中并无详细记载。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研究,在地方“大量的监生实际上并不进京就读于国子监,对于他们而言,这一功名重要乃在于他们绅士地位和特权得以承认,并且为进一步的加官晋衔提供了一个开端”[5]4。因而阳大鹏的监生功名可能是通过捐纳获得,获得了监生功名自然也算作地方绅士,拥有绅士身份后,自然也要维护地方利益,这是绅士在地方获取名誉与利益的基础。孙竞昊指出:“对于明清时期的地方士绅而言,官方所授予的头衔只是将他们的自身的身份法定化,他们实际的影响则通过对于参与地方事务得以实施。”[6]因而他们在地方的表现,是维护地方利益和显示自身权势的双重选择。
湖南耒阳所承担的漕粮十分沉重,史载“耒阳邑完纳钱粮,向系以钱折银,运至省城,易银解司,倾熔折耗,烦费滋多,收兑漕米,涉历河湖,需用亦复不少”[7]。在地方上民众并非是向官府上交本色,为了运输方便官方所要求交纳的是折色,民人需要将所收获粮食进行售卖来获得铜钱,再到市场上换取白银送到州县。然而清代官方制定银两与制钱的比价为一比一千,但在实际市场交易中,大多数的情况下并非按照官方所制定标准进行交易。根据刁永凯统计,在湖南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的1两银子换1428钱,到道光二十六年时(1846年)1两银子则可换1923钱。[8]116在不到十年间,银与钱二者比价上涨了约30%。民众生产能力并未伴随着银两比价提高,在道光时期中国也并无重大农业技术的突破,对耒阳而言,当地多山地形也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时人言:“耒土近燥,厥田下中,间有膏腴,不过十之二三。加以旱干,时逢民食为艰,十年五旱,五年三旱。……耒则为利甚薄,荒歉之岁,即隅为播种卒之逢年者稀,故终岁勤勤,良农亦未必尽丰,其势然也。”[9]1136先天的地形已经限制了农业发展,农民终年辛勤地劳动但所得却十分有限,当时湖南银价上涨又迫使民众要缴纳更多的粮食,若在此时地方胥吏再加以盘剥,必然使得地方民众无法承受。
耒阳的胥吏对税粮征收与他处大致相似,“耒阳征粮,由柜书里差收解,取入倍于官。”[10]13068这种情况下民众更倾向于求助地方绅士,来帮助他们缴税以避免胥吏侵夺,绅士帮助乡邻代缴税款,使他们不用亲赴县衙自行缴税,避免了在路途上的花销,作为交换绅士收取一定报酬。但在民众眼中,这一报酬比胥吏的勒索要轻很多,而官方认为此种包揽是不被允许的。在康熙时为乡民发放滚单,明确的标明田地、银米的数额以及春、秋两季完粮的期限,使民众明白所交税粮数目,并鼓励将税银自投封柜,以保证民众不被胥吏蒙蔽,并试图建立政府与民众的直接联系。但不幸的是这种尝试始终没能成功,多数地方民众仍依靠绅士来缴纳税粮,地方官员也默许了这一情况,若绅士的包揽在合理范围内,并完成了上级的考课任务,那么此种行为亦是可被容忍的。
随着清中后期人口的大量增长,需更多公务人员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中,但在地方政府中人员的配置与前代并无太大差别,办事人员的不足增大了地方施政过程中的难度与成本,现实中地方事务的需要,在地方上要供养更多办事者,在地方基层中办事人员的增加需中央财政支持,但是有清一代朝廷似乎并无此打算。在地方政府中里差与书役,对他们所发放的薪酬无法赡养其家庭,自然无法希图他们捐私奉公。在清人描述中,他们多是贪婪无厌之辈,借助官方所赋予权力勒索地方民众,作为自身工作的报酬,同时亦欺瞒上司,将官长的权力不断架空。但地方官员也必须依靠他们,因在朝廷考课当中,最为重要的指标仍是地方治安与钱粮人口,清代知县满三载就会进行轮调,对于地方事务并无太多精力进行关注,而顾亭林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所言就是此种情况,长期处于一地,对于地方事务更为熟悉的自然是胥吏。民众在他们眼中自然是加以盘剥的对象,在耒阳亦是如此,陈岱霖言“殆征漕之日,一任书吏包揽,高下其手,州县利于借贷之便私,书吏乐于取偿之加倍,官吏朋比,竟成锢习。”[11]地方官员对于这一现象,无法做出太多的改变。
三、从闹考到攻城
民众对地方胥吏征收浮费的承受能力有一定限度,若超出这一限度自然会引发不可预料的结果,在平日当中乡民首先会委托绅士向官府请求减免,因在地方上绅士享有官方所赐予的一些特权,可与州县长官较为平等的沟通,耒阳段拔萃就漕粮积弊问题向县官李金芝呈请,但李拒绝了这一请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段拔萃北上京控,按照惯例案件会被发回原省交由巡抚处理。中央对于此类事件,一般是直接发回地方,“此案段拔萃等,供词闪烁,非提集全案人证,不能质实……所有段拔萃、段孟辉即段基望、并段克明等、著一并解交陆费瑔,督同万贡珍就近饬提各要犯,同被控书役人等到省,秉公质审,按律定拟具奏。”[12]将段拔萃发回原省后,巡抚陆费瑔并未将段所控告的书役等治罪,反而将段定为“刁生诬告”,责以廷杖后发配充军,段拔萃先被拘至耒阳县狱中,衙役们为进行报复,密谋要让段拔萃死于狱中,在清代犯人卒于狱中的情形实不胜累举,到咸丰时期刑部仍奏:“为监犯日食粟米多致病毙,恳恩仍照旧章改放老米事”,可见在狱中囚犯的死亡十分常见,为了避免这一结果,段拔萃的族人为展开了一系列的营救行动。
得知段拔萃被关入耒阳狱中后,段氏族人找阳大鹏商议,决定在地方先组织罢考来对县官施加压力,因为若是耒阳县试不能如期举行,必然影响衡阳府的府试,知县李金芝定会被罢免,但段氏族众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分。《大清律例》当中载:“如有借事聚众罢市、罢考、打官等事,均照山、陕题定光棍之例分别治罪”,“为首者照光棍律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13]317虽有如此严厉的规定,但阳大鹏与段大荣、徐思诚、段基望等人还是组织乡民入城阻考,他们刊刻传单在县城内散发,数日间城内已是群情汹汹。作为对这一出格举动的反击,县令李金芝将段拔萃之子以张贴抵制告示为由逮捕入狱,并宣布择日庭审。在这一情况下,阳大鹏与段氏族人协商后决定直接劫狱,将段拔萃与其子救出。清廷得知段拔萃被救出后,对县令李金芝亦有处分,“查明耒阳匪徒起衅根由,请将办理不善之知县革职一摺。……并参撤之前任耒阳县知县李金芝,前于段基望等纠众劫犯阻考鬨堂一案,亦有应得之咎,准其各归本案,由该抚彻底严查,分别定拟具奏。其署耒阳县事江华县知县叶为珪,署任年月,并著确切查明具奏。”[14]3413原地方知县李金芝被罢黜后,又重新调来叶为珪主政地方,段拔萃被救出后,又自行前往湖广总督衙门投案,“其党杨大鹏等纠众赴县劫而纵之,段拔萃寻赴湖广总督衙门投首”[15]36。
将段拔萃救出后,耒阳东、西两乡民人拒绝向官府交粮,在地方上段、阳二氏与宗族头人等组成了公局,向县中民户直接征粮,并招募乡民进行训练。“段大鹏率人日造兵械,招募乡愚,……民自为铁碑,造告示锲其上,遍立四乡,官遣人仆碑,拘立碑者,遂作乱”。[15]36段、阳二氏派人阻止粮户进城向官府交粮,减少了地方政府税收,稳定的税收是地方政府得以维持运转的关键,这一举动被叶为珪视作叛乱之举,遭到地方政府的强力反弹。在叶为珪派兵弹压过程中逮捕了阳大鹏的弟弟阳大鸠,随之阳、段两家的暴力行为进一步升级。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夏五月十七日,阳大鹏与僧倡贯、郑星木等人在西乡起事,他们聚起千余人的队伍向耒阳城进发,并得到了东乡响应,蒋文昌、蒋庆云兄弟亦在观音阁、道子洲等处聚集乡民加入阳大鹏的队伍中来进攻耒阳城,但是县城连攻不下,在二十三日时义军甚至动用了大炮,“三炮以松树为质,实药百余斤,……至是则三发三裂,自杀数十人,乃退”[15]36。事发后城内兵士向外送信时皆被义军所阻,最终只能“诈为卖浆者,内文书履中,始得达衡州。”[15]37六月初六日报闻,道光对此事十分震怒,下谕:“匪徒抗粮滋事,纠合至千余人之多,并敢持械攻城,拒伤官兵。实属罪大恶极,必应迅速剿办,净绝根除。”[16]湖南巡抚陆费瑔、提督石生玉与总兵英俊奉旨带领五千清军来围攻阳大鹏,六月中清军进军西乡鱼陂洲,阳大鹏不敌溃逃,败走杉木岭,后被押解至京师遇害,至此该事件才算结束。
四、地方善后及时人反应
该事件平息后,清廷对耒阳大力的进行了整顿,首先对地方知县进行了撤换,“前署知县叶为珪征收钱漕,既经查有匪徒捏冒约总事,并不严拿究办,另举验充,仍饬差追,以致刁民藉口,实属办理不善,叶为珪著即革职,以示惩儆。”[17]将诱发地方动荡的知县裁撤,亦对于地方上作为交代。随后数年对县令的替换亦是十分频繁,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始,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之间,在耒阳已经换了六任官长,分别为李金芝、叶为珪、雷铎、徐台英、金叩、刘悳熙。侧面反映出了清廷认为耒阳极为难治,试图通过频繁调换官长来调整施政政策,从而保证局面稳定,除对于官长的撤换外,清廷也亦裁减了地方浮费:
又另片奏耒阳士习民风,夙称刁悍,如私藏军器、敛钱议事及刊刻无名传单,均请严禁等语,著即照所议严行饬禁。至该匪等叠次控告钱漕,以书差浮勒为词,著将里差名目永远革除,饬令各乡议举约总甲长,由官点验,按年轮充,以除积弊。其余一切善后章程,著该抚悉心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查耒邑完纳钱粮,向系以钱折银,运至省城易银解司,倾镕折耗,烦费滋多。收兑漕米,涉历河湖,需用亦复不少。官吏遂不免假公济私,任意朘削,致启讼端,现已裁减浮费,明定章程,并严禁占匿拖欠包完垫完之弊。惟该县仅设驻城把总一员,额兵四十名,情形单薄,应添千总一员,兵丁八十名,以资保卫。请将酃县千总一员,移驻耒阳县城,另拨外委一员,移驻酃县。所添兵八十名,以二十名驻县城,以六十名驻东乡适中之下东湖地方,归新设千总管辖。下部议,从之。[18]
可以看到,清廷平定地方骚乱后,对于地方积弊有所裁革,但其处理的逻辑也仅仅只惩处胥吏和里差,禁止地方民众的反抗,增添军队以备非常,这本是朝廷对地方动荡后十分寻常的处理办法,然而漕粮征收却仍是如故,只言要“裁减浮费,明定章程”,该举措并未能消除在耒阳地方的积弊,但实际上事变发生的原因并非在此。
清代人口的数量有着极大的增加,然而州县数量却并未有太大变化,在当时全国有1200至1300个县,[19]5清廷依靠这些基层机构来对全国广大的民众进行管理以及征收赋税,这些县要分别管理几万到数十万的人口,但州县在人员配置上与前代并无太大差别。虽人口增长,然而朝廷对于州县的经费调拨并不充裕,地方官员时常需要以自己的薪俸来支付公共事务支出。如雍正时田文镜上奏:“臣查各府州县之城垣未修久也,盖府、州、县城垣历年即久,不但残缺,其少有残缺者,臣经以饬令地方官不时捐资修整。”[20]513可见至晚在雍正时依然需要下层官员自行维护塌毁的城墙,虽然中央经常会资助重大的水利工程修筑,但到17与18世纪,地方更小的水利设施如堤、陂确是由地方上的经费来筹办。中央所允许的地方官员合法收入显然无力支付额外费用,地方州县的长官都无法获得足够收入,更不必说手下的各班衙役,他们在地方对民众压榨也就无法避免,若是无法通过清廷所制定的制度获得合法收入,对于基层的办事者来说,本身并不受太多道德约束,充作贱役的目的就是为了养活自身,那么对于普通民众的盘剥自然无法避免,因而陋规之弊朝廷虽屡次禁止,但却始终无太大成效。
在裁处叶为珪后,清廷委派徐台英作为新任知县,徐台英入《清史稿》,他在分析阳大鹏之变后的地方乱局时,认为发生变乱的原因在于丧失了对地方民户与田土的掌握,“有贱丈夫焉,不胜其好逸恶劳之心,欲安坐以待钱粮之至,因循浸久,遂成包征包解之痼疾”[21]7。他将弊端归于地方官员的懒政,实际以地方政府人员配置,并无足够能力对全县各乡人口都进行覆盖,这一做法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地方也无法承担此种官僚机构的规模。其次是在地方官员对征粮底册的管理日益混乱,无法确切掌握地方土地的实际流转,“今一切懵然不知,日坐深衙门牌饮酒,奏销至矣,民欠奈何?官曰无忧也,有柜书在,包解而已矣,……彼里差者有所不为也,惟代垫而后可以禀官追给,惟禀官追给而后可以鬻人之妻,卖人之子,据人之产而百姓将无词。”[21]8地方官员对于地方土地无意核查,致使里差为民代垫钱粮,但代垫后的民众仍要向里差缴粮,里差的代垫并非无偿,他们所索求的回报自然比正税更多,地方百姓告解无门,最终酿祸。针对以上问题,徐台英上任后做了如下改变:
事平,台英遂尽革里差,时上官欲命举甲长以代里差,仍主包收包解,台英以甲长之害,与里差同。因集乡绅问之曰:“巡抚命汝等举甲长,何如?”曰:“无人原充。”台英曰:“甲长所虑在不知花户住址,汝等所虑在甲长包收,吾今并户於村,分村立册。以各村粮数合一乡,以四乡粮数合一县。各村纳粮,就近投櫃,粮入串出,胥吏不得预。甲长只任催科,无昔日包收之害,此可行否?”众皆拜曰;“诺。”台英曰;“隐匿何由核?”众曰:“取清册磨对,有漏,补入可耳。”曰:“虚粮何由垫?”曰:“虚粮无几,有则按亩匀摊可耳。”数月而清册成,粮法大定,大鹏之乱,诱胁者多。台英禁告讦,一县获安,以忧去官。[22]13067
徐台英将对地方粮册重新进行编订,各个花户被重新纳入村中,将里差裁革后,地方官府的权力进行了收缩,赋税征收权下放至民间,在各乡设封柜使民众可就近完粮,使他们并无路途之虑,免受里差对自身的盘剥。徐台英将里差责任归于乡里,但在地方上绅士作为有着巨大能量的人,不可能不对地方税收施加一定影响,数十年后,面对太平天国所造成的乱局,清廷将地方上的征税权与兵权下放,终使地方在日后逐渐脱离了中央控制。
阳大鹏起事对当时文人亦造成极大震动,冯桂芬当时作为广西乡试的正考官路过衡州,有江浙在湖南为官的人为其陈说此事,但多有不符,“近时积习,官与民相诟,而官诬民尤甚,文恭尝为余言:‘吴民驯懦州县已甚状,公可谓有平心,而余几为官楚者所绐矣’。”[15]37可见当时民与官二者相仇,官民关系已然不睦。魏源亦注意到了耒阳事变,他认为漕运制度的弊病,正是为这些包税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其言:“崇阳圜万山中,胥役故虎而冠,凡下乡催征钱粮漕米,久鱼肉其民。”[23]11魏源所言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崇阳的钟人杰起义,而后阳大鹏复蹈其辙,阳大鹏与钟人杰二者行为同归而殊途,叹道:“呜呼!国家转漕七省,二百载来,帮费日重,银价日昂,本色、折色日浮以困。于是把持之生监与侵渔之书役,交相为难,……而湖南耒阳复以钱漕浮勒激众围城,大吏至,调两省兵攻捕于瓦子山、曾波州,弥月始解散,俘生员欧阳大鹏等于京师,论功行赏,与湖北崇阳一辙。”[23]12冯与魏二人都将生监视作在地方上的包税者,地方胥吏作为地方税收中实际的执行者,也是刻削于民,但这些胥吏作为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一部分,他们的作为如若激起地方事变就会受到朝廷严厉惩处,但在大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被地方官员所默认。
清代税收制度多承袭于明代,即对于人口以及土地的确切统计,一为人口清册,记录人丁的田赋以及各项劳役;另一项则是土地清册,记录应纳税土地的数量,位置及拥有者。在明代时设立里甲制作为赋税征收的基础,迟至明中期后,里甲制因各样的原因而难以为继,里甲本身亦从代表人口与家庭的单位,转变成了对政府进行纳税土地的单位。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里甲逐渐转变成为纳税土地的单位后,民众对地方政府纳税数额仍是不变的,固定化税额使得地方政府的支出无法满足,在征税过程中自然会频繁出现缺额,地方税收不足,在此后发生了耒阳地方上的胥吏对民众的盘剥,以及为对抗盘剥所引发的阳大鹏等人的抗税行为。这也是在清中后期,清廷无法对民众新开垦出土地进行全面统计的结果,但在当时清廷无力也并不愿推行这一措施,任何加税行为都被视作是“与民争利”,长期儒家教育使得君主更倾向依靠“仁”来完成对于国家的治理,例如在地方受灾时宣布蠲免赋税,来显示君主深泽厚恩,任何赋税增加则被视作刻薄小民,动摇国家根本。这一观念使税收长期保持固定数额,同时对地方州县的留存亦十分有限,短缺的银两使州县官无力承办地方上的公共事务,官员升迁所考核的是税额是否完纳,他们自然会与胥吏二者相互联合,在盘剥乡民后与胥吏联合并共同分肥。
这一行为与生员的利益是相背的,明中后期科举制功名的终身化与免税特权也被清代所继承,这些特权也使生员和监生们形成了新的阶层,他们借助特权向乡人收取银钱来代缴税粮,以便使得自身获益。在乡民们看来,与地方上的绅士打交道是麻烦的,然而与贪婪的胥吏打交道,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因而民人更为倾向借助绅士作为与官方的中介。在地方上税收若不是被胥吏控制,那么便是被绅士所控制,鸦片战争后,地方税收的增加使得绅士试图全面控制地方财富,以减少清廷对于地方的榨取。但这在道光帝的眼中,对地方政府征税权的夺取已经威胁到了朝廷安危,只能速派大兵剿灭,二者绝无共存可能。
五、结语
道光时期耒阳所发生的阳大鹏之变,其中有大量的当地绅士亦进行了参与,这在此前是十分罕见的举动,因绅士地位的获得在于国家的授权,绅士依靠国家所赋予的特权得以生存,相对于国家来说还需要绅士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二者相互承认且利用。但在鸦片战争后清廷的财政压力陡增,加重了对于地方的盘剥,同时长期固定税额使得民众对任何赋税增加都难以接受。
而在耒阳这一事件中又显示出了绅士与国家相背离的一面,绅士们联合设立公局来反抗地方政府,借助公局直接向乡民收取税粮,并直接建立武装来反抗当前统治秩序。阳大鹏借助东、西二乡所组成的武装进攻耒阳城,若是成功,那便是直接接管县城,但之后又是如何发展我们也不得而知。此前官府将绅士视为与民众间的中介,乾隆时汪辉祖曾言:“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某乡有无地匪,某乡有无盗贼,吏役之言,不足为据,博采周谘,惟士是赖。故礼士为行政要务。”[24]10但在此时绅士变成了联合民众与官府进行对抗的反叛者。此后西方力量的不断进入,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积累,终在阳大鹏之变数十年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廷在太平军军事胜利的不断冲击下,逐渐丧失了自身权威与合法性,在官方武装溃败后,只能寄希望于地方团练来重新恢复社会秩序,出于环境压力或者自身利益的诉求,掌握武力的绅士开始频繁的侵夺官府的“正式权力”,表现出强烈的自治倾向。[25]随着清廷对地方上的控制也被逐渐削弱,只能依靠地方精英控制和稳定地方,这一过程中,中央的政权与财权二者都相继萎缩,阳大鹏起义或成为此后绅权不断扩张并与地方官府冲突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