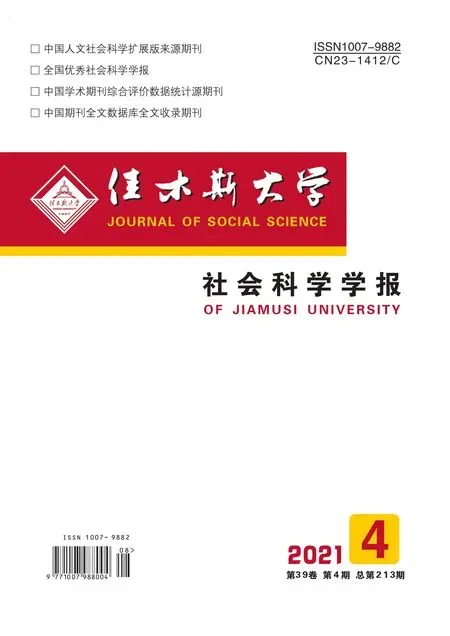柏拉图洞穴喻的后殖民解读*——以康拉德《进步前哨》为例
2021-12-07安芳慧
安芳慧,周 苹
(黑龙江大学 西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引言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著名的英国小说家,其“现实浪漫主义”的写作特点引起了学界大量学者的关注。康拉德于1857年出生在当时沙俄统治下的波兰,年轻时作为水手去了法国,定居英国后继续随商船航行至非洲、南美等地,足迹遍及全球,进而他的写作风格受到了4个民族文化地区的影响,同时受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的影响,康拉德作品继承了浪漫主义的特点,结合他海上所见所闻的经历,对20世纪初帝国殖民背景下的社会、人性展开了讨论,逐渐形成一种其特有的“现实浪漫主义”特点。《进步前哨》(“An Outpost of Progress”)是康拉德1896年出版的一篇短篇小说,环绕两个在非洲管理贸易站的白人所展开,小说最后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两人发生了冲突争吵一人被误杀,另一人之后也选择了上吊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自“文明”的他们均再无法回到原本的“文明”世界。
文明与野蛮是后殖民批评家们重点关注的一对概念。“后殖民”是一个历史性的术语,当一个国家终止了他对另一个国家的殖民统治虽然殖民终止,殖民地的民族赶走殖民者的军事统治势力,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但是殖民国家对其文化、社会、思想产生的影响,并不会随之停止,甚至可能会一直影响下去。大部分殖民者们都打着文明教化野蛮的旗号对当地的土著作威作福,追求自己的利益却不顾他人的死活,小说中康拉德将文明与野蛮解构,“野蛮”的土著对“文明”的白人反而产生了教化的影响。
无独有偶,柏拉图的洞穴喻也强调了教化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一开始人们在洞穴中被铁链锁住受环境因素限制对世界的认识只是若隐若现的影子;之后那个被放走的人看到了真实的火光,出了洞穴之后又看到了阳光下的世界,认识到了自由、真实与文明;但是当他返回洞穴,把外面的世界描述给同伴们的时候,洞穴里蒙昧的人们反而认为他在胡言乱语甚至还可能杀死他。从后殖民的角度来看,康拉德《进步前哨》中的两位白人主人公出于教化目的赶赴西非,最后反倒被这些“野蛮”、原生态的文化教化了:他们从“文明”的洞穴走了出来,“野蛮”的世界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最后被代表“文明”的公司抛弃最终自我崩溃,这一过程恰恰和柏拉图的洞穴喻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之处。但小说中的教化现象与洞穴喻中的教化又有怎样的不同呢?知网上研究康拉德《进步前哨》的中文期刊仅有十几篇,多是从象征、后现代文明主题、话语分析等角度进行文本分析,国外研究《进步前哨》的论文也很少,研究方向也与国内大致一致。本篇论文将用后殖民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身份认同(Identity)、他者化(Othering)这三个概念分别对小说中与洞穴喻类似的三个认知阶段进行解读与类比,挖掘康拉德对文明与野蛮超前的解构理解与哲学思考。
二、欧洲中心主义——“文明”的洞穴
小说中两位代表所谓主流文明的白人主人公经过英国社会文明几十年的教化已经形成了“文明”白人的价值观。从后殖民视角把他们的角色投射到柏拉图的洞穴喻中,与之相对应的,他们就是被锁链绑住困在洞穴里的人。他们完全靠生活在欧洲文明中的白人社会进行“影影绰绰”的有限认知,而在他们的认知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当时欧洲各国所宣扬的欧洲中心主义。
简单来说,欧洲中心论认为欧洲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优越[1]41-52,158,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就是以欧洲文化为衡量标准,贬低其他文化的存在价值。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假定的阶级优越性。这种价值观带来的其中一种影响就是19世纪20世纪欧洲各国向世界殖民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并不觉得殖民有任何的问题,他们反而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他们把光和文明带到了未开化的土地上,教化当地的土著,让他们见识文明,而实际上,他们其实是在用一套冠冕堂皇的理想化思想自我合理化对其他文化不尊重、造成伤害的事实。
受这种“文明”洞穴的影响,所有康拉德在《进步前哨》中描写的白人或多或少地都有一种高高在上、自我感觉良好的优越感。小说中提到,两个主人公在打发时间的时候,找出了几份国内的旧报纸,上面夸夸其谈地讨论了什么叫做“我们殖民地的扩展”[2]8。报纸上宣扬了作为文明人的权利和责任,认为传播文明这项工作是非常神圣的,并且赞美了那些四处奔走把光明信仰和贸易带到地球的黑暗地带的人的丰功伟绩。两个白人主人公读完之后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并且为之自豪,并且幻想百年之后,西非土地的文明史上会记有他们两个的名字[2]8。可笑又可悲的是,这两个人仅仅在这片土地上待了半年就相继离开了他们的“文明”世界。
非常讽刺的是,小说中两个白人主人公所在的跨国公司叫做“伟大文明”,这家“伟大文明”公司在西非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只需要两个白人管理,十多个从别处运来的黑人奴隶进行守卫的贸易站。更讽刺的是,公司董事把凯亦兹和卡利尔他们二人送到大洋彼岸的贸易站后说了一大套客气体恤的话,告诉他们这里的贸易前景大有可为。可是转头回到汽艇上,对着自己的老仆人却说终于甩开了两个笨蛋,贸易站这点儿盈利毫无用处,半年之内都不用理他们的死活了[2]3。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统治阶级的眼里,文化与教化只不过是他们用来统治世界的工具,而一个个独立生活的人与个体也只不过是在他们手下做事的笨蛋,而他们眼中的伟大文明,只不过是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从后殖民的角度来看,欧洲社会所推崇的欧洲中心“文明”,无疑是“野蛮”的。他们运来一些所谓的“野蛮人”,肆意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随意支配,这种行为恰恰是非常野蛮的;对待当地合作的向导马可拉时,没有丝毫的尊重,张口就是混蛋、魔鬼和畜生,这种态度是野蛮的;用劣质的生活用品换取当地人珍贵的象牙从而牟取暴利,将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对其他人的不平等欺骗上无疑也是野蛮的。平时斯文、体面的文明人也会干出特别野蛮的事。他们口中所谓的文明也只不过是一件美化、遮掩野蛮行为的虚伪外衣。
三、身份认同——洞穴外“野蛮”的世界
身份认同是一个旧身份不断分裂,新身份不断形成的去中心过程[3]37-44。经过几十年白人“文明”社会的教化,凯亦兹和卡利尔这两位主人公现在突然来到了非洲相对未经开化野蛮原始的环境当中,此时的他们就好像是从“文明”的洞穴中走向了洞外未开化“野蛮”的世界。受其影响,他们对原来的文明世界的世界观产生了自我怀疑的同时,试图去适应这个“野蛮”的世界。
小说中两位白人主人公虽然对能亲手建造新的文明世界有着一种骨子里的自豪感,但是他们的感觉能力并没有被“文明”麻醉到麻木和迟钝的程度,他们仍然能感受到一份无助的孤独感。“他们忽然被孤立无援地抛弃,面对一片荒芜,却感到非常孤单。这片蛮荒包含着蓬勃的生机,神秘地闪现出来,这就变得更为神奇,更为不可理解”[2]3。其实他们也只不过是两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凯亦兹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攒一笔嫁妆才来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卡利尔是一名退役军人,仅剩的自尊心让他没办法再在亲戚家蹭吃蹭喝,决定自食其力才接下这一份苦差事。他们在文明、群居、无忧无虑的世界里呆得太久了现在不得不独自来到这样一个野蛮、荒芜、让人压抑的世界。
其实他们所熟悉的白人文明社会,给予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并不高。康拉德在小说中提到,白人社会确实曾经细心地照顾过他们两人,但这不是出于任何的善意,而是因为一些“稀奇古怪的需要”,社会“禁止了他们所有的独立思想,所有的首创精神,所有超越常规的事。他们只能在成为机器的情况下生活。就像无期徒刑的囚犯被囚禁多年以后获释一样,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自由才好,这两个人缺少实际锻炼,不会独立思考,不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能力”[2]5。“文明”社会确实教化了他们,但是也同化、统一了他们。以前在城市里,他们两个每天都很忙碌似乎不会迷茫。作为维持社会运转的齿轮,二人一直在进行机械性的工作,并没有在文明社会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一下子让他们离开城市的喧闹,接受整个世界的寂静与自由确实很难,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直被好吃好喝地养着,可是一旦把它放回到野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生存下去了。他们一直尽力又勉强地维持心理的平衡。到了非洲他们两个什么事都不用做不用担心每天的生活,只是游手好闲然后变得更加昏庸懒散。刚开始他们还可以怡然自得,可是随着时间慢慢地过去,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看到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河马,鳄鱼还有一望无际的森林。一切的走向没有文化宣扬的那样走向进步,反而变成了静止、退后。生理上,他们两个人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精神上他们的脾气也都急躁了起来。唯一苦苦支撑他们继续下去的动力就是他们自诩高级、高尚、文明的进步追求。
可是这最后一丝假想的麻木安慰也被这片“野蛮”的土地上的“野蛮”打得粉碎。和追求高级文明进而时刻都保持得体大方、体体面面的当地黑人向导比起来,这两位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文明人已经变成了无能的废人;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他们还不如当地的野蛮人强壮果敢。平时和当地的土著做的贸易一直是由黑人向导独自交流协商的,两位白人主人公也乐得清闲,可是这样暂时的平衡被一支异军突起的部落小队所打破。这一支部落小队并不是当地的土著,他们跟别的部落打仗,抢夺财富,抓女人和小孩,每个人都极其强壮,他们的首领和黑人向导马可拉偷偷达成贩卖人口的交易,用这个贸易站仅存的10个奴隶兵和当地的一些土著黑人,来交换他们抢夺到的象牙。两个白人全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只顾着在晚上和这些来做生意的土著一起喝酒吃饭,结果第二天早上醉酒醒来,发现昨夜和他们喝酒的所有黑人全都不见了,还发现了一具反抗黑人的尸体。这件事情带给凯亦兹和卡利尔的冲击很大,在小说的结尾,送补给的汽艇迟迟不来,他们的物资短缺,心态逐渐崩溃,互骂对方伪君子,奴隶贩子:“就我自己也是个奴隶贩子,在这个该死的国家里没别的,只有奴隶贩子”[2]21。两个人之间的谈话越来越激化,最后两人因为要不要在咖啡里放糖这件小事而动起手来。卡利尔被凯亦兹开枪打死,凯亦兹也选择了自杀。
从整体上来看,发生在卡利尔和凯亦兹之间的悲剧可以被理解成为二人追求身份认同感失败的结果。为了让自己本来的生活过得更加有意义一点,二人选择来到这个“野蛮”的世界,可是远离了以前禁锢他们的文明社会之后,两个人在西非的土地上仍然被一座无形的监狱困住了,而这座无形的监狱就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他们渐渐地发现在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文明,在野蛮面前毫无用处,没有任何优势,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给他们徒增烦恼。所以最后二人情绪爆发选择了以这种最原始的方式解决问题,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而最后他们的身份,既不是文明的,也不是野蛮的,他们是这两种身份的杂合体(hybrid),陷入了二元对立相持不下的僵局。
此外,当地的黑人向导马可拉也可以被看作是文明身份与野蛮身份的杂合体。马可拉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斯文的英文名字,叫做亨利·普赖司(Henry Price)。小说里描述当地的人们都叫他的原名马可拉(Makola),和加纳一个著名小集市的名字相同,而他自己从来不用他的本名,从头到尾一直用英文名字。英语中“price”有价值、价格的含义。马可拉既想要在白人文明面前展现他的自我价值,又被白人“物质”的世界深深影响。在文化程度上,马可拉可能学习得不算出色,可他却把白人文化里的劣根性学了个十足十——他竟然可以为了象牙,轻轻松松地把自己的同胞当作奴隶和物品卖给别人。后殖民评论家们把这一种殖民现象叫做模仿攀附(mimicry),认为这种现象多发生在顺从殖民统治的被殖民者身上。殖民者向他们灌输了高级文明的观念,成功地把他们洗脑。这些被殖民者们,希望自己能被高级文明认可,所以竭力地去模仿“文明人”的言行举止和生活习惯,这种现象间接地反映出他们对自身文化缺乏归属感和不自信的心态。而归根到底,这位黑人向导,也是在追求自己扭曲的身份认同感。
四、他者化的幻灭——回归“文明”洞穴的失败
一直到卡利尔和凯亦兹两人之间的冲突爆发之前,他们都在“翘首以盼”,希望“伟大文明”号汽船可以立刻出现在他们面前,给他们运送补给物资,甚至幻想大船可以尽快接他们回家。可是卡利尔和凯亦兹都没有机会和之前“文明”洞穴里的人再生活在一起了,甚至凯亦兹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意回归白人的“文明”社会。小说结局凯亦兹的自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他者化的幻灭。
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源于殖民者一厢情愿的优越感,土著居民被他们理所当然地定义成野蛮、落后、未开化的原始人,觉得只有他们的文化才是文明、高级的,这样一来殖民者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而被殖民者则被他们进行边缘化的处理。殖民者聚焦于“自我”,认为自己文明中的价值观体系才是正确;而此外的所有人都被当作“他者”,被殖民者归为异化、低下、劣等的异类,这一过程即被称为他者化过程。
可是一旦这样“他者化”地想问题之后,就会造成一种结果。那就是,“文明”的世界将只有一种由统治阶级制定的对错、价值观体系。这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姑且不提,“他者”文明中所认为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有多么科学或者多么正确,因为本质上科学或正确与否与这种文明能否存在并不矛盾,殖民者们不应该并轻飘飘的一句“他者”就把一个客观存在的价值完全抹杀。
凯亦兹最后选择自杀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对“文明”的逃避。在这片孤寂的西非土地上,凯亦兹和卡利尔见识到了一个与之前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程度完全不同的部落。贸易站旁边的部落中也有德高望重、修养极高的智者,身强体壮的部落首领,部落和部落之间也会存在打斗与扩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者”文化与殖民者们沾沾自喜的高级文化及四处殖民的冷酷行为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就破坏程度而言,“文明”甚至影响力更大一些。在小说的最后,凯亦兹听到了远方传来的汽船鸣笛声,“好像什么被激怒的残暴的野兽在嚎叫。进步在河里呼唤着凯亦兹哪。不但进步,还有文明以及种种美德哪。社会在呼唤着他的有造诣的孩子回来,照料他,指示他,审判他,定他的罪。它呼唤她回到垃圾堆上来,他是从这垃圾堆上远走的,如此才合乎公道”[2]26。凯亦兹误杀了卡利尔,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此时的凯亦兹对高级文明的崇拜幻想已经完全破灭,此时此刻他已经不想让所谓的“文明”来对他进行审判,在他眼中可能“文明”杀的人比他要多得多,可能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会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来逃离这个世界。
但同时我们也应考虑到凯亦兹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他可能没有反殖民主义思想家激进、先锋的思想,他可能做不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这种境界,那么他听见汽船鸣笛声后为什么还要选择自杀呢?我们也可以把凯亦兹的行为理解成为一种最后的坚持,即使这样孤独的坚持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可能凯亦兹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他当时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他这么多年“文明”教授给他的教养,在这份教养面前他不是一个特别先锋或是坚强、清醒的人,面对这个情形他有一丝懦弱,而他懦弱的原因就是他实在不忍心,或者说,不敢打破他的这份教养——教养就是他仅剩的底线,面对这条底线凯亦兹没有办法轻轻松松地就跨过去。尽管此刻他对他者化的价值观已经全然幻灭,可他还是想要尽最后一丝“文明”人的体面,对自己开枪打死卡利尔负责。即使这样孤独的坚持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可凯亦兹还是想要给卡利尔和他自己一个说法。而此时被“文明”抛弃的凯亦兹已经比大多数欧洲的“文明”人高尚许多了。
五、结语
康拉德的《进步前哨》无疑是一部立意深刻的短篇小说,两个白人男性被欧洲“伟大文明”公司派到位于西非的殖民地负责与当地的土著进行贸易,但是来到海边的贸易站之后,他们只是待在贸易站的小屋里,欺负老实的那一部分土著,肆意地作威作福;当二人面对比他们还要强横的土著时,便立刻陷入了无能为力、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本着教化目的的他们反而被这些“野蛮”、原生态的文化教化了。他们期待汽船来接他们回去,可是对“伟大文明”公司来说他们只是两个听话、愚蠢的傻瓜。日复一日的等待让卡利尔和凯亦兹对“文明”的崇拜幻想全然破灭,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从后殖民的角度来看,小说《进步前哨》中两位主人公从“文明”走向“野蛮”的经历,与柏拉图的洞穴喻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一开始接受“文明”洞穴的教化,到触碰洞穴外的“野蛮”世界,再到回归“文明”洞穴的失败,这一过程也与后殖民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身份认同、他者化这三个概念能够高度契合。康拉德巧妙地解构了文明与野蛮这对看似对立的概念:它们只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两种状态而已,而且这两种状态是互相依存的,当文明嘲笑野蛮的同时,所谓的文明也在自我消解。
在殖民者看来,没有西方人的支持和领导,这个世界的偏远领域简直就没有生命、历史、文化可言,没有独立或完整可言。用康拉德的话来说,如果那些地方有什么可写的东西,也不过是些腐朽不堪、堕落败坏、无可救药的现实[4]50-55,而这些现实恰恰是由殖民者们打着“文明”的旗号实际上却在做一些“野蛮”的事情造成的。从后殖民的角度来看,“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人们没办法一刀切式地做到完全的“文明”和完全的“野蛮”,康拉德一百多年前于《进步前哨》中所反映的这种扭曲、歧视“他者”的现象值得我们现代人的关注,这对我们尊重现代社会中的多元化、多样性也会带来一定的自省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