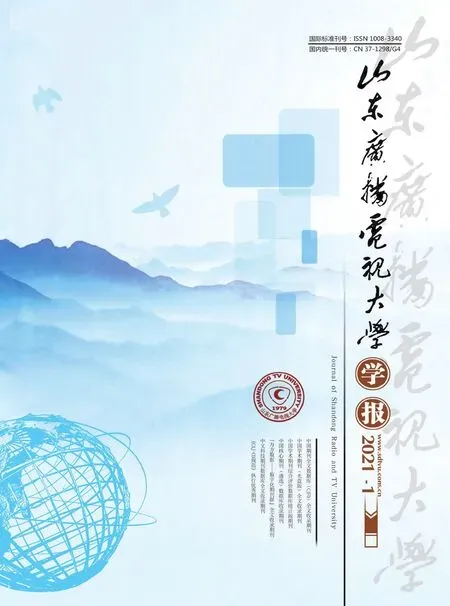现代人困顿踽步的生活日常
——威廉·格纳齐诺小说《幸福在幸福远去的年代》叙述主题的三维分析
2021-12-04杨扬
杨 扬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继2004年斩获德国文艺界最具权威的“毕希纳文学奖”后,威廉·格纳奇诺又于2007年获得“克莱斯特奖”,2013年因其幽默荒诞的创作风格将“卡塞尔文学奖”收入囊中,2014年格纳奇诺被授予文化奖章——法兰克福“歌德徽章”,成为德国出版界和评论界的热议作家。
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幸福在幸福远去的年代》被作者本人称为是“回归现实主义的小说”。[1]此外,格纳奇诺还将这部小说列入德国批判性时代小说的行列。小说主人公Warlich是一位研究海德格尔的哲学博士,当他27岁博士毕业想在大学和社会上寻找相应工作时,却四处碰壁,无奈之下只能“大材小用屈居”[2]为一家洗衣店的送货员。事实证明,这位研究海德格尔的哲学博士的确能力过人。经过几年的经营,洗衣店规模壮大,承接订单可观。现年41岁的他也成为了这家本城大型洗衣店的管理负责人,和他的女朋友本城一家银行分行经理Traudel一起住在一间三居室的公寓里,过着“中等阶级”[3]的生活。但对哲学的追求一直萦绕在Warlich心中,经过痛苦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Warlich对现有的工作和生活几乎失去兴趣,也因一次工作时间在街边观看游行,被老板辞退,彻底与现实生活割裂。在无法理解男友内心的困惑和痛苦的情况下,Traudel最终亲自驱车将Warlich送进了精神病诊疗所。格纳齐诺从不同维度将以Warlich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人的压抑困顿呈现在读者面前,激发共鸣,引人深思。
一、观察者身份下的城市漫游记
格纳齐诺笔下的人物大多和作者一样,生活在法兰克福。格纳奇诺深谙书写人物,同时也是在记录城市的道理。早在其1999年出版的散文集《延伸的目光》中,他就开始对笔下人物眼中的事物进行尽可能细致的描述,力求再现城市生活日常。“通过对大都市的文学性描述,…… 有利于深入研究现代个体身份塑造视角下个体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文学性文章就是展现这种联系的场所,在此,作者通过对现有的城市空间内个体感知和城市特性的描述,突出主体的身份探寻。”[4]观察成为了主人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纽带。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Warlich极度敏感,对身边的人和事观察细致。对外界的观察之于他可以说是一种享受,较之于坐在办公室里调度车辆、统筹业务更能让他获得愉悦感。在他的眼中,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忙碌的人们都是背负着这个效益至上的社会带来的重压,日复一日重复手中的工作,没有一丝一毫的激情和喜悦。
小说开篇就是Warlich对公寓附近一家拥挤的咖啡馆的描述:Warlich已经工作九小时,一天的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些许欢喜,只有在这家挤满了人的鲜有空位的咖啡馆里,他才感受到了一丝舒适。周围的人亦是如此。“我周围的大部分人显然也很疲倦。整个被抽空了,几乎一动不动坐在椅子上,让我感觉特别美。”[2]进入咖啡馆的鼓手,原本想要通过艺术的方式赚取生活的开支,结果却令人惊奇地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认为自己根本不会打鼓,也不想打鼓,更愿意直接乞讨。“他只是吹了几个拍子,然后就拿着一个纸杯,沿桌乞讨。”[2]而更令Warlich惊奇的是,周围的人忽略了鼓手拙劣的表演,还是大方地给了他钱。Warlich正极力按捺住内心的冲动,想要向周围的人宣讲现实的荒诞,却很快发现“其他人早就知道这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悲凉。”[2]由此,资本主义效率至上的社会弊端便可窥一斑,人们机械地完成每日的任务。习惯性的工作给人带来的只有麻木和冷漠。而城市也渐渐同化,变得毫无特性。“这块区域让人没什么印象,而且更糟糕的是:这里到处都是一个模样。”[2]“街道排列愈发给人一种进了一个常年无人打理的动物园的感觉。人们虽然生活在这里,但他们已然忘记他们曾经的家,如同动物园栅栏后可怜的动物。”[2]城市这个无数个体的栖身之所,和生活其中的人一样,变得灰暗、木讷、毫无激情可言。到处一片落败景象,前一年的落叶还堆积在原处,空无一人的店面,而商场门前则是成群的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人。迷茫的、固执的人、羞耻地在垃圾桶里翻找瓶子的人、蜷缩着身体的酗酒者、到处闲逛的青年法西斯分子、四处躲藏的海报张贴者、目光深沉的看门人……为了掩饰和弥补生活的暗淡无光,人们只能从外部给它披上看似光鲜亮丽的外衣。他们经常穿着“绿色的裤子,柠檬黄的T恤,蓝绿条纹的袜子,蓝白花纹的沙滩袋,还有红白方格的浴巾。”[2]似乎这样装扮以后,生活便真的可以绚烂多姿。
Warlich的教育背景和求职经历也折射出现代社会的麻木和对人们的无情压迫。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甚至是精英教育的哲学博士,Warlich研究过海德格尔,本应学以致用,“向社会传输我们最最匮乏的知识,诸如自省、批判性思维、哲学启示。”[1]但他毕业后在校园里和社会上都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只能在27岁时选择成为这家洗衣店的送货司机。这一职位无论是就他的专业还是学历来说,都是极不相称的。但这却是社会仅能为一个哲学博士提供的职位。他的哲学功底和博士头衔最后要用来为洗衣店的新策划撰写宣传稿。这一点其博士导师早就开玩笑地提醒过他:“这种教育的勋章,这里指我的博士学位,在我们的社会中毫无用处。”[2]周围的人大多也对拥有博士头衔的Warlich“另眼相看”。洗衣店的老板认为他学历太高,不适合送货司机的职位;Traudel总高估他的教育背景,对他满是仰慕和崇拜,而事实上,“我早就想告诉她,社会上有大量的像我这样的多余的专业人士,经过漫长的求学后最终决定,研究一些错误的内容,获取博士头衔。而大学只能违背本意地不去回绝这种做法。”[2]当Warlich41岁失业时,等待他的也只有物业管理员这样的工作。后来他被送进精神病诊疗所,那里的病友也大多同他一样具有博士头衔或体面工作,如Petzold博士是一位艺术教育工作者,患有间歇性妄想症;Adrian博士在北德一间气象站从事气象研究,是“最后出口”[2]患者群体的成员。如此看来,现代社会留给知识分子的生存活动空间并不是它所一直标榜的那样,是自由的,是符合发展个人需求的。
格纳齐诺笔下的城市,只是人们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家,这里随处可见的是无形的牢笼。工作场所有人被监视,居住的公寓也只是无言的空间,Warlich和Traudel在家几乎没有话题,要靠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声响制造生活气息。格纳齐诺曾在德累斯顿德国语言与文学创作学会上发言说:“城市小说在城市经历的灭亡后……就只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小说。其主人公不再……透过城市接受部分城市特性成为自我的特性。这些新的在城市中游荡的‘我’远离自身的支离破碎,因为他知道,在经济社会,捆绑消费力的现状下,是毫无个人初始感受可言的。因此,这些‘我’只是把城市看作自我内省的场所。”[5]这也正是格纳奇诺笔下主人公多沉浸于自省和臆想世界的原因。
二、尝试者身份下双重生活记
早在格纳齐诺于2009年出版的自传性质小说《女人,房子,一部小说》中就出现过“双重生活”(Doppelleben)的概念。在这部《幸福在幸福远去的年代》里Warlich也是在不断尝试,想要开启这种双重生活的模式。
Warlich毕业后从事的是和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在洗衣店他的事业发展很顺利,很快就从送货员上升到了经理。即便如此,他也无法从中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和成就感。在餐厅和其他同事共进午餐对他而言也是难以忍受的经历,“一开始我觉得不感兴趣,之后是长时间的厌烦,然后是强烈的反感,想要逃离。”[2]而老板此刻分派的任务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解脱。这种对工作,对周围的人,和对自己内心的敏感与由此产生的陌生感,使Warlich无力承担外界施加给他的强大压力,时刻与心灵的莫名疲惫相抗争,感到精力透支。“我再一次发现,人类(我)的精力只够支撑我们度过第一个半天。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发明一种‘半日生活’的项目。每一个人都应有权,在第二个半天里从第一个半天里缓缓神。”[2]他所追求的是理想化的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时满足。第一个半天为生计而承受各种压力,从事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工作,与毫无好感的人共事,为的是最后可以拿到维持体面生活的工资;第二个半天交给自己的想象力或白日梦,让精神或心灵有独立的放飞时间。受这种想法的困扰,他“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想要自己的生活走上另一条轨道的渴望,变得愈发强烈。”[2]
Warlich从不曾真正将哲学丢弃或遗忘,哲学的世界对他来说是自我解脱的一方净土,他一直幻想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我经常再次回到哲学讨论课堂,找一个座位坐下,期待着有学术委员会或任何一个人过来对我说:您来了,真是太好了。我们一直想要给您打电话,我们想要给您提供一个大学教席。”[2]正因一直抱有此种幻想,Warlich想到了开设“平静学校”—— 教授人们如何缓和焦虑、平复心绪的课程,将自己的哲学观点分享给表面波澜不惊,实则内心焦虑不安的人们。他甚至还邀请了当年的同窗Gerd Angermann博士参与授课,并建议其授课课题为:“逃离世界的自我阴暗”。[2]从Warlich平日对外界的观察和内心独白可以看出,他已长久地沉浸在自己的哲学思考中,并想要将此传播给周围的人。他经常在Traudel面前发表关于哲学或文学的长篇大论,使得Traudel对他也愈发敬仰和崇拜。
格纳齐诺在小说前半部分把Warlich对于自己的哲学修养描写得越是自信,越多地使用哲学领域的专业词汇,如自我阴暗、自我羞愧,就越能和小说后半部分中Warlich深陷精神神游无法自拔形成强烈反差。对于能够成功开设“平静学校”Warlich一直深信不疑,他深知社会中人们对这种课程的强烈需求,也为此进行了充分的课程设计,他的这一想法还得到市政当局的支持。在一切可以实现自我精神需求满足的美好愿景下,和文化局工作人员Heilmeier博士的面谈让他的心情一下跌至谷底。Heilmeier博士直接称“平静学校”课程为“流行学术”,无情地向Warlich 关上了研究严肃学术的大门,并直言市政当局早有开设此类流行学术课程的打算。“人们拥有大把的闲暇时间,但只有极少数人利用这多余的时间在真正学点东西。我们必须帮助他们!”[2]听到“流行学术”这个词,Warlich瞬间愣住。“流行学术明显正和我的计划背道而驰。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能和我的设想联系到一起。”[2]之前准备的所有开场白和课程设想顿时显得苍白无力,且课程的名称也被认为是“老旧过时的”。
一系列打击使Warlich同时享受物质生活的富足和精神生活的充沛的梦想化为了泡影。自己的哲学观点无法被他人接受,进一步使得他心中那座衡量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外部环境无法满足内心的需求,Warlich进而选择逃遁进内心的精神世界。“双重生活”的尝试彻底失败,也意味着他多年的大学学习毫无意义,学以致用在他的业余生活仍然无法实现。而后突如其来的解雇,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物质与精神的天平彻底倒塌,生活的双重性连一重也无法实现。格纳齐诺喜欢在小说中使用关于“双重”和“一半”的表达,如“双下巴”,“双层胸部”“一半的孤独”,[2]这也是作者预示生活双重性的方式。
三、选择者身份下的精神神游记
小说一半的篇幅都是对Warlich内心活动的描述,格纳齐诺在这里选用了他一贯擅长的意识流创作方法,如内心独白、思维流动和介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的自由间接引语。“在意识流小说刚兴起之时,内心独白与意识流被认为是同一概念。随着意识流小说的发展,小说对人物意识的描写更加细致,层次更加分明,意识流又演化出自由联想、感觉印象、蒙太奇、象征意义等艺术手法,于是内心独白便自然地成为意识流小说艺术层次中的一部分。”[7]作者退出全知视角,力求通过客观的叙述,将主人公Warlich推到读者面前,在了解资本社会体制下普通人日常辛劳工作的外在状态的同时,深刻解读人物内心的敏感、迷惘和矛盾。这样的写作方式,拉近了读者和小说人物的距离,使读者产生共鸣。随着在社会中的处处碰壁,Warlich也在外界社会和内心世界中摇摆不定,小说最后以开放性结尾将疑问留给读者:到底选择回到现实生活,还是选择继续留在精神诊疗所逃避?
(一)内心独白
格纳齐诺的小说中内心独白比例与描述性语言不相上下,已深嵌入主人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其行为发生偏差的主要原因。开篇坐在咖啡馆里Warlich就用独白的方式表明自己之所以倍感疲倦是因为“过度敏感和羞愧”,[2]对于自己手上塑料袋上印着的消费广告感到羞耻,他将它们踢到桌子下面,不愿让旁人看见;对于咖啡馆侍应生衣服背后印刷的菜单感到不适,当侍应生背对自己时,内心的痛苦油然而生;对于邻桌年轻人使用吸管吸取饮料而发出的吞咽声,Warlich愿意支付五欧元令其停止。
Jürgen Zenken在其《德国20世纪独白小说》中提到独白主人公的意识类型,“就主人公内心与社会关系在其意识中的映射,可以区分适应型和不适应型两种极性行为。”[8]“不适应型的我”与外界存在客观事实上的隔离;“适应型的我”则与外界社会和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及团体没有冲突,只是无法承受自己内心的矛盾。Warlich显然属于后者。他拥有高学历,令人艳羡的工作,拿着可观的薪水,在城市里有自己的住房,他人眼中温馨的家,相处多年的女友,一切顺理成章得使他称得上中等阶级人士。而其内心却急于突破当下,享受孤独,一方面Warlich渴望改变生活,另一方面他又因自己内心的各种奇思异想和不安分感到羞愧。正是这样的矛盾心理使他最终被送进了精神诊疗所。
(二)意识流动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曾明确将幻想的白日梦比作“空中城堡”,并断言“一个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未得到满足的人才这样做。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单一的幻想都是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满意的现实的纠正。”[9]沉浸于幻想中的人正是出于被压抑的内心冲动,而逃遁进精神世界,以期在那里实现现实生活中无法被认可的想法。
Warlich正是一个不甘于现状、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现代人,但对于如何改变,他没有一点头绪,于是出现了各种城市漫游途中的幻想和思维流动。“我发现在路边停靠的一辆汽车车顶上有一块咬了几口的蛋糕,……我不认为这块蛋糕属于车主,如果是车主的话,他完全可以坐在车里好好享用这块蛋糕,我更倾向于这是一个路人一边走一边吃蛋糕,由于突发事件他把蛋糕随手放在旁边停靠的车顶上,就走掉了。我觉得他肯定躲在哪里,等待时机,回来拿走他的蛋糕。他肯定不能忍受把这块美味的蛋糕送给汽车的车顶。现在我认为,这块蛋糕极有可能是他偷来的,然后被发现了,被跟踪了,在他享受美味的路上差一点被抓住。我站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货车后面,等着这个人回来。……我自己也变成了一位水果商贩观察的对象,……我觉得她认为我正在策划一次偷窃或其他的坏事。”[2]Warlich从一块蛋糕想到了蛋糕的主人,开始思考主人丢弃蛋糕的原因,进而判定主人是偷蛋糕的小偷。意识的流动极具主观性和跳跃性,如果不是发现水果商贩也在盯着自己,这种思维的流动还将继续蔓延。在河边看见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玩耍,Warlich幻想着此时能发生一起灾难,如孩子从母亲身边跑开,不小心落水,这时他就可以跳入水中救起孩子。“母亲看见她受到惊吓的苦恼的但还活着的孩子,会非常幸福,警察会赶过来给我和孩子披上暖和的毛毯,记者也会出现,采访我和那位母亲,并为我们仨拍照。在这一天之内我就会变成好心的市民榜样,年末还会因此被授予舍己为人奖章。”[2]
可事实上,“我”只是一个脑袋空空的城市漫步者,幻想着自己可以脱离现在索然无味的生活轨迹,成为一个有所作为、被人关注、不至淹没于人海的有独特想法的人。幻想儿童落水,和前面等待抓捕蛋糕小偷一样,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成为和现在不一样的人,这也同时验证了小说开篇提到的自己想要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但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臆想和对周围的揣测之中,徘徊于现实与想象之间,以至于最终幻想的生活似乎战胜了现实的处境,可以让他得到更多的满足,小说最后,Warlich陷入思考:自己真的要离开精神诊疗所,回到冷冰冰、无处吐露个人思想的现实吗?
四、结语
威廉·格纳奇诺曾写道:“艰难的作家是那些对家园怀有最炙热情感的人,他们笔下晦涩难懂的语句直射内心,拉近彼此的距离。”[10]而他本人就是这样的写作者,他的小说曾被评价为平庸乏味,多描写城市漫游所见、所思、所感,过于细节化和琐碎化,没有跌宕起伏的曲折情节,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生离死别,让读者大喜大悲。如同这部小说《幸福在幸福远去的年代》,作者用细腻的语言,通过对主人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跳跃性描述,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将一个生活在我们之中的外在平庸无奇,为生活奔波,辛勤工作,实则内心思绪汹涌澎湃的人,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因自己“过度的敏感和羞耻心”而饱受折磨,极力想要冲破内心牢笼的束缚,开启另一种生活的现代人推送到读者面前。就像小说最后Warlich面对精神治疗师解释自己的病情时所说的:“我正在经受一种伪装抑郁并伴随极度羞耻的折磨。”[2]格纳齐诺通过细腻的笔触将现代人在效益至上情感淡薄的异化社会下,蠢蠢欲动的渴望突破却又惮于变化的内心挣扎跃然纸上,告诉大家Warlich这样的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是他,是她,是他们,抑或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