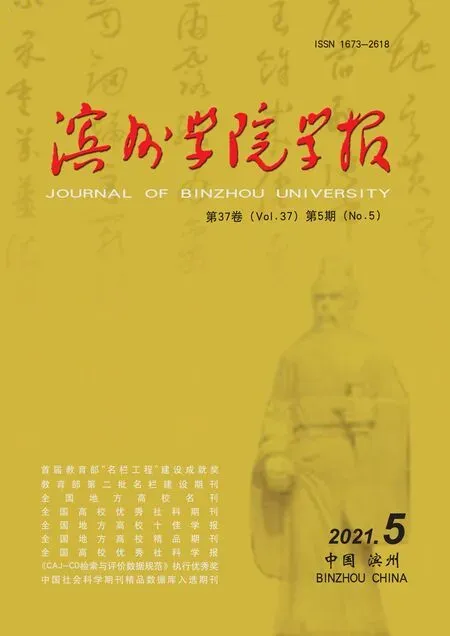徘徊于逃离与回归的路口
——莫迪亚诺的巴黎印象
2021-12-02王嘉伟
王嘉伟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在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六十载的创作生涯中,巴黎这座城市既是他作品的支撑又是他无法摆脱的挂念,但对于莫迪亚诺来说,巴黎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执念对于某个群体来说,是真实存在的,对于他们而言执念或许是终其一生而求解的心理谜题与探索的生命意义。莫迪亚诺的执念是巴黎,他把他的执念放在了作品所勾勒出的文学地图上。
一、躲避都市的挤压:逃离巴黎
在莫迪亚诺的创作中,读者对于巴黎的印象是由一个个或真实或虚构的微观地点组成的。这些场所在作品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作者来说它们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作品中的呈现来看,作者却并未给它们画上温情的色彩,相反,在作者笔下,这些场所不约而同地体现了作者最为突出的一个态度——逃离。结合《一度青春》《来自遗忘最深处》《多拉·布吕代》及《青春咖啡馆》等作品,可以发现,莫迪亚诺所注重的场所包括咖啡馆、小旅店及寄宿学校等等。
(一)咖啡馆:隔绝于世的灰色地带
自17世纪以来,咖啡馆遍布于巴黎大大小小的街区中。最初,咖啡馆多作为贵族与富有资产阶级的聚会场所,在上流社交圈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后来随着咖啡的普及与咖啡馆数量的增加,咖啡馆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举办公共沙龙的场所。人们不仅在咖啡馆中谈论日常生活、沟通感情,更在其中交流政治见解或进行文艺创作,多种思想在咖啡馆中碰撞交流,咖啡馆俨然成为新型的文艺公共领域。可见咖啡馆作为公共空间的一种,不仅有着极强的社会功能,更存在着文化功能。比如说法国作家萨特与波伏娃就同巴黎左岸地区的咖啡馆联系极为密切,二人在位于圣日耳曼大道的花神咖啡馆相识、相会,共同工作。对于莫迪亚诺来说,他同样注意到了咖啡馆的社会及文化功能,比如咖啡馆在莫迪亚诺的作品中会经常为关键人物的偶遇提供机会,或者会成为解开谜题的关键,甚至会被人物当作暂时安歇的避难所,所以在莫迪亚诺的作品中咖啡馆经常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出现的,但咖啡馆在作品中的意义又不止于此。莫迪亚诺突破了咖啡馆作为公共空间所固有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而赋予了它更为独特的意义。
咖啡馆被莫迪亚诺具化为更具私密意义的个体精神空间,它将人物与自身生存的日常空间相隔离。比如说莫氏在作品《青春咖啡馆》中指出的“固定点”概念,“船长”每天都在孔岱咖啡馆中记录每个顾客的名字等信息,他将这些信息称之为“固定点”,他也认为“必须在大都市的漩涡中心寻找一些固定点”[1]9。在这些描述中,外面的都市生活与空间是处于漩涡之中的,处于其中的居民需要寻找一些固定点不致时时被漩涡所影响,而咖啡馆的意义正是如此。咖啡馆的空间与外面的都市空间隔离开来,外面的漩涡将个体淹没而在咖啡馆的空间中个体可以得到暂时的休憩。人们或者借咖啡馆的隔绝空间躲避婚姻生活,或者排遣孤苦的厄运而享受短暂的愉悦,抑或他们通过留下姓名等极具个性的特征来确定自身在社会中存在的证据与意义。所以在莫氏的作品中,咖啡馆相对于外面漩涡般的都市空间,确是一种更具私密意义的个体精神空间。
咖啡馆被都市人视为隔绝于日常都市生活的独立空间,他们通过咖啡馆摆脱日常生活的漩涡,咖啡馆的悲剧意义也基于此而展现,即日常生活可以摆脱,但个体精神的孤独与迷失却无从躲避。此悲剧意义在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在作品《狗样的春天》中“我”曾坐在和平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产生迷失之感,“我感到自己也是迷失在一座陌生城市的旅客”[2]74,咖啡馆成为人物陷入孤立与无根状态的导火索。而在作品《青春咖啡馆》中,作者所虚构出的孔岱咖啡馆则更具代表性。孔岱咖啡馆是个三教九流人物的汇集之所,其中的人物可被分为三个群体即观察者、游戏者与孤立者。矿业学校的学生、侦探盖世里及“船长”可被视为观察者,阿达莫夫等一众人为咖啡馆中消遣取乐的游戏者,而关键人物雅克林娜则为孤立者。这个游戏的群体无时无刻不在排斥着外人,比如他们喜好拼酒,若要融入咖啡馆便要与他们拼命狂饮,他们对于异常独特的雅克林娜毫不在意甚至戏谑玩笑般地将之称为露姬,他们的种种行为无一不在排斥雅克林娜。这座咖啡馆连同其中的游戏群体对于雅克林娜为代表的这类外来人来说正是铜墙铁壁。雅克林娜来到咖啡馆的目的就是想逃避痛苦的婚姻与日常生活,但孔岱咖啡馆从未真正接纳她并给她歇息的机会,而她与咖啡馆的人物环境也异常格格不入。在咖啡馆中雅克林娜并未获得精神的慰藉,她依旧是一个孤独的精神流浪者,所以她在城市中继续逃离,最后选择了终极的逃离方式——死亡,而这对于作者来说同样如此,这是逃离希望的最后破灭。
(二)小旅店:逼仄遭弃的地下世界
小旅店这一场所在莫迪亚诺的作品中大多都是藏污纳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发生着巴黎最为不堪的阴暗事件,比如说偷情、吸毒及死亡等等。与此同时,莫迪亚诺作品中的人物多为巴黎城中飘荡的“流浪者”,他们年轻、贫困而无所依靠,只能将这些处于底层的小旅店当作“临时之家”,正是这些“临时之家”成为他们产生逃离巴黎想法的“催化剂”,作品《来自遗忘的最深处》所展现正是巴黎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旅店的这一面。作品中的“我”贫困漂泊以贩卖旧书为生,重要的是对于巴黎毫无认同与归属感。“我”所栖身的小旅馆狭小异常,“我躺在床上,房间太小,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没有凳子,也没有椅子”[3]24。而同行女子雅克丽娜的房间更是被阴暗与毒品所包围,“靠窗沿的床上,被子掀开,窗帘拉上,床头的灯罩被拿掉,小小的灯泡仍留下一片阴暗区。仍是这种乙醚的气味,比往常更强烈”[3]16。逼仄阴暗的旅馆房间对于巴黎的漂泊者来说无异于牢笼。
在牢笼般的旅馆环境中,人物呈现出一种虚无、无助的非正常生存状态。“我”与雅克丽娜在房间中吸食乙醚之后会感觉陷入虚空之中。“我们两人挤在一张窄床上,我们领受到一种虚空、清新、腾云驾雾的感觉,轻飘飘似乎被一阵龙卷风带走。”[3]20在雅克丽娜的男友出门之际,“我”还与她在旅馆房间发生关系,但欲望的释放带来的却是沉重的无助感。“一旦我又剩下一人时又感到自己重回到昨天的那个点上:对任何东西都不敢确定。我没有任何法子,只有待在房间里。”[3]36小旅馆空间的压抑将吸毒后的虚幻与偷情的恐惧不安加倍放大,最终“我”同雅克丽娜放弃巴黎逃往伦敦。毫无疑问,巴黎这座城市的空旷造成了“流浪者”的漂泊感,而小旅馆的狭窄窒息则成了他们逃离巴黎的最后一把推力。
(三)寄宿学校:精神压抑的“集中营”
在莫迪亚诺的笔下,寄宿学校对于孩子来说是个类似于纳粹集中营的存在,无论是在有一定自传性质的《缓刑》中,还是在故事性更强的《多拉·布吕代》中都是如此。在作品《缓刑》中,“我”和弟弟因身边缺失父母而在一个充满了“佣人”的家庭中生活,“我”对于母亲擅自选择的寄宿学校并无半点留恋,在一次次逃学与开除的循环中重复。
《多拉·布吕代》则表现得更为强烈,作品中老布吕代夫妇为了避开纳粹的屠杀而将女儿多拉送到玛丽亚圣心寄宿学校。学校名义上为犹太人提供保护,但实际上它被黑色的高墙笼罩在阴影之下,同样是一座禁锢人的“监狱”。“那段时间实行宵禁,她印象中的寄宿学校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墙壁、教室、医务室——除了修女们白色的包头巾。在她看来,那里更像是一个孤儿院。铁的纪律。没有暖气。吃的只有大头菜。”[4]37在寄宿学校阴暗空间的压迫下,年幼的多拉主动舍弃庇护而选择出逃,之后多拉遭到纳粹逮捕并辗转于多个兵营,最后她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名单中永远消失。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作者本人,他们在被迫进入寄宿学校之后均做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出逃。学校的冷漠与孤独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而出逃后他们所面对是更为冷漠孤独的巴黎,之后的飘零、流浪与再次出逃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死循环。实际上以作品为映射,莫迪亚诺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在冷清的巴黎空间之下的封闭循环。寄宿学校只是众多他想摆脱的负担的代表,而他也别无选择,只能陷入次次的出逃中。
咖啡馆、小旅店及寄宿学校只是巴黎对其众生压抑驱逐的缩影,作品中也有其他场所空间的描写象征着巴黎对于个体的驱逐。如给人以强烈的恐惧感的城中荒废古堡、人人企图摆脱累赘而急于出走的车站、混乱昏暗而毫无生气可言的酒吧及舞厅等。这些空间构成了繁华之都巴黎的另一种样貌,是莫迪亚诺在二十世纪对巴黎这朵“恶之花”的再度书写,作品中的人物在这些空间中游荡、漂泊,最终又都选择离开。这些场所构成的不仅是莫迪亚诺的巴黎地图,更是他的逃离路线图。
二、重拾短暂的希望:回归巴黎
在莫迪亚诺的作品中出现的场所并非只有城市中心的咖啡馆与小旅店,同时,对于他来说,执念于巴黎也并非仅限于逃离的态度与倾向。
在莫氏的小说中存在这样一类与咖啡馆等相对应的场所,即非常令人心驰神往的、独立在巴黎城市中的隔绝地带,比如说森林、大学城等。在作者笔下森林极具魅力,比如在《青春咖啡馆》中侦探盖世里游荡于巴黎街道时曾有这样的强烈意愿:“我是唯一的散步者,感觉自己远离巴黎,到了索洛涅(森林)的某个地方”[1]30,“我想离开这间大厅,到索洛涅去,继续我的闲庭信步,享受自由空气”[1]31。森林一类的自然区域对于游走于街头的巴黎人来说正是这样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向往之地,正如学者史烨婷在《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空间》一文中所指出的一般:“在他眼里,巴黎市中心是最肮脏的地方。相反,布洛涅森林是个‘由绿荫笼罩的大小湖泊、林间曲径和茶社酒吧所组成的神秘王国’。”[5]234
在森林之外还存在这样一片不同寻常的区域即大学城。莫氏作品中屡次出现的大学城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纯洁性的空间,它显示着与咖啡馆等其他区域截然不同的特点,它可以让走私贩子卸下低俗丑陋的外表而重返天真。比如《一度青春》中游走于巴黎危险交易之中的走私贩子布罗西埃,平日以插科打诨甚至无赖至极的世俗面貌示人,但一旦回到大学城他便俨然成为一名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再也不是那个声音浑浊的布罗西埃。路易心想,这现象真奇特,一个人居然有两种声音”[6]98。这种变化正是在大学城这一独立的区域空间中显现出的。除此之外,大学城还拥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即庇护。无论是谁都可以办到假学生证件,凭借证件则完全可以在大学城中来去自如得到庇护。这与大学城外的巴黎景象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照,而发挥此作用的大学城区域在作者笔下有一个系统性的称呼即中立区。比如在《废墟的花朵》中有过这一归类,“巴黎旁边的这个中立区,给了它的居民外交豁免权。越过边界——凭借手中的假证件——我们就受到了庇护”[7]44。而在《青春咖啡馆》中对于中立区有着更为正式的表述:“在巴黎是有些中间地区、一些无人地带的,那里处在一切的边缘,处于中转过境甚或悬而未决状态。在那里能享受到一定的豁免权。我本来可以把那些地方称作自由免税区的,但是中立地区更确切。”[1]95中立区在作品中就是个避风港一般的存在,它将其中的区域隔绝于巴黎城区而为他们提供庇护,而作者对于这个区域则为完全的肯定,这同森林一样,作者均对其报以了欣赏的态度。
诚然上述区域代表了作者的向往之所,但这也只是作者向往的一面,现实并非如此简单直接。森林这一类的自然区域被作者赋予了肯定的含义,对于飘荡街头的巴黎人来说,布洛涅、索洛涅森林甚或于卢森堡公园这样的空间有着轻松愉悦一类的意味,但《青春咖啡馆》等作品中也明确指出这种情况只能是“意愿”与“想象”,或者只是曾经的经历及路过时短暂的停留。而对于中立区来说,作者则有着更为明确地表示。比如在《青春咖啡馆》中,作者指明它提供的只是暂时的疗愈:“我觉得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伤口已经彻底痊愈了,从今往后我没有任何理由躲藏在一个中立地区了”[1]130。所以中立区是避难所,但它只能是提供暂时躲藏机会的避难所,它的庇护不可能会持续长久或永远,藏于其中的巴黎人终究会再返回于巴黎城中。
总而言之,森林或以大学城为代表的中立区这一类区域确是一些独立于巴黎城区的存在。这类区域与巴黎城区之间形成的对照也是确实存在的,但它们的定位也仅仅是意愿中的向往、短暂的经过或停留以及暂时的庇护,它们并不是这些飘荡在城中的巴黎人的家,也无法让他们隔绝于巴黎而长久地生存。作者笔下的这些巴黎人最终的处境仍未能得到改变,所以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回归于巴黎,而这种主动逃离却又不得不回归的状况也正是作者对巴黎复杂矛盾态度的体现。
三、深陷于巴黎执念:内外交困
巴黎是莫迪亚诺成长的地方,也是他创作的见证,在这两组场所与区域的对照中体现出的正是莫迪亚诺对于巴黎的印象与态度。逃离的想法对于他来说愈发强烈,但是他始终无法逃出巴黎的控制。逃离变为暂时性的逃避,最终无论主动或被动他只能选择回归并继续陷于巴黎的挣扎中,而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有两方面的原因值得探究,即莫氏个人的经历与战后巴黎的社会裂变。
就莫迪亚诺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他始终处于漂泊的无根状态,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宗教归属感。莫迪亚诺父亲为犹太人,母亲为非犹太人。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母亲为避免日后犹太姓氏给莫迪亚诺带来麻烦,所以在他幼时为其举行了天主教的洗礼,但这一举动却给莫迪亚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即身为犹太人后裔,他并不为天主教所接纳,而因为接受过天主教洗礼,他也并未得到犹太教的承认,就这样在宗教身份的归属上因定位不清而难以找到自己的信仰与文化根基。其二是亲人角色的失位。莫迪亚诺的父母在其幼时便处于分居状态,父亲是一个从事投机生意的黑市商人,行踪神秘而从未承担过正常的父亲职责,以《环城大道》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均可以反映出他与父亲的隔绝冷淡关系。[8]莫迪亚诺的母亲是一个剧场的小演员,每天的奔波并不足以养活其母子二人。同时母亲更是对其毫无母爱的关怀而视为累赘一般的存在。莫迪亚诺在《家谱》中曾经指明过这一点:“有时候,我就像一条没有家谱的野狗;有点过分放任自流,萌生一种幼稚的欲念,白纸黑字,详详细细写下她由于心狠和轻率,让我遭受的所有委屈。”[9]71而莫迪亚诺可以得到的唯一慰藉与陪伴正是其弟弟,兄弟二人的陪伴关系在《缓刑》中得到了体现。[10]可悲的是,弟弟在幼时便患疾身亡,莫迪亚诺最后的一丝亲情陪伴也就此斩断。所以无论从宗教还是家庭的归属上看,莫迪亚诺都是处于一个孤独漂泊的无根状态,而巴黎正是为其提供了与亲情隔绝的生存与漂泊空间。
然而对于莫迪亚诺来说巴黎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他与巴黎的关系正是他与其父母关系的反映。巴黎城中各个场所及区域几乎都有着莫迪亚诺与父母的纠缠过往,比如说上文所提及的咖啡馆等。在作品《家谱》中作者曾提到咖啡馆是我与父亲每次密会的选择场所。父母在分居几年后,父亲选择再婚,但继母对于莫迪亚诺则是万分厌恶而不准父亲与其会面,所以咖啡馆成为次次密会的掩护场所。莫迪亚诺每次都在母亲的驱赶下带着索要抚养费的任务来到咖啡馆与父亲会面,但父亲则在咖啡馆中一次次地通知要将他打发到远处而摆脱责任。所以,咖啡馆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会在莫迪亚诺的作品中成为一个排外与逃避的场所。其余的场所同样如此,寄宿学校是父亲一次次安置莫迪亚诺的去处并企图以此来隔绝父子的关系与父亲的责任,小旅店则是莫迪亚诺母子勉强度日的地点象征。对于莫迪亚诺来说,这些场所毫无例外都显示着父母对于莫迪亚诺的伤害,而巴黎正是这些场所的合集,所以莫迪亚诺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于巴黎的逃离倾向存在一定的家庭影响因素。
在与父母关系的挣扎中莫迪亚诺受到驱赶,但他对于父母却并非完全是仇视与逃避的态度,相反他曾表现出希望与父母亲近的意愿。在自传体小说《家谱》中,他表示:“一九六二年二月,我趁封斋节前的星期二放假,不顾三十九度的高烧,乘人满为患的火车回巴黎,希望父母见我生了病,会留我在巴黎住几天”[9]58。在面对母亲的苛责与冷漠时,他则选择了这样的态度:“现在我保持缄默了。我也宽恕了她”[9]71。而面对父亲的一次次排斥,他也站在父亲的角度上思考:“现在我还想,是什么神秘的命数总唆使他,将我打发得远远的”[9]95。所以结合来看,莫迪亚诺心底存在一个极其强烈的渴望即获得父母的接纳,而获得父母接纳的表现就是回到父母身边,也就是回到巴黎,所以父母的接纳便等同于巴黎的接纳即回归于巴黎。但实际上莫迪亚诺并未获得父母的认可与接纳,他一直挣扎于同父母的关系无法自拔,同样他也挣扎于同巴黎的关系而无法摆脱。
莫氏巴黎执念的外部形成因素来自城市与社会的挤压。在莫氏看来,巴黎已然是一座充斥着绝望的城市,正如他在作品《狗样的春天》中所说:“七月的巴黎,在我出生的那个七月,这座城市仿佛已被抛弃”[2]86。巴黎是座被抛弃的城市,而其留给居民的则是极度的空虚,但其居民却曾进行努力并希望改变它。同样在《狗样的春天》中,摄影师冉森想在空虚中“截取下巴黎的田园风貌:防风林,沟渠,悬铃木树荫下的路面,沙罗纳街的圣日耳曼钟楼,瀑布街的楼梯”[2]86。巴黎的城市空间是空虚与荒芜的,这种氛围中的努力态度实际上会充满温情与浪漫的气息,但残酷的巴黎并未允许这种浪漫成为现实:“他在寻找已然失去的纯真,以及为幸福和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设置的背景,但在那里,人们已不能继续幸福地生活”[2]86。冉森用照片留下的巴黎的纯真一角是刻意而为的营造,这种虚幻并不能改变巴黎的真实状态。对于作者与生活其中的居民而言,巴黎有着让人绝望的悲剧色彩,它抹杀掉一切企图改变的希望。
在绝望之外,巴黎这座城市的孤独气质同样让作者无法忍受。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其著作《空间的诗学》中曾指出:“巴黎没有家宅。大城市的居民们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11]31。这是对巴黎城市状态最真实的写照,人们生活在毫无温情可言的“盒子”中,而莫氏笔下人物所蜷居的小旅店等临时性居所正如这样的“盒子”一般,人们在其中感受着巴黎给予的孤独与清冷。在“盒子”之外同样如此,莫氏曾在作品《多拉·布吕代》中描写过巴黎的外部场景:“从那以后,我试图寻找多拉踪迹的巴黎都跟这一天一样荒凉和寂寥。我穿过冷清的街道。对我而言,甚至在晚高峰的时候,当人们朝地铁口蜂拥而去的时候,他们都一直是冷清的”[4]131。街道的清冷与人们之间的冷漠已成常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这种城市环境之下的孤独感,而承受能力终将崩溃,逃离也就成为莫氏的必然选择。
巴黎的城市特点给予了莫氏无尽的绝望与孤独,但同时虚无的体验也无时无刻不在给予其压力。这种虚无与当时巴黎所处的时代特点存在必然的联系,即战后巴黎的不堪现实。莫氏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他的战争问题思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于巴黎战后历史阶段状况的见证。他曾在作品《多拉·布吕代》中对于战后巴黎的城市状况有过正面的描写:“我再次体会到一种虚无感。我明白是为什么,小区大多数的楼房在战后根据市政府建设的决议都被有条不紊地拆毁了”。巴黎在战后忙于消除战争的痕迹,甚至给需要拆除的破败区域命名为“孤岛16号”。物理空间上的战争痕迹可以被战后的规划所消除,但对于精神世界来说并非如此。战争的创伤记忆与战后城市大肆拆除重建的现状使他顿感虚无,他对于这种行为评论道:“人们已经毁掉了一切,为了把这里变成像瑞士村庄一样,再也无法质疑它的中立”[4]124。这是莫迪亚诺对于巴黎战后历史阶段最尖锐的讽刺。法国维希政府在战争期间极为懦弱而偏居一隅,战后迫不及待消除城市中的战争痕迹,这并非重建而是虚伪的掩盖。这种掩盖带给城市中个体的只能是不可逆转的二次伤害,而巴黎正是这一欺骗行为的城市代表。对于莫氏来说,目睹战后巴黎现状而产生的虚无已然变成其自身感受到的压迫,这种行为对于其个体的伤害并不亚于战争本身。
作为现代都市代表的巴黎,她在自身膨胀发展的同时却并未给予生活其中的个体以充分的关照。巴黎城市空间中弥漫的绝望氛围将个体渺茫的生活希望扼杀,她的孤独气质不断给个体施以压迫并使其难以独善其身,而她在战后历史阶段所选择的虚伪行径则将战争对于城市与个体的伤害放大到极致。种种巴黎城市与社会层面的特质不断迫使个体产生逃离巴黎的强烈冲动。莫迪亚诺是城市个体的代表,他所产生思考的咖啡馆、小旅店等同样是巴黎城市特质的缩影,巴黎的“都市病”正产生并蔓延于城市的这般角落。然而逃离并不是属于莫迪亚诺的排解。莫氏父母及亡弟构成的家庭情结在巴黎,身世坎坷漂泊后的精神归属是巴黎,甚至出逃完成但感到难以生存后渴望留恋的收容地同样是巴黎。莫氏是属于巴黎的,无论巴黎予其压迫与否,他都不得不选择回归至巴黎。这是他内外交困的选择,同样亦是其非理想主义的真实写照。他向往脱离巴黎城市压抑氛围之外的生活,但同样他对于自身及所处环境又有着异常清晰的认识,而无法成为理想主义者的莫氏,也就不得不置身于巴黎的闭锁循环中,徘徊于巴黎的城市执念。
综上来看,莫迪亚诺与巴黎这座城市的关系,一方面是他深受巴黎所困,但另一方面巴黎又是他绕不过去的执念。他对于巴黎看似矛盾的选择既来源于原生家庭的影响,又是城市与社会挤压所必然导致的后果,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闭锁循环。巴黎制造了莫迪亚诺的孤独,这孤独也成就了莫迪亚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