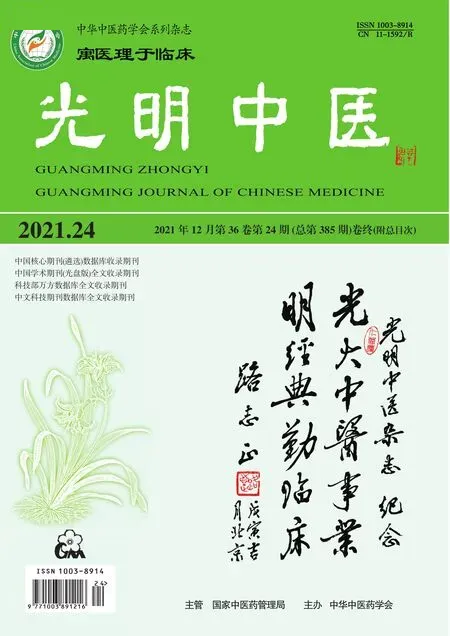仲景见病知源指导下失眠治验的回顾*
2021-12-01王冠雄胡鑫才张光荣
王冠雄 胡鑫才 张光荣
失眠是指即使有合适的睡眠机会与良好的睡眠环境,但对睡眠的时间和(或)睡眠的质量仍感觉不满意,且明显影响到日间生活的一种主观感受[1]。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慢性失眠症的患病率在6%~30%。我国普通成年人群中失眠的患病率在9.2%~11.2%[2,3]。因此探究对失眠的治疗显得极为重要。中医学自古对失眠已有论述,且因其治疗形式灵活、方法多样,效果稳定,不良作用小而被广大患者接受。在张仲景“见病知源”理念的指导下,践行“读经典,做临床”的学习方法,始终将经典指导临床贯彻于实践。通过运用所学治疗1例较复杂的失眠病例取得了较好疗效。现对验案的临证思路和方法及历代医家对失眠的认识进行回顾,以就正于同道。
1 中医学对失眠的认识
1.1 病名的沿革失眠,在中医内科学中称之为“不寐”。《难经》最早提出“不寐”这一病名,《难经·四十六难》载:“老人卧而不寐……血气衰,肌肉不滑,荣卫之道涩, 故昼日不能精, 夜不得寐也”。有学者考证[4],在现存医学文献中,有关此类病证的最早记载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始将本证称为不卧、不得卧和不能卧。纵观中医学的发展历程,不同的医家和著作对不寐的病名认识不完全相同,主要有:目不瞑、不得眠、不得卧、不能卧、不眠、卧起不安、起卧不安、卧不能安、不得卧寐、不得睡、眠寐不安、寝卧不安、睡卧不安、卧不安席等。并有医家已将“不寐”列为独立疾病,如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卷之四》列“不寐”。
1.2 对失眠病因病机的认识
1.2.1 古代医家的认识《灵枢·邪客》有:“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阳气盛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在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有关失眠的病因涉及到外感内伤两类,如内伤中提出“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外感中有《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憹。栀子豉汤主之”的论述。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胆虚实第二》中认为,温胆汤(半夏、竹茹、枳实各二两,橘皮三两,甘草一两,生姜四两)治大病后虚烦不得眠,属胆寒者。宋代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有云:“平人肝不受邪,故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归,是以卧则魂扬若离体也”。认为邪气内扰于肝,则血不能归藏于肝以养人之神魂,所以出现不寐的情况。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杂证谟·不寐》提出“不寐证虽病有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则尽之矣……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耳”。更有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提出了不寐有气虚、阴虚血少、痰滞、水停、胃不和等并给出了对应的治疗方药。清代《冯氏锦囊·卷十二》指出“壮年人肾阴强盛,则睡沉熟而长,老年人阴气衰弱,则睡轻微易知”。总之,古代医家认为不寐的病机总属阳盛阴衰,阴阳不交。并将不寐分为虚实两大类,实者多见肝火、痰热、瘀血等;虚者多见肝、心等血虚所致的虚烦不得眠,以及热病后期所致的胆寒不得眠[5]。
1.2.2 现代医家的认识周仲瑛[5]认为失眠多因饮食不节、情志失常、劳逸失调及病后体虚所致心肝脾肾的阴阳失调,气血失和。徐云生[6]总结邓铁涛治疗失眠的经验,认为失眠病位则以心肝胆脾胃为主,总的病机是阳盛阴衰、阴阳不交。肖相如认为产生失眠的根本原因是“日出不作,日入不息”“心不静而体不动”,顽固性失眠病机的根本在于阳不入阴,肾虚不藏[7]。《中医内科学》[8]将不寐的证治分为肝火扰心证、痰热扰心证、心脾两虚证、心肾不交证和心胆气虚证, 分别治以疏肝泻火、镇心安神, 清化痰热、和中安神,补益心脾、养心安神,滋阴降火、交通心肾,益气镇惊、安神定志。有医家从五脏论治失眠[9],治疗上可以根据五脏藏神的特点,对症用药,重点应调整脏腑气血阴阳、辅加以镇静安神可以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综上可知,现代医家认为不寐的产生是以各种内伤因素导致的阴阳不交为基本病机,五脏气血阴阳失和为特点。
2 见病知源初探
在《伤寒论》原序中有言:“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说明仲景著述的目的并不是把所有疾病的具体治疗写出来,而是想通过著述来告诉后世医者治病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以期达到“见病知源”的目的。如果能够“见病知源”,即使有些疾病暂时不能治疗,也知道寻找治疗方法的方向在哪里。仲景临证注重四诊合参,审证求因,故能够做到见病知源而后治之。其撰写的《伤寒论》更是深刻体现其临证理念,如《伤寒论》第16条所云:“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虽然仲景此段文字的本意是提出对误治、逆治的处理原则,但纵观《伤寒论》全篇,无不体现“脉-证”合参的辨证思维和方法,如书中叙述的“辨病脉证并治法”,主要是讲先通过辨脉和临床证据来认识疾病,而后言治法。其治疗疾病的过程是对“病位”“病因”“病机”“病势”等辨识并鉴别之后再言诊断和治疗。因此,原文虽源于误治逆治,但其指导意义不止于此。此条文突出了“疾病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生命自然规律,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书中提出的六经辨证不仅要求对“病之源”所属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有清晰的认识——这是“见病知源” 的重要环节,同时也要对疾病的来龙去脉有清晰的把握。这样才能在中医治病“因势利导”的大前提下,给邪气以出路,找到疾病痊愈的途径。“源”一旦出错,则万虑皆失。当前现代医学治疗失眠主要采取镇静催眠等方法,此举不仅毒副作用多而且停药后易反复[10]。而中医施治则采取调和阴阳、疏肝养心、解郁安神等法,显现出疗效稳定、毒副作用少等优势。然固守证型论治则属刻舟求剑而疗效不高,认识疾病的来龙去脉方可取得预期的效果。
3 失眠验案
患者,女,65岁,家庭主妇,于2018年8月15日以“失眠3个月余,消瘦2个月余”为主诉就诊。自诉1年前因一次感冒发热后开始出现胃肠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食欲减退,纳后腹部痞满,后经西医静脉点滴用药等治疗(具体不详)后症状略有减轻,但效果不佳。近半年来体质量下降5 kg余,其中近2个月来下降3 kg余。偶眼痒,面部、背部偶有发麻感。3周前不明原因胸痛,现已自行消除。2周前偶有心悸,自服西洋参数次后症状消失。咽喉部偶感有物梗阻,吞咽无异常;平素血压偏低[最近一次90/60 mm Hg(1 mm Hg≈0.133 kPa)],目前血压在正常水平;平时心事重而容易影响夜间睡眠。现病史:近3个月来因心烦而致睡眠差(大致过程:晚上22点左右睡——凌晨1~2点醒——早晨5点勉强入睡——5点半左右起床——上午10点前后疲乏欲睡——晚上22点左右睡);记忆力减退;吹风扇和冷空调则易引发咳嗽伴流眼泪,每咳久方有少量清稀痰,咳嗽可自行缓解。无畏寒;平素出汗少,出汗不均,主要在头胸背部,下肢无汗;无口干口苦,口淡、伴有较强饥饿感,洗漱口腔时欲呕;纳食不馨,但能勉强进食,进食量如常;喜热饮,嗜食咸味;阴雨天降温等气候变化时颈背部、膝关节酸痛;大便成形,色褐,前硬后软,每日1~2次,排便过程无不适;小便清,无夜尿。望诊:面色黄,消瘦面容,稍显憔悴;舌质淡红,舌尖缘有少数黑瘀点,苔白底,中部左侧微浮黄、右侧及舌根部黑苔,舌下络脉短细,不明显,色偏淡。脉象:脉细弦不流利;左寸不受按,关较浮,尺略沉;右寸关略浮,尺略沉。2018年8月14日某市三甲西医院电子胃镜报告示:食管炎(霉菌性?);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诊断:不寐;咳嗽;虚劳?西医诊断:失眠;体质量下降原因待查?(食管炎,霉菌性?慢性萎缩性胃炎?)。证候诊断:太阴(脾、肺)气虚;少阳风饮郁热,表里相兼;厥阴瘀热。方拟防己黄芪汤合小柴胡汤加减。处方:汉防己12 g,生黄芪20 g,甘草9 g,白术9 g,柴胡15 g,黄芩9 g,党参15 g,法半夏9 g,岷归尾6 g,生姜3片,大枣4枚。5剂,常规方法水煎服。
9月18日二诊:患者自述服药后再吹风未引发咳嗽,食欲增强,上午疲乏欲睡大减,但夜间睡眠无明显改善,且膝关节酸痛较明显,其余情况大致同前。脉象:脉细弦;尺沉;左关略不受按;右脉略缓。舌相:舌淡红略暗,舌尖有黑瘀点,苔淡黄,中后根部厚腻且有少许浮黑点。证候诊断:太阴(脾)气虚;少阳风饮郁热,里证兼表;厥阴瘀热。方拟防己黄芪汤合小柴胡汤加减。用药:汉防己12 g,生黄芪20 g,甘草9 g,白术9 g,柴胡9 g,黄芩9 g,党参15 g,法半夏9 g,生姜3片,大枣4枚,丹参9 g,杜仲9 g。5剂,常规方法水煎服。
2019年3月2日三诊:患者自述服药后夜间睡眠略改善,但有时明显胸口闷痛牵涉至后背正中,且食欲略减退。追问病史得知胸背痛发作之前曾食用鸡汤和大骨汤。无咳嗽,大小便情况无变化。舌相:舌淡红略暗,苔白,中后根略厚腻;黑苔消失。脉象:脉弦略细。2019年3月2日某市二甲中医院腹部彩超示:胆囊炎。证候诊断:少阳兼厥阴气郁;食湿内阻。方拟柴胡疏肝散加减。用药:柴胡10 g,白芍15 g,枳实6 g,青皮10 g,香附10 g,炒麦芽15 g,延胡索10 g,厚朴10 g,炒鸡内金6 g,炙甘草3 g。5剂,常规方法煎服。
半个月后电话随访,患者自述服完上5剂后症状改善明显,但偶感胸口闷痛牵涉至后背遂自行去药店购药5剂服用。再回访,患者无胸背痛,舌苔正常,体质量恢复,睡眠佳,精神状态良好。
4 治疗思路分析
该患者因睡眠障碍3个月就诊,但其起病却要追溯到1年前。3次就诊的时间间隔较长,可以看出患者就医意愿很低。尤其是第二、三诊之间,患者的睡眠问题并没有明显改善,是因为胸背痛难以耐受而不得不再次就诊。因此,在收集病情资料时要注意了解疾病的起始及发展过程。现对各诊次的思路做一分析。
首诊:患者因1年前外感发热出现了食欲减退、饮食无味、嗜睡、疲乏等表现,一般这种属于表证误治导致中焦脾胃气虚之象。从病史中患者咳嗽伴流泪、咳出清稀痰等症可知有饮邪;其咳久方有少量白色清稀样痰,说明饮邪不在肺胃,而在少阳焦膜。根据吹风后咳嗽出眼泪且结合脉象可诊断为表气虚夹风饮,同时患者眼痒、面背发麻之感均属风的表象。根据心烦不寐、洗漱时欲吐、有咽梗感等症,结合饮食不馨、精神倦怠,即如“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从患者突出的症状可知其少阳病是表里相兼证,即少阳里证内有饮邪郁热,少阳表证表有风饮。根据心烦失眠以及患者凌晨醒的时间(伤寒论第328条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舌尖瘀点以及脉弦不流利等可知厥阴有瘀热。据姚梅龄教授临证脉学[11],脉弦不流利也可提示饮邪,脉细提示气虚,仲景亦有言“伤寒三日,少阳脉小”,左关较浮提示有少阳表证,右寸关略浮说明太阴少阳有表邪,两尺略沉说明老年肾气不足,第二诊出现膝关节酸痛明显进一步印证。舌苔见浮黄、黑苔说明内有火热之邪。而心烦失眠这一主诉的病因不好确定,有以下3种可能:①由少阳病引起;②可能由厥阴瘀热引起;③由前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来看,此患者虽有三处偏态(气虚;少阳风饮郁热,表里相兼;厥阴瘀热),但这三者的轻重缓急不一样。虽然患者目前最突出的症状为睡眠紊乱,但根据病史可知,患者的食欲差、体质量明显下降等造成睡眠紊乱。因此追寻疾病的起病情况,认识其来龙去脉,而后按照“见病知源”理念和仲景辨治的一般先后顺序:先表后里、先气后血、先阳后阴,方可“因势利导”获得预期疗效。故应首先治疗太阴里虚和少阳病这2个证候,其次才是厥阴瘀热。故第一次治疗先拟用防己黄芪汤合小柴胡汤加减。防己黄芪汤功效益气固表,健脾利水,主治表虚卫气不固,风湿(水)伤于肌表,水湿郁于肌腠所致的风水。此处借用以治风饮,可祛患者已有之风饮,并益气健脾,助患者恢复脾气和卫气,构建体表防御力,抵御外来寒风之邪。其中汉防己祛风利水,黄芪益气固表,兼可利水,两者相合,祛风除湿而不伤正,益气固表而不恋邪,使风湿俱去,表虚得固;白术补气健脾祛湿,既助防己除湿行水之功,又增黄芪益气固表之力。小柴胡汤为和解少阳的代表方剂,既可祛表邪又可化痰饮、清里热,同时补益中气,可令其表里之邪均除,恢复正气。其中柴胡苦平,入肝胆经,透泄少阳之邪,并能疏泄气机之郁滞,使少阳在表之邪得以疏散;黄芩苦寒,清泄少阳里热,柴胡之升散得黄芩之降泄,两者配伍为和解少阳的基本结构;中焦痰饮上泛,胃失和降,以法半夏、生姜化饮降逆止呕;岷归尾性温活血止痛力强,并可兼顾厥阴之瘀阻。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从太阳传入少阳,缘于正气本虚,故又佐以党参益气健脾;再佐入姜、枣,调和营卫;甘草和中,兼可调和诸药。两方并用,诸药相伍,祛风化饮健脾与和解少阳并用,扶正与祛邪兼顾,使风饮俱去,枢机得利,食欲增强,疲乏欲睡大减。但首诊治疗只考虑解决疾病的源头,针对失眠不会有大的改善。
二诊:通过患者自述(受风不再咳嗽等)及舌脉诊可知其表证已解,太阴病和少阳表证好转,少阳里证未见明显好转,但肾气略虚,遂加入补肝肾的杜仲,并将升散的柴胡减量,使柴胡和黄芩按1∶1入药。同时考虑到第一诊后患者睡眠没有改善遂将性味偏温的当归尾换成既清血分热又活血,味苦、性微寒的丹参,这样可以避免药物对失眠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因脾胃之气的恢复尚需时日,故其余用药暂时不变。此时病源已得处理,适当调整表里药物的比例,另需兼顾血分瘀热。故用药后夜间睡眠略有改善。
三诊:此次就诊距离上诊的时间较长,患者素有脾胃气虚,后因饮食不节,出现了胸背痛、食欲略减的情况,结合彩超检查考虑为“胆囊炎”。考虑患者是在经过前两诊的治疗后,机体进入自我修复的过程,但少阳病尚有残余之时,此时患者食用油腻之品,突然加重胆囊的负担,故导致此病的发生。综合前两诊的治疗可以认为现在患者睡眠不佳主要是少阳厥阴气分郁滞所致。根据舌象和神的变化可知厥阴之郁热较为轻微。因此本次方拟用柴胡疏肝散加减以疏肝行气,活血止痛,消食化湿。又可兼顾少阳胆经。方中取柴胡,入肝胆经,条达肝气,透邪外出;白芍敛阴养血柔肝,与柴胡合用以补养肝血,条达肝气,可使柴胡升散而无耗伤阴血之弊,为调肝常用组合;厚朴燥湿消痰,下气除满;此外方中陈皮、延胡索、枳实、香附可增强疏肝行气、活血止痛之效。故服后肝胆条达,气血通畅而痛止,营卫自和而寐安,诸症亦除。
整个治疗过程,首先要根据四诊信息判断患者的证候,即对其病因、病位、病机和病势要有清晰的认识。然后遵循表证为先,病源为先的一般原则加以治疗方可做到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取得理想的疗效。以本病案为例,该患者虽以失眠为主诉来就诊,但其体内疾病关系略微复杂。根据仲景“见病知源”等理念,先治疗其源头之证和在表之证,即太阴和少阳两经的病证。姚梅龄教授曾强调表证与许多内科病证关系密切,而中焦脾胃是药物进入人体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中转站。因此只有当表证已去且脾胃功能得到一定的恢复后,再进一步深入去治疗少阳和厥阴的里证,方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否则,若在首诊就针对睡眠障碍治疗,表证不解除、脾胃运化功能不能恢复,饮邪停滞,药物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5 小结
本次治验是读经典、用经典的一次实践。当代中医科班出身的中青年大夫在治疗内科疾病时,很多不会想到用伤寒方和温病方,更少将解表法用于内科病初起及感受外邪引起急性发作者,以致临床疗效不理想。寻其原委,发现对于许多杂病是由外感病误治失治所造成的,许多杂病的初起阶段和急性发作阶段往往是外邪犯表触发的,等等诸如此类的理论与事实均不了解。此种现状,不仅与经典著作学习得不深不透有关,同时和人为地将外感时病与内科杂病一定程度的割裂亦有关。这是没有注意到仲景所说的“见病知源”,而更多的是去套证型的思维在误导。中医治病要经过辨证后方可“见病知源,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只有正确认识疾病,认识疾病最初的来源,分层次、按步骤治疗,使机体“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着眼于“以平为期”。例如此例患者虽以失眠为主诉来就诊,但不能简单地去治失眠这一内科病候。而应当根据四诊信息进行辨证,分析出疾病的起源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最后的临床疗效满意,患者机体恢复健康。通过这一次的临床实践,更深刻地理解了仲景《伤寒论》“见病知源”理念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