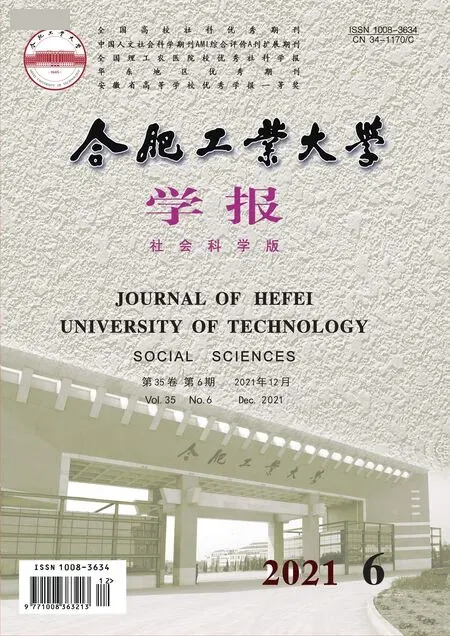存在主义视角下的《雨王汉德森》
2021-11-30高薇
高 薇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安徽 淮北 235000)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索尔·贝娄一直关注着现代物质社会中的个人状况:在十分优越的物质条件下,个人深陷于“现代生活的空虚”,无法摆脱精神上的压抑和孤独。他在作品中始终致力于在空虚之中“捍卫人的尊严”,通过鲜明的个体——反英雄式的、非正统的主人公——探索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意义及存在的价值。《雨王汉德森》(以下简称《雨》)正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作品。该书讲述美国大富翁汉德森在豪华的物质世界里苦闷于自我的迷失,毅然出走,在一位土著向导的带领下,孤身深入非洲最原始的神秘内陆,在阿内维及瓦利利部落遭遇凶险的磨难,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最终对自我存在的意义有所感悟,带着重建的信心返回美国。
汉德森喜剧般、近乎荒谬的探险经历,其实质是作家所作的一种极为严肃的对于生命、存在、死亡等问题的哲学思考。这种“思想的旅行”是从存在主义出发的,但他不愿意自己的行程终结于存在主义文学式的绝望。他是一位乐观的信仰者,相信“这多种多样的存在有着某种意义、某种趋向、某种实际价值;它使我们对于真旨、和谐、以至正义有了指望”[1]。索尔·贝娄在作品中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切合了存在主义哲学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如存在的价值、死亡的意义、理性的压迫等。为了这种意义,贝娄进入汉德森庞大痛苦的躯体内,与他一起努力寻找。基于贝娄的积极信仰,汉德森最终找到的生命的意义是爱的复萌,即在物质世界中丧失的人际情感的复生。
一、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哲学起源于20世纪初的德国,并在法国得到进一步发展。海德格尔在他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始终探讨着人的存在意义问题,他希望通过对人(“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的存在进行现象学的分析,也就是存在论的分析,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追问西方哲学最古老的问题——人的存在意义问题。首先,他认为人立于世,就是所属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者,人的存在是“生存”,人的“生存”是“向来我属”的,基于人的这种特殊性,他对人的存在展开分析。接着,海德格尔提出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两种可能性,即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海德格尔告诫人们要倾听良知的呼唤,把沉沦于常人世界中的自我转向本真的存在状态,回归本真的存在。在看似充满希望的归途中,汉德森,也可说是贝娄自身,始终不能摆脱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悲观感的缠绕,从而使全书有了一种复杂且矛盾的内涵。
二、《雨》:描写富人的流浪
因为本来就拥有大量的金钱和高尚舒适的生活,所以汉德森对金钱早就没有任何兴趣,他一直认为:“我有三百多万元,除掉缴税、抚养费和一切开销,我还有十一万元收入,那是绝对清楚的。像我这样的人要这么些钱有什么用?”[2]27而且从父亲那个时代起,汉德森的家人就有了花不完的金钱,他们会用百元的钞票当书签,随意地夹在书里又随意地忘掉。在这些充沛的物质堆里,汉德森没有感到幸福,相反的却是整天怒气冲冲,认为自己“总会有流泪发疯的那一天”[2]27。因为这些物质让他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和拼搏的机会,所以他感到自己内心有着无所适从的空虚感。走出这种富裕的生活,在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去进行一番艰苦的创业活动,展现自己的才华,这一切简直成了汉德森的一种奢望。
年过半百的汉德森下决心走进了非洲丛林里,一心一意想帮助蒙昧的部落人做些事情,以实现他的个人价值。汉德森身体强壮,又当过特种兵,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和知识。可是,好心的汉德森在作家调侃的笔调之下却几乎成了一个现代版的“堂吉诃德”。汉德森的莽撞举动使阿内维部落失去了唯一的水源,作者用夸张戏谑的笔调描写“优秀品质的荒谬探索者汉德森”的荒唐行径,显示出文明与蒙昧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沟壑,二者之间的扞格不入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是更严重的灾难。因此当汉德森离开时,在阿内维部落里,“甚至牛群都被牵回屋里,好让它们不再见到我。这就是我如何在既毁灭了他们的水源,又毁灭了自己的希望之后,丢尽了面子,灰溜溜地离去的情况。”[2]77
经历了碰壁之后,汉德森并没有后退,因为他仍然一心想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他坚信自己是有价值的。汉德森不在乎金钱,也不在乎他的举动是否合乎世俗,他在乎的就是解读自己内心的那个“我要,我要”的答案。于是他又来到瓦利利部落,在瓦利利人最重要的祈雨仪式中,汉德森独自搬起了雨神像里最重的一尊门玛女神。在这场胜利之后,瓦利利人推举他当了雨王,而且还推举他为部落首长的接班人,可以说汉德森终于实现了他的价值,找到了内心的平衡。
三、“猪”:人的异化
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基于新一代思想家们所认识、总结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生存状况: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等外在因素支配着他的命运,无法抗拒的异己力量压制了他的自由,扼杀了他的个性[3]。《雨》一开始,贝娄通过主人公汉德森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现代个人所面临的异化的恐慌。汉德森拥有三百万美元的遗产,生活在最优越的美国现代物质文明之中,却精神苦闷、行事疯癫。他的反常行为的中心是:在豪华漂亮的庄园里办“臭气熏天”的养猪场。这一荒唐行径并非毫无缘由,而是基于他“对生活的总的看法”:人正如猪这种“聪明”而肮脏的动物,生活只是为了被制约、被屠宰。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处境比“猪”还糟,因为猪可以生产出“火腿、动物胶、猪皮手套和肥料”这样的实物,有其实质性的内容,而他自己呢,只不过是一件“洗得干干净净”、被物质的金箔层层包裹、“装饰一新”的战利品,完全失去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含义。
然而贝娄展现的不是一个完全被制约的个人。极度不满的汉德森以他癫狂荒谬的举动实施了存在主义所提倡的对压迫自我的外在“理性”力量的“反抗”。他养猪,以一种挑衅的姿态珍视它们;他打架、酗酒,无视任何社交规范;他在地下室里拉琴、开枪;他拒绝谈爱,厌恶妻子满嘴大道理地说教;他诅咒世界,诅咒一切。而这一切“乖张行为”,用存在主义思想的先驱之一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在实质上“仅仅是为了贯彻他自己”:
设若他找不到方法,他就会蓄谋破坏与制造混乱,会发明一切样式的折磨痛苦,以便贯彻他自己!他会向全世界发动诅咒,而由于只有人会诅咒(这是……人与其他兽类的首要区分),他可能因他的诅咒而达到他的目标——这就是说,他让自己相信他是一个人而不是钢琴键[4]。
为了表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汉德森做着痛苦而徒劳的努力。
四、“章鱼”:死亡的威胁
对于做着徒劳反抗的汉德森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认识到死亡的“可能性”。一方面,他渴望拥有存在的某种意义,大声疾呼“我要;我要……”却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意识到,死亡将无视他的渴望,随时发生。这一意识是通过水族馆里的一条章鱼来表达的:“它的眼睛冷漠地在向我诉说着什么。……在这无边的冷漠中,我感到就要死了,……。我心想:‘我的末日到了,死神正向我招手哩。’”[2]21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宇宙对人的期望和需求是无动于衷的,死亡随时威胁着人。此时的汉德森恰恰是处于这样一种面对死亡的“真正焦虑的时刻”,“那种令人觉得孤独凄凉的无着落感,茫然若失,以及缺乏具体而实在的感觉”,不停地“困扰着他”[5]。汉德森努力逃避死亡的问题,与内心的渴求作着苦苦的斗争,继续着他外在的无用反抗,直到死亡通过伦诺克斯小姐再次传递威胁。面对伦诺克斯生前积聚的大堆终将归于虚无的破烂,他终于忍不住向自己发出呼喊:“汉德森,采取行动,作出努力吧。你也有一天会死于这种瘟病的。死亡会消灭你。除了一堆垃圾,什么也不会留下来。……而还能抓住的是——现在!为了一切?走吧!”[2]45正是出于这次事件的直接驱使,汉德森登上了去非洲的行程。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死,真正的存在才成为可能,认识到自己要死尽管可怕,但也是解放:它使我们摆脱那些日常的小小牵挂,从而能够实施关键的筹划,进入真正个人化的生活,这就是“向死的自由”或“决断”[6]。我们不能说汉德森这时获得了这样一种“自由”,因为他毕竟和托尔斯泰笔下直面死亡的伊凡·伊利奇不一样,死亡没有真正地降临到他身上,只是通过旁人向他传递了一种“共享的命运”的讯息,但他毕竟是采取了“行动”,作出一次萨特所提倡的“真正的选择”,决心去抓住生命的意义,获得存在的“自由”。从这点上来说,汉德森确实是贝娄所确定的乐观主义的个人。不管客观现实是多么地令人沮丧,他突出鲜明地站在那里,勇于选择与行动。
五、“蛙塘”:非“理性”的真实
存在主义思想家们对传统哲学的反抗都集中体现在“反理性”上。他们认为,现代世界的一切外在现实——科学、机构、理论等,建立了一系列“理性”的假象,掩盖了生活的真实,个人要认识自己的存在意义就必须抛开理性,直接、积极、充满激情地去体验存在[7]。而贝娄作为一个作家所孜孜以求的也正是穿透世界一切“表面现实”的虚假印象去获得生活的“真实印象”。他举例说,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利奇被虚幻蒙蔽,只有最后的痛苦才撕毁了种种伪装,看穿了“实利”,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汉德森的非洲之行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象征:远离充满着现代的喧哗与骚动的美国意味着摆脱无数的虚假幻象;深入最原始的非洲内陆意味着回归原始性——生命的源泉——去追求生存的真实。汉德森最先进入的阿内维部落是这种原始性的理想的代表:它几乎是超乎人类的历史与地理之外的。当女王威拉塔莉向汉德森指出他所挣扎渴求的是“活下去”,他几乎是欣喜若狂了,他感觉在这史前的静谧祥和中,生存的意义、超越死亡的秘密将会被揭示。然而希望以喜剧式的悲剧告终:他想帮助阿内维人扫除“蛙灾”,结果却炸毁了阿内维人赖以生存的水塘,从而也结束了阿内维人对他的友谊和他们可能会给予他的启示。从象征的角度来看,炸药——文明世界理性科学的代表——无情地阻碍了他获取生命的真实的努力,而这一真实,非“理性”的真实,它本来孕育在原始而神秘的蛙塘的意象之中。汉德森在阿内维的失败经历似乎表明,现代的个人想摆脱“理性”束缚的努力将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它如此顽固且不易觉察地存在于他的意识之中。
六、“人”与“狮”:“自为”与“自在”
汉德森离开阿内维后进入的瓦利利部落代表着“黑暗”的中心,在这里,死亡无处不在。迎接汉德森的就是一具死尸,这又一次强烈地唤起了他对死亡的不安和焦虑,而国王达孚时刻生活在死的威胁中(他随时都可能会被野蛮地处死),却又如此地自由自在,汉德森不由地想到自己总在那里“求变化”却总是感到“厄运当头,始终惶惶不安”,而达孚和阿内维女王却是两位少有的“求存在的人”,他们生活得“称心如意”;于是他在心中呼喊:“够啦!够啦!该是完成‘变化’的时候啦!是‘存在’的时候啦!”[2]176在这里,贝娄所选择的哲学思路是典型的萨特式的。萨特认为,存在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自在的存在”,即一个物体同其本身等同的存在;一是“自为的存在”,即人类的永远自我超越的存在。“自在”是“自为”的理想,却永远都达不到,因为人不可能变成物体,这就造成了“人类的根本的不安和焦虑”。汉德森所说的“求变化的人”正是“自为的存在”,永远要求变成“自在”却不能够;而“求存在的人”是一种理想,即“自我”实现了“自在”却又保留“自为”。因此,达孚和阿内维女王是贝娄给汉德森设置的两个理想。阿内维女王这一史前原始的理想已被证明是无法达到的,因而只有达孚来承担这一责任。
达孚对汉德森的引导是以狮子阿蒂为手段的。他要求汉德森与他一起进入狮笼,与阿蒂共处,甚至模仿阿蒂的行为。对达孚来说,阿蒂代表着野性的大自然,因而象征了真正的“自在的存在”,只要能够融合了阿蒂的“狮性”,就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找到美的真实,从而使“自为”变成“自在”。然而最终达孚的阿蒂只被证明是又一虚假的幻象:在捕狮台,当巨大凶猛的野狮挟带着真正的野性的气息“迎面扑来”的时候,汉德森才真正感觉到“死亡的召唤”,“它的吼叫如同在我脑后猛击一掌”[2]342。它带来的后果是残暴可怕的:达孚死于重伤,汉德森也因而感受到了死亡对他自身的猛烈冲击——无嗣的国王死后,将由身为雨王的他来担任国王,承担随时随地都可能会被处死的可怕命运。如果说汉德森一直以来都寻求着一种真正“唤醒心灵沉睡的时刻”,那么他现在应该是得到了。这并不是“自为”与“自在”的理想重合,阿蒂这一假象只是证明了二者无法到达统一状态,但是在野狮以恐怖的一击杀死达孚之后,汉德森确实认为自己找到了生命的真实:虽然死亡是恐怖且不可避免的,宽恕和爱却能够使人获得“活下去”,即“生存”的信心和希望。
在这种重建的信心的鼓舞下,汉德森宽恕了达孚对他的欺骗,宽恕了导致达孚的死,又威胁他的生的瓦利利人,怀着对达孚、对向导洛米拉尤、对死去的父母兄弟、对妻子和孩子的新生的爱,超越了死亡的威胁,重回美国,去建立有意义的生活。
七、“人”与“熊”:共享孤独
通过汉德森的经历,贝娄所显示的最终态度是乐观主义的:对人生来说,爱是一切真实的真实,是最最重要的,只是它不是靠理性、靠强加的说教可以获得的,只有穿透一切假象,依靠自己的直觉投入地去感受生命才能获得这一真谛。但是,在汉德森身上,这一点的深层却多少带着存在主义的悲壮意味。在作品的结尾部分,汉德森在返国途中回忆起了老熊史莫拉克:
可怜的散了架的老东西和我,就我们两个,每天要表演两次高坡滑车。……出于一种共同的绝望的心情,我们在表演过程中互相抱住了,脸贴着脸,这时我们似乎失去了所有的支撑,开始作垂直下降。……如果说史莫拉克和我同为被抛弃者,是观众面前的两个小丑,而在我们的心灵中却是兄弟——我被它熊化了,它也说不定被我人化了——这么说,我并不是带着赤子之心去跟猪打交道的。
……某种深刻的东西已经被刻在我的心头了。到头来我不知道达孚是否自己也能发现这一点[2]378-379。
这种“深刻的东西”,史莫拉克和少年汉德森共享的这种状况,正是存在主义所总结的现代人的状况:人是孤独的,宇宙对人的期望和需求是无动于衷的,死亡随时威胁着人。这种状况的结果是史莫拉克和汉德森的拥抱,汉德森所体验的“熊”性正是这样一种在共享的孤独与绝望前相互怜悯的情谊。它不同于“猪”性——个性的完全地被制约;也不同于“狮”性——人所无法到达的“自在”状态[8]。作品所暗含的意义似乎是:只有这种“熊”性才是人所应该而且能够到达的状态。汉德森的“爱”的悲凉正基于此种个人灵魂深处的孤独感。
八、结 语
贝娄曾经承认,在他的作品中最与他本人相像的角色就是“汉德森——荒唐的高贵品质寻求者”。在汉德森的“喜剧式”的探险之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作家本人极其矛盾的思想体验。他从存在主义式的角度出发,探索了死亡、理性、存在等重大问题,努力为处于摇摇欲坠的世界中的主人公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与光明的前途。然而带着重建的信仰回归美国的汉德森依然不能摆脱内心深处的悲观感受;我们也不得不怀疑,仅以内心的这种探索,个人到底能否超越环境的荒谬?如果外界局势没有一丝改变,他要建立新生活的行动有无可能实行?他会不会又重新激起厌烦的情绪呢?对于这一点,贝娄无从答复,所以他没有去描写汉德森回到美国后的新生活,而只是刻画了一个归途中的汉德森:一个“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在极地苍茫的白色大地上飞奔的鲜明的现代人。抑或我们可以说这正是作家本人探索精神的黑白剪影:他相信,荒谬的外部物质世界只是五彩的虚幻,个人以其确定无疑的价值和尊严是可以突出、鲜明地超乎其上的。所以,贝娄是一位信仰者,他追求以一种他所信仰的内在本质——“在宇宙之中,在物质和现实生活”中的“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因素”[9]——去对抗他无法否认、且为之苦闷的外在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