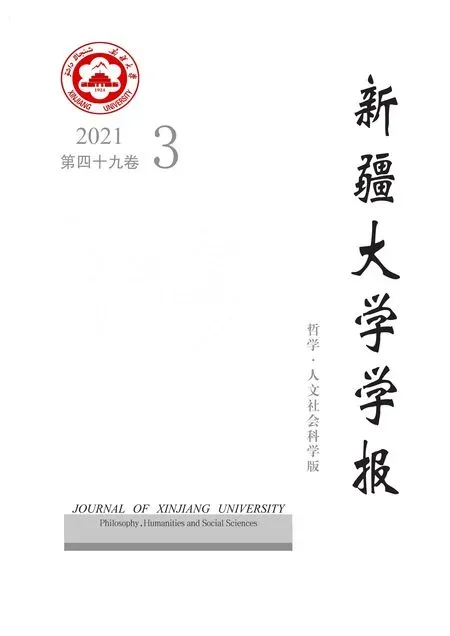金时习汉文传奇小说《龙宫赴宴录》新论*
2021-11-30韩东
韩 东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金时习(1435—1493),字悦卿,号梅月堂、清寒子、雪岑,朝鲜王朝初期著名诗人与小说家。相传金时习少而能文,被时人称为“神童”。五岁时,他曾被世宗召见于大内,因所赋“三角山诗”被大加赞赏而闻名国中。公元1455年,21岁的金时习在三角山读书之时,听闻端宗叔父首阳大君篡位,于是闭门三日不出,在一番痛哭之后,尽焚书籍并削发为僧,开始了长达10 年浪迹山林的生活。公元1465 年,31 岁的金时习在金鳌山上筑室,此后直到37岁一直居于此地,他著名的传奇小说《金鳌新话》便是写于这一时期。①参见(韩)郑炳昱《金时习年谱》,《国语国文》第7辑,1953年,第6-8页;(韩)朴熙秉《韩国传奇小说的美学》,首尔:,1997年,第173页。《金鳌新话》目前只有“甲集”传世,全集由《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醉游浮碧亭记》《南炎浮洲志》与《龙宫赴宴录》五个短篇构成。当然,无论是故事场景还是叙事手法,《金鳌新话》的创作都明显受到明代瞿佑《剪灯新话》的影响,这一点在以往的先行研究中早有论述,②参见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7-385页;王晓平《亚洲汉文学》(第2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5-255页。在此无需赘言。
在这五个短篇中,学界争议较大的无疑要算《龙宫赴宴录》,这主要是指学者们对“龙宫”空间象征的看法存在分歧。目前的解读有两种主流观点:一是受瞿佑在《剪灯新话》的《水宫庆会录》与《龙堂灵会录》中构造理想世界来寻求自我安慰的创作意图影响,认为金时习也是由于对现实生活不满,因而将自己的才华和价值寄托于虚幻的世界之中,通过构造一个理想的龙宫空间,来安慰或消解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挫折情绪。③参见汪燕岗《韩国汉文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8-50页;李岩、池水涌《朝鲜文学通史》(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01页;韦旭升《韩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9页;李娟《朝鲜古代汉文小说的文体生成及其文化叙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一是受金时习在世宗朝的自身经历影响,认为小说主人公韩生被龙王传召,并在龙宫中与诸神进行诗会的场景,影射的是金时习当年被世宗在王宫中召见并礼遇的往事,因此,《龙宫赴宴录》中的故事就是对金时习过往生活的再现,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④参见周有光《朝鲜李朝诗人和小说家金时习》,《国外文学》,1984年第3期,第32页;金宽雄、金晶银《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史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6页;(韩)李家源《韩国汉文学史》,首尔:普成文化社,1987年,第209页。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观点,也还有一些“少数派意见”。如有人认为《龙宫赴宴录》中的宴会情景嘈杂且无节制,龙宫根本不是一个理想的空间,韩生将宝物放入箱中是不愿向人提起龙宫的往事,小说呈现出金时习因试图参与现实政治而造成的内心挫败感与惭愧感。①参见(韩)严泰植《〈龙宫赴宴录〉的〈剪灯新话〉接受意义与禁忌的小说倾向》,《语文论集》第59辑,2014年,第147-175页。也有人认为《龙宫赴宴录》中的龙宫是金时习假想心理体验的形象化空间,对龙王与龙宫神圣性与权威性进行的描写,反映出金时习面对世祖篡位的态度已然发生了改变。②参见(韩)朴日容《〈水宫庆会录〉·〈龙堂灵会录〉与〈龙宫赴宴录〉的构成与创作理念》,《古小说研究》第46辑,2018年,第135-179页。还有人认为《龙宫赴宴录》中的龙宫是金时习设置的一个假想体验的空间,目的是为了传达自己对世祖篡位之后朝廷传召的认识与态度。③参见(韩)林治均《〈龙宫赴宴录〉的幻想体验研究》,《精神文化研究》第34卷第3号,2011年,第7-26页。除此之外,也还有人认为《龙宫赴宴录》的创作与圆觉寺落成会有关,龙宫就是金时习当年参加圆觉寺落成会经历的空间再现。④参见(韩)郑圭植《〈龙宫赴宴录〉的创作与圆觉寺落成会》,《古小说研究》第38辑,2014年,第158-179页。
事实上,如果仔细比较金时习《龙宫赴宴录》与瞿佑《水宫庆会录》《龙堂灵会录》的龙宫空间叙事,就可以发现瞿佑所描写的龙宫是一个虚构的理想世界,而金时习所描写的龙宫却影射的是现实世界。同时,如果说《水宫庆会录》《龙堂灵会录》中的理想世界是美好的,那么《龙宫赴宴录》中的现实世界却并不美好。而为何说并不美好,又影射的是怎样的现实世界,金时习如此创作的契机与动机又是什么,就是本文意欲阐明的三个问题。
一、“龙宫”的空间意味
《龙宫赴宴录》中龙宫空间的并不美好,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认识:
其一,从“瓢渊”的传说来看,龙宫是一个暗含杀戮与不义的空间。关于龙宫的所处之地,金时习在小说开篇便明确写到:“松都有天磨山,其山高插而峭秀,故曰天磨,山中有龙湫,名曰瓢渊。”[1]380也就是说,龙宫的处所在“瓢渊”。而高丽诗人李奎报曾作《题朴渊》一首,并对“朴渊”的来历阐说到:“昔有朴进士者,吹笛于渊上,龙女感之,杀其夫,引之为婿,故号朴渊。”[2]因此,有学者认为金时习在一开始介绍龙宫的出处时,很可能化用了这样一个民间传说。⑤参见严泰植《〈龙宫赴宴录〉的〈剪灯新话〉接受意义与禁忌的小说倾向》,《语文论集》第59辑,2014年,第155-156页。那么,“瓢渊”与“朴渊”是一回事吗?事实上,由于发音相同的关系,在朝鲜古代社会中,“朴渊”与“瓢渊”的名称存在混用现象。如李瀷(1681—1763)就曾指出:“瓢渊者,即今天磨山朴渊是也。俗传昔有朴进士者吹笛渊上,龙女感之引以为夫,故名之。……瓢之俗名与朴音同,故名也。”[3]而且有意思的是,金时习本人曾亲自游览过天磨山的“瓢渊”,期间还创作过一首《瓢渊》诗。对于这段往事,金时习在《宕游关西录后志》中记载到:“余自少跌宕,不喜名利,不顾生业。……素欲放浪山水……又登天摩、圣居诸山,以观众峰巑峭之状、瓢渊湫瀑之雄。”[4]如此,则金时习在《龙宫赴宴录》中描述龙宫的处所时,很显然结合了自己当年的“瓢渊”游览经历。而小说开篇以龙女杀夫招婿传说中的“瓢渊”作为“龙宫”所在地,就是在暗示“龙宫”并非一个美好的空间。
其二,从龙王邀请韩生的缘由来看,龙宫无法成为体现韩生价值的空间。关于男主人公的个人情况,金时习写到:“前朝有韩生者,少而能文,著于朝廷,以文士称之。”[1]380可就是这样一位名著于前朝的文士,却被瓢渊的龙王邀请来为新建的“佳会阁”题写上梁文。“佳会阁”是什么处所呢?龙王说:“寡人止有一女,已加冠笄,将欲适人,而弊居僻陋,无迎待之馆、花烛之房。今欲别构一阁,命名佳会。”[1]383则“佳会阁”是龙王为女儿及未来女婿准备的婚房。而《水宫庆会录》的主人公余善文也因有文才被广利王邀至龙宫,为龙王新建的“灵德殿”题写上梁文。“灵德殿”又是什么处所呢?广利王说:“敝居僻陋,蛟鳄之与邻,鱼蟹之与居,无以昭示神威,阐扬帝命。今欲别构一殿,命名灵德。”[5]9则“灵德殿”是龙宫中最能彰显“神威”与“帝命”的地方,也即龙宫核心权利机构的象征。相比之下,不难发现金时习虽然套用了《水宫庆会录》中的叙事框架,但他将题写上梁文的处所由原来的“灵德殿”转换到“佳会馆”,则韩生自身的价值便没能得到彰显,这样的情节设置暗示了龙王对韩生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并没有重用韩生的打算,这与《水宫庆会录》中余善文的境遇明显有别。
其三,从宴会场景的描绘来看,龙宫作为美好空间的定位存在局限性。《水宫庆会录》中的宴会描绘,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场景:一是文人作文;一是表演嘉宾助兴。余善文题写上梁文与献水庆宫诗二十韵,属于一个场景;“美女二十人,摇明珰,曳轻裾,于筵前舞凌波之队,歌凌波之词。……歌童四十辈,倚新妆,飘香袖,于庭下舞采莲之队,歌采莲之曲”[5]11,则属于另一个场景。相比之下,《龙堂灵会录》中的宴会场景较为单一,主要由伍君、范相国、张使君、陆处士与子述的吟诗构成。所以,相比之下,金时习《龙宫赴宴录》的宴会场景设置,大体借鉴了瞿佑《水宫庆会录》中“文人作文”与“表演嘉宾助兴”相结合的模式。比如除了韩生、神王与江河君长的相继咏诗,还有“蛾眉十余辈,摇翠袖,戴琼花,相进相退,舞而歌碧潭之曲,……总角十余辈,左执䈁,右执翮,相旋相顾,而歌回风之曲”[1]386-387。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金时习在描绘表演嘉宾助兴场景时,还添加了《水宫庆会录》中所没有的一些特殊人物,那便是“郭介士”与“玄先生”。
有一人自称郭介士,举足横行,进而告曰:“仆岩中隐士,沙穴幽人。八月风清,输芒东海之滨;九天云散,含光南井之旁。中黄外圆,被坚执锐,常肢解以入鼎,纵摩顶而利人,滋味风流,可解壮士之颜。”……即于席前,负甲执戈,喷沫瞪视,回瞳摇肢,……于是左旋右折,殿后奔前,满座皆辗转失笑。戏毕,又有一人自称玄先生,曳尾延颈,吐气凝眸,进而告曰:“仆蓍丛隐者,莲叶游人。洛水负文,已旌神禹之功;清江被网,曾著元君之策。纵刳肠以利人,恐脱壳之难堪。山节藻棁,壳为臧公之珍;石肠玄甲,胸吐壮士之气。……”或缩头藏肢,或引项摇头,……曲终,夷犹恍惚,跳梁低昂,莫辨其状,万座嗢噱。[1]389-392
对此二人的出现,有研究者认为是为了增强龙宫宴会的“戏谑性”效果,而且这两个角色能够看到韩生自己的影子。也即:金时习此处是在向读者暗示,在龙宫的其他人眼中,作为自我化身的韩生其实和郭介士、玄先生一样,也只不过是别人的“笑料”而已。①参见(韩)林治均《〈龙宫赴宴录〉的幻想体验研究》,《精神文化研究》第34卷第3号,2011年,第16-17页。
其实,从这二人的自述来看,所谓的“郭介士”不过是一只螃蟹,而“玄先生”亦不过是一只乌龟。有意思的是,螃蟹与乌龟本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他们却非常喜爱自我标榜,对自我的定位也远超常人。郭介士把自己包装成“隐士”与“幽人”,玄先生也把自己美化成“隐者”与“游人”。但从二人在龙宫中丑态百出、惺惺作态的情景来看,他们根本担不起一个“隐”字,反而更像是哗众取宠的小丑。由此可见,金时习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反衬对比的叙事手法,凸显出强烈的讽刺意味。因此,金时习对“郭介士”与“玄先生”这两个角色的添加,无疑是出于对龙宫宴会“品味”的调整意图。即如果说《水宫庆会录》与《龙堂灵会录》中的宴会还算优雅,那么《龙宫赴宴录》中的宴会则已经充斥着戏谑与丑态。郭介士与玄先生显然是沽名钓誉、献媚投机之徒的化身,可他们却也偏偏登上了高雅的龙宫厅堂。这里的韩生实际上是一个冷眼旁观者的角色,金时习就是这样通过韩生的第三者视角,传达出对龙宫品味的怀疑与否定。换句话说,这一情节的设置,并不是暗示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而是映射出龙宫鱼龙混杂,根本不是美好之地。
其四,从韩生游览龙宫的经历来看,龙宫不是能够自由出入的空间。无论是《水宫庆会录》,还是《龙堂灵会录》,主人公在龙宫宴会结束之后,就拿着龙王赏赐的礼物回到了人间。但在《龙宫赴宴录》中,金时习却另外添加了一段主人公游览龙宫的经历。韩生在宴会结束之时,主动向龙王提出观览龙宫的请求,龙王爽快答应并派二位使者陪同。由于当时整个龙宫都被云雾所笼罩,龙王便召唤“吹云者”施法,于是云开雾散、天宇清朗,韩生便首先得以观览“朝元楼”:
纯是玻璃所成,饰以珠玉,错以金碧,登之若凌虚焉。其层千级,生欲尽登,使者曰:“神王以神力自登,仆等亦不能尽览矣。盖上级与云霄并,非尘凡可及。”生登七层而下。[1]397
“朝元楼”虽然富丽堂皇,但韩生却没有办法尽观其美,因为七层之上是龙王的特权。其后,韩生来到“凌虚阁”,在使者的指引下他看到了能使“百物皆震”“山石尽崩”“大木斯拔”“洪水滂沱”“怀山襄陵”的“电母镜”“雷公鼓”“哨风櫜”[1]388等神器,但当韩生询问掌握这些神器的电母、雷公、风伯与雨师在何处时,使者答道:“天帝囚于幽处,使不得游,王出则斯集矣。”[1]399而且,在韩生因为好奇打算拔弄这些神器时,又受到使者的劝阻而未能成事。最后,韩生又来到一处所,这里“长廊连亘数里,户窗锁以金龙之錀”[1]399,而上锁不让观览的原因,在于这里是龙王珍藏“七宝”的地方。
有学者认为,此处的“电母镜”“雷公鼓”“哨风櫜”等物,影射的是世宗当年主持创制的“天文仪器”“测雨器”“自击漏”等科学仪器,是龙宫为世宗朝堂象征的直接证据。①参见李家源《韩国汉文学史》,首尔:普成文化社,1987年,第209页。不过,仔细分析金时习对韩生游览龙宫经历的描述,可以发现两个事实:一是龙宫中掌握特殊技能的神灵都受制于龙王,他们并没有自我行事与发挥神力的自由;一是韩生在朝元楼、凌虚阁的游览并不痛快,他也受到各种限制而未能尽兴,尤其是“七宝”之地则根本没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金时习添加游览龙宫的场景叙事,实则是要向读者明确龙王才是一切的主宰,所有人都得听命于龙王,而没有自由行事与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综上所述,可以基本确定金时习在《龙宫赴宴录》中构建的“龙宫”并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样一来,无论是从“自传”的角度将龙宫看作是当年世宗朝廷的真实再现,还是从“消解与安慰”的角度将龙宫看成是一个虚构的理想世界,这二者都不符合逻辑与事实。
二、“龙宫”与世祖朝廷
《龙宫赴宴录》中的龙宫,究竟影射的是怎样的现实世界?金时习在其中描述宴会座次时这样写到:“神王南向踞七宝华床,生西向而坐。……王劝三人东向。”[1]382这种座次排列方式,明显突出了龙王与三河神、韩生之间的等级差别。分列东西方向的韩生与三河神,无疑象征的是朝堂上的东西两班,②一般来说,朝鲜王朝社会可分为两班、中人、良人与贱人四个阶层,而所谓的“两班”大体是指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文武”功名的士大夫阶层。所以,“两班”又可分为“文班”与“武班”,上朝时“文班”站东边,“武班”站西边。参见(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新修版),首尔:一潮阁,1992年,第234-268页。南向而坐的龙王无疑是整个宴会的绝对主角与权威。所以,这里的龙王和现实世界中的君主身份非常契合。金时习通过韩生与三河神之口,反复强调龙王的“神威”“威重”的原因,大抵也就在于此。这样《龙宫赴宴录》中的龙宫就更可能影射的是当时的世祖朝廷,而龙王就是世祖的化身。理由有三:
其一,世祖的篡位登极充满了腥风血雨,这与瓢渊中龙宫的杀戮与不义形象契合。在世祖走上权利顶峰的过程中,朝鲜社会经历了两次极其惨烈的杀戮事件。一次是“癸酉政变”中对辅命大臣的谋杀;一次是“端宗复位”事件中对集贤殿等文士的捕杀。
1452 年,朝鲜文宗李珦(世宗李祹嫡长子)病逝,年仅12岁的王世子李弘暐继位,是为端宗。根据文宗遗命,皇甫仁、金宗瑞与南智等人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端宗处理国政。一年后,首阳大君李瑈(世宗李祹次子,文宗同母弟)以皇甫仁、金宗瑞等人密谋推举安平大君为王的借口,发动了“癸酉靖难”。首阳大君先是带领武士在金宗瑞家中击杀了金宗瑞本人及其儿子,其后又假传王命,让领议政府事皇甫仁、吏曹判书闵申、兵曹判书赵克宽、议政府右赞成李穰等人入宫,并将他们先后诛杀,还派士兵杀害了尹处恭、赵藩、李命敏与元矩等大臣,安平大君李瑢(首阳大君李瑈同母弟)最终也在流放途中被赐死。“癸酉靖难”之后,首阳大君任命自己为“领议政事判吏兵曹兼内外兵马都统使”,端宗从此成为傀儡国王。1455 年,首阳大君又逼迫端宗将王位禅让于自己,是为世祖,而端宗则被封为“上王”。
一年之后的1456 年,金礩在思政殿告发成三问等集贤殿学士图谋端宗复位,于是世祖广开捕杀之路,对谋反者进行残酷的处罚。在前后不到一月的审问与处罚中,共有朴彭年、柳诚源等4人被执行“尸体车裂刑”;成三问、河纬地等37人被执行“生体车裂刑”;绞刑与充为奴婢者更多达百人。除此之外,锦城大君李瑜(首阳大君李瑈同母弟)在流放途中被赐死,端宗也因知情不报从“上王”降封为“鲁山君”,并流配至江原道宁越清冷浦,直到1457 年端宗在宁越被赐死,整个“复位事件”才算告一段落。③参见(韩)柳永博《端宗复位谋议者司法处理》,《震坛学报》第78辑,1994年,第125-145页;(韩)《朝鲜世祖代端宗复位运动的再照明》,《人文学研究》第33辑,2002年,第99-111页;(韩)《世祖的继位过程与政治文化的变动》,《人文科学研究》第31辑,2013年,第289-328页。世祖在这两次事件中的表现,可谓残忍与暴虐。在朝鲜王朝历史上,如此残酷的处罚再也没有出现过。正如19世纪后期朝鲜士人崔益鉉所言:“国家化理之盛,莫尚于英显二陵。……世教民彝之变,莫惨于乙丙两年。”[6]这样的惨剧给当时的金时习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冲击,如在《金鳌新话》的另一个短篇《南炎浮洲志》中,金时习就曾借炎浮洲王之口批判到:“有国者,不可以暴劫民,……有德者,不可以力进位。”[1]377由此可见,金时习采取了一种较为隐晦的表达手法,通过借用龙女杀夫这样一个传说,来暗示世祖朝廷的杀戮与不义。
其二,世祖篡位后频繁举行功臣酒宴活动,这与龙宫中的宴会场景设置相暗合。由于受“名分”与“正统”问题的困扰,首阳大君在掌握政权后意识到,朝政根本无法托付于以儒学立身的儒士,而只能依托那些曾跟随自己政变的大臣。所以,“癸酉靖难”之后,首阳大君册封靖难功臣43名;“端宗复位事件”之后,登上王位的世祖又册封佐翼功臣46 名。这些功臣把持着朝廷的重要部门与职位,成为世祖处理朝政与巩固王权的重要支持势力。为了笼络与安抚这些手握大权的功臣,以及化解自己精神上的矛盾与不安,世祖经常广开名目在宫内外大肆举行公私酒宴活动。正如功臣梁诚之所言:“殿下优礼大臣,每设酌相欢,极为盛事。”[7]卷3,2-3世祖正是通过这些酒宴活动,深化与功臣、宗亲之间的感情与同盟意识。因此,有学者就曾指出,世祖已经把“酒席政治”作为自己巩固王权的一个重要环节。①参见(韩)崔承熙《世祖代王位脆弱性与王权强化策》,《朝鲜時代史学报》第1辑,1997年,第50-54页;(韩)崔承熙《朝鲜初期政治史研究》,首尔:知识产业社,2002年,第365-366页。
这种“酒席政治”有两大特点:一是世祖与大臣们的“过饮”;一是宴会中世祖与大臣们的嬉戏互动。世祖曾于思政殿设酒宴招待申叔舟等功臣,期间世祖与申叔舟就“过饮”问题有过这样的对话:
功臣等过饮而死者颇多,如李季甸、尹岩是也。且花川君权恭、桂阳君璔、领中枢院事洪达孙等虽不死,亦已羸惫,是大不可。予欲一禁,使不得饮酒,何如?叔舟对曰:“一禁为难,令勿过饮为便。”[7]卷28,5
由于功臣中有多人因酒宴中的过饮导致死亡或患病,有鉴于此,世祖曾有过禁酒的念头,但正如申叔舟所言,禁酒不太现实,只能下令不得过饮。同时,酒宴中君臣之间的互动活动也非常多。其中,世祖让大臣起舞或世祖与臣下之间进行和诗的场景就颇具戏剧性。
上酒酣,命领议政郑麟趾起舞,大司宪金淳对舞。……上出所制慕世宗诗,以示麟趾,麟趾即和,进曰:“更令文臣和进。”上曰:“然,予以诗示诸臣,似乎夸张,无乃若陈后主、隋炀帝乎?”麟趾对曰:“陈后主、隋炀帝,吟风咏月而已,今主上制诗,思慕先王,何自比陈、隋?”[7]卷7,24
郑麟趾与金淳虽然都是支持与帮助世祖登上王位的功臣,但为了活跃酒宴的气氛,世祖让二人对舞以供大家取乐。而不管是大臣的起舞,还是君臣之间的和诗,在世祖与功臣的酒宴活动中,总是透露出强烈的嬉戏与玩乐的氛围感。金时习本人对这些扶助首阳大君篡位的功臣们本就没有什么好感,《岭南野言》就记录着金时习一段趣事:“过西江,见韩公明浍别业板上诗有:‘青春扶社稷,白首卧江湖’先生遂改扶字以危,卧字以污而去。”[8]3-4很显然,在金时习看来韩明浍这样的功臣,不过是危害社稷的罪人。不难想象,金时习对世祖与这些功臣的酒宴活动,秉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龙宫赴宴录》中的郭介士与玄先生在表演完毕后,龙王与宾客们都前俯后仰、乐不自胜,接着便是“木石魍魉、山林精恠起而各呈所能,或啸或歌,或舞或吹,或抃或踊”[1]393。而这种宴会情景,正可作为功臣宴会的一种写照。
其三,世祖篡位后采取了强化王权的举措,韩生在龙宫中体验到的诸神与自身自由受限的场景正好影射这一问题。世祖篡位之后,为加强王权而施行了两大政策:一是推行“六曹直启制”,规定大小政事皆由六曹的最高长官直接向他报告;一是“废除集贤殿与中止经筵”,限制士人议政与朝堂谏言。对于前者,靖难功臣李季甸、河纬地曾强烈反对推行,世祖为之震怒,命人摘下二人的冠服,并大声训斥到:“听于冢宰,君薨之制也。汝以我为薨耶?且以予为幼冲,不能裁决庶务,遂使权移于下乎?”[7]卷2,5对于后者,就连世祖本人都认识到了由此而造成的官员“失声”现象。他说:“予即位以后,言官有不得尽言之势。……一则以予有严威,言之恐得罪。以此进退商量,议论合否,不能展职,予知其弊久矣。”[7]卷8,18所以,相比世宗朝廷而言,世祖朝廷的王权虽然得到了强化,但是朝廷政治风气也因此走向僵化,大臣的政治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此一来,龙宫这样一个并不美好的空间,就更吻合于现实中的世祖朝廷。
在小说的末尾部分,金时习也因此表达出对龙宫的隔绝意识。《水宫庆会录》中的余善文离开龙宫时,龙王赠送“照夜之珠十,通天之犀二”[5]12;《龙堂灵会录》中的闻子述离开龙宫时,龙王“以红珀盘捧照乘之珠,碧瑶箱盛开水之角,馈赠于子述”[5]87。这种赠送礼物的情节,在《龙宫赴宴录》中也有运用,即韩生离开龙宫时,龙王“以珊瑚盘盛明珠二颗、冰绡二匹为赆行之资”[1]400。但与《水宫庆会录》中余善文接受礼物后,“携所得于波斯宝肆焉,获财亿万计,遂为富族”[5]12的描写不同,《龙宫赴宴录》中的韩生在接受礼物后,则是“藏之巾箱,以为至宝,不肯示人”[1]400。这里金时习为什么要更改瞿佑原有的叙事结构?有学者认为,是因为韩生得到礼物的贵重程度明显不如余善文与子述,本就不是拿得出手的宝物。所以,对于韩生而言,龙王对其的重视,自然无法与余善文、子述相比,韩生因而不愿将这一不光彩经历示人。①参见(韩)严泰植《〈龙宫赴宴录〉的〈剪灯新话〉接受意义与禁忌的小说倾向》,《语文论集》第59辑,2014年,第165-166页。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忽略了龙宫对于韩生而言,是否是值得肯定与怀念的空间这一根本问题。
结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韩生在得知自己被龙王邀请的真正缘由,与看到龙宫莺歌燕舞与小丑作态的丑相,以及自己在龙宫中种种受限的经历之后,所感受到的“龙宫”并不美好、且没有自由的意识,才是《龙宫赴宴录》的表达主旨。所以,《水宫庆会录》中的余善文利用龙王的赏赐发家致富,改变了自身的生活境遇,这符合瞿佑通过理想世界来寻求自我安慰的创作主题。而《龙宫赴宴录》中的韩生却将龙王的赏赐紧锁于箱中,自己的生活状况也未发生改变,其原因就在于他与瞿佑的理想不同,他希望与现实政治隔绝,因而“龙宫”就被设定为一个无法实现心理补偿与安慰的空间。
三、《龙宫赴宴录》的创作契机与动机
金安老在《龙泉谈寂记》中曾记录金时习的这样一则趣事:“光庙尝作法会于内殿,岑亦被拣预,忽凌晨逃出,不知所之。遣使踵之,则故陷街里溷秽中,露半面而已。”[9]按照金安老的说法,金时习为了不参加世祖在内佛堂举行的法会,竟然决定凌晨遁走,但可惜运气不佳,不慎落入街道污水之中。这则故事充满戏谑性,其传达出的核心主旨是金时习非常抵触世祖举办的佛事活动。
然而,真实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金时习其实曾因佛事活动而与世祖有过两次交集,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早有论述。②参见(韩)郑炳昱《金时习研究》,《首尔大学校论文集》第7辑,1958年,第172页;(韩):《金时习谚解事业参加与节义的问题》,《语文学报》,2004年第26辑,第16-19页;(韩)沈庆昊《金时习评传》,首尔:,2004年,第224-256页。而能够产生交集,主要还是因为有孝宁大君的从中周旋。孝宁大君李補是太宗李芳远的第二子,也是世祖的伯父,其为人与世无争,酷爱佛法。“孝宁大君補奉佛甚笃,自少至老尤甚,以桧岩寺为愿刹,常往来斋施。”[7]12金时习因与佛徒交好,且“喜作禅语,发阐玄微,颖脱无滞碍。虽老释名髡深于其学者,莫敢抗其锋”[8]1-2。所以,他得到了同样信佛的孝宁大君的关注与青睐。
据《梅月堂稿》的记载,世祖九年,时年二十九岁的金时习因购买书籍而前往都城汉阳,此时世祖正召集人员翻译佛经,由于孝宁大君的举荐,金时习被召至王宫的内佛堂,进行了为期十五天的佛经翻译活动。③参见(韩)郑炳昱《金时习年谱》,《国语国文》第7辑,1953年,第8页。世祖十一年,时年三十一岁的金时习,又被孝宁大君邀请前往汉阳参加新建成的圆觉寺落成会,对于这段往事,金时习曾如下记述到:
余于已酉春,卜筑金鳌山室,若将终身。三月晦,孝宁大君以从马召余曰:“圣上重新古弘福寺,命名圆觉,落成会仆荐于圣上,上命召赴庆会,弛饮蜂啄涧之心,勿逆来赴。”余于是幡然改曰:“胜会不常,驰贺便回,以终余年。”即克日上京,以参嘉会。[10]15
对于金时习这两次应召的经历,有学者认为是金时习为了获得世祖颁发的“度牒”而采取的权宜之策;④参见(韩)沈庆昊《金时习评传》,首尔:,2004年,第226页。也有学者认为这是金时习出于信仰佛法的本能与无法拒绝孝宁大君的考量而做出的行动⑤参见(韩)《梅月堂金时习研究》,首尔:民族文化社,1961年,第99页。。事实上,到了30 岁之后,金时习对待世祖的看法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梅月堂续集》中收录有金时习创作的《望卿云百官致贺》,此诗创作于圆觉寺落成会之际,通篇内容明显洋溢着歌颂世祖的意味。
圣主中兴五百年,熙熙功业政超然。鼎新日月唐虞盛,挽古乾坤礼乐鲜。庶政已修崇竺法,千官初贺捧尧天。觉皇有鉴如回瞬,应寿吾王万有年。[11]
当然,从诗歌内容来看,金时习赞扬的出发点无疑还是世祖的虔诚“礼佛”态度。又据《梅月堂稿》的记载,早在内佛堂翻译佛经时,金时习就曾高度赞赏过世祖礼佛的虔诚。“余在禁堂,闻传导之声,俄有击门板者,僧迎之,则膳夫。……又一日乃送薏苡粒一掬,又一日乃送杜梨七八颗,皆新味也。余问中使曰:‘主上分送几处?’中使曰:‘每宗室戚里,以新而献之,必先献文昭殿,次送此堂,而后进膳。’余思之曰:‘物虽微,诚则大’。”[12]由于有了佛教信仰这层联系,金时习对世祖态度就变得微妙起来。如金时习在接到孝宁大君邀请其参加圆觉寺落成会的消息后,曾作《圆觉寺落成会》一首,他写到:“谁信逸民参盛会,五云朵里喜周旋。”[10]15可见此时金时习的态度已和早年因世祖篡位而浪迹山林的态度明显不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世祖王权的巩固,金时习早年因世祖篡位而浪迹山林时的那种愤世嫉俗心态已经慢慢得到缓解。①参见(韩)《金时习谚解事业参加与节义的问题》,《语文学报》第26辑,2004年,第19页。
但是,这里必须要明确的是,金时习对世祖的态度变化也仅仅限于佛教信仰层面,并不涉及对世祖个人及其政权的肯定与赞扬,更没有试图走入世祖朝廷的打算。因为他在参加完内佛堂的佛经翻译活动后,世祖与孝宁大君就曾挽留其在汉阳居住,这让一心返回金鳌山的金时习十分为难,为此他专门呈诗表明自己希望返回金鳌山的态度:“蒙恩初下九重天,荆棘难堪捧瑞烟。涣汗圣言虽至渥,膏肓臣疾实难痊。”[10]15而且在金时习参加完圆觉寺落成会之后,世祖又曾挽留其在圆觉寺居住,但他又予以了回绝。
上将还宫,引见赐言,命居此寺。余其时无心际遇圣明,惟以泉石遨嬉为志,居京不数日而遂行。[10]15
世祖篡位登极之后,其王权合法性与正当性一直受到质疑,而当他无法利用儒学来巩固王权时,弘扬佛法与创建佛寺也就成为他稳定国内政局的重要手段。在圆觉寺创立之初,世祖就曾与身边亲近大臣商议具体细节,建造途中他也多次亲临视察,建成后他又亲自主持并参加落成会,这都足以说明世祖已然将圆觉寺重建当作王权巩固过程的一环。②参见(韩)《世祖的佛事行为与意味》,《白山学报》第78辑,2007年,第165-191页。所以,这里世祖邀请金时习在圆觉寺居住,很显然是想将金时习纳入自己的“政治圈”,但金时习对此的态度却很是决绝。后来金时习在返回金鳌山的途中,又再次接到了世祖的传召,但他再次予以了回绝:
但以臣夙遭罪衅,慈母早背,幼失鞠育之恩,守坟奠祭,苫块依制,遘此宿疾,每于寒热辄复增剧。初欲游山玩水,报圣上水土之恩,年才立岁,膏盲迫身,不得遂愿,是可怜也。且南方地暖,仅可安躯,已结茅茨,已养沉疴者有年。及蒙圣擢,载惧载感,受命如京。然随例受恩,既僭越吾分,而疾病之躯,安得勉强动止也?故不敢承命,扶舆起卧,行至半途,伏乞许严光长往之抗节,蒙怀琏遂闲之明诏,曲怜垂慈,弃置山野。噫!草芥尘土,岂能補太山之一;阿潢污行,潦不可加巨海之一沤。仅摅微怀,仰尘圣鉴。[10]16
由此可见,面对世祖抛来的“橄榄枝”,金时习除了和第一次回绝一样声称自己“体弱多病”之外,还强调了自己能力欠缺无法为朝廷贡献力量。这种态度在金时习途中呈给世祖的陈情诗中也能感受到:“微臣岂堪挂冠去,病轿只随连舸书。倘获霈恩令遂志,插香长祝五云居。”[10]16金时习说自己既算不得什么人才,又重病缠身,若世祖能放自己归还金鳌山,那么自己必将诚心为其祈祷。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的金时习并不愿意走进世祖的朝廷政治,而是钟情于金鳌山的归隐生活。通过上面的考察可知,金时习这种抉择的背后,与他对世祖朝廷政治的负面认知与评价有关。
当然,世祖对金时习的认知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时习的归隐态度。金时习晚年在写给襄阳府使柳自汉的信中曾说到:“光庙之初,故旧乔木,尽为鬼簿,……仆之志已荒凉矣。遂伴髡者游山水,故人以我为喜释。然不欲以异道显世,故光庙传旨屡召,而皆不就。”[10]12此处的光庙,即指世祖。由此可见,世祖发动的篡位登极事件,直接造成了金时习早年意志消沉与佛徒交好而浪迹山林的局面,而他不接受世祖传召的原因在于不愿意以“异道显世”。这里所谓的“异道”,就是指他为外人所熟知的佛教徒身份,而他之所以不愿以这样的身份显世,其根源就在于他怀揣的是儒者的心志。③金时习的思想世界存在内外两面性,外在的是佛学,内在的是儒学,也即是常说的“心儒迹佛”。参见(韩)郑炳昱《金时习研究》,《首尔大学校论文集》第7辑,1958年,第183-187页。换句话说,金时习对世祖看待自己的态度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不愿走入世祖的朝廷之中,也就还与他切身感受到世祖对自己认可的局限性有关。在世祖的眼中,他是一位名僧,但在自己的心中,他却把自己定位为儒者,所以,他并不愿意以佛教徒的身份走入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
回过头再看金时习创作《龙宫赴宴录》的契机,就可以发现正是与他当年被世祖传召的经历与体验有关。而《龙宫赴宴录》作为金时习审视世祖朝廷的产物,其创作动机自然是为了表达自己决心远离世祖政治的态度。如果说瞿佑试图通过龙宫经历来实现自我的推许与炫耀①参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第2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2页。,那么金时习则是试图通过龙宫经历来表明自己的心志。所以,金时习笔下的龙宫空间便不可能是一个理想中的美好世界,而是一个充满诸多问题的现实世界,而他自己则希望能够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